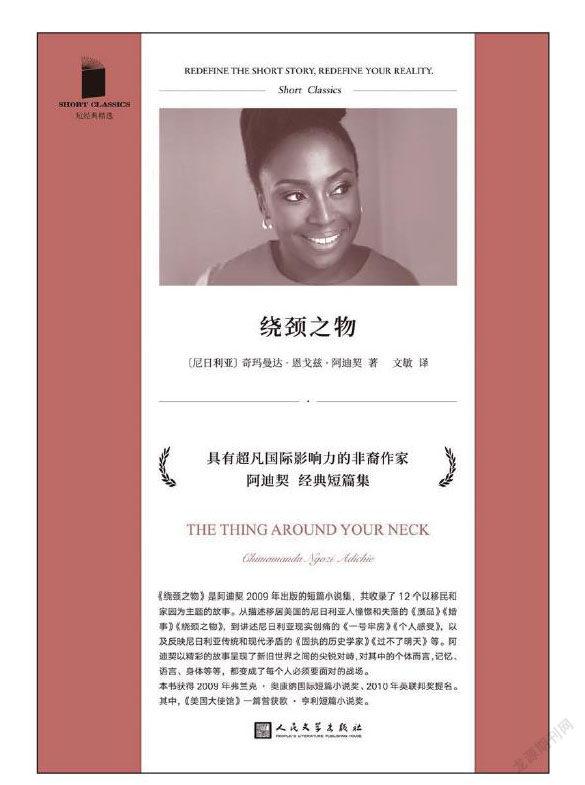
我们家第一次遭窃,偷儿是我们的邻居奥西塔,他从餐厅窗口爬进来,偷走了我们的电视机、录像机和我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几盘录像带:《紫雨》和《颤栗》1。第二次遭窃,是我兄弟恩纳玛比亚干的,他制造了有人擅闯入室的假相,偷走了母亲的首饰。事情发生在星期天。我父母去我们的老家姆贝斯看望祖父母了,恩纳玛比亚和我去了教堂。他开着母亲那辆绿色的标致504。在教堂里,我们像往常那样坐在一起,但我们不像往常那样互相碰碰胳膊肘,悄声讥嘲某人丑陋的帽子或是磨损得开了线的束带长袍,因为当时恩纳玛比亚只坐了十分钟,没说一句话就溜出去了。在牧师开口说“弥撒结束,愿众位平安”之前,他又回到了座位上。我有点儿懊恼。我估计他是跑出去抽烟,或是去看某个女孩了,因为他手里有车,但他至少得跟我说一声他去哪儿了。回家的路上,我俩都默不作声,恩纳玛比亚把车泊在我家长长的车道上,他打开房门时,我停下来摘了一些红龙船花。一进屋,我看到他站在客厅中间。
“我们家遭窃了!”他用英语说。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房间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撒了一地。甚至在那时候,我就已经觉出这情形有些夸张,抽屉都被拽出来了,好像干这事儿的家伙故意要给现场目击者留下某种印象。不过,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太了解我这个兄弟了。后来,父母回家了,邻居们一窝蜂地拥了进来,嚷嚷着“倒霉”,又将手指掰得噼啪作响,上下耸着肩膀,我独自坐在楼上的房间里,忍着胃里的阵阵恶心,因为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恩纳玛比亚干的,我知道。我父亲也明白。他指着脱落的百叶窗板,说那是从里面掰开的,而不是从外面搞的(恩纳玛比亚还真有这么聪明,没准弥撒结束之前他就能赶回教堂了),而且,那窃贼竟然准确地知道母亲的首饰搁在什么地方——她的一个金属衣箱的角上。恩纳玛比亚瞪着一双受伤的眼睛,表情夸张地看着父亲说:“我知道我过去的行为让你俩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我从来不会做这种有损你们信任的事情。”他说的是英语,使用的是那种夸张的词汇,诸如“很大的痛苦”和“有损”什么的,他作自我辩护时常常这样。然后他就从后门跑出去了,那天晚上没有回家。或是第二天晚上出走的。或是第三天吧。他两个星期后才回来,满脸憔悴,浑身散发着啤酒气味,哭着嚷着,说他很后悔,是他偷了首饰卖给了埃努古的豪萨首饰商,隨后花光了所有的钱。
“你把我的金首饰卖给他们得了多少钱?”母亲问他。当他说出数字时,她两手捂着脑袋大叫起来:“噢!噢!上帝杀了我吧!”好像是说,她觉得本该卖个更好的价钱。我真想过去扇她一巴掌。我父亲让恩纳玛比亚写一份报告:写他偷首饰的经过,卖首饰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以及在此期间他跟什么人混在一起。我估计恩纳玛比亚不会说实话,而且我觉得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可他喜欢报告,我这个当教授的父亲。恩纳玛比亚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像模像样的报告。况且,恩纳玛比亚十七岁了,已经留起了精心呵护的小胡子。他正处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阶段,这个年纪挨老爸手杖已经不像话了。那么,我这父亲还做了什么呢?恩纳玛比亚写完报告后,父亲把它塞进他书房那个钢制文件柜抽屉里存档,那里面保存着我们在学校里的成绩报告单之类的东西。
“他就这样伤他妈妈的心。”父亲最后只是这么嘀咕了一句。
当然,恩纳玛比亚并非存心要伤害她。他这么做,是因为母亲的首饰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辈子积攒下来的金器。他这么做,还因为其他教授们的儿子也都这么做。我们这个宁静的恩苏卡校区里偷盗成风。男孩们从小穿着锃亮的棕色皮凉鞋去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学校上学,看着电视里的《芝麻街》、读着伊妮德·布莱顿2的书、吃着玉米片早餐长大,现在这帮人开始撬开邻居家窗上的遮蚊罩,推开玻璃天窗爬进人家屋里去偷电视机和录像机了。我们都认识这伙偷儿。恩苏卡校区是个小地方——三条街上房子挨着房子,彼此只隔着一道矮栅栏——所以我们不可能不知道是谁偷的。尽管如此,他们做教授的老爸老妈在教员俱乐部见面,或是在教堂和会议上碰头,只是口口声声抱怨起镇上的小混混窜到自己这神圣的校区来行窃。
这些行窃的男孩都是一些挺拽的家伙。他们夜晚开着父母的车出来游荡,将驾驶座往后移,伸长胳膊,手刚够着方向盘。奥西塔,就是恩纳玛比亚偷窃事件之前几个星期偷了我家电视机和录像机的男孩,总是那副深沉样儿,戴着一顶帽子,走起路来很有风度似的。他的衬衫总是熨得很挺括,我曾经注意过栅栏那边的他,看到他就闭上了眼睛,想象着他朝我走来,跟我说,我是他的。他从未觉察到我的关注。他偷了我家的东西后,我父母根本不会去埃布比教授家里,要求他儿子把我们的东西还回来。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这都是镇上的小混混们干的。可他们知道是奥西塔干的。奥西塔比恩纳玛比亚大两岁,大部分行窃的男孩都比恩纳玛比亚大一些,这也许是恩纳玛比亚不敢去别人家行窃的缘故。也许,他觉得自己的年纪有资格去偷母亲的首饰了。
恩纳玛比亚跟母亲长得很像,蜂蜜色的皮肤,大大的眼睛,一张丰满而弧线优美的大嘴。母亲带着我俩去市场时,商贩们都起哄说:“嗨,太太,你怎么把这么好的肤色浪费在男孩身上,女孩的皮肤倒是生得这么灰暗。男孩要这么漂亮干什么用啊?”这时,母亲就会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她有责任为恩纳玛比亚的好相貌表现出顽皮的开心样子。恩纳玛比亚十一岁那年在学校里用石块砸了教室的玻璃窗,母亲给他钱去赔偿损坏的玻璃,却没把这事儿告诉父亲。二年级时,他弄丢了图书馆的书,她对他的班主任说是被我家的男仆偷走了。三年级时,他本该每天提早离校去参加教义问答,结果他一次都没有去过,以致后来都没法接受圣餐礼,而母亲却对别的家长说他考试时得了疟疾。他拿了父亲那辆车的钥匙,用肥皂做了印模,还没来得及找来锁匠就被父亲发现了,可母亲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他怎么能做这样的实验,也没怎么当回事。当他偷了父亲书房里的考卷去卖给父亲的学生时,母亲冲着他大喊大叫,而转身却对父亲说恩纳玛比亚毕竟十六岁了,本来就该多给他一些零花钱。
我不知道恩纳玛比亚是否后悔偷了母亲的首饰。我一直没法从我兄弟那张挂着微笑的漂亮脸庞上看出他的真实感情。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事儿。就在那时候,我母亲的姐妹送来了自己的金耳环。就在那时候,她又在摩齐亚太太那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来了一套吊坠耳环,那个迷人的女人是做意大利首饰进口生意的,我母亲每月一次开车去她那儿付首饰款。自从发生恩纳玛比亚偷窃首饰事件后,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事儿。好像我们假装恩纳玛比亚没干过这事儿就能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如果不是三年之后,恩纳玛比亚在大三时被逮进了警察局,这起偷窃事件也许再也不会被人提及。
我们这个宁静的恩苏卡校区刮起了一股帮会风。大学里几乎所有布告牌上都用醒目的粗体字写着:对帮会说不。最出名的帮会是“黑斧帮”“海盗帮”和“皇家海盗帮”。它们曾经代表着温馨的兄弟情谊,后来却演化成了人们称之为“帮会”的东西,那些对美国饶舌歌手如数家珍的十八岁小伙子,正经受着神秘而古怪的人生启蒙,以至于他们当中时不时会有一两具尸体撂在了奥迪姆山上。枪支、打打杀杀的忠诚,还有斧头,俨然成为了流行时尚。帮会大战成了最火的时尚:如果一个男孩向一个属于“黑斧帮”头目的女孩献殷勤,那么过不了多久,这男孩在去买香烟的路上,大腿上就会被人捅一刀,然后他没准摇身一变就成了“皇家海盗帮”的人,然后他那些“皇家海盗帮”的弟兄们就会闯入一家啤酒馆,顺手逮来某个“黑斧帮”男孩,朝他肩头射一枪,第二天,发现一个“皇家海盗帮”成员死在那家餐厅里,尸体倒在一排铝制汤盆上,当天晚上,在某个讲师家里,一个“黑斧帮”男孩又被砍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的CD音响上鲜血淋漓。这些都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事情。这些非常事件很快就成为常态了。女孩子们下了课就窝在宿舍房间里,而教师们听到苍蝇嗡嗡地飞过也会全身发抖,大家都被吓坏了,于是就召来了警察。他们开着摇摇晃晃的蓝色标致505飞快地驶过校园,锈蚀的枪管伸出车窗,像是在吓唬学生。恩纳玛比亚在课堂上笑翻了,回到家里又议论起来,他觉得警察本该表现得更好一些。所有的人都知道,帮会男孩手里的家伙比警察的更先进。
父母亲默不作声地注视着恩纳玛比亚哈哈大笑的面孔,我知道他们也在担心,不知道他是不是帮会中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他是。帮会男孩都很拉风,而恩纳玛比亚就挺拽的。那些男孩们看见他走过就大声喊他的绰号——“疯客!”——跟他握手。女孩们,尤其是当红的“大鸡仔帮”女孩,跟他打招呼时,拥抱的时间似乎也太长了点。他可以出入所有的聚会,无论是乏味的校园活动还是镇上更狂野的派对,他都是备受女人欢迎的男人,同时也是哥们圈子里的哥们,就是那种一天抽一包乐富门香烟、坐下来就能干掉一箱星牌啤酒的家伙。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他不是帮会中的人,因为他太受欢迎,跟所有不同派別的人好像都是哥们,倒没有一个敌人。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这兄弟是否有——胆量,是否敢于铤而走险——混入帮会组织。只有一次,我当面问他是不是帮会中的人,他惊讶地看着我(他的睫毛长而浓密),好像我本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之前他说过,“当然不是。”我相信了他。我父亲也相信了他。可是我们对他的信任几乎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已经被捕,并以帮会成员的罪名被起诉了。他对我说——“当然不是”——是在我们第一次前往关押他的警察局探视他的时候。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个燠热的星期一,四个帮会成员蹲守在校区大门口,拦截了一位教授驾驶的红色奔驰车。他们用枪顶住她的脑袋,逼她离开车子,然后他们把车开到工程学院,在那里,他们开枪射杀了三个刚走出阶梯教室的男孩。当时是中午。我正在附近上课,我们听到了猛烈的枪击声,我们的讲师第一个冲出教室。然后是一片尖叫声,楼梯上突然乱七八糟地挤满了张皇失措的学生。外边,三具尸体躺在草坪上。那辆红色奔驰鸣着尖厉的喇叭开走了。许多学生当即拿包走人,摩托车司机以高于平时两倍的收费送他们去停车场。主持学校事务的副校长宣布取消所有夜间课程,晚上九点以后学生一律不准出门。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枪击发生在热热闹闹的大白天,或许对恩纳玛比亚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宵禁开始的第一天,晚上九点他就不在家,那个晚上他就没有回家。我估计他是住到朋友家了,再说他也并不经常回家。第二天上午,一个保安来告诉我父母,恩纳玛比亚被逮走了,他和另外几个帮会男孩一起被塞进警车送往警察局了。母亲一听便尖声大叫:“不许这么说!”父亲平静地谢过保安。他开车带我们去了镇上的警察局。在那儿,一个治安警官嘴里含着脏兮兮的钢笔帽,说:“你们是来找昨晚被捕的那几个帮会男孩吗?他们被带到埃努古去了。案情非常严重!这回,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铲除这些帮会祸害!”
我们回到车里,新的恐惧攫住了我们。在恩苏卡——我们这里是个生活节奏缓慢、与世隔绝的地方,而镇上的生活节奏更缓慢,更加与世隔绝——总还能够想想办法,父亲也许认识警方的头儿什么的。但在埃努古,我们却什么人都不认识,那是驻扎着尼日利亚陆军机械师的州府城市,那里有警察总部,繁忙的十字路口都配有交通监督员。那儿的警察遇到棘手的案子就会大开杀戒,并以此闻名遐迩。
埃努古警察局四面筑着围墙,形状不规则的院子里挤满了一幢幢房子,悬挂着“警务专员办公室”牌子的大门外堆着几辆锈迹斑斑的报废车。父亲将车驶往院子另一头那个长方形的小平房,到了那儿,母亲拿出钞票,还有乔洛夫炒饭和肉食贿赂两个当班警员,那些东西都装在一个扎紧的黑色防水胶袋里,于是他们准许恩纳玛比亚走出牢房,跟我们坐到一棵伞形树下的长凳上。没人问他为什么明知夜晚宵禁却还待在外面。没人抱怨警察毫无理由地闯进酒吧,逮走了所有在那儿喝酒的男孩和酒吧侍者。我们只是听恩纳玛比亚说话。他叉着两腿坐在木头长凳上,面前摆着盛着米饭和鸡肉的保暖瓶。他的眼睛有所期待地闪闪发光:一个马上要开始表演的艺人。
“如果都像管理我们这间牢房那样去管理尼日利亚,”他说,“我们这个国家也许就不会有问题了。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我们这间牢房里有个老大,叫阿巴查将军,他还有个二把手。你一进这间牢房就得给他们交钱。如果不交,你就有麻烦了。”
“那你身上有钱吗?”母亲问。
恩纳玛比亚笑笑,由于前额添了一个小虫叮咬的丘疹般的疱块,他那张脸甚至变得更漂亮了。他用伊博语说,在酒吧里被逮捕之前那一刻,他迅速将钞票塞进了自己的肛门。他知道如果不藏好就会被警察拿走,他也知道到了牢里需要用钱来打点自己。他咬了一口炸鸡腿,又改用英语说:“阿巴查将军对我藏钱的这一手非常欣赏。我已经过了他这道关。我一直在说他好话。他们唱歌时,我们新进去的人都得捏着耳朵做蛙跳动作,他只让我跳了十分钟,而别人差不多要跳三十分钟呢。”
母亲抱住自己的身子,像是感觉很冷。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细心地观察着恩纳玛比亚。而我则想象着,我这个在老大面前过了关的兄弟,如何将几张一百奈拉3的票子卷成香烟般粗细,然后用手伸进裤子后面忍痛塞入体内。
过后,我们驾车回恩苏卡的路上,父亲说:“在他闯入自己家里行窃那回,我就该有所行动了。我本来就该把他送进牢房。”
母亲盯着车窗不吭声。
“为什么?”我问。
“你看,这回倒是把他震住了。难道你没看出来?”父亲露出苦笑问我。我可没看出来。那天是没看出来。在我看来,恩纳玛比亚似乎安之若素,他能将钱一股脑儿塞进屁眼里。
恩纳玛比亚第一次被吓着,是看见一个“皇家海盗帮”男孩的哭泣。那男孩长得高大强壮,传说此人有过杀人记录,下学期有望成为帮会头目,可是现在被关进牢房,吓得缩成一团,牢房老大在他后脑勺上敲了一棍子,他还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我们第二天探监时,恩纳玛比亚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口气里充满了不屑和失望,好像突然让他看到“绿巨人”原来是罐绿油漆。几天后,他又受了第二次惊吓,那件事情发生在一号牢房,那间牢房离他的牢房很远,两个警察从一号牢房拖出一具肿胀的尸体,在恩纳玛比亚他们的牢房前停下来,以确保他们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见了那具尸体。
就连牢房老大对一号牢房也心存畏惧。恩纳玛比亚和同牢房一些能够出钱洗澡的人,用盛过油漆的铁桶贮满水,拎到院子里去擦身,警察就在一边看着他们,还常常冲着他们叫喊:“别洗了,否则把你们关进一号牢房!”一号牢房是恩纳玛比亚的噩梦。他不能想象还有比自己这间牢房更可怕的地方,这间牢房里塞满了犯人,他经常被挤得只能贴着四处开裂的墙壁站着。墙壁缝里全是小虫子,咬起人来非常厉害。每当他叫喊起来,同牢房的人就称他“牛奶香蕉男孩”“大学男孩”“奶娃娃男孩”。
那些虫子个儿很小,咬起人来却挺凶。晚上咬得更凶。牢房里的人都是脑袋顶着别人的脚丫子,侧着身子睡觉,只有牢房老大能够整个背脊躺在地上很舒坦地睡。也只有牢房老大可以享用盛在盘子里的木薯饭,享用每天送进牢房的菜汤,其余的人只能每人喝两口。这是恩纳玛比亚关进去的第一个星期告诉我们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不知墙壁里的虫子有没有咬到他脸上,不知他前额蔓延开来的丘疹疱块是不是受到虫咬的感染。有些丘疹疱块的尖顶上已经渗出了脓水。他一边抓挠一边说:“我今天不得不坐在一件雨衣上,一直坐在那上面。厕所都漫出来了。星期六才冲厕所。”
他的声调像演戏那样夸张。我很想叫他闭嘴别说了,因为他好像很享受自己这种没有尊严的受害者的新角色,因为他不明白:警察允许他出来享用我们带去的食物该有多么幸运,那天晚上他在外面喝酒是多么愚蠢,而他被释放的几率是多么不确定。
在他被关进去的头一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去看他。我们坐着父亲那辆旧沃尔沃上路,因为我们觉得母亲那辆更旧的标致504在恩苏卡校区以外行驶不太安全。当我们驶过路上的警察岗哨时,我注意到父母的不同表现——难以捉摸,但确实不同。只要我们被粗野而贪贿的警察拦下检查,我父亲就不再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了。他从不说起我们被警察延误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不肯向他们行贿,也不提起警察拦下那辆巴士的事儿,当时我那漂亮的表姐奥杰奇正在那辆车上,他们把她一个人拽出车外,骂她是婊子,因为她有两个手机,又向她索要钱财,她在大雨中跪在地上求他们放她走,因为那辆巴士就要开走了。而我母亲也不再嘀嘀咕咕地抱怨了,这都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不适症状。我的父母都沉默不语了。他们不再有以往那种感觉,以为不再批评警察似乎就能让恩纳玛比亚早日获释。恩苏卡校区的高级警司曾用过“微妙”这词儿。恩纳玛比亚是否能尽快被释放,可能会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尤其是在埃努古警察局长上了电视,沾沾自喜地做了关于逮捕帮会分子的访谈节目之后,帮会分子的问题变得更突出了。接着阿布贾4的大人物也来事了。每个人都要出来做些什么。
第二个星期,我对父母说我们别再去看恩纳玛比亚了。我们不知道这样来来回回还得跑多少趟,再说每天在路上驱车三个小时,旅途成本也太高了,就让恩纳玛比亚自己照料自己也没什么坏处。
父亲惊讶地看着我,问:“你这话什么意思?”母亲冲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便朝门口走去,她说没人求我去那儿,在我无辜的兄弟受苦的時候,我大可以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她朝车子那儿走去,我跑着追过去,可是当我冲到外面,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于是抄起红龙船花丛旁边的一块石头,掷向沃尔沃汽车的挡风玻璃。挡风玻璃裂开了。我看见细细的裂纹像射线似的在玻璃上散开,然后转身上楼,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躲避母亲的狂怒。我听到她在大叫大嚷。我听见父亲的声音。最后,一切都归于沉寂,我没有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那天,没人去看望恩纳玛比亚。这小小的胜利让我有点儿吃惊。
我们第二天去看他了。我们都没提起挡风玻璃上的裂纹,那散射的裂纹就像河面的涟漪冻成了冰花。那个皮肤很黑很讨人喜欢的值班警察问我们,为什么昨天没来,他已经在惦记我母亲的乔洛夫炒饭了。我原想恩纳玛比亚也会这样问,甚至会感到不快,但他却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沉静,他这种表情我以前从未见过。他没有吃光眼前的那份炒饭。他的目光一直游移开去,看着院子那边一堆差不多全毁的汽车(都是一些事故车)。
“出什么事了?”我母亲问,恩纳玛比亚马上开口说话了,好像他就等着人家发问。他的伊博语说得很平稳,语气既不高也不低。前一天,他们牢房里塞进来一个老人,大约七十五岁上下,一头白发,满脸皱纹,身上有一种退休官员的老派清廉气质。他的儿子因抢劫武器被通缉,警察没抓到儿子就把他给关进来了。
“那人什么都没干。”恩纳玛比亚说。
“可你也什么都没干。”母亲说。
恩纳玛比亚摇摇头,好像说她没听懂。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变得更压抑了。他的话少了,而且大部分话题都跟那个老人有关:他没有钱,买不起洗澡水,别人都拿他取乐,或是污蔑他把儿子藏起来了,牢房老大对那老人根本不屑一顾,而老人看上去非常害怕,显得那么弱不禁风。
“他知道儿子在哪儿吗?”母亲问。
“他已经四个月没见到儿子了。”恩纳玛比亚说。
父亲也说了一些看法,他说不管那老人是否知道儿子的下落都与案件无关。
“当然啦,”母亲说,“这么做是不对的,但警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如果他们找不到要抓的人,就会把他的父母或亲戚给关起来。”
父亲的膝盖轻颤了一下——那是一个不耐烦的表示。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提起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这人生病了,”恩纳玛比亚说,“他的手一直在颤抖,睡觉的时候也在抖。”
父母都沉默了。恩纳玛比亚拧上保暖瓶盖子,转身对父亲说:“我想把这些东西给他吃。可是如果拿进牢房,那个阿巴查将军会夺走的。”
我父亲走过去询问那个值班的警察,是否允许我们见一下恩纳玛比亚牢房里的那个老人,就几分钟。这回当班的是一个尖酸刻薄的浅肤色警察,母亲每次把贿赂他的炒饭和钱塞过去,他从来都没一个谢字。这会儿,他嘲笑我父亲说,让恩纳玛比亚出来已经足以让他丢掉饭碗了,而我们居然还想把另外一个人也弄出来,我们以为这是寄宿学校的家长访问日?难道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关押犯罪分子的高度防范之处?父亲回来了,坐下叹了口气,恩纳玛比亚沉默地抓挠着他的疱疹。
第二天,恩纳玛比亚只是略微动了一下自己的那份炒饭。他说起,警察说要清洁牢房,用掺了除垢剂的自来水冲刷牢房地面和墙壁,那老人买不起洗澡水,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这时急忙冲进牢房,脱下衬衫躺到地上用那些带有除垢剂的水擦拭自己羸弱的背脊。警察看了都哈哈大笑,他们逼他脱光全身衣服到外面的走廊上去游行示众,然后又大声笑着说,他那个贼骨头儿子知不知道他老爹的阴茎都皱缩干瘪了。恩纳玛比亚说到这些,目光凝视着橘黄色的炒饭,当他抬起头来,我看到我兄弟的眼里噙满泪水——我这俗不可耐的兄弟——我的心里对他涌起一股柔情,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两天后,校区又发生了一起帮会杀人事件:一个男孩在音乐系大楼前用斧头砍了另一个男孩。
“这样好。”我母亲说,她和我父亲正要再次去拜访恩苏卡的高级警司。“他们现在可不能说帮会男孩都被一网打尽了。”我们那天没去埃努古,因为我父母在警司那儿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但他们回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恩纳玛比亚和那个酒吧招待很快就会被释放。那些帮会男孩中有一个是警察的线人,他坚持说恩纳玛比亚不是帮会成员。那天早上我们比平时离家要早,没有带乔洛夫炒饭,太阳已是热辣辣的了,车窗玻璃全都被摇了下来。母亲一路上显得紧张不安。往常她总是时不时提醒父亲,“小心啊!”好像父亲没看见另一条车道上的车子在危险地转弯,这回她更是不停地这样嚷嚷,以至于我们还没有走到“九英里”的地方(那儿沿街叫卖的小贩总是蜂拥而上,端着盛满熟鸡蛋和腰果的托盘围住汽车),我父亲就停下车发起火来,“到底是谁开车啊,乌佐奥玛卡?”
那个布满了建筑物的院子里,两个警察正在伞形树下抽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一开始,我心头一紧,以为那是恩纳玛比亚,但不是他。警察每抽打一下,躺在地上的男孩就蜷曲着身子叫喊一声。我认识这男孩,他叫阿波依,长着一张猎狗似的脸,阴沉而丑怪,经常驾着一辆雷克萨斯出入校区,据说他是“皇家海盗帮”的。我们进去时,我竭力不去看他。那值班警察脸颊上有一个部落标志的刺青,每次接过贿赂物品,他总会说一声“上帝保佑你”,这回一看见我们,他眼睛就瞟开去了。一阵刺痒爬过了我全身的皮肤。我知道事情不妙。我父母把警司的通知交给他。那警察没有看通知。他知道释放的命令,他告诉我父亲,那个酒吧男孩已经释放了,但这个男孩的事情有点儿复杂。我母亲嚷起来:“这个男孩?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儿子在什么地方?”
那个警察站起来。“我让我的上级来向你们解释。”
母亲冲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衬衫。“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父亲把她拽开,那警察掸了掸自己的衬衫,怕被她弄脏了似的,然后转身走了。
“我儿子在什么地方?”父亲的声音是那么平静,却像钢铁般掷地有声,那警察站住了。
“他们把他带走了,先生。”他说。
“他们把他带走了?”我母亲打断了他的话。她一直在大叫大嚷。“你说什么?你们杀了我儿子吗?你们杀了我儿子?”
“我的上司说,你们来了就去叫他。”那警察说,这回说完便转身匆匆走出门去。
他离开后,我感到一阵透心凉的恐惧,差点要像母亲那样追上去揪住他的衬衫,让他交出恩纳玛比亚。警察头儿来了,我仔细观察他脸上那种不露声色的表情。
“你好,先生。”他跟我父亲打招呼。
“我儿子在什么地方?”父亲问。母亲在一边喘着粗气。事后我才意识到,就在那一刻,我们三个各自都在怀疑恩纳玛比亚已经被彪悍的警察打死了,而这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编一个说得过去的谎言来告诉我们恩纳玛比亚的死因。
“他没什么事儿,先生。我们把他转移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他。”那警官好像有些惴惴不安,他的面部表情依然一片空白,但他不敢跟我父亲的视线相接。
“把他转移了?”
“我们今天早上接到释放的命令,但当时他已经被转移了。我们没有巡逻队,所以我就在这儿等候你们过来,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去他那边。”
“他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地方。我会带你们去那儿的。”
“为什么要把他转移走?”
“当时我不在这儿,先生。他们说他昨天犯了监规,于是就被带到一号牢房去了,后来,所有一号牢房的人都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他犯了监规?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当时不在这儿,先生。”
我和那警官并排坐在后座。他身上散发着某种陈年的樟脑丸气味,我母亲的箱子里似乎永远都有那种气味。一路上,除了他向我父亲指路外,我们没有任何交谈,十五分钟后,我们就到了,父亲把车开得飞快,我的心跳也一样急促。那是一个小院子,像是荒废已久,里面长着一丛丛过于茂盛的野草,到处都是废酒瓶、塑料袋和纸片。那警官没等我父亲停稳车子就打开车门冲了出去,我又一次感觉到了恐惧的寒意。我們所在的这个地方,路面没有铺沥青,也没有路牌和警察局的标志,空气中一片沉寂,一种让人感到陌生的荒凉。但那警官出来时带着恩纳玛比亚。正是他,我那英俊的兄弟,向我们走来了,看上去几乎没变样,但当他走近我们,母亲拥抱他时,我看见他畏缩着向后退了一步,他左胳膊上满是鞭痕,只是看上去不那么显眼,鼻子上还有结痂的血块。
“噢,我的儿啊,他们为什么把你打成这样?”母亲问他。她转向那个警官,“你们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儿子?”
那人耸耸肩,他的举止中有了一种傲慢,看上去,他起先似乎也并不清楚恩纳玛比亚是否安然无恙,可现在他得说几句了。“你们没有把孩子管教好,你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在大学里工作。你们的孩子犯了事,你们觉得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你很幸运呐,太太,非常幸运,他们把他给放了。”
我父亲说:“我们走。”
他打开车门,恩纳玛比亚上了车,我们开车回家了。一路上,父亲没有在任何一个检查站停留。在一处岗哨前,一个警察举枪示意,试图胁迫我们停下来,但我们飞快地过去了。途中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她问恩纳玛比亚,是否要在“九英里”那儿停下来买一些点心?恩纳玛比亚说不要。我们到达恩苏卡时,他才开口说话。
“昨天,那些警察来问那个老人,问他要不要来一桶不用花钱的水。他说好的。于是他们就逼他脱下衣服顺着走廊走过去。我牢房里的那些人都大笑起来。但也有些人说,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恩纳玛比亚停了下来,他的眼神有些游离,“我冲着那些警察大喊。我说这老人是无辜的,他身体有病,如果他们一直把他扣留在这儿,他们永远都别想找到他儿子。他们叫我马上闭嘴,否则就把我弄到一号牢房去。我不在乎。我就是不闭嘴。于是他们就来把我拖出去,揍了我,然后把我带到了一号牢房。”
恩纳玛比亚说到这儿不说了,我们也不再问他什么。我脑子里想象着他扯着嗓门高声咒骂那些警察的情形,骂他们是蠢货、白痴、没有脊梁骨的软蛋、虐待狂、狗杂种,我还想象着那些警察大吃一惊的样子,那个牢房老大也张大嘴巴,一脸惊愕,而其他狱友都被这英俊的大学男孩的胆大妄为吓得目瞪口呆。我还想象,那老人带着令人惊讶的自尊,平静地拒绝脱下自己的衣服。恩纳玛比亚没有说起自己在一号牢房的遭遇,也没有说起被转移到新监舍以后的情形,在我想来,那是让人稍后就消失的地方。我那漂亮的兄弟,本来很容易将这段人生故事大肆夸张渲染,但他没有。
(本文选自《绕颈之物》一书,99读书人202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