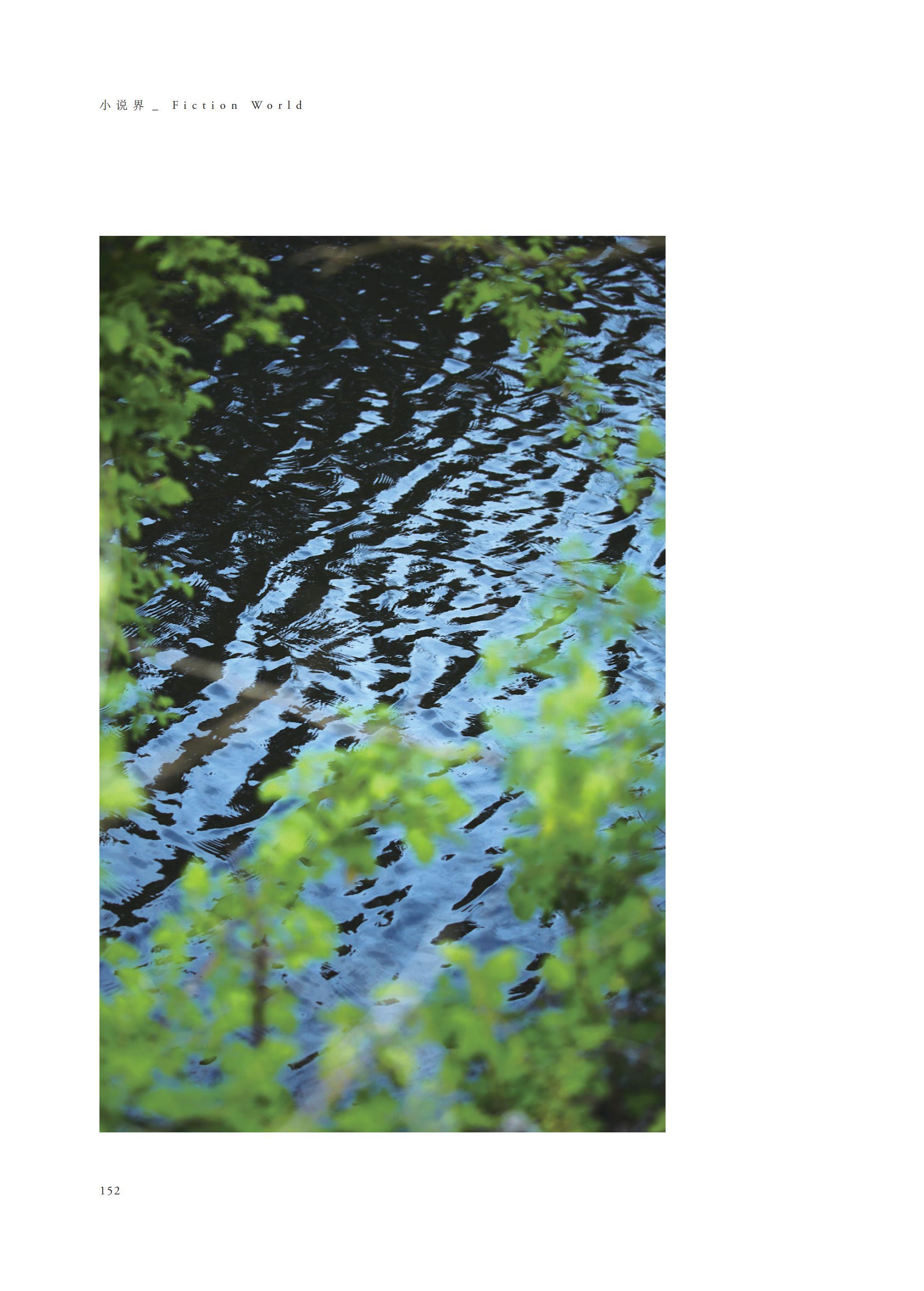
身后廊上的宫人是陌生面孔。对此伍子胥并不意外。自夫差在艾陵大败齐国,又不顾自己屡次进谏反对,决意与勾践议和,伍子胥便鲜少上朝,入宫长谈更不再可能。出使齐国归来后,伍子胥每日赤足披发,在庭院中那片小池塘边垂钓。
“相国……”王命难违,宫人再次躬身将手中的乌木盒举过头顶。姑苏城的梅雨季,空气溽湿如蒸过的厚幔。芭蕉纹丝不动,梧桐花刚开过,残留的香气间有蝉鸣,一声比一声急促,又突然安静,仿佛有人一脚踩空。汗水从宫人的额角滴下,双手酸软,但他不敢松开手里的盒子,又叫一声:“相国。”声量并不见增加。
伍子胥收起钓竿。宫人暼见鱼钩上没有饵,水色清浅的池中,似乎也沒有鱼。见伍子胥走近,他赶忙收回目光,俯得更低了。伍子胥接过乌木盒,打量一下盒子的长短,又掂了掂分量,道:“回去禀君上,就说,武员谢过他。”说完不等宫人直起身,便头也不回地穿过回廊,来到堂后的书房。桌上的酒是刚端上来的,灰陶酒瓶曾系上白色长绳,悬在清凉的井中。此刻,酒瓶在桌上留下一圈水迹。
微小的穿堂风,书房外的竹林沙沙作响。窗外的绿意,映得那光洁的乌木更见油亮,如深潭又似暗夜。“若我替公子光杀了吴王僚,将来你当真就能报楚平王杀你父兄之仇?”那时,专诸就站在这书房的烛火里,直视他的双眼这样问他。
“这吴都越来越像个牢笼,相国您熟读的兵书里明明有那么多脱困之术,却不走?”孙武驾扁舟离去前,在暮色四合的姑苏渡口这样问他。
“当年你不愿去楚都,现在却又为何还要回吴国呢?”临淄城外的大风里,鲍牧扯着他的衣袖这样追问他。
更早些时候,那是多少年前呢,伍子胥诧异,竟有些记不真切了。“求生比寻死难,复仇更难,你做得到吗?你当真要走这条路吗?”在天色灰蒙的城父,哭红双眼的兄长这样问过他。门外,是郢城来的马车,由四匹黑色的高头大马拉着,它们打着响鼻,十分不耐,好像在责怪他,这一生总是舍易取难。
可惜日暮途远,人心愁苦,更难的那条路总也要有人走。
不过,伍子胥举起酒杯时,想起还有这么一个人,自年少相识起,就并不提问。因为,这个人啊,凡事自有他的解答。所以当天下人都为自己的倒行逆施震惊的时候,那个人独自驾车去往秦国,在陌生的朝堂上,在众人嘲讽的目光里,日夜不停地哭了七天七夜,直到秦哀公的兵马驰援稷地。
“包申胥,这一杯就敬你吧。”伍子胥仰头喝下杯中的酒,打开了乌木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