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学理的角度综述了孙逊先生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以小说评点为中心的小说论研究,另一个是《红楼梦》为中心的小说文本研究,彰显了红学在其学术成果中的主导地位。另外,本文还梳理了孙逊先生二十年来“情本”说的演进发展脉络,并就“情本”说的内涵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析。
面对着电脑,我迟迟不能按下一键,只是黯然神伤。那个总是笑盈盈的孙逊兄的脸,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我眼前掠过,我想对他说什么?对朋友们说些什么?不由得久久地、久久地“沉思往事立残阳”!
说起来,我俩年龄相仿,在同地从事同类的工作,又几乎同时走上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道路,特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差不多同时招收博士生后,年年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中,几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到他病重。这三、四十年的交情,使我心中抹不去的是对他的钦佩,我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做学问能登高望远,有雄才大略,又才思敏捷,能广结人缘的难得的朋友。
1981年,他以《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崭露头角,使我关注了这一个陌生的名字。当时我刚回复旦不久,对上海滩上高校圈子里的人两眼墨黑,只是在同事口中了解到他早在做一些《红楼梦》的工作。这部《初探》,一时受到“红学”界耆老如周汝昌、冯其庸等先生的激赏,当在情理之中。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红学的外行人看来,也觉得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说它是红学史上的第一部脂学专著,而深感到它确实在脂评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本来,新红学实由脂评而来。脂评就是新红学的命根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就是立足在脂评之上建构了他的体系。周汝昌先生所说的“真正的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等,无一离不开脂评。所以自胡适考证《红楼梦》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触碰脂评者实际上也为数不少,但一般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的,“只是写几篇文章,一麟半爪的作些探讨”,又都是在狭隘的红学文献学的房间里兜圈子而已。孙逊兄的这部《初探》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在我看来,就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因是“第一部专著”而“填补了空白”,而在于不但变“一麟半爪”的脂评文献学的研究为全面、系统地进行观照与梳理;更重要的是走出脂学文献学研究的小房间,用小说艺术学的眼光来探讨脂评在小说批评史上的价值。
说起这部《初探》在脂评作为文献资料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面性、系统性,在其论述有关脂本的版本、评者及评语透露的与小说相关的“真事”、小说作者的家世生平、创作过程中的修改情况与八十回后发展的大致轮廓等各个方面,都作了全方位的论述,其规模意度不同凡响。而且,它的全面性、系统性不是简单地建筑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而是包含着诸多他独自研究的心得。比如,第一回写到葫芦庙大火,“接二连三”,“牵五挂四”,把一条街全烧光了。甲戌本于此有批语曰:“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又联系此回癞头和尚对甄士隐所念四句言词中说到“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有旁批云:“不直云前而云后,是知讳者。”都可证脂评作者是“知者”,知道这场大火是隐指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皇上亲谕江南总督范时绎去查封曹家。又如他用一节的篇幅,列举了20个问题,详细地梳理了脂评透露的小说八十回后情节发展的大致轮廓。诸如此类,足见工夫,在“真正的红学”史上,其历史功绩也不可小觑。
不过,我在第一时间内对这部专著的关注,并不是与周汝昌、冯其庸先生们站在同一个角度上欣赏的。他们是站在所谓“真正的红学”、实际上是“红学”文献学的基础上给予这部著作以高度评价的,而我是从小说的艺术批评的立场上看出它与以往的脂评研究是不同的。他已走进了一个新天地。正是在这意义上,我说孙逊兄在脂评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之所以显得有些另类,倒不仅因为我始终是一个“红学”的门外人,而主要是当时我正在编写小说批评史,所以就很自然地从小说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脂评。《初探》尽管在全书十九节的篇幅中仅仅用一节的位置来写脂评“总结了小说的艺术成就并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艺术见解”,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没有摆脱胡适等将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简单地同“八股的作法”等同起来的影响,不时给脂评套上“形式主义”的帽子,但从总体来看,这一节实际用了40余页较多的文字,充分地肯定了脂评的文论价值。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他在不到一千字的《引言》中,用了近三分之一的文字强调了“本书的意图”不同于过去的研究“偏重于脂评所提供的有关作者家世和小说情节发展线索的勾稽,偏重于诸如脂砚斋为谁等问题的探讨和各类评语的归类”,而是更注意“对脂评本身思想艺术见解”的探讨,“试就它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作一初步的评析”。这充分地说明了他是清醒地、自觉地认识到了脂评的研究必须要开辟一条新路。这才是他真正的出类拔萃之处。
当然,他能闯出一条新路,也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当时随着学界对小说理论批评的开始重视,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古代评点大师金圣叹的重新评价,一系列古代小说的评点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脂砚斋而言,比《初探》稍早一点发表的文章中,如叶朗先生的《不要轻易否定脂砚斋的美学》(《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就指出:“脂评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关于曹雪芹的生平和创作方面的一些资料(这一点过去学者多半是肯定的),同时也在于脂砚斋本人的美学思想也有不少合理的内容(这一点过去被忽略和否定了)。”远在美国的王靖宇先生的文章《“脂砚斋评”和〈红楼梦〉》也说过:“其实脂评只有一小部分涉及作者和其他有关问题,而大多数确实与诸如作者的创作意图、《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等纯系文学批评的问题有关。”(《红楼梦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期)就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孙逊兄得风气之先,将脂评的小说论最早写入了专著之中。不久,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和多种小说批评史著作陆续问世,都给脂砚斋以较高的评价。越到后来,绝大多数研究脂评的论文、著作及学位论文都是着眼在小说论,而从“真正的红学”去研究脂评的,恐怕倒是凤毛麟角了。于此回首一看,更觉得《初探》的问世,其意义非同一般了。
以上拉杂所谈,只是从脂学的研究史上来说《初探》的价值,假如换一个角度,从孙逊兄个人的学术研究史来看,《初探》也是他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特别是小说评点学的出发点。在人们印象中,孙逊兄以研究《红楼梦》名世。其实,他对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的研究也是很下功夫的。《初探》最后论脂评的历史地位时,有一节专论“脂评和我国古典小说的评点派”,以当时的眼光,勾勒了从李卓吾到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再到脂砚斋的历史过程,从而肯定脂砚斋在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中的地位。之后,孙逊兄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小说论方面的文章,例如《明清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真”“假”概念及其内涵》《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再评价》《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中国小说批评的独特方式》《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范畴体系及理论贡献》等,还与孙菊园先生一起编了一本《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将古典小说的美学资料全面地进行了搜集与整理。其书共分六编:一总论、二小说与现实生活、三人物形象、四情节结构、五文学语言、六表现手法;每编之下又细分若干节目,如总论编下分有四目:“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我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的演变”“从‘稗官野史’到‘文学之最上乘’——我国古代小说历史地位的变化”“两两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我国古代小说的比较研究”“‘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我国古代小说评点中的鉴赏论”。在每一节目前都有一篇短论,概述了本节所收材料的主要内容与历史演变。全书卷首又有一篇总论,抓住了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认识、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等三个突出的问题,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理论上开辟了以前建筑在诗文批评基础上的文论所未涉及的命题,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所以这本书,不只是一部资料集,也可当作一本“中国古代小说论概要”来读。到1992年,他又发表了一篇长文,再论了《脂批与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比起《初探》中对于脂批及小说评点的批评来,不仅论述的对象更为丰富,对于金圣叹等人的评价更为公允,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的认识有了飞跃,彻底抛弃了“八股的作法”“形式主义”等帽子,能客观地总结中国古代评点的短长得失,指出它虽有一些先天的不足,但“不妨害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自有其优长之处:“它创造了一种比较自由的批评形式,能于作品正文的字里行间将小说作者在思想上的深刻寓意、艺术上的独运匠心,用寥寥数语就剖示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在阅读正文的同时不太费精神即可领略体味”;它虽然显得不够系统,“但却能讲出许多大块理论文章讲不到的妙处”;它“性质虽是一种文学批评,但却更多地带有鉴赏的成分,是理性的批评和感性的鉴赏的一种有机结合”;它是一种“瞬间的感受和即兴式的随想”,然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而未及详细阐发的理论命题和美学思想,“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文论的宝库,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和批评也不无借鉴和启迪”。这些总结,难能可贵,即使在今天,还是很有现实意义,因为从骨子里瞧不起评点、瞧不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的还大有人在!
在关注《初探》同时,我对他的《金瓶梅》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起来了,并由此而一点一点地走近了他。1979年朱星先生发表了《〈金瓶梅〉考证》,打响了文革后《金瓶梅》研究的第一枪。尽管我第一个作出了反应,写了篇《〈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但我当时的兴奋点在金圣叹与《水浒传》,并没有进一步去关注《金瓶梅》,直到1982年才又写了篇《〈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到1983年发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后,才逐渐将兴趣往《金瓶梅》方向转移。而实际上孙逊兄也是在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且力度大大地超过了我,就在1979至1980年间,他竟一连发表了《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论〈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及其严重缺陷》《论〈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关于〈金瓶梅〉的社会历史背景》《〈金瓶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几乎包罗了《金瓶梅》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显然,他是当时《金瓶梅》研究的领跑者。之后,他又就作者、人物形象的分析及“性思维”等问题不断拓展他的研究视野,并在这基础上与詹丹先生一起写了两本通俗读物《金瓶梅概说》与《漫说金瓶梅》。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金瓶梅鉴赏辞典》,尽管署名是“上海红楼梦学会、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编”,但全书是由他负责总的设计,他又具体负责撰写了不少部分,所以在我心目中,始终将此书与他联系在一起。1991年,由我主编的《金瓶梅大辞典》也出版,就是落后了一步。两者相较,虽然内容都是在解释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和有关知识,但我深感到他们是兵强马壮,书中有不少内容明显比我们解释得更精准、更好,所以一直想有朝一日能作进一步的改进。总之,当新时期“金学”研究的浪潮兴起之初,孙逊兄就是一个出色的弄潮儿,只是他后来事多,慢慢地淡出,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上面从《初探》出发,回忆了孙逊兄的小说评点研究与《金瓶梅》的研究,这是由于这两个方面与我的工作交集较多,所以首先想到。其实,他于《初探》之后,是从两个大方向继续迈进的:一个是以小说评点为中心的小说论研究,另一个是《红楼梦》为中心的小说文本研究,这当然包括《金瓶梅》和其他小说在内。尽管他对《金瓶梅》所下的功夫比之“其他小说”来明显较多,但《红楼梦》还是他主攻的方向,写的文章也多。这次文集以《红楼梦文化精神》专辑一集,就集中了他的红学成果。恕我对《红楼梦》完全是外行,自知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流行话语距离较远,为了不自找没趣,所以就一直敬而远之,也因此大多数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我都没有碰过。孙逊兄发表的有关文章有的也拜读过,但更有一些过去未曾注意,这几天匆匆翻阅了一下,觉得有一些文章写得很实在,如《金陵十二钗的排列次序及其寓意》《〈红楼梦〉人物与回目关系之探究》《论“三副”之冠红玉》等,不跟风,不附势,不走套路,不说套话,从文本出发,就小处着眼,层层推断,步步深入,所作的结论大致都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假如从大处着眼的话,他所提出的“情本位”说可能是他红学研究中最为着意之笔。
本来,要回答一部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的主旨是什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恐怕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个人的变幻不一,总会有千差万别的答案,但人们总是想找出一个最接近客观真理或作者旨意,而又能统领全局的主题来。1990年,孙逊兄面对着有关《红楼梦》主题的众说纷纭,觉得假如用单一的角度、排它的眼光去归纳一个主题,恐怕有失于片面,于是开始从三个层次来论述《红楼梦》的主题:第一个是文学审美层次的主题,是小说本体所描写的爱情悲剧、婚姻悲剧、青春悲剧和命运悲剧在内的家庭悲剧、社会悲剧和人生悲剧所显现出来的主要思想。第二个是政治历史层次主题,也就是说“《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勾结和倾轧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内容,可以把它当作历史来读”。他认为“只要我们不把这一提法和文学审美层次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那么我们很难说它一定不符合作品的实际”。第三个层次,就是“最高的哲学层次”。推究《红楼梦》的哲学层次是当时俞平伯先生提出来的。孙逊兄认为,俞平伯先生提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确是《红楼梦》客观存在的一种主要哲学观念”。不过,孙逊兄在解释《红楼梦》的色空观念时,与俞平伯不同,其关键是在色、空之间掺入了一个“情”字。他说:
曹雪芹在“色即是空”的宗教哲学命题里,掺进了“情”的观念。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在“色”与“空”之间,引进了“情”作为中介。“因空见色”和“自色悟空”即为传统的色空观念,而“由色入情”和“传情入色”则为曹雪芹的创造发明。“由色入情”指由万物而生的情感欲念,它和“五蕴”之一的“受蕴”比较接近;“传情入色”则把人的情感注入万物之中(包括有情之物和无情之物),这是曹雪芹贯穿于《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据脂批透露,小说末回为《情榜》,榜中不仅有书中所有比较重要的女子的“芳讳”(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四副册共六十人,另加宝玉为诸艳之冠,计六十一人),而且以“情”为中心内容对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一个个作出评语,如宝玉宗“情不情”,黛玉为“情情”(以上参见甲戌本第八回、庚辰本第十七和十九回批语)。所谓“情不情”,按照脂批的解释,即“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甲戌本第八回),前一个“情”字用作动词。而黛玉的“情情”,则是对世间之有情之物,彼能以一痴情去体贴。两者合观,即对世间所有有情之物和无情之物,都须以一痴情去体贴。这也就是“传情入色”的内涵。
这段话,文字不多,在这篇文章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只是在最后从哲学角度来论述《红楼梦》主题时,作为对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论”的一种补充或发展提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一段话关系重大,是孙逊兄日后明确提出“情本”说的基础。因为“情本”说的核心思想、论证逻辑及基本论据,都在这里已见端倪,只是还没有加以展开而已。
至1991年,孙逊兄又接着发表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色”、“情”、“空”观念》,进一步生发与强调“情”在“色”“空”之间的“中介”作用。文章在重引了《红楼梦》中“空空道人因空见色”一段话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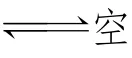
这段话不仅表示了不同于俞平伯先生的观点,即“把‘情’字排斥在外而把《红楼梦》的观念仅仅归结为‘色空’二字”,而是更明确地把“情”字上升到“色”“情”“空”三者中“最重要”的位置。其“情本”说已呼之欲出。另外,这篇文章补充了曹雪芹的“情”观是接受了明代中叶以后如汤显祖、冯梦龙等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影响。
再经过了十余年的思考,于2006年,孙逊兄终于在《红楼梦的文化精神》中明确地提出了《红楼梦》的“情本”说:
《红楼梦》主要的文化特质和精神便是“情文化”或者叫“情本思想”。这个“情”首先包含了男女之情,但同时又不完全是男女之情,它还包括了家族亲情、世俗人情,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爱之情。《红楼梦》“情本思想”的提出是我国古代小说人性关怀的自然结果,而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以及它在哲学上达到的高度,则为古代所有的文学作品所难以企及。
同时,文章又从与汤显祖、冯梦龙的“情本思想”相比中,将《红楼梦》的“情本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说它“无疑更具有一种哲学的形而上意味,更具有现代的色彩和意义”。
至此,我们可见孙逊兄构建《红楼梦》“情本”说,是在“色空论”的基础上,大致经过了20年时间的琢磨,分三步走而最后完成的。第一步,是在“色”“空”之中掺入了“情”作为“中介”;第二步,强调“色”“情”“空”三者中,“情”“最重要”;第三步,就明确《红楼梦》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就是以“情”为“本”,是一种“情文化”,因此而《红楼梦》在哲学上、文学上都达到了其他作品所难以达到的高度。至于后来发表的一些与“情本”说相关的文章,如《“情情”与“情不情”:〈红楼梦〉伦理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现代阐释》等,实质上都是用“情本”说对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具体诠释而已。《红楼梦的文化精神》就标志着他的“情本”说建构的完成,而“情本”说也就是他红学研究中的标志性成果。
孙逊兄拈出的《红楼梦》“情本”说,的确有它的妙处,所以自2006年在《文学评论》上正式发表《红楼梦的文化精神》之后(2004年《文汇报》已载其讲演的摘录,恐影响不大),立即在学界产生了反响,陆续有一些学者跟上用“情本思想”或“情本位”来解读《红楼梦》了。
其实,关于《红楼梦》的主旨,小说作者自己已说得很清楚,就是“大旨谈情”(第一回)。脂砚斋也一再强调此书是“通部情案”(庚辰本第四十六回批),是“一篇尽情文字”(戚序本第六十六回批),是“随事生情,因情得文”(甲辰本第八回批)的“真情痴之至文”(戚序本第十八回批),“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甲戌本第八回批),等等。因此,假如从作者原本的创作意图来看,而不是从各色人等的接受来看;从作品的主色调来看,而不是从各种次要的杂色来看,《红楼梦》的创作无疑是自觉地以“情”为本位的。
但是,假如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待《红楼梦》是以情为本位,未免会失之空泛。因为中国古代从来就认为文章都是因于情、本于情的。较远《礼记》《尚书》等经典中的有关言论不算,与文论直接相关的如屈原《九章·惜诵》说“发愤以抒情”,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认为“情者文之经”,都说情是文的根本。就小说而言,《三国》《水浒》宣扬“忠义”,“忠义”何尝不是一种“情”?李卓吾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忠义水浒传序》)狄平子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都不是说《三国》《水浒》《金瓶》出于“情”吗?所以,难怪在文论界、美学界不少人早就认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重视理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重感性,“情本位”。假如以这种颇为流行的认为中国文学都是“情本位”的标尺来看,说《红楼梦》“情本位”就等于没有什么意义了。
然而,为什么大家觉得《红楼梦》“情本位”说,还是有道理,比起说“大旨谈情”来更到位,更有新鲜感呢?这里的奥妙,就在于将这个“情”字本来有的两种含义混起来理解。情,一般就是指人类所有的喜怒哀乐的感情,中国文论中所说的“情本位”,就是这个广义的、笼统的“情”。从这意义上看,没有一部作品不本于情。但这个“情”,在诗、词、曲与戏剧、小说、民歌中常常又专指男女之情,也就是爱情、恋情、情色、情欲之类的“情”。那么,《红楼梦》作者及脂砚斋所说小说中的“大旨谈情”的“情”是什么情呢?也就是读者会接受《红楼梦》有别于《三国》《水浒》之类不同的“情”是什么情呢?显然是后一种情。请看甲戌本《凡例》说:
第一回题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
第五回写进“太虚幻境”后,见一座宫门,上面横书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对联,大书云: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再接着《红楼梦引子》云: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以上这些揭示小说主旨的带有纲领性的文字都可证这部小说所写之“情”主要是指痴男怨女之间的风月之情。再从其书名来看,《石头记》《情僧录》固然难以判别其主什么情,但从《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而言,明显都是指向儿女风月之情的。原稿中的“情榜”所开列的名单,也就是一些不同层次的青年女性。更何况,小说中的故事确实也主要是围绕着“闺友闺情”转的,作者就是本于亲身经历过的“情”的基础上写就了这样一部小说的。我们今天也只有站在这一点上,其情之解才有别《三国》《水浒》《西游》《金瓶》等等,其独特的而不是一般的“情本”说才能真正成立。
但是,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的《情史》及《红楼梦》这类主要写儿女私情的作品,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一般士子用儒家正统的眼光看来,往往会觉得是与“理”有违的,这正如汤显祖所说的:“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辞》)因此,要使这种情得到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认可,必须要将这种“情”普适化、合“理”化。汤显祖将杜丽娘的爱情上升到人类的“至情”,冯梦龙更将情说成在天地间贯穿于一切,所谓“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都是在将“情”向普遍的人性靠拢。不但如此,冯梦龙还直截了当地将此情向儒家的经典接轨。他在《情史叙》中说:
《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首《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而汪然有余乎!
这就将《六经》写有的若干男女之情,灌注到所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将所有人情归结为皆从男女之情始,于是再提升到“《六经》皆以情教”。这就将男女之情与人类的普遍感情以及儒教的精神完全统一起来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引导下,说《牡丹亭》《情史》《红楼梦》这类作品“情本位”,就使人既觉得其作品既不脱男女之情的本旨,又可与出于人类本性与社会习染所成的各类感情相吻合起来,甚至自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引入西方的各种哲学、政治、伦理等观点后,用各种五花八门的价值判断来解读《红楼梦》的主旨,都可以用“情本位”来统而观之了。所以,我认为孙逊兄深得汤显祖、冯梦龙等论“情”之神髓,用“情本”说来解读《红楼梦》既符合作品的本旨(作家的创作本意)与主旨(作品的主要内容),又能与现代的一些精神相接轨,自有其高妙之处了。这比起那些抓其一点,不看全局,全凭己断,自说自话地探讨《红楼梦》主题的做法来,自有楼上楼下之别了。
孙逊兄虽然着力于《红楼梦》的研究,但对其他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也多有广泛的探讨,且其多以敏锐的眼光,紧跟时代的脚步,探讨那些新鲜的、热门的话题,诸如小说与宗教、图像等多种文化的关系、小说与地域特别是都市文化的关系与尝试用新思维来探索小说艺术表现的某些特点或规律性的问题,特别是晚年全身心地投入了东亚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其功甚伟。
对于这种域外汉文小说,过去我茫然无知。1986年,我在东京大学第一次读一本《红白花传》时,一时还搞不清是中国人写的还是朝鲜人写的,当时根本不知道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外国人用汉字写的小说,所以没有引起重视。后来知道法国的陈庆浩先生与台湾的王三庆、陈益源、王国良等先生关注了这类小说,并已着手整理、出版。记得当时陈先生还找过我,希望能合作进行全面的整理。我也深知这一工作极有意义,但考虑到我的能力与条件有限,正所谓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只能作罢。想不到孙逊兄能勇挑重任,团结各路人马,孜孜矻矻,呕心沥血地将林林总总的东亚汉文小说陆续整理后,总其成而推诸世,并率领团队成员写了一批有关的论文与专著,为切实地打开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能不令人钦佩。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名声岂浪垂。孙逊兄之所以能得到学界的敬重,受到学子的爱戴,不仅仅在于为人能“逊志时敏”,广结善缘;也不仅仅在于为学科的建设鞠躬尽瘁,搞得风生水起;更重要的是他甘心于青灯下潜心于学业,能不断地与时俱进,以致成果累累,美不胜收。今就我寸心所得,在匆忙之中略书一二,与其说是对孙逊兄文章的赞颂,还不如说借此以寄托我的哀思。走笔至此,一种芝焚而蕙叹之悲陡然从心中升起,念及近年来故交逐零落,禁不住老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