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与“雅”之间艰难抉择的旧体译诗:以《鲁拜集》为例
汪 莹
《鲁拜集》的名声已经足够响亮,中译本也已经足够丰富(甚至泛滥了),但仍然持续成为出版的热点。仅从近年看,自2011年以来每年都有新出译本,尤其2016年7月到2017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的译本连续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张鸿年、宋丕方译本 《鲁拜集》,译自波斯早期写本中收诗数量最多、相对较全的1462年 《乐园》抄本,共收五百五十四首,同时增补了著名的伏鲁基考订本中未被收录的十一首,总数达到五百六十五首。这是目前从波斯原文翻译的 《鲁拜集》中译本中收诗最多的。张先生在波斯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崇高,这个用了他数十年心血、并和宋丕方先生一同努力完成的译本,在精准上,即使我们不懂波斯文也觉得毋庸置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眭谦的《莪默绝句集译笺》,中华书局2016年8月出版钟锦的《波斯短歌行:鲁拜集译笺》,都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而且采取了旧体七言绝句的形式,译者却都比较年轻。
三本书的翻译理念却存在极端的冲突
然而三本书的翻译理念却存在极端的冲突。这反映在张鸿年、宋丕方译本以“《乐园》本《鲁拜集》出版工作小组”署名的出版后记和钟锦译本的译序里。前者指出:“据菲氏英文本译成汉语的《鲁拜集》越来越多,某些品类已经超出了正常翻译的范畴,甚至丧失了理性的制约。如此的所谓‘翻译’,值得警醒。”后者指出:“诗之译,信为最下矣。”前者批评的对象,似乎重点之一就是使用旧体的译者:“海亚姆的诗篇仿佛真的成了一个酒瓶,……酒瓶中装得下‘平水韵’和‘阶级斗争纲领’之种种。”看来前者认为海亚姆容不得“平水韵”,那用旧体的翻译根本就是个错误。(“阶级斗争纲领”显然指另外一个旧体译者:柏丽。)后者所针对的,正是谨守原初语言文本语义的翻译理念,甚至贬抑为“奴译”:“信与雅必不得兼,宁丧其信,不失其雅。失其雅,则为之奴矣。”当然,双方决非互相指责,我所说的只是表现在各自翻译理念上的极端冲突。揭示这一点,也决非为了使冲突激化,而是从中反思诗歌翻译的深层美学因素。
外国诗歌的新内容必然要求新语汇,而这种新语汇往往与中国古典诗体的固有程式存在疏离,而这种疏离完全在于中国古典诗文自身的特征,并不在于时间因素
失“信”:旧体译诗显而易见的弱势
在这个冲突中,“《乐园》本《鲁拜集》出版工作小组”无疑是译界主流的观点,郭延礼的说法可为代表:“翻译外国诗歌用中国古典诗体,又用文言,很难成功。”除开现代白话强大的话语权之外,旧体译诗显而易见的弱势,给了主流观点充足的理由。这个缺陷和中国古典诗文自身的特征密切相关。中国古文辞自先秦秦汉、诗词自唐宋以来,已经形成一种书写程式,这种程式使得它们和日常口语逐渐疏离。这一点在古典作者那里,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意识到。吴德旋指出:“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凡是不合这种程式的,自然被蔑视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即使如敦煌变文、白话小说那些曲尽人情的作品,也终究不齿于正统之列。甚至在中国戏曲里,情况也一样,梅兰芳讲:“我们过去唱的古典歌舞剧都有它的时代关系,除了插科打诨的小丑例外,别的演员如果嘴里念出了新名词,就好像不很调和。”都是同样的道理。
近代以来,新学渐盛,这就使人逐渐感受到诗古文辞的约束。于是颇有数辈人物,提倡“我手写我口”,主张直用新词,如黄遵宪、梁启超,都名闻一时。可是行之不久,就发现这种新兴写法和旧有程式之间颇有龃龉,很难协调。黄遵宪坚持用旧体,所以晚年编定《人境庐诗草》,那些“我手写我口”的作品几乎删完。相反的是,梁启超后来毅然投入白话文写作了。不难看出,白话文比文言少受程式的约束,更容易表达新事物,用它来翻译外国诗歌自然要得心应手得多。外国诗歌的新内容必然要求新语汇,而这种新语汇往往与中国古典诗体的固有程式存在疏离,而这种疏离完全在于中国古典诗文自身的特征,并不在于时间因素。译界主流拒斥用中国古典诗体翻译外国诗歌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有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反驳:海亚姆时当中国北宋,为什么不能用与此时代相对应的中国古典诗体来翻译呢?这个反驳其实并未切中问题的要害。

很多所谓的准确翻译其实是不达意的
失“雅”:白话译诗易被忽视的弱势



田世昌讲的“文为散体,殊失外美”,指出了“信”和“雅”之间的冲突;而“过重直译,有难索解”,则是“信”和“达”的冲突。自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我们总是误认“雅”、“达”是在“信”的基础之上的修饰,而忽视了其间的冲突。落实在译诗上,“信”和“雅”之间的冲突是首要的。菲兹杰拉德的《鲁拜集》翻译引起的广泛赞誉和纷纭聚讼,也可以看作是冲突的又一体现。我想,菲兹杰拉德之所以采取他那样大胆的译法,也一定考虑到田世昌讲到的那两点。这些冲突的揭示,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反思白话译法和旧体译法的得失。可以说,因为文体自身的关系,旧体诗译者对这种冲突的感受远远超过白话诗译者,从而他们对译法的探索很可能更为深入。可惜的是,因为时代对于白话的青睐,他们的探索被大大忽视了。
不过颇多的旧体诗译者本身的旧诗素养并不高,出现了一批“信”、“雅”两失的译作,也给旧体诗译作带来负面影响,这在《鲁拜集》的新译本上尤其突出
“信”“雅”两失的《鲁拜集》旧体诗译本
在中国古代,的确存在过很多旧体译诗,不仅成功,而且不少脍炙人口。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越人歌》(《说苑·善说》)、《敕勒歌》(《乐府诗集》卷八十六),以及耶律楚材译的《醉义歌》(《湛然居士文集》卷八)。历史的偶然使得《鲁拜集》在那时并未传入中国,其翻译自然无法实现。但海亚姆的诗篇和中国古典诗体之一的七言绝句在形式上极为相近,它们的相容似乎只是迟早的事情。后来黄克孙译本的出现及广泛流传,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考察这些译诗的成功之处,也许能够让我们看到旧体译诗的优长。



新出《鲁拜集》旧体诗译本在翻译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
有了对之前旧体译本的客观认识,我们发现新出旧体译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具体对比各种译文,不仅有助于我们比较优劣,也有助于认识旧体译法所进行的探索。可以说,中国的旧体译本都延续菲兹杰拉德的译法,我们按照菲氏对原诗修正、增饰、误译的情况,分别考察。至于中译本的种种情况,便请读者自己体会了。黄克孙译本地位非常,也用来作个比较的尺度。先看菲氏修正的情况。张鸿年、宋丕方译本自然是白话译诗的典范,本文虽不关注其翻译理念,但很感谢给我们提供了波斯原文精准的汉译,便于我们进行比较。我们比较的文本是菲兹杰拉德译本的第三十一首。在张鸿年、宋丕方译本所据的《乐园》本中列第十八首:

菲兹杰拉德译本:

眭谦译本:

黄克孙译本:

钟锦译本:


菲兹杰拉德译本就显得很大胆了,他增加了一个“穿越七重门”的意象。根据菲氏注释可知,土星掌管第七重天。这个增加,不仅使前两句添了动态,也让后两句显得凝练,全诗更有力度。菲氏简直是在批改原作,这样大胆的翻译,似乎任何中译本中都还没有见到。
眭谦译本几乎是对菲兹杰拉德译本的直译,虽然“帝阙”显得过实。“致极尊”把菲氏的注释“Saturn, Lord of the Seventh Heaven.”都译出来了。然而文字仍然典雅,可以见出译者对旧诗语言运用的功力。当然,也因为这首诗的意象和中国文言并无太多冲突。
黄克孙译本很精彩,不过,似乎换成了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然而要说原诗中有什么失去的东西,似乎也找不出来。钟锦译本延续了黄克孙译本的思路,不过又把神话故事换成了玄思冥想,也就和原诗的意境更近些。用屈子“天问”代指“宇宙中一切疑难”,用庄子“生也无涯”代指“死亡之结”,自是他最常用的译法。
再看菲氏增饰的情况。文本是菲兹杰拉德译本的第十八首,在张鸿年、宋丕方译本所据的《乐园》本中列第一百一十五首:

菲兹杰拉德译本:

黄克孙译本:

钟锦译本:

眭谦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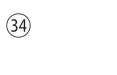

菲兹杰拉德译本将麋鹿和狐狸换成了猛狮和巨蜥,荒凉成了蛮荒,应该是为了符合英伦人士对东方遗址的想象。又让野驴在巴赫拉姆墓上踩踏,使那蛮荒变得更有画面感,同时点出巴赫拉姆以狩猎野驴闻名。平添了一位杰姆西王,大概也是为了英伦人士对东方豪奢的想象,用杰姆西王的豪饮来增添色彩。很显然,菲兹杰拉德的译文比波斯原文来得更精警,尤其符合英伦人士的视域。而且原诗盛衰无常的感慨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在豪奢和蛮荒的强烈反差色彩下显得更为深沉了。辅以英文自身的美感,经过如此创造的翻译,替代波斯原诗风靡全球实在不难理解。
客观地讲,黄克孙这首的译文不算很好。华表丹墀都已成空,台榭焉能尚存?缀以“荒凉”二字,菲氏译文的蛮荒气象全被破坏了。猛狮换成虎,本无不可,何况为了呼应“李广弓”,然而巴赫拉姆猎驴的故实却被牺牲了。让我很怀疑黄克孙这里是否参考了温菲尔德的译文。其实,以“李广弓”类比巴赫拉姆王的狩猎,并不恰切。好在黄克孙对于旧诗的感觉尚好,“虎踪今遍英雄墓”,约略能够透出些感慨来。

眭谦译文以“羿王”和“人皇”这样的中国远古帝王,给波斯近于神话的历史增添气氛,显得别出心裁,虽然丧失了一些异域的色彩。“长蛇封豕”的转换,使译文极古雅,“守无言”从静穆中突显蛮荒,很合英译的精神。但用“驰践”,似乎“羿王”之“元”遍野俱是。而“犹梦黄粱伏草宛”,晦涩之外,“黄粱”的典实也欠妥当。
再看菲氏增饰的情况。文本是菲兹杰拉德译本的第二十五首。在张鸿年、宋丕方译本所据的《乐园》本中列第四十一首:

菲兹杰拉德译本:

黄克孙译本:

眭谦译本:

钟锦译本:


黄克孙译文不佳。以“饭颗”比喻现世操劳是牵强附会,“莲花”句近俗,“棒喝”的典实在这里也不切。译诗整体显得草率。
眭谦译文按照他惯常的风格,以古雅的辞句尽量直译原诗。只是“今世辛劳”对译TO-DAY prepare,稍嫌质实。以“司辰”译Muezzín,和钟锦以“鸡人”译之,译法一致。但钟锦译文,就“鸡人”生起联想,用长乐宫喻行乐,用建章宫喻求仙,分指今世、来世,辞句雅丽。但疏忽了长乐之行乐和TO-DAY prepare并不贴切,菲氏译诗透出的及时行乐已先被否定,诗意就近于庄子的随化浮游,与原意相差较大了。


翻译诗歌也并不是对原诗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解释,而是要用译语文化的诗歌形式展现原诗的意境之妙,让译文读者感受诗性之美


? 张鸿年、宋丕方译本《鲁拜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0页。
? 《波斯短歌行:鲁拜集译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页。
? 张鸿年、宋丕方译本《鲁拜集》,前揭,第440页。
? 《波斯短歌行:鲁拜集译笺》,前揭,第18页。
?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二节,见《论文杂记初月楼古文绪论 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8页。
? 这正是以文言翻译著名的林纾在《致蔡元培书》中的话。
?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见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北京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四卷第295页。
? 转见施蜇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840-1919)》,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39页。





































编辑/张定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