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印,何积石先生庆幸与此四者结缘。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喜信史前文字妙,诗书画印数因缘。”他沉浸在“诗的意境,书的韵味,画的气象,印的感受”中,不断“挖掘自我,实践自我,提升自我”,这本《印学杂咏》正是他几十年求索的一个精神标识。阅尽荣枯前世悟,和诗投老会知音。”所谓“知音”,可以是某一种人,与他相似的“文人”;也可以是某一种精神,即他所向往的人文精神或曰“业余精神”。
一
认识何积石先生虽已有年,但我对他的为人、从艺和治学,所知十分轻浅——只知他于书、画、印都有造诣,建树甚多,曾举办或参与了多次个展和联展;也知他于诗词也有修为,吟咏甚丰,更常将“印”之话题注入诗中,乃成别具一格的“咏印诗”。这种“一诗一印”的组合,如老枝著花,拙巧互映;似古潭游鱼,动静相适。我不仅常在手机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更在主流报刊和专业期刊上见到。不过,直到他将一本《印学百咏》放在了我的手上,我才真正感到了他的分量。
《印学百咏》收录了何积石先生的108首七言绝句,分印式、印史、印人、印话四个块面,实现了以诗咏印的系统。这108首诗中有史料、有评析、有理性,有形象、有感情、有意境,互为交织,单读可以成篇,统览则成体系。这108首诗的呈现方式,并不是工业化的印刷体,而是由近百位书家、文人分别书写,增添了个性恣肆、纷繁多姿的美感。此举并非邀众造势,而是何积石先生出于对诗的珍爱,并在全书的结构布局、内容编排、审美感受等方面务求多元多样、尽善尽美的愿望及努力。与诗相配,书中配以大量经过精挑细选的古今名印。何积石先生治印五十多年,于此道的心力最深,尤对印之题材作了挖掘和开拓,将绘画的因子融入其中,乃成“肖图佛印”。他的华居“百佛精舍”,因此得名。至此,诗书画印在《印学杂咏》中得到了全面和充分的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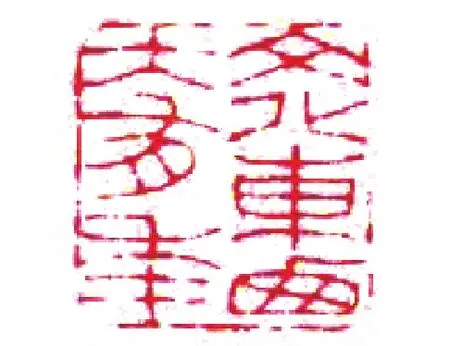
正文“文化东西大有年”(何积石 刻 )

边款“形色虚伪,气象高要。壬辰六月,积石”(何积石 刻 )
诗、书、画、印,我不知道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河中,几时成了中国知识者的共同精神河床。他们以此四者言志、表意、抒情、标识自我,无论得志还是失意,快乐还是悲伤,自遣还是交际,无论青春还是迟暮、天南还是海北、春夏还是秋冬……都将四者融于一炉,成为自个体而至全体的精神架构,自现实而至理想的艺文风光。这样的知识者古称“士大夫”,今称“文化人”或“文人”。至于四者的轻重与先后,我以为“诗”乃基本,不仅因“诗”乃文学各类体裁之首,更因“诗”乃所有艺文的思情之源、追求之境,贯彻于创作的目的、思维、方式及过程的始终。总之,唯有将“诗”完全彻底地注入书、画、印中,方能使线条、色彩、刀法既呈现出世界的丰富,又辨析出人性的复杂。比如苏轼,时人评其诸艺曰“书不如画、画不如文、文不如诗、诗不如词”,甚为精辟。倘倒转次序为“词不如诗、诗不如文、文不如画、画不如书”,便不是苏轼;若真是苏轼,则他便不是公认的“天才”,至于“通才”,两千多年来根本不缺他一位。又如齐白石被公认为以画最名,却自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足见其识见之深、智慧之高。何积石先生对“诗”在四者中的地位了然于胸,自将108首七绝作为全书的核心内容,正如胡中行先生在序中所言:“说到底,这是一本以印学为题材的诗集。”
谈及这108首七绝的创作过程,何积石先生自言“三五首,七八首,轻吟畅想,杂咏抒情,率真生意,就事推敲,陆陆续续地衍化出的心境”。诗境是心境的衍化和铺展,总体为质朴而又脱俗、语醇且又意清。如咏南北朝私印:“铁骑扬尘锁大江,梵音隔世绕晴窗。庙前剑客徘徊久,遗老龙孙难搭腔。”又如读印所感:“金石声传在冷斋,华章陶冶作书呆。以称盛世名山醉,更觉热肠时代猜。”思维跳跃性大,语言地气感强,意境空灵度高。与诗相应,他对历代印蜕的取舍原则正是“不媚俗,不使怪,避俗为先,文气为要,技巧辅之”。不仅以诗言诗句诗行,更是以诗风诗格诗境作为全书的引领和统领,正是何积石先生编著《印学杂咏》的初心,恰如吕金成、韩祖伦先生所评:“欲臻诗、书、画、印于通境,非唯自吟自娱以自许,实扬人文精髓以清流。”
二
由此不禁想到徐中玉先生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梳理以及对古代知识者思维模式的总结。他以《艺概》为例,认为此书乃“看似零散片段,实则系统严密”的大著,“短短几句话便谈出了精微的道理,思辨寓于鲜活的比喻之中,是中国特有的不可轻看的理论形式”;进而认为如此学风贯通融汇,这般文风生动鲜活,可以消减百多年来形式大于内容的“文艺概论”的抽象、空洞和乏味;最终得出结论,当代文艺理论作品“如能兼有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岂非更好”。岂止《艺概》《沧浪诗话》《人间词话》《饮冰室诗话》等都是学和理论的质地、诗与散文的表达,而徐中玉先生所总结的传统文艺理论四大思维特点,即“审美的主体性、观照的整体性、论说的意会性和描述的简要性”,我觉得可视为对传统艺文研究和创作——尤其是随笔和诗的总结。我读苏轼散文,时见艺文散论,无论自评还是评他都闪烁着妙语、睿智和卓识之光,令人会心难忘。我还觉得以作诗来谈文论艺,理应是其中最为高级的手段,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方式。以我寡闻,这样的古代典籍几乎不见,即便是“以诗论理”成风的宋代,也没有专门的著作,其中原因,想必极为复杂。尽管“以诗为体”的学术著作至今未闻,却也并不妨碍今人尝试。祁志祥先生对《印学杂咏》作了“以诗论印的印学专著”的定位,便有此意。他还论证道,因此书“七绝字数有限,意有未尽”,故在“每首诗后都有一段古文札记予以说明、阐释”,加上书末还有作者关于印章定义、历史衍变、印家特征、时代风格的长篇论述,所以“本书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诗,而在于印”。
确实,108首七绝篇幅虽短,却有颇高的学术含量和较强的思辨色彩。如咏甲骨文字:“卜辞出土撼安阳,刻画天真笔法藏。犹忆当年龙骨梦,问谁读破古文章。”表明了甲骨的出土和形状,叙述了曾经的误解和勘谬,指向了当今治学和弘扬的任重与道远。又如咏两汉魏晋公印:“流年征战忘生死,累月贪功泪未知。急就章前贤杰表,菩提树下洗心时。”标示了“急就章”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衍变发展结果。何积石先生以绝句的容量和质量,承载了对印学的理解和见解。然而诗毕竟是诗,既难达成传统学术散论的效果,更难达到当代学术论文的标准。诗既然是诗,叙述的安排、论理的逻辑,必须服从于诗的创作思维,其中既有所长,长在宏观的大处着眼;必有所短,短在微观的精微入手,包括叙述、引述、辨述、论述等等。更何况诗既然是诗,必有感性内涵和感情色彩,这一点也在108首绝句中随处可见。何积石先生对诗的写作有明确的要求,首要是满足“艺术的儒雅”“技巧的丰富”“形式的意趣”,次之是展现“广博的变化”“真伪的辨析”“雅俗的区别”,再次是符合“时代的特征”“人文的特色”“学术的特意”,但在其中,无处不见心之起伏与情之波动,如《咏战国官印》:“挥师马上夺城郊,悬月乡头唤菜肴。善解楚秦言语用,又兼齐鲁信符敲。”又如《咏唐代官印》:“访友开元梦有因,撞钟想到踏沙人。王维秉烛觅诗意,杜甫寻花正养神。”《咏共和国公章》:“红星装点耀神州,仿宋字形争上游。立志万年精进路,方圆九派赞歌遒。”语出自然而有韵,理生平实而有情,体现了诗之情志的本质属性。
三
由此不禁想到列文森先生关于中国传统知识者的“认知模式”及“存在原则”的看法,可资参照。这位美国学者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写到,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长期的、执着的“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既重专业,更求融通。刘绪源先生以此生发,将这种“业余精神”阐释为基于专家并“高于专家之上的文人精神”。中国传统的知识者是绝不满足于只当某个领域的专家的,尽管专家们的学问可以做得极深、位置可以坐得极高。刘绪源先生认为,如果只当某个领域的专家,对内易失去人所应有的博大和兴趣,对外易丧失对人文、社会、家国的关怀与投入,从来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者的选择。而“业余精神”所具有的融合之功、接通之力,恰能弥补当代中国知识者的普遍缺失——“学术当然要走深刻综合分析、多元多样表述和系统逻辑之路,而且最好走中国人独有的方式。”我以为对于当代中国知识者来说,西方学术的问题意识、逻辑思维、形式理性是必要的,中国学问的阐发意识、形象思维、品质诗性则是必须的,然而孰重孰轻,还是要看每个人的经历、性格和兴趣偏好而定。何积石先生没有机会走“西式”的学养之路,这使他的问学历程及研修兴趣几乎完全走了“中式”的杂家,也即通才之路,故而他的艺文论述不以逻辑和规整见长,而以形象和圆融取胜。这便是《印学杂咏》既能被胡先生认作“诗集”,又能被祁先生视为“学著”的原因——他不属于“专家”,而属于“文人”,《印学杂咏》展示了龚定庵所谓“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的几丝气息和某些气象。
百多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盛行,学术体制化、专业细分化和艺文市场化渐成常态,加上由来已久的教育应试化,导致知识者们的学问边界变得特别清晰,能力范围变得异常扁平。另外,百多年来至少有三段时期,古典精神被抛弃,传统艺文被冷落,通识教育被忽略,导致当代的“文人”及“业余精神”逐级削弱和逐渐淡薄。还未等人们开始反思和重审,文学已一败涂地滑向了边缘,技艺早已一往情深地归顺了市场,文学与技艺桥归桥,技术与艺术路归路。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几乎所有的知识者都“自然”地被纳入早已结构好的仿西式教育体制、学术框范、创作模式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诗、书、画、印,自然也早已开始了各归各的旅途,而“大师”的内涵和外延,便急速缩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近年来不少对“最后的国学大师”的赞美与哀叹,大概都指向了诗书画印一体化为标志的“文人”及其时代的消逝吧。的确,专家一大堆,大师没一位;业务一大摞,情怀没一丝;酸味一大碟,趣味没一点,令人不适而又无奈。这使我想起林语堂对“读书人的三境界”的描述——末等职业读书,中等业务读书,上等趣味读书,此言可资参照。尽管专家们也有创作,也在研究,也出成果,却趣味寡薄、举止呆板、面目僵硬,如果不是个性使然,则多半是因没有完全地继承了传统精神、弘扬了文人质地,无法成为一个能为芥子更能容须弥,关爱自我更能关怀社会的真正的知识者。
不过,尽管时不利兮,仍有一些当代人依然保持了这样的向往和追求,尤其是那些未受、少受西式“规训”的人。在何积石先生看来,后者的言行“反而暗示了民族文脉在历史风雨中摇曳的身影和顽强根基的珍贵”。何积石先生熟读古今印家的大著高论,发现当代印章创作者人云我云,当代印学研究者人云我云,居然也都是“各归各”。他心有所感,试图通过诗的方式、通过“文人”或“业余”的方式,去捉摸那些大著高论本身的偏颇和雅俗交叉的误区。我认为他若真的发现了某些偏颇和误区,那绝不是一个人的,而是群体的;那绝不是某阶段的,而是长时期的。我更认为这些偏颇和误区,绝非何积石先生一己之力所能纠、所能解,不过也足以令人为他感到敬佩了。
何积石先生为人谦逊,经常自称“本性痴,眼界狭,肤浅得很”,多次自谦学历不高、技艺不精。但他对诗、书、画、印集于一身的“全才”身份,却是坚持而又引以为傲的。他常说“只会诗之,不会书之”或相反,“只会画之,不会印之”或相反,对自己来说都不是完美的,尽管自己才华有限,灵感不足,对上述四门均难以登堂入室,却愿秉承初心,一路而行,所愿足矣。简而言之,即“印为风流,诗当别裁,蓦然回首,初心未改”。何积石先生虽其貌不扬、边幅不修甚至口齿不清,又心骋不羁、出言不审甚至桀骜不驯,与我理想中的古代知识者峨冠博带、风流蕴藉的形象差距甚远,却也不得不承认在他身上,确实具有某一类从更加久远而来的风骨,恰正是在当今罕有的心灵映现。我以为称他为“大才”,想必他不认可;称他为“通才”,大半他会承认。自古“大才”少幸而“通才”极多,当今“大才”无更是“通才”极少,如此评价绝非溢美,反而是客观中肯的。
诗、书、画、印,何积石先生庆幸与此四者结缘。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喜信史前文字妙,诗书画印数因缘。”他沉浸在“诗的意境,书的韵味,画的气象,印的感受”中,不断“挖掘自我,实践自我,提升自我”,这本《印学杂咏》正是他几十年求索的一个精神标识,正如他在词中所填:“临窗邀月,千秋问道,情到诗添。”这本《印学杂咏》又是他多年来寻觅的一个人际领域,正如他在诗中所写:“钝刀千载梦搜寻,太古印魂追到今。阅尽荣枯前世悟,和诗投老会知音。”所谓“知音”,可以是某一种人,与他相似的“文人”;也可以是某一种精神,即他所向往的人文精神或曰“业余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