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逃亡》(Flee,2021)凭借深刻的主题、精彩的叙事以及动画与新闻素材相结合的表现形式,获得第94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纪录长片三项大奖提名。事实上,早在《逃亡》创纪录获得众多奖项之前,已有大量利用动画来言说非虚构事件的影片上映,例如《自闭心灵》(A is for Autism,1992)、《从记忆中汲取》(Drawn from Memory,1995)、《摸索前进》(Feeling my way,1997)、《他母亲的声音》(His Mother's Voice,1997)、《天安门上太阳升》(Sunrise Over Tiananmen Square,1998)、《后座宾果》(Backseat Bingo,2003)、《瑞恩》(Ryan,2004)、《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2007)、《芝加哥10》(Chicago 10,2008)、《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绿色革命》(The Green Wave,2010)、《校塔枪击案》(Tower,2016)等。我国第一部手绘纪录片《大唐西游记》也于2007年在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上档,《我的抗战》(2010)、《我的抗战Ⅱ》(2011)、《苍狼之决战野狐岭》(2012)、《西汉帝陵》(2015)、《黄桷坪的春天》(2016)、《大唐帝陵》(2020)、《战武汉》(2021)、《用生命,守护生命》(2021)等利用动画服务于影像纪实功能的影片亦取得不俗成绩。
然而,如同硬币的两面,经由动画来言说非虚构事件的影片在获得发展与关注的同时也饱受争议,焦点在于:动画能否言说非虚构事件?纪录片能否通过动画的形式进行表现?“动画纪录片”这一提法是否成立?比如,“动画片的内容并不与现实直接相关,而是创作者通过对现实的抽象性概括与造型化的模拟呈现出的艺术形式,作品的性质自然不仅具有虚构的成分,其内在的区别与通过正常的影像拍摄所具有的特质也是显而易见的。”[1]余权、刘敬:《素材的要义——也谈“动画纪录片”的合法性》,《中国电视》2013年第5期,第58页。“以动画的形式来表现非虚构的事件,这样的做法还是会让人感到诧异,因为从逻辑上来看,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动画形式的本体是以漫画为代表的图绘造型,这类造型表现出了创作者个人对于表现对象的主观化想象,也就是意指,通过意指性的造型,观众看到的是被创造者艺术化、虚拟化了的对象,而不是可以轻易确认的对象本身。”[2]聂欣如:《“非虚构”的动画片与纪录片》,《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第79页。“一般来说,纪录片的声像内容特别强调对来自客观生活现场实地景象情态的真实记录,因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具有不容置疑的可索引性;而动画片的声像内容则主要来自艺术家的想象创作,通常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没有可索引性。这应该是纪录片与动画片最为根本的一个不同,且这种不同显而易见、难以混淆。”[3]倪祥保、陆小玲:《动画元素运用于纪录片创作初探》,《中国电视》2018年第6期,第95页。
支持用动画来言说非虚构事件的学者们认为“动画可以为我们呈现实景拍摄无法表达的方方面面:古老的历史、遥远的星球以及被遗忘的历史。动画的表现能力实际上超越了仅仅视觉化不能实拍的事件和情景,它还能够唤起我们对银幕上所看到的进行想象和思考,把所看到的动画影像与现实进行联系,激发和丰富了观众观看的体验”[4]孙红云、乔东亮:《动画现实:认识动画纪录片》,《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第86页。。“和作为符号的摄影影像一样,动画同样可以指向现实,特别是经常出现在声轨上的现场同期声,更让观众明确感知此时创作者对现实世界进行指涉的意图。”[5]王迟:《素材的含义——对动画纪录片争议的延伸思考》,《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88页。“动画纪录片并没有因其对动画的运用而失去对现实的指涉,反而因其处处逼近真实而肯定了物质现实,这是其作为纪录片身份合法性的根本确证。因此动画假定性和纪实美学并不仅仅是一组对立的关系,它们也统一于人们对逝去世界的追忆、重整、记录和还原,统一于对历史真相和现实观照的努力之中。”[6]郝帅斌:《历史题材动画纪录片的创新表达空间——以〈大唐帝陵〉为例》,《当代电视》2021年第1期,第70页。
两派观点鲜明,论证的理由与依据各不相同。那么,双方为什么争论不休?问题的关键点又在哪里?笔者试图参与到论争中,并以创作实践为基准,总结归纳非虚构内容和动画片形式重新组合所带来的艺术创新,最后基于影像艺术的创作要素以及相关理论,探究分析非虚构动画片的真实特性。
一、非虚构动画片的生成机制
非虚构动画片是“非虚构”与“动画片”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既可以理解为艺术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创作的类型或样式。从逻辑上来说,非虚构与虚构是相对应的。依据《新华词典》的解释,“虚构”指“作者不是简单地摹写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编造出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从而塑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1]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新华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09页。而“非”字在《新华字典》中有四种解释。在“非虚构”一词中,它的合理解释应该跟“是”相反,即不、不是。因此,“非虚构”是不虚构,是与虚构叙事相对立的文本类型。“非虚构”强调文本中涉及的人和事遵循“大事不虚”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也就是它的内容是可验证的,真实性是其底线和生命线。“非虚构创作本身并不是对事实的简单罗列与拼凑,而应该是作者对事实材料进行处理或艺术加工,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审美话语系统呈现事实,即以美的形式让读者在阅读社会真实的同时获得审美的艺术享受。”[2]王光利:《非虚构写作及其审美特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213页。非虚构创作最大的奥秘来源于创作者,他们认为其创作的作品内容是绝对真实的,这个“真实”不仅指事件与场景的真实,还包括他们的观点、态度、想法虽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但却是非常真实的。这种立足于艺术真实之上的“真实”,一方面能够揭示真相、还原事实;另一方面体现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理性反思的特质。动画片指“利用某种机械装置使单幅的图像连续而快速地运动起来,从而在视觉上产生运动的效果”[3][英]史蒂芬·卡瓦利耶:《世界动画史》,陈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5页。。人们谈及动画片时,往往热衷于讨论其有多“卡通”或多“逼真”。这恰好代表了动画片的两个基本方向——一边是坚持将现实艺术化,另一边则是竭力营造真实感。“现实艺术化”将动画片认定为一种夸张的虚构,其本质是一种表现艺术,创作者希望通过斑斓的色彩和另类的线条构造出另一重世界。它既可以是宫崎骏在《风之谷》(Nausica? of the Valley of the Wind,1984)里营造的风沙末日,也可以是押井守在《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2017)里建构的赛博未来。在动画的虚拟性表达中,创作主体起着主导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使动画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竭力营造的真实感”表明虽然动画的本质特性是假定性与夸张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动画就不能反映真实生活。早在九千多年前,古埃及人便试图通过壁画来记录记忆中追捕猎物的场景。我国距今五千余年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壁绘制有人形舞蹈图案,亦在描绘原始先民的生活场景。基于这点,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等艺术理论家更是将艺术的肇始归因于模仿。他们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模仿是人产生快感的源泉。原始艺术中的绘画便具有描摹并反映人类生活的特点,是在观察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再现。如今,动画在广泛的技术和风格加持下,如单帧动画、木偶动画、泥土动画、电脑动画等,显示出对现实生动、形象且逼真的还原能力。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使用CG技术制作的一系列恐龙自然史动画片,如《与恐龙同行》(Walking with Dinosaurs,1999)和《恐龙星球》(Planet Dinosaur,2011),以及我国制作的编年体史诗动画片,如《西汉帝陵》和《大唐帝陵》。
目前,“非虚构动画片”在中国学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李刚和孙玉成在《从模拟真实到追求真相:非虚构动画影片中的表现与纪录》中提到:“非虚构动画影片可以更准确地用于区别为人们所熟知的基于虚构情节的剧情动画片。这种基于创作题材的归纳很好地避免了跨领域边界模糊所导致的歧义与误解。”[1]李刚、孙玉成:《从模拟真实到追求真相:非虚构动画影片中的表现与纪录》,《电影艺术》2012年第6期,第98页。聂欣如在《“非虚构”的动画片与纪录片》中解释为:“作者创作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允许作者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2]聂欣如:《“非虚构”的动画片与纪录片》,《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第49页。冯果和吴健在《动画片中的非虚构事件——以〈我在伊朗长大〉为例》中认为非虚构动画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影片所描绘的是真实事件;二是使用动画这门媒介艺术。”[3]冯果、吴健:《动画片中的非虚构事件——以〈我在伊朗长大〉为例》,《当代电影》2017年第1期,第186页。根据上述总结,我们将非虚构动画片定义为: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使用动画的技术手段讲述非虚构的人和故事,并通过声音、色彩、剪辑等创作手法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非虚构动画片随着技术创新和动画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态势。然而,如上文所述,非虚构动画片在获得发展与掌声的同时,也饱受争议。笔者认为,非虚构同虚构是对立的,但不与任何一种讯息及其传播技术对应和对立。在非虚构动画片中,动画只是一种技术与媒介,是创作者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的“艺术再创造”。创作者对真实的坚守、对纪录精神的追求,观众对影片真实性的认可,是非虚构动画片创作的圭臬所在。在非虚构动画片中,人物、环境及事件都与现实世界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指涉现实的过程中,真实得以彰显。正如英国学者保罗·沃德所言:“动画电影为我们理解真实的现实世界提供了一条被强化了的路径。它得益于这样一种独特的辩证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关于真实人物(我们也可以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正在看的是一种动画方式的重构,它与现实并没有那种我们所熟知的索引性关联。”[4]Paul Ward, Documentary: The Margins of Reality,London: Wall flower Press, 2005, p.91.
同时,关于真实的讨论一直持续不停。一方面,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技术语境下,原本不可置疑的现场实录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数码合成技术可以把两个拍摄于不同时间的照片天衣无缝地合成在一起。譬如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中,阿甘可以与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握手。巴赞提出的只有摄影机才是唯一复原物质现实的观点被打破,电脑成为新的再现工具参与到“转录”现实的过程中[1]巴赞指出:“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令人信服的、任何绘画作品都无法具有的力量。不管我们用批判精神提出多少异议,我们不得不相信被摹写的原物是确实存在的,它是确确实实被重现出来,即被再现于时空之中的。”详见[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页。。数字语境剥夺了皮尔斯符号学所提出的影像的索引性特权[2]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分为图像符号、索引性符号和象征性符号。在皮尔斯看来,照片属于索引性符号。他写道:“照片,特别是快照,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些方面,照片与它们所代表的物体完全一样。但这种相似性是由于照片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即它们在物理上被迫与自然界逐点对应。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它们属于第二类符号,即那些通过物理连接的符号(索引性符号)。”详见Peter Wollen, Signs and Meaning in the Cinema,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13, p.103.,使得影像作为证据的资格被人怀疑。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实拍的纪录片从一开机就受制于背后的操控者,更何况在后期制作过程中还存在对素材的编排。重要的不是形象究竟是什么,而是它们为何被建构以及背后的生成机制。虽然非虚构动画片可能无法提供与过去时刻的直接联系,但它通过使用动画这种更加立体、翔实的表现手法,能够将略显苍白和简略的真实还原到观众眼前,同时在视听效果上丰富观众的感受,允许超越真人的时间和空间表达,带领观众探索过去,共享经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其之所以“叫好又叫座”,是因为捕捉到了与受众产生共鸣的本质真实,而不是做到哲学上的“绝对真实”。
非虚构动画片以真人电影无法实现的广度和深度呈现世界,从而为我们提供对现实的增强视角。生活是丰富而复杂的,其方式并不总是可以被观察到,这反映在当代非虚构动画片风格和主题的多样性中。譬如华裔导演、画家王水泊创作的自传体二维动画纪录片《天安门上太阳升》通过作者的第一人称画外音与动画相结合的方式,对同代人从“红色梦”到“美国梦”的成长历程进行回忆、反思与叙述。美国电影《芝加哥10》中法庭审判的过程由于不允许使用相机而未被记录下来。为了能够完整还原整个事件,以弥补真人影像资料的缺失,审判镜头和其他没有被拍摄记录的关键场景便依据23000页的法庭记录,以动画的方式进行重建,其音频也全由配音演员完成。BBC制作的世界上第一部恐龙自然史动画片《与恐龙同行》、我国制作的抗疫题材动画片《战武汉》《用生命,守护生命》并不存在索引性图像,而是采用动画的方式讲述自然、生物、社会生活与人文故事。通常在非虚构动画片的创作中,还存在一些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譬如在老年人谈论性生活的美国非虚构动画片《后座宾果》中,为了保护老年人的隐私,让其自由、坦率地表达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导演承诺他们不会出现在镜头里。
此外,非虚构动画片和传统纪录片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支持和补充。“纪录片提供了进入一个共同的、历史性的构架机会。与其说是(虚构)一个世界,不如说是向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个世界的机会。”[1]Bill Nichols,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p.109.而非虚构动画片呈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事件,这些人物不仅在故事里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而且可以表现出实拍拍摄不出的“抽象感情、感受、意念具体化、形象化,使爱憎、好恶、褒贬、悲喜、哀乐等情感更为浓烈,强化主题思想,使作品意境深化,产生艺术魅力”[2]王晖:《非虚构:链接于文学与影视之间》,《当代文坛》2019年第10期,第95页。。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通过实拍的方式呈现现实世界,而非虚构动画片则采用动画的创作手法,以真实事件为核心,插入直接素材,在间接的观察中,呈现出与真实相对应的现实世界。
除此之外,伴随着非虚构动画片的繁荣发展,“动画纪录片”这一表述在国内外电影论坛、学术文章和影视评论中已然出现,尤其随着大量作品的不断涌现,这一名称已经越来越通用。但“动画纪录片”与“非虚构动画片”具有明显区别。前者涉及纪录片的风格、内容、形式、技巧、手段等各个方面,且“动画纪录片”这一称谓对动画片与纪录片的定义都带来挑战,其本体和边界含糊不清,有消解艺术分类、混乱类型、混淆影像材质的倾向。而后者依托于动画的记录立场,尽管自身在纪实中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实拍影像的特别的纪实风格,兼容了档案资料、访谈、原始视频素材、新闻报道、录音等在内的创作要素,并基于真实事件进行叙事言说,拥有独特的探索精神及对社会人文的深刻表达。非虚构动画片实践着“不是使用动画来言说的纪录片,而是具有纪录精神、追求真相的非虚构动画影片”[3]李刚、孙玉成:《从模拟真实到追求真相:非虚构动画影片中的表现与纪录》,《电影艺术》2012年第6期,第97页。的创作要义。同时,非虚构动画片这一称谓避免了因纪录片的准则而引起争议,为其赢得了更加自由、艺术的发展空间。
二、非虚构动画片的表现策略
非虚构动画片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丰富多样的美学特征,以及超越单纯“转录”现实的风格。它能够以现实为底本但超越现实,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生动形象的故事叙述中揭示真相。真实声音是非虚构动画片创作的第一手资料,为影片提供了事实内容与声音证据。布莱恩·温斯顿指出:“法律上对于证据的概念对纪录片中的‘事实’十分重要……纪录片中极其重要的一项技巧的采访,也源于法律。”[4][英]布莱恩·温斯顿:《纪录片:历史与理论》,王迟等译,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第124-125页。正如证词是法庭上的证据一样,采访也成为非虚构动画片的证据。采访弥补了非索引性影像所遗留的空隙,受访者的身份得到保护,使得访谈较为轻松且自由,观众听到的是一次真实的互动记录。《逃亡》中的主人公——受访者阿明是一位从阿富汗逃难到丹麦的难民,影片由他的自述展开。随着导演与阿明谈话的深入,画面出现相应的动画场景:阿明童年的花园、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街头、导演回忆两人在高中校车上的初遇……通过两人的互动交谈,结合相关的动画场景,观众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令人心碎的难民逃亡细节。《校塔枪击案》以当事人的故事叙述为牵引,匹配相应的动画与资料影像,梳理出令人揪心的案发全过程。该片精准刻画出了枪击案现场的恐惧氛围,当事人的口述使影片本身更具可信度,让观众能够更真实地了解这个发生于50年前的枪击案。
声音不仅指向现实、交代内容,还担负着引导动画创作的任务。合适的听觉效果可以帮助观众理解那些看似非写实、有些又较为抽象的动画。《与巴什尔跳华尔兹》采用古典音乐、老式摇滚乐和爵士乐等多种音乐形式。片中的华尔兹曲被赋予强烈的仪式感。当一群士兵被围困在战壕内,从多个角度受到攻击之时,年轻的士兵弗兰克如神灵附体般跳出战壕,伴着“华尔兹”乐曲举枪疯狂向敌人、空中射击,姿势宛若在跳华尔兹舞。背景音乐和画面的结合,使“华尔兹”舞曲俨然成为生命的舞曲。该段落通过华尔兹舞曲的使用,既点明了片名,又渲染了悲壮的气氛,同时强调出对时间感知的主观性,展现出战争的残酷与记忆的混乱。《他母亲的声音》根据采访的声音记录,匹配相应的动画来表现一位母亲叙述儿子遇害的过程。影片通过声音为图像提供引导、渲染情绪,深刻地展示出这位母亲的丧子之痛。
非虚构动画片中的色彩会影响受众的情绪和感受,色调的变化可以传达出特定的视觉语言。《校塔枪击案》中的动画分为黑白和彩色两种,案发当时为黑白,其他时间为彩色。当克莱尔与男朋友在餐厅用餐时,画面是鲜艳的颜色。两人从彩色餐厅走出时,克莱尔与男友还是彩色,而远景中的校塔则为黑白色。随着一声枪响,画面充满红色,两人的身形变为白色剪影。随后,整个画面由彩色转变为黑白。红色底色铺满画面,象征鲜血和犯罪,与白色剪影形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震撼着观众的视觉神经。创作者以看似夸张的动画表现受害者的痛苦和凶手的残忍。整部影片中校园枪击案现场均为黑白色,案发外场景则为彩色。案发现场内有特殊意味的元素也被渲染成彩色。比如当一位名叫丽塔的女孩奋不顾身地跑去陪伴受枪伤倒地的克莱尔时,女孩的头发是红色的。影片把女孩的头发制作成红色,在黑白画面中显得亮眼但不突兀。这除却是丽塔的体貌特征信息外,也象征着克莱尔虽处于危险境地,但仍然拥有生机和希望。

图1 电影《我在伊朗长大》海报
《我在伊朗长大》是导演玛嘉·莎塔琵回忆录性质的自传式非虚构动画片,黑、白、灰为主色调的画面色彩组成了剧情表达的基本形式。这部非虚构动画片通过色彩的表达,至少营造出三套各自独立的“能指系统”。首先是电影语言的能指,即现实生活的直陈。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机场片段呈现的都是现实生活。在黑色、灰色、白色的大基调下,辅以绿色、蓝色、红色等简要色块,展现出现实世界相对明亮的调性。其次是回忆性能指系列,即针对时空的插叙与倒叙。该片的大部分片段都是导演玛嘉的回忆性叙事,在个人的追忆性旁白中,匹配相应的动画场景(以黑、白、灰色块为主),旨在表现灰暗、低沉的记忆时空。第三种是影片中意指社会、历史、文化对象的视听记号。该部分导演通过转述叔叔、爸爸等人的言语,同时穿插个人幻想,并以黑白为主色调进行动画呈现,旨在表现玛嘉看似道听途说的主观真实场景。该片将黑色、白色和灰色的色彩属性与精神意指运用到极致,真实、生动、形象地揭露出导演本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录、回忆和反思。
剪辑能够增强非虚构动画片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德国美学家鲁道夫·爱因汉姆提出:“任何一个镜头段落都应该有一个鲜明的运动格式:或者是一景接一景地增加速度,造成紧张的节奏;或者是有控制的快慢交错,从而创造出一定的节奏。”[1][德]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杨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第153页。例如,《校塔枪击案》中,剪辑与声画就做到了完美配合。在枪击案的开头段落,创作者以摇滚乐作背景,通过高频率剪辑的方式,使红色底色、白色剪影接连出现,以此表现受害人相继被击中的场景。该段落中人物奔跑、中弹画面、枪声、玻璃破碎声、救护车鸣笛声,穿插实拍的诸如带有弹孔的玻璃、受伤者接受采访、救护伤员等场景。同时,采用晃动镜头、高速横移镜头、降格镜头,表现出案发现场的混乱与危险,冲刷出痛击与求生的小高潮。再如,影片《与巴什尔跳华尔兹》开场便出现一群恶犬急速奔跑的场景,在高剪辑率的镜头切换中,画面中的角色快速奔跑。猎犬凶狠的表情、四肢肌肉的张弛、呼喘狂吠等动作,将观众带入到战争的紧张氛围中。同时,在加速、减速、停顿等节奏变化下,视觉画面得到丰富,可看性与趣味性得以增强。
三、非虚构动画片的真实特性
非虚构动画片总是比实拍影像更具想象性和个人意识,但其并没有伪造索引性,相反,它使用动画的方式将情节和细节呈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代影像,成为一个无形的物理存在,向观众展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获取事件信息的方法。非虚构动画片确证了“在动画的语境中,‘事实’可能不会被看作是对现实的客观记录,但可以成为建构‘真实’的质证”[1][美]保罗·威尔斯:《美丽的村庄与真实的村庄——关于动画与纪录片美学的思考》,李晨曦、孙红云译,《世界电影》2015年第1期,第161页。。(一)展现人物的精神状态
非虚构动画片能够展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其创作宗旨不是通过动画图像实现逼真的美学,而是将动画用于不同的目的,揭示复杂、混沌、凌乱,有时又总是相互冲突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能够凸显人类的精神状况。在精神状态的呈现中,非虚构动画片特有的“解释能力”被充分挖掘出来,使得创作者能够深入研究一个本质不一定在可见范围内但却得以达到顶峰的现实。英国著名动画制作人约翰·哈拉斯提到:“动画可以渗透到身体和机器的内部,展示其内部的运作,包括另外一些复杂的内心动态(梦境、回忆、知觉、狂想),并且作出一板一眼的或概念性的解释,使得被解释的东西更容易理解。”[2]转引自[英]吉尔·内尔姆斯主编:《电影研究导论》,李小刚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245页。而正是这种揭示功能,让非虚构动画片的创作朝着揭露真相的方向发展,为非虚构动画片赋予一种纪录精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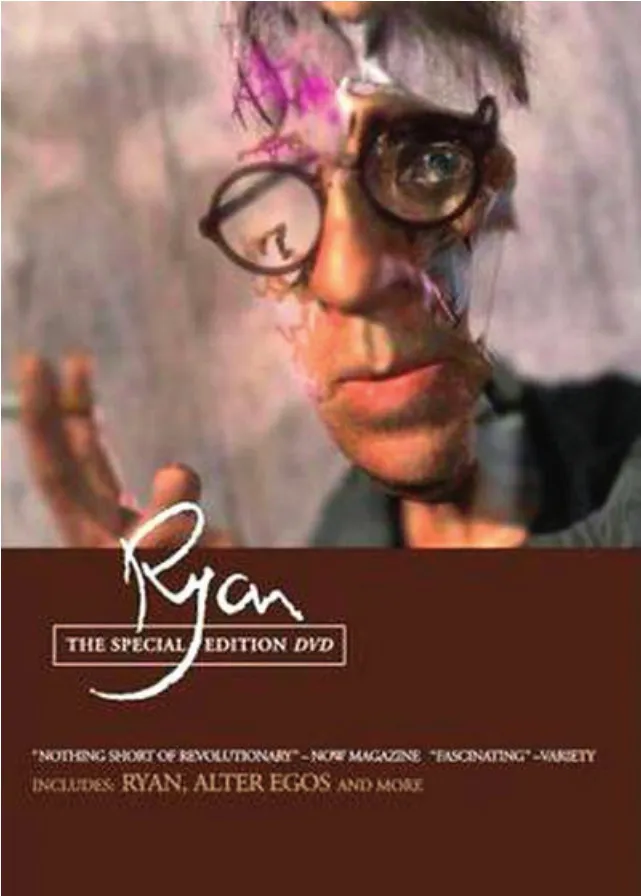
图2 电影《瑞恩》海报
由克里斯·兰德雷斯执导的心理现实主义影片《瑞恩》记录了加拿大著名动画师瑞恩·拉金在经历工作和生活的苦难后一蹶不振、沦落街头、成为乞丐的故事。同为电影工作者的兰德雷斯不忍瑞恩走向堕落,决心拍摄一部非虚构动画片,一方面记录命运的离奇悲歌,另一方面劝说这位落魄大师重新出山。影片中的主人公依据人物原型创作而成,他只有一只眼睛,瘦骨嶙峋、面目狰狞,以此凸显瑞恩糟糕的身体状况和凋敝的精神世界。在兰德雷斯和瑞恩关于酗酒一事的讨论中,兰德雷斯希望瑞恩戒酒,以期其能够更好地进行创作,但瑞恩却并不认同。随着两人矛盾升级,瑞恩的愤怒表现为一系列尖锐的红色尖刺,从他的头上冒出来,随后身材前倾,冲着兰德雷斯大声吼叫,以至于头发直接从头上掉下来。如此夸张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瑞恩当时的不满情绪。亦如导演所言:“就《瑞恩》来说,我认为动画就是捕捉真实的生活、现实。它能够(至少我希望如此)提炼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并将其转化成一种超乎寻常的、离奇的东西。”[1]Judith Kriger, Animated Realism: A Behind The Scenes Look at the Animated Documentary Genre.New York:Focal Press, 2011, pp.139-140.影片《自闭心灵》揭开了自闭症患者的心灵世界。影片中的每一张画作都由自闭症患者创作而成,旁白由一小部分能够讲述自己想法和感受的自闭症患者叙述。动画在片中作为一种工具手段,与自闭症患者创作的画作结合起来,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所描绘和叙述的经历。影片《摸索前进》通过镜头移动、画面拼贴和手绘图案等方式,带领观众体验都市生活的琐碎,展示出导演的情绪与感受。
(二)唤起内心真实记忆
除了展现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外,非虚构动画片还能够唤起真实的记忆,进入人类的内心世界。动画的这一功能可以展现非虚构主体所经历的现实,往往与大多数实景拍摄所能得到的素材完全不同,它能够用来解释没有严格意义上记录的现实,将生活中看不见的方面以抽象或象征的方式形象化,使观众能够从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促进观众对可能远离其自身的主体产生认识、理解和同情。影片《逃亡》通过阿明的自我叙述,将观众带入20世纪80年代阿明在阿富汗的童年生活,记忆由此展开。当他穿着妹妹的睡衣、听着音乐在喀布尔街头奔跑跳跃时,自由欢畅的氛围洋溢在整个画面中。之后,阿明的故事开始变得悲伤和支离破碎,他的记忆被伤痛所掩盖——一个妹妹被绑架,父亲、母亲和兄弟被杀害。随着采访的深入,阿明对过去回忆得越来越深。当他开始谈论一些感觉非常痛苦的事情时,或者是他自己没有看到而只是想象到的场景时,观众可以听到他讲述的语速变慢,词语之间存在较长停顿。比如当他的父亲被带走时,或者姐姐们在船上的集装箱里时,阿明不在现场,所以不能告诉观众事情的确切情况,但他的恐惧感是存在的。在极端创伤的时刻,即阿明不能或不愿意回忆的时刻,动画变得几乎是抽象的——污浊的黑白炭笔画,人物奔跑、儿童尖叫……动画用一种比阿明经历更诚实的方式讲述故事,将实拍影像难以描述的情节出色地还原出来。这种动画形式给纪实事件涂上了虚构的色彩,其中夹杂着阿明主观的回忆视角,竟带来意想不到的沉浸感,使这个从阿富汗到俄罗斯,中转爱沙尼亚,最后曲折抵达丹麦的偷渡故事焕发出极其强烈的感染力。正是通过动画这一层和真实之间的“安全垫”,将本不可能被讲述出来的故事还原出来,也让观众相信他们看到的是客观与深层次的东西。
“我的抗战”系列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Ⅱ》)以1931年至1945年的抗战历史为基底,以抗战亲历者为叙述人,通过他们的回忆性口述,将观众带入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找寻湮没于时间黑洞中的历史。影片在朴素的木刻版画、丰富的色彩、节奏紧凑的配乐和口述史的共同配合下,不断探寻着老兵们的抗战印记,“实现了个人生命史与时代背景、社会结构的结合,展示了特殊历史阶段中历史及人性的丰富与张力”[1]王宇英:《影像记忆:口述历史的介入与超越——崔永元〈我的抗战〉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8期,第85页。,让只属于个人的生命故事一次次地引起观众的认知与理解。影片以动画作为技术媒介和叙事手法,表现人物、反映心境、演绎史实,在凝重的抗战历史回忆中寻找生动的生命轨迹,提供了私人影像的表达空间,填补了历史记忆的空白,给予观众前所未有的观看体验。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记忆并不是将无数固定的、了无生气的、零碎的痕迹重新激发出来。它是富有想象力的重构或建构,基于我们对一整套系统有序的过往反应或经验的态度之上。”[2][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2页。经由非虚构动画片,被遗忘、令人困惑且通常是记忆碎片的过去世界被探索出来。
(三)揭示现实世界的奇观性与多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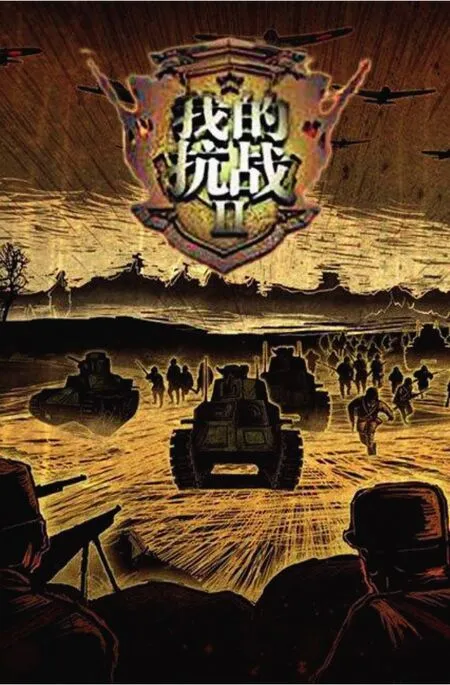
图3 电影《我的抗战Ⅱ》海报
非虚构动画片能够呈现表象与意义、景观与知识、幻想与真实性之间的张力,使得存在与发生不再有赖于空间的物理性。世界的多样性和奇观性通过动画的方式得以显现。这样的呈现使得非虚构动画片具有了认识论的潜力,促使其在景观、视觉享受和对知识的渴望之间建立联系。动画的使用为非虚构影像的视觉表达带来高度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将非真实带入真实的世界。创作者难以用实拍表达的诸如内心独白、精神状态、思想观念、个人情感等场景通过动画得以展现,使得奇观再现成为可能。法国理论家居伊·德波提出“景观社会”这一概念,即“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3][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鲍德里亚称之为“拟象”。他说:“在这种拟象中,所丧失的是全部的形而上学。不再有存在和表象的镜像,不再有现实和现实的概念的镜像。”[1]A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2.在非虚构动画片中,现实的物质王国转变为动画世界。此间的“物质王国”并不指如实拍般的索引性图像,而是指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图像化”[2]海德格尔指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详见[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86页。。经由动画的艺术表达,真实由浅表抵至内里。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且这种意义是对话的,它不仅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对话,也是观众与作品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世界相互渗透的双重过程”[3][法]埃德加·莫兰:《电影或想象的人:社会人类学评论》,马胜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
此外,多义性和奇观性的起源就在于人类进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世界后,精神世界的滥觞、世界统一的丧失。这种丧失表现出当今社会人类要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们成为思想独立体,变为一个个碎片而存在。非虚构动画片采用后现代主义的一般特征,优先模仿,拒绝客观权威的概念,因此“真实”是碎片化的和不连贯的。正如罗拉所言:“我认为现在非虚构电影中的主观性,是人类经验在后现代和全球化的世界里日益碎片化的反映和后果,以及我们设法反映和应对这一碎片化的需求和欲望。”[4][意]罗拉·拉斯卡罗利:《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洪家春、吴丹、马然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9页。非虚构动画片可以被看作是通过唤起个人记忆、探索和创造“另类档案”的方式和干预官方历史的一种手段,是重新塑造过去的方式,一种自下而上讲述历史而不是自上而下接受历史的方式。非虚构动画片在“动画魔法”的加持下能够质疑以往呈现的真实,重新解释真实,告诉人们对真实存在不同的看待方式。因此,非虚构动画片有可能成为重新诠释我们对社会、历史和世界认知的有力工具。譬如《与巴什尔跳华尔兹》可以以一种表演性和表达性的方式参与个人和集体记忆,绕过官方、书面历史的限制。正如导演福尔曼所言:“我想把大家带到我的梦幻旅行当中,但却不是我随心所欲想去的地方。首先,因为之前我做了许多资料搜集工作,如果将我自己的经历和我所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人的经历相比,我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幸运儿了,我在影片中看到的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直接目睹大屠杀,但是这些日子即便我只是看到和经历了很小的一部分,关于战争的残酷性并没有改变。”[5]转引自王庆福:《也谈动画纪录片:真实在什么前提下可以被保证》,《中国电视》2011年第1期,第80页。
(四)呈现陌生感
非虚构动画片的真实性还源于影像与所表达的现实世界具有一定的陌生感。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6][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6-7页。非虚构动画片中的影像大部分是完全建构的,并不存在对表象世界的捕捉,与实景拍摄的纪录片具有一定的距离。观众在观看非虚构动画片的过程中,需要将动画图像转换成熟悉理解的视觉信息。在转化的过程中,陌生感得以生发。非虚构动画片的一大特点在于影片含有真实的声音,甚至影像。真实的声音、确凿的影像与虚构的动画之间形成矛盾的新奇感,能够防止观众趋向画面同质化,使他们增加批判性的思考。当观众领悟作品的意指性灵韵时,非虚构动画片立足于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因果逻辑铺展开来,非虚构动画片的陌生感即由此而来。从本质上讲,非虚构动画片是在动画虚拟的表象下揭露出真实的内核,而正是这一虚拟化过程,拉开了观者与影片之间的距离,使观众在时间、空间和剧情上都有“脱节”之感。而这种感觉带给人们的差异化体验,正是艺术的超越现实之处。四、结语
非虚构动画片从生活中选择可以讲述的故事,以动画的艺术形式和个体性的视觉方式进行逼真展示,艺术性在选择与结构的真实中得以呈现。非虚构动画片在实拍影像和虚拟世界间找到了平衡的罅隙,不管是采用夸张、变形或神似的手法,还是延宕某个采访中的情绪过程,其都是对历史的影像化表述,是一种力求生动的非虚构叙事。同时,非虚构动画片需要创作者“个体体验”的介入,“去发现、质疑、品味、探索、观察、交流、好奇,最重要的是思考”[1][美]雪莉·艾利斯编:《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刁克利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7页。。经由非虚构动画片,个人的视点、情绪、精神状态以及碎片化的记忆得以强化,呈现出在深度和广度上实拍所达不到的“这个世界”的经验表达。虽然非虚构动画片在纪实方面存有缺陷,但其在表现真实方面的探索实践值得业界去思考和探讨。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动画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发展、艺术观念的变化革新、优秀作品的不断涌现,非虚构动画片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2]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动漫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动画纪录片及其美学特征研究”(项目编号:DM20224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