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深处的忧郁
——读燕赵齐霁诗集《凡响·启蒙诗篇》
□徐敬亚
那一瞬我一定是某部分魂儿出了窍。我推开高楼大厦,分开众人,在字缝人丛中一眼就认出了那张忧郁的脸——是那张哀伤的嘴脸使我对一座城市忽然产生了畏意。突然来临的、仿佛能噎住喉咙的凝重,竟降临在轻松的酒席。几分钟内,我会见了无数游走幽灵。我突然发现:在我多年熟悉的城市中,竟深藏着一本沉重的诗集,藏着一位哀伤的诗人,藏着一股凌驾于世俗时空之上的宿命咒语。
我说的——城,是深圳。诗,是《凡响·启蒙诗篇》。人,是燕赵齐霁。
2010年夏天,在深圳特区报乘长风餐厅。正当酒席乘风驭浪之际,我却莫名地翻开了这本诗集——它页码很薄,像个穷人。它装祯黑白分明,像个法官。它无序无跋,除了诗不多余一个汉字,像街上走过一个自言自语的乞丐。
那是一次神奇的阅读。只略略几眼,读得我心惊肉跳。在这个轻浮的城市里,还有如此横枪立马之人吗?我合上诗集,像关闭了字字霹雳。重新回到酒宴,心还停在那些匆匆的字上,听着人世红尘谈话,像一个心怀鬼胎的潜伏者。
越是匆匆一瞥,越能一眼识出远近疏离。越是不经意偷窥,越让人莫测背后暗藏的杀机。对于某些诗人、某些诗,说出一瞬间感觉其实已经说出了作为词语同谋者的全部。
忧郁,人类内心永远无法抚平的精神丝绸
文明史上,几乎没有一处山川被人类这么飞快地堆满了连天的沙石砖瓦。30年,这座城市制造楼房的速度比神的降临还要快。繁华与财富早已成为它暗中的代名。它的写字间办公室里坐满了意气洋洋自若的人。30年,它从渔村跃升为中国财富金字塔最尖利的部分。它的上空飘荡着堂而皇之的旋律。它的印刷机上写满了好词好句。然而,诗人往往选择与财富相反的方向,与感觉良好相反的方向——他并没有仇恨,他只是满怀忧郁,只是向一种“快马跑成骷骨”的速度与“唯我独尊”的模式提出置疑:当水泥变得坚硬当坚硬变得愚蠢当愚蠢唯我独尊
当大海成为墙壁当道路成为阻碍当神明不再
当灵魂冒烟当灵魂被点燃当灵魂学会尖叫
当你我成为看客当看客背对窗子当窗子已经堵死
当水泥四分五裂当云层纷纷剥落当快马跑成骷骨
当我没有来过当我没有看过当我没有说过吧
——《忏悔十:封建的水泥》
以“神明不再”为由,对现实发出哀怨,对理想国予以呼唤,这是古今诗人们一贯的套路与手法。这种悲悯的情怀显然不符合高歌猛进者们的视角。有钱势的人总是祈祷神灵护佑人间繁华,但是谁能永葆富足呢。就连神也不能确定每一瞬间都是快乐的。堆积财富的动作不管多么优雅,良苦用心的背后,怎么能不隐藏人类贪婪的嘴脸和耿耿内心。那正是人类忧郁的根源。
真正的诗人都是忧郁的,甚至是全面悲观。他们太了解文明强大的惯性和力量,也太了解自我的渺小。因此他们太知道理想与信念在现实的失败必将多么必然。于是诗人便自我品尝更大的精神痛苦,于是燕赵齐霁仿佛预占山头一样主动交待般地抢先说:当我没有来过当我没有看过当我没有说过吧……
忧郁并不是诗人的专属品。尘世间也会有世俗的忧愁与哀伤,但这些纠结的精神迷津,不但具体,而且临时。正如病,病因清晰,对症下药,常人的精神伤痛总会结痂总会痊愈。而到了诗人这儿,情况严重得多:
啊,我的哀歌,在人间寻找错误
有些错误是原创,有些错误是摹仿
——《哀歌二十二》
我的同胞沉迷于人前的虚假
或者直奔金钱和荣誉的
昏头胀脑的忙碌之中
——《哀歌十》
当诗人将自己忧愤的标的物指认为“人间”与“同胞”时,他的忧伤显然超越了个人生存的私怨而进入了伦理与社会学范畴。而当思想与理性又时时提醒出绝望结局时,他的忧伤便进入了古老思想史的悲剧行列。几千年来,与文明对抗的思想似乎都闪着光,但人们却忽略了这光芒最初刺伤的却必定是发出光芒者本身。启蒙者的精神与肉体关系往往尴尬:他的思想代替着整个人类良知承受光荣,而他的肉身却时刻代替灵魂蒙难。再光荣的苦难也不会令人愉悦。再深沉的忧郁也绝不快乐。人类心中那块永难抚平的精神丝绸不停地疼痛起伏,摧毁过多少优秀诗人、智者的美好生活与平凡肉身。
我们是当代的老蜜蜂酿造狗日的苦水
我听到了大慈大悲的菩萨说
他们虽然不幸却习惯了不幸
——《哀歌十二》
从自己身上找不到罪过
这就是一种罪过
——《哀歌十五》
诗,一定是一个阴暗的咒语。诗人不但总能在生存中找到悲伤的理由,更善于给任何幸福生活披上一层忧郁外衣。“虽然不幸却习惯了不幸……找不到罪过就是一种罪过”——天啊,以此之眼看来,世上还有幸福,红尘还存欢乐吗?这,已经不是思想,而是一种诅咒、一类宿命、一项悖论。与其说诗人借菩萨之口道出箴言,勿宁说是内心永无安宁的诗人向世界发出的自白、困惑与哀叹。
写诗,是一种可怕的习惯。诗人是一个积郁难返的角色。
世俗的欢乐,常常变得遥远而浅薄——更准确地说,致命的不是遥远,而是浅薄,是自己也无法逃离的、自我鉴定式的浅薄。那些世人们完全可以忽略与忍受的人类过错,以一种不可饶恕的方式折磨着诗人。是谁给了诗人以先知与受难者的双重权力,谁就同时赋予了他永无安宁的内心苦难。一整套贯穿生命的不愉快通道,就是这样被安装在诗人的生命直觉系统。他先是用忧郁折磨自己,然后用忧郁的诗折磨全世界。他的忧郁由于没有理由,因此没有起点。由于没有方向,所以也消失了终点。像每天含着一枚纯白苦涩的茶碱片,他煞有介事地代表着全人类在纯白色的精神疼痛中日夜翻滚,并煞有介事地写书以宣示后人。
忧郁,深圳白领刚刚学会的烦恼
对于诗人与国家的关系,于坚有一个漂亮表述:“在我们的时代,诗人由于被市场社会放逐而成为一种国家污点。”在我看,这一恶毒命名,显然属于诗歌圈子内部的一种自我嘲讽。但它却无奈地正视了诗人社会地位的窘迫。诗人之所以成为工商秩序中不受欢迎者,不是由于他们不聪明,而恰恰过于聪明。对诗的过度沉溺而带来的工作消怠,使他们至少成为国家劳动效率领域的间谍。没有人怀疑诗人的智慧,人们怀疑的是他们智慧的箭头方向。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虽然一批又一批诗人惨遭上司白眼并由此颠沛流离的故事此起彼伏,但诗人离经叛道的传说却从未停止。其实,准确地说,早在他们被工商社会放逐之前,诗人早已在内心里自我放逐。显然,燕赵齐霁不属于那些装疯卖傻的流浪诗人。他在一座忙碌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角色中,把自己隐藏得很好,很安稳。但他的诗,还是泄露了这个深圳白领内心的隐秘:
呵白领,从他们走路的姿势我就知道
他们在鸟瞰这个世界的时候驼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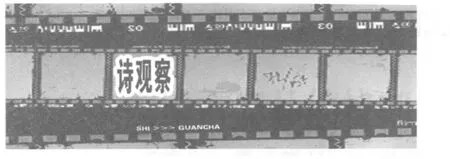
请把白领写进小说吧
他们除了上班这点事还有什么事
——《哀歌十一》
在为白领书写日常生活自白时,燕赵齐霁使用了一个漂亮而虚幻的肢体姿势——因过于频繁鸟瞰世界而几乎致残——“鸟瞰”与“驼背”的对比,勾画了白领心怀天下却又佝偻负重的劳累窘像。后两行,看似纯口语白话,却诗意盎然。辛酸戏谑中充满了一个文学先知对白领生活的自我蔑视。
“白领”,作为具有知识背景的脑力劳动阶层,在中国尚属新潮生活形态概念。在我看,白领是现代社会中最承重的群体,也是一个最躁动、分裂的群体。几乎每一天,都有向上与向下这两股方向完全相反的力,在暗中撕扯着这一表面稳定的人群。白领阶层无疑最具野心。年龄与学识的双重优势,使他们中未来工商领袖的因子力在不断涌动、攀爬。而作为现代消费意识最强、职场消耗却最大的青春部落,白领阶层也是消积怠工、应付了事、内心波动失衡的代名词。在经过了人口迁移后的短暂得意之后,深圳白领终于学会了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不尽烦恼。
细心品读燕赵齐霁的诗,我同时在定位深圳白领的生活经纬。在这位比一般白领严重忧伤的诗人作品中,我读出了两个刺眼的名词:“房奴”与“纸匠”。
四季的回廊里,为了金钱
让我放慢脂肪的燃烧,我是一个纸作的房奴
有木柴有火焰。我欲望的骨骼已经倾斜在金钱余晖中
……
我们成了金钱的苦役犯……我的灵魂
在一场商业炒作中被自己低价卖掉
——《忏悔三:房奴》
房奴,这是白领在国家金融体系内的另一个银行代号。由于无法克制的生活需求与尊严欲望,他们提前预支了晚年的空间幸福,以出卖人生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报酬为时间代价,成为了自己生命债权的人质。在房奴遍地的今天,燕赵齐霁这段饱含辛酸意象的诗句,说出了多少青春公众的半世辛酸:四季回廊……金钱……燃烧的脂肪……纸作的房奴……木柴……火焰……欲望骨骼……金钱余晖……苦役犯,那不是诗化的意象,那是千千万万人的呻吟。而最精彩的、我更看重的,是他对职场的身份剖析,那是中国当代少见的、有廉耻感的自我认定——燕赵齐霁对纸人的自杀式剖析,是这部诗集中最高贵、稀有、独价的部分:
我内心穿着苦役犯的囚衣,坐两平米的格子
让我的思维站好角度,我与纸约定了今生
……我穿过夏天,我出汗,我被空调降温
我喝着茶,我把报纸编排,纸媒呻吟的年代
我有纸的脆弱和柔韧的性格
……我是疼痛的纸
我被……投入造纸厂火碱池,带着所有人的口水
和这个时代丑恶的眼神
——《忏悔一:纸》
纸匠,这是我的偶然命名。中国自古有木匠、铁匠、皮匠。他们并非造木造铁造皮者,只是削柴锻金革毛,即以其为原料或道具显示技艺的匠人:“我活在水泥里却像一根儿脆弱的芦苇/我活在语言里却像一堆没用的纸屑”。于是我把写字为生的人称为纸匠。
进行简化推导吧——以纸为生,即以字为生。以字为生,即以话为生。以话为生,即以心为生。以心为生,即以真为生——以真为生,呜呼,岂不即以痛苦为生以口水为生以白眼为生!
至此,燕赵齐霁的第一类忧郁已真相大白。职场的四季,到处都是文学的疼痛——表面明亮、温暖、豪华而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每天都暗中挥舞着阳光般的屠刀,无情切割着一个白领的血肉与心灵。他的忧郁,怎么可能仅仅是代替人类蒙难,怎么可能是艺人们装出来的矫情。
忧郁,比哭泣更平静更持久更阴暗
像一滴混浊的眼泪,燕赵齐霁把他和他的诗深含在深圳高楼大厦阴沉的眼框中。我曾在中国北方民间
逃离,又从南方民间浮现
——《哀歌十五》
我的过去是石头,我的未来是废墟
——《忏悔四:顺从的水泥》
是什么给了诗人如此幽暗的口气与险恶词语。仿佛一束寒冷追光,把他捕获的全部词语粉刷了一层不安气息。在燕赵齐霁另一些诗中,我读到了比哭泣更悲伤更持久的沉郁。它,不是白领无奈的现代迷津,而是那沉重得无法逃脱的个人记忆。是的,是那些由持久的日常经验所积累出来的记忆,一切根源正是那永无法抹去的历史。
说到历史、记忆,我要议论几十字的黄昏。
直到这些年,也就是说直到晚年,我才懂得黄昏是一件无比漫长的事。2005年夏天在呼伦贝尔,我一分一秒地眼看着天空缓慢地变黑,看着白昼一点点地被黑夜绞杀,足足历时六、七个小时。相似的是,历史事件之退出舞台,正如这幕自然界背景更换一样柔韧漫远。任何一个残酷事件的结束,仅仅表明它再不能发展。而对于苦难,其实它才刚刚诞生。最容易被史学家们忽略的是,苦难一旦停止,仅仅意味着它立即成为当事者痛苦记忆的开端,刚刚成为后世永恒追讨的命题。
我注意到,饱尝记忆之痛的燕赵齐霁,在诗中多次提及他死灰色的童年:
我暗淡的童年的围栏是连绵的山,石头嶙峋
如鸡骨的柴扉,那些饿殍在原野间穿行
……口吃的蟋蟀或者朗诵的纺织娘
潜藏在以水泥花朵崛起的城市
——《哀歌四》
一种廉价在喧哗里放歌。几十年前
童年的背上烙下的贫瘠,是乾坤
在扭转时间。萝卜、白菜还有豆荚的成长
——《哀歌五》
我苦涩的童年穿不破雨幕,瓜棚外的蛙鸣
两只被撕掉翅膀的蜻蜓,心愿的爬行
让我想起十里铺夏天的无助
——《哀歌七》
对于童年,燕赵齐霁的诗中的名言是:“人生最好的典藏应从童年开始”。可惜,这个“出生的一刻就有一个问题要问”的敏感诗人记忆中有太多悲伤、愤慨。过去,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才对往事耿耿于怀,我惊奇燕赵齐霁竟也对那些陈年往事忧心忡忡。他写顾准,写林昭,写钱老爷子……我忽然觉得他得了病,我们民族得过病。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种族,恶毒的记忆永不会消失,它早已化为内心淤伤。在潜意识范畴,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每一个日常经验。而从心理学角度,凡属不能化解的刻痕,都属心理毒瘤,它阻挡营养,任何新鲜感觉无不接受着它的浸袭而使人反常不宁。
然而,下一代人的愤怒毕竟已经转化。诞生几十年的燕赵齐霁可能已经愤怒了几十年,他反倒以一种极平静口吻,叙述离他那么遥远的无可奈何故事。越平静,越无可奈何:
中原上没有人在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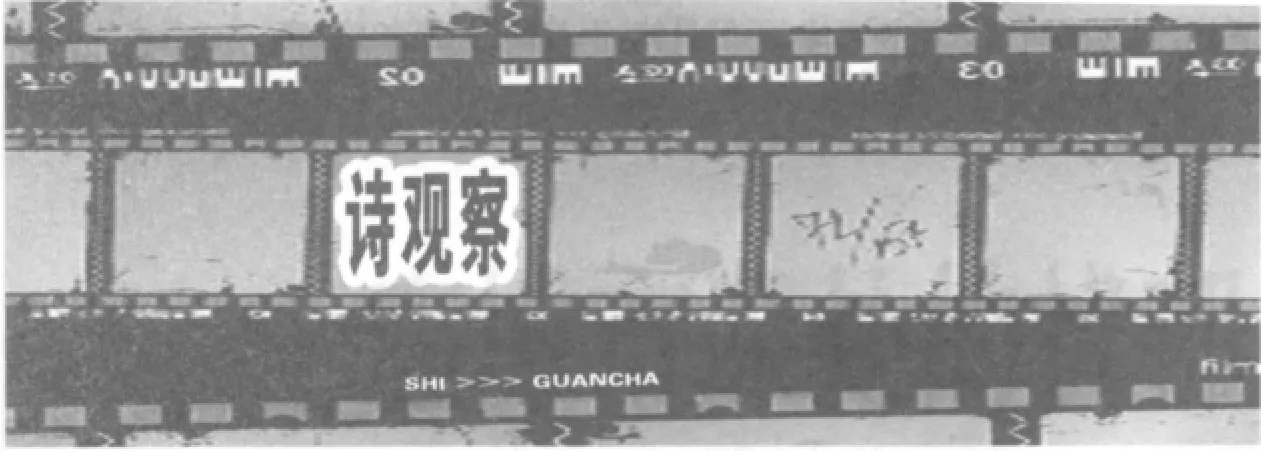
中原上找不到顾准的家
十月菜地落下白霜
星星长出了青色火苗
顾准在浇水站岗和发烧
——《怀顾准之一》
平静。死一样荒凉。没有。没有。有的只是白霜、青火。
发烧,仅仅两个字,立刻把站岗与浇水变成炼狱,把中原烧成一片大火。
他写林昭的死,写得轻盈、灵巧。用快马、黎明、铁窗、子弹等精确流转的意象,完成了一次无可挽回的跨时空追悼。
乘着快马我想逆时间而上
要在黎明前敲响她的铁窗
但我没有子弹那么快
子弹已经穿过了她的胸膛
——《念林昭之五》
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早已从容地清洗了无法遮掩的血痕。而往事残淡的余光却在一个几乎与它无关的后生身上回光返照。只是这种回光以一种自我戕害的精神方式映射。这回忆,注定无法平衡,其结局只能是一个人饱受灵魂的每天煎熬。诗人的忧郁显然已超越了个人恩怨,成为种族内悲的抽搐。虽然,这种艺术悲情充满了灰暗,甚至不乏恶毒,但诗歌之箭却总是没有固定的靶向,哪怕它与某些政治家道德家们恰巧站在了一边。
我无法更深入地评价往是与今非,我只是为诗中那些迟受追悼的受难者感叹与庆幸。当历史的债务不能支付现金时,它会以一种折磨后世的方式,为当年不屈的血液支付无尽的利息。
当忧郁大于技巧
对一部忧郁诗集进行技巧性评头品足,是不人道的。这正如对一位无声哭泣者的姿势进行舞美评估或对其眼泪进行无聊的化学分析。在这部诗集的封面,作者不是已经书写了“凡响”与“启蒙”两个巨大的词语吗。对此我还能有什么细话可说。且诗人在署名处印上了“燕赵齐霁”四个大字,这更使我陡增了莫名悲愤。燕赵,那不是古老的中原大部疆土吗。那不是壮士一去不返之岸吗,那不是产生由于愤怒而把眼框瞪裂者的山河吗。
我个人一贯倾心于宏大的人文情怀,一贯赞赏诗人的情绪力度与理性宽度。燕赵齐霁的诗显然归属于此种雄性意识。史诗般的从容、开阔、简炼:
北天有云,南天有雨,人民在炼钢
北天有云,南天有雨,人民在逃荒
……
人民在哪里?人民没回答
人民在哪里?人民各自忙
——《人民在哪里》
任何诗人作品,都是包含多种手法的复方制剂。燕赵齐霁之武库亦是十八多般。如:“四季的回廊里,让我放慢脂肪的燃烧”。脂肪怎样燃烧?那燃烧又怎样自我调控怎样放慢?如:“欲望的骨骼倾斜在金钱余晖”……这些具备了西方批评模式观照的复杂手法,在本部诗集中并不多见,它们不是燕赵齐霁的主要美学手段。他更善于用沉重的句子击打读者,或者说击打自己。
于是,我只负责认定它的忧郁。
他,是本时代越来越稀少的知耻者。也许是童年的贫困经历与记忆拯救了他。也许是遥远时代的蒙昧与耻辱激怒了他。也许是现代社会道貌岸然的异化与无奈暗中戏弄了他。这一切,使《凡响·启蒙诗篇》的内在美学原则具有浓重悲剧成份。这悲剧超越了个人命运,它更多属于公众全民,甚至全种族。雄浑而略显粗糙的诗歌操作,恰暗中吻合了“凡响·启蒙”这一阔大人文命题。正如鹰的美只能高显于空旷蓝天,如匍匐刨食于杂草中比鸡还丑笨一样,诗人的忧郁在这种重锤手法下反而表现得清晰、明了、震撼。
这个人的这些诗,我反复看。也许,它们本不是为了发表。他把它们写出来,只是为了排遣那些无法排遣的内心苦闷。他更不是为了证明一座什么城市。是我硬把它与城市相连,是我忽然为这座城市在想像中增加了无数的同谋者。
2004年底,像认识燕赵齐霁一样,我认识了深圳的路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诗人。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与称谓:“朋友是一些爱热闹的人,以致我常常走进某一个生活圈子。当他们面对政客、有钱的人、或者同样的一个小职员、司机、牙科医生,或者某个来历不明却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时,他们找不到体面的词语,往往会大声说:他是一个诗人……诗人,在这里是一个让双方都不致于尴尬的称谓。”路云16岁开始写诗,但很久以来,谁也不知道他是诗人。但他有一个“沉默的抽屉”,里面装着几部诗集的稿子。用时尚的话说,在公开的诗人名单中,他们并不“在场”。但他们却实实在在活在自己真实的诗歌经历中,活于默默抽屉。显然,燕赵齐霁比路云离世俗更远,他把自己埋藏得更深更静。他的诗即使放在抽屉,也在抽屉最深处。
没人能回答,深圳还有多少像燕赵齐霁和路云这样的“沉默抽屉”。但生存的腻风柔雨中,失途羔羊的无助中,一定有暗中高人在精神迷津中徜徉并为我们暗中指点迷津。正如燕赵齐霁那些纸上的忧郁——他被思想捕获,又被忧郁浸泡,他在逃离挣扎中获得了灵魂的安宁,也由此获得了自我拯救。
我想说,纸也是好的。通过文字在纸上的书写与传播,他的诗也同时救赎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2011-1-18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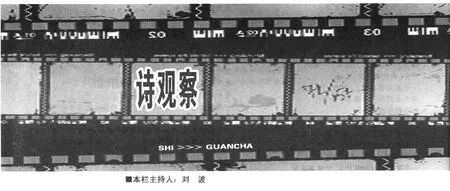
(本期封面用图选自《艺术与设计》2010年总第2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