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写进诗:漫谈诗歌的全球写作
[澳大利亚]欧阳昱
此文为欧阳昱2015年11月24日在汕头大学的演讲。谈及他游走世界的诗歌写作。
诗歌;全体写作;演讲
这个话题听起来很大,因为我至今没去过南美,没去过非洲,除了迪拜,也没有去过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但若把生活了24年的澳大利亚所在的南半球和生活了35年的中国所在以及去过的那些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和北美洲国家的北半球加在一起,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全球”,至少应该是超过了50%的半球。若把写进诗中的各大洲的人算进来,其中有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阿拉伯人和美洲南北两大洲的各色人等,那就差不多比较接近全球了。记得在澳大利亚曾经听说有位诗人,搞了一个诗歌项目,要把他一生见到的所有人都写进诗里。我觉得很有意思,虽没有刻意这样去做,但碰到机会,也会把某个令我感兴趣,过后一辈子再也见不着的人写进诗里。诗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就是碰巧落到你头上的一滴雨,这些雨滴加起来,就是我笔下涉及去过的国家和见到的人的诗。
三十年前,我给刚出生的儿子写了一首至今都没给他看,也忘记给他看,现在即使给他看,他也不一定看得懂的诗,寄托了想周游世界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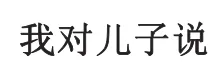
中国不能装下世界
世界能把中国装下
中国是船
世界是海洋
中国太小太小
世界很大很大
中国是屋
世界是空间
你长大是要做船
还是要做海洋?
是一闪即逝的星
还是永恒的空间?
1991年4月18日,我第一次踏上了南半球最大的岛国澳大利亚,开始了三年半的博士攻读生涯。我在一首诗中,记下了去国之后的感觉。

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
我记得曾经死过一次
飞向异国的天空中
洒遍了我骨灰般的记忆
在人来人去的机场
没有人为我送葬
我为自己灰色的过去
低声唱起一首哀曲
在蔚蓝色的太平洋上空
我埋葬了我的旧梦
把餐巾叠成一朵朵洁白的小花
凭吊那不再属于我的大地
从此我心中的故乡
被我永远地流放
如今即将离开澳大利亚
我又再度经历死亡
在著名的流放之乡
流浪者无处流浪
我这只劫后余生的候鸟
我这匹魂系天涯的独狼
我曾经有两只舌头
一只中文一只英文
我曾经有两颗心脏
一个东方一个西方
而如今我一无所有
唯有再度去流亡
前面提到的“去国”,用英文来说应该是复数的。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幻的,一个已经离去,一个在心中想要离去,真实地反映了人生无处可逃的心境。其实,我的四方游历,并不总是与“诗”俱进,比如早在1986年,我作为随团翻译,就已经去过纽约和加拿大不少地方,如温哥华、卡尔加里、班夫、尼亚加拉瀑布、蒙特利尔、詹姆斯湾等地,可那时,我足迹所至,没有留下一线诗痕。眼中看到的一切,脑中想到的一切,都未与纸张发生“诗”合作用,只是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而已,从诗歌角度讲,至今是个遗憾。但留得活人在,不怕没诗写。当年我在La Trobe大学读博士时,我的导师John Barnes教授专门教过澳大利亚诗人Kenneth Slessor的诗,说他诗歌的一大特点是,当时当地不写诗,而是根据记忆写。我听后特别不以为然,觉得诗歌这个东西,最好随时有感觉随时写下来,一放就不新鲜,就馊了,像饭菜一样。没想到,25年后,我竟然也采取此法,来对待当年那些没被我写进诗中的国家了。

今早这个人
戴墨镜
坐在阳光的前廊
在我走过的那一刹那
仿佛一幅壁画:
高统帽
黑眼镜
白衬衣
一个白人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与孤独打成一片
在那儿的阳光下
坐一整个早晨
我想起25年前在加拿大
Shawinigan看到的一模一样的情况:
老人坐在阳光下的前廊
一动不动地晒太阳
当时代表团的领队老倪说:
哎呀,我永远也不要过这种生活!
这个人很凶
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早年写作,涉及记忆的不多,年岁越大,走的地方越多,时空的交错也变得越加频繁,记忆经常会像小型地震一样,随时随地都会爆发,比如,我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参加文学节,便写了一首与加拿大有关的诗,呈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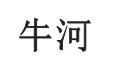
在海边
转了一圈回来
时近四点半
想吃饭
Thailicious没开门
要到五点半
Shannegan’s嫌太吵
而且都是白人
不想吃
来到一处
有家越南餐馆
也要五点开饭
就坐到旁边的街边
跟几个看似
印度尼西亚人
无事可干的人
坐在一起
大家互相都不理
我兀自抽烟
写诗
跟从来都不联系的人
居然发起短信
直到五点差三分
要了一份Noodle in Soup with Beef
直译是牛肉面汤
其实是越南牛河
还要啤酒,结果没有
只有Ginger Beer
意思是“姜啤酒”
老板居然哄我说:
味道跟啤酒差不多
其实差远了
我只是因为外面太热
最后才勉强要了
当降温的甜水喝
还没喝完
牛河就上来了
白的是豆芽菜
绿中带黄的是柠檬
红红绿绿的是
切成小丁的朝天椒
还有几大片
绿叶子
我扯来就往牛河上盖
吃进口里很香
却又怎么也嚼不烂
老板用英文说:
你要把它扯断
撕开,否则吃不动的
因为这是Basal
很熟悉的一个名字
是从前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连续剧中
旅馆老板的名字
我扯断撕开之后
果然好吃
但满手都是油
吃着吃着,我就想起
1986年的蒙特利尔
有天晚上我在那儿也吃了一盆牛河
同时还跟该餐馆一个打工的华人聊天
吃完聊完后我去付钱
却被告知:他已经给你付了!
我感动的结果
是把这个对陌生人友好的传统
藏在心里
有一年为一个镇江来墨尔本的代表
团当翻译
竟也带着其中一个觉得面善的团员
请去好好吃了一餐
没让他掏一分钱
付钱时又想起了
蒙特利尔那顿免费的牛河
今天在达尔文
我吃的牛河的确不错
比十几年前吃的好很多
最好的是
它连同那次遥远的记忆
正式进入我诗
前面说过,要“把你写进诗”,也就是把人写进诗,包括素不相识的路人,即凡是能让我产生诗意的人,尤其是平头老百姓。诗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就是一个既要让诗人活、让大人物活,也要让从不见经传的人见经传,通过我诗而活下来。下面这首写的就是一个公交车上的男售票员:

谁说现在人都不看书了?
即便你教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一年只看零本
或只看三本
那也不能下结论说
现在人都不看书了
这不
我前面这个卖票的巴士
乘务员
面前就放着一本
《最后的一个道士》
撕过票后
或滴滴地打过卡后
他乘空展书阅读
不像我
总拿着笔
怕错过有意思的东西
就那样一页页翻着
看得还很慢
很仔细
白发不是三千丈那种
连三寸都不到
但已根根毕露
他肯定不知道我
会请君入诗
他现在
就在我的诗里
至于贩夫走卒、卖小菜的、做保洁员的、看门的等等,都无不被我请入诗中,包括动车上坐在我旁边,从头至尾没有讲过一句话的乘客。我觉得无论飞机、火车、动车、轮船,还是其他交通工具上偶尔碰到一起,却从未交流过只言片语的人,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一种隐喻,说明人与人的相遇,只是极为偶然的事件,碰到一起,就再也不会碰到一起了。有一个这样的乘客,就这样被我写进诗中,那是在从上海到温岭的动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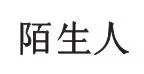
从松江南去温岭的动车上
有个陌生人坐我左手
也许是因为两个座位共一个扶手
他老把右胳膊肘伸过来
时时弄得我不太舒服
这人穿双鲜红的运动鞋
年纪大约二十四五
一路上他几乎不看书
只偶尔翻翻车上的杂志
其他时间不停用他的拇指
在手机上敲敲打打
我直到下车之时
也没有跟这人说话
从温岭到上海虹桥的动车上
我还是坐窗
左边有两个陌生人
这回我的胳膊肘一直搁在扶手上
这个小伙子一次也没碰我
尽管我也一次也没碰他
他时不时俯身向前
在他那张伸不出来的小桌子上
看手机上的小说
他旁边那个满脸横肉的汉子
则一刻不停地玩游戏
那游戏的音乐声
现在已不记得
但当时我可以从头到尾唱出
这两个人
我直到下车,也一句话没说
好像也无此必要,从来都是如此
顺便提一下
上次去温岭,坐车四小时
中间上厕所小解
和谐号马桶堵塞了
晃晃荡荡一马桶黄水
我只好立刻退出
这次从温岭回
我坚持了四个半小时没拉
脑子里晃晃荡荡的就是那个和谐号
马桶
国内写的这类诗、这类事此处按下不谈,还是继续谈国外的事、国外的诗。2004年,我应邀参加丹麦的诗歌节,一口气跑了8个国家十几个城市,写了上百首诗,记得在巴黎香榭丽榭大道上,就中文英文一连写了好几首。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接触,因此感触良多,一发而不可收“诗”。此前在国内,看过很多名人、名诗人写的在欧洲游历的诗,都是美轮美奂那种,无法从他们的笔下,了解除了欧洲之美的任何其他细节,但我的眼中,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于是,它们——这些细节——进入了我的笔下,例如这首写在香榭丽榭大道的诗:

在外面旅游
吃饭
是很重要的
我们找到一家Quick
类似McDonald麦当劳
要了一个King Fish
大碗可口可乐筛来
大块面包要来、大袋Fries装来
塞了个死饱
到厕所拉尿
两句法文
被我认出来:
Vive Asse
大意是:
屁股万岁!
法国的同性恋是如此
中国的同性恋
由此可以推想之
诗,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交流,一个中国人、前中国人,走到再远的地方,他所看到的一切,无不跟他的原籍国、祖籍国发生某种诗意的关联。毕竟他用的语言还是汉语,还是那个与“诗”俱来、哪怕英语再好,也无法忘却的语言,就像血管中流动的血液一样。这就是当年我写的欧洲诗,所呈现的一种状态。它并因旅途的流动而洗尽了一切铅华,让语言简单到直接勾勒、几近失语的地步。比如下面这首:

1944年
死的两个人
一个人被刻在桥头石上
一个人被铭在门牌号码旁
不知谁
把鲜花同包鲜花的塑料纸
用胶带黏附在它们旁边
我只能读懂:
mort pour la France
(为法国而死)
我不知道
2004年的今天
在中国
还有谁记得
1944年
为国捐躯的人
可那是中国
而这
是巴黎
古人说:诗言志,其实不一定都是如此。诗,有时也是一种批评、文化批评的武器。上述那首诗,写于塞纳河畔,因为我在那儿普通人家的门上,看到了令我“诗”然起敬的东西:1944年为国捐躯的人,到了2004年的60年后,还有不知名的陌生人在他们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前献花,这样的细节,让我深受感动。同时也想起了似乎未曾发生过类似之事的中国。在巴黎见到过的这种让人感动的事,还不止一次地见到。例如,我就曾在地铁站口亲眼看见一个年轻人,为一位不认识的女性,把她一只十分沉重的大包裹,从几十级的台阶下,一直搂着抱上了台阶顶端。仅凭这一点,我就不能不说,我很喜欢法国人。
人如此,但城市并不如此。中国人,包括中国媒体,只要提起巴黎,总要冠之以“浪漫”一词。以我所见,巴黎一点都不浪漫,我看到的,到处都是人类生活的痕迹,跟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人类生活的痕迹都不相上下。这促使我对这个所谓的“浪漫”城市进行了新的诗歌思考,由于这方面写了很多,无法一一例举,仅举一例如下:

终于看到了
蓬皮杜中心
这个丑陋的
建筑物
以后碰到人
谈起巴黎时
可以说
我去过蓬皮杜中心了
却不必告诉他们
我对楼上
18、19世纪
或20世纪
的精典绘画作品
毫无兴趣
不过
偷拍了两张
中心外靠画肖像为生的
法国的中国人
其实,欧洲诸国中,让中国人最瞩目的,还不一定是法国,也不一定是德国或英国,而是世界地图上几乎最靠北,形似一根阴茎的瑞典。它每年发的那个奖,几乎让所有的人都心向往之、垂涎之,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我们没去冰岛,也没去挪威,独独去了瑞典,瑞雪兆丰年的瑞,典雅的典,除了有我的瑞典翻译朋友相邀,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现在回头来看,我的诗歌中竟然很少有歌颂赞美,这也奇了怪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大约是与生俱来的反骨在作怪吧。与法国相比,在那儿我写了36首,瑞典我写得很少,仅6首,现选一首中文的念一念:

晚上6点
这时,我们离开si de ge er mo
双层bus爬上又一座高架桥
黑色的河水
无声地流过
一座板着面孔的城市
我想起蘸满mustard的鲑鱼
我想起Lars
和
昨天在斯德哥尔摩遍地的雨①
经与庄园老师商量,确定研究生听众中,一般都能听懂英文,这令我高兴,正好借此机会,把在瑞典写的一首英文诗放在这儿念一下:

This country must understand standards
It’s beautifully wooden
Its people,before I forget
Seem to have a thing or two
About other people,people
I can see where they come from
For example,in relation to Chinese poetry
When they mention the unmistakable
influence on a supposedly top
Chinese poet by a supposedly top
Swedish poet
Or when they refer to Chinese poetry,past and present
As nothing comparable to big poetry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or france or England
That remains to be seen,I mean
I have not read any contemporaries of
my fellow
Poets from these countries
And seem to have managed to live well
Poetically
I don’t think Australians
Would be that stupid
As to giv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o total strangers
For their so-called achievements
Stockholm,by the way
Reminds me of a sullen face
Forever brooding on the impracticalities
of prize-giving
And on who next is going to owe them more
On my departure,anyway
I sawa guy digging into a rubbish bin
Fishing for something I imagined
That resembled the nobel prize
Only it’s rubbish
In some other speak
老实说,欧洲地方跑多了,觉得就像一个大国,分成了很多国名、说着不同语言的省份一样,尤其是每到一处都逛博物馆或画廊,到了最后,感觉脚都像要跑断一样,眼睛看起了老茧。倒是在葡萄牙这个衰落的殖民帝国中,尝到了别致的诗味,如下面这首:

在葡萄牙
常常可以看到
沉思冥想的人
前天
我在里斯本一个门洞里
看见一个亚洲人
整个脑袋低下去
看着地面沉思
今天
在Cascais的海边
我又看见一个穿球鞋的黑人
抽着烟、低着头
在那儿沉思
他的脸
让人想起这个帝国从前的不可一世
和如今的一世不可②
当天在同一个地方,我又接着写了一首诗:

这个黑人
扭过头来
冲我一笑
我的她说
不会是对你的
录像机发生了兴趣
我说:绝对不会
一个沦于沉思的民族
使我感到亲切
时空和记忆绞缠,时序在纸上留下可循的痕迹,但在记忆中,却前后颠倒,难以厘清。大致的顺序应该是,我在欧洲开眼之后,又去了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等。我想先从马来西亚说起,一来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很多华人,包括华人作家,都移居到澳大利亚,二来是因为,我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名叫Vin de Cruz的教授,一个很好的马来西亚印度裔的朋友,现已仙逝,但生前曾常常谈起他在马来西亚的经历,特别是他跟马来西亚华人结下的深厚友谊。所以我一想到亚洲,往往就会首先想起马来西亚。我在马来西亚写的第一首诗,就跟他有关。在这首题为《白人》的诗中,我说:
……
Vin,我的马来西亚印度
朋友,一直和华人有深厚
情谊,比大陆人和华人
还亲密
儿子也是,朋友中无一个白人
倒是有印度人
我过去那个国家的人
崇拜白人之盛,最后吃亏的
也是他们自己
因为白人不会把他们看成朋友
而只可能是永久的异己
……③
在马来西亚,我注意到,马来族的人的样子很特别,待人接物十分谦和懂礼,在海边吃饭时,我发现了感人的一幕,便欣然写进诗中:

在大马
北马的
槟城
我在黄昏的
海边
看到了马
骑马的马来
小伙子
很英俊
像电影中一样
穿过海、山、云
分层叠起的背景
还频频对我示好
我也报以微笑
挥手让他们走掉
就在这时
一匹马突然停住
马尾翘得老高
像一根棍子
朝后伸出去
靠股根处竟还稍稍隆起
劈里啪啦几砣大屎
波澜壮阔而出
英俊的马来小伙子
没有疾驰而去
却跳下马来
在马屁股后蹲下
掏出一只红塑料袋
等我从马来蟹上再度
抬起头来,这位马来
的英俊小伙子
已经牵转马头
手里拎着满满一袋马屎
陪马回家去
好像下班回家
从菜场顺便买一提东西的人
马来过的地方
只有马蹄印记
和被骑手抚平的沙地④
每到一个新的国家,走马观花看风景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用思考的眼睛进行观察。诗,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一种观察的产物。例如,我就注意到阿拉伯情侣特殊的示爱方式,如下诗所示:

白人已经不浪漫了
只看到一个中年白男
给他的中年肥白婆推油
在Penang的Ferringhi海滩
那风景真是煞风景
黑人不浪漫
在这个看不到非洲人的地方
所有比非洲人白
比白人黑的马来人
都看不到儿女情长的举动
华人也不浪漫
即使昨天坐BMW来举行婚礼的一对
也没有当众接吻
倒是伴娘穿得很露
高跟得让人想入非非
唯一浪漫的人
倒是可能来自阿拉伯的年轻情侣
蓄着髯须的男子
和全身长袍只露眼睛的女子
手拉手在海边走来走去
而且,就在我游泳的泳池里
这位连下水都不脱去袍子的女子
与她穿短裤的须发男子
脸对脸地搂在一起
下面我就不知道了
但上面,他俩的嘴巴
不停地啄吻
女子的眼睛同时朝四面看去
一接触我就立刻转开
把书遮住书缘和我腿之间
那条可看的缝
老婆羡慕地说:
他们好浪漫呀!
是的,我在心里说
可我们在外面,连手都没牵过⑤
不仅是观察,也是发现。诗歌走到哪儿,都需要有新的发现。新大陆不仅仅是被哥伦布发现,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新大陆、微新大陆等着被眼睛发现、被诗眼发现,从而进入诗中。像下面这首写于泰国,部分关于马来西亚的诗所表现的那样:

世界还有很多地方
等着我们去开发
用眼睛或耳朵开发
昨天在马来西亚
我发现他们的失业率低于零下
出租司机说得好
找不到工作的人
只有两种:
the lazy or the choosy
生性懒惰者
或挑三拣四者
我心里想
这句话是否也可以用在
找不到朋友的人身上
不过,找不找得到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今天在泰兰,我是说泰国
我发现
我接触到的四五个泰国女性
都没有涂蔻丹
或曰指甲油
白白净净的指甲
很好看
我终于忍不住了
就问为啥
卖金银首饰的女服务员
用比较夹生的英语说:
Ka-ters。我好容易才明白
她的意思是说:
要看是什么性格的人
我想起我教的那些80后的大陆女生
几乎无一不涂得鲜亮
包括黑色和多色的
我又想起昨天在吉隆坡机场
见到的一个黑人女性
不仅指甲涂黑
甚至每根指头的末端都抹黑
手心手背都点上黑斑
成一种神秘的图案
这种种小小发现
令我的旅途
不比当年哥伦布的
更少乐趣⑥
我在马泰两国,还有一些别的小小发现,也一一写在诗中,此处仅选两首,给大家念一下,也算是一种新的形式,即把传统的讲座与诗歌朗诵结合起来的形式,这大约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那时,我发现,我在澳大利亚(包括中国)参加的很多学术会议,都十分枯燥无味。时间限制在二十分钟内,一篇花了很多时间写的有分量的稿子,最后不是只念到一半,就被人举牌警示时间已到,就是以极快的速度,闪电般地把稿子念完,而在无意中造成一种抢读的滑稽效果。诗歌朗诵则限制在15分钟内,如果一首首念,还可以多读几首,一旦插入解释,留给诗歌的余地,往往所剩无几。有了这个发现后,我有意把诗歌嵌入英文论文中,以事论诗,以诗论事、说事。这种做法,我好像在别人那儿尚未见到。
我在马泰的一个发现,是亚洲这两个国家的人对读书的态度,因为那儿人们几乎不看书,好像也没有专门的书店,书,似乎都是放在超市里卖的,于是便有了下面这首诗:

无论在大马
还是在曼谷
走到何处
都看不到一个捧书
阅读的人
只在从吉隆坡
去曼谷的班机上
看到两个看书的
日本人
和一个看书的
白人
如果不算我这个
从上机到下机
一直在看书的
黄种人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情况会这样
我想可能与宗教有关
但印度籍的马来西亚司机
不同意
他说:看书不过是一种
习惯
跟看球、看戏、看赛马
并无太大
区别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从他的话中
还听出了这个言外之意
现在,不是我觉得别人
Sad了
而是我觉得自己
很sad⑦
我的另一个发现,与喜欢在这些国家游历的西方人有关。据我所知,澳大利亚的白人特别喜欢在泰国生活,因为那儿有充足的阳光、大好的海滩、火辣辣的食物和女人。最近看完的法国作家Michel Houellebecq的长篇小说Platform,讲的就是如何在泰国寻觅“sex tourism”(性旅游)的经历。因此,只要见到这些人,我就会仔细观察,有了感觉就写进诗里,如下面这首:

在曼谷出行时
我又有一个新发现
我们一上车
都就近靠前找个座位
可刚才两位西方人
本来和我坐在
平起平坐的位置
眨个眼
就搬到我后面去了
我不知我身上
是否有native的气味
但我已隐隐感到了
危险
尤其当我想起昨天
那辆大车
一车的西人、白人
都偏爱后面
就像我一个学生说的
坐在教室后面
能更清楚地看见教室发生的一切可在曼谷的车上
我逐渐体会到危险
一是坐得靠前
可能在撞车时
与司机同归于尽
二是坐得靠前
我的后脑勺没长眼
不知何时被人
从后面给以致命一击
敲得粉碎
后
从来就是先
历史
就是今天⑧
写到这儿,我不觉想起加拿大华人诗人Jimmy Wong-chu(朱蔼信)写的一首英文诗,题为“Equal Opportunity”(《平等机会》)。大约十年前(2014年),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首诗就很喜欢,不仅翻译成了中文,而且还介绍给了我的学生,如下:

(加拿大)朱蔼信著
(澳洲)欧阳昱译
加拿大早年
铁路四通八达
每一站都带来新的机会
当年有条规定
华人只能坐
最后两节
车厢
也就是说
一直坐到火车翻车
前面坐的人
全部死光
(华人搭起祭坛,感谢佛祖)
于是又产生一条新规定
华人必须乘坐
前面两节
车厢
也就是说
一直坐到又一场车祸
要了后面
所有人的命
(华人搭起祭坛,感谢佛祖)
经过激烈的辩论
还是常识占了上风
如今,华人
可以乘坐
火车的任何地方
泰国盛行佛教,贫富差别很大,但在这样的国家,也能体会出一种罕见之美,如我在河上之行所感觉到的那样,当场便在船上手书了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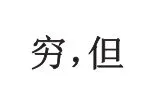
穷,但
很阳光
穷,但
不很脏
穷,但
住水边房
穷,但
满脸笑样
穷,但
不悲伤
穷,但
有生活
穷,但
有指望
穷,但
有花香
穷,但
有椰树
穷,但
有家乡
穷,但
有佛堂
穷,但
有国王
穷,但
有思想
穷,但
无所伤⑨
这一点,也可以从这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人日常的手势上可见一斑。例如,我这个一向讨厌“V”手势的人(它在我看来一是不假思索地媚西,一是看似很二,伸出两根指头,不就是一个“二”字吗?),到马来西亚后,学会了他们为了表示三个民族(马来族、汉族、印度族)团结一致而伸出一根食指的“一”字动作,觉得进入汉语的语境之后,更添加了汉语中的新意,如一心一意、一往无前、独一无二,等。因此,我不仅学会了这种手势,用在日常的拍照中,而且也把对两国这种手势的思考,写进了诗中:
手势
在马来西亚
只要你说谢谢
服务员就会笑笑
同时把右手放在心上
我想
那是表示诚心诚意
我觉得
这远比澳洲人
动不动就伸中指好
在泰国
人们不再把手放在心上
而是合起来
指尖对着鼻尖
双目微闭
我喜欢这个姿势
一直告诉自己
做一个同样的动作
来表示友谊
可直到最后
还是伸出右手在胸前晃晃
不过,我还是觉得
这个动作远比中国的握手好
不会握一手汗
或一手水
更不会握一手
冷淡⑩
在海外旅行-我说的“海外”(overseas),是澳大利亚的国外,而非中国说的“外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也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果不把这些写进诗中,那简直是天大的缺失、缺“诗”。我在泰国遇到一对澳大利亚夫妇,谈起了他们的故事,觉得有意思,便写进了诗中:
杰夫是我在北碧府的桂河
认识的一个澳大利亚人
手臂一伸
就是一大片已经发白的老毛
这是一个信守传统价值观的老人
结婚五十四年,老婆就在身边
无法接受儿子结婚又离婚
再找一个小的事实
无法接受媳妇年过四十
还要当什么career woman的事实
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无法接受澳大利亚
年轻女子生十个孩子
每个父亲都不重样
然后一生躺倒在政府身上
由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来供养的事实
更无法接受政治正确到这样一种地步:
自己把父母离异的孩子收养下来
儿童保护组织却不让自己哪怕轻挨
一下孩子
更不要说搂抱了
连在自家走路
都要择道而行
避免有娈童嫌疑
老人已经退休
宁可把所有闲暇花在泰国
这个地方虽穷,他说
但人很开心,而且很好
真的很好?
诗,不仅仅是发现,也是回忆,与个人身体挂钩的回忆。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装满记忆的仓库。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是记忆的触发器,如下面这首写于泰国的诗所显示的那样:

在Ayuttaya的一座佛堂
我脱鞋走上石阶
被烫得小叫了一声
脚板心的一烫
让我立刻想起了四十多年前
还是个挺奶仔时的
长江
夏天顶着毒日头暴晒
脚下越烫越要走
觉得那才有英雄气概
看完坐佛后回来
走下台阶时
又被烫了一回
记忆长在了脚上?
一个带着语言行走的人,所到之处、所到之国,都会自觉地把注意力转向该国的语言,并将其与自己的母语和父语(我个人的独创)进行对比,令其入诗。例如,我在丹麦时,曾写过一首关于该国语言印象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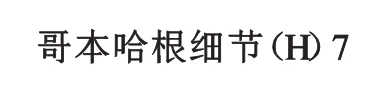
我们说海
他们说Hav
我们说花园
他们说Have
我们说海港
他们说Havn
一个在这头
一个在那头
我们的形状
颇象一个H
在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我则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可以把杜甫那句“润物细无声”推进一步,扩大到“润国细无声”,如下面这首中所表述的那样:

在泰国
我见到很多人
看上去都像华人
却一句华语都不会说
我又见到很多人
明显是泰国人
却不时会说一两个汉字
比如我在河上泛舟
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
该河叫啥河
我的黑黑的泰国导游
一听我问“湄南河”就说
“Mei Nan He”
发音一点不错
不像西人,把“河”发成“he”的音
我还发现
他们的三和四
他们的八九十
都与汉语发音接近
甚至他们大象的“象”
也与汉语一模一样
而且文字都有四声
这让我想起
满大街都是汉字的日本
600年前史书都用
汉字写成的韩国
华人进入英文也
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的马来西亚
汉文字啊汉文字
就如此润国
细无声?
实际上也是润语细无声,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正好就此转到日本。我2009年5月,到这个国家去了10天,写了二十几首诗,包括一首中文长诗,查了半天后才发现,其中英文诗大大超过了汉语诗。我那首长诗题目为《日下的本本》,诗中把中日两种语言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说:日本是“活脱脱一个/中国文化日下来的本本”。因为太长,此处就不选用了,只举一首短的为例。

面前走来一个人
胸前别的牌上
写着:村濑
大约又是一个以
村为单位的一种姓
这些姓
像田中
像清水
像村上
像山门
像水井
等等等等
说明整个日本
依然是一个原产自
山水的民族
原本就是
中国的根
干脆别叫日本
就叫日根?
在日本,我想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死。这么一个已经进入西方的国家,其现代史沾满了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血迹。有意思的是,我在日本写的英文诗中大量提及这点,但只有一首中文诗提及,呈示如下:

据说
日本人
活得最久
是的
杀人越多
活得越久
像吃鱼
吃得多
活得也越久
意思就是说
鱼也
死得最多?
当然,我在别的地方,也写到了日本,尤其是日本人,如有一次在香港开国际会议期间,认识了一位日本的教授,此人给我留下的印象,被我写进了诗中。我吃惊地发现,该诗写作之日,正是9月18日,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同一天,诗中发生的事情,尽管发生在两年前,但写作和回忆的日期,却正好发生在这一天:

日本人的凶相
直到2009年
依然毕露
我说的只是一个日本人
还是日本来的一个
会讲英语会教英语的教授
他说的英语
我不大听得明白
你的明白?
后来我们一起到外面抽烟
他把每一砣烟灰
都弹进自备的纸盒子里
多么清洁的民族啊!
我并没有自惭形秽
在我们的民族
灰飞烟灭才形象生动
更因为,事后,晚上
欣赏完香港太平山顶下的景象之后
盛宴的席间
该教授第一次当着大家的面
义务扮演了叫兽的角色
当面训斥了另一位华人教授
不过是因为后者
开了一句如果在华人当中开
就不会有事的荤玩笑
那个华人教授当然是我
而那个叫兽的发作
更多地让人觉得
他从华人眼中看出
人家觉得他的英语
真不咋的
于是,活生生地展演了
当年在南京开杀时
电影都表演不出来的
日本凶相?
写到这儿,本想就此打住,但突然想起,曾有一年,我来过汕头,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来,原打算住两天,结果只住一天就走了,倒是写了好几首诗,其中两首都以“汕头”为题。如果大家有兴趣,我选其中一首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再读另一首别的。

直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为何
到这个地方来
舷窗下的秃山秃地
看上去颇像
青海
听我坚持打表
出租司机很不客气
说声:我靠,什么规矩不规矩
他把车开得飞快
我坐在后面很急
没有安全带可戴
沿路都是菜地
我闻到人粪尿的气味
使我想起了丹麦
一入店就上网
一上网就接通
唯独hotmail打不开
我如同断线的风筝
与世界失去联系
外面楼群似有所待
是的,我想写本英文小说,
但那是将来的事
而此时,一群鸟砸下来
朝楼缝之间冲刺
阳光下,一切暴露无遗
黑的更黑,白的更白?
另一首题为《双早》,如下:

汕头这家饭店
288元一晚
送双早
还送双份
夜宵
另有388元一晚
的海景房
也是双早夜宵全含
我选择了只看这座陋城的288元
而没住海景房
因为我知道
夜幕降临之后
大海漆黑一片
而夜晚
总有睡觉那么长
10月30号这天早上
我一张嘴
吃了一份早餐
把另一份
以及四个夜宵
还给了本来预定两晚
但只住了一夜的饭店
在连熟人都没有的城市
一个人要吃双早
很难?
如果还有时间,我想把刚发现的去年在澳大利亚写的一首诗放在下面,读给大家听听。我在澳洲当翻译,接触到很多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也从他们那儿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时就会把他们写进诗中,比如下面这首中,就是我在一家医院,为一个作心脏搭桥的华人病人当翻译之后写下来的:

在中国,如果我做心脏搭桥手术
每个医生都要塞钱
包括麻醉师
要是我不塞怎么办,我问
那就痛死你!他说
在中国,一个搭桥支架
进口的要七万
国产只要三万
糟糕的是,他收你七万
但放进去的是国产
问题是,他说,国产的用不了多久
就会出问题
那怎么办?我说
只有继续塞钱,他说
一直塞到他们保证用进口的
在澳洲,病人说,我这个手术
从头做到尾,一直做了8个小时
做我的是个印度医生
做完后人累瘫了,靠在墙上
话都说不出
我女儿听他说出为什么后
决定不让孙子读医生了
原来,印度医生说
虽然医生一切都好
但,每年都有一两个死在手上
毕竟成功率不可能百分之百
因此,因此,医生感到十分sad
病人说,想来想去,还是澳洲好
开刀一分钱没收
连1000块澳元的救护车费,也都免了
而且,他都不知道医生是谁
对他来说,医生不过是一个裁缝
把病人内部的衣服缝合之后
又去缝合,下一个人
不需要认识,不需要送礼,不需要人情
病人后来告诉我
之所以造成心脏搭桥
是因为在中国吃坏了身体
血管堵塞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像一条河流,坏死了四五条支流
后来我和病人
取得了一致同意
宁可对自己苛刻一点
也不能放纵,口腹之欲
心脏介绍会完后
病人不打招呼,便扬长而去我望着他的背影
我想着他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
为他写这首诗?
读诗说文至此,我想,我的话也基本上讲完了。欢迎大家提问,欢迎大家评论,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①写于2004年5月4日夜晚。
②2004年5月24日写于里斯本的Cascais海滨。
③该诗2012年4月24日手写于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内。
④2012年4月25日晚上9点50分写于槟城Park Royal Hotel。
⑤2012年4月27日下午1.18分写于槟城Park Royal Hotel。
⑥2012年4月29日下午6点18分写于泰国曼谷Intercontinental Hotel Bangkok。
⑦2012年4月29夜在曼谷的Nara晚饭时手写,5月6日星期天晚上10点30分修改并打字。
⑧2012年5月1日晨手写于去Floating Market的车上,5月6日星期天晚上10点46分修改并打字。
⑨2012年5月1日游览泰国水上市场时在机动小舟上手写,当晚在Holiday Inn的562房修改并打字。
⑩2012年5月1日星期二手写于去Floating Market的车上,5月6日星期天晚上10点54分修改并打字。
?2012年5月2日上午9点55分写于Holiday Inn早饭后。
?2012年4月29中午乘车手写于Ayuttaya的车上,5月6日星期天晚上10点35分修改并打字。2012年5月16日晚上10时01分再改。
?2012年5月2日下午写于曼谷去看晚会的小巴上,5月6日晚上10点17分打字并修改于金斯伯雷家中。
?2009年5月7日下午4点50分写于京都一家叫“八(三点水)桥”的商店附近。2009年5月10日晚上6点55分修改于金斯勃雷家中。
?2009年5月6日12点57分写于京都的Kyoto Tokyu Hotel;2009年5月10号星期天晚上6点26号修改于金斯勃雷家中。
?2010年9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点05分写于金斯勃雷家中。
?2011年10月29日星期六下午2点24分写于汕头海滨路18号汕头嘉和海景酒店。
?2011年10月30日星期天上午9点23分写于汕头海滨路18号汕头嘉和海景酒店。
?2014年7月24日9时01分写于金斯伯雷家中。
(责任编辑:张卫东)
Writing You into Poetry:A Casual Talk on My Global Writing of Poetry
[Australia]Ouyang Yu
This article,based on a speech OuyangYu gave at Shantou Universityon 24 November 2015,is about his writingof poetrythroughout the world.
Poetry,global writing,a speech
I04
A
1006-0677(2016)1-0016-15
欧阳昱,学者、作家、翻译家,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思源”学者兼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