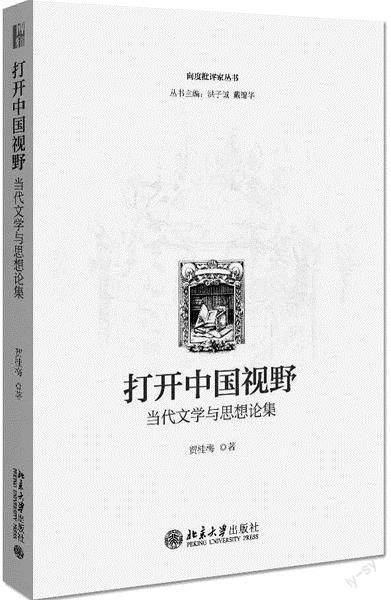
“历史化”近年来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口号。近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上,这一概念甚至以“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为题,成为年会的首要主题。参会学者阐述拓展历史化研究的可能路径。有的学者认为提出它意味着与当下性的关系,“文学史研究应当对接当下生活,从而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化”作为学术实践意味着应该对史料进行充分挖掘、分门别类整理并进行专门史研究;还有的主张它意味着开掘稀见史料①。总之,对于参会者来说,似乎它意味着文学研究的中心不仅是对作家作品意义的分析阐释,而是纳入相关的文学制度、期刊文献史料、人物本事。这种对“历史化”的认知侧重于对实证性材料的搜集,而且从其要“对接当下生活”来看,它显然试图从当下的视角来观照过去。
然而,学界也公认围绕这一概念本身也有不少争议,尚未对它形成共识。对于另外一些学者比如贺桂梅来说,它意味着“在一种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新的现实问题意识中,来重新定位和理解”文学②。什么是这种“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新的问题意识”?如果说在最先提出“历史化”原则的杰姆逊看来,它意味着从阐释模式的历史化: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理解阐释客体,到评论者立场的历史化: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来反思阐释行为;还意味着从文学文本的历史化,即揭示被叙事文本压抑在内部的历史潜在矛盾,到文类批评的历史化:呈现理论方法在建构中掩盖的矛盾、被压制而未言说的时代本源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在实践中实行这种原则?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以这一原则从新异的理论视野,对复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社会史料和文化现象加以新的阐释的动向,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其所取得的成果、经验和走向值得加以总结。贺桂梅就是这个群体性现象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她十余年来所发表的上百篇论文的精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打开中国视野:当代文学与思想论集》中得到集中体现,从中我们可以得窥一二。由于它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代”正在进行的一次革命性重构的阶段性成果汇总,因此以它为样本,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的发展动态的总体背景下,概述它提出的新命题、新论断并仔细检视其所依赖的理论新方法,对于我们了解和判断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新趋势不无裨益。
这是因为21世纪以来二十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研究重点,同时也是方兴未艾的学术热点。它们分别是1980年代文学的研究,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化加速时代的文化现象探寻,以及1940—1970年代即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而这三个重点、热点与本文集的四辑颇为对应。因此本文即以此书所涵盖的研究课题和问题意识为讨论基础,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代正在进行的目标调整、话语重构和方法探寻,作出一个初步的回顾、反思和总结。
一、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分裂的主体”与虚幻的中产意识
199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对于1980年代文学的再认识形成了研究的一个热点,学界如程光炜、洪子诚等学者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进行了一些资料考证和新的思考,带动了这一时期重新成为学界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贺桂梅1998年开始写作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198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此后她持续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反复思考,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的思路。而她的这种研究和其他学者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体现了阐释学视野下的历史思辨性特征。
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和“纯文学”思潮和相关文化现象是在这次“重读1980年代”的研究重点。对于前者,《“叠印着(古代与现代)两个中国”:1980年代“寻根”思潮重读》一文指出它关乎当时中国作家“主体性”建构的两难处境:在“文革”之后认为落后于西方的心態与民族主义话语的鼓动下,文化界被一种自我改造的焦虑所缠绕,面临着身份认同困境。换句话说,作者看到了当时内外因素的互动作用:寻根文学的产生并非只因当时的中国作家们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刺激,同时也有民族主义话语被作为克服和转移“文革”激进实践造成的合法性危机的内部因素的作用。另外,作家们希望与中国文化传统建立新的关联形式,但由于仍然无法摆脱现代化逻辑的羁绊,因此在接纳新启蒙思潮批判传统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只能在主流之外的“非规范”文化中寻求出路。这一希望国家“现代化”,又对民族文化怀有“乡愁”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寻根思潮确立中国主体认同的基本历史情境:叙事主体纠缠在两种不同方向的话语张力之中,并顾此失彼”④。这种“历史化”的工作有效“还原”了思潮和创作潮兴起的时代背动因,揭开了由于观念“物化”和“神话”笼罩在事物之上的面纱。
然而作者同时注意到,问题辩证的一面在于,虽然此时知青作家尚陷于烦恼意识之中,然而回城后艰难而庸常的日常生活打破了朝向未来的幻梦,又给予了他们回顾乡村生活的契机;又或者,当一些作家如王安忆在打开国门之后的欧美之旅中,意识到异域文明的绝对他者性,这带来了民族主体意识的诞生。由此,民族国家认同促使了对于民族生存状态的“发现”和书写。但在这种种动力之下,他们对“本真的中国(文化)”的探寻本身却也存在两面性:将本质化的中国文化看作能够包容并且超越政治(国家)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化观”,另一方面,关于“中国人”自我主体意识的发现和“文化中国”整体性想象的重建又有其价值。从前者看,寻根作家对国族内的少数、边缘族群的文化进行书写虽然建立在对汉族中心文化的批判之上,却只是中心文化的理想自我形象的投射。尽管指出这一问题,这里作者并没有落入后殖民批判批评“宗主国(殖民)文化”并意图对其加以裂解的窠臼与陷阱。相反,她看到了作家在重叙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对“文化中国”整体性想象的重建的意义:书写这些风俗是“作为‘中国人’的主体发现‘自我’的时刻”,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与民族认同之间自我分裂式的主体表达⑤。这种在回归历史语境后作出的不偏不倚的两面性判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型特征。
但作者超越此前的学者同类研究的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她不将那种“文化中国”的历史叙事看作是本体性事实,而是进一步去追问这种叙事如何建构,其知识表述如何构成且源自何处。由此她发现这种叙事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国内的考古大发现产生的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说”,以及由此产生的史学界的民族史新叙事和哲学—美学学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史新表述。换句话说,1980年代“层层播散的知识体制”带来的“新常识”,促成了寻根文学作为文学—文化领域的“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行为”⑥。在历史化原则之下的自觉探寻,使得作者不但发现寻根文学产生的秘密,还进而探视其泯灭的根源,揭示了寻根作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构只是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优先论”的变奏形态,这导致其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对中国“起源”的重叙,只是在西方这一现代主体注视下的倒影式呈现。尽管如此,研究者辩证的一面再次显现,即认为寻根文学所提出的问题事关后现代化国家的主体性问题,仍具有内在意义。
如果说在作者看来,寻根文学潮为知青一代在重新认知古老中国的表象下,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其提供了“主体性”的支撑的话,那么稍后兴起的“纯文学”思潮及其哲学美学伴随物“诗化哲学”,则是为正在生成的中产阶级看待当下中国及其文化心理的“主体性”,提供了意识形态弹药库。这一分析也是从1980年代的社会语境入手。出于对“文革”激进政治的厌倦,让文学远离政治成为当时不少人的共识。但这种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论,以及将以“反政治”或“非政治”作为“文学性”的标签,本身却也是政治性的声明。其实,“纯文学”思潮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都包括了一系列主体性或主体意识的建构,这三种现象因此得到了重点剖析:“诗化哲学热”、以“转向语言”为表象的“文学理论热”与“重写文学史”潮流。对于它们,研究者都分别给予了犀利的评判。
“诗化哲学”虽然仍在其时秉持浪漫主义的主体性认知的“人道主义”思潮脉络上,但却远离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将审美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认知:基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它提供了解决这一分裂的似是而非的方法。与此同时,它采取了现代主义的以美学来干预现实的美学思路,为1990年代的自由市场体制提供了虚幻的主体及主体意识。这一剖析可谓见表知里,多重辩证。
对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理论热”的解析也是如此。其时中国文学界以倡导“文学语言学”和“叙述学”为研究重心的、被称为“新潮批评”的形态,无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非人道主义”倾向,仍然是强调语言创造意义,本质上是将曾经的“政治(社会)决定文学”的模式颠倒为“文学决定政治(社会)”。换句话说,它始终徘徊在人道主义思潮的“主体论”和“中心化主体”的认知方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而为枳。研究者对此的剖析体现了明确的场域意识。
对于“重写文学史”的潮流,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1980年代前期已经将被“革命范式”文学史剔除出去的作家作品和思潮重新纳入学科重建,而1985年以后流行的“重寫”则只是要完成一种否定性的评判,其评判的依据并非是声称的审美分析法,而是视其与当时官方主导观念的疏离而定。这一发现揭开了这一思潮自我声称的“纯文学”主张,与主导者潜在的文化政治意识的关系。
进一步地,国内研究界兴起的“重写”思潮被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域和国际视野下加以检视。这股思潮的“纯文学”理路受到韦勒克《文学理论》所倡导的“新批评”方法的启发。正是二元对立的冷战历史结构使得新批评评价标准显现所谓“纯文学”的有效性,而且在中国,“新批评”关于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划分契合于冷战格局中的中国/美国的“内”与“外”。“内部”被认为是本真的、纯粹的、文学的,“外部”是非本真的、政治的。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内在的历史结构也未消失,而仍在很大程度上形塑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⑦。在我看来,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研究界主体性尚无法完全建立的一个根源。这种将重写文学史潮流与国际形势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的做法,为前人所未道,其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化要求所主张的“总体性”原则和研究方法的体现。在研究者细密的历史化解剖下,1980年代两个性质不同、也从不同方向上重建主体性的尝试的实质显露了出来。
二、21世纪初文化研究的新阐释:“中空的主体”及其重建
贺桂梅一直强调对于现代中国的国族叙事问题的考察,需要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观察视野,这样才能给予更深入透彻的阐释。这种努力在第二辑“21世纪的中国问题”包含的对新世纪初中国的三个文化个案的分析中都得到体现。这一研究取向反映了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趋势,即“转向”研究更为广阔的文化现象,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社会文本进行剖析和阐释。
新世纪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及其带来的“中国崛起”与相关论述,国族叙事由此发生相应变化。作者看到当前大片题材和类型的单一性,明显受制于中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上的位置,即为了进军北美市场,在文化表述上呈现出自我东方化色彩。对此她以对古装题材的影片为例说明,因为它们展现了中国大片面对国际市场时的“翻译语法”:将古代中国的故事以现代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转译。这带来了作者所称的“欲望的透视法”与“中空的主体位置”。
作者的分析以海外李安的《卧虎藏龙》与国内张艺谋的《英雄》为对比展开。前者展现了“古典中国”里的“中国情调”,中国风景是“欲望的能指”,创造出来的武侠世界的内在的情感世界是为“所指”,是以“布尔乔亚式”的主题生产出“内面的人”的观看欲望,这就是“欲望的透视法”。而内地导演的大片如《英雄》则以关于象征性阉割的故事来呈现对权力/秩序的效忠与臣服。由于内在主体性的缺乏,这些大片需要使得有关“中国”的一切都呈现为“可看的”,因此影片中充满的其实主要是物像和视觉的奇观。当题材内容从“江湖”向“宫廷”转移时,认同的对象指向中央王朝正统,“江湖”与“朝廷”之间趋向和解。《英雄》的结尾无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刺客与秦王共同追求的“天下”理想献祭的场面,象征着权力的占有者与反叛者都共同融入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一系列影片如《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也都可以作出这种国族体认的政治潜意识的解读:通过取消/掏空反叛者的合法性,将“中国”的历史叠合在“王朝”的历史之上,使关于国族的历史书写成为国家/政权的历史,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联。
如果说这种分析并非新见,那么对为何会出现这种景观作者诉诸的更为广阔的国际场域,则是颇为少见的在“总体性”视野下的追问与洞见:在强势的西方/资本权力面前,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或代表着资本全球化的强势国际政治权力)互相媾和却不可化约,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内部权力/反叛之间和解的理由。由此中国大片无法形成内在个体的欲望透视法则,它与“民族寓言”的相似只是模棱两可,只是以国家主义形态呈现民族向心力⑧。虽然对为何无法形成“内面的人”从而形成内在的(中产阶级)主体性,作者在这里并未给出更多解释,但在下一个关于“性别问题”专辑的一篇文章《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中,则从另一角度有所说明。即由于中产阶级作为“新阶级”在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和暧昧性,使其更适合用女性面孔来加以呈现,比如杜拉拉“赋予这个‘新’阶级以一种尚未真正获得主体性的、仍在梦想/镜像之中的欲望化表达的可能性”⑨。这一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进行的将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经验进行有机关联的分析思路,体现了历史/政治阐释学的分析方法的要义。
当“中国崛起论”支撑的主体意识与国际市场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大片中关于中国内部权力格局的呈现就会被改写,同时其中作为国际化策略的“东方”表象与“亚洲”市场及其国家关系的再现形态也将随着改变。因此,中国大片中呈现的“中空”的、“匮乏”的主体位置,在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区域与全球地位的上升已经有所改变,另一种新的国族叙事被塑造出来。在这种构想中,20世纪中国作为“落后民族挨打”的民族主义怨恨记忆被认为需要化解,从而出现了如《霍元甲》《南京!南京!》这样的影片。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叙事张力,或许将意味着一个新的中国国族主体的出场。以上分析不同于当前大多数文化研究者所做的表象解读,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或后现代主义理论所进行的“消费社会批判”,而是在深度模式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批评原则和历史性辩证方法。
这一新的中国国族主体的面貌在思想界也有所表现。《“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一文细致梳理了21世纪初随着中国崛起而在国内学界涌现的各种“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话语,指出他们都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出发来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文明”在此意味着新的阐释平台和研究范式,致力于打破古/今、中/西乃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种种区隔,站在“中国主体性视野”中探询当代中国历史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意味着从西方中心范式尤其是现代化范式向“中国学派”的转变。
作者对此所作的肯定,体现出她对新时代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正在进行的“文化自觉”努力的关注。与此同时,她也对这一潮流保持反思:“文明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虽然被“中国崛起”和“传统文化热”所加持,其致力于建构的中国主体性内部也包含两面性。一方面,缺少政治化的自觉使得传统文化往往成为强化社会凝聚力与调解、转移结构性社会矛盾民族主义运作的場地。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市场形态以及独特的世界观体系也是在“现代”之外来思考人类社会的重要资源。因此她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批判性思想资源,以重新构建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主体性位置⑩,这意味着真正有自我反思意识的主体性建构的开始。而这种主体性建构的范例就是作者在此文中所提到的汪晖,这本文集中对汪晖近年来的研究也另有一篇总结性分析。作者指出汪晖通过古今对话把传统中国的“内在视野”变成我们自身的内在反思性的视野,在古典与现代处于同等的、“互为主体”的思想平台上,为研究者回应当代问题提供批判性资源;以“人民”为主体探寻新的的普遍政治的可能性,这与其他不少文明论者以传统的“天下”世界观与“士”的社会功能为当代形态却缺少转换构想的论述,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与她所评论的汪晖在研究方法上存着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批判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和启蒙主义把自己限定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框架内;都认识到今天的“社会科学”是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而兴起的学科建制,需要加以反省;在对待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也强调了“互为主体(性)”。甚至我们在读到她偶尔批评汪晖没有把“现代化理论”彻底历史化的时候11,我们也会思考她是否有时候也没有将“女性的权利”(“我是女性,我和男性不一样”)彻底历史化。当然,这只是本书唯一给某些读者这个感觉的地方,而作者在文中也一直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与女性话语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她将女性主义话语和意识加以历史化更多时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在分析小说《青春之歌》时,她就反驳了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这一小说中的政治叙事一概视为结构化、本质化的男/女权力关系模式或关于性/欲望的性别关系的“再解读”12。
这些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原则贯穿阐释始终的特点也都深刻体现在本书第三辑关于“性别问题”的三篇文章的分析里:它们分别审视形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文化和政策具有关键意义的“延安道路”中的性别现象,将三个不同时代文学和文化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并同时检视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以及对丁玲一生所变和不变的主体性特征进行重新阐释。显然,所有这些对文本进行的历史性的考察,都意在以“再解读”为载体,为新世纪中空而匮乏的主体,特别是为当代社会主义女性话语实践,提供启发性的理论思考和借鉴。
三、1940—1970年代文学的再解读:“英雄”与“新人”的主体性
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个趋势是运用新思路,对于1940—1970年代即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范畴进行再解读。这也是近二十年“重写文学史”的研究重点。本书的第四辑就从“民族形式”建构的角度,重新思考了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实践的历史机制,借此探究当代文学“在何种意义上既延续了五四的现代化诉求、又塑造了当代中国现代性书写的独特路径”1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和相当一段时期来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不少致力于“解构”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新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不同,她所做的是坚持社会主义价值意义的历史探寻。而她是按照杰姆逊所说的“历史化”的原则思路来完成这一使命的。在这一方向上,近十年来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所进行的工作也颇为令人瞩目。14
这种研究的独特性在书中重新阐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区别中首先得到体现,人们今天理解和谈论的文学仅仅是柄谷行人所说的现代文学、民族—国家、内在的人的三位一体结构,而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我理解则与此不同:“人民”超越了特定阶级的局限,其政治形态的想象也要求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要超越所谓的“国民”(或“内在的人”)的“个人主义”,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想象15。作者由此批评了两种主流观点,一是新启蒙话语否定“当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将其视为“畸形”文学形态;二是“新中国文学”“共和国文学”(更不用说“民国文学”)这些概念的倡导者强调的“当代文学”不过是“现代文学”的延伸与变形,将其视为“民族—国家文学”的特殊形态,或“国家文学”16。总之,它们都拒绝考虑社会主义理念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历史作用和价值。
但阶级论和国家论都无法清晰而自觉地阐释如福柯、柄谷行人所点明的“现代文学”中文学、人、国家的三位一体话语装置,因此对当代文学阐释呈现出模糊性,而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可以从它对现代文学在这个装置所展开的质疑之处入手,故而“民族形式”框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在此框架下,“民族形式”论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视为当代文学的两个“真正起源”。引用的一些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意在说明,“当代文学”的发生是直面并克服中国社会城乡的结构性鸿沟的现代化实践的结果。这使得其建构“内在地包含了如何创制出同时包容西欧式民族—国家与古典中国的‘帝国’传统的政治主体和政治形式这种历史要求”。与此同时,1940—1950年代“冷战”格局在亚洲形成,当代中国关于国家政体与文化认同的构想,又内在地必然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求。因此,1940—1970年代的当代中国,其国家构筑与文化认同的基本形态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帝国”的历史传统与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三者的混杂17。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实践中的矛盾和冲突是这三种结构性力量和文化势力碰撞重组的结果。这种在动态的历史性关系网络中审视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特征的做法,显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的重视事物关联性、互动性的精髓。
这一“三重历史结构”下的当代文学关于个体—社会的内在想象方式表现在对“新人”的书写上。对于“新人”的阐释在过去这些年并不少见,但大多出于较为简单的政治观念性图解,而当我们诉之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角度加以观察时,就会发现力图超克“内在的人”而创造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人”“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必需,也是有着地区、阶级、族群等多重内在差异性的当代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必要过程,因而必然与民族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紧密地关联在一起”18。但“新人”与“人民—国家”的构想始终存在含糊性和内在的紧张,因此常常未能摆脱“类型化”或概念化、理念化。这是因为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念上都还存在个人与集体、人物个性与理念类型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框架。而在“民族形式”的诉求上引入中国历史与文化资源,可以提供突破这种框架的可能性19。这种重新审视“新人”的研究因此突破了在观念中寻找对应物的简单方法,而体现出综合社会学、政治学和比较文化学视域的跨学科的特征。
在对具体的文本解读中研究者看到,在表现农村合作化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新人”常常并不占据小说的中心位置,真正主人公常常是村镇或结构性的社会单位(家、户、村、社),在其中个人处于伦理性地位。换句话说,人物并不是这一空间的中心主体,而是空间的结构性因素与力量的呈现。在这一结构下,不但“内在的人”的现代小说的透视法则被摒弃,主人公超越个人主义的主体形象也不能完全用社会主义的阶级理论解释。这种空间—主体的书写模式以及人物主体性内涵及乡村社会人际关系,与传统中国“礼仪社会”的构想潜在吻合。在《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一文中,作者详细阐明了这一点。去核心家庭化的户与社的关系想象已经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这种“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是建立在公共性社会劳动的基础上,并在劳动者自我管理的过程中自发地出现,触及了在传统社会关于“公”“大同”理解的基础上展开“社会主义”想象的可能性20。它是对于一种中国“内生性现代主体”构造的独特尝试21。但遗憾的是作者在这里还未对其内涵详加阐释,而是说明虽然社会改造中城乡结构关系的变化使得赵树理文学塑造的历史主体丧失了现实土壤,但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农村问题、全球格局中文化自觉的内在诉求,又与赵树理作品形成具有历史意味的对话。这种在历史动态性变化的社会结构中探寻文学文本生成与演变的前因后果,不但可以发现其审美特征,而且在“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之下,对于社会与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也可得出洞见。这不是对于文学采取社会学研究范式,但却让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成果彼此互补,都从中受益。
在另外一篇《40—60年代革命通俗小说的叙事分析》一文中,作者检视了革命通俗小说,发现其“讲故事”的意味远大于“写小说”的意味。但远为重要的是,她的问题意识在于看到了这一文体以独特方式串联起了古典、现代与当代的文学形态,为讨论三者的连续与断裂提供了具体的场域22。古典中国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礼仪、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三者间,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与话语装置上的不一致性,这导致“英雄传奇因其相似性而作为一种叙事类型被调用,同时又因其话语装置上的不一致而无法超越古典,从而必然被置于次一等的位置上”23。这里的论证层层深入,逻辑严密,结论颇为令人信服。对不同文体的分析结合了对它們的由古到今的历史性内容与社会性内涵的讨论,对其包含的政治性和文化性潜文本的引入,得以有效解释这些文体特征之间的关联和本质区别,使得它达到了杰姆逊所说的历史/政治阐释的深度和高度。
四、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历史化/政治性的阐释实践
要想建立主体性,需要一种自我反思的意识,对自己的理论预设和文化/政治立场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知,并不断进行自我清理。作者不满于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1980年代中国文化圈所谈论的“五四”传统,而将此议题转化为对这种思潮所依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预设下的诸种话语形态的历史性分析,考察其特定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这里的基本问题意识是“一种批判性的自反工作,即那些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真理或价值观的东西,是怎么被构造出来的,它回应的是怎样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因为“研究者总是在他/她置身的当代语境和意义系统来看待过去那段历史”,他们的结论就包含着研究者对那个时代的“基本历史判断和对当下知识状况的现实判断”24。由此我们不但发现研究者强调阐释者主体性的介入,而且那种自我批判的反思性正是其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种反思性首先表现在研究者的总体性意识。作者认为对于国族叙事问题的考察,需要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观察视野,才能给出更为深入透彻的阐释。贯穿其研究始终的“中国认知”与“主体性建构”都在这一总体观念下得到诠释。
其次,围绕在研究对象及其认知框架和历史结构身上的“权力关系”得到重点关注。有时这种对权力关系的重视被归之于后殖民批评的启示25;有时它又被比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在谈到伊格尔顿将其文学理论最终归结为“政治批评”时,贺桂梅谈到他所指的“政治”是“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政治的批评”指向了对“语言(或含义)形式和权力形式之间的那种多重关系”的发掘26。但更多时候,这种对“权力关系”的强调让我们想起福柯的知识谱系学:比如要揭示出“寻根”文学思潮和“纯文学”的文本实践及其知识谱系。但细究之下,我们将发现,贺桂梅所实践的并非是尼采、福柯式的那种知识谱系学和权力关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下的历史化与政治性的阐释立场。
这一关键实质可以从研究者的具体分析操作中见出。比如,她总结自己清理“纯文学”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特性”的工作,揭示的是“纯文学”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所完成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对“意识形态”去蔽的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一贯的批判职能。作者自己则把她的基本研究方法称为“知识社会学”,并认为曼海姆划分的“总体意识形态”和“特殊意识形态”来对“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历史性及其对话关系进行理论性思考”的方法给了她很多启发,认为其独到之处“在于它能够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视野中来观察知识主体的特殊位置,并对知识主体的‘特殊’视角与这种‘总体性’之间的关系,做出有效的自反性的理论说明”27。曼海姆对于贺桂梅方法上的启示,就在于这种对带有马克思主义唯物立场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关注,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本身就是自反性的。她所看重的“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历史性及其对话关系”也正是杰姆逊所主张的历史性/政治性的阐释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在本书中没有详细阐明“历史化”这一概念,有时只是简略一句带过:历史化是“在一种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新的现实问题意识中,来重新定位和理解”28。但她所表述的“必须将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纳入思考范围。‘文学性’问题从来就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语境”29,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历史和文化语境”作为所研究的文本概念的“潜文本”的杰姆逊所说的“历史化”的深刻内涵。在这种实质上的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化的工作中,作者首先看重对“文学体制”的清理(而“文学性”实际上正是“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看到她提出如下主张:“为了实现对文学(研究)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对那些仍内在地制约着我们认知和理解文学的‘文学体制’进行一种自觉的历史清理。只有跳出这一体制,‘纯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能被认知。”30
“意识形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里,指的是“错误意识”,但贺桂梅也没有直接用这个概念。在谈到寻根文学潮的时候,她提到作家“渴望把自己投入那崇高客体,并成为它的化身”的“集体无意识”31。与其说这里指向的是荣格分析心理学里的概念,不如说它接近于杰姆逊的政治阐释学里的核心概念“政治无意识”。而贺桂梅的分析与杰姆逊的阐释学最为接近的一个表征,就是时常出现的“寓言”概念的运用,不管是直接运用杰姆逊所提出的“第三世界寓言”或“民族寓言”,还是间接使用的“历史寓言”32。有时,“寓言”以一种更深刻的含义出现,比如她说1980年代文学界引介“新批评”可以视为社会/文化变革的自我否定的“寓言”33。这种解读实际上将社会现象也当作潜在的文学和文化文本,以及潜伏于文学和文化文本内部的“潜文本”,属于杰姆逊所言的“历史/政治阐释学”的内涵。在具体的阐释实践中,作者既利用了各种理论比如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洞见,又运用了西方各位社会学家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但她从来没有盲目跟风地使用西学理论解释中国文本,比如她指出中西方运用同一理论却导向了不同的结果34。这种对语境差异导致不同后果的认知,也是其看重的辩证意识的产物。
中国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在讨论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引入文学研究后,会导致文学研究丧失“美学”特性,或者是否能够有效解释文学问题。但贺桂梅的研究实践证明问题不在于社会学视角的引入,而在于是否研究得当。比如,她注意到地理空间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透过内陆乡村民众的阅读记忆与文化习惯,以及与之伴生的生活—伦理—世界观,而与古典中国小说/社会传统建立起直接的关系。”35这一洞见可以说是她的一大发现,不但可以从宏观层面解释文学范式的变迁,而且可以从微观层面阐释文本的特征。又如在《长时段视野里的中国与革命——重读毛泽东诗词》一文中,她综合运用了李零、唐晓峰等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来理解毛泽东诗词中的革命山水的地理载体和内在世界观的想象依据,以及从其所表现的山水景观的“地理时间”来理解其宏阔美学视野的时空架构36。由此,她异常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诗词在不同时期艺术特征的变迁。也正是通过社会学(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引入,使得她还可以解释一些更大历史时段的问题,比如当代文学在“文革”期间的激进化,以及1970—1980年代的转折。
引入这种政治经济学框架进行文本和现象阐释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比如在《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一文中,她说明自己要“探讨(文本中)女性主体塑造在不同时期的表意实践,由此呈现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历史性变迁与共时性结构”37。另一方面,她也指出“正是制度形态和权力结构的规约性,而不是作为‘人’的‘本质’,决定了(文本中)女性问题之政治性的同一性内涵”38。这种在历史性的社会机制与文学和文化文本间双向互动彼此显现,正是杰姆逊所说的历史性/政治性阐释的要义,也是化解担忧社会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学科分隔焦虑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该会议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和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举办,于2021年10月22—24日在中山大学召开。参见赖宁:《“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暨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顺利召开》,“中国新文学学会”公众号2021年10月30日报道,https://mp.weixin.qq.com/s/t2Kultf48c8O214FbOYk2Q。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113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賀桂梅:《打开中国视野:当代文学与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7、25、33-34、39、70、90-91、184、138、103、211、219、220、226-227、229-230、234、289、287、281、279-280、7-8、73、71-72、9-10、7、43、43、28、29-34、62、55、282、157、187页。
③Fredric Jameson,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12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14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6贺桂梅:《长时段视野里的中国与革命——重读毛泽东诗词》,《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王晓平,同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