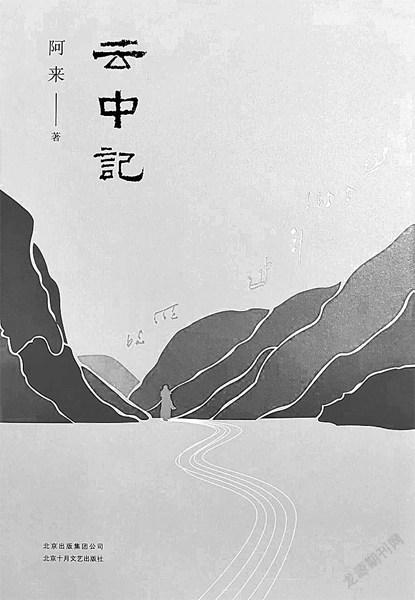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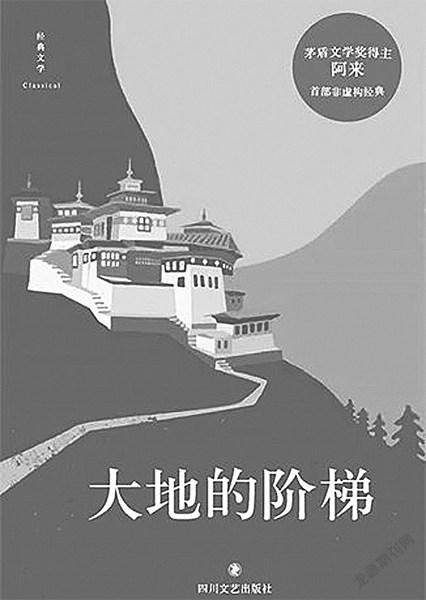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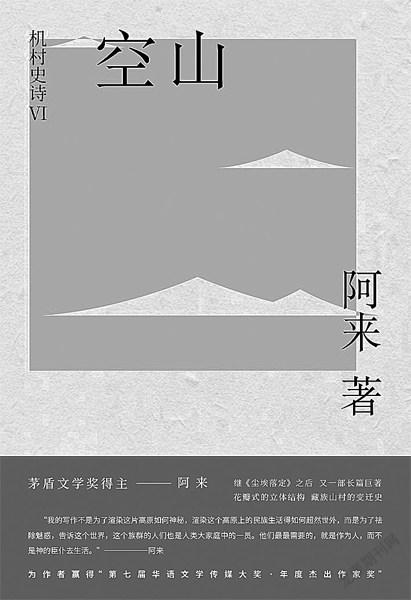
一
如果从迄今为止的写作历程来判断,说藏族作家阿来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有鲜明生态意识的作家之一,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这有他的《大地的阶梯》(2001)、《成都物候记》(2012)①以及其他大量地理生态散文,还有长篇小说《空山》六卷本②(2004—2008)和《云中记》(2019)等作品为证。后者在2021年度获“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评委会授予的“年度杰出作家奖”,以褒奖阿来“延续了一种由边地与少数族群出发而通达全球视野与普遍共识的开阔写作,书写了万物并生不悖,文明和谐共处”③所取得的成就。
这种生态意识的形成,首先来自作家个体的切身体验。阿来的出生地四川马尔康县马塘村本来处于一片茂密的白桦林中,满坡的林子曾是童年阿来采药和嬉戏的天堂,“但我没有能够与这片美丽的树林度完整个少年时代”,白桦林在20世纪60年代因城市建设需要被采伐殆尽,“古村岂止是失去了这些白桦,我们还失去了四季交替时的美丽,失去了春天树林中的花草与蘑菇,失去了林中的动物。从此,一到夏天,失去庇护的山体被雨水直接冲刷。泥石流年年从当年的泉眼那里暴发,冲下山坡阻断交通”,但事情远没有停止,“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飘满了大树的尸体”④。这当然是四十年之后阿来的回忆和审视,已经带上明显的生态批判眼光,这里所记录的儿时经验本身,也并没有在阿来创作的一开始就成为其核心主题。我们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所看到的,是阿来对于康巴藏族历史的传奇式叙事,他当时在叙事艺术上的针对性,主要是为“逃脱那时中国文坛上关于历史题材小说、家族小说,或者说是所谓‘史诗小说的规范”,要“在这僵死的规范之外拓展一片全新的世界,去追寻我自己的叙事与抒发上的成功”⑤。这种对“边地”藏族叙事的史诗性追求,也是阿来写作独创性因素中贯穿至今的重要内涵之一,从《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六部曲,正好是四川阿坝嘉绒藏族地区20世纪历史变迁的投影。
阿来的生态意识的真正唤醒,应该也是感受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的生态思潮的结果。随着中国大规模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展,一时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断出现,客观上迫使中国作家开始认真对待生态问题。1999年是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年份。这年10月在海南召开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是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各地的三十多位作家和学者与会,带来了经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生态批判思潮,他们反思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在生态问题上可能存在的盲点,呼吁重视生态问题,质疑无视生态的所谓“成功”,“唤醒对草木虫鱼悲情的感受”⑥。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坛生态意识的广泛觉醒,对现代化与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进入一个高潮,韩少功、张炜、蒋子丹、叶广芩、贾平凹、于坚、迟子建、雪漠、陈应松等作家先后都创作出具有明确生态意识的作品。就在同一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起组织了名为“走进西藏”的“文化创作出版活动”⑦,阿来是首批受邀的七位作家之一。虽说这是一次由媒体事先策划的行旅写作活动,后来也被视为“媒体策划与批评”的一个典型案例⑧,其策划重点在于对边疆区域文化的考察、探险与记录,但阿来并没有完全按发起方的预定路线与方式行事,而是把旅行与写作的重点放在故乡四川阿坝的嘉绒藏族聚居区,自称是“预谋已久”的意图。他“更多的将不是发现,而是回忆,我个人的回忆,藏民族中一个叫作嘉绒的部族的集体回忆”⑨。这里不得不提及阿来本人复杂的族裔和文化身份:阿来虽然自认属于藏族中几乎最为边缘的嘉绒支系,但事实上又是藏回混血——母亲是虔诚藏族佛教徒,父亲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阿来早年生活在藏语山村,通藏语方言而不会藏文读写,接受汉语学校教育并以汉语写作。由此可知,作家阿来对于语言、文化与族群身份具有天然的敏感。
正是1999年的这次故地重游,使阿来得以重温早年记忆,并逐步获得批判性的审视眼光。这种回忆与审视,至少包含了兩种精神指向:第一是指向四川阿坝地区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阿来对那些来自域外他者的西藏想象,始终保持一种警醒与批判,不论是神秘诗意意象,还是“边地少数民族”想象,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阿来所质疑的那种“西藏是一个形容词化了的存在”⑩。它们首先排除了具体的历史性;其次,又把西藏想象为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于阿来的故土而言,那就是阿坝地区的嘉绒支系差异性和特殊性。第二是指向川西北这一特定地域的地理生态处境。阿来对方圆八万多平方公里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理,有一个精确的描述:“这个地带在现在的地理描述中应该是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第一弯上的若尔盖草原,和草原东边一直向四川盆地逐级而下的岷山山脉和邛崃山脉的腹地。”11这西北部的草原和东南部的山地一起,就构成了从四川盆地到世界屋脊这一“大地阶梯”的过渡地带。
这两个精神指向对应了阿来的两种观察视角:一则是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历史、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人文视角;一则是在东亚大陆板块整体中的地理视角。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阿来的人文地理学视野。而阿来在20世纪末的那次故地重游所激发起来的生态意识,正是基于这一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这也是他的生态观念和生态书写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中国作家的明显特点。从这种观念与视野基本形成而言,作为非虚构文体的《大地的阶梯》是阿来写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认为,书中的这段文字是上述审视眼光的典型表述:
从四川盆地边缘纵深向青藏高原边缘的阶梯形群山达两三百公里是一个巨大伤痕。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痕。虽然这个伤痕地带也曾有过民族间的冲突与一些战争,但这些冲突与战争大多发生在冷兵器时代,还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生态灾难。这个伤痕的造成,就是进入现代史的近百年间,人类以和平的方式,以建设的名义,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与生存的名义,无休止索取的结果。12
作为隐喻的大地伤痕,既对应着人类冲突的历史创伤,也对应着自然所经受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人文与地理、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在这段批判性文字中交集。自此以后,阿来的虚构性写作也在史诗叙述的架构中增添了一种明显的、富于特点的生态视野,这在随后问世的“机村史诗”六部曲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尤以《天火》与《荒芜》为最。不过,这种观念与视野的形成,如何转化为虚构写作中的创造性,需要作家在叙述和表达上的持续探索和尝试。
对阿来而言,文学传统中的自然书写是首先需要反思和扬弃的对象。他对汉语文学传统中大量自然书写,取一种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自然,已被过分人格化,花鸟鱼虫、梅兰竹菊、豺狼虎豹,在一代代文人笔下,都已演化为隐喻、象征或者意境,如丁香的愁、莲花的洁,其象征意义已经固化,相应的自然意义则日渐萎缩和退化,并极言在“我们的抒情文学传统中,自然是消失和不存在的”。阿来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断或许因其偏激会引来争议,但他提出应该像梅特林克、普里什文、契诃夫和屠格涅夫那样,“把自然和人当作同样的生命来看待”13,“把自己融入自己的民族和那片雄奇的大自然”14的主张,至少体现了其对文学的自然书写方式的自觉,并在外来文学中获得了某种方向性的参照与启迪。
不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建构性的探索与创造本身。在《大地的阶梯》后记中,阿来曾这样放话:“我坚信,在我下一部长篇创作中,这种融入的意义将用更艺术化的方式得到体现。”15这里所说的“下一部”,会是指哪一部作品呢?如果按照写作时间,可以认为阿来所指的是《空山》即“机村史诗”系列,批评家张学昕就是这样认为的16。但阿来的艺术尝试与探索的路并没有终止,在其迄今为止的长篇小说中,《云中记》更应该是他理想中的“下一部”。
二
长篇小说《云中记》以2008年“5·12汶川地震”为背景,讲述四川阿坝嘉绒藏族村寨云中村的灾难遭遇及其灾后重建故事。阿来本无意把它写成一部生态小说,作品的题记之一就是“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消失的城镇与村庄”17,“歌颂生命,甚至死亡”才是这部地震题材小说的本意18。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发生在阿来的故乡,他又是救灾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书写这一重大又亲历的事件本是顺理成章的,但阿来却迟迟不愿下笔,而要等到大地震十周年之时才开始动笔。这十年间,他相继出版了《瞻对》(2014)、《蘑菇圈》(2015)、《河上柏影》(2016)和《三只虫草》(2016)等几部作品,但所写都不是那场地震。因为阿来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有关灾害中的惨烈、悲情、救助等大量细节,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而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书写,除了作为亲历者呈现灾难场景、叙述刻骨铭心的悲情外,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如何能使文学之光不被现实所吞没呢?
对于阿来,长达十年之久的情感控制、经验反刍和动机酝酿,是为了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对于这个题材的表达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云中记》所呈现的以“一个人,一个村庄”为核心,“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19。一个人“就是祭师阿巴”,一个村庄“就是位于岷江岸边半山腰,海拔2800米的一片台地上的嘉绒藏族村寨云中村”,它在“5·12汶川地震”中沦为废墟,并处于震后山体的断裂带下,五年后又与山体平台一起,轰然坠入岷江。这样,在地震发生十周年之际,阿来终于找到了针对这场地震的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其中写嘉绒藏族苯教的最后一个祭师,如何完成他的志业,祭奠一个倾塌了五年的村庄,回顾她的历史,超度她的灵魂,最后与她一起消亡。全书的叙述笼罩在一种浓重的悲怆氛围中,就像小说题记之二所顯示的基调那样:“向莫扎特致敬/写作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如此,作家阿来的“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20。
《云中记》的故事是从大地震五周年之际展开的:汶川地震后,云中村的幸存者全部内迁到四川平原腹地,村民们在移民村过上了新的生活,种茶、打工、开民族风味的山菜馆等,但重大伤亡和家园倾毁所带来的深刻心理创伤仍难平复,村里的藏族祭师阿巴一直惦记着死难者的亡灵和自己的职责。在地震五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阿巴不顾次生地质灾害的危险,在两匹马的陪伴下,毅然只身上山,回到随时有坠塌危险的云中村废墟,以嘉绒苯教的仪式,为天地山川、草木屋宇与人畜亡灵祭祀超度,并执意与云中村共存亡,最后同村庄一起坠落而下。
小说的叙事,也以上述情节为线索,以时间为章节标识而依次展开21,叙述阿巴在地震五周年祭的三天之前,独自上山返回云中村废墟,从准备和实施祭祀,到随后几个月的独自守候,最后随云中村一起坠落的经过。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阿来并没有正面展开地震发生时的惊恐一幕,也没有正面呈现震后的惨烈与救援中的悲痛无奈、奋不顾身和守望相助的具体场面与情节,即不以现在时态连续展开灾难叙述。所有关于大地震的发生、震后救援与重建的大量场景与细节,都是穿插在阿巴的祭祀招魂仪式中展开,以主人公意识回闪及对话等方式交错呈现。这种叙述结构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既指向“5·12汶川地震”及震后救灾这一核心事件,也指向震后五年间当地村民对严重心理创伤的修复和灾区的重建;在相反的方向上,更指向云中村的震前历史,乃至追溯到族裔迁徙传说与起源神话。这就使作者得以从地震大事件的正面叙述中挣脱出来,获得表达上的某种自由空间:不仅可以确定一个特定的叙述角度,还可借此呈现和表达时空上更宽广、意蕴上更复杂的主题,其中也包括这部小说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意义上所体现的意涵。
如前所述,阿来本无意于把这部地震小说写成一部生态小说。虽然文本中也涉及了许多有关生态问题的场景和情节,如过度放牧致使草地荒漠化、滥挖兰草导致资源枯竭、对野生保护动物的捕猎、盲目建造水电站导致泥石流灾害,等等。这些当然是生态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内容,但并非《云中记》这部地震小说叙事的关键构成,它们与地震这一核心情节并不具有必然关系,事实上作者也没有对此费太多的笔墨。
本来,生态主义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反思与批判人类如何在文明进程中不加限制地向自然攫取,由此导致自然生态的系统崩溃、资源枯竭、灾害频发等严重后果,由此调整当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但地震是天灾,其根本起因即地壳运动与人类行为和意愿本来并无关联22。如果说生态主义意在追究生态恶化进程中人类所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面对地壳板块运动所导致的地震,人类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它的降临,包括对生命的毁灭、对生态的破坏。如此,关于地震天灾的叙事似乎只能归于宗教宿命主题,或如道家哲学所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情”,人类对之只能无可奈何。但如果扩大问题域,答案就不会那么简单眀了:如果说地震的发生并非起因于人类也非人类可以控制,那么地震灾害包括它的次生灾害给不同时空、不同文明程度、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类群体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不同的;如果引入文化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视野,则有可能揭示特定地震带与特定的族群、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具体历史关联。由此还可进一步追问:在一场特定自然灾害爆发与次生灾害的后续发生过程中,相应于不同的预防、救灾和重建的手段与机制,同等程度和相似类型的灾害对不同社群的身体与心理、生产与生活所造成的伤害,其方式与程度有没有、有何种差异?这种差异的具体成因如何?《云中记》正是在这一维度提供了想象和进一步阐发的空间。
小说叙述的“5·12汶川地震”处于中国四大地震带之一的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震带上,是印度板块大陆嵌入并挤压的结果。阿来借笔下瓦约乡乡长仁钦的分析,向读者呈现了这一视角:
世界地理板块,印度次大陆从南边冲过来,使得青藏高原高高隆起。这股力量一路往东,瓦约乡所在的岷江河谷这些高耸又破碎的山地,就是这股持续不断的力量压迫的结果。这力量在地下积蓄,过百十年就爆发一回。那在地下暗黑处运行的力量只顾造成新的地貌,却对地面上的人间悲剧毫无同情。23
从地震学角度看,这种地壳运动并不起因于生活于地表的芸芸众生,但这片土地为什么由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的人群依附其上?为什么处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界的山峦皱褶地带的阿坝地区,恰好祖祖辈辈生活着嘉绒藏族?阿来通过祭师阿巴对云中村历史由近及远的回忆,追溯了嘉绒藏族古老的族群迁徙历史,使这一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问题得以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这里,具体而独特的地理、民族、宗教、文化与历史相互叠加,作为天灾的地震也与特定的人群和生活方式相互交织。而与地震相关又远远超出地震的生态系统的种种遭遇,也就在这多重交织中才可以全部显现。这其中就包括了生态批评通常所关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即使相对于地震这样的天灾叙事,也不必然与生态问题无关,而同样可以呈现其生态批判的意义。
因此,尽管阿来不是刻意将《云中记》写成一部反映生态问题的小说,但其生态意识使他能把小说所要思考的生死问题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中,置于现代文明进程所遭逢的种种问题中去认识。正如小说另一则题记所示:“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24阿来所思考的有关生命的意义、灵魂的有无、族群与认同、信仰与科学、仪式与疗治的关系等问题,不仅属于人类自身,也属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大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云中记》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品。
三
在“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给阿来的颁奖词中,“边地与少数族群”这一关键词,对《云中记》的描述虽然并不完整,但也反映了该作在当代汉语文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作品给汉语读者带来最深印象的,或许不是所叙述的“5·12汶川地震”这一著名事件本身,而是在灾难背景下所呈现的主人公阿巴这位藏族苯教祭师形象,阿巴所施行的古老祭祀仪式及其感染力,以及借助阿巴所上溯的嘉绒族裔历史与古老传说。
《云中记》祭师阿巴所信奉的是藏地苯教中最传统的一支25。由于它根植于藏族原始文化之中,因而对藏文化特性及传统有着深远影响。阿来在小说中所描述的是在藏地最为原始、行将消亡的宗教传统,选择一个祭师阿巴作为主人公,显然有着复杂的寓意,阿巴与“阿坝”谐音,也透露了这一消息。而今天作为阿坝行政中心的“马尔康”这个地名,也是源于15世纪之前当地曾建起的一座规模宏大的苯教寺院。
在藏族聚居区,其古老而悠久的宗教观念和仪轨行为,已经完全内化于藏族民众的共同生活习性之中。今天藏族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中,有许多也是古象雄時期留传下来的,比如转神山、拜神湖、插风马旗、插五彩经幡、刻石头经文、放置玛尼堆、打卦、算命、转经等习俗都有苯教遗俗的影子。小说《云中记》中“第七天”一章中阿巴所吟诵的阿吾塔毗的传说26,就对应了这一最为古老的神话传统。阿来选择藏文化的这一脉传统作为小说主要呈现的对象,显见其追溯自身文化血脉的宏愿。其实,阿来在这方面的准备,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阶梯》就已经有系统的呈现。
儿时的阿巴只在黑夜里和山野无人处(在磨坊憩息)偶尔看到父亲的一些祭祀动作。改革开放后,政府为拯救民间文化遗产,说服阿巴担当起祖辈的职业并将他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阿巴作为祭师最起码的一套祭祀仪式规程,还是在当地政府组织的“非遗传承人”培训班上,由邻村的一位佛教喇嘛来传授的,这位喇嘛显然在信仰上不认同、甚至瞧不起阿巴的苯教,声称“你们的阿吾塔毗不可能同时是金刚手菩萨”,只能作为金刚手菩萨的陪侍27。而阿巴一开始也并不接受这一神职身份:“呀!怎么可能!一个人听过《不怕鬼的故事》那本书里的全部故事,上过农业中学,当过云中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电员,现在怎么成了一个祭师?”28他是在被动地接受“非遗传承人”这一名号,为配合当地政府开发旅游资源而主持起祭山仪式后,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知识、信仰和祭山仪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慢慢寻得苯教祭师身份感。
真正使阿巴领悟苯教传统的是云中村的老喇嘛的临终传授29。阿来在小说中设置的这位老喇嘛,是作为祭师阿巴的精神导师形象出现的。他的身份虽然是个佛教喇嘛,但实际上却是苯教的传人。小说里喇嘛出场时就已经是一副老态,似乎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牙齿脱尽,几乎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每天呆坐于门前的苹果树下。但这个形象正是传统蛰伏待机的象征:苯教古老传统借助于佛教的面目和喇嘛的躯壳保存下来,等待着它真正的传人。已经有了苯教祭师身份的阿巴,对这位同村的老喇嘛的态度,也逐渐从不在意变为好奇与疑惑。只是有一天老喇嘛突然喝令阿巴跪下,在兜头一盆冷水之后,再给阿巴一番面授机宜。从此阿巴神清气爽,眼睛明亮。而喇嘛之后则又至死闭口不语了。我不知道阿来笔下这一段情节,是有苯教传说的原型依据,还是阿来的想象虚拟,但它不仅生动,富于传奇色彩,而且形象地寄寓了阿来呈现藏地古老文化传统的用心。
从人物塑造角度看,老喇嘛醍醐灌顶式的“棒喝”或“点化”,是阿巴精神成长历程的一次突变。但作者并没有直接呈现人物内心变化过程,而是给予如上所述的传奇性叙述。与此形成对照的另一次精神突变,就是他亲历并目睹的陡然降临的大地震,灾难的惨烈场景给云中村人所带来的重大心理震慑、刻骨的生死伤痛和普遍的精神迷惘。在灾后重建和移居的五年里,阿巴反复追问着生死的价值、灵魂的有无和神灵的意义。作者并没有明确地告知,阿巴这个云中村曾经的“文化人”和“第一个发电员”最后有没有真正信奉古老的传统,他对有没有灵魂似乎仍存有一丝保留,但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祭师的身份与责任显然有了深深的认同。他对地震后一起来到移民安置地的云中村人说:“你们在这里好好过活。我是云中村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30在另一处,小说以叙述人口吻这样陈述:“但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是……如果万一有的话,那云中村的鬼魂就真是太可怜了。作为一个祭师,他本是应该相信鬼魂的。他说,那么我就必须回去了。你们要在这里好好生活。我要去照顾云中村的鬼魂。”31正是灾难的突然降临,逼迫着阿巴完成了作为祭师的身份认同,又独自返回云中村废墟,为那里所有自然与生命遗存一一施祭,并陪伴古村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从而践行了作为最后一个祭师的使命。
四
作为自然灾害题材小说,《云中记》虽然将灾难发生的惨烈场景和抗震救灾的过程以五周年之后片段性回溯的叙述方式加以克制性呈现,读者仍能借此想象当年举国救难、全民赈灾、守望相助的感人情景。对于阿来这样成熟的作家来说,这样的场面与基调的展现与叙述把控,是读者意料之中的。但阿来在灾难叙述的同时显现了另一个特质,即伴随这种基调的对于所谓“灾民心态”32的种种表现与“表演”的刻画与批判,这种清醒的批判意识既针对大地震这一灾难场景中的某些特定行为,也指向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异化”现象。它们包括对灾难的商品化消费、表演,乃至唯利是图的行为。如央金姑娘灾后的舞蹈直播,祥巴策划的乘热气球观看云中村废墟的旅游项目,以及其他一些对死亡与痛苦的麻木心态,等等。总之,在阿来的叙述中,灾难所引发的惊恐与创痛、救难赈灾的悲悯与感人,并没有淹没其对“灾民心态”的审视与批判。这种批判意识的获得和呈现,一方面是之前的“史诗性”写作追求的某种延续与变奏,另一方面也是他将这一重大题材的写作冲动克制、延宕了十年之久的一个回报。
而这种批判理性在作品叙事中的呈现,正与原始苯教传统及祭师阿巴的形象有关。在作品中,这种原始信仰传统中对生灵万物一视同仁、对善恶的包容与超越,与阿来所谓的“灾民心态”形成一种精神价值上的鲜明对照。需要指出的是,阿来的这番用心,并不是真要为古老宗教振衰起敝,更非宣扬具体的宗教教义。正如刘大先所说的,“自始至终,叙述者与叙述对象都没有确认灾难死者的鬼魂或亡灵的真正存在,他们只是阿巴情感与幻想之物,而非某种超验的实体性存在,这与文学史上那些鬼怪幽灵判然不同……因而也并没有产生恐惧、异类、神秘之感,而是与生者的认知和创造有关”33。但作者以阿坝地区这一亚欧大陆板块(《大地的阶梯》)的皱褶地带,同时也是历史文化中处于多重边缘区域的灾难故事,和行将消逝的民间宗教祭师形象,作为小说的核心叙事场景、线索和主要人物形象,意在呈现一种古老文化与精神传统的象征。它为汉语读者呈现藏地精神文化传统的悠久、丰厚与多元,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多元文化与平等观念,以及对社会文化生态平衡与和谐的祈愿。
这种原始信仰传统也为文学作品引入了一种万物有灵的生动的叙述视野。这样的传统崇奉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神鬼精灵和自然物。由法师进行占卜、祈祷、禳解、咒术、祭祀及各种特殊仪轨加以表现,有着萨满时期古老信仰的一般特征。从文化发展进程来说,这种泛灵信仰是人类最初对自然万物的朦胧认识的表现。这一万物有灵世界,在《云中记》的叙述中,通过祭师阿巴的视角和他主持的祭祀仪式而一一展开。一年一度由全村男女共同参与的“朝山节”是祭奠山神,它是祖先阿吾塔毗的化身;为村头的神树——老柏树行仪作法,它的最后枯死是地震的前兆;震后重返云中村,阿巴为每家每户焚香祈祷,为每一位遇难的亡灵招魂超度,无论男女老幼、良善或顽恶、大度或吝啬;在阿巴眼里,山林的大小动物,田野的一草一木,村里的石碉、磨坊、塌屋、残墙、柴垛子、水池子,乃至水里的绿藻们,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都可以倾听与对话。在这个泛灵世界里,更有如遇难于巨石下的阿巴妹妹(仁钦母亲)显灵于鸢尾花这样的动人情节,它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手段,而是整个泛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阿来本无意于将《云中记》这部地震题材小说写成一部生态文学作品,但在追溯本土古老信仰传统,呈现泛神观念和通灵视界的同时,也许是无心插柳,恰好为当下人与自然关系这一生态命题及其文学表现,提供了一种激发和运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途径和生动的作品,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生态功能多样性的追求。
《云中记》这部经作者十年酝酿的作品,为书写“5·12汶川地震”这场灾难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他选择了以“一个人”(祭师阿巴)——“一个村庄”(云中村)为基本叙事架构,激发并表现了一个族群的文化传统记忆,将作者、叙述人、人物及其文化原型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熔铸到一个悲剧性的形式结构中,从而使作家本人的书写行为与祭师阿巴形象的祭祀行为,形成互为映衬和隐喻的关系,也使文学言语行为与语言(文本)结构相互耦合,共同体现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话语的施为功能。同时,《云中记》还在文学功能的多元化发掘和神话原型叙事开拓的向度上,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文本。它以一个灾难叙事,为恢复文学对创伤心理的疗治功能,克服文学因现代分化所导致的功能单一倾向,做出一次成功尝试,因而在媒介与文化融合的当代语境中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可能34;它还为发掘与转化中国丰富的神话原型资源,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题材和路径,从而在更加开阔多元、更具文化纵深的意义上,想象、呈现与阐发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为同世界文学的其他伟大传统间展开有效的对话,呈现了一个成功案例。
【注释】
①此书有三个版本:《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花重锦官城·成都物候记》(成都时代出版社,2018)和《成都物候记》(“阿来散文集”之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②《空山》六卷本系列,又称“机村史诗”六部曲,包括《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
③“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由十月杂志社组织,首届奖项于2021年9月4日在贵州绥阳颁发,评选范围为2019—2020年度发表作品。见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90061。
④⑨11121415阿来:《大地的阶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55-56、338-339、13、58、343、343页。
⑤阿来:《世界:不止一副面孔》,载《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207页。
⑥白尔木:《人与昆虫的共同命运——99海南“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纪要》,《新东方》1999年第6期。
⑦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由新闻出版机构组织的考察与写作活动一度成为文化热点。其中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解读中国民族文化万里行”,于1999年组织的扎西达娃等7位作家“走进西藏”、2000年组织贾平凹等9位作家“游牧新疆”,随后出版“解读中国系列丛书”;此外,2000年,鹭江出版社策划名为“极地沉思”的考察写作活动,组织葛剑雄等6位人文学者赴南极考察写作。
⑧宋炳辉:《文学媒质的变化与当代文学的转型》,《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⑩阿来:《西藏是一个形容词》,《青年作家》2001年第1期。
13阿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与书写》,《科普創作》2020年第3期。
16张学昕:《孤独“机村”的存在维度——阿来〈空山〉论》,《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
17阿来:《云中记》题记之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18192032阿来:《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有关〈云中记〉的一些闲话》,《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2期。
21小说共12章,章节标题依次为: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和第六天、第七天、第一月……第六月、那一天。
22地震一般分为天然地震和人工地震。人工地震当然与人类活动相关,可以纳入生态问题讨论。这里所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地震,即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
23262728293031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339、162-164、172、79、174-180、46、58页。
24阿来:《云中记》题记之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25苯教是古代西藏地区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又称“苯波教”。“苯”的本意为反复念诵,“苯波”(Bon-po)则是反复念诵者,原是藏族在远古时期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巫师称谓,尔后逐渐演化为这种宗教的名称。
3334刘大先:《作为记忆、仪式与治疗的文学——以阿来〈云中记〉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