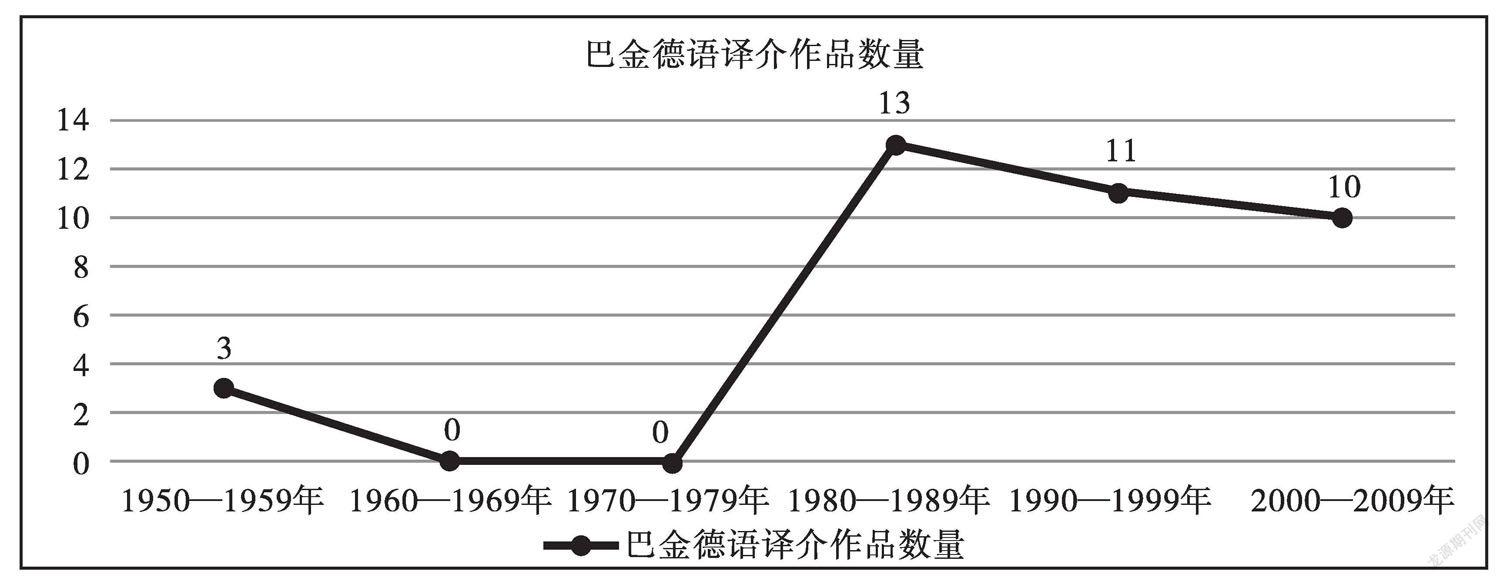
一、散文与诗的交织
必须承认,《北流》并不是那种好读的小说,在其中,我们读不到特别完整的故事,也找不出一条清晰的主线。比起那些熟稔于挑动观众情绪的“说书人”式的小说,《北流》更像是作者的喃喃琐语。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于读者的确构成一种挑战,整部小说像作者用八年心血浇灌的“意义迷宫”。也许,越是复杂的作品,就越需要一种总体化的读解方案,将小说里纷繁芜杂的细节重新结构成清晰的建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将《北流》还原为一个具体总体,其中每一个局部的意义都由其他部分来规定:所谓形式与内容、文本与历史、“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些被既往批评话语建构出来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实际上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现在,让我们从小说的语言开始。
作为进入小说世界的通道,《北流》开篇是組诗《植物志》,这组诗充满野性与巫性的独语/呓语;疯长的林莽爆发着神秘而梦幻的生命激情,而个体记忆(操场、小学新校舍、外号“猪仓”的女生)与地方志(宋朝的北流河、苏东坡上岸处、桂系军阀的礼堂、1949年的马)的线索则穿插隐现在语言的丛林之中,似乎随时准备展开他们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然而,甫一进入小说正文,这样的阅读期待随即被打破。我们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时间在此缓慢流逝的日常世界。在这里,人物与事件多而琐碎:沉闷乏味的旅行,庸碌繁杂的日程安排,无数毫无意义的细节(机场读物的书名、候机大厅的电视新闻、茶馆里的“原创音乐致敬晚会”)被叙述者以忍耐而克制的眼光一一扫过,在平静中压抑着一种烦厌的情绪。
事实上,这种语言模式的切换并非偶然现象。散文语言和诗性语言的相互交织,构成了贯穿小说全局的语言特点:以对日常生活事无巨细的记录为主体,而隐喻、幻梦与意识流的手法则混杂其间,这使得散文的经验之流常被诗的跳跃性所隔断。这种局部的语言肌理的非连续性,反映到结构体例上,则表现为碎片化的书写以及频繁的删改、拼贴。从文末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从初稿写成到在《十月》正式发表,一共经历了八年八个版本的十余次修改,动辄变更几万字,并且会像搭积木一样将小说的“零件”拆散又重组。
的确,《北流》的结构看起来像是由各不相关的“零件”组装而成,除了作为主体的“注”和“疏”之外,还有“植物志”这样的诗歌、“异辞”这样的民间歌谣、“时笺”这样的谈话记录,更不用提注疏之中还穿插着《李跃豆词典》《突厥语大词典》等虚构的词典。语言的断裂加上结构的破碎,其所造成的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文体的“非小说化”。诗歌与散文的拼贴——这样的写作毫无疑问与传统的小说拉开了距离,该如何理解这部“不像小说的小说”?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抑或结构的失败?
比起这些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评价,历史化地考察作者的创作发生史或许更有意义。正如林白在创作谈中所坦言,形式的创新并非“要格外让人吃一惊”,而是作为一种结构策略来考量,目的是为了“把那些纷繁杂芜的名堂一一摁倒放平——让那些纷繁复杂既保持原貌,又能舒服地进入一本书”①。也就是说,林白在设计本书结构时,面临着如何处理鲜活个体经验与“一本书”的完整性之间关系的问题。如果说在以往的“私人写作”中,幽闭的个体与完整而狭窄的世界(房间)相适应,那么当个体的经验领域来到了向外开放的历史时空,个体与总体之间的矛盾就必然发生。在写作中,林白时常感到叙事的困难:“觉得自己的叙事不好,故自我降低为半叙事。不然会丧气。给自己一种名堂振作起来。”②那些看似不相关的素材,犹如榕树多出来的气根,是作者结构全书必不可少的支柱:“若非长篇里插进一众‘气根,可能早就崩溃了。”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与体例的创新并非刻意为之,而恰恰是为了解决小说的结构性难题而产生的结果。
戈德曼在论述小说文体学时曾指出:“事实上,唯独根本的破裂将产生悲剧和抒情诗,而破裂的缺乏,或者一种单纯的偶然的破裂将导致叙事诗或者民间传说。”④而小说则介于二者之间,是一种自我在总体性危机中弥补裂痕的尝试。只有在一个完整的世界中,自我的同一性才会产生,因而安顿素材的过程对林白而言,也同时是“安顿自己”的过程。从小说篇名的更易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用心所在:从最开始的《降落伞》(各条线索和脉络如伞一般收敛)到后来的《织字》(语言的缠绕和连绵不断地生长),小说的结构初步显现,却无法被纳入一个稳定的体制,以至于作者“每隔几天就要找出一个新的命名,需以新的命名策动某根神经”⑤。直到友人提出《北流注》,“这个书名照亮了结构,注、疏、笺,瞬间涌出”⑥。传统注疏文体由一个点向外发散的开放性结构,正好适应于作者在一个敞开的时空中重新组织个体经验的需要。而本书的另一名称《简繁志》,则无疑应和着全书诗与散文相交织的文体特征。“注对经的简来说,正好是繁。”⑦本书表面上只有“注”而没有“经”,实际上所有的“注”都是自我作注,是注自己,而“经”则可视作那些隐藏在“注”和“疏”中的个体情感爆发的瞬间,那些穿插在散文中的诗。
实际上,回顾林白近年来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林白诗歌的创作开始狂飙突进,“想着是一处生命能量被开启了”⑧。这种写作文体的转移似乎是一个征兆,意味着作者心中不可遏止的激情,正在日益冲破由叙事建构的完整性图景。因此,产生于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北流》也就成为一种临界的写作,一种在历史的开放空间中重新编织个体经验进而重建总体性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北流》创造了联结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独特的注疏文体,在长篇里插进“气根”,用诗的光芒照亮了散文的大地。
正如李敬泽所说:“《北流》几乎可以看作是林白所有著作。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经历了沧海桑田。这个沧海桑田不仅仅是作为故事,也不仅仅是作为叙事,而是作为一个人类的经验。”⑨将自我的经历作为一个人类的经验,铺散在故乡的田野之上,《北流》的结构或许可以被视为作者精心打造的容器。借助这样的容器,作者试图在自己的私人经验中重新寻找到一种连通历史的具体普遍性。因此,形式的创新深刻关联着作者的生命体验,关联着特定主题的呈现和表达。C56CCDF7-D66B-4F4C-B5D5-0C57C5E30769
二、反抗平庸
如同《北流》的结构是一种从中心向外发散的注疏式文体,这部长篇的人物虽多而繁杂,却同样构成一种由中心向外发散的人物谱系。李跃豆是小说唯一同时兼具三种人称叙述的中心人物,从这一中心出发,其他人物皆可根据其与李跃豆的关系加以定位:外婆、远照和远素姨婆的故事构成了跃豆所追认的母系氏族脉络,对她们的回忆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庞天新和罗世饶作为跃豆的表哥,他们或存在或虚构的传奇经历寄托着跃豆的理想;米豆作为跃豆的弟弟则是跃豆的反相——无欲无求,随遇而安;汪策宁、韩北方和H等作为跃豆的情人而出现,是跃豆欲望投射的对象;作为跃豆的朋友,泽红与泽鲜代表着跃豆未曾实现的可能性;而陈地理和赖诗人则在一种象征的层面再现了跃豆的激情……这些人物被归置于“李跃豆—我”的元叙事中,作为自我的无数镜像,从不同视角出发,沿着不同的线索为《北流》贡献主旋律的多重變奏。
这种“自我”的复调在林白之前的小说中也可以找到痕迹,最典型的即是《说吧,房间》中的“我”与“南红”的互相映照。然而在《北流》中,这种双线交织的结构扩大为无数声部的交响,它们在“跃豆”这个中心人物的指挥下共同构成统一的和弦。因此,《北流》的主题没有体现在完整的单线叙事之中,读者所感受到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故事,而是无数叙述细节中反复出现的一种诗的韵律:庞天新生命中那个充满力比多的“∞”字符号;在远素姨婆想象中支援世界革命的天新;赖诗人追逐春河的脚步;陈地理仰望星空的身影;罗世饶的流浪;泽红的私奔;更不用提在李跃豆身体里疯狂生长的南方的丛林……无论每个人的故事如何不同,我们都能将它们放在统一的坐标轴上:一边是沉沦的庸俗世界,一边是位于时间之外的“时光的支流”上超越性的彼岸世界,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以不同方式进行对平庸生活的抗争,他们要么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如同诗人(罗世饶);要么陷于灵肉分裂而成为疯子(陈地理/赖诗人);要么彻底远离现世而成为圣人(米豆/泽鲜)。
这种面对平庸世界的或抗争,或逃离,或崩溃,即成为小说世界里的“变”中之“常”,让散文化的生活时时回响起诗的韵律。小说语言中“散文化”与“诗化”的风格差异,恰好隐喻性地表达了小说的“主题韵律”——那就是平庸的此岸世界与超越性的彼岸世界之间的矛盾。然而,如果只是重复地书写一种对超越性生活的渴望,那么《北流》的主题也不过是对《月亮与六便士》的复写而已。这不是这部实验性小说真正的价值所在。不要忘了,我们正在阅读的是向历史敞开的个人化写作,因而,当诗的韵律真正落实到主人公对故乡的凝视,在这种重复之下的差异也就具体地显现出来。
事实上,叙述的重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症候,弗洛伊德作为最早思考重复行为的心理学家之一,将重复解释为心灵机制面对不愉快的、被压抑的记忆时的抵抗。林白对“超越性”的追求似乎永远伴随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一种无法与现实和解的紧张感。无论是《说吧,房间》中的南红,还是《北去来辞》中被时代抛弃的左派知识分子史道良,这种对超越生活的“诗”的渴望似乎已形成林白写作的共同母题。从《北流》的故乡书写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其中蕴含的复杂情感。
关于故乡,李跃豆在一开篇就直言不讳地说:“私奔的激情大于返乡,当然如此。”⑩“私奔”与“返乡”常常是拿来相互比较的对应物,如果说前者意味着丢开过往的一切,与所爱的人共赴一场未知的旅途,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么返乡则无非是回到自己厌倦的地方,回到亲戚们的饶舌与庸常琐事之中。如果故乡也有什么让人怀念,那一定不是此刻自身所在的故乡,而是那个在记忆里重建,在“时间的支流”中闪闪发光的故乡。私奔的激情源于对彼岸的向往,而故乡一旦被记忆推向时间的彼岸,则也会变得和“私奔”一样迷人。李跃豆对老家亲人的态度正是这种矛盾情感的写照:跃豆返乡时面对母亲和弟媳一家,感到一种“局外人”的冷漠,而当被昔日的恩人远素姨婆拉住手臂时,甚至“受到惊吓,又感到恶心”11;可一旦进入对往事的回忆,这些亲人们瞬间变得可爱又可敬。远照和远素,她们一改“此刻”的衰老面容,在自己的时代里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成为拥有“超人”意志的女英雄。跃豆“重返”故乡的过程,也同时应被视为对故乡本身的“重构”,就像小说中对北流方言的运用也同时是作者重新学习语言的结果(“普通话的用词语法她多少年都没有用熟,后来连家乡话也陌生了”12)。可以说,跃豆在小说里真正怀念的故乡,是在个人记忆中美化的“一个人的故乡”,而作者在小说中书写的北流,则是被个体生命所经验的“身体里的北流”。
这也是为什么穿插在小说正文之间的,除了记载家乡方言的《李跃豆词典》,还有《干燥亚洲史》《西域语大词典》等看似不相干的内容。实际上,这些词典式文体的征引和杜撰表征着作者的一种“博物学旨趣”,一种对“诗和远方”的向往,就这一点而言,故乡方言与西域方言的性质并无不同。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作者怀乡情感的全部内涵,在那南方的林莽之中,在北流方言的乡音与异辞下,作者所要追寻的不仅仅是一种超越庸常生活的激情,更包含了一种回归总体性的隐秘渴望,一种在地方身份认同中重建共同体的欲求。这是“返乡”大于“私奔”的地方。正如李跃豆的独白:“你在摇晃中,既渴望激情,又希望得到安宁深沉的静谧。”13如果说前者是尼采追求的“瞬间的强力”,那么这种创造必须永不停息,一旦无法提高,强力意志便沉降为庸俗的生活,这正是小说里泽红“私奔”的命运。相比于泽红,泽鲜的修行则是后者的写照,并被叙述者赋予了更高的等级秩序:“她的私奔更英勇无畏吧。更彻底,更传奇。”14这是一条比尼采式“激情”更为本真的道路,一种回归存在之家园的选择——这也是李跃豆“返乡”的深层意图,无处发泄的激情背后,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
“诗性”的瞬间爆发其实并不是作者真正渴求的灵魂归宿,如果说“诗”与“散文”分别代表着矛盾的对立两极,那么“小说”则是对这种矛盾形式的最终超越,是综合了理想与现实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为什么在《北流》中,作者反复尝试“散文”与“诗”的文体,却最终仍试图将这两种文体结构成一篇小说。叙事的艰难彰显出这篇小说的难度,无法超越的二元对立导致了主题的“强迫性重复”,这就需要跳出文本,因为文本自身的矛盾正植根于现实的矛盾之中。C56CCDF7-D66B-4F4C-B5D5-0C57C5E30769
三、“女性”的共同体书写何以可能?
陈晓明在《北流》研讨会上非常敏锐地注意到:“林白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像植物一样生长过,像植物一样扭曲过。”15林白与陈晓明同属五十年代人,有意味的是,林白对于“这一代人的生活”的书写,既没有同代际作家的“史诗情结”,又始终与时代的风潮保持距离,而呈现出一种被延宕的“青春写作”特点。对这一特征,林白本人也有所意识,她在《北去来辞》中即以主人公海红的口吻写道:“下一年就是二○一三年,海红将满五十岁。经过这么多年纠结的生活,她感到自己终于褪尽了文艺青年的伤感、矫情、自恋和轻逸,漫长的青春期在五十岁即将到来的时候终于可以结束了吧?”16犹疑的语气透露出告别青春的艰难。
如何解释这种“青春期”的延宕?《北流》给我们展现出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一场漫长的精神流亡。这实在是现代文学中“娜拉出走”故事的当代变体,当李跃豆们逃离了扼杀自己个体性的原生家庭时,他们发现自己如萨特所说的那样孤独地“被抛入世界之中”。精神需要一个家园,但现实生活中的家园却不属于自己,这就是李跃豆只能够靠想象和回忆来寻找故乡的原因。在回忆中发光的“永生的金色的时间”17,李跃豆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母系氏族,这里有亲爱的外婆、英雄般的母亲远照、慈祥的远素姨婆以及善良的阿姨们。可在现实中,这些女性都不属于她,在她们和她之间,永远藏着一根不能被消化的“簕”。这根簕——懦弱无能却无法躲开的菲勒斯——是文中所有女人(包括李跃豆自己)为之旋转奔忙的中心。正因如此,当李跃豆看着自己的母亲和弟媳没命地宠着孙子阿墩时,“有一瞬间,她觉得时空置换,隔着层层空间和时间,她变成了那个永远不会受到褒奖、为了救自己只能奋力读书考大学的姐姐,阿墩则是那个永远受到保护、永远被寄予厚望、却又永远依靠母亲的海宝”18。
正是这样一根横亘在女性之间,并深藏在女性身体中的“簕”,造成了女性共同体书写的难度。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回顾“李跃豆”的成长经历,不难发现正是共同体的爱的缺失,导致了她一次又一次从生活中逃离:在童年最需要双亲陪伴时,因男孩海宝的出生被带离母亲身边,而父亲的角色则始终缺席;青年时代向往革命,却因双脚泡烂不能劳动而被当作反面教材;成年之后纠缠在与男性的情感关系之中,却始终爱而不得,空留遗恨;到中年返归故乡寻根,却发现与乡人关系日渐疏远,成为一个无法共情的局外人。每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跃豆都将身体里无法排解的激情投向新的目标,却如同浮士德一样不断经历各种挫折,因而躁动的内心也就始终无法安顿下来。这种游离于各种社会结构之外的孤独感,就只能以“文艺女青年”的姿态来言说,以反讽的方式来自我疗愈。
项静在阅读林白时,注意到其作品中“叙述人与人物的自我意识,构成一种奇特的二元反讽关系”19。这一反讽诗学在《北流》中最典型的象征呈现就是幼年的“罗世饶”对圭宁县的凝视,这个被唤作“小五”的男孩热爱爬树,从树上俯瞰圭宁的街道。这个情节无疑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生活在树上既是从庸碌生活中超拔出来的尝试,又意味着与世界保持一种反讽的距离。而在这种反讽的诗意之下,则掩盖着无法解决的虚无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又是“家园”的隐喻,“小五”看着圭宁的街道,正如李跃豆看着在回忆里“永生的金色的时间”,它们是如此美丽,却又如此遥不可及。
应该说,《北流》体量虽大,却是一部低姿态的作品,作者在创作谈中也坦言其“没有野心”20。然而,或许是受佛法影响,作者在叙述中唯因谦卑,而更见真诚。正因为其真诚,林白才会不求结构的恢宏,而是以注疏的形式,将个体经验伸展到故乡的田野中去,可谓结合了《一个人的战争》中的私人独白与《妇女闲聊录》中的乡土记录,用诗性激情联结起散文化的现实经验。也因为其忠实于个体生命感受,我们才会在小说反复叙述的主题韵律中,品味到一种超越生活的激情,以及这种激情背后的孤独与历史难题。
在原计划题于卷首的小诗《织》里,作者将自己想象为一只名为“织”的鸟,“用尽毕生的力/织它并不需要的那块布”,而在织布的金银彩线之下,“是虚空/只有无尽的青草”。这或许是对《北流》最好的注解吧,女性、南方与失落的革命,个体与时代的难题编织在一起,化为一场斑斓的梦境,“壮阔,且徒劳”21。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20林白:《就这样置身其中》,https://mp.weixin.qq.com/s/v5LvdY48ZEF-JJkoa7kBBg,2021-10-18。
④[法]呂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1989,第200页。
⑨15黄茜:《将世界的丰富性寓于语言之中,林白最新长篇小说〈北流〉出版》,《南方都市报》2021年10月25日。
⑩111213141718林白:《北流》,《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双月号第3-4期。
16林白:《北去来辞》,北京出版社,2013,第411页。
19项静:《经验与书写:一个人的总结——林白论》,《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21林白:《母熊及其他(九首)》,《山花》2020年第10期。
[黄平、何卓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文系2021年度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SG25;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批准号:2019ECNU-HLYT003]C56CCDF7-D66B-4F4C-B5D5-0C57C5E30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