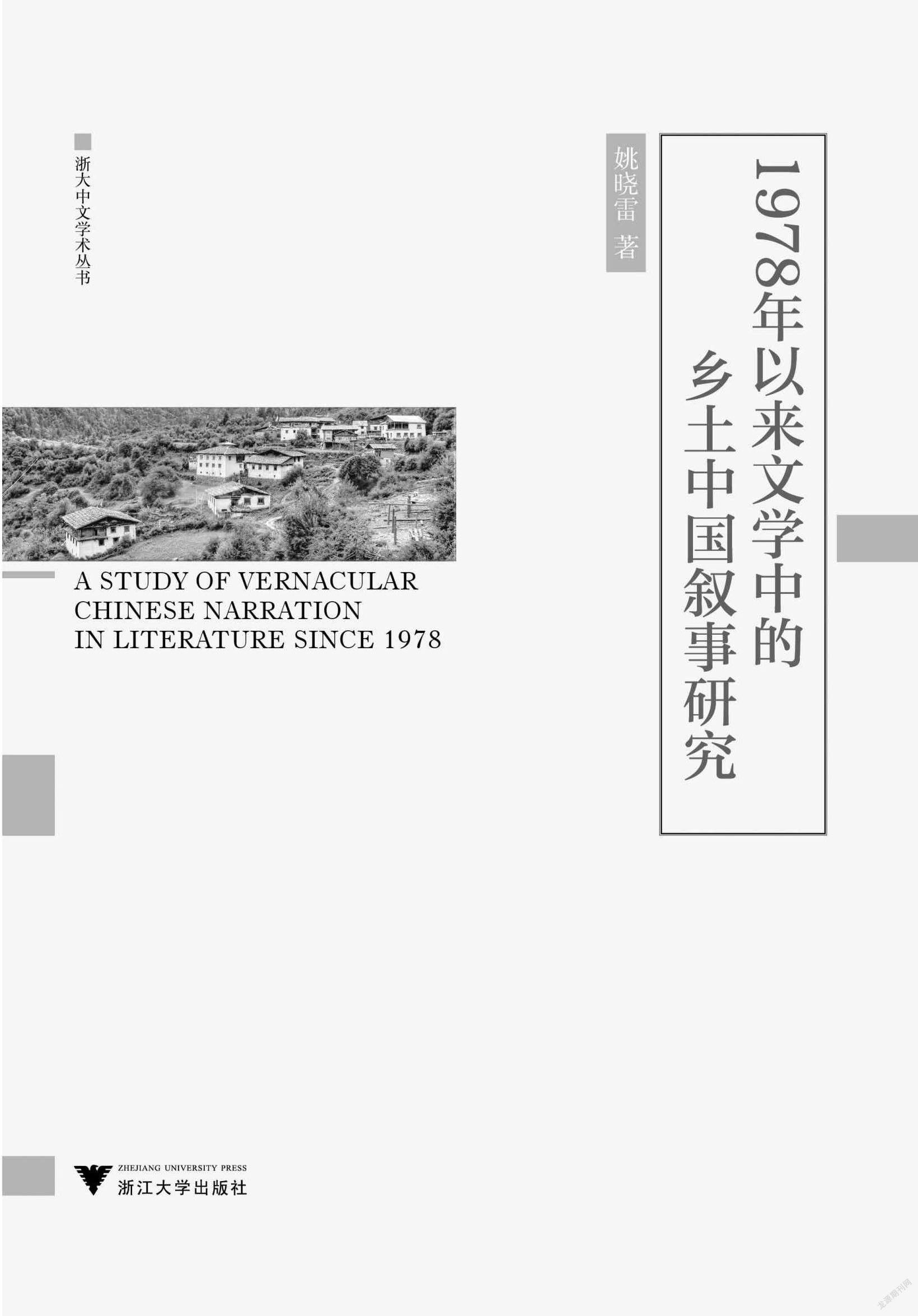
编者按:
关于新时期乡土中国叙事的研究,以及相关民间文化形态研究,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
近日,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读了浙江大学姚晓雷教授的新著书稿《1978年以来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叙事研究》,就文学创作的“道”和“术”的关系以及民间理论审美形态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艺创作中“道”“术”一体,不可分割,“道”是通过“术”来体现的,作家并不承担单纯传播“道”的任务。“民间文化形态”指作家的一种审美形态,“自由自在”作为其主要的审美精神。姚晓雷在答复中认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观念系统而言,人文学科的许多具体概念、思潮及创作追求都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所呈现出来的面目是经过“术”改造的,故需要从“道”与“术”两个方面进行辨析;“启蒙依赖症”是指当下一些作家在创作中把固有的一些启蒙成果教条化、套路化的现象,它事实上已经严重影响到许多作家的创作思维,使他们在追求“代言”而非“立言”;“自由自在”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风格是成立的,但这有可能导致民间文化形态脱离实体支撑的空心化,以及对价值评判的非历史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国和教授在阅读了陈、姚通信后,认为陈思和与姚晓雷的分歧只是表象,两者精神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进而结合70后作家的乡村书写经验,阐述了民间立场、民间形态和民间叙事是当下人文知识分子文化理想追求的面向之一,基于现实感的民间审美想象是乡村小说创作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发展方向。
三位学者融思力、学问与坦诚的学术讨论,颇具专业精神、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本刊组发于此,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晓雷:
你好。你的书稿《1978年以来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叙事研究》,在我这里已经放了一两年的时间,早就答应把读后的意见告诉你,但总是拖拖拉拉,好几次打开书稿,读了前面部分就放下了,照例是被别的事情打断;再续起来还是从第一章读起,然而又被打断。这样重复了好几遍,关于田小娥“四副面孔”的部分已经读第四遍了。如果不是这次疫情弥漫神州,也许还会拖下去,但现在总算有时间了。春节以来,以读书排解闲愁,旧文债也将一件件清理。你的书稿内容繁复,无法一目十行轻松看过,反倒是边读边想,慢慢咀嚼,引起我对很多年不再思考的文学问题——关于乡土和民间理论的思索兴趣,于是,也就有了与你一起讨论的愿望。
同时我还想赞扬几句。在读你的书稿时,我又把你当年的博士论文《乡土与声音——民间审视下的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类型小说》找出来翻了一遍,那本书完成于2002年,出版于2010年,前后算起来距今又十八年过去了。那曾是我非常看好的著作。我一直期待你在这本书的基础上继续往上努力,在乡土小说研究领域有更大的突破性的贡献。现在你终于奉献出新的论著,由河南地域文化研究到乡土中国视野下的四十年文学扫描,从民间理论审视文学到民间理论的自我突破与反思,气象和视野都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我欣赏你在学术上的探究精神,也为你新见迭出的理论研究和不断拓展感到高兴。另外,在这部新著里,你已经呈现出成熟学者的风采:你树立起自己的理论目标,抓住了“乡土中国”这个社会学的概念,把它改造成文学叙事,并以此来总结四十年文学的某种创作现象。我以为这一概念的关键词,是“中國”而非在“乡土”,你力求从乡土叙事的视角来概述四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而这些方方面面的变化又绝不限于乡土本身。虽然你在绪论部分对这个概念的阐释还不够清晰,但只要联想到当下每个人所陷入的生存处境,就不难理解在现代化进程中飞跃发展的现实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乡土”在正、负两个方面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我们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像你当年对河南文化具有的“侉子性”的分析一样,你对当下中国的“乡土性”的认识,需要何等敏锐的眼光。也因为这样,我不能不说,如果你从文学的范围再走出去一步,走得更远一点,那就更好了,“乡土中国”的意义,与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毕竟有很大区别。这一点,你应该让读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于文学创作,你也有自己的批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你对一些创作现象进行了清理和批判,有些描述很有意思。我对书中第九章、第十章的论述更感兴趣,你对“偏至化民间主体形象建构”中“怪”“鬼”“妖”“魔”等类艺术形象的分析,对“乡土中国叙事气质类型”中“虎气”“猴气”“驴气”“猪气”的划分,不一定准确,但有趣也有启发,让我想起一位二十多年前英年早逝的天才评论家。
又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上来。我读了书中第十三章“关于若干当下乡土中国叙事理论范式的思考”,在前面几章你分析的是创作,文学创作本来就见仁见智,无从讨论,这一章你讨论的是文艺理论范式,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民间理论也在你的反思范围,这让我有机会认真思考相关问题。但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想这些事了,现在的想法不知道能否表述清楚,且试试吧。
第一个问题是文学批评理论的“道”与“术”的关系。你在这一章里,把理论视角放在“道”与“术”的辩证关系上,把各种理论范式归纳为“道和术双重层面上的困难”“离道而扬术”“借术以求道”“既乏道又乏术”等类型,这很有意思,但我也有点困惑,直截了当地说,文学理论批评范式里,“道”的批评与“术”的批评怎么可能分开来谈呢?举个例子,我读了第二节,是你对“离道而扬术”的地域文化批评范式的“反思”。你先是对“寻根文学”理论等作了一番梳理,然后就批评说:“尽管地域文化范式对克服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政治化、概念化有一定作用,但客观地看,它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毕竟地域文化视角本质上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视角,而不是站在现代人本立场去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对话的价值论视角……”后面还有一段论述:“在现代社会里,愈往后发展,地域对人的存在的影响愈不确定,因为随着交往的便利和频繁,不同地域之间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融合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本质上的趋同——对压迫的本能的反抗、对自尊的基本维护、对自由的渴望等,都是那么的相同,而建立在人性共同价值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思考才是所有伟大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这两段话让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在你看来,像文学创作中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的描写,都是属于“术”,而深入思考人性共同价值才是“道”。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在文学创作中,这个“人性共同价值”的“道”是如何显现的呢?不就是通过各种艺术创作手段、语言、风格,也通过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和创作特色来表现的吗?离开了这些你认为的“术”,人性共同价值的“道”又从何处来展示呢?你也曾说到,在“寻根文学”的创作实绩上产生的“地域文化范式对克服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政治化、概念化有一定作用”,那就对了,如果按你所举的“对压迫的本能的反抗、对自尊的基本维护、对自由的渴望”等几条“道”的特征,那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表现的不就是这些“道”的内容吗?而“寻根文学”却把文学的政治化转向了文学的文化审美,地域文化批评范式由此产生。地域文化审美的范畴比政治范畴更加丰富多元,更加接近了文学自身,因此也更加接近人性。从文学史的传承上说,地域文化批评范式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药蛋派等创作理论的提出,在当时也是抵制过于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的理论武器,按你的说法,都是借“术”而参与了“道”的建构,更何况“寻根文学”在新时期文学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至于你说它“起的作用是有限的”,那也是不错的。文学理论本来就不是宗教,它的功能是从创作实践中发现倾向性的问题,及时提出来加以研究和解决,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未来如何发展,我们并不了解,所以任何文学理论都只能是阶段性有效,可以被证伪,哪里有万世不变的文学理论呢?
所以,讨论文学理论范式固然要关注“道”,但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一定是透过各种各样多姿多态的“术”来显现的。这不是说,“道”即是“术”,而是“道”附体于“术”才能呈现。就像人的生命与人的身体的关系,生命固然比身体更精彩,但生命是通过身体各个器官来维持和升华的,一旦去掉了这身臭皮囊,再精彩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文学批评也是这样,只能借助于分析研究“术”来达到对“道”的感悟与弘扬,地域文化批评范式适用于对地域色彩浓厚的寻根文学、文化风俗小说、西部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可以把这类文学的优势和美凸显出来。在这一类题材的创作中,对卑微人性的关注和对自由的向往总是它的基调,人性在其中,“道”也自然会在其中,这需要批评家和读者自己去细细体会。文学创作总是会有优秀与拙劣之分,也总是有粗制滥造的,这是创作的具体问题,不能由理论范式来承担责任。
我在读你对创作的批评时也有这种感觉,你似乎一直在寻求升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某种精神抽象物,譬如所谓“道”,所谓“思想”,一旦找不到这些被预设的抽象物,你就会抱怨作家的水平不够,认为他们没有达到你的理想境界。其实这也不是你个人的习惯,也是当下学院派批评的普遍现象。书中有一段对莫言的批评:“总之莫言的最大贡献在呈现本土社会历史的各种艺术元素创造性集成、阐释的个性化发挥方面,而不是其立足于人类文明前沿面向对现实和未来的思想原创力,不是在当代社会思想的顶端添砖加瓦。不只莫言,许多其他作家这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接下来你说了一大段“启蒙依赖症”,我不太明白,姑且跳过,接着你总结说:“这个时候它(指启蒙理论范式的失败——引者)把作家逼上了一个不得不选择的十字路口:要么在沿袭中衰退,要么在创造性的思想探索中浴火重生,高屋建瓴地审视和把握这个时代。”这些话都讲得很好,确实高屋建瓴,也确实很痛快,可是我问的是:你怎么可以把整个思想界衮衮诸公的使命和任务这么轻易加到作家的头上?“立足于人类文明前沿面向对现实和未来的思想原创力”,“在当代社会思想的顶端添砖加瓦”,“在创造性的思想探索中浴火重生”……你一口一个“思想”,这些都是文学家应该承担的使命吗?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做到了,还是曹雪芹、鲁迅做到了?好像周作人说过,癞蛤蟆垫床脚,不如一块破瓦片,反倒把制药的蟾酥浪费了。你说小说表现人性是一种“道”还能让人理解,但是你要求作家在“当代社会思想的顶端添砖加瓦”,那不就是让蟾蜍垫床脚、让狗耕地吗?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是说文学与思想无关,也不是说作家在创作中不需要具有思想力量。但是中国式的“道”也好,西方式的“思想”也好,它本来就存在应该存在的地方,不需要用它的本真面貌出现在文学创作里,至少优秀作家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尝试着做,大约也是失败的。因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劳动形态不一样,劳动产品的功能也不一样。文学家是通过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在创作中熔铸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以此传达他们对世界的特殊理解。作为一个评论家,应该借助艺术形象来解析、发现其中的深刻意义,当然他也需要借助某些思想,但绝不是把文学当作思想的复制和演绎,更不能把文学创作等同于思想家的劳动。其实这些道理都是一般常识,你都了解,但怎么会对莫言以及“许多其他作家”提出这样高的要求呢?
你所批判当代作家的“启蒙依赖症”到底指什么?我从你的书里找不到充分理由。但我知道,所谓“启蒙”的文学,恰恰是一种思想为先导的文学,评论家之所以喜欢讨论启蒙文学,就是因为启蒙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常常是思想大于形象,或者因为思想过于鲜明,以至于简化了艺术形象自身的复杂性。鲁迅研究中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你所批评的“启蒙话语理论范式”可能与此有关,但是莫言所开创的文学叙事,属于“乡土中国叙事”也罢,不属于也罢,他的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启蒙话语里摆脱出来,还原了活生生的血肉之农民形象,还原了耻辱的、痛苦的、粗野的,但又是形象饱满、元气淋漓的中国农民。新文学作家从来没有用这么夸张的手笔来创造农民的形象,就是因为莫言真正表达了被压抑的农民的心声,他被农民自身的文化力量推动着,走到了启蒙文学的对立面。你可以说他的小说是“反启蒙”,但不存在什么“依赖症”。你批评莫言缺乏“思想”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应该诠释一下,莫言缺的是书斋里和文件里的“思想”,但他的笔下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奔腾的血液和跳动的心脏,以及强大的生殖能力和繁衍能力,与苍白的“思想”相比较,哪一种更靠近文学本体呢?
第二个问题,我想談谈民间批评范式中的“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记得当年你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我们就文学中的民间形态理论做过多次讨论,很可能当时我对“自由自在”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以致让你到现在还心存疑惑,责任在我;或许是我确实也没有想得太明白,你的质疑提醒了我,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过去一直就民间形态理论中的两个问题没有能深入研究感到遗憾,一个是关于藏污纳垢的美学形态,另一个就是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我有好几次都想认真研究这两个题目,但总是因为忙,再加上时过境迁,也提不起兴致了。感谢你在书中把这个疑问重新提了出来,时隔二十多年的理论还有人能够提出反思和回应,这在学术研究中是最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我先把现在能够想到的意思说出来,做个解释,希望得到你的继续批评和质疑,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问题深入讨论下去。
我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中是这样阐释的:“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民间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确实,这段话里有许多语焉不详的地方。但很显然,这里的“自由自在”是指一种审美风格,不是民间的本体特征。
为什么我要在审美形态的范畴里讨论民间的自由自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文明发展到国家统治形式的阶段,人类社会是被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者是通过对后者的剥夺来达到对后者的统治,这种剥夺,不仅仅是物质的剥夺,也包括思想意识的控制,所以,民间社会的自在状态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再者,民间的“自由”不是指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它主要体现为对生命形态的肯定,即生命行为不受限制和约束,尤其是对抗国家制度及其文明所造成的约束与压抑。譬如民间文艺中自由恋爱的表达。正因为我是在生命形态上肯定自由的意义,所以我用“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作为这种民间自由传统的注释。这里的“原始的生命力”不是从时间上来定义的,而是生命形态中的某些来自原始人类的生命基因,表现在冲破一切束缚对自由自在形态的追求与实践。即使当下的人类生命中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生命基因,它的时间性就表现为对“生活”的拥抱,或者说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楔入。其三,为什么民间的自由自在是一种审美风格?在1995年我访问日本时,也曾经有一位日本学者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民间社会在现实层面上不存在真正的自由自在,所以它对于自由自在的想象和向往,只能是在虚拟的文化形态里完成。这也是我对民间文化形态价值判断的依据。我对文学中的民间文化形态的探讨,都不是指实在的民间社会,而是在文学创作中的观念的民间文化。而观念的民间文化形态又是实在的民间社会形态的反映。所以,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审美乌托邦,而是一种在虚拟的文化形态中表现出来的现实价值所在。
我这么说,可能你还是会觉得不清楚。我们再举一个具体的创作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自由自在”到底指什么。《白鹿原》是一部经典的民间叙事。但是你也许注意到,我没有解读过这部小说。其实是我太慎重,这部小说内含复杂的民间文化形态,也是我一直想表述的民间本相,但是我怕讲不好,反而让人误解,所以就一直犹豫着没有下笔。现在防疫期间,无法去找原书重读,只好凭印象随便说几句大概的意思。这部小说一开始就写庙堂自毁,民间崛起。辛亥革命以后,国家没了王法,白嘉轩在当地大儒朱先生的支持下,自立乡规,构建起一个有秩序的民间社会。但这个民间社会只是一种变相的地方政权形态,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民间,所以,它不可能实行自由自在的理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嘉轩与田小娥的冲突产生了典型的意义。
田小娥是什么样的人?在白嘉轩的眼里是个十恶不赦的“妖孽”、伤风败俗的女人;在陈忠实的眼里她是封建时代无数贞节牌坊的對立面,一个为自由而死的灵魂;在你的眼里她有“四副面孔”:既是封建吃人礼教的牺牲品,又是欲望的化身、阶级复仇的厉鬼、瘟疫般的恶魔形象,你对这个形象的态度是有褒有贬。然而在我的眼里,很简单,田小娥就是高压下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理想,在她身上集中反映出民间对自由自在的向往和追求。为什么作这样的理解?因为,田小娥的追求自由自在并不是自觉的、理性的,与卢梭的那一套理论毫无关系,她的所有的追求,都是来自她身体内部的生命力的冲动,也就是你所说的第二副面孔:欲望的驱使。女人的欲望强烈本身无罪,但是在封建礼教的规范下,她的欲望得不到宣泄与满足,于是就出轨、淫乱,然后一步一步地被驱逐、迫害、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地,最后化作厉鬼向人类报复,还是受到了“正气凛然”的儒家道德的镇压,终于化为灰烬。这样一个从生到死到毁灭的过程,都是生命的过程,就是“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欲望的义无反顾的强烈追求。但这样一种追求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是不可能被允许在现实民间社会中存在的,田小娥的对立面不是官府法律,而是土生土长的民间人物:白嘉轩、鹿三,一个是白孝文的父亲,一个是黑娃的父亲,实际上就是族权和夫权(父权)的变形结合。这就说明了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理想状态的民间社会,只有渗透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理想的、被抽去了精血和灵魂的虚假民间形态,白嘉轩与田小娥的悲剧性冲突,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被统治阶级的意识所覆盖和控制了的民间权力与理想中民间永恒的自由自在的生命追求之间的冲突。而后者这种以死相拼的生命追求往往在民间文艺与民间风俗中,以合法的形式,被曲折地碎片式地表达出来。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一例。
当然,田小娥所表现出来的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并非完美无缺,因为被迫害的残酷性决定了她只能以非道德的形态出现,淫女、厉鬼,包括她性格里具有的恶魔性因素等,这就是民间藏污纳垢的美学形态特征之一。在民间形态里追求自由自在,与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纯洁的自由女神相距甚远,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的阶级、阶级斗争以及追求解放等概念也关系不大。你在“四副面孔”中罗列的田小娥的所谓“阶级报复”,其实就是民间淫女在男欢女爱中的恶作剧,联系到阶级复仇说事,就说大了。
我不知道通过这样的举例分析,你能否同意我所说的民间自由自在精神的意义。我觉得文学中的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论提出以后,引起误解甚多,其中最主要的误解就是把观念中的民间文学形态与现实社会中的民间社会(或者更直接还原为乡村社会)混为一谈,这一点可能也是我以前没有讲清楚其中道理所致,给接受者带来了困惑。我要深感抱歉的。
真不好意思,一封信竟拉拉扯扯写了这么许多题外的话。不过我很高兴,现在朋友之间的学术交流实在太少,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写出心里流淌出来的真实想法。希望你不要介意,如果你觉得这篇书信有助于你进一步思考、研究这个课题,那我也感到欣慰了。
希望保重身体,利用这个因灾难来临的疫情长假,埋头做好我们的学术研究。
2020年2月17日
(陈思和,复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