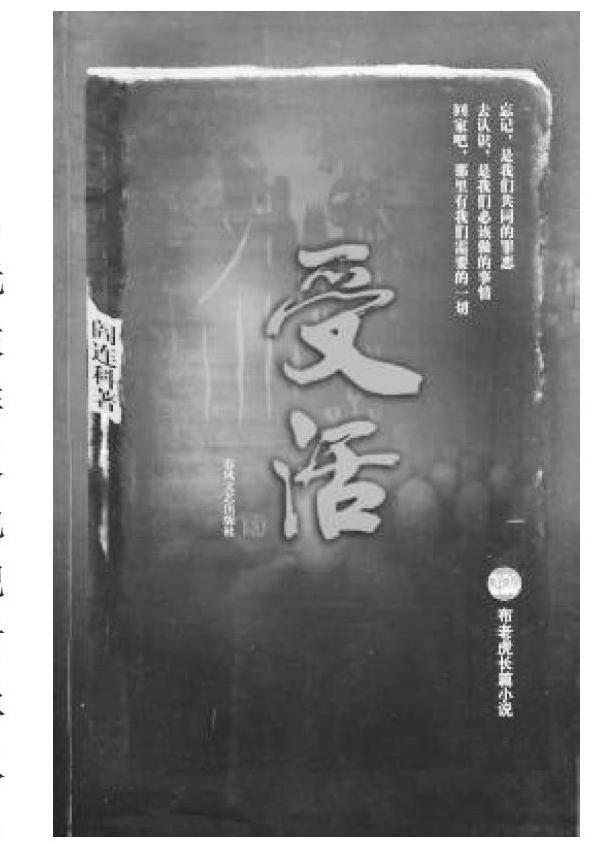
一
阎连科小说叙事的重点在农村,农村叙事的关键在农村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农民精神状态。当然,他的农村叙事毕竟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和非虚构的,所以,他所反抗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论①又反过来成了凝聚他农村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瑶沟、粑耧、三姓村、受活庄、丁庄、炸裂村等,既清晰映射着历史的回声,也承担着历史遗留给它们的命运苦痛。从“革命”跨到“城镇化”的快车道,中间经历过的无数历史细节,都不是几个僵硬冷漠的词条所能道尽,其中对人的改造均以不可更改的观念形态保存到神经中枢了。这时候,感受阎连科的叙事,只能从阎连科开始,而不宜启用文学史惯用的“从前”式或“谱系”式思维方式,盖因阎连科聚焦的农村社会现实,并不在正统的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史里,它在强势政治经济话语所构建的主流价值体系中,他叙事中的“连续性”集体无意识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叙事进入到这一层面,按理说,阎连科应该具有更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思想,可是,遍翻他的对话、创作谈、“文学理论”,他用得最多的的确不是现代性概念,而是用他的“神实主义”②反抗现实主义。由此可见,这并非他的自我解构,恰好是他无意识状态下自觉而真诚的叙事状态。研究者正是抓住他的这种冥冥当中的又是“文学的”“审美的”元素与泛苦难化③做文章,有意无意忽略了他小说非常接近现代性叙事的一面。“疾病”“残疾”叙事正是阎连科从深层以解构的方式触及农村社会现代化难题的一个视角,这是“疾病”“残疾”叙事是其小说主体而非手段方法的重要原因。
当然,“疾病”“残疾”叙事从最初对生命病态本身的思考,到进入“疾病隐喻”,可谓源远流长,贯穿古今中外文学史。《荷马史诗》所谓“疾病在夜以继日地流行”,《茶花女》《悲惨世界》等正面描述的肺病、艾滋病、癌症,以及《荀子·解蔽》“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时正之”中无中生有的幻觉病症,一直到《金瓶梅》《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中各种与身体病态相关的疑难杂症出现,“疾病”叙事的广度和深度开始慢慢增加,有的甚至开始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道具,“疾病”叙事也就有了神秘色彩,成为映射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隐喻情结。然而真正由隐喻修辞上升到思想潮流高度的,是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和19世纪西方颓废派文学中的疾病隐喻,这两条线索分分合合,相互影响也相互解构。启蒙中国现代小说的前身当推清末新小说,它们与留日学者的思想论述一起合力推进了隐喻话语体系的形成。1895年严复在《直报》发表《原强》,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译发原刊《字西林报》英国人评甲午战争的文章,均不约而同以“病夫”喻中华民族,开启了“身体”与“国家”概念并置的先例。稍后,梁启超“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④,康有为《公民自治篇》“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⑤等,“新民”“公民”出现并变“身体”为“民”,遂使“国”与“民”紧密结合,个人由家族依附转向为国奉献。旨在“小说救国”的清末小说诸如《女娲石》《新法螺先生谭》《新中国》,作者的政治立场虽有别,但“换脏腑”“洗脑”“造人术”的理念均以西医为背景,不约而同弃绝了阴阳五行学说和“辨证施治”的“中医”的根底,并开始将西方作为“健康”的尺度,体现了怀疑精神与救世情结相与为一的价值取向。⑥
作为隐喻的“疾病”与“治疗”,对称性地驱迫着文学文本话语生产方式,向现实主义的“身体国家化”逻辑演变。正所谓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试图透过他们所能掌握的文化、符号和言谈资本,将国民的身体做一次根本的改革,使身体与国族的发展不再两不相干⑦,“病”与“药”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隐喻话语体系得以初建,“身体国家化”的文化遂与日后政党伦理要求的“集体主义”取得了一致的可能性。⑧
二
中国现代文学30年(1919—1948)的文学史框架内,疾病隐喻的文本书写范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19—1928年为第一阶段,疾病隐喻主要在民族、国家意识启蒙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就不详述。简单说,代表性人物有魏源、林则徐、梁启超、陈独秀和鲁迅等,他们倡导民族、国家的概念,把“民”“国”从君主“一姓之私业”的怀抱中解放出来,朝着民族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方向迈进。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精神分裂症,正是大众国家民族意识昏聩、王朝缺乏现代化国家管理制度和权力制度意识所致。《药》中革命者夏瑜就是想要把大众的王朝天下观念变为现代国家意识不得而被患有“疯病”,治疗方案是“朕即天下”观念培养起来的专制制度刽子手的“杀戮疗法”。身体得肺病的华小栓,思想上同时也得了“愚病”,相对应的药方是夏瑜的血和夏瑜的现代化民族、国家意识。除此之外,还有终日奔波在买卖人血馒头食物链上不觉悟的华家及康大叔、阿义等。鲁迅所建构的疾病隐喻话语系统表明,在国家、社会、个体的三维体系中,个体如果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个体就不会自觉为社会和国家努力,也不会有维护自身和他人权利的意识。⑨1929—1938年为第二阶段,疾病隐喻主要在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启蒙下进行,是对第一个阶段个体的身体从宗法制牢笼解放出来的不满,表现出向更大范围更大空间敞开去追求自由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患的便是大时代中叛逆女性心灵上苦闷创伤的病⑩,隐喻的是个体自我力量对外在环境和秩序操控能力的丧失,以及对这种丧失的反抗11。1939—1948年为第三阶段,疾病隐喻主要在个体存在价值启蒙意识视阈下进行。李建伟和杨金芳选取了张爱玲小说的确很有代表性,特别像《金锁记》中曹七巧一样的人物,他们所患不是别的,是自我意识过强从而招致疾病,“自我意识过于强大,会让他们疯狂地占有、攫取和毁灭,撕掉人性所有的光环,呈现出病态的本质”12。无论是个体意识匮乏造成人性的软弱无力,还是个体意识过于强大而造成人性的废墟,都隐喻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狭隘、自私、软弱国民性的死穴。
相比较,西方颓废派文学中疾病的隐喻似乎更接近张爱玲的思想余绪,并把张爱玲的疾病隐喻未能完成的目标推到了极致。在19世纪浪漫主义自由理念推动下“反自然”“反道德”乃至“反常”的迷恋“疾病”的颓废者形象,他们没有过多启蒙民族、国家的滞重思想包袱,也没有过多身体受难的苦痛,更多的是对于自由的信念和行动。属于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用“颓废病”隐喻并蔑视、疏离和反叛“自然的”“道德的”“正常的”“健康的”却又是平庸化的布尔乔亚式优越地位。波德莱尔、于斯曼等颓废派作家在逾越常规的非理性生命状态中探索和创造崭新的美,带来了开启“反思”的“震惊”效应,由此彻底颠覆了古典主义的审美范式;他们将从浪漫派的“忧郁”发展而来的神经质的“怨怒”作为颓废主人公的情感底色,以精神分裂作为其常见的病理学症状,以“反自然”的行为与心理作为其唯一颓废生活的特征,精确地描绘出以啜饮自由感为唯一生存理想的颓废者形象。13
当然西方文学中,这样的思潮昼伏夜出,一路潜行,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世纪时,古典浪漫主义主人的大小商人、手工匠人、靠租金遗产或其他闲钱而碌碌无为的阶层,历经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在时机成熟时迅速成为中产阶级的同义词。到了现代,布尔乔亚因是推翻封建秩序、为自由贸易革命的主力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领衔主流政治经济,一跃而成了主要社会力量。到了19世纪,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在欧洲消退,暴发的布尔乔亚群起而代之,由社会的主要力量而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者。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现代价值本来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在立法的逐渐演变中也保护了布尔乔亚的利益,于是布尔乔亚成为现代社会实际的上层阶级,其经济地位、社会声誉得以巩固。正因此,马克思将布尔乔亚纳入现代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范畴,我们将其译为“资产阶级”。不过,在欧美通行的话语中,布尔乔亚保留了前现代的某些含义(如有闲钱也有闲暇的人),也指现代社会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群体特征。在颓废派作家崛起的时代,布尔乔亚的另一副面孔已经暴露无遗,其资产阶级化优越感风气日盛,其贪婪、狭隘、庸俗、保守的恶质也显露出来。这个时候,欧洲文学开始对布尔乔亚做审美的评判。莫里哀、波德莱尔、福楼拜等文学大师笔下的布尔乔亚,不仅庸俗、无知、贪婪,还言必称进步、科学、光明,给自己披上光荣的外衣,俨然现代的化身。而以美学判断审视它,布尔乔亚的光荣外衣立刻被脱掉了,美学判断因此填补了政治经济学对布尔乔亚分析的不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对此解析尤为深刻,影响尤为深远。其“大资”和“小资”,如郝麦、查理(Charles)、勒乐(Lheureux)、罗道夫(Rodolphe)、立昂(Léon)等,或拿庸俗当光荣,或拿无能作专业,嘴脸市侩却招摇过市,话语无知却雄辩滔滔。爱玛·包法利(Emma Bovary)天性浪漫,不甘于布尔乔亚庸俗的生活圈,一心要超越之,无奈却将高尚与庸俗混淆,一次又一次被布尔乔亚欺骗,结果在布尔乔亚的世界里沉沦堕落。爱玛一心想超越布尔乔亚,反而沦陷于布尔乔亚,是《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最大的反讽。“爱玛·包法利,就是我”,福楼拜这句话和他的小说联系起来,意思是他剖析爱玛的浪漫错在何处,也是对他自己浪漫情感的反思和清理。《包法利夫人》之后,警惕浪漫之幼稚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福楼拜之后的小说”即成为现代小说的同义词14。
现在清楚了,我们谈疾病的隐喻时言必谈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15,就其产生背景而言,它之所以是“针对泛滥成灾的疾病隐喻进行祛魅的奠基之作”16,是因为作者除揭示在社会中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逐渐被隐喻化因而主张消除隐喻的幻象,回到事实本身以外,该著还告诉人们,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不应是不断将新的“意义”附于现象之上,正像西方颓废派作家所隐喻的那样,应该把表面搬运启蒙话语骨子里却反启蒙精神的贪婪、狭隘、歧视、虚伪、庸俗、保守、恶质,当作现代文明社会普遍的文化痼疾解构掉。桑塔格意义的“反对阐释”,也就是反对隐喻,这无疑是对社会高级形式的呼唤,可是这一思想诉求我们暂时还根本不具备,我们仍需在隐喻中探求真相、了解病根。
三
有人统计过阎连科小说中各种奇谲怪诞的残病。《受活》中有失明症、肢体瘫痪、失聪症、侏儒症、小儿麻痹症;《日光流年》中有喉堵症、烧伤、妇女病;《黄金洞》中有痴呆症、迫害狂想症、肢体瘫痪;《炸裂志》中有精神病、心脏病、偏瘫症;《风雅颂》中有精神病、偏执狂、相思病、妇科病、臆想症;《坚硬如水》中有疯魔症、妄想症、精神病;《你好,金莲》中有肢体瘫痪、早泄症;《耙耧天歌》中有癫痫症、痴呆症;《丁庄梦》中有艾滋病;《艺妓芙蓉》中有肢体萎缩、肺病;《速求共眠》中有傻痴症、妇科病、瘸拐、恶绝症(癌症)、亢奋性精神欲望病17,等等。显而易见,这些名目繁多的病残基本上是无法治愈的,身体残缺者属于先天性疾病,心灵残缺者大多则属于在自然村特有的集体无意识文化氛围中致残致病情況。心灵残缺在大的隐喻背景看,既有点接近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个阶段的情景,也有点接近19世纪西方颓废派作家的隐喻所指。但绝不是两者相加或两者混合的产物,是两者经过中国当代社会巨变与主流话语反复挤压后深度异化变味的第三种形态。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宏大视野已然消逝,但民族、国家意识中以此之整体取代彼之整体的诉求,却明明暗暗转换成了最后的堡垒——肉体这个剩余价值并以隐喻方式而存在。中国现代小说第二、三阶段疾病隐喻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均因被打断而双双失灵,丁玲小说中疾病对个体自我命运操控力及其对应的丧失反抗力的隐喻,张爱玲小说中疾病对更高一级别人性固有劣性的隐喻,统统被悬搁。至于19世纪西方颓废派文学中“颓废病”的隐喻,自然又比张爱玲的疾病隐喻更高,肯定不在阎连科的疾病隐喻之内。按照阎连科小说中残病的叙事功能和比例,可归纳为个体失语隐喻和农村现代社会机制缺席导致的基层社会变形这个整体隐喻。前者比较单纯,能够通过阎连科本人反复强调的个体对城市、权力、金钱三种贪得无厌的欲望追逐解释清楚。后者比较复杂,既非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所能解释,亦非19世纪西方颓废派文学中“颓废病”隐喻所能分析,它是由历史中国逻辑地发展到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难题的隐喻性表达。
没有“革命者”高爱军与夏红梅(《坚硬如水》)“革命”疯魔症、妄想症、精神病的普遍隐喻,就没有三姓村(《日光流年》)中村民“喉堵症”的后果。“喉堵症”隐喻基层社会失语,个体为“活过四十”不得不被死死绑架到高爱军、夏红梅式的战车上,几代村长也就成了“革命”话语与“革命”价值的发展者、生产者。在国家、社会、个体的三维体系中,非但阻断了从个体而社会而国家的生成流程,而且只剩权力一维一枝独秀,个体、社会、国家三维悉数阙如,导致延长生命这样个体化的命题,只能一次次被权力一维假启蒙之名包办代替,在这个宏大隐喻底下才不时暴露出个体疾病隐喻的主题。而许多研究者偏偏抓住的就是这个个体疾病隐喻,无疑是对阎连科疾病叙事的错位。因为阎连科的病残叙事是整体性的,阎连科也深知,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早已不是“五四”启蒙时代,更不是西方颓废派文学生长的时代。在他的时代,个体疾病隐喻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话语能量,个体疾病隐喻也不可能有效指涉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基层社会。
《受活》究其实质,其叙事是对个体疾病隐喻的试探,结果是失败了。他的叙事便转向了社会资本,受活庄残疾人“绝术团”巡演的前前后后几十年里,残疾人的合法性自国家话语退化成经济话语开始算起,经济话语以代理人的现代性的名义成为“民”与“国”之间的纽带,执行着现代革命史意义“国”对“民”的“启蒙”职责。可是,这种代理性“启蒙”扬弃了真正的启蒙价值,纵容了人性恶并以“恶话语”来描绘愿景。看起来“退社”是为着病残人个体负责,其实不然,被经济的循环逻辑操控的病残必须为抽象的国家概念交付更加高昂的学费,以防脱轨于经济现代化。这时候,人的现代性已经被经济现代化所取代。同样是疾病隐喻,启蒙视阈下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国”,是从君主“一姓之私业”的怀抱中解放出来还给大众的一个个人意义的礼物,对于大众来说,“国”与“民”的权利是等值的,大众不可能不充满期许。而受活庄的病残人透支残缺肉体预支的完全是一个经济上的黑洞,巡演是为了筹集“购列款”,但“购列”能不能实现,即是说“民”与“国”之间兑换的价值是否等值,则一定不由病残人决定,病残人的主体性、主动性是被屏蔽了的。“绝术团”里的病残演员能做的,只有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消费残缺,以至于心灵致残为止。整个过程中,看不到鲁迅疾病隐喻首先是个体启蒙的信息,非但如此,阎连科的病残隐喻所表征的是个体地位一步步被取消、个体意识一次次被否弃的结论。与其说这是荒诞、诡异的审美震惊,不如说是经济话语强化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的人的异化后果。这就为后续发展埋下了深深隐患。虽然是极端化隐喻,然而阎连科能体察到经济高速运转中农民及农村社会资本结构性赤字这一点,正是他比同时代其他疾病隐喻叙事者更透彻的地方。
这一层面再体验《丁庄梦》《炸裂志》中的病残隐喻,的确不单是阎连科对荒诞、怪异、恶魔性一类审美形式以及索源体、絮语方式18的迷恋,而是阎连科现实叙事逻辑的一个自然延伸,其病残隐喻也就有了更深入的思想针对性。
丁庄和炸裂村都是整体性病残隐喻。丁庄人因集体买卖血浆而整村沦陷于艾滋病,炸裂村在城镇化神话中不得不以卖皮卖肉卖血透支唯一的肉体这一经济资本而集体塌陷于精神病、心脏病、偏瘫症的精神深渊。两个村的奋斗目标不尽相同,前者为着致富,后者为了城镇化。但两个村的欲望驱动却惊人相同,都是以经济指标为终极引擎。《丁庄梦》的故事起因于一种朴素的对比,邻村人卖血致富了,丁庄人也是人岂能落后?丁庄人对卖血的犹豫也源于一般知识的匮乏,校长丁水阳说人的血就像水,是不断更新的,循环往复抽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为血头丁辉带领村人买卖血浆赋予了一般知识合理性。这个逻辑中,显然没有科学思维,或者说科学思维服膺于经济思维和一般知识合理性了,为艾滋病的隐喻确立了方向。《炸裂志》的故事起因于炸裂村孔、朱两家族的权力斗争,故事发展遵循了因经济而权力,因权力而人伦崩塌的逻辑,最后以权力胜利者孔明亮变成真正的權力“空心人”、经济强势者朱颖变成真正的身份迷失者而告终。毋庸置疑,到了这一层,《受活》那里作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整体性病残隐喻,分解成了两支。一支隐喻健全人的经济主义后果,另一支隐喻健全人的权力主义后果。由村长而市长的“空心人”孔明亮,由孝顺体贴温柔善良而阴险奸诈身份合法性被人伦注销的朱颖,既表征了身份终结而权力运行照常进行,也印证了灵魂已死而肉身驱动的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依然如故。
四
这不禁使人想起阎连科“反抗”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小说中“人身羁押”的题外话。巴尔扎克杰作《幻灭》中发明家赛夏由于债务以及他的姻兄吕邦泼莱的伪证而陷于破产,成了库安泰兄弟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他们想要逼迫他说出他所发明的、可以给资本主义报业提供廉价纸张的秘方。按照当时的法律,要是债务人无法偿还债权人,他的身体就应该受到羁押。这种人身羁押旨在让债务人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资产。换言之,身体被认为是对不够数的物品的补充,而身体的羁押就是进行偿还的一种方式。《交际花盛衰记》也同样遭遇了更加极端的人身羁押,吕西安被指控敲诈而被捕,关押在附属监狱,他在那里把自己吊在单身牢房的窗户栅栏上,自杀身亡。吕西安的身体为它的违法付出的最后代价,也体现在《人间喜剧》的那些核心小说中,它始终是巴黎社会从最下层的女人、化名伏脱冷的罪魁祸首雅克·科兰乃至吕西安自己的欲望对象。“巴尔扎克对于法律体系所界定的身体的关注提供了进入现代身体观念的一个象征性的通道,在这种观念中,个人最终要为身体——并且,以身体——承担责任。”19在这里,资本化的身体的矛盾清晰可见,它属于经济体系,而与此同时它又被视为个人自己的、最后的、也许是唯一的拥有。《交际花盛衰记》的女主角艾丝苔正好落入了这个矛盾之中,她到底有没有权利处置她自己的身体?她的“解答”是一个妥协,她将与银行家纽沁根上床一个小时,来偿清债务,而后自杀。
非常相似,阎连科《受活》中受活庄病残人“绝术团”被柳县长以“退社”为条件挟持巡演赚钱买列宁遗体用来拉动旅游经济,穷极几十年,“购列款”是筹够了,但“购列”工程却被叫停了。被“拘押”在“列宁纪念馆”的病残人又被“圆全人”以买吃的为由长久“羁押”,最后又公然把病残人身上的所有积蓄一洗而空,病残人于是被彻底打回原形,回到受活庄不得不从零开始,又一次进行原始的却是被外界意识形态深度改造的病残生涯,身体资本化也就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奇特隐喻。
虽然一个是死,一个是活,但病残人这一回的活,却比艾丝苔的自杀更失去尊严。
历史有时真是惊人的相似,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的《人间喜剧》作者的所感所悟所见,居然与“反抗”现实主义并且以荒诞、怪异、恶魔性小说著称的阎连科曲折委婉隐喻的认知,不约而同。
从政治经济学乃至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丁庄与炸裂村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文化与价值的层面审视,病残隐喻指向的结果无一例外,都奔向了心灵与精神病残的方向,这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难题所在。看来,无论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19世纪西方颓废派文学中的“颓废病”隐喻,还是阎连科小说中整体性病残隐喻,其思想表达不可能脱离具体时代主要的流行价值趋向而存在。
既然如此,阎连科实在不必以“神实主义”来标新立异,阎连科的研究者也大可不必因为“神实主义”而有意制造文学的“进化论”,那样反而会给文学减分而不是加分。■
【注释】
①阎连科《发现小说》一书是一部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一开头他就以“我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表明了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立场,“神实主义”正是他用以全面反抗他认识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武器。阎连科:《发现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②《发现小说》一书是关于“神实主义”理论建构的专书,全书共六章,前五章分别从解构现实主义的几层“真实”入手,逐步推出“零因果”“全因果”“半因果”“内因果”,第六章得出“神实主义”特征。经过仔细分析可知,他主张的“神实主义”其实更适合于帮助读者鉴赏不同类型小说,并有助于从叙事手法上分辨不同类型小说的形式结构,但与他的小说创作实践并没有必然逻辑关系,更不存在互补互解的关系。这一点是要特此说明的。
③乡村苦难与乡村人物命运苦难是批评家对阎连科小说“疾病”“残疾”叙事的主要看法,代表性文章主要有南帆:《反抗与悲剧——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姚晓雷:《走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祭》,《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陈国和:《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生命寓言书写》,《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洪治纲:《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林舟:《乡土的歌哭与守望——读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当代文坛》1997年第5期;余萃:《苦难生存中人性深层的探究——论阎连科“耙耧系列小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等等。另外,专门以阎连科小说各种“疾病”隐喻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有王阁娟:《阎连科的文学世界:以疾病为视角》,2019;高芳芳:《论阎连科小说的疾病书写》,2013;杨婷婷:《论阎连科小说中身体疾病与心灵残缺的书写》,2018;陈怡:《新世纪小说中的疾病与医疗书写(2000—2010)》,2017;等等。
④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
⑤载顾成敏:《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165页。
⑥⑧郭继宁、郑丽丽:《“疾病”与“治疗”——对清末新小说中一对隐喻的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⑦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第20页。
⑨1112李建伟、杨金芳:《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以鲁迅、丁玲、张爱玲的小说为例》,《齐鲁学刊》2016年第5期。
⑩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933年第2期。
13杨希、蒋承勇:《西方颓废派文学中“疾病”隐喻发微》,《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4[美]童明:《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第75-76页。
15[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16张维时:《一场文明的祛魅行动——疾病隐喻理论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7杨婷婷:《论阎连科小说中身体疾病与心灵残缺的书写》,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18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19[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第81-87页。
(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