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份“国家刊物”,《诗刊》从1957年创刊以来就与中国当代诗歌命运紧密相连,而分属中国作家协会的“政治”身份,又给这份刊物平添了一丝权威的意味。到1964年12月停刊以前,《诗刊》的八年是一度辉煌的年代。创刊号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增加了《诗刊》的政治筹码,也奠定了《诗刊》从此的“皇家”地位,此后的新民歌运动、工农兵诗歌等,都表现了《诗刊》迫近现实的姿态。1976年1月复刊号又发表毛泽东词二首,80年代初期的《诗刊》为朦胧诗的推介和讨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关朦胧诗论争的大部分文章都登载在这一时期的《诗刊》上,包括1980年第8期登载的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直接成为朦胧诗论争的导火线。1980年,《诗刊》社举办了第一届青春诗会,此后每年一届,从青春诗会上走出了许多优秀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王小妮、于坚、韩东、翟永明、西川等。
诗歌界“清除精神污染”后两年,时代的变化使得《诗刊》杂志本身也出现了变化。从1985年开始,《诗刊》渐渐失去引领新诗潮的能力,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步步后退,直至90年代在市场化的洪流中退出曾经据守的高地。
一
1.刊物风格及创作群体
如果用两个关键字来形容80年代中后期的《诗刊》,那么应该是“改革”这两个字。纵观1985年到1989年的《诗刊》杂志,核心是紧扣改革的。无论是杂志的卷首语、编辑后记、诗论、刊发的诗歌,基本的价值取向即是否紧密联系了这样一个“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时代”。1985年第3期一篇《要讴歌新时代的改革者》的文章如是说:“要求诗人以文艺工作者的态度来写诗,不能拘于内心的小情感,而要面向大时代,要歌颂新时代的改革者,诗人自身必须是改革的热心促进派、真诚的拥护者。”在内容上,《诗刊》不仅卖力地提倡诗人写作能够反映时代的诗歌,还就诗的题材、风格、流派、表现手法等方面提出了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观点。在198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上,编委李瑛和刘湛秋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时代需要多种风格,但尤其需要惠特曼和‘五四’时代的郭沫若,他们不仅是狂飙式的气势、奔放的情感与一个开拓的时代精神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诗中所表现出新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同时,《诗刊》社1986年相继刊发了“改革与诗四人谈”专栏,大力鼓吹诗应当承担起表现和宣传改革大业的重任。
1987年第9期的卷首语这样写道:“生活波澜壮阔,而当代中国又处于改革之中,每个人都可能碰到很多如意和不如意的事。诗人所见所闻,感慨颇多,发而为诗,抒人民心声,这正是诗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希望诗人们更密切接触生活,热情拥抱生活。编辑部热望读到有生气的作品。即使艺术欠火候,但有生气就可。”与此对应的是《诗刊》每期以大篇幅刊发政治诗、改革诗。描写领袖的《小平,您好!》(1985.5)、《为紫阳画像》(1986.10)、《“急性”的悼念——哭耀邦同志》(1989.5),讴歌改革、抒写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伦理价值观念变化的《 筑路时代》( 1985.5)、《 中国企业家》( 1987.7)、《 夜广州》( 1988.1)、《 深圳记事》( 1988.5)等。
这种诗人要写“伟大的时代”的观念,与那种“大写十七年”的口号其实是很相似的。诗歌贴近现实并没有错,然而单纯重视诗歌政治功用而抹杀自身诗艺追求的例子,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靠向时代的同时也带来了将诗歌变成时代“传声筒”的危险。
《诗刊》在栏目设置上,也体现了传统“拼盘”风格。1985年到1989年这五年间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栏目设置:卷首语、某一主题的诗(如5、6月的儿童诗,10月的无名诗人专号和刊授学员作品,11、12月的“青春诗会”专栏等)、纪念诗歌(如纪念《讲话》发表45周年,纪念抗战50周年等)、名家诗作(冯至、陈敬容等老诗人的作品)、讽刺诗、散文诗、抒情短诗、台港澳和外国诗歌、旧体诗、诗歌评论等。介绍翻译的外国诗人诗作中,以苏联、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古巴等国家居多,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如布罗茨基、加里·斯奈德等,一直到1988年王家新接手“外国诗”栏目时才出现在《诗刊》上,更不用说艾伦·金斯伯格这样的诗人了。
1985到1986年被称为理论界的“方法年”,这一时期《诗刊》发表的诗评诗论最多,然而大部分诗歌理论还是停留在古典主义式诗论上,谈古典诗词里的意象,谈诗人如何通过感觉、激情、想象去了解世界,谈诗画相通的理论,谈通过字的挪动和变化达到不同的效果,谈诗的空白……很难有新意感。
这一段时间刊发的诗歌大都与现实紧密联系,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对一些具有探索精神的诗虽不表示否定态度,然而也看不出鼓励和扶持的姿态。粗略统计,这五年期间在《诗刊》上出现频率较高的诗人有:冀汸(9次)、张志民(8次)、刘章(8次)、罗洛(8次)、刘征(7次)、蔡其矫(6次)、公刘(6次)、沙白(6次)、韩作荣(6次)、陈敬容(6次)、刘湛秋(6次)、简宁(6次)、赵恺(6次)、章德益(5次)、张学梦(5次)、陈显荣(5次)、陈所巨(5次)、苗得雨(5次)、梅绍静(5次)、雁翼(5次)、张子选(5次)、叶延滨(5次)等。作者群的构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归来诗人”群体,包括鲁藜、流沙河、邵燕祥、顾工等人;另一类是青年诗人,青年诗人群体再分为两类,朦胧诗人和一些现实主义风格的诗人,像出现频率较高的陈所巨、梅绍静等人,都是属于现实主义风格的。1985年以后正是第三代诗人活跃的年代,然而《诗刊》对这些诗人的选择都比较谨慎,尤其是被视作“口语写作”的这一派诗人,除了于坚在1986年11期发表的《生命的节奏(四首)》外,其余的诗人几乎没有被涉及。
这一时期的《诗刊》,对时效性和外部社会的关注与对探索倾向诗歌的刻意回避,构成了复杂的混合体。刊物风格从整体上看是持重、保守的,虽然偶有亮点,如1986年第9期刊发的翟永明诗歌、第11期的于坚诗歌等,但由于自身立场的制约,总体质量并不足观。
2.编辑构成及办刊定位
在七月派和九叶派集体失语的年代,只有政治上可信可靠的、艺术追求符合权力意识形态的人才能跻身文学官员之列。纵观1957年创刊以来到80年代末的主编构成,几乎全部是30年代活跃在国统区或解放区的“进步诗人”。在建国后文学权力重组的过程中,如穆旦等人公开发表诗歌都已成为困难,更遑论掌握文学权力,还有显例如胡风一派的作家诗人等。1976年《诗刊》复刊后,主编群体依旧是这些老资格的被视作“政治可靠”的诗人官员。历届主编从臧克家、李季、严辰、邹荻帆再到张志民、杨子敏,都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本。再看编委,1985年的《诗刊》刊尾标注的编委成员包括:丁国成、公刘、艾青、田间、朱子奇、阮章竞、严辰、李瑛、杨金亭、克里木·霍家、吴家瑾、邹荻帆、邵燕祥、柯岩、赵恺、流沙河、鲁藜、臧克家。到1985年12月除却当年去世的田间,编委依旧。1986年主编换成了张志民和杨子敏,克里木·霍家1989年从编委名单上消失,余下的编委成员结构一直保持到了1989年末。这些编委们的履历和身份依然显赫,如柯岩,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妻子,自身则是中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后来成为作协书记处书记。主编和编委是决策层,对刊物的总体方针起导向作用。从《诗刊》登载的一些记录当时各种会议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主编对刊物的总体把握和定位。杨子敏说:“在庆祝《诗刊》创刊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将努力做到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安定团结,以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诗歌有一个稳定的繁荣发展的环境。”“党的十三大召开后,改革正在新的形式下继续、深化……改革与诗才真正成为时代向诗歌提出的一个历史课题……时代孕育、选择自己的诗人……真正属于历史的诗人,也总是首先属于自己的时代……这种高度的敏感和使命感,把诗人与时代的息息相通同‘气象观测员’式的附声附和,判若云泥地区别开来。”1985年2月的《诗刊》上发表了18位老诗人联名签署的《为诗一呼》,其中半数的诗人是曾经或现任的《诗刊》编委成员,包括严辰、屠岸、鲁藜、艾青、邹荻帆、李瑛、公刘和张志民等,他们认为“诗是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他们不满于新诗受到冷遇的现状,呼吁各级文艺领导重视新诗,给新诗的发展以关怀和支持。诚然,诗歌的发展繁荣在当代中国还有理由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但希望依靠官方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来推广发展诗歌显然有些不切实际。
最能体现办刊方针的莫过于1986年的《〈诗刊〉编辑谈〈诗刊〉——记〈诗刊〉编辑部的一次谈心会》,文章明确提出了对《诗刊》的定位以及目前关注的八个问题。作为总的方针政策,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提出:“编辑部有不少同志,从《诗刊》复刊以来,便一直耕耘在这块土地上……大家认为,刊物首先要从宏观上把握我们的时代,学习理解党的方针政策,要和我国广泛而深入的经济改革的宏伟任务情感交融,要思考诗歌如何适应改革的新形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改革本身就是创造,有广阔的可探求的空间。当前,刊物殷切希望我们的诗歌创作,能够更加切近现实,切近生活,使广大读者能从刊物上发表的诗作中,感到改革精神、时代气息扑面而来,闻到现实生活的烟火味,听到历史激流的轰鸣。”此外,刊物也重申了兼收并蓄的原则,对编辑素养、鼓励青年诗作和诗歌评论等方面表示了关注。
在编辑心态上,官方刊物的权威地位使这篇谈话隐隐透露出一番优越感:“由于诗坛空前繁荣,各地诗刊、诗报以及群众性的诗歌活动越来越多,《诗刊》将加强对全国诗歌活动的调研工作,加强与各地诗歌社团的联系。并大力扶植群众性的诗歌、朗诵活动。”
对处于决策层的主编们来说,《诗刊》负有引导民间诗歌活动,将官方的文学政策传达贯彻下来的责任,作为一种标杆和楷模,《诗刊》当然首先要严格符合意识形态,不能跨越雷池禁区。
执行这些操作的是普通编辑,他们从成千上万的稿件中选择符合标准的诗歌。普通编辑们当然有对诗歌的艺术追求,但面对强大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滤网,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探索和调整。后来一些编辑的回忆录,如王燕生和唐晓渡,曾经提到过当时这种环境下自我妥协的矛盾心理。
由于主编和编辑双重因素的影响,《诗刊》最终呈现的刊物风格与这一时期的刊物定位之间存在着距离。正如前述,《诗刊》迫近现实的姿态与实际登载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混合的风格。同一期刊物,既可以有描写改革的诗、锋芒毕露的政治讽刺诗、略显古板的旧体诗,也可以有张枣的抒情诗、口语诗、外国现代派诗——虽然这样的努力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二
只需简单回顾1985到1989年间国内各种民间诗歌团体和刊物风起云涌的景象,就可以理解《诗刊》在此阶段受到的实际冲击是何其巨大:1985年1月白桦主编的《日日新》和整体主义的《现代诗内部参考资料》在成都创刊;同年3月包括韩东、于坚、丁当在内的“他们”文学社在南京创办《他们》;4月,上海的孟浪、陈东东、王寅、陆忆敏等创办《海上》和《大陆》;7月,民间诗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和《圆明园》创刊;1986年5月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创办《非非》诗刊;稍后黄翔等在贵州发起“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并印行同名诗报;1987年3月廖亦武执编的民间诗歌出版物《巴蜀现代诗群》发行;5月,孙文波主编《红旗》和严力在美国创办的《一行》印行;1988年7月,民间诗刊《幸存者》印行,主要成员有芒克、杨炼、唐晓渡等;9月,《倾向》创刊,主要成员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11月,《北回归线》创刊,成员包括梁晓明、耿占春等……这一时期各种民间诗歌团体的冲击使得《诗刊》独领风骚的地位最终被打破,诗坛不再是建国初延续下来的大一统天下了。各种思潮派别迭起,多元化成为一种趋势。时势逼迫诗歌刊物必须做出应对,否则,就只能被新诗潮抛到后面。
毋庸置疑,80年代是现代诗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因为它第一次打破了建国以来甚至上溯到40年代解放区的传统诗歌写作范式和观念的笼罩,也由于诗歌内部开始的自我嬗变。这场民间的诗歌团体运动的高潮是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推出的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多达84个民间的诗歌团体在刊物上展示了自己,多取向的价值形态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的基本生态,现代诗终于由众多的民间诗歌群体推向了历史变革期。
《诗刊》在这一时间段遭受的冲击,不仅来自于众多民间刊物,另一方面,自身稳重有余、锐气不足的特点也使它开始丧失青年读者。主要将创作触角停留在社会和道德领域的诗歌已经不再能唤起读者的阅读新鲜感,何况判断诗歌好坏的价值标准也已经出现裂变。同一时期一些有影响力的诗歌选本已经不再局限于《诗刊》推荐的诗歌,到80年代末,这些诗歌选本甚至与《诗刊》的诗歌形成了两极分化的对立物。直至现在还能被诗歌爱好者念念不忘并很可能定格在中国新诗史上的诗歌选本,应该包括:徐敬亚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唐晓渡、王家新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
在这样一个写作手法和写作经验风云变幻的年代,《诗刊》刊发的诗歌还有像《神奇的盐粒》(1985年11期)这样的“革命老套”甚至嘲弄读者智力的诗歌,且看《神奇的盐粒》其中一段:
盐从何处来/是否想过/敌占区老乡的配给盐/家家口里攒/肚里挪/好容易积少成多/半夜背过封锁沟/不料被鬼子发觉/八百多斤盐/八个老乡牺牲/我们死也不能忘记呵/指导员的热泪/是冷彻心田的冰水/欢嚷嚷的饭场/一下落进了/透不过气的沉默里/我们品尝的盐里/有我们亲人的血呵/我们还仿佛看见/白发父母们的老泪/我们还仿佛听见/红颜妻儿们的悲啼
在选择诗歌的标准上,《诗刊》强调遵循贴近现实的原则。1987年第11期的青春诗会专号,卷首语明确表示,入选的诗作都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的。“读者都希望我们能推出比较优秀的青年诗人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可选择往往又不尽如意……我们是考虑到不同风格和题材的,我们也希望这些诗人的作品在内容上尽可能贴近现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选择的标准一直延续至今,一位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回忆:“作为此届诗会的与会者(第18届青春诗会,引者注),我唯一的遗憾是诗会期间初选上的拙作《基本功》、江非的《到北方去》、魏克的《到处都是魏克》最终没能在当年第10期《诗刊》‘青春诗会’专号上露面,而是换上了内容上更为‘保险’的作 品。 ”
总体来说,《诗刊》的刊物风格和诗歌水平已经明显与当时风云巨变的诗坛产生了深刻的断裂和分歧。作为官方刊物,生而俱来的意识形态规约限制了《诗刊》向更前沿的领域探索,它作为诗坛领袖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无从支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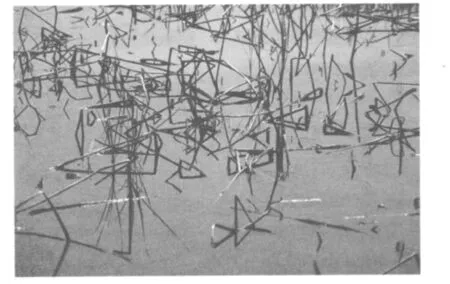
80年代中后期对《诗刊》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时代,这个时期既不同于“文革”结束初期文学与政治相呼应的蜜月期,也不同于后来90年代商品经济浪潮下的众神狂欢时代。一旦权力意识形态的控制不能不有所放松,文化政治环境不再像建国初期那样趋向于制度性的“收紧”,读者对于刊物也有更大选择可能的时候,《诗刊》如果不能有所作为,就不再会是诗人和读者心中的“圣地”了。
结 语
诚然,《诗刊》并不是消极应对这场时代变革的,在有限的控制范围内它也做出了一些应对,如举办诗歌朗诵活动、召开评论家会议、刊发青年新作、举办诗歌大赛等。1989年举办的“珍酒杯”新诗大奖赛,算作是第一次与商业合作的努力。相较于它的姐妹刊物,同属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后者显然做得更好一些,这也使得它的“衰落”延缓到了90年代。总之,在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诗刊》几乎是以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来应对波涛汹涌的外部进攻,终被新诗潮抛到了后面。从1985年的杂志直接翻看1989年的杂志,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间隔距离。对于一份诗歌刊物而言,1985到1989年是《诗刊》被迫后撤的一个过程,然而对中国新诗来说,这是一段也许再不会遇到的黄金时代。有意思的是,一份官方刊物的后撤正是新诗多元化、多向度进展的有力印证,也正是这种多元化和多向度,开辟和代表了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的又一次蓬勃发展。
【注释】
①《要讴歌新时代的改革者》,《诗刊》1985年第3期。
②《为了诗的繁荣——一次诗歌座谈会的摘记》,《诗刊》1985年第4期。
③此统计不包括旧体诗和诗论作者。
④《诗刊社举行创刊三十周年招待会》,《诗刊》1987年第2期。
⑤《〈诗刊〉编辑对话:纵横诗坛》,《诗刊》1988年第1期。
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诗刊》1985年第2期。
⑦《〈诗刊〉编辑谈〈诗刊〉——记〈诗刊〉编辑部的一次谈心会》,《诗刊》1986年第6期。
⑧参阅《王燕生:见证八十年代》和《人与事: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二文。
⑨资料整理自唐晓渡《人与事: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
⑩卷首语,《诗刊》1987年第11期。
?刘春:《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