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编辑部,北京 100125)
一、自然作为家园和信仰
在汉语语境中,“自然”一词具有复杂多义的含义,除了指大自然之外,也可形容一种状态,比如自然而然,任其自然;还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这些意思又相互关联相互缠绕,显示出自然一词具有的张力。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道法自然”,就同时蕴含了这多种意义。自然就是家园。在《诗经》《楚辞》等最早的诗歌中,就呈现出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诗经》中有大量关于草木的描述,如荇菜、卷耳、蕨薇、荠菜、芹、梅、栗、葛麻等,这些很多是可供食用、药用和制衣的日常必需品。《楚辞》里则有桂、椒、杜衡、薜荔、兰、芷、蕙草等,起着装饰美好生活的作用。这些诗歌里营造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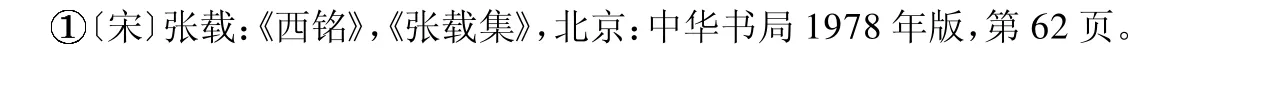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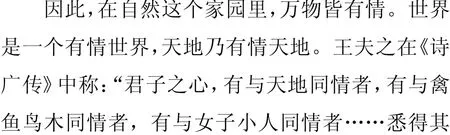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清〕张潮:《幽梦影》),宇宙是有情天地,生生不已。天地、人间、万物都是有情的,所谓“万象为宾客”(〔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侣鱼虾而友麋鹿”(〔宋〕苏轼:《赤壁赋》),“好鸟枝头亦朋友”(〔宋〕翁森:《四时读书乐》)等等。情,是人们克服虚无、抵抗死亡的利器。世界,是一个集体存在、彼此感应、相互联系、同情共感的命运共同体。
自然被认为是永恒的象征。自然之永恒性,体现在山水精神中。对照人类的有限短暂一生,山水是永恒的。作家韩少功在散文《遥远的自然》中分析:“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山水本身本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山水也成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人格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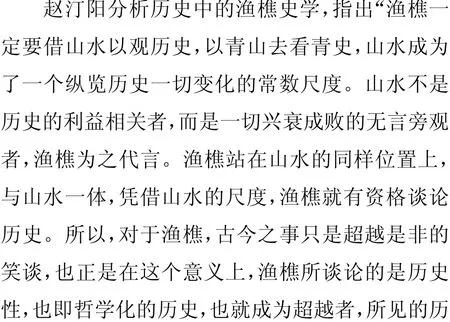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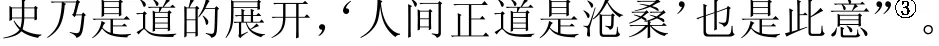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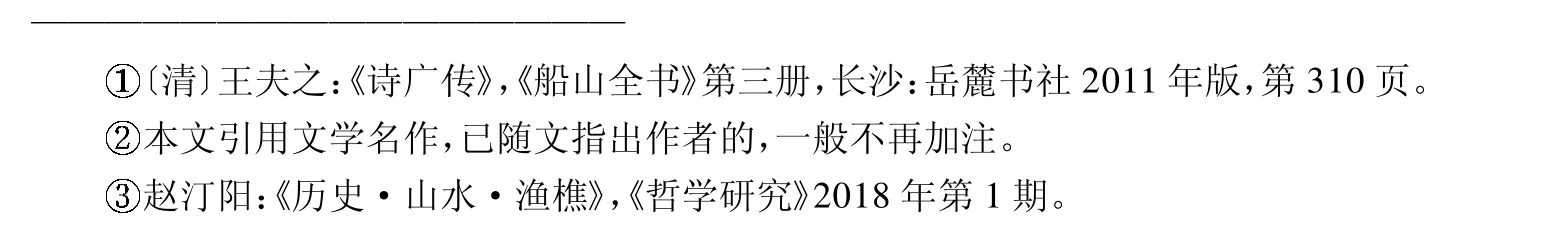
赵汀阳认为山水具有在地而不远人的超越性,因此山水被当作道的形象。作为道的显形意象,山水确实坐落在世界里,是人间世界的一个内部存在,与具有“在地超越性”的山水相对应的是熙熙攘攘的社会和似水流年的历史。仁者智者借得山水的尺度以观历史,因此能够平静理解人世。传说渔樵是山水之友,识得山水之象,于是渔樵被看作山水的代言人。这种渔樵史学,本质上就是指认自然山水的永恒性,还有超越性。
自然还是中国人的信仰。任何文明都需要超越性的向度。自然在中国文明中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推崇的都是自然神,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崇拜的都是与自然相关的神灵,比如与物质生产有关的神农氏、燧人氏、妈祖等,与人间生活有关木匠祖师爷鲁班、纺织女神黄道婆、药王孙思邈等,还有自然神龙王、雷神、风神等,都建立庙宇祭拜,各地则供奉着土地神,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
自然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其安抚人心慰藉情感的功效。自然山水具有强大的精神净化作用,灵魂过滤功能。诗人谢灵运很早就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明代汤传楹《与展成》文中称:“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里更进一步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看见山水,人们可以忘记一切世俗烦恼,可以化解所有焦虑紧张,所以古人认为山可镇俗,水可涤妄,山水是精神的净化器。西方也有类似说法,比如把自然看作“人类的避难所”,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认为现代人应该到自然之中去“施行精神洗礼”。
所以,中国传统,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的亲缘关系。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是诗人灵感的来源。道法自然,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张璪),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自然山水可以安慰心灵,缓解世俗的压抑。山有神而水有灵,王维称其水墨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画山水诀》);晚明董其昌云:“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画禅室随笔》)明代诗人袁宏道说:“师森罗万象,不师古人。”(《叙竹林集》)以自然山水为师,是众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艺术实践的共同心得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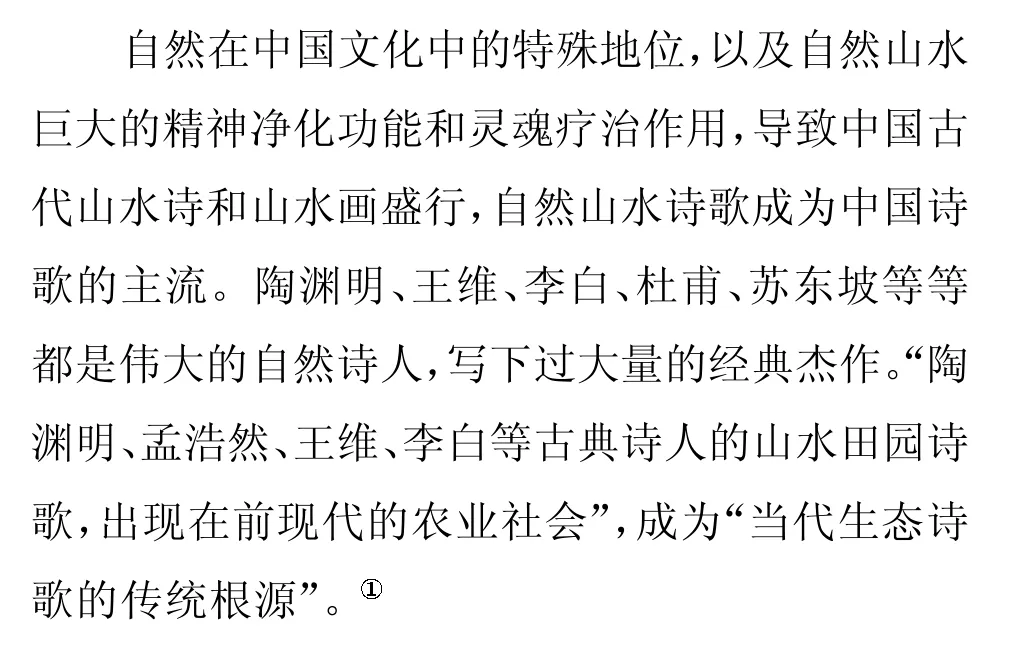
二、古典诗歌与自然
(一)陶渊明
陶渊明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诗人,他的诗歌里,不仅仅有山水田园,更重要的是,他是真正的“道法自然”,他把自然作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把自己作为自然和历史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是真正做到了在自然中安心安身。
陶渊明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诗人,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一般认为,自然作为一种观念,就是在魏晋时期确立的。魏晋时期名教和自然之争,开启了思想解放,启蒙了人的觉醒,“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种种观念束缚,冲破礼教的桎梏,是当时的一股潮流,并从此打开了任情任性的闸口。陶渊明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实践者和行动者。“归去来兮”,就是陶渊明的个人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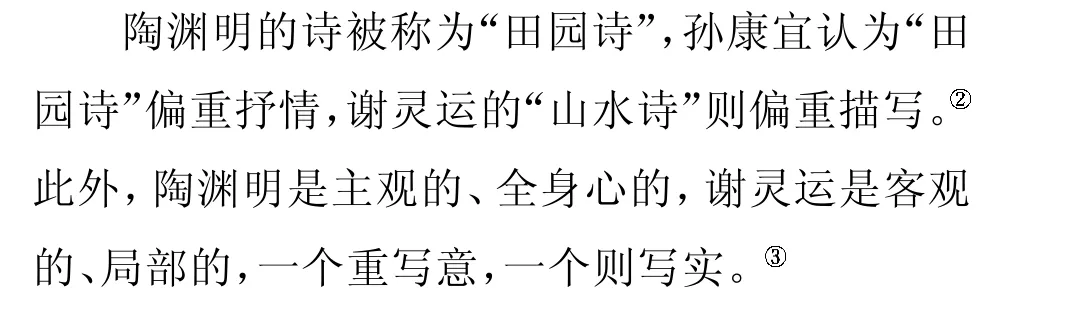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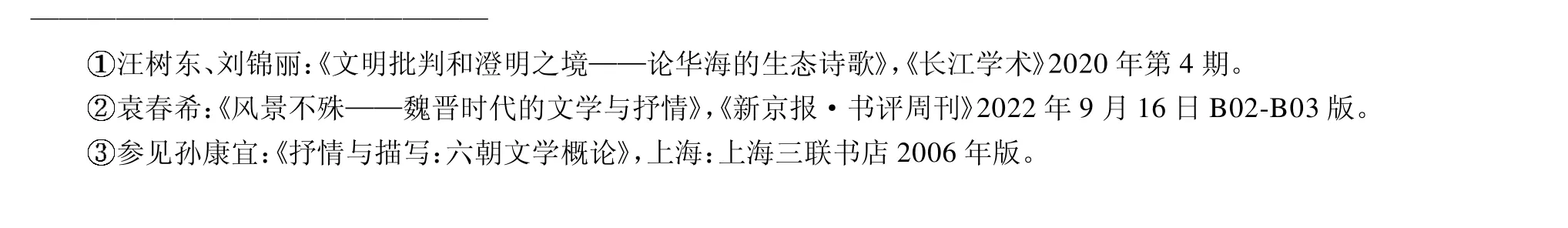
陶渊明的“田园诗”最重要的特征是抒情,一种扩大了的自我抒情,比如对田园的真心热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很满意自己居住的地方:“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对耕读生活的沉浸:“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对乡土的眷念:“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连风也是有情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渊明喜爱菊松兰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秋菊盈园”,“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春风”“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等;陶渊明对自然的真心热爱,所以才会有退隐之后的由衷感叹:“久在樊笼里,终得返自然”。
因为陶渊明的隐逸个性,他基本上回退到了自己个人的空间,他不像谢灵运那样开山拓道,到处巡游。因此,广阔的大自然还在等待另外的人出场,那就是李白。
(二)王维
王维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融合者和集大成者,在他和孟浩然之前,田园诗和山水诗各自发展。王维在更高层次上统合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他是以“道”或者说“禅”统合了抒情和描写,写意和写实,呈现出更高的自然意境。王维时代,隐逸风气流行,王维将自己隐退在山水之后,让自然自己呈现。越往后,王维越来越更彻底融入乃至消泯于自然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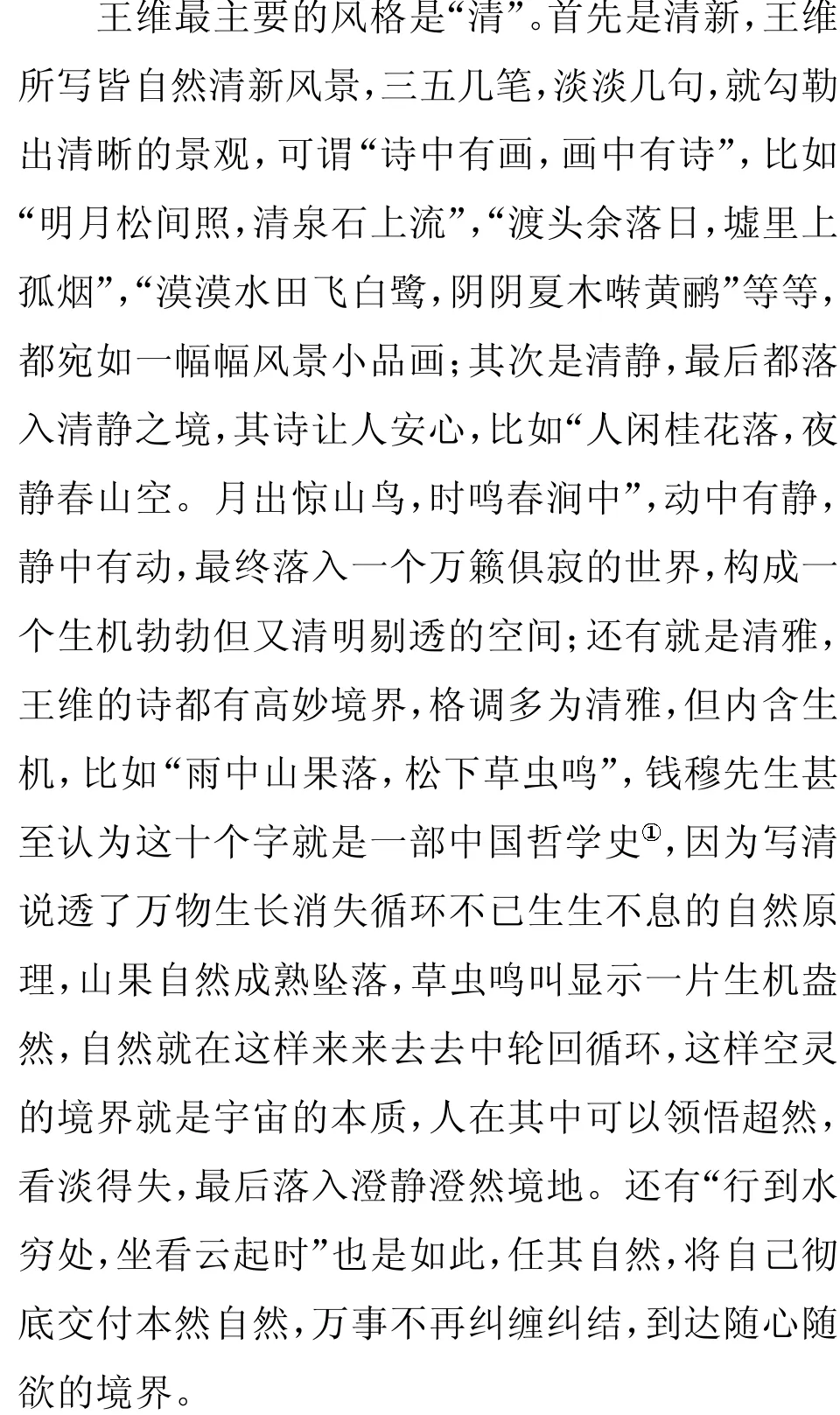
王维的诗,可以说将自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以致成为山水诗的最佳典范。
(三)李白
李白与自然一体,他仿佛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如果说陶渊明和王维在自然面前是退却的姿态,是向内的,李白则是出击的状态,是外向的,其主体性如同那些崇山峻岭,醒目而挺拔。
李白自己就是崇山峻岭和大江大河,“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只有李白,如此张扬又如此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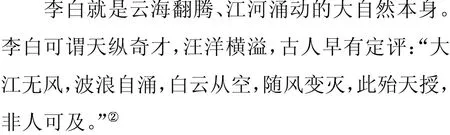
李白诗中多壮丽意象,上天揽月随处摘星辰,下海骑鲸顺手捞珍珠,可谓气吞山河、包孕日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样气势磅礴的诗歌,只有李白写得出来。李白喜欢宏大叙事,用一切大词:大鹏、大鱼、巨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绝顶等等,这和到处开疆拓土、万邦朝圣的盛唐精神是一致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青山相对处,孤帆一片日边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一生游历了无数名山大川,“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真正做到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也是其开阔自由精神和豪放壮观气象的彰显。
李白的诗歌风格,比起王维的精心精致精美来,更加自由恣肆,无所顾忌,所以他的诗歌风格更加变化多端,既有豪放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也有悲壮如《蜀道难》等,还有小清新的《玉阶怨》等,以及人世缠绵的《长干行》等等。
(四)杜甫
如果说李白本身是大自然的化身,杜甫则是在自然中获得慰藉和安心。杜甫总是将人事置于广阔的大自然背景下来展开:“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何其壮丽!杜甫能把景色写得如此恢弘开阔,其实还是源于其强盛的生命意志力,这种生命意志力使他任何时候都不气馁。所以无论他本人处境如何凄惨,他的诗歌仍然让人读来有一种生气,因为,大自然本身是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
《旅夜书怀》特别典型,这首诗只有八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杜甫晚年孤独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另一方面,这首诗似乎又一点也不悲凉,“天地一沙鸥”,其实,何人不是如此啊?何况还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样值得人生留恋的瑰丽景色。
还比如《秋兴》之一:“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前面还是“听猿实下三声泪”,最后却说“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杜甫总能从大自然中找到美丽、温暖和安慰,个人在自然的广阔中得到了慰藉。
(五)苏东坡
苏东坡游于山水之间,不仅仅是游走,他还游心。苏东坡的自然观和陶渊明相近,也是将自己视为浩淼星空长河中的一环,承前启后,所以他不焦虑,也不气馁,他怡然自得,游刃有余,在自然之中,心安理得地平静对待自己的遭遇,安度自己的一生,即使最困苦的时候,他也总有办法自得其乐,享受生活。苏东坡因为和陶渊明心有戚戚然,所以特别喜欢陶渊明,甚至专门写“和陶诗”。
《前赤壁赋》里就泄露了苏东坡的心底奥秘:“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人其实都只是自然长河中的一环,做好该做的事情就可,其他就交给时间和历史,所以苏东坡感叹:“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至此,苏东坡获得了超脱的心态,不再恐惧死亡,而是将自己托付于宇宙消长变化的时间长河之中。珍重当下,珍惜此刻,成为他最自然的选择。苏东坡最终达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可以说和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一脉相承。
苏东坡明了世界和生活的本质,所以总是乐观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人生下一场,即使不断被流放,但他认为自己平生功业,恰恰在三个流放之地:黄州、惠州与儋州。苏东坡的《定风波》最能体现他的从容心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的这种广阔胸怀,可以说是具有“天地境界”,所以其创作也是汪洋恣肆,相比陶渊明的恬然冲淡,苏东坡可以说包罗万象,以致要用“苏海”(韩潮苏海)来概括其创作。而苏东坡对自己的创作也有一个总结:“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就是真正的文无定法自然而然。因此,苏东坡的诗词,有豪迈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婉约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飘逸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明丽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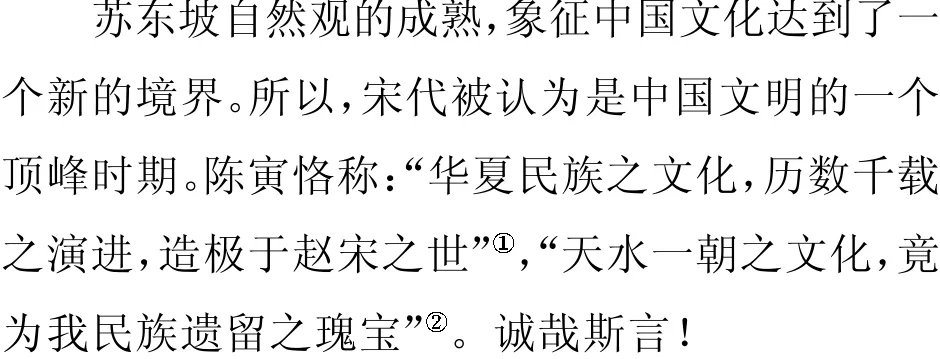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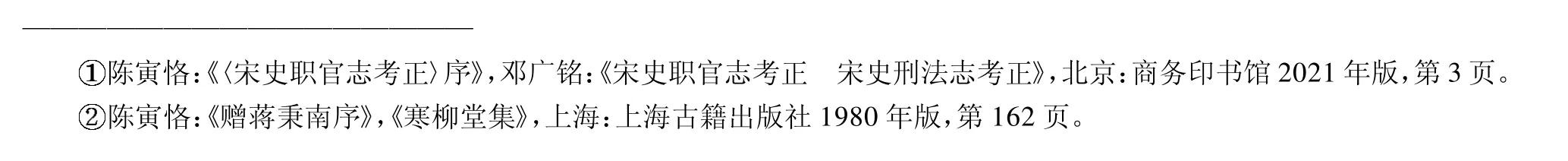
三、自然重新被关注,成为生态问题
自然再次被关注,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的,那就是变成了生态问题。所谓生态问题,与现代性有关。生态问题一次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都与环境污染有关,尤其一些重大的污染事故比如水污染、农药污染、鲸鱼大象猎杀、珍稀动物濒临灭绝等等,还有就是和每个人有关的情况,比如温室气体上升、雾霾、沙尘暴、北极冰川融化乃至病毒瘟疫大爆发等等,这些表面上是外在环境问题,但其产生,也与人心的变异有关。
“生态”这个词古已有之,原指美好生动,南朝梁简文帝《筝赋》“佳人采撷,动容生态”;唐杜甫“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等等,后有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的意思。而在现代观念里,生态是指生物和生命的状态,及与周围环境、万事万物的关系。如果说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那么这个家园的内涵,已经被置换为环境——人和其周边网络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等外部世界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出现不协调,就是生态出了问题,生态系统被破坏,生态自然循环出现故障。所以,生态成了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
生态的和谐平衡,已经成为现代人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而在古代,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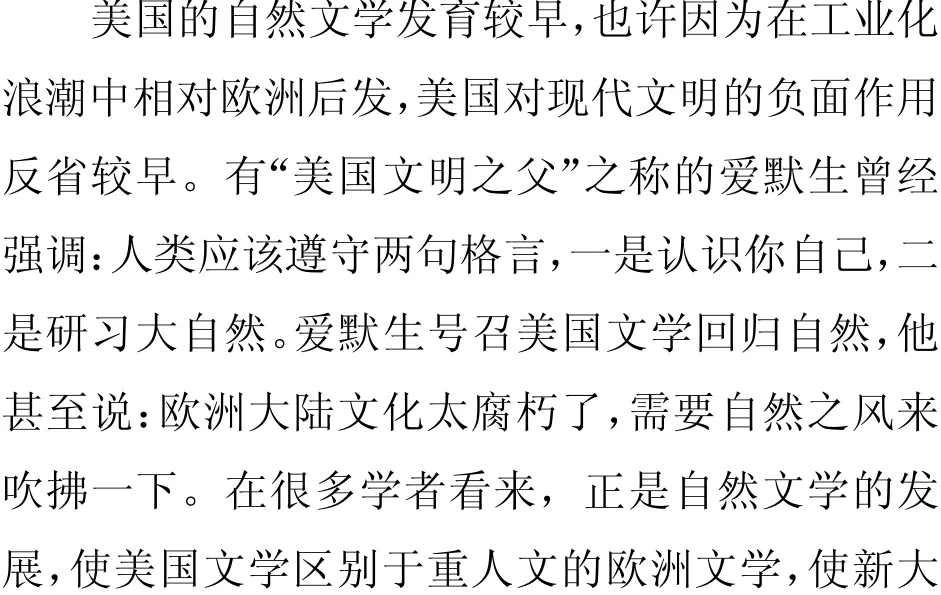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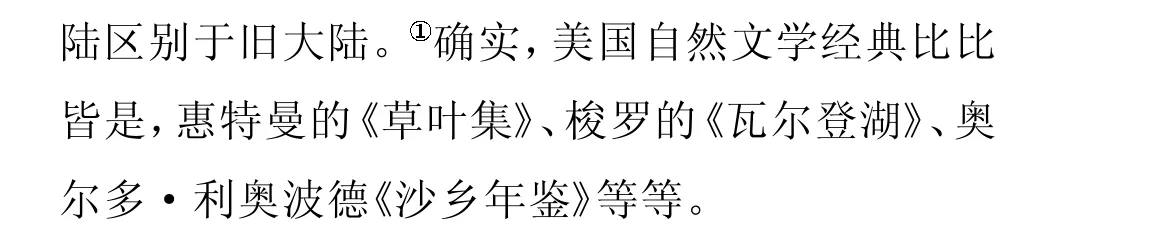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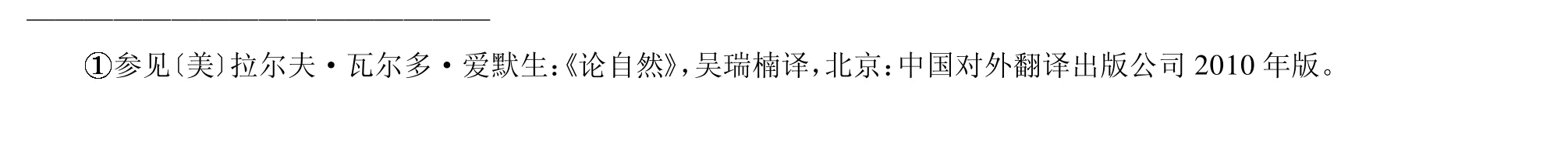
美国文学的生态问题,可以说直到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现才引起广泛注意,也可以说,自然写作从此转化为了生态文学。因为,生态危机让人们越来越有紧迫感。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纪实性散文作品《沙乡年鉴》中提出著名的“土地伦理”,他说:“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野生生物就像和风和日出日落一样,自生自灭,直到它们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消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质量的生活是否要在自然的、野生的和自由的生物身上花费钱财。我们人类对于整个生物界来说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那么能够真正看到自然界中的鹅群的机会比在电视上看更重要,有机会发现一只白头翁就像我们有权利说话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自然这个概念被生态替换,本身就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
生态危机也反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是所谓“人定胜天”的僭越观念,完全抛弃“天人合一”的优秀传统。在西方,上帝死了,人僭越上帝之位,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自然的征服者,不再尊重自然和其他物种,将它们视为可任意驱使随意采用的资源和材料。自然问题从此变成一个经济问题或科技问题,而非人类所赖以依存的家园,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安居之所。自然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中国追随西方后尘,开始加快“征服自然”的步伐,在经济高速运转的同时,生态越来越陷入深重危机。
二是所谓“文学是人学”的极端渲染,忘却了“道法自然”“万物有灵”的准则,抛弃了“境界”作为中国文学最高评判标准和最高艺术价值的传统。“文学是人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最著名的一句口号。在基督教背景下,这句话不难理解。基督教曾以关注人的堕落与救赎为借口,以来自天国的拯救为许诺,对人性强行改造和压制。文艺复兴以后,人的解放成为潮流,人性大释放,文学也就以对人性的表现和研究作为最主要的主题。但“文学是人学”的说法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就是过度将自我人权置于其他生命的权利之上。人类优先原则,导致了其他物种甚至种族的大规模灭绝。中国现代也步其后尘,五四时期强调所谓“国民性改造”,夸大中国人人性中的黑暗面和负面,导致民族普遍地自卑和自贬,并且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人性被简单地理解为“欲望”,甚至,“人性恶”被视为所谓普遍的人性,说什么“人性之恶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至文学中勾心斗角、人欲横流、尔虞我诈、比恶比丑、唯钱唯权的“厚黑学”流行,其内容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每一页都充斥人斗人。从官场、商场到情场、职场,连古典宫廷戏、现代家庭情感剧也不放过。至此,真善美被认为是虚伪,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清风明月、青山绿水隐而不见。自然从当代文学中消失隐匿了,以致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在2000 年前后逐渐出现时,仿佛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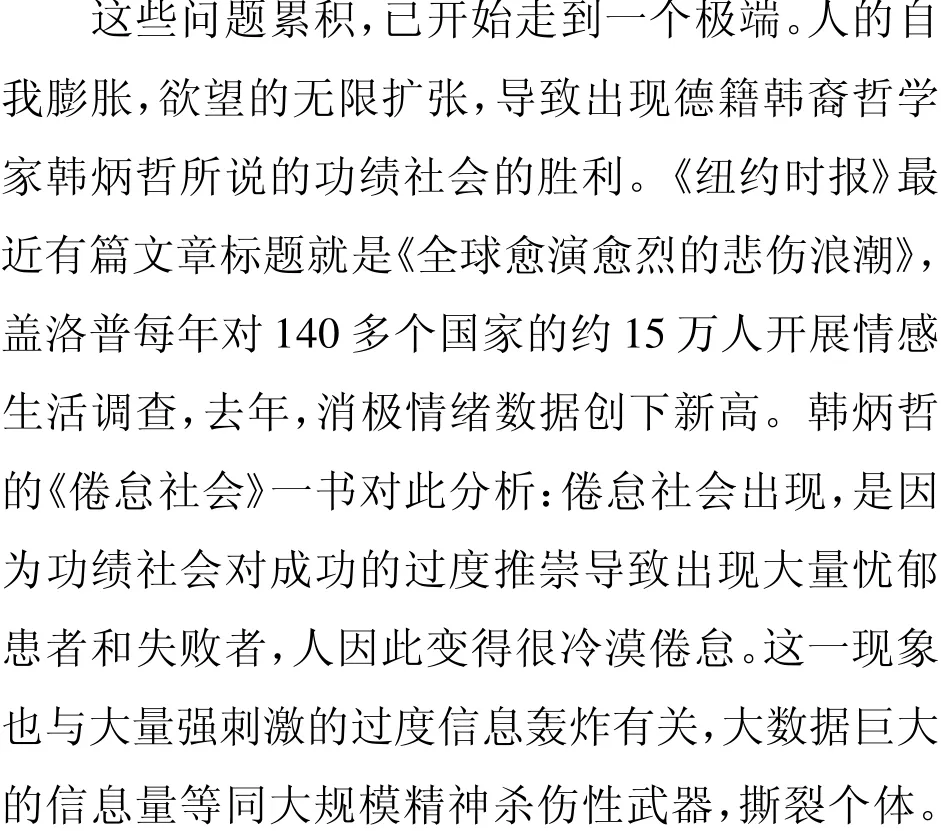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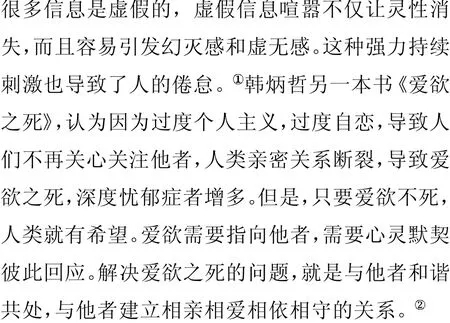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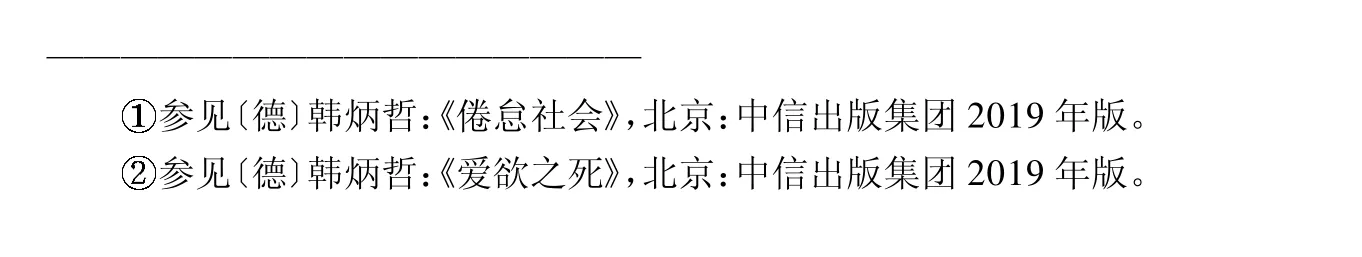
自然,无疑是最大的他者之一,是人类的尺度和镜子,也是人类最应该敬重的他者,只有心怀自然,我们才能守住家园。自然这一人类的家园,是我们唯一可以寄托心灵抚慰情感之所,这样,人类才能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
海德格尔很早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呼吁回复天地人神的循环,人只是这其中的一环,反对把人单独抽取出来,作为世界的中心和主角,凌驾于万物之上。人应该严守自己的本分和位格,在天地人神的循环中葆有敬畏之心,谦逊行事。这可以说与中国古代智慧相互呼应。在生态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律,更要强调人类集体的自觉自律,构建人与自然的万物命运共同体。
四、从古典诗歌中学习什么?
面对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诗人往往会秉持最古老的价值,而最古老的价值往往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是人类价值的根基,是新的时代价值创造转化的基因和源泉。所以,我认为,只有重新学习借鉴古代的自然观,才能最终解决现代生态问题。
在当代,秉持古老的自然观,就是一个当代生态主义的立场和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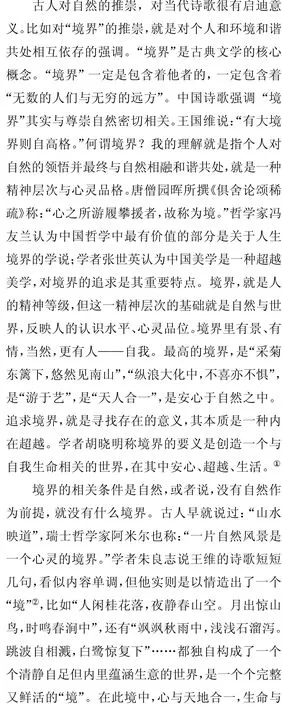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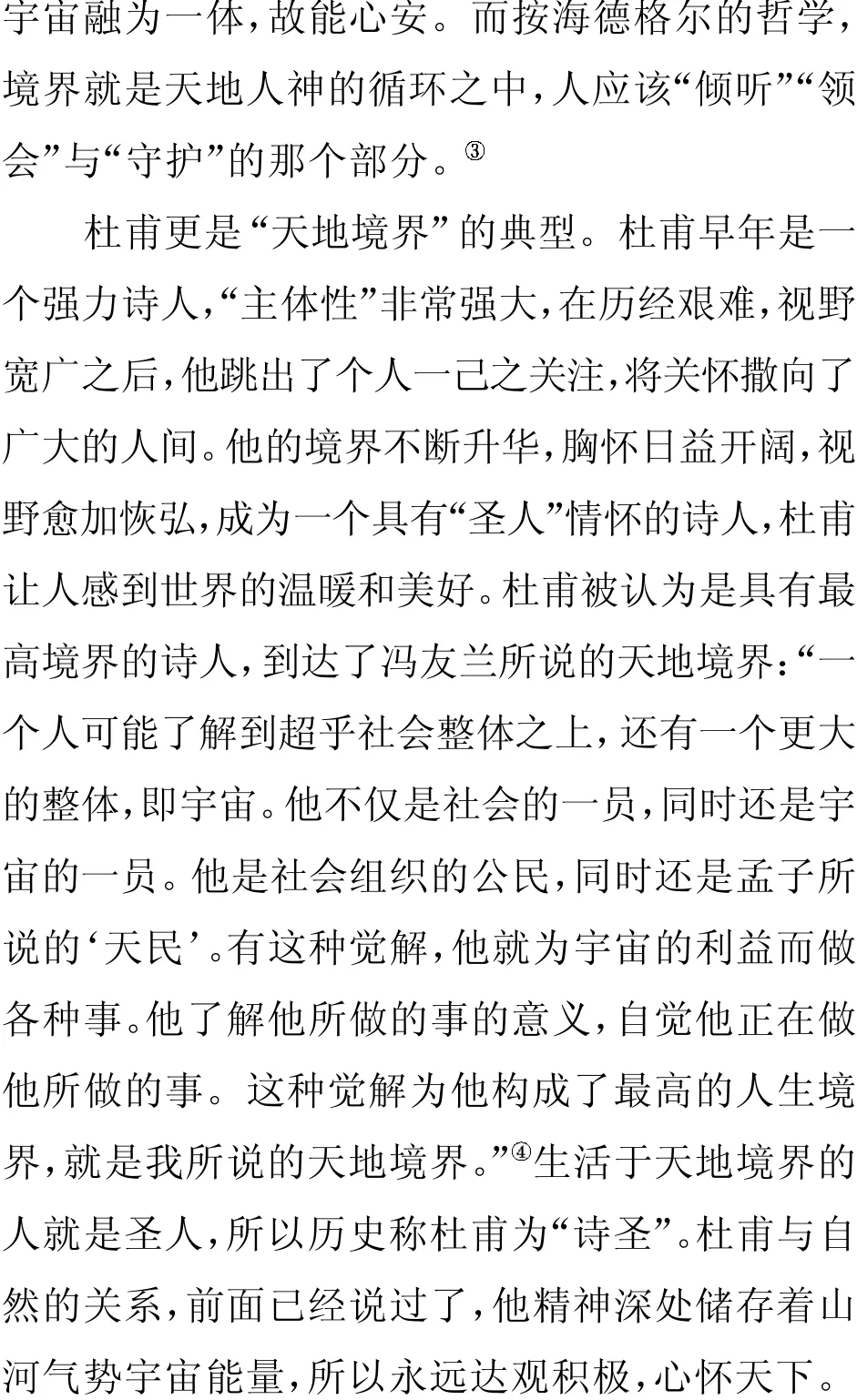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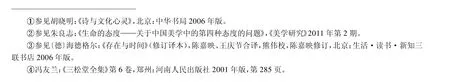
当代文学包括诗歌如果关注自然,就应该继承或者说重新恢复或者说光大创新类似关于“境界”这样的美学观念、规范和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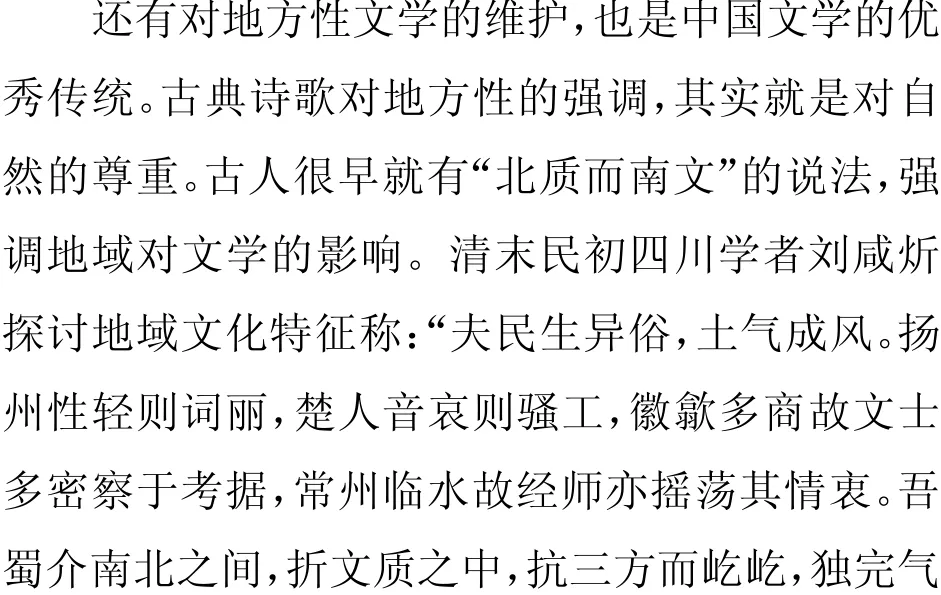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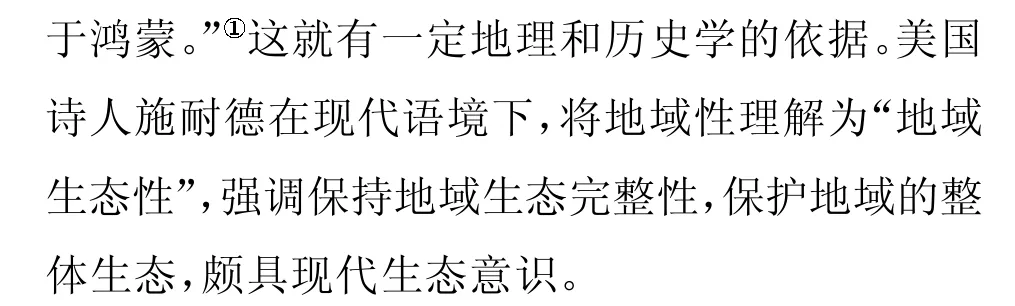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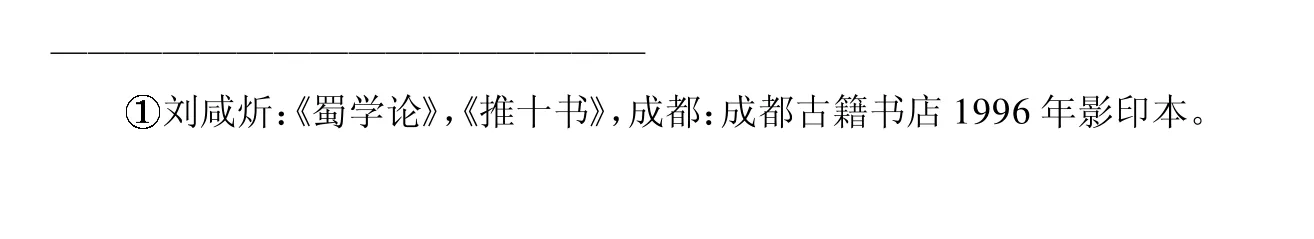
江南文化曾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很长一个时间段,江南之美曾是中国之美的代表。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自然和生活融合,理想和现实并存,诗意和人间烟火共处。江南最符合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将“道法自然”变成了现实。“道法自然”是诗意的源泉,江南文化因此被称为“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也;“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亦江南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还是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难忘江南……江南曾是自然、生活与诗意的最佳结合之地。古代的江南诗歌,就是地方性成功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