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如果说戏剧因素的穿插运用对艾伟来说相对轻车熟路,那么,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庄润生乃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学家,所以,艾伟要想更好地完成《镜中》这部长篇小说的另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建筑学知识的相对丰富。比如,关于云南丽江那所希望小学的建筑:“润生在世平的陪同下考察了白族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民居。他吃惊于白族建筑的繁复与古旧,有一种类似魏晋时期的建筑风格。润生创造性地吸取白族民居的传统元素,建筑材料最后以当地随处可见的石料为主,为了营造适度的年代感,润生购买了一些已被当地百姓废弃的石头房子,拆来被岁月风化的石料,随机分布在新的石料中间。”“润生保留了白族民居的屋顶,只是在线条上更多使用几何形状,把原本夸张的飞檐做成庄严的三角形,不过屋顶处白族的彩画被保留了。”正因为庄润生在设计建造边地的这所希望小学时很是费了一点心思,所以学校建成后,遂因其建筑特色而被誉为“全国最美希望小学”。当然,与一所希望小学的建筑相比较,小说中更为炫目的,则是曾经获得过建筑学界最重要的阿迦汗建筑奖的庄润生关于山口洋子那个道场的创造性建筑理念的构想与实践。也因此,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作家艾伟为什么会拥有如此丰富的建筑学知识。只有到这个时候去查阅作家的履历,笔者方才注意到,却原来,艾伟上大学时所学的专业就是建筑学(1988 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建系,该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如果不是科班出身,接受过系统地建筑学教育,要想如此得心应手地把丰富的建筑学知识有机地嵌入到一部长篇小说的文本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通常情况下,只要谈到理想的长篇小说,我们都或许会强调其史诗性的品格,或某种“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中国那部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红楼梦》,往往会被当作“百科全书”类长篇小说的一个杰出典范。其中建筑学、园林学、植物学、药物学、气象学、服饰学、食物学等各方面知识,简直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一般地丰富驳杂。要想完成如此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创作主体一定要尽可能地了解把握各方面的知识,要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杂学家”。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拥有足够的艺术智慧和审美创造能力的前提下,一个作家的知识储备或者说“杂学”谱系越丰富,就越是有可能创造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来。也因此,尽管肯定还谈不上具备“百科全书”式品格,但对于艾伟在长篇小说《镜中》对于诸如建筑学、戏剧等方面知识的积极征用,我们最起码应该从这个向度上做出相应的理解和判断。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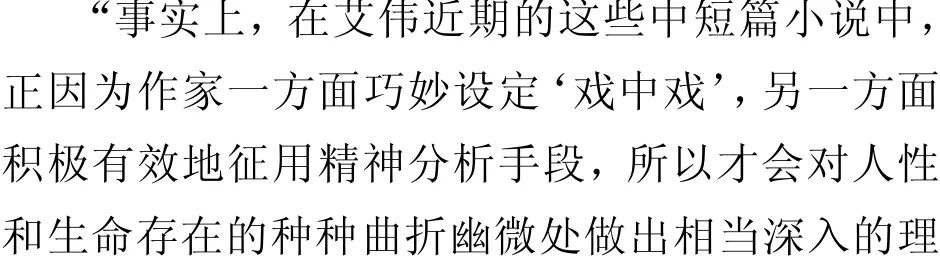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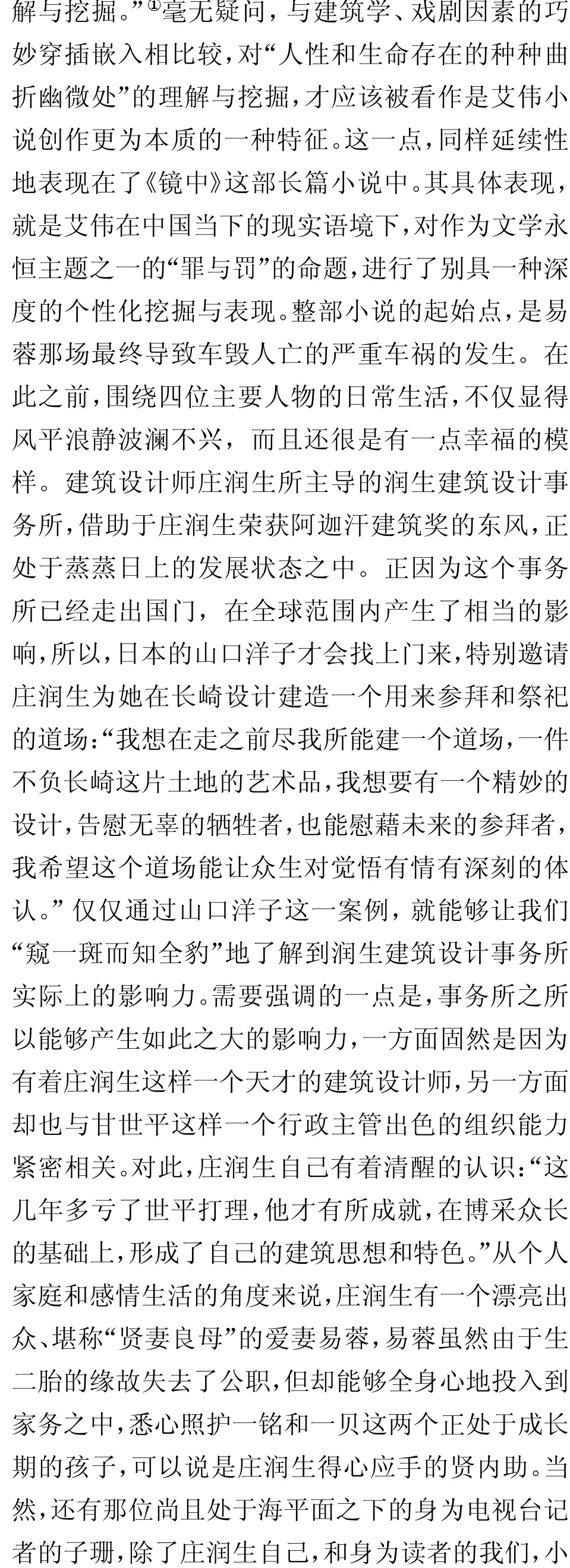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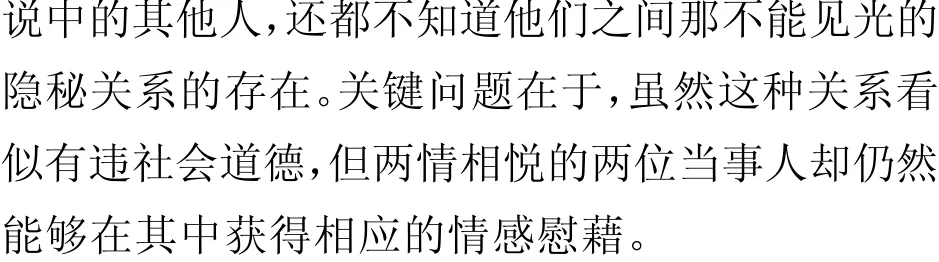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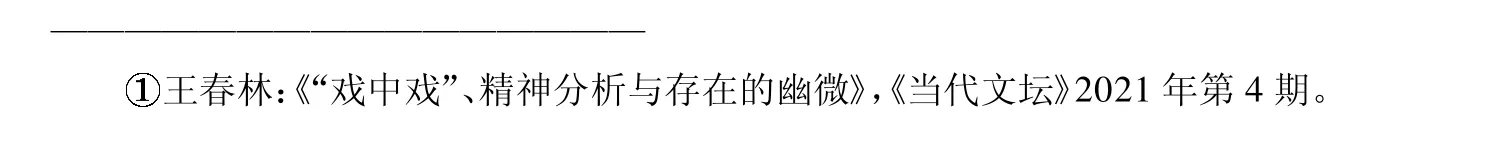
但所有这一切看似幸福无比的平静生活,却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而发生了倾斜,并被彻底颠覆。一向以善于挖掘勘探人性幽微而著称的作家艾伟,正是凭借着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在彻底撕开生活那温情脉脉的表象之后,围绕“罪与罚”这一命题展开了很多时候甚至会令人窒息的艺术书写。首先被推上道德和人性审判台的,正是那位天才的建筑设计师庄润生。庄润生之所以会因为这场车祸的发生而追悔自责不已,乃因为车祸发生的时候,他正在西湖边那个名叫刘庄的高级酒店里与情人子珊幽会,正处于两情缱绻的温柔乡里。依照庄润生的习惯,每一次和子珊幽会的时候,都会把手机关掉。这一次,当易蓉第一时间向他打求救电话的时候,所遭遇的情况正是关机。尽管说即使庄润生开着机第一时间接到了易蓉的电话,他也已经无力回天,根本不可能改变车祸已然发生、悲剧已然酿成的残酷事实,但他却还是认为车祸的发生与自己有关,痛感自己必须承担相应的罪责。对于这一点,身为当事人的子珊早已心知肚明:“凭子珊对润生的了解,负罪感正折磨着他。子珊看到润生虽然强忍着情感,还是泛出泪光,子珊也跟着流下泪水。子珊从润生的神情中知道他没说出的话。润生已做出了选择。这也是子珊这几天反复在心里盘旋的。发生这个事件后,她意识到她和他难以继续了,障碍是如此确定无疑,仿佛一座大山横亘在他和她之间。是的,他们的关系不再像从前那样单纯了,从前中间只有易蓉,他们可以假装忘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润生儿女的死亡令他们的关系沉重到难以承受。”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男人,庄润生虽然因为车祸的发生,因为一双儿女的惨死而主动断绝了和子珊的情人关系,但却仍然希望在最后时刻满足子珊曾经的愿望,那就是,想方设法把她送到纽约去学习她热爱的动漫电影编导专业。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庄润生自己的做贼心虚,所以,哪怕是躺在病床上的易蓉无意间的一个目光,都会让他心生愧疚:“易蓉直愣愣地看着他,润生觉得这目光穿透了他,或正在解剖着他。她知道了一切了吗?她出事时他关机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他怀疑她的目光里不仅仅是哀伤,还有对他的审判。”然而,也正所谓隔墙有耳,庄润生原以为自己和子珊的事情做得非常隐秘,没想到,长期伴随在他身边的甘世平却早已对这一切都明察秋毫。也因此,为了能够帮助润生早一点从痛苦和愧疚中有所摆脱,甘世平在经过了一番犹豫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把易蓉车祸发生时处于醉驾状态的残酷真相告诉润生:“或许有一件事可以拯救润生,可以减缓润生的负疚感,就是告诉润生真相。世平昨晚想了整整一宿,纠结着是不是要把车祸当天的一切告诉润生。他不能让润生沉溺于舔舐自己的伤口而不能自拔。”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出事那天,驾车的易蓉处于醉酒状态,血液里的酒精浓度竟然高达120 毫克,竟然达到了酗酒的程度。不出甘世平所料,在地下室不无惊讶地找到了易蓉储藏着的各种各样的酒,确证她的确有着饮酒恶习之后,庄润生的愧疚心理果然暂时有所缓解:“那一刻,强烈的愤怒从润生心中涌出,消解了出事以来充斥他心中的愧疚。原来如此,原来是易蓉杀死了一铭和一贝。”问题在于,尽管“对易蓉的怨怼和某种程度上的仇恨缓释了润生的愧疚感,好像就此他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生活下去的借口。”但虽然如此,一个无法回避的情况却仍然是,由于包括后来自杀的易蓉在内的一家三口亲人的死亡这一事实,一直会时不时地袭击庄润生,令他生出某种难以言说的生存虚无感。
实际的情况是,一直到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易蓉到底为什么会在酗酒之后驾车,而且车上明明还载着一铭和一贝兄妹俩。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庄润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自己和子珊经常幽会的那个刘庄高级酒店,其实到处都暗设有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可以随时随地把他和子珊在酒店里的活动情形记录下来。关键更在于,正是在查看监控屏幕的过程中,庄润生方才得以进一步发现,其实易蓉和两个孩子早就知道了他和子珊之间的隐秘私情:“原来如此,那天他和子珊约会时,易蓉带着孩子们一直跟踪着他。易蓉一定亲眼看到他挽着子珊进入刘庄的某个房间。孩子们也都看到了。”到这个时候,曾经一度有所解脱的庄润生再次确认,自己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一切明明白白,最终的源头在他这儿。易蓉知道了他和子珊的事。他想象易蓉见到他出轨后的心情。也许易蓉酗酒就是在怀疑他出轨之后。”依循如此一种逻辑,在庄润生的想象中:“她遭受到巨大的打击,失望和愤怒让她失控,她飞快地开车,驶向钱塘江大桥,她失去了判断力,汽车不幸撞到了钱塘江大桥北堍的铁围栏上。”一场车毁人亡的大悲剧就此而彻底酿成,而悲剧的根本源头却在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庄润生这里:“至此润生明白他是所有不幸的源头。他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饶恕。”从这个时候开始,“罪孽深重,不可饶恕”这八个字就如同一座巨型建筑(请注意,正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既然身为建筑设计师,即使在被愧疚感将要压垮的时候,想到的比喻,也仍然与建筑紧密相关)“在不断膨胀,压迫着他”,直至“让他喘不过气来。”
如同庄润生一样被某种沉重的罪恶感强势缠绕的,是车祸的直接酿成者易蓉:“出事之后,除了亲爱的儿子一铭和女儿一贝,她想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脸。一铭和一贝的离去已把她打入地狱,如同她对润生说的,是她亲手杀死了他们,她是个刽子手。她并没有对润生说出‘刽子手’三个字,但在心里她这样对润生承认了无数遍。也许她只配拥有着骷髅一般的鬼脸,像鬼一样地在人间生活,不配再成为一个人。她还想,如果她死去,也只配下地狱。”虽然处于某种酗酒后的失控状态,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就那么悲惨地死去,即使在内心里对丈夫庄润生有再大的仇恨,身为人母的易蓉,也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自己。但其实,要想理解易蓉这样一位庄润生根本就不了解的现代女性,我们就不能不追溯分析一下她和身为昆曲名伶的养母之间的那一段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因为养母不仅一直都是单身,而且总是不断地换男人,所以,易蓉自打记事起听到的,就是东边房间里传来的母亲和别的男人的做爱声与打闹声:“这些声音构成一种奇怪而垂死的气息,充斥在这幢宅子里,而易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成长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由于长大后的易蓉出落成了一个大美人,那些围绕在养母身边的男人们,便会在觊觎她的美色的同时,对她进行百般挑逗。而敏感的养母却又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一切都迁怒于易蓉。时间一长,一种报复之心的酿成也就难以避免:“也许是出于嫉妒,也许是一种潜藏的道德感作祟,她早已对母亲不知餍足地贪恋与男人的鱼水之欢看不惯了。”正是在如此一种心理的主导下,易蓉选择了一个母亲最喜欢的导演下手,和他一起上了床:“这是她的第一次。她本来只想报复一下母亲,就此收手。可是青春的情欲让她欲罢不能,深陷其中。她知道自己其实并不爱他,但还是自愿委身于他。她因此对自己充满了鄙视,觉得自己甚至比母亲还不堪。”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易蓉明明知道这个导演是一个令人唾弃的渣男,只要有剧团请他拍戏,他必要睡一个女演员。所以,易蓉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易蓉因此对自己的轻佻感到恶心。她的内心里充满了罪恶感,对那个男人的厌恶日增,曾动过念头杀掉他。”不可思议的一点是,鬼迷心窍的易蓉不但没有将杀人的想法付诸实践,而且还鬼使神差更加频繁地与导演厮混在一起,直到后来被母亲发现。母亲和易蓉的关系本来就不够好,这件事更是雪上加霜地使她们的关系更加糟糕。
在与庄润生结识后,面对着来自于他近乎于狂热的追求,早已明确认识到“润生并非自己的菜”的易蓉,之所以最终决定嫁给他,其实和她急于摆脱养母这一隐在的动机紧密相关:“他们还是在一起了。易蓉嫁给润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出于对润生的爱,她只是想逃离养母,逃离这幢旧宅,而润生刚好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由此可见,庄润生和易蓉那看似水乳交融的夫妻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庄润生狂热地喜欢着易蓉,而易蓉却并非如此。只不过,对于易蓉真实的心理状态,庄润生并不知情而已。虽然说在后来的夫妻生活中,易蓉也曾经努力地想要让自己爱上润生,但努力的结果却并不理想。既如此,不愿意伤害润生的易蓉,就只能够如同演员一样竭尽可能地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她因此扮演着润生想象中的那个女性形象:勤快、顾家、照顾孩子,热爱生活,更重要的是保持一种类似‘母仪天下’的端庄,有时易蓉恍惚时会把润生当成自己孩子中的一个。”也因此,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就是,如果说易蓉对庄润生有爱,那这爱也并非男女两性之爱,而是一种类似于母爱的亲情(到后来,庄润生之所以会背叛易蓉,和子珊走到一起,其实也是因为他直觉到易蓉对自己的情感存在某种问题)。当然,因为一铭和一贝的死亡所导致的罪恶感之外,致使易蓉最终决绝地走向死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自己的严重被毁容。在相关的叙事话语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易蓉是一个对残疾有着强烈抵触心理的女性。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如同易蓉这样连别人的残疾都无法面对的女性,你又怎么可能指望她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自己那一张被严重毁容后可谓是满目疮痍的脸呢?
同样被某种罪恶感困扰的人物,还有那位后来远走异国他乡的子珊。子珊之所以会有罪恶感生出,与她身为庄润生的情人这一身份紧密相关:“两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初到纽约的日子,子珊情绪坏到极点。事实很清楚,易蓉出事同她有关,在世俗的眼里是她以不光彩的角色插足到润生的生活中,她逃不了罪责。”但在强调子珊那种连带的负罪感的同时,我们却更需要在这里检讨一下她和庄润生那多少有点不对等的情人关系。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如果说在庄润生和易蓉的关系中庄润生是狂热的追求者,那么,到了他和子珊的关系中,子珊反而成为了狂热的追求者。这种情感模式,早在他们的情人关系刚刚开始时就已经被奠定。虽然说由于在采访的过程中暗中爱上了庄润生,但她那一时冲动之下发给他的内容为“庄润生,我爱上你了”的短信,却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应。然而,半年时间过去之后的某一天,润生却突然找到了她:“那天他们几乎迅速在一起了。做爱后,润生还哭泣了。”原因到底何在呢?“后来她对润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想起那天他脸色苍白眼神落寞的样子,意识到润生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她问过他,为何突然想起来找她。他不响。为何他认定她半年后还会继续想念他。他不响。为何他认定她一定会和他上床。他还是不响。”实际的情况是,虽然叙述者并未做出明确的交代,但在前面的相关情节中早已有所暗示。那就是,在生下一贝之后,易蓉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彻底的性冷淡。以至于,庄润生曾经在情急之下,甚至“几乎是强暴了易蓉”:“他感到易蓉在他的身下挣扎,她在拼命地推他,打他,踢他。他听到易蓉的喊声,他听到易蓉在说:‘你同他们一样,就是禽兽。’他根本就不顾,进入了易蓉,并迅速地结束。”也正是在那一次,庄润生被儿子一铭在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正因为在易蓉这里严重受挫,所以,润生才会以那样一种“脸色苍白眼神落寞的样子”突然出现在子珊面前。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他们两人的情人关系中,庄润生就成为了手握主动权的掌控者。即使在庄润生已经明确宣布和子珊中断关系之后,他仍然可以随时召唤子珊,并不管不顾地强行和她上床。无论如何,庄润生的这种态度都会在子珊的内心深处造成难以抚平的严重精神创伤:“她已不止一次感到他的冷漠,在她与他的关系里,他牢牢控制着主导权,而她却像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应召女郎。她爱他,他却总是辜负她的爱。也许到了地球的这一边,距离可以让她忘掉他,疗愈她的伤痛。”但即使如此,即使子珊移民美国后身边已经有了码农舍尔曼,她却依然无法忘怀庄润生,不仅时常思念,而且还总是要打听了解他的行踪。事实上,也正是凭借着她的这样一种似乎永无休止的关切,也才有了后来那简直带有传奇色彩的不惜万里迢迢的营救行为。因属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如上所述,庄润生、易蓉、子珊他们三位都被某种强烈的罪恶感所缠绕,那么,甘世平呢?他难道真的可以置身于事外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但要想剖析甘世平的罪恶感,话题却还得从庄润生的自我惩罚或者说自我救赎开始说起。通过回放的视频了解到易蓉对自己的出轨早已心知肚明后,庄润生坚决认定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然后,就是一场大病合乎逻辑的发生:“自从认定自己是害死易蓉一铭一贝的凶手后,润生大病了一场。不是那种非常突然的病,而是一点一滴生长、凭润生理智无法意识到和控制的病。”“他觉得脑子已不受他控制,悲伤和无助会突然袭击他,置他于崩溃的边缘。”正是在如此一种境况下,润生开始尝试着喝酒,并最终失控后成为酒精依赖的严重酗酒者。与酗酒同时发生的,更有唯庄润生自己才能明显感觉到的某种自我精神分裂状况的日益加重:“润生知道自己乖张。在另一个维度,有一个正常的、理性的自己在肉身的上空看着他,并对他的行为做出判断。那个理性的自己想纠正他,让他归于日常和人间。他也想听从那个自己发出的命令,可他做不到。肉身内部也有一个指令,那个混乱的内部发出一些让他难以把控的沮丧和软弱的情绪,同时发出关于意义的追问,他因此被弄得精疲力竭。润生感到这两个指令一直处于战争之中,胜负难定。”所有的这一切症候,一场大病,开始酗酒,严重的自我精神分裂,其根源都在于庄润生坚决认定自己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责任者。其中某种自我惩罚的性质,昭然若揭。为了让润生早日走出困境,甘世平曾经设法把他送到飞来寺禅院里去静修。正是在静修的过程中,一贯只是相信科学的润生开始认识到某种超越于个人生存之上的强大意志,也即所谓命运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指向一种更强大的意志吗?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产物吗?如果没有那个意志,偶然会构成如此和谐如此庞大的秩序吗?”尽管说静修也没有从根本上让润生从那种强烈的负罪感中摆脱出来,但他试图以建造希望小学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救赎的念头,最初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萌生。两所希望小学,一所建在安徽老家,被命名为“一铭小学”,另一所建在西南边陲的云南丽江,被命名为“一贝小学”。因为润生曾经发愿每年都要到“一贝小学”上一堂课,所以,他便在2015 年初的时候,来到了位于云南丽江的这个白族小山村。在小山村,内心仍然被罪恶感压迫的润生再一次回想起了车祸刚刚发生时山口洋子给他讲过的一番话:“诚如两年前山口洋子所说的,当悲伤醒来,那种撕心裂肺的磨难才开始,无助、悲伤、愤怒、孤寂以及仇恨将成为一个无底洞,不但如影随形,还会发酵和增长。他像一个溺水者,被灭顶的巨浪抛入深渊之中。这两年,润生老是想起山口洋子,山口洋子确实是她的一面镜子,照见了他这几年的感受,其中的解脱之道也和山口洋子几乎类似。”既然提到了镜子,那么,在这里,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艾伟的这部作品为什么要被命名为“镜中”。首先应该注意到,作家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的确曾经多次提及镜子。比如,“山口洋子的家庭悲剧像是润生的一面镜子。这个启示吓了他一跳。”比如,“司机就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她再次确认自己有多么可怕。”比如,“他看见对面的墙成了巨大的镜子。镜子里的事物一直在变幻。时间好像停止了。他的脑子无法停下来,如果可以,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自己的脑子停止转动,哪怕一秒钟。镜子里的事物是他看到的还是脑子里浮现的?”再比如:“博尔赫斯说,镜子是为了让人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个反影,是个虚无。因此,镜子才那么使人害怕。你看那躺着的神志不清的人,长时间滴水不进的人,就是一个虚无之物,哪怕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打在他身上。”还有就是,“当子珊和润生在一起时,她有一种骄傲感,润生像一面镜子一样矗立在子珊面前,从这面镜子里,子珊照见了完美的自我,犹如一位优雅公主一样的自我。”以及,“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浴室氤氲,他侧脸看镜中的自己,镜子沾满了水汽,他的脸显得十分破碎。”综合以上各种描写情形,对艾伟的“镜中”语义,大约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其一,是镜子的本义,人可以在镜子看到自己的形象,可以借助于镜子反观自我。其二,人物和人物之间彼此互为镜像,以他人为镜,相互映照折射。其三,正如同小说中所引述的博尔赫斯的那句名言一样,也可以借助于镜子做一种形而上的人生哲学思考。其四,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镜像,包括艾伟在内的作家能够借此而关注表现人间百态世间万物。
二
话题再回到庄润生的西南边陲之行。润生这一次到云南丽江来,原本只不过是想要履行诺言,给希望小学的孩子们讲一堂课,没想到的是,因为无意间看到一则由于缅甸的政府军和果敢同盟军之间爆发战争,大量缅甸难民涌入中国的新闻,他的命运却会就此而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看到这一条新闻之后,润生便顿然生出了想要去边境的难民营做一名志愿者的强烈意愿。但谁知等到他们的汽车快要抵达边境时,却被武警的关卡拦阻。“如果不是这时候穆少华出现,润生可能没办法到边境,只得回去,那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穆少华是一个退役的特种兵,用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他之所以要携带一架拥有两千四百万像素的莱卡高级相机来到边境,主要是因为退伍后被分配到一个街道办做主任,成天面对的都是些婆婆妈妈的琐碎事情。在电视上看到这边有难民营,就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他的行为动机不是出于善念,而是想要亲眼看一看战争的模样。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目的地却是一致的。就这样,润生携同穆少华一起来到了边境小镇的难民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志愿者。或许是因为润生的一系列行动都不合常规,所以,穆少华在见面不久的时候,就曾经询问他是不是做过什么亏心事,但润生给出的回答却是直截了当的:“你说对了,我是个罪人,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这样的问答所再一次凸显出的,依然是庄润生貌似怪异行为背后的自惩与自我救赎的根本动因。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彭少男的男孩不仅偷走了穆少华的莱卡高级相机,而且还把它卖给了果敢同盟军的一名军官,如果不是润生和穆少华结伴一起去找那位军官索要相机时在归途上迷路,他们就不仅不会被缅甸政府军抓获,而且更不会被最终投放到位于缅北的一所监狱里。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被关押起来的润生灵机一动,以短信的方式通知甘世平把一本装订好的被命名为“致世间的遗书”的动画稿寄给远在美国纽约的子珊,如果不是子珊由此而判断出润生肯定置身于某种困境之中的同时,巧合地在BBC制作的一期事关缅北监狱的纪录片中敏感地发现了润生的一个特写镜头,如果不是子珊到纽约后结识了一个名叫韩于琪的神通广大的老人,如果不是这位韩于琪老人在关键时刻慨然出手相助,那么,也就不会有子珊不惜万里迢迢的那一次缅北之行,当然,身陷囹圄的庄润生也就不会获救出狱。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不是润生被救出后,不仅一时失忆,而且还无意间激发出了子珊的恨意:“毫无疑问,这个男人一直深爱着易蓉,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子珊算什么呢?子珊一直以来深藏着的对易蓉的恨意爆发了。她突然想砸烂一切。”就这样,“在愤懑和失控情绪的支配下,子珊对润生道出了真相,来自易蓉在邮件里说出的真相。”
更进一步地,也正是由易蓉在自杀前的一刻专门写给子珊的这封邮件,艾伟的笔锋一转,转向了对似乎一直置身于事外的甘世平罪恶感的揭示与表现。却原来,在看似由易蓉一手导致的那场车毁人亡的车祸事件中,同样逃脱不了罪责的,也还有早就跟易蓉背着润生有了私情的甘世平。在易蓉之前,世平曾经有过一次类似于偷情一般的初恋:“一场失败的初恋给带给世平难以平复的创伤。这创伤持续了好几年。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恨过她,他相信她爱过他,并且他无法忘记她美好的身体。”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易蓉和世平之间,最早采取主动行为的,是易蓉。那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借居于润生家的世平竟然发现易蓉躺在自己的床上:“回头一看,吓了一跳,易蓉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身上什么也没穿,几乎赤身裸体。不过她看上去神色安详,正在熟睡中。”不敢造次的世平,吓得慌忙逃走。虽然如此,但易蓉那一丝不挂的身体却从此之后常驻在世平的脑子里无法被清除。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他在床边再一次看到易蓉的时候:“然后,他睁开眼,是半夜,室内黑暗,阁楼的天窗投入一缕月光,使得屋内的陈设隐约可见。他看到易蓉站在那儿,身上什么也没穿。他以为是梦的一部分,后来意识到这不是梦,真的是易蓉。”正是在这两件事情相继发生后,世平下定决心从润生家里搬了出来。但尽管如此,该发生的却还是终究要发生。面对着来自于易蓉的强劲攻势,脑子里早就无法清除易蓉身体形象的甘世平最终全面失守。也只有在面对世平的时候,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易蓉,才坦承了自己对润生所持有的基本情感状态:“我没爱过润生。”“我和润生结婚时没爱过润生,当然我不讨厌润生,润生迷恋我,让我很享受,但我知道对我来说那不是爱。我嫁给润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逃离这儿(指养母留给易蓉的位于运河边的老宅)。润生是个好人,心地善良,至今还是一个少年,可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事实上,也正是在与易蓉的私情发生后,世平才对易蓉有了真正的认识:“他听到她在叫他的名字,他和她已来到西边装着彩色玻璃的房间,在她的床上,世平觉得她口中的名字听起来像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他,是另一个世平。而另一个世平正在和易蓉翻云覆雨,而易蓉也是另一个易蓉。这倒是一个事实,刚才易蓉的故事彻底改变了世平原来对易蓉的印象。”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去,世平“承认自己爱上了易蓉,他相信对易蓉的爱比他认为的还要早。”但其实,易蓉的情况也差不多,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她曾试图抗拒这种情感的诱惑,那段日子,她不停地和润生做爱,然而不争气的是脑子里出现的全是世平”。
关键问题在于,虽然说易蓉和世平他们俩的这种感情完全称得上是真正的两情相悦,但毕竟易蓉是润生的妻子,而世平也是润生的好兄弟。无论如何,他们俩的私情都既会对润生造成伤害,同时也会让他们自己陷入到某种负疚感之中。请注意他们俩的这样一种对话:“易蓉变得温柔,说:‘世平,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知道我爱你,但你知道的,润生需要我,他已是我的亲人,我不想伤害他。’/‘我们这样难道不是在伤害他?’世平说。 /‘他不知道就不是伤害,不是吗?’”由此可见,在世平这里,早已明显认识到他和易蓉的偷情,是对好兄弟润生的一种伤害。然后是这样一种对世平复杂心理的描述:“世平自己都感到不可理解,他对易蓉抱有如此强烈的执念和热情,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寻找某种幻觉的赴火的飞蛾。这世上有些事没有道理可讲,道理是一回事,但身体比道理更顽固。他和易蓉的约会成了世平情感生活的全部,那些曾经折磨着他的对润生的内疚感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日渐淡漠。好像他和她天然如此。”所谓内疚感的日渐淡漠,所充分说明的,就是在世平的内心深处,曾经被这种内疚感严重折磨。要害处在于,一方面,即使是如同世平和易蓉这样的两情相悦者到后来竟然也都会变得千疮百孔:“在我和润生的婚姻期间,我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我相信他也爱我,我们在一起时有过美好的时光,我感激我的生命里有他陪伴。但像所有相亲相爱的有情人最终都会走到激情耗完的时刻——但愿你和润生不会——我和他到头来也是千疮百孔。”另一方面,即使是身为当事人的世平也只有通过易蓉最后时刻留下的那封邮件才了解到,却原来,一铭和一贝竟然都不是润生的孩子。既然不是润生的,那肯定就只能是世平的。也因此,在倍感震惊的同时,甘世平内心里生出的便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罪恶感:“他洗了一把脸。当他把温热的毛巾敷到脸上时,他的泪水夺眶而出。然后他蒙着脸哭泣起来。”“在和易蓉相处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们老是吵架。他记起易蓉有一次骂他,你这个伪君子,夺走了润生的一切,总有一天,你会被审判。”在当时,因为是在吵架时随口说出的话语,所以世平其实并没有在意,但只有在读到由子珊转发给自己的易蓉邮件之后,甘世平方才意识到时候到了:“他那时候把这话当成易蓉吵架时随口而出的气话,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现在他知道审判的时刻到了。”但其实,早在车祸刚刚发生的时候,出于某种愧疚心理的拷问与煎熬,世平就想到过应该离开备受伤害的润生:“他想过离开润生。他已无法面对润生。然而即便在出事的一年之后,润生还没有完全摆脱伤痛,理智告诉世平,此时此刻他不能放弃对润生的责任,他得照顾他,他还得想办法使事务所运行下去。如果他此刻离开,事务所一定会关门大吉。他不能丢下一个烂摊子撒手不管,他不是个不负责任的人。”然而,等到他读到易蓉的邮件之后,内心里更加充满罪恶感的甘世平终于意识到,自己接受命运处罚并实现自我救赎的时候到了。
如果说易蓉的自我救赎方式是服药自杀,子珊的自我救赎方式是前往缅北监狱救出庄润生,并帮助他完成了那个富有深意的动画稿制作,庄润生的自我救赎方式是建造两所希望小学,同时前往边境的难民营去做志愿者,那么,甘世平的自我救赎方式,就是不仅曾经两度自觉领死,而且更是在大火中冒险救出了润生。第一次,是夏天的时候,他们俩一起到青岛去潜水:“润生因为脚抽筋,用手死死缠住世平的脖子,他曾怀疑过润生早已洞察了一切,以此为借口想要杀了他……现在看来,那一次润生是想在海底掐死他。”第二次,是在他们联袂抵达日本之后,木村先生带着他们去打猎:“正疑惑时,世平觉得后脑勺一阵灼热,他突然意识到此刻润生正拿着猎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他没有转头看一眼润生,他相信自己的感觉。”“他断定润生已经知道一切真相。他没有任何慌乱,闭着眼睛准备迎接润生对他致命的一击。他觉得他是应得的,他松了一口气,也许从此以后一切可以得到解脱。”关键在于,庄润生之所以先后两次放弃自己的复仇计划,都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感受到了某道光的存在:“他无法放下仇恨,但他实在没法对世平下手。他想起那道光,那是一个启示吗?是在这一刻来提醒他让他放过世平从而得以拯救自己吗?”然而,就在庄润生不仅先后两次放弃复仇的计划,并且在内心里其实已经原谅了甘世平的情况下,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那就是,由于地震晃动而把润生点着的蜡烛推倒并引起严重的火灾,但润生却由于食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之后怎么都醒不来。值此关键时刻,正是世平不管不顾地冒着生命危险冲到火势熊熊的房屋里,把仍然处于沉睡状态的润生硬是给救了出来。而他自己,却因为伤势过重的缘故,到最后自己拔掉了注射器而死亡。最终以一命还一命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精神救赎。
三
阅读《镜中》,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除了艾伟一如既往通过精神剖视的方式挖掘表现各色人物心理幽微的艺术特点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对象征手法的巧妙征用。具体来说,这一特色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由庄润生最早起意创作而由子珊最终补充完成的那个动画稿。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修改后的最后一幕:“最后一幕是在天堂,那只蚂蚁站在一个四面佛像前(四面佛的形象显然来自吴哥窟),润生很快认出上面形象所指,正面的佛像一半是易蓉的脸,一半是子珊的脸。背面的佛则模糊不清。另两边则是一铭和一贝的形象。当然都是写意,现实中他们的脸没有佛像那么饱满正大。那只蚂蚁从四面佛像中的一个小洞爬了进去。一会儿,在四面佛的背面,那个面目模糊的佛像变成一半是润生一半面目不清的形象。剧终。”子珊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那个面目不清的形象,其实应该是甘世平。与此相对应的一点是,庄润生最终把动画稿的题目由《致世间的遗书》修改为《致人间的情书》。从“遗书”到“情书”,凸显出的正是人类一种被救赎的希望。其二,则是在经历了一番真正的人生大磨难之后,庄润生为山口洋子所设计的那个将要建造在海面上的道场:“润生开始在纸上绘制草图。整个道场将建于海水之中,通向佛殿的道路将由清水混凝土和玻璃构筑成一个卐字形的通道,象征人生的迷宫。在这个通道里要创造出原设计中生命各个阶段的感受:一个灰暗的童年,一个野心的青年,一个至暗时刻的危机,以及突然的解脱。”这里人生的四个阶段,毫无疑问来自于庄润生自己真切的人生体验。灰暗的童年,指的是他因为父亲的出轨所导致的不幸的童年生活。野心的青年,指的是他在建筑事业上以获得阿迦汗建筑奖为标志的巨大成功。至暗时刻的危机,指的是那场突如其来的重大车祸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精神危机。突然的解脱,指的是人生顿悟后的精神救赎。这一建筑的关键处还在于有海水因素的充分介入:“海水会让光线变得更为绚烂,更为令人晕眩。更重要的是海水将使光线变得有重量感,可以以此象征人生难以承受的重荷。这些带着‘重量’的光线将带给朝拜者既宽阔又逼仄、既自由又压抑的感觉。”这其中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人和建筑两方面因素的彼此深度交融:“但这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人,人和建筑是一体的,上天让他体验到人间的悲苦,努力让他学会慈悲,他意识到无论是他还是世平还是芸芸众生,谁在人间没有悲苦?”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到这个时候,庄润生终于实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精神超越。所谓“谁在人间没有悲苦”这一句,更是在罪的意义上做了普泛化的推断。他的如此一种推断,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圣经》中耶稣指着那犯了奸淫罪的妇人说,谁如果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打她这一重要的场面。也正是在以上这些建筑思想支撑的基础上,在受到《致人间的情书》的影响之后,庄润生打算在长崎的道场里摆放一尊四面佛像:“他想象,未来,在寺院建好后,人们穿过海水底下或黑暗或色彩斑驳的隧道后,突然站在光之下,看到这样一尊既有天真相,又有温柔相,又有恐怖相,又有自在相,一尊既人间又圣洁,既复杂又单纯的佛像,人们一定会像他此刻的心情,重生或涅槃了一样。”实情也的确如此,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矛盾冲突的罪恶的人间,可以说人人皆有罪孽。怎么办呢?唯一可行的,大概也就是如同庄润生们一样,在意识到罪恶存在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忏悔,最终获得一种精神的救赎可能,获得人生的重生和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