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 翻译系/翻译研究中心,香港999077)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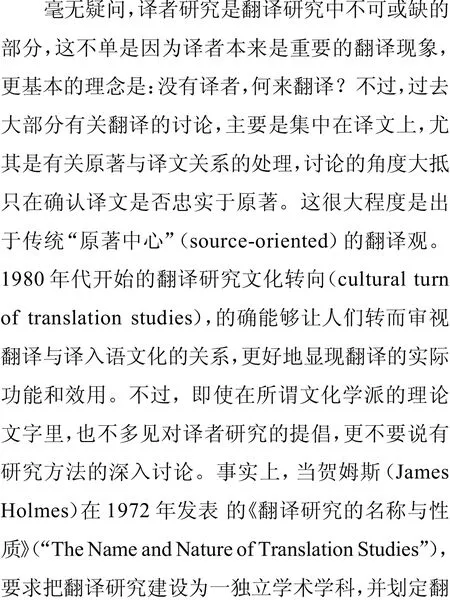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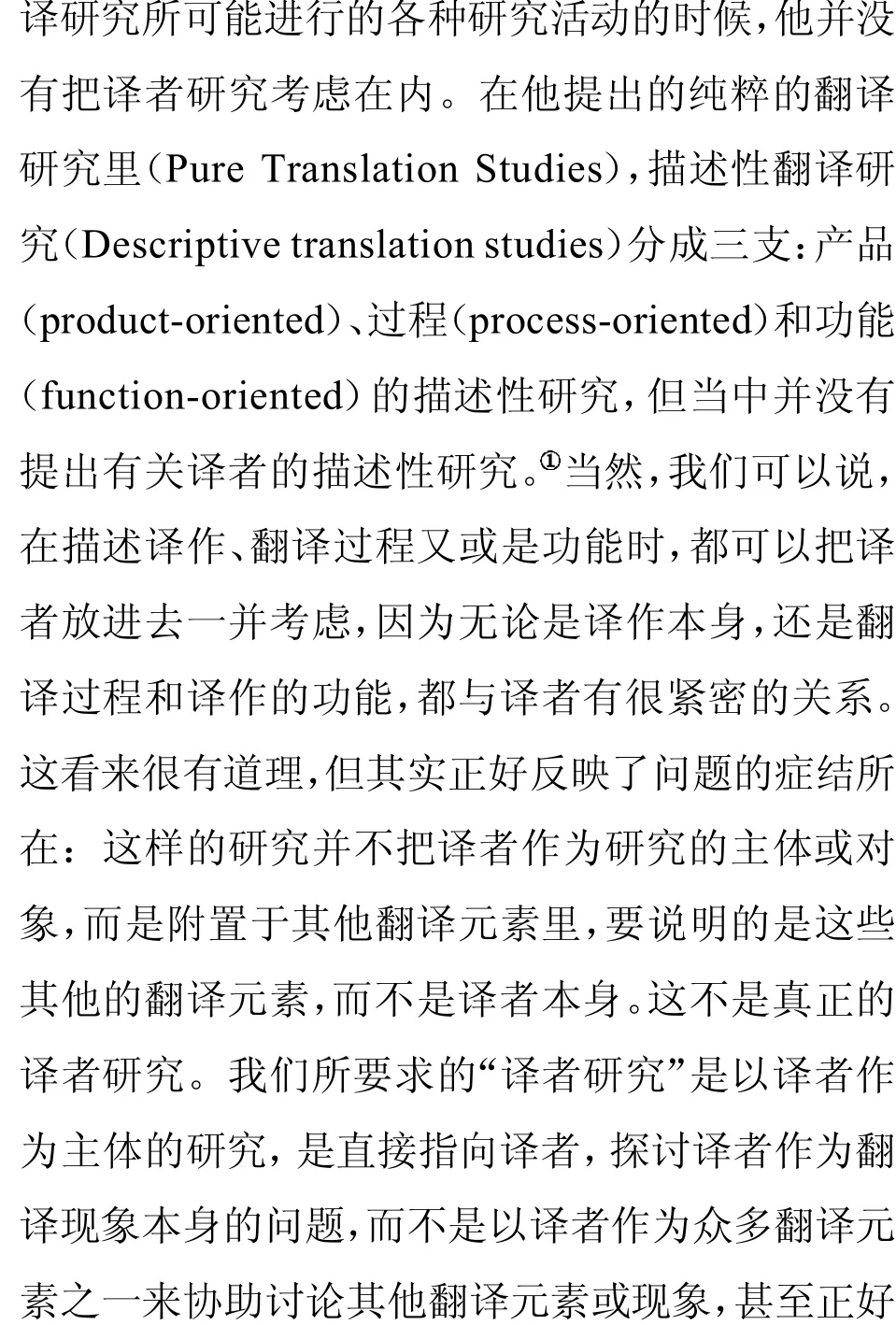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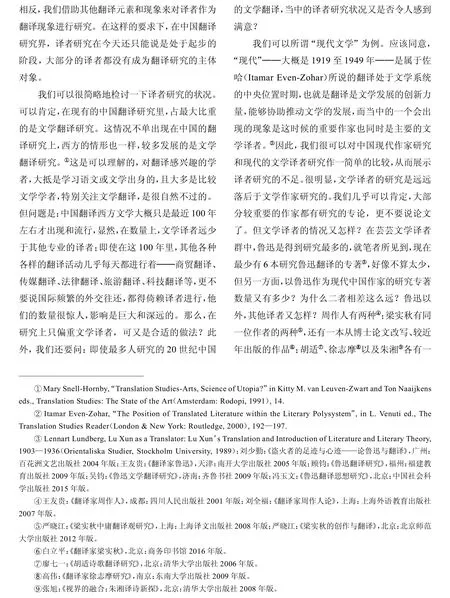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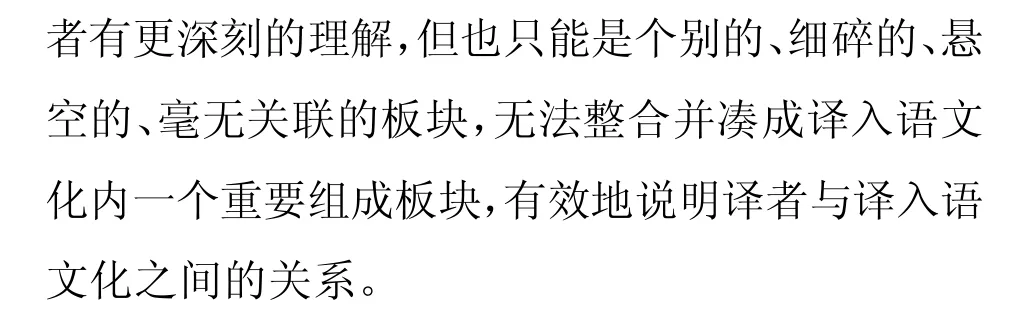
另一方面,这样的译者研究集中在他们的翻译活动上,忽略了译者的其他文化活动。其实,译者本身就是文化中的个人,即使最专业或职业化的译者,他/她的活动不可能只限于翻译活动,而这些翻译活动跟其他各方面的活动是挂钩的、配合的,甚至互动的。文学译者的例子最易理解,他们的创作跟翻译是整体性的,不讨论他们的文学活动,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翻译活动。创作以外,他们的出版活动呢?社会活动、教学和学术研究……跟他们的翻译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吗?文学译者以外,其他的也一样。例如清中叶以来广州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他们除了要负责翻译工作外,还要处理其他大量商贸事务,更要与中英双方的官员打交道,协调西方商人在华的贸易以至生活,他们的翻译活动甚至可以说是附属于其他活动的。现有的研究大都只集中讨论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忽略译者其他的活动,无法全面展现完整和真实的译者。
此外,由于这种译者研究所强调的是个别译者自身的价值和贡献,结果是无可避免地集中于一些所谓重要和知名的译者,上面说过的现代文学翻译家研究现状,便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鲁迅、周作人、胡适、梁实秋等都是文学翻译大家,为他们立传立论,无疑是合适的,但如果译者研究只是停留在这些重要人物上,那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毕竟所谓的大家名家数目不多,占译者的比例极为微细,即使多做名家研究,也不可能较完整地窥视译者的真正角色和贡献。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很多极其重要的发展都跟一些不知名以至不知道名字的译者相关,甚至由他们所推动。又以广州体制的通事为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聘用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为译员前,中英贸易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中英各种交往,都是通过这些通事来进行,他们在中英关系史上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他们绝对不是什么翻译名家,甚至绝大部分连名字也不为人知,以现有的译者研究模式进行,这些曾对人类发展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译者肯定不会成为研究对象,而我们对广州体制的翻译活动便不可能有较完整的理解,从而对错综复杂的近代中英关系的理解也不可能完整。这样的状况理想吗?事实上,从广州通事这个例子可以引伸出来的,就是译者研究不应该只限于单独或个别的译者,译者群体也应该纳入在译者研究的范围内。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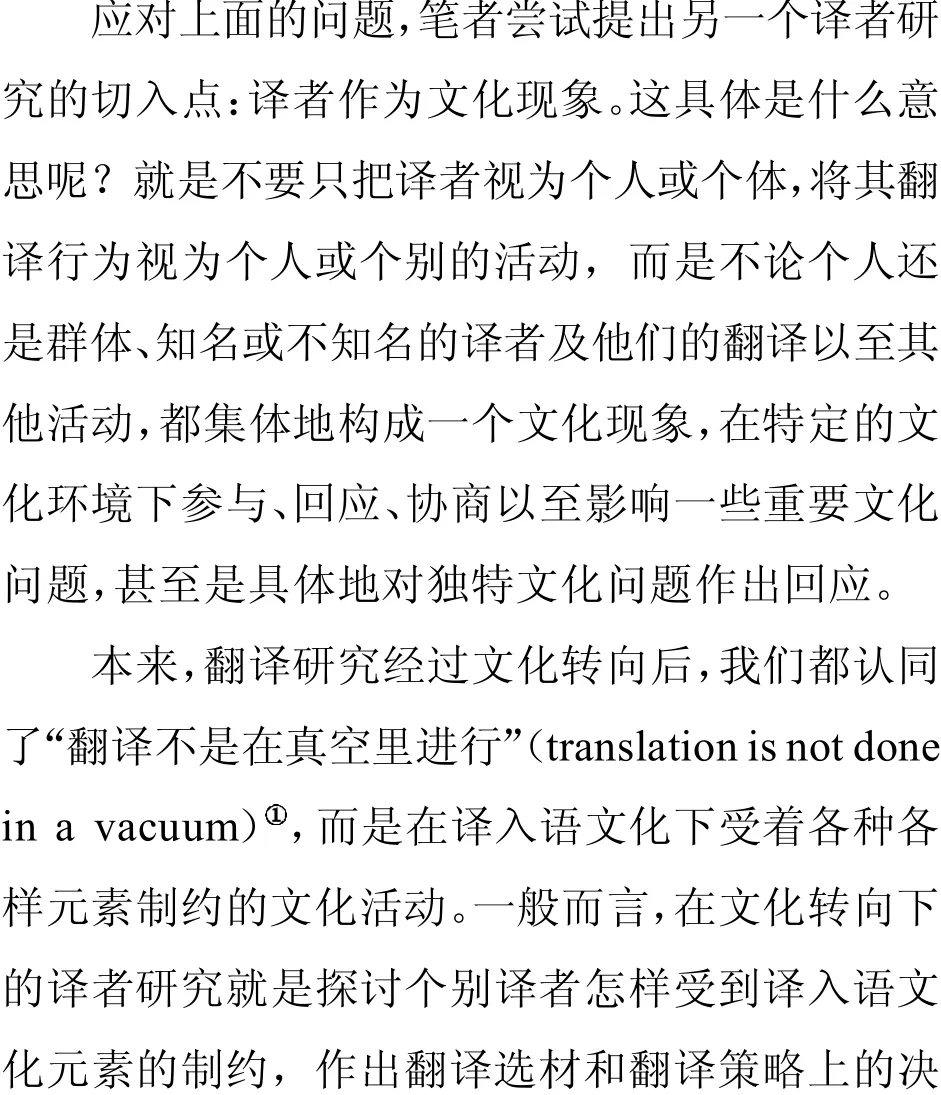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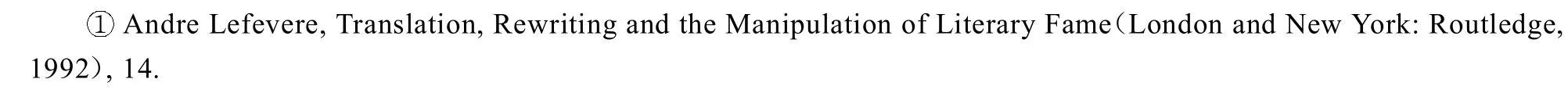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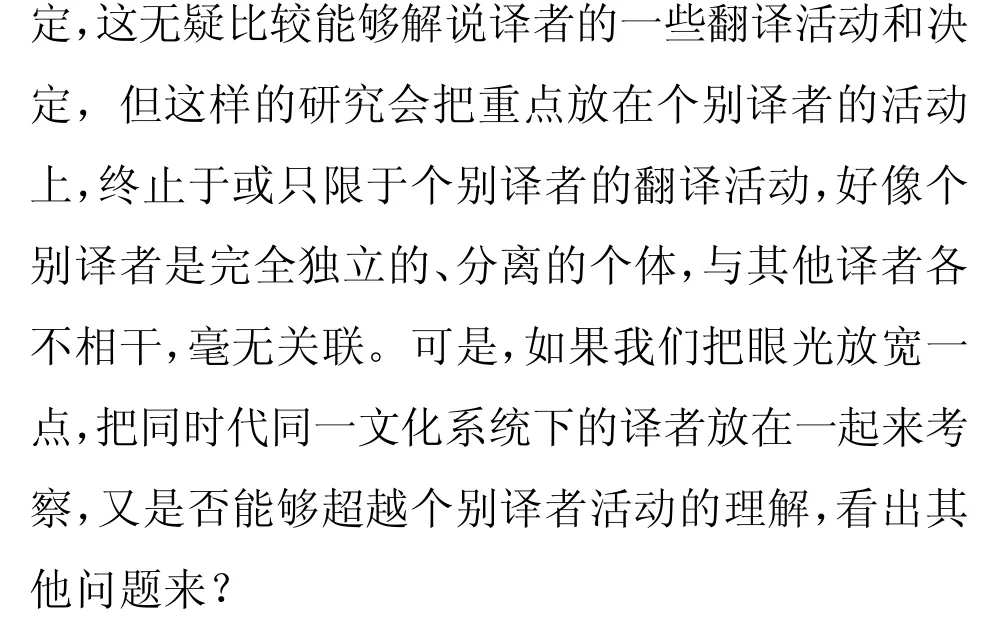
其实,同时代同一文化系统下的译者面对的,是接近甚至相同的文化元素、文化现象以及文化问题。因此,尽管他们各自进行表面看来很不相同,甚或的确很不相同的翻译活动,但很多时候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一定相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些文化元素、现象或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翻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行为,有着一种共同性甚至标志性,因而在总体上构成一个文化现象,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主要文化现象挂钩和互动。以译者为文化现象,跟译入语文化现象关联进行考察,已经不是个别译者特定的翻译行为的研究,而是更大范围、更整体性的译者行为研究;同时,这样的研究不会终止于译者本身,而是联系到更大的社会、文化方面去。我们不单以社会和文化元素去解释或理解译者的翻译和翻译行为,更通过同时代同文化的一些译者的翻译和翻译行为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状况,一方面更好地展现译者在整个文化中的功能和位置,说明译者与文化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一个从来很少人关注的角度——译者的角度去观照社会和文化,从而得到更深邃的理解。
必须强调,在我们认定同一文化下进行的翻译活动具备集体性,不同译者都在回应相同或接近的文化现象和问题时,并不是说所有译者的翻译活动都十分接近,这跟事实不符。我们不应该排除个别译者的独特性,因为毕竟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背景,际遇、经历,以至目标,因此,即使面对相同或接近的文化现象或问题时,也会有不同的体会、思考和反应,结果,尽管整体而言他们是在回应着相同的问题,但他们具体对应的方式,也就是他们的翻译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不单是我们在翻译史上见到的客观状态,更是以译者为文化现象进行译者研究饶有意义的地方,因为实际上是探究不同译者怎样以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去应对一个文化问题和现象,既能标示不同译者的独特性,增加对个别译者的理解,又能分析不同译者的共通性,在更大的文化层面上,更好地展现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译者所起的整体作用,有见树见林的效果。
以译者为文化现象的译者研究,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它并不排除个别译者的研究,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先从个别译者入手,不过,它不会是所谓的“全面”译者研究,也没有必要罗列或说明译者所有的翻译成果或活动,只会抽取相关的部分,针对某一个文化现象或问题来进行深入分析,不会停留在所谓“Who- When- What”的表面论述。
第二,它不局限于个别译者或知名译者,不论个别知名或不知名的译者,都会被视为一个译者群体的组成部分,集体地应对一些文化问题和现象。
第三,在分析译者的文化位置时,不会只集中或局限于他们的翻译活动或文本来进行研究,而是集结译者其他足以说明相关文化问题的各种各样活动,包括创作、出版、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样的研究模式能够对译者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及理解。
三
也许在这里可以利用笔者在过去十余年一直构思和撰写的一本书稿《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译者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研究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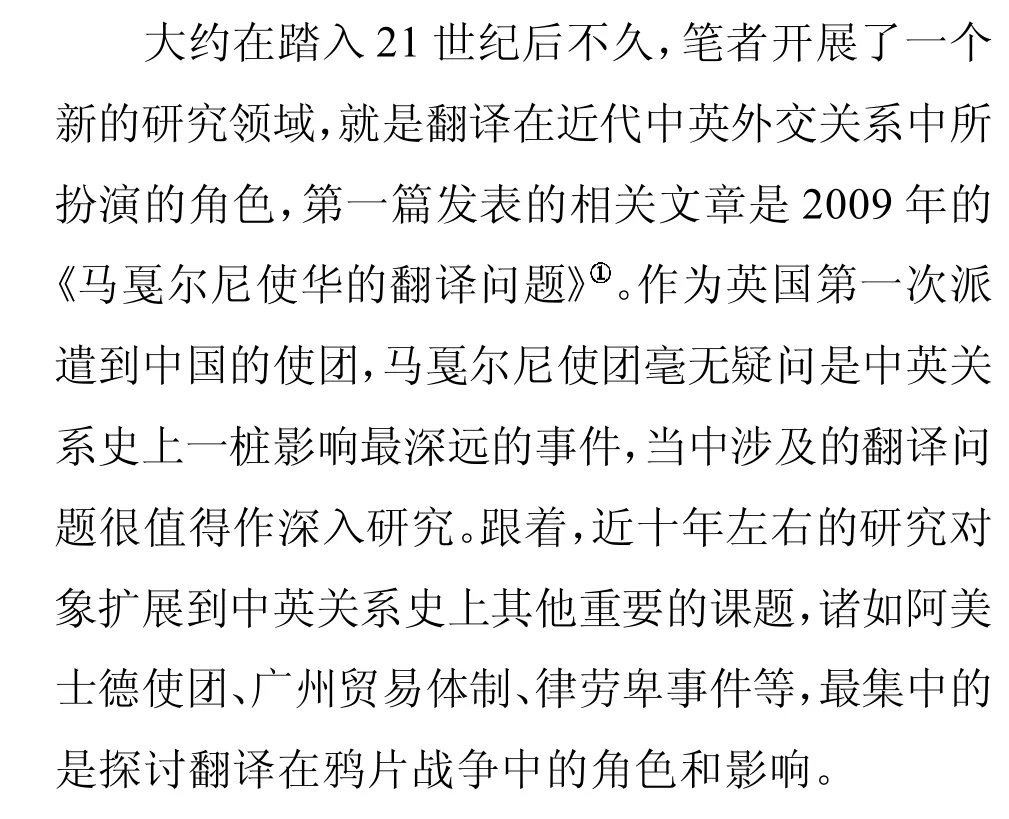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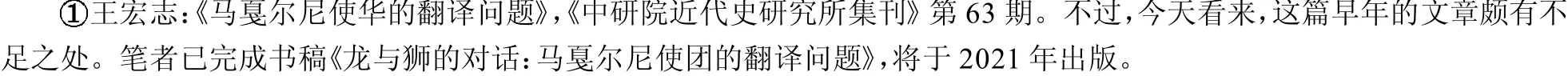
在中英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里,译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有可能左右历史的进程,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在研习译者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活动和位置时,尝试找出一个贯穿18—19 世纪、长期有力地影响着译者的文化元素或现象:天朝思想。
毫无疑问,天朝思想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不可能在这里作深入讨论。如果用最简单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外族外国的一种主流态度和论说,或者更具体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外族和外国人看成是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没有开化的蛮夷。笔者认为,在明末以至清末(最少在1860 年代以前),这样的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其中一个主要元素。笔者正在撰写的《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就是以传统天朝思想下的蛮夷观作为整个研究的框架,贯串一系列个别译者或译者群,从明末1637 年英国第一次商船队到达广州,第一次与华贸易的通事李叶荣开始,至1860—1870 年代在清廷派遣几次到欧洲的使团出任译员的张德彝。
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天朝的译者”,指的是在传统中国天朝大国思想下,在中英交往过程中活动和运作的译者,因此不只限于在清廷或为中国官员工作的中国人通事或译员,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涵盖了全部在17—19 世纪参与过中英交往过程的译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刚提过在清廷或为中国官员工作的中国人通事或译员;二是为英方(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或宗教团体)服务的英国译者;三是为中国朝廷工作的西方人译者;四是为西方人聘用提供翻译服务的中国人译者。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英国的译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尽管服务对象不同,工作环境和待遇很不一样,工作目标以至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但其实都无法摆脱这天朝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的翻译活动就是在这些制约下进行,而且几乎无可避免地必须回应这些制约。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做着相同或差不多的翻译工作,又或是以相同或相似的翻译策略来从事翻译,刚好相反,正由于不同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位置,他们对于天朝思想的制约会有不同的态度,有些是配合的,有些是抗衡的,有些是调和的,因而产生的回应模式很不一样,翻译活动和策略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过,不管是配合也好,抗衡也好,调和也好,这些制约的确存在,也的确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要对明末以来至清中叶以后甚至清末年间参与过中英交往的译者及其翻译行为有较准确和全面的理解,便必须对作为翻译制约力量的天朝思想做深入分析。
同样地,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天朝思想对于译者及其翻译行为具体的制约是什么。概括而言,天朝思想对译者及翻译行为的制约,以及明末以来中西交往的译者怎样以一个文化现象作出集体性的回应,大概有好几种不同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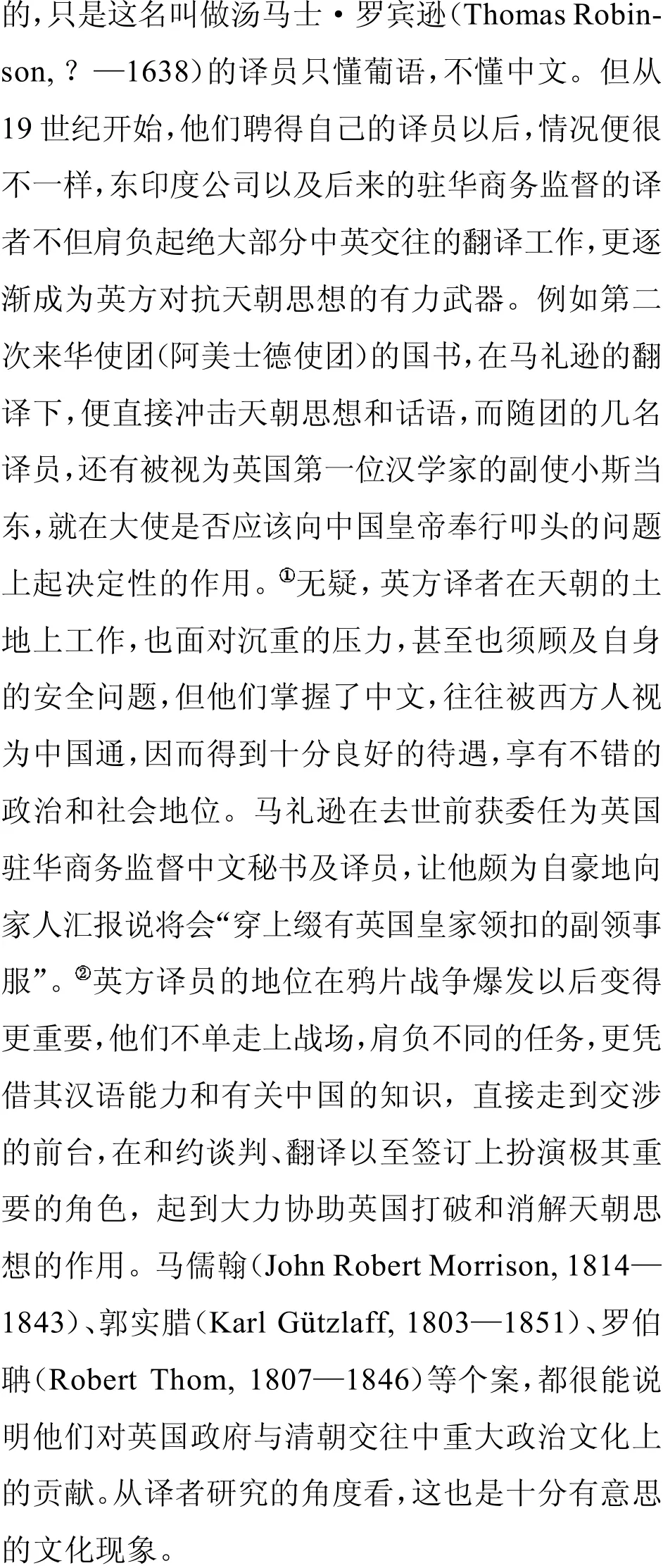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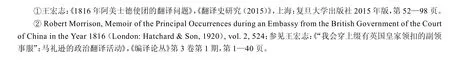
四
其实,天朝思想以外,在漫长的翻译史中,影响和制约译者行为的文化元素和问题很多,不少极有意义的课题尚待发掘和处理。以文学翻译为例,清末民初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不少具有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的思想,放在晚清中国受尽列强侵略的政治背景里,便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译入语文化问题。不同的译者会采用什么方式来回应?他们认识到这些作品中的帝国主义思想吗?他们刻意回避这些思想吗?还是视而不见?又或是大刀阔斧地删除?他们会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供中国读者各取所需吗?怎样拿来?当头棒喝吗?鼓吹模仿吗?还是若无其事地全盘接受?各种应对方式起什么作用?另外,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工农兵文艺、阶级斗争为文学主导思想,提出思想改造,摒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这对不少从民国时期进入新中国时期的文学作者和翻译者造成很大的冲击。在新的文艺和政治思想指导下,尤其经历过思想改造的过程后,面对崭新的工作环境和出版条件,他们怎样调整从前的翻译活动,从而追上新时代的需要,配合国家的文化政策?不同译者可能有相近或完全不同的学习过程和应对方法,都清楚地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以至对作品的诠释、解读和流播,甚至他们的其他文化活动上。这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对不同译者作个别的个案研究,很能增加我们对个别译者的理解,但整体地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文化现象,就更充分地说明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和状况,更清晰地展现译者怎样构成特殊的文化现象。
文学翻译以外,明末以来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翻译活动和行为中,是否也能找出一些重要的文化问题,展示集体的制约和回应?例如不同传教士在翻译西方宗教作品,又或是在翻译中国典籍和文学作品时,怎样应对传统中国思想的力量?又或者在19 世纪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加剧后,作为主要掌握中文能力的传教士,又怎样在世俗与宗教之间作出取舍,为西方国家担任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译员,尤其当时中外政治交往涉及不少诸如鸦片贩卖等道德问题?这都是以文化问题入手来考察译者的有趣课题。
总而言之,现有的译者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个别的译者。在现阶段译者研究还很不足的时候,这不但无可厚非,甚至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所有译者研究都只停留在个别译者传记式的书写,不能从文化的层面展现更具普遍性、更深层次的意义,也明显是不足的。把译者视为文化现象,对应某些重要文化问题,审视译者在这些文化问题上的作用和角色,展现一个时代和文化的译者们翻译行为的集体性和普遍性,这也许是进一步推展译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