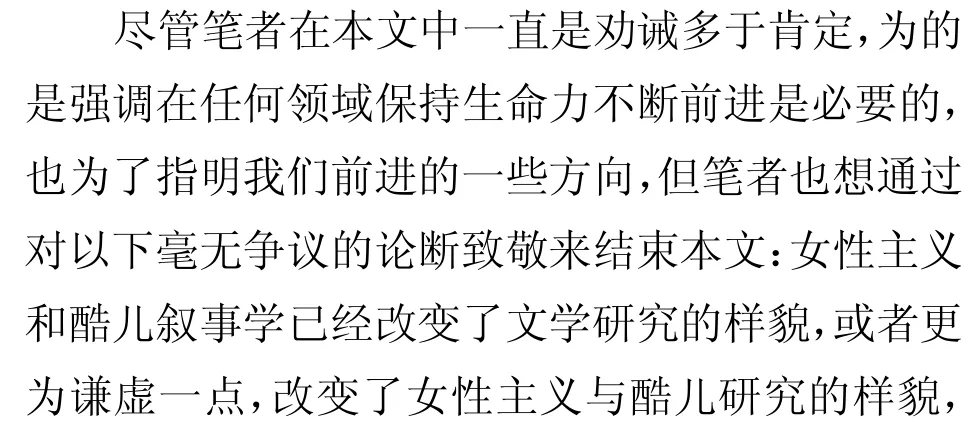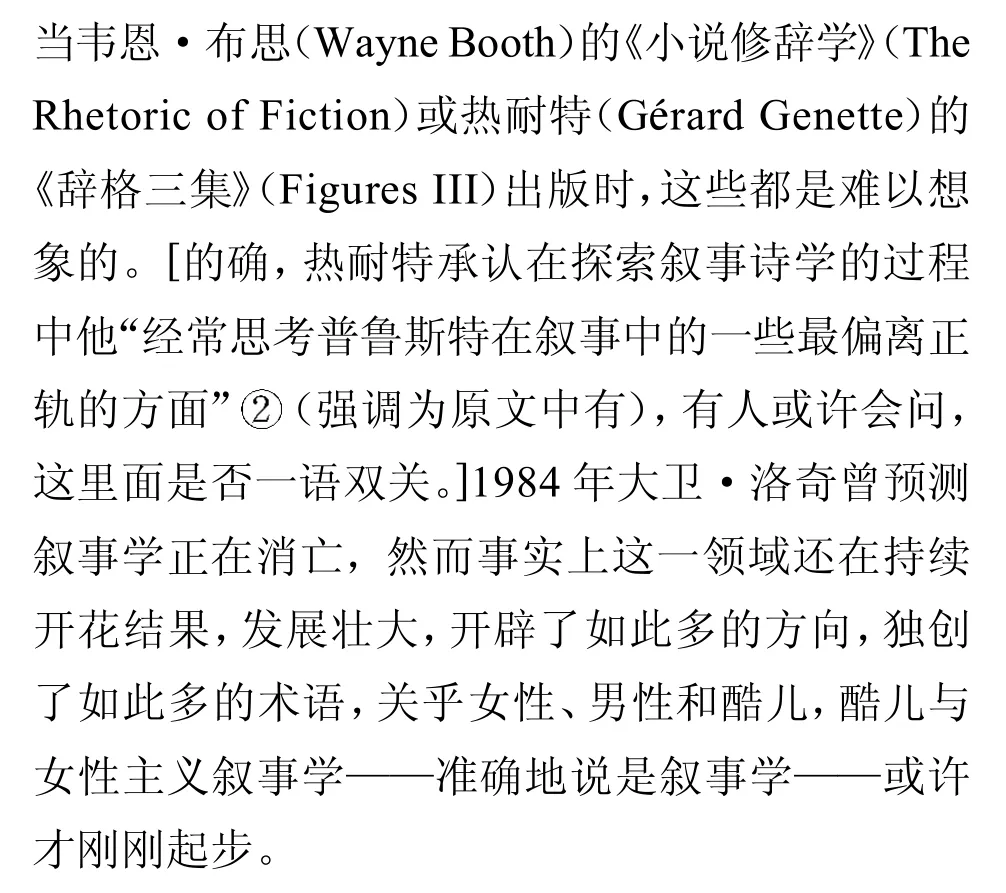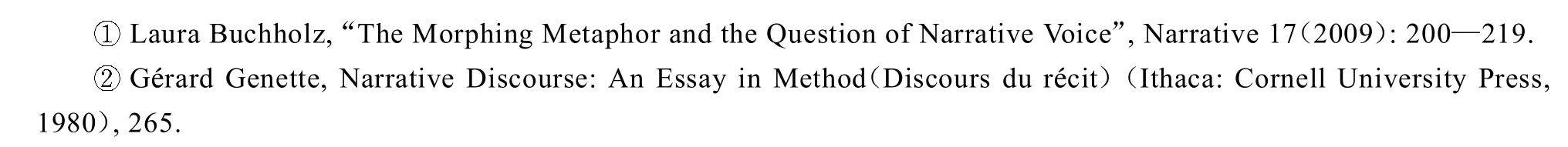(1.布兰迪斯大学 英文系,美国 马萨诸塞 沃尔瑟姆 02453;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710126;3.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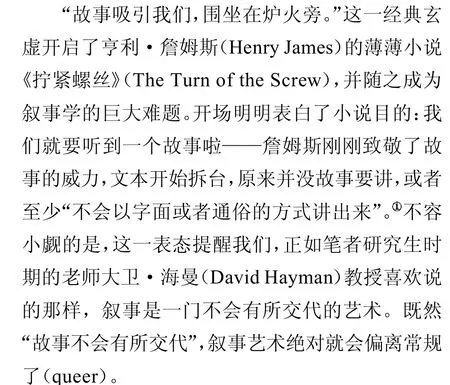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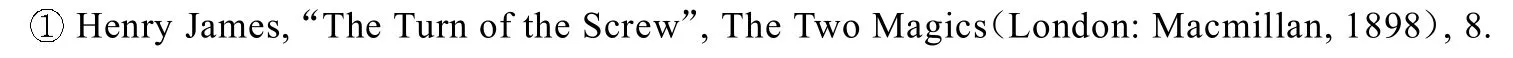
以这段文字作为开篇,笔者是要说明,正是因为“故事不会有所交代……不会以字面或者通俗的方式讲出来”,叙事恰恰需要叙事学。正是因为叙事作品成功掩盖了自身叙事策略,叙事学为我们了解故事如何进展以及如何“吸引”我们提供了关键方法。正是因为那些叙事策略是作为叙事内容存在的,除非我们将故事理解为形式,否则无从理解。叙事所依仗的性别安排以及性别安排所依仗的叙事复杂、细微,有时还难以捉摸,因此女性主义及酷儿研究有可能是叙事学特别的受益者之一。笔者开篇提出这些主张,是有意倒换一下早期的研究重点:如果说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推进叙事研究向酷儿理论和女性主义纵深发展的话,那么现在则强调女性主义及酷儿研究——甚至叙事研究——朝叙事学深入迈进。尽管女性主义与叙事学联姻成就斐然,语境叙事学便是其最大的成果,但叙事学的益处还未充分显现出来。深挖这些益处确实需要在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上做些调整,特别是在提倡归纳总结法和交叉性方法上,以及仔细考察术语和所选批评方法的优先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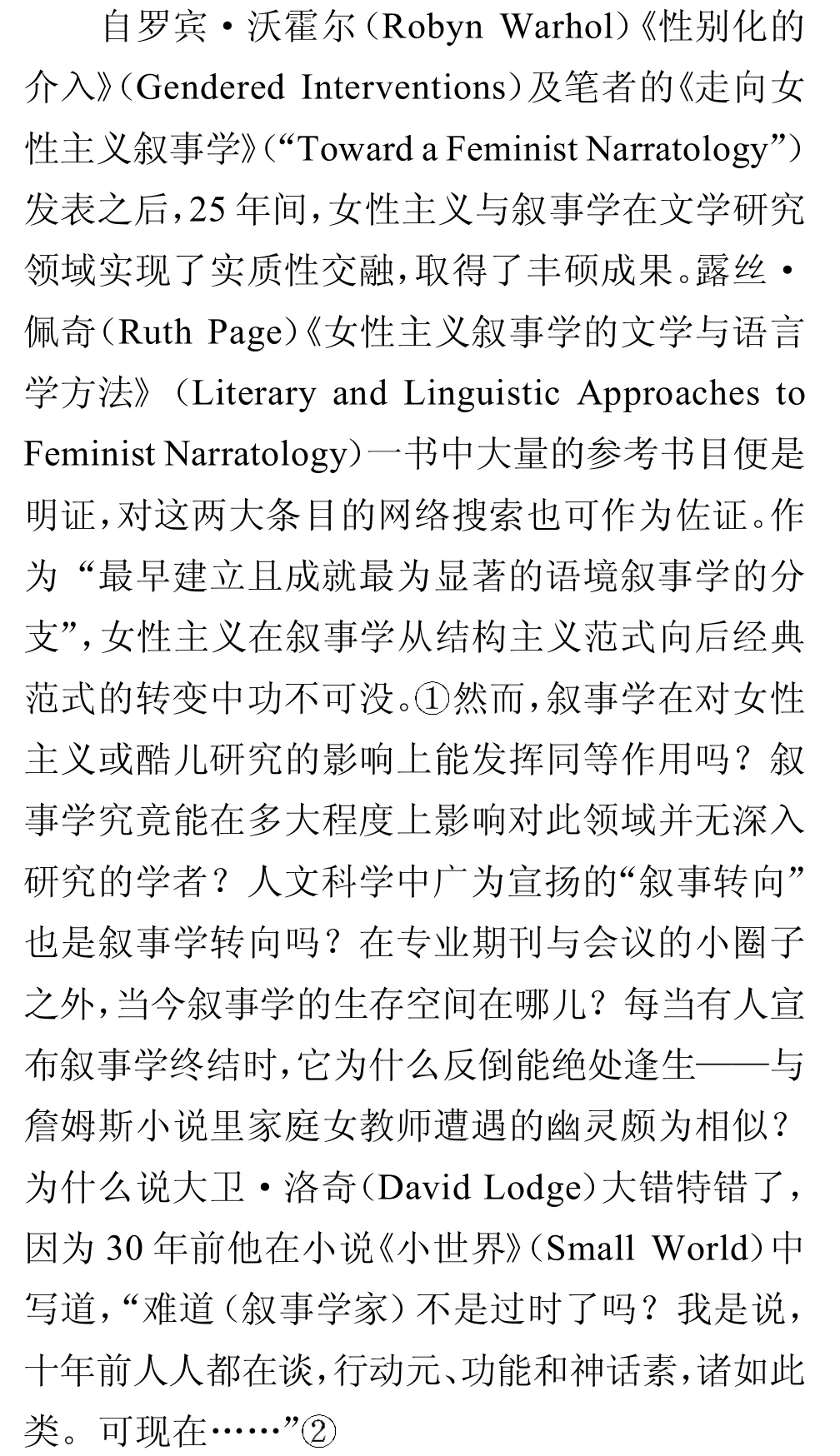
本文旨在介入当下现状并提出一些看法,作为推动叙事学向纵深发展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助力从事女性主义和酷儿研究的知识分子实现其目标。笔者将论证女性主义及酷儿叙事学所涉及的经典文本过于狭隘,建议如何扩展它的历史学和地理学范围(这一扩展非常重要),并提出一种交叉叙事学的设想,促成制图学(cartographic)转向,超越文学研究的自限,呈现女性主义与酷儿研究更为广阔的叙事学前景。本文还将讨论再现问题,特别是酷儿叙事的再现,指出这既关乎形式也关乎内容,因而叙事学关注的重点应该是酷儿叙事的再现与叙事本身的局限。最后,本文还将试图说明除非我们将叙事形式当作叙事内容来研究,否则“故事不会有所交代”,而这一策略可能有助于弥合业已存在的——在笔者看来是错误的——文化批评与形式研究上的分歧,小说理论与叙事理论潜藏的裂痕便是明证。此外,本文还将探讨女性主义及酷儿文学研究,以及其所涉及的意识形态或基于身份议题的探索——它们都受惠于叙事学,因为此类批评实践具有模仿论偏向,易于忽略嵌入形式之中的违规、颠覆和偶发现象。最后,笔者将指出保留叙事学字面及实际意义是很有必要的,但叙事学应当不单单为叙事学家所独享:我们需要引入新方法以解决本领域里因乱立术语和论题而带来的恐慌——或许就是失误。所有这些议题很难由一篇论文言尽,因此笔者不免要冒着讲不清楚的风险,或者更糟的是,只能以字面或通俗方式讲得言不及义。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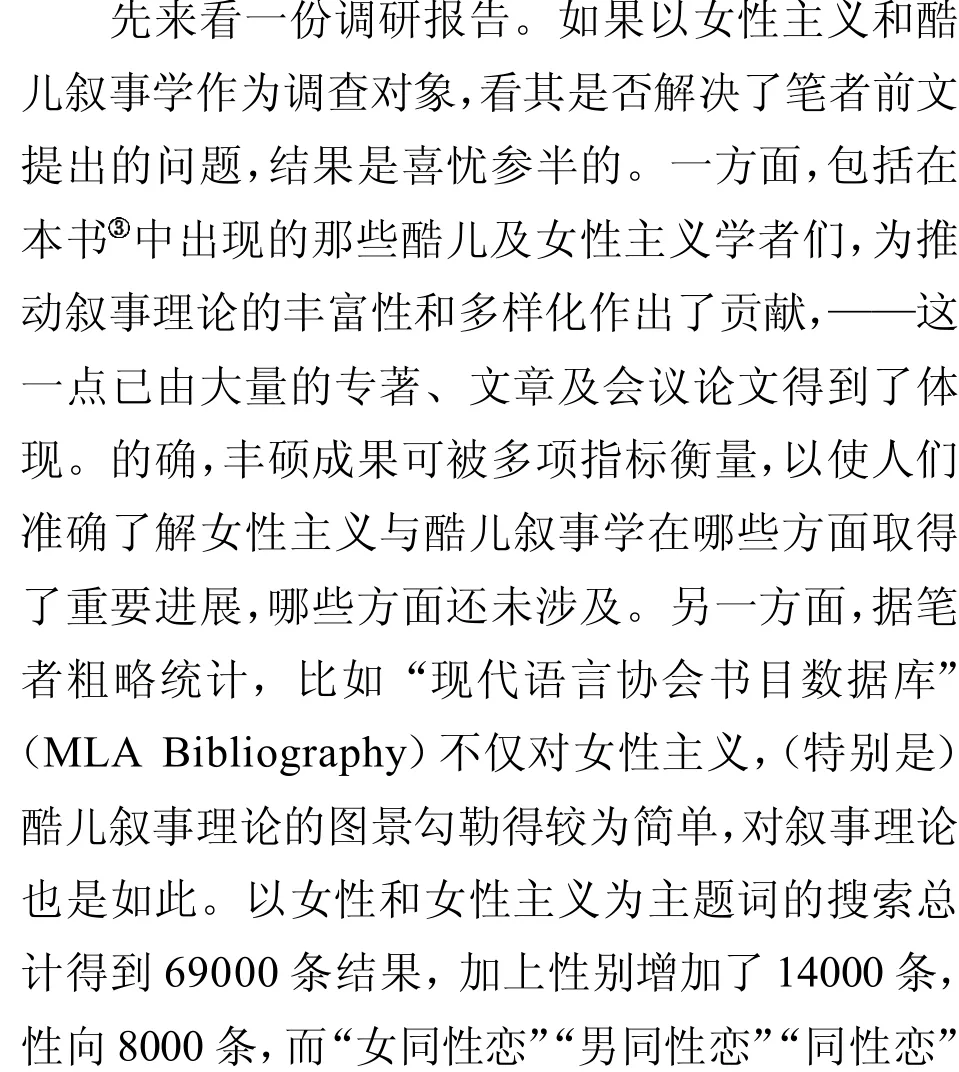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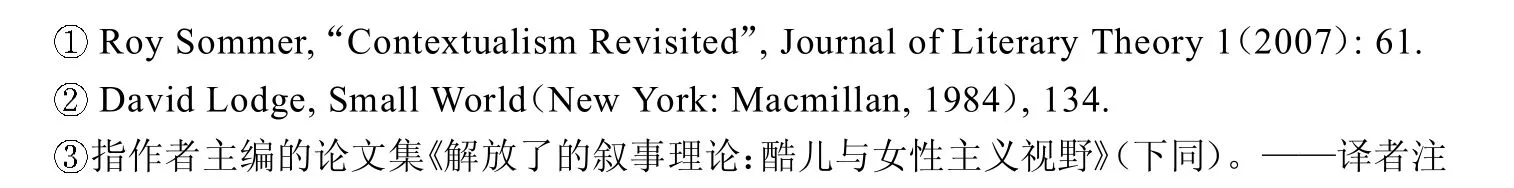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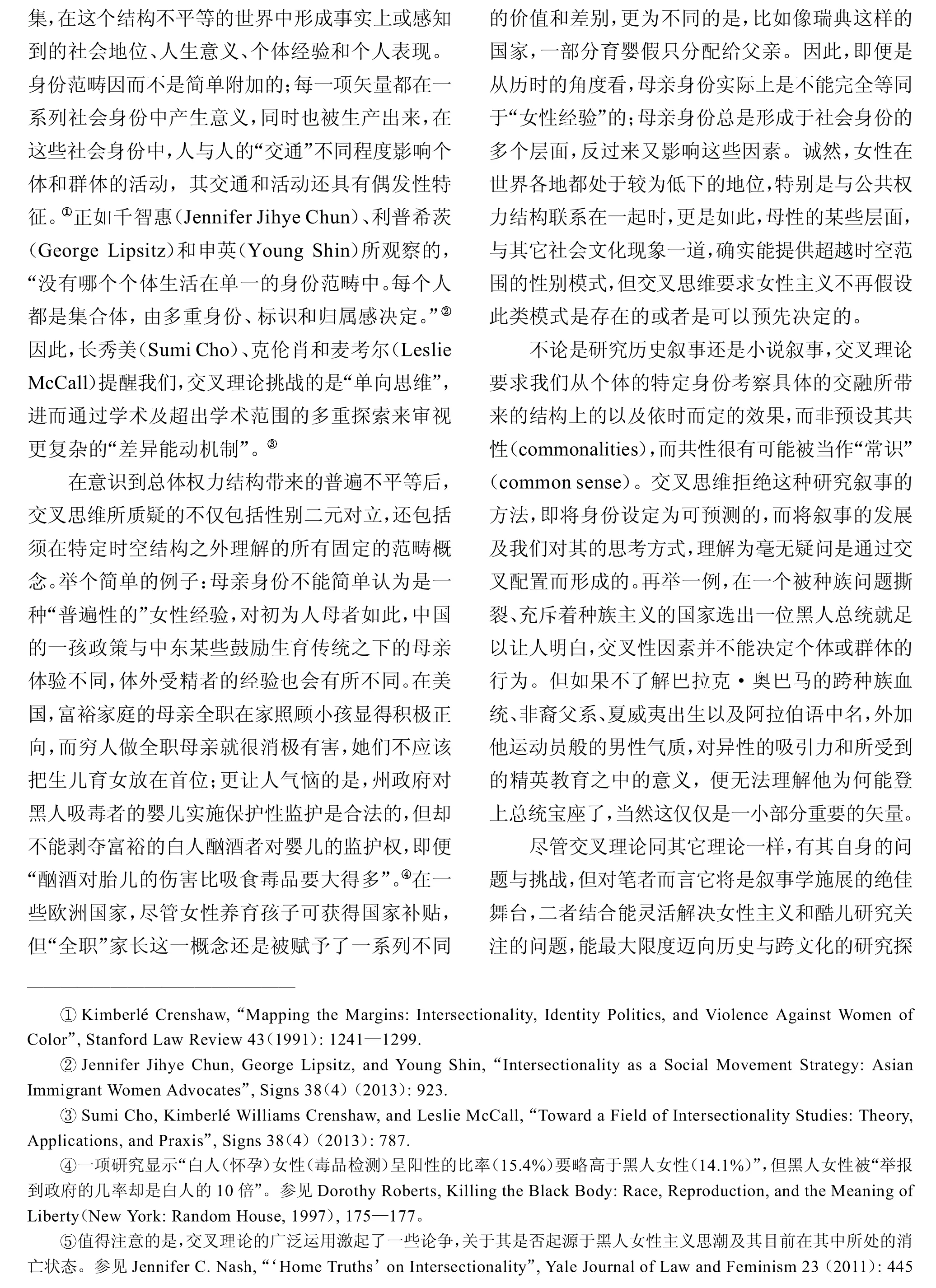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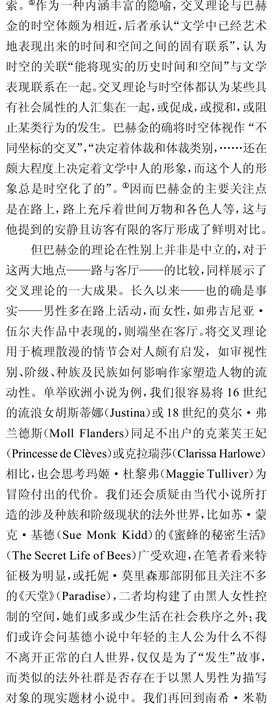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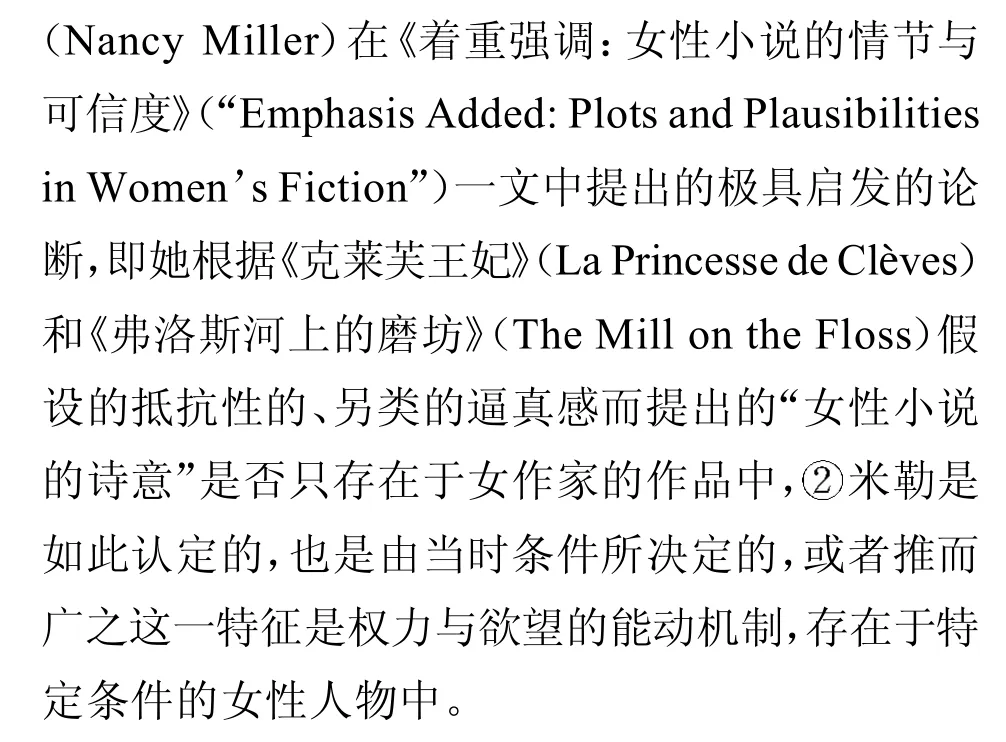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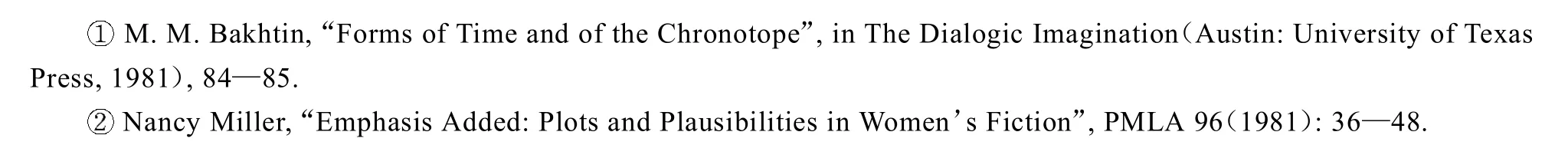
三
笔者呼吁将交叉理论付诸实践,并非旨在将小说文本降格为社会活动,将粗略的范畴强加于复杂的人物之上,或者用简单的阐释去理解叙事事件。但笔者认为,我们确实应当大规模践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在《表图、地图、树形图》(Graphs, Maps, Trees)中提出的模式,通过交叉的时空观来分析个体叙事与群体叙事是怎样影响个人身份(即人物)和行为(即情节)的,以一类新的历史观在广阔的世界叙事的范围内勾勒出这一影响机制的面貌,从而对叙事形式实现“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我们可以梳理一类叙事形式的发展脉络,比如自述故事叙述(autodiegetic narration,即由主人公叙述),这一形式崛起于17 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和18 世纪的英法,19 世纪在西方逐渐减少,却在日本与中国萌发出来,在世纪之交反殖民斗争的拉丁美洲与南亚地区则大量涌现,直至今天成为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流行的模式。我们也可以将叙述者及不同的叙述策略同我们所知的时代背景、地域和作者身份联系起来,进而发现这些不同的叙述模式在文学史上占据何种地位。此类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验证以作家的社会身份为参照来研究文本是否有效,进而反思或检验作者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女性主义叙事学者曾经主张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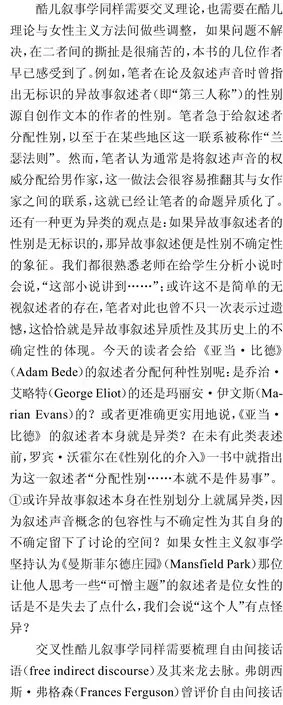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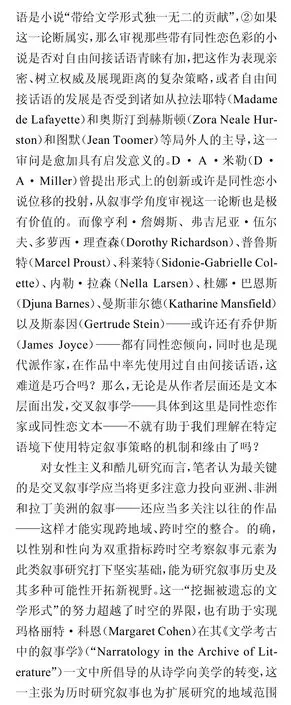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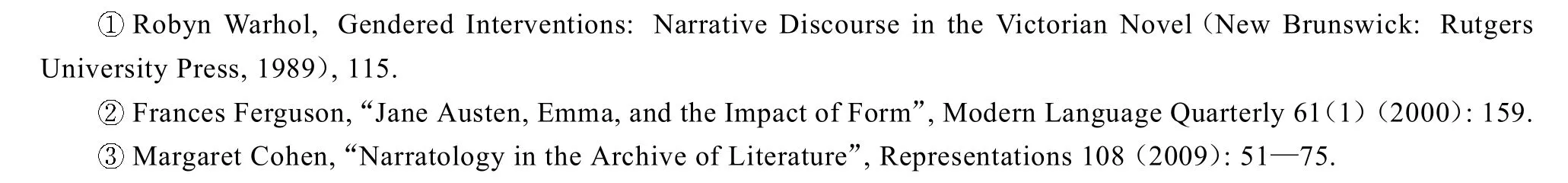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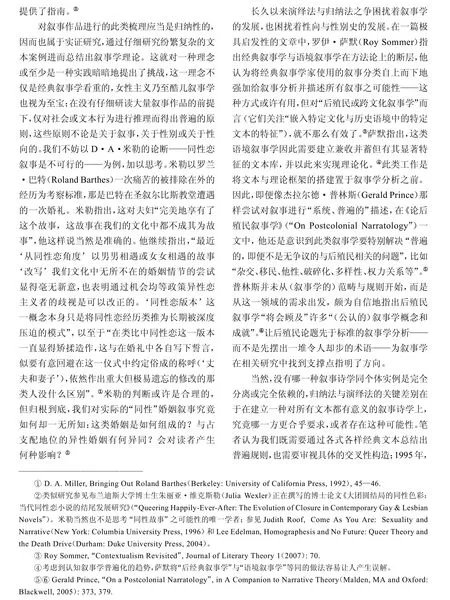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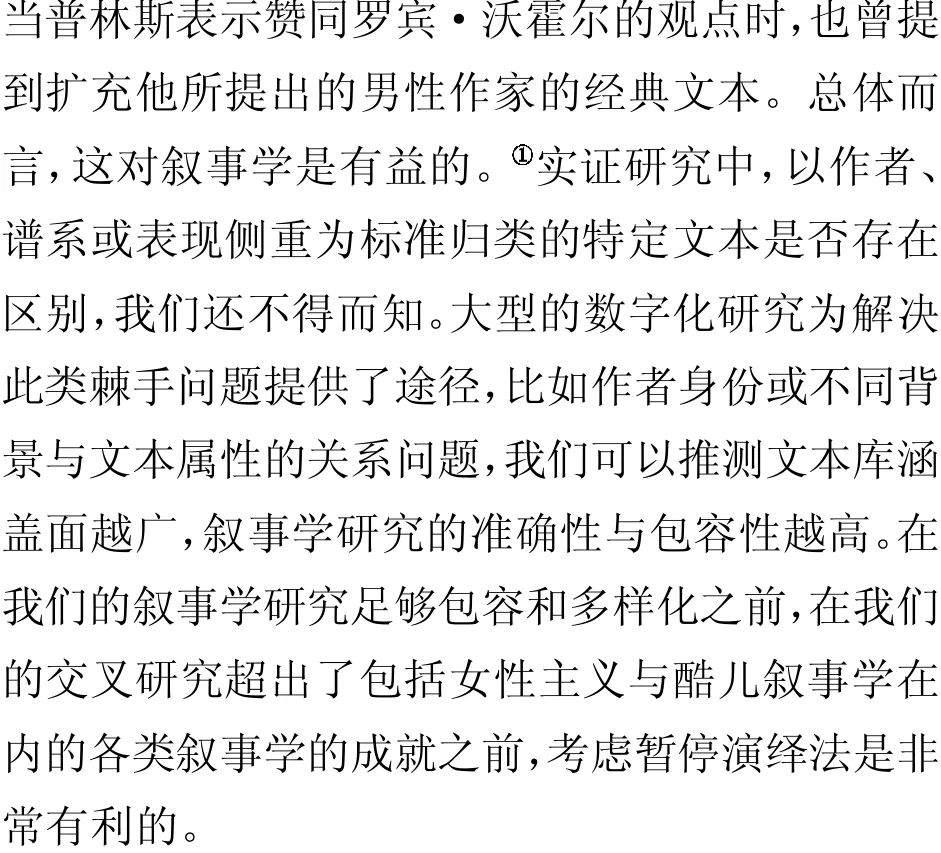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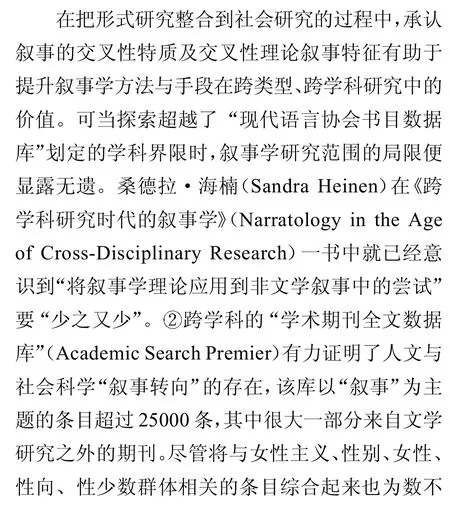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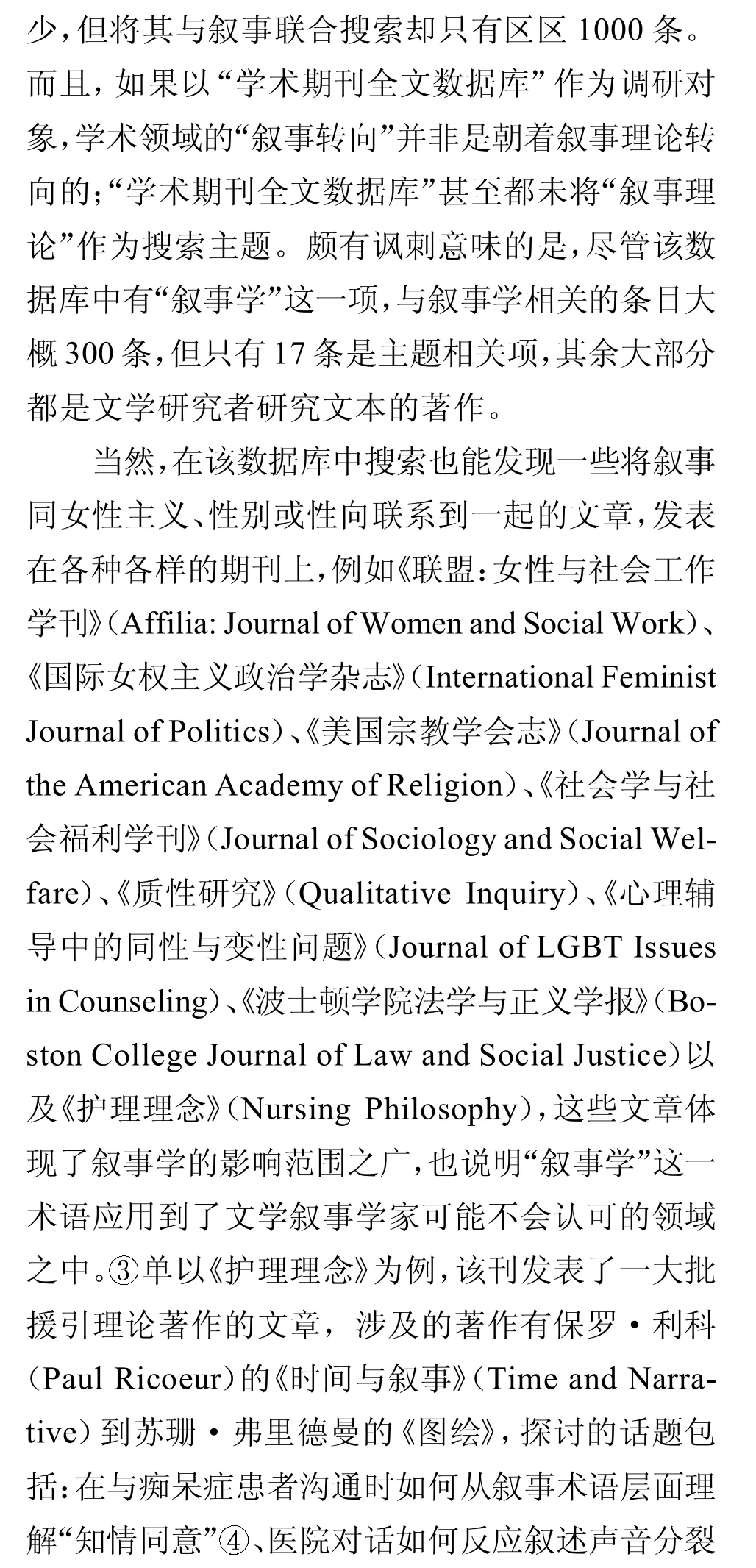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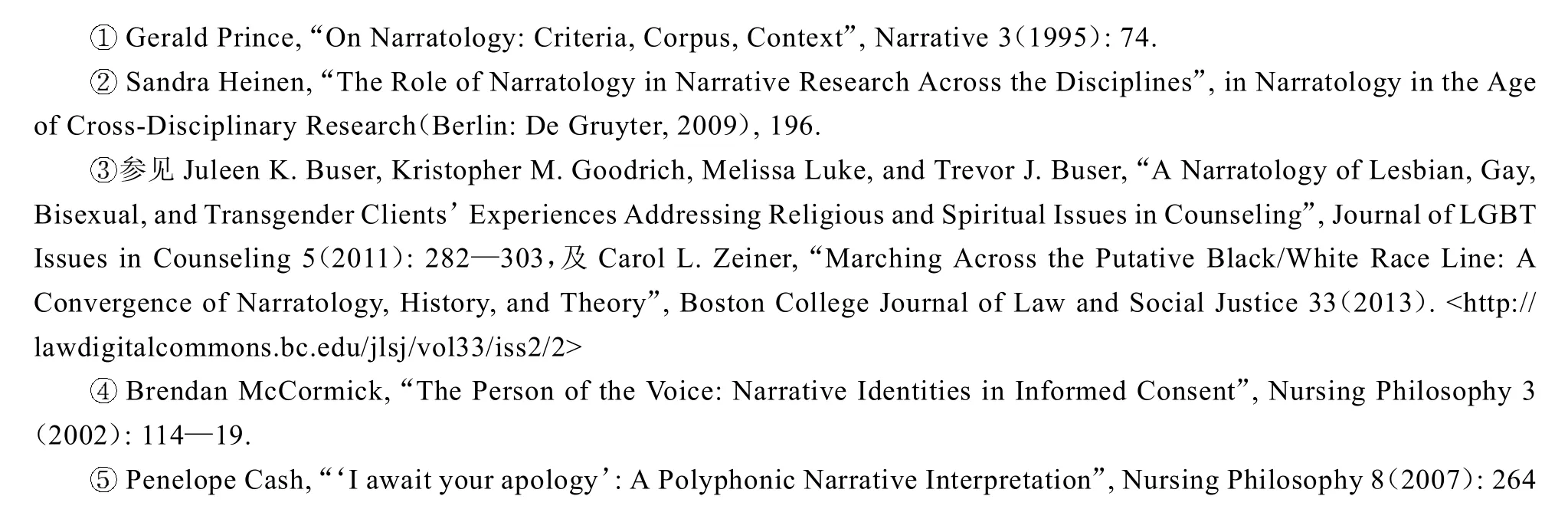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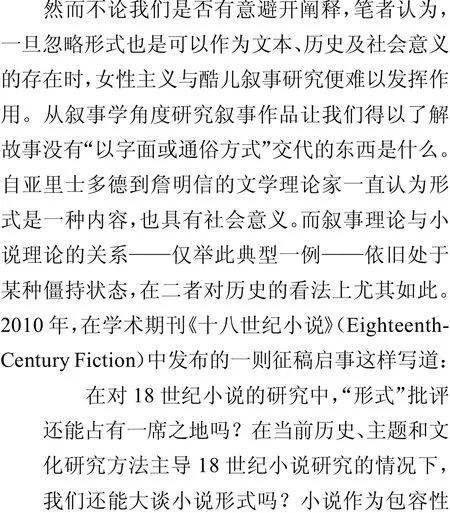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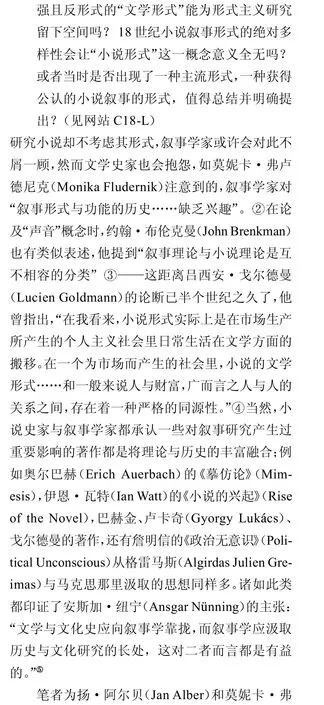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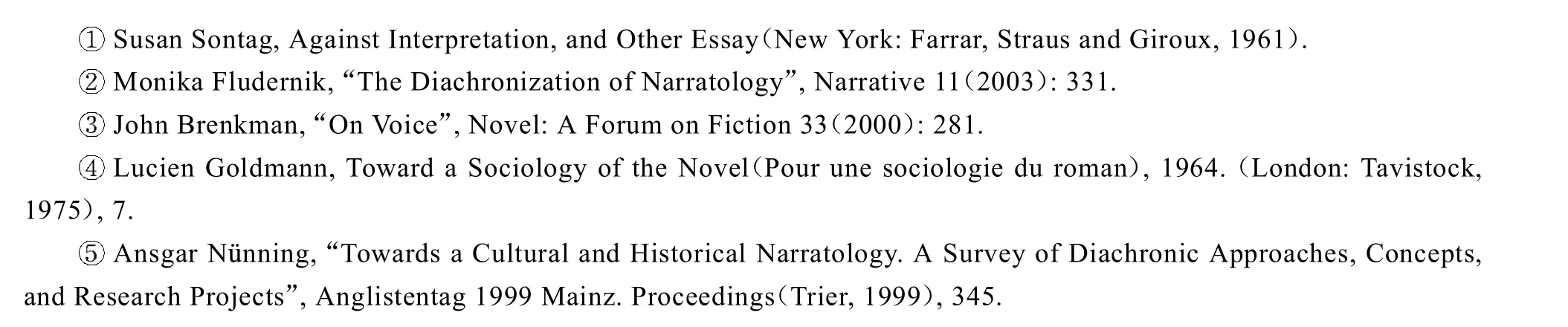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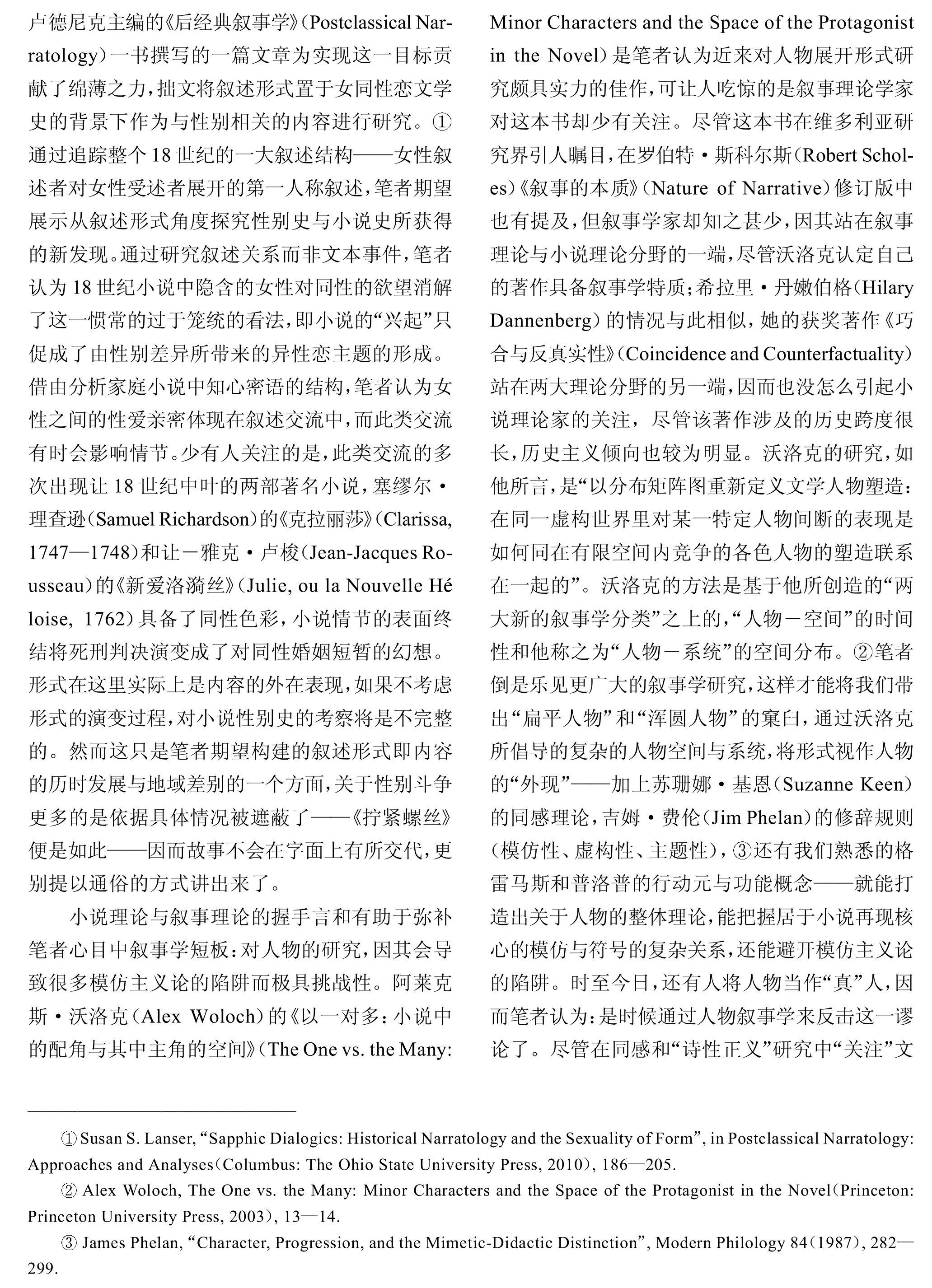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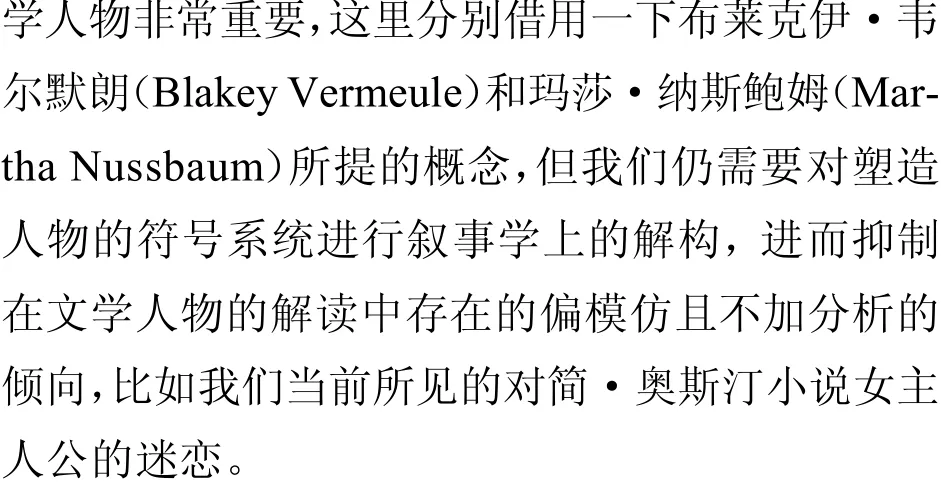
六
本文通篇都坚持用“叙事学”一词,尽管在女性主义和酷儿叙事理论研究内部很多人对此避之不及。的确,正如本文标题所强调的,笔者强烈主张叙事学对结构的精准把握、方法论的启迪意义,都决定了其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单词、一个概念和一种批评实践而固步自封。通过所选例证,笔者试图证明最经典的叙事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探寻文本结构,也能帮助我们探究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因为杰拉尔德·普林斯曾做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断,语境因素已经嵌入文本的结构中,尤其是在他所提的受述者概念的构建上。但为了让这类叙事学研究更加“名正言顺”,笔者不得不提一下圈内人安斯加·纽宁回顾本领域历史时提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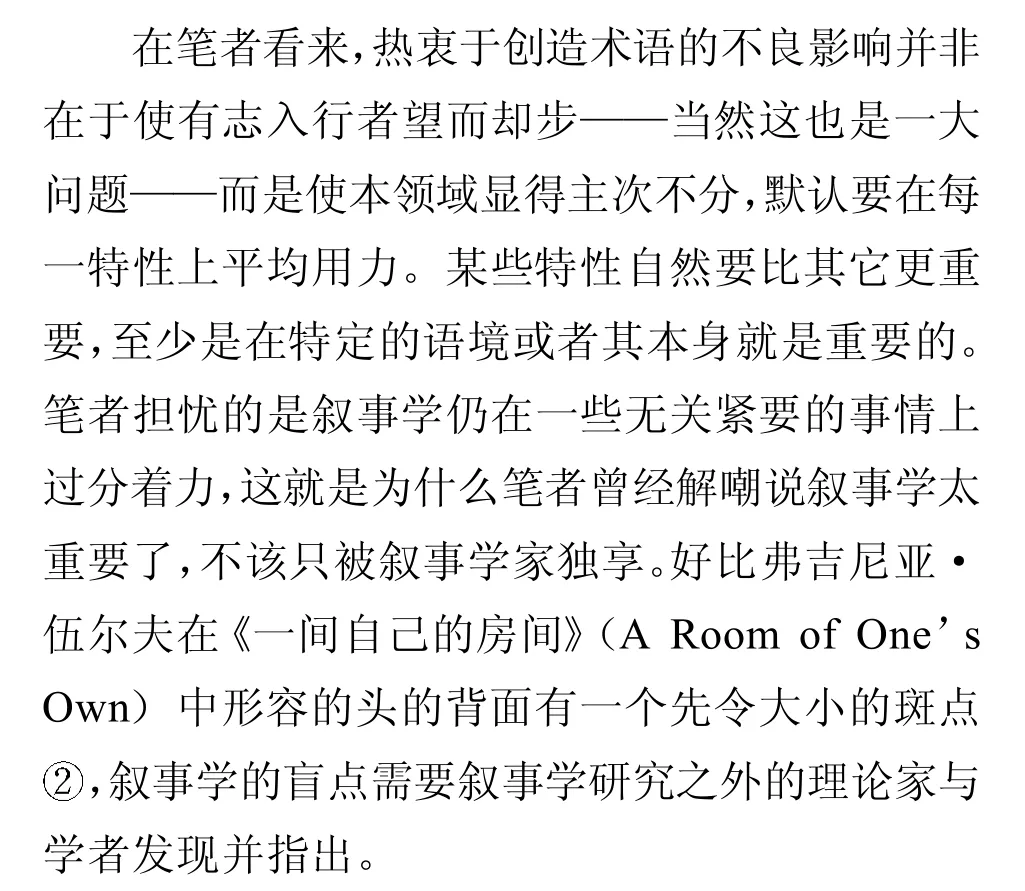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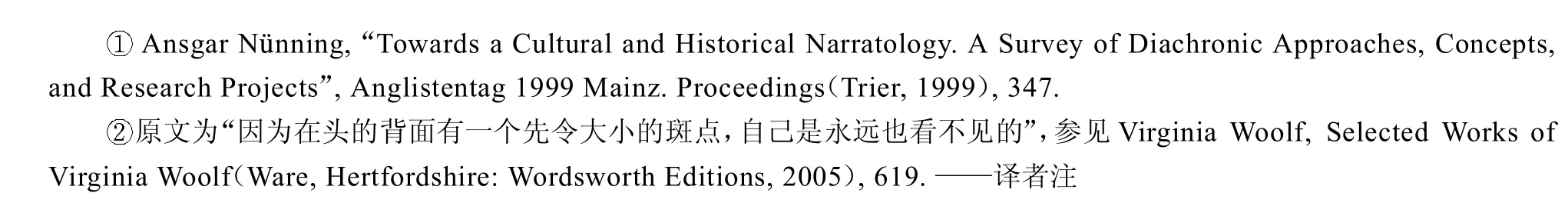
因此笔者呼吁从事女性主义与酷儿叙事研究的学者同时做这两项工作:对叙事概念做全面检查,以便推广那些适用性强能产生广泛共鸣的,再对与之相关的术语进行检查并重新评估。让我们站在局外人角度——激进的酷儿研究理论家或比如《护理理念》的读者的角度——以查明哪些概念他们觉得是特别有用的。让我们审问一下与这些概念相关的术语,来决定他们是否有必要在文字上或引申义上保持“希腊语”特性——不论是否源自希腊语,还是本身“让人难于理解的”。这就意味着——让人想起希腊语另一隐含意义——我们的术语和概念是有些怪异的;自《叙事行为》(Narrative Act)开始,笔者就认为二分法不如定范围,在一个性别模糊(gender-queer)外加数字变形(digital morphing)的时代,我们或许得弄清在何处模糊界限是有利的,就好比笔者提到的异故事叙事的情形。当然,鬼故事和心理剧的元素在詹姆斯的《拧紧螺丝》中频现,让人难于分清二者界限,也诱使读者难于在二者中作出选择;形式上相同的策略却导致文类的二重性表里不一,或许会使我们意识到在叙事学中不能将归类的准确性等同于排他性和单一性。劳拉·巴克霍尔兹(Laura Buchholz)从“变形”(morphing)角度研究自由间接话语 提醒了我们,还有互联网上无所不在的通过数字拼图技术打造的一系列“乔治·W·奥巴马与巴拉克·奥布什”(George W.Obama/Barack O’Bush)的变形照也充分说明,二者兼有或许比非此即彼更为准确,以不合常理的方式处理文字和图像就好比《拧紧螺丝》处理小说故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