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引 子
歌德《浮士德》之难懂,在于其具体场景和台词。一般认为,《浮士德·上》比《浮士德·下》容易懂。即便如是说,也是相对而言。比如《浮士德·上》第一个单元,通常称“学者剧”,大多数读者(或观众)所能把握的终究只是主要线索、主要情节或主要问题,其次则止于赏析个别词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主要情节线索概可从逻辑关系较为清晰的片段捕捉,而名句则无外乎符合常识的人生哲理。换言之,即便在通常认为易懂的学者剧中,仍有大段场景或台词晦暗不明。这对于200 年后的中国读者如此,对于德国观众也莫不如此。
正如《浮士德》法兰克福2017 年版题记所写:在《浮士德》研究和注疏工作进行了160 年后,“仍有某些场幕,或则完全出于习惯,或则出于无知,至今无人予以解读。这尤其涉及作品与时代史、与自然科学、神学和文化史的关联。而正是这些关联使《浮士德》成为一部恢弘的尘世之诗”。
一部作品,尤其一部戏剧,由连贯的情节和台词构成,找主线、找重点、找名句式的进入方式,依然只能着力于熟悉的地方而无视陌生部分,其结果是重复印证已有的结论,对于拓展对作品的认识却无补益。事实上,在歌德《浮士德》的地图上,布满魔法、炼金、占星、招魂、占卜、巫术、催眠等各种“秘术”场景。所谓“布满”,意为对于上述种种,剧中连贯上演大段乃至整场戏份,并非偶尔穿插某些元素。《浮士德》可谓完整再现了德国乃至欧洲的秘术传统与秘术实践。
可以盘点一下:《浮士德》下部第一幕宫廷政治戏中,有占星师作为国师辅政,有以魔法制造纸币解决帝国经济危机,有招魂海伦娱乐宫廷;第二幕有精灵的催眠,有以炼金术和魔法炼制人造人,带领主人公前往“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第三幕的核心是浮士德和海伦穿越时空相聚;第四幕第二场军事作战中,除水漫金山、海市蜃楼等多种魔法外,还出现水晶球占卜、古代军事作战中常见的鸟迹占卜;第五幕有梅菲斯特指挥部下挖掘运河以建设海外掠夺通道,或挖掘排水沟以拦海造陆改造自然。
很显然,这些秘术要么充当情节发生的动机,要么构成所在场幕的贯穿或核心情节。从舞台演出来看,它们制造出悬疑、惊悚、光怪陆离、滑稽的效果,与作品中的严肃思辨和壮美抒情穿插,既提供丰富体验、满足猎奇心理又深化主题。
这些场景,即属于那些出于“习惯”或“无知”,为《浮士德》注疏所忽略的片段。它们长期湮没在理念史或意识形态建构式的解读中。因为这些统称为秘术或神秘知识的东西,乃是自18 世纪启蒙以后,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为确立自身地位、界限和合法性——所要系统扫除和彻底批判的“他者”。200 余年的抑制和贬斥,导致对它们的普遍误解和无知,无知又导致习惯性忽视。
20 世纪70 年代后的自然科学史研究认为,神秘学或秘术,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中与信仰、理性并立的一足;是与宗教传统、理性哲学和现代科学并列的一个维度;它们尤其与经验、实验科学,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其发生,从古代经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建立在对宇宙和神的思考与探索之上。对于这一领域的特质、规律、形态、历史作用及潜藏的危险,歌德的《浮士德》提供了全面而生动的图解。
继而,在19 世纪上半叶,建立在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之上的现代学科分类出现后,秘术因其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特质,成为鲜有人问津,处于科学研究、公共话语边缘的“学术上的无家可归者”。《浮士德》在这个意义上又可谓一个集大成的收容所。
再看《浮士德》上部,盘点作为第一单元的“学者剧”,会发现,它连贯上演了多种秘术,换言之,神秘学知识几乎依次贯穿所有场次:开场中,浮士德决心转向魔法,他翻开秘术典籍,念符咒召唤土灵显现并与之对话;“城门外”一场,与浮士德书斋中摆满的炼金术器具呼应,具体谈到如何以炼金术制药以治疗瘟疫;“书斋一”一场,浮士德念四大元素咒、基督教的驱魔咒令梅菲斯特现身,梅菲斯特困于辟邪的五角星;“奥尔巴赫地下酒馆”中,梅菲斯特施魔法变酒并施定身术脱身;“女巫的丹房”一场自不待言,有镜像占卜,更有女巫炼制让人返老还童的催情丹药,在递与浮士德饮用时,戏仿教会仪式,上演了整套巫术咒语和黑弥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由上述盘点可见,同时也是众所周知,神秘学是一个“复杂到鱼龙混杂”的庞然大物。本文无法论及《浮士德》剧中所有可归为秘术的场景,而只聚焦上部学者剧中与自然哲学和经验科学相关的片段,具体说是聚焦有益的,并为正统教会和“科学之母——神学”所宽容的自然魔法和炼金术。《浮士德》客观再现了这两种秘术在16 世纪至近代早期的形态,给予了它们应有的关注和肯定。另一方面,学者剧也充分暴露,脱胎于经院和形而上学的经验和自然科学,自近代繁荣之初,便带有脱离“心灵习性”和“理智德性”的倾向,与宗教和道德分离,它们引发的无限认知宇宙的欲望,进入私人领域,转化为归纳法式的体验世界的追求,借助魔鬼提供的无限可能性,使科学成为追逐物质利益、实现权力意志的手段。
一
自然哲学、自然科学勃发,在近代经历了两次高潮。16 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前后是一次,18、19 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时期是第二次。第一次的特征,是自然魔法、占星学、炼金术等摆脱形而上学,借助经验和实验,开始向自然哲学、自然科学过渡;第二次的特征,是统称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问,借助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向现代学科分类的转化。歌德的《浮士德》,一则因为主人公所处时代,二则因为作者生平,恰与这两个阶段、两次高潮合拍。
《浮士德》的同名主人公,其历史原型格奥尔格·浮士德(约1480—1540)与马丁·路德(1487—1546)生活在同一时代,人称神学博士、炼金术士、魔法师和占星师。这是15—16 世纪现代学科分类出现前,博学之士通常被冠以的名号,同时也符合他们的实际身份。作为戏剧人物,浮士德明显综合了阿格里帕(Agrippa von Nettesheim,1486—1535)、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1493/1494—1541)、皮科(G.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诺斯特拉达姆斯(Nostradamus,1503—1566)等同时代神秘学大师的生平和学说。同时学者剧尚直接提及、间接影射了当时多位著名医生、炼金术士和占星师。
而歌德(1749—1832)本人生活在18、19 世纪之交,作为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他的色彩学、光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质学研究,见证了从博物学向现代自然科学的转化。与歌德同时,瑞典人斯威登堡(Swedenborg,1688—1772)的神智学和灵异说,德国医生梅斯梅尔(Mesmer, 1734—1815)的动物磁力学、德国医生凯尔纳(Kerner,1786—1862)的实验心理学和催眠术,连同其中所包含的自然哲学、自然神学、泛智学,方兴未艾。《浮士德》本着人间大戏、包罗万象的宗旨,对上述神秘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交错引用,仿佛唯恐不能将之尽数搬上舞台。
总体上讲,《浮士德·下》因创作时间晚(主体在1825 年以后),多呈现18、19 世纪之交神秘学和自然科学景观;《浮士德·上》更贴近16 世纪的样貌。具体而言,本文所探讨的学者剧,其基底成文于1770 年代,是歌德最早提笔创作的部分,因直接取材当时仍在流行、讽刺历史人物浮士德的傀儡戏而以16 世纪话语为主;同时——尤其在1780 年代续写的部分——掺入了18 世纪下半叶善感文学、狂飙突进文学的观念和语言,而两者,即16 世纪的神秘学与18 世纪虔诚运动引发的善感文学,在情感体验、自然观、通灵思想上本就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就造成浮士德前后台词之间,甚至一段台词内部,存在时空错位、时空穿越的片段。
学者剧的开场已为通盘定下基调。舞台提示:在“高拱顶、狭窄的哥特式房间”,浮士德“不安地坐在写字台旁的扶手椅上”。其中“哥特式”,是一个集时间和建筑风格为一体的概念,表明这是一个中世纪以后经院学者的书斋;“不安地”则进一步暗示主人公已步入近代(所谓“新时代”),躁动不安以及由此引发的怀疑和追求,是这个新时代的表征,也是浮士德最为明显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整部《浮士德》剧上演的即是浮士德受此“不安”驱使,追求“天上最美的星辰”“地上极致的兴味”(第304—305 行)的一生,直至他在第二部第五幕为实现个人意志、获得极权统治而“狂躁不安地”剪除一切异己。
浮士德,或曰近代早期学者,其所有辩证发展轨迹即肇始于这个“不安”:受“不安”驱使,他们不满足于经院和形而上的知识,开始转向自然魔法——在当时属于被宽容和允许的秘术,也是现代经验和实验科学的前身,——从而启动了自然科学发展进程;同样受“不安”驱使,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作为手段的经验和实验当作终极目标,以归纳法追求无限认知和体验,导致求助魔鬼拓展其超自然的可能性,使知识和智识背离信仰和道德约束,转而服务于恶。
在著名的开场独白中,浮士德首先称自己“把那哲学,/法学和医学,/可惜还有神学,/统统学了个遍”,(第354—357 行)意即他修习了当时大学所有科目:作为各学科基础的“自由艺术”(哲学)以及三门正式和正统学科——法学、医学以及最高级的神学。“可惜”与下文呼应,加强语气,极言其尽管学习了最高学问却仍自感一无所知。浮士德作为学者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兀兀穷年,名义上获得“硕士”“博士”头衔,又担任了十年教师,到头来却发现“我们什么都不可能知道!”(第364 行)
准确地说,这段台词描摹了15—16 世纪学者所面临的困境,符合历史上浮士德的身份和处境。首先彼时的知识尚未膨胀到不可总揽的程度,也无后来严格的学科界限,一位博学之士尚可做到通盘研习。其次,所谓“什么都不可能知道”,特别指无法知道形而上学以外的知识。因当时的学问处于经院传统,哲学等同于“逻辑训练”,法学专注于罗马法注疏,神学的核心同样是对圣经和教会典籍的注疏,也就是说,所有正统学问都在那些“高高摞到拱顶”,“熏黑的羊皮纸卷”中。
而以浮士德为代表的近代早期学者显然已经意识到,逻辑推理不可能产生新的知识,典籍注疏不可能满足近代萌发的对宇宙、对自然万物在物质和客观意义上的探索和认知。亦即,用中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经院方法,以形而上的路径或书本知识,无从认知如下文台词所言——“是什么从内部把世界联系在一起”。这句关键表述实际引用了皮科的说法,代表了那一代人的追求。为获得如此“真知”,其所需要的方法和手段在学院中尚处于缺位状态。就当时来讲,即便距自然科学最近的医学,也还停留在以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为基础的盖伦医学传统。
而另一方面,由浮士德书斋陈设可见,近代科学亦萌芽和诞生于旧日的经院环境。学者剧准确描摹、历史再现了发轫时期各学科不分彼此的胶着状态:除墙上的书卷,地上还堆满“烧杯、烧瓶和插满流管的仪器”(第406—407 行),其中散落“兽骨和人骸”(第417 行)。除正统典籍外,浮士德手边显然还摆放着诸如“诺斯特拉达姆斯”的著作和《所罗门咒语》之类的魔法秘籍,以致他在后面的情节中信手拈来。神秘学著作、炼金器具、医学标本大约均属于16 世纪学者书斋的标配,表明主人已特别关注魔法、炼金和解剖等实验学问。
反之亦见,近代最早从事自然和经验科学的人,那些17—18 世纪自然哲学家、科学家的先祖,即是这批学贯神学、法学和医学的学者。他们的学问,近代早期发轫之际的自然科学,必定发生在神学和形而上学指导之下。只是浮士德们显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更进一步:使科学摆脱神学和形而上框架,获得进一步独立和自律。因据科学史考录,在神学和形而上学框架中,实验的目的首先为印证神的意志、宇宙规律和创世法则,而不在于发现新事物或新规律。实验本身尚不针对“科学”意义上客观、物理和活生生的“自然”。
于是浮士德决定投身“魔法”。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魔法,指16 世纪后为正统教会和世俗机构所宽容的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尚未过渡到梅菲斯特出现后的魔性魔法(maleficium,schwarze Magie)。16 世纪的魔法学把魔法大体分为两类:具有神性的自然魔法和具有魔性的魔性魔法。后者在民俗中也称黑魔法,是起破坏作用的巫术和作祟之法,自中世纪以来被认为是与魔鬼结盟的产物,为教会和世俗机构所禁止。自然魔法则接近魔法原初的本质,本为关于神的认识,属于神圣的知识,是自古以来用于探究宇宙奥秘并试图对宇宙超验力量施加影响的方法。只是这些知识、认识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为当时的科学所解释,不能为实验所证明,不能为逻辑所论证,因此是神秘的学问,属于秘术—神秘学范畴。
《浮士德》学者剧所涉及的自然魔法,主要基于古希腊尤其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整体和万物有灵论。根据这种看法,宇宙是一个整体,万物之间相互“作用”,人作为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存在通感;万物有灵,宇宙自然和人之间因通“灵”之故,可借助“直观”和“直觉”进行沟通。在这个意义上,浮士德转向魔法,便是如其所言,试图“借助精灵的力量和嘴巴”,捕捉“自然”的“心灵力量”(第423—424 行),或通过“灵与灵的交谈”(第425 行),认识世界内在关联,“直观所有作用力和根源”(第377—384 行)。可见就“与时代史、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关联”来讲,《浮士德》的开场独白,表达的即是16 世纪学者,从经院-形而上学-神学,转向自然魔法-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冲动,预示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由逻辑演绎向经验科学、由从静止出发到关注运动、由演绎法向归纳法的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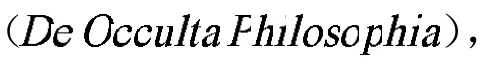
在转向魔法后,浮士德打开“诺斯特拉达姆斯的秘籍”,顿时“感到”有“精灵”在身旁飘荡,观之“大宇宙的符号”他“倍感”神清气爽。他终于“感觉”到人与世界的关联:“精灵的世界并没有关闭”,只不过此前他的“感官封闭,心已死去”。是魔法打开了浮士德的感官和心灵,帮助他抛开逻辑推理、形而上的演绎,直接与自然交流,在“朝霞”中“沐浴尘世的胸膛”(第444—446 行)。“他盯着魔法书中的大宇宙符号”(舞台提示),狂喜地发现:
万物是怎样编织成整体,
相互赋予生命引发运动!
上天的力量是怎样沉浮,
金色水桶是怎样相互传递!
满载馨香祝福的翅膀
从天而降穿过大地,
万物和谐地在宇宙回响!(第442—453 行)
短短数行,营造出一幅生动的魔法-自然哲学之宇宙图解:宇宙整体论(“万物编织成整体”)、相互作用和联动说(“相互赋予生命引发运动”)、上天的力量上下传送(“上天的力量沉浮”)、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金色水桶相互传递”)、神性的赐福和移觉(“满载馨香祝福的翅膀”)、毕达哥拉斯-乔尔吉亚的宇宙和声(“万物和谐地在宇宙回响”)——所有生命和运动、上下运行和相互作用、色香声音等感官感知,共同打破形而上学静止的认识,以诗的象征语言汇聚一处,既呈现自然哲学对宇宙的想象,也描摹出不同学说之间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关系。
从对现状不满,决心投身魔法,到从秘符获得丰富想象,接下来,与灵面对面交流,直接获得真知和奥秘便顺理成章:“浓烟升腾”,“红光闪烁”,浮士德“神秘地”念动符咒,土灵(土元素之灵)现身——歌德曾亲手绘制土灵“火焰身形”的草图——与浮士德开始“灵与灵”的对话。在此,《浮士德》学者剧出现第一个热烈、神秘甚至惊悚的戏剧性高潮。对自然魔法的呈现也就此告终。
二
与自然魔法相比,炼金术在宇宙观、认识论、研究路径方面有着类似前提和共通之处,两者相辅相成。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炼金术有系统和完善的类宗教或准哲学的指导思想,其秘传典籍同样卷帙浩繁。炼金术在古希腊和古代东方世界都很发达,中世纪晚期阿拉伯炼金术传至欧洲,引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炼金术繁荣。与浮士德同时代的著名魔法师,几乎都同为著名炼金术士。学者剧在紧接下来的“城门外”一场,记录和呈现了另一秘术传统——作为现代化学、实验科学前身的炼金术。
15—16 世纪炼金术士的典型形象、具体工作和所面临的困境,剧中借浮士德对父辈的讲述,予以了丰满呈现。与书斋所陈设“先祖”的炼金器具相呼应,浮士德回忆起父亲的身份和职业:“家父是一位神秘的绅士”,抱着“诚实的态度”,却“以独特的方式”,通过“异想天开的努力”,去“思索自然及其神圣的领域”;他“加入炼金术士的秘契,/把自己关闭在黑厨房里,/按照不计其数的方子,/把相克的物质倒在一起”(第1034—1041 行)。
该段讲述首先颇具代表性,描述了炼金术士在时人眼中既高尚又可疑的矛盾形象:他们一方面是令人尊重的绅士,对自己的职业抱诚实态度,工作目标是高尚的探索自然及其神圣领域。这无疑为炼金术士的身份和职业赋予了充分正当性;另一方面,“神秘”、晦暗、特立独行、“异想天开”,又贴切再现了外界对他们的普遍怀疑和负面评判。其次,讲述特别指出炼金术士的秘契性质。这大概如同今日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炼金术行当,各门派均以秘符记录实验成果,以秘传方式传授门人。接着,台词简要勾勒出炼金术士工作的实验性质:他们在“黑厨房”——现代称“实验室”,按不计其数的“方子”——现在称实验方案,把各种物质加以混合,以备蒸馏、萃取、挥发、结晶等下一步流程。其中“不计其数”用了夸张的修辞,但也暴露出实验的归纳法特征,以及实验者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
《浮士德》学者剧对炼金术的再现,并未停留于点到为止,也未流于庸常的俗套,而是扎实地给出了一个知识性的历史记录:
红狮,勇敢的求婚者,
在文火中与百合结合,
随后把两者用明火
从一个洞房煎熬到另一个。
接着伴随斑斓的色彩
曲颈瓶中显现年幼的女王,
这即是药品……(第1042—1048 行)
从语言风格到过程描述,这是一段极为经典的炼金过程记录:把“红狮”,红色、阳性的氧化汞,“勇敢的求婚者”,与“百合”,白色、阴性的盐酸(或盐酸与氨合成的白色烟雾),放入蒸馏罐(曲颈瓶或提纯锅),用文火化合。炼金术通常将阴阳性的物质的化合,比作国王与王后的婚配;然后再用明火“煎熬”,此言进行蒸馏,形成的混合气体从一个曲颈瓶(洞房)进入另一个;气化后的固体在另一个曲颈瓶内壁凝结,是为彩色沉淀,等于经过明火提纯的汞盐结晶,炼金术语称之为(国王与王后诞育的)“年幼的女王”,药物制成。
引文以炼金术特有的隐喻、寓意、象征性语言,既晦涩又诗意地记录了一次化合、分解、蒸馏、挥发、固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未经秘仪入门者无法窥其堂奥。但同时也可以看到,除秘传要求外,这种语言包含了另一种在今日科学话语中陌生的对世界的理解。红、白等斑斓的色彩,描绘出一个彩色世界;化学过程,通过隐喻与动植物等自然界生物、人类男女婚配,继而与国家政治领域联系在一起;自然科学中的文火、明火,与人类社会的温和、炽热形成类比;化学的蒸馏带有了人受“煎熬”的情感……可见在近代早期,自然科学滥觞之际,炼金术士与魔法师等前现代科学家,尚把宇宙自然与人以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通过隐喻、类比、寓意、象征相互映照,遵循共同的法则和规律。
炼金术有史以来通常设有两大目标,一是变贱金属为贵金属,二是研制延年益寿的丹药,故而从中衍生出冶炼和制药两大实际功用。在实际操作中,炼金术以术为主,是经验和实验科学的前身。歌德在演示16 世纪炼金术制药功能的同时,也揭示出实验科学的危险在于其结果的不可控性,这也是炼金术士所面临的困境:为治疗瘟疫辛苦研发的药物,很可能具有奇效,如剧中被治愈的农民,世代把浮士德父子奉为圣人和神明,感恩戴德;但更有可能成为“地狱般的膏剂”、“猛于瘟疫”的“毒药”,致使千万人丧生,如浮士德汗颜地自认为他父子不过是“无耻的凶手”(第1055 页)。这何尝不是现代实验科学、现代科技仍然要付出的代价和仍然要共同面临的困境。
歌德对炼金术的态度,有尊重和认可,也有怀疑和批判,两方面都建立在他对这门学问全方位的认知之上。歌德的文学自传《诗与真》记录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对炼金术持续的关注。1768 年歌德因病中断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回法兰克福父母家休养。其间他从通晓炼金术的医生处获赠一种“秘密自制”的“万灵药”,并得知“神秘的化学的兼炼金术的书籍”,包括韦林(Welling)的《大卡巴拉》(Opus mago-cabbalisticum,1721 年写成,1735 年出版)。时年19 岁的青年歌德因服用如此研制的药物治愈了重症,后便在家中设置了一个小型实验室,进行炼金术试验:
我就已经开始装设好一套小小的仪器,安着一个带有砂浴器的小风炉。我很快就学会用炽红的火绳,来将玻璃管变做曲的直的容器,各种混合的药品都放在容器中蒸发。然后将“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特别的成分玄秘地奇怪地来调炼,特别是用一种闻所未闻的方法来制出中性盐。[以下详细描写制作硅盐酸的过程]
由《诗与真》的表述可知,歌德清楚知晓炼金术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关系,他既研读帕拉塞尔苏斯和瓦伦汀(Valentinus)等大家作品,也关注海尔蒙(Helmont)和施塔凯(Starkey)等其他门派的代表,并努力寻找各个学说建立在“自然和想象”上的理论和原则。“红狮”和“百合”之说即受到韦林等人著作的启发。《诗与真》中老年歌德带有反思的回忆,为揭示《浮士德》与炼金术的关联提供了实证和自证。
就此话题需要特别指出,关于炼金术的具体描述,尚未出现在《浮士德·早期稿》(1772 或1773年)中。因根据历史传说,浮士德出身农民而非炼金术士之家,其他文献、文学作品中也查无此据。歌德笔下早期学者剧的雏形本围绕以通灵为特征的魔法展开。歌德实则在1795 年后——恰好在所谓古典时期——增写了这段虚构的浮士德身世,并且不惜笔墨,前后分别进行了大段铺垫和评价,究其意,显然在于要特别记录和探讨炼金术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客观上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近代自然科学的面貌,由此使近代学者的形象更加丰满,一方面也公开演示了实验科学的问题和危险。
三
在《浮士德》学者剧中,歌德先是以近乎中立的态度,历史地呈现了作为经验和自然科学前身的魔法和炼金术。浮士德的形象和言说,综合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代大师的身份和思想。就这点来讲,歌德冲破了历代以浮士德为素材的文学戏剧所遵循的道德说教框架。因为无论哪个版本的浮士德故事书,还是以马洛的《浮士德悲剧》为底本的流动剧团演出,抑或是民间流行的浮士德傀儡戏,无一例外,均一上来就把浮士德当作离经叛道的黑魔法师,令其与魔鬼歃血契约,并最终将其置于万劫不复的结局:“浮士德,厌烦了金色的/智慧的恩赐,投身/魔鬼的技艺,接受了/秘术,没有比魔法/更喜爱的东西,为之竟至把最重要的:/自己心灵的福祉,唾弃。”歌德显然并未照搬这一传统套路。
历代对浮士德素材的演绎,其形态取决于文学在近代的功能:文学一方面充当传播知识的媒介,一方面服务于寓教于乐的宗旨。因此黑魔法之说,以及借助它开启的丰富想象,满足了近代读者对知识的猎奇和对娱乐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类作品必须起到警示作用。因在各正统教会、世俗机构看来,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萌芽,很容易与灵知主义结合,导致偏离或背弃理性和正统信仰,进而引发社会的混乱和无序。自中世纪晚期,学者与魔鬼结盟的模式,在大众心态中得到普遍认可,成为阅读或看戏的普遍期待。
歌德的塑造既在正统教俗框架中,又不囿于此,而是同时立足启蒙人文主义立场。换言之,到了歌德《浮士德》的学者剧,魔法、炼金术母题,方才摆脱浮士德素材的单一模式,其中一部分得到正面、带有同情色彩的描述,并被赋予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然而与此同时,歌德也辩证地呈现了自然科学在近代发轫之际所携带的危险。导致危险的,是经验科学的引入及其合法化,直到它置换形而上学,占领独尊和统治地位;另一方面,经验科学所依靠的归纳法,从手段转变为目的,由此释放了被禁锢的欲望,引发人对无限可能性的追求。对其推波助澜的,是近代与之发生共振的世俗化和私人化:经验、欲望、无限追求,逐渐从对宇宙的认知,转移到对世俗世界的体验;从教会和世俗的公共知识领域,进入私人领域,与个体私欲和感性经验相结合,导致原本受道德约束的感官体验、物质占有欲、权力欲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而在这些领域追求无限可能性的做法,在人文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正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不同于中世纪意义上的撒旦。梅菲斯特诚然同样是恶的化身,诱惑浮士德作恶,但相比之下,他的功能更在于提供无限可能性,助力主人公满足归纳法式的感官体验,刺激其更大的对情爱、物质、权力的欲求。魔鬼的这一形象和功能,在16 世纪浮士德故事书中已见端倪,200 年后,在18、19 世纪之交歌德的《浮士德》中,变得更为清晰,得到进一步强化。也就是说,学者剧后面的部分尤其《浮士德·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法术,毫无疑问是作祟之法,但它们首先服务于浮士德“永无休止、毫无约束”的“追求”。
从另一角度讲,鉴于歌德对积极意义上秘术的宽容,转向魔法并不意味一定引发与魔鬼的契约。《浮士德·早期稿》并未出现与魔鬼契约的情节,即传统意义上的魔鬼母题本身并非歌德最初关注的对象。这从反面证明,魔鬼、黑魔法之所以必须出现,是因为其作为手段的必要性。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经验作为新的认知方法,陡然与私人领域、与感性体验联系在一起,进而成为目的本身。这种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换,待至歌德时代,经历了善感运动、狂飙突进后愈加凸显。回顾上文讲到的浮士德面对“大宇宙符号”发出感慨一段,其中反复出现“感觉”一词,简直夸张到反讽的程度。该词严格讲并非历史概念,而是歌德时代善感运动的关键词。它在上下文中,一则指示自然魔法与经验科学的关联,一则提醒,16 世纪普遍意义上的经验,已过渡到18 世纪强调个人体验的“感觉”。
这样,按照逻辑,经验科学的归纳法也将顺理成章进入私人领域,与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浮士德并未真正展开自然科学研究,而只是把其方法转用于纯粹的“感官享受”和“火热激情”。(第1746—1751 行)魔法不过充当了从书本到“感官享受”的跳板,符咒不过松绑了被约束的“火热激情”。因此浮士德一旦走出书斋,走进自然,感觉到胸中另一个“灵魂”(即感性的灵魂),或一旦告别羊皮纸卷,走出形上世界,进入庸常生活,魔鬼便出现并成为受欢迎的黑色“贵宾”。浮士德从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感性诱惑驱使他完全放弃理性、科学、知识、思考等“人类至高无上的力量”,转而求助于“炫目的魔法”和“欺骗的精灵”,因为只有魔鬼的魔法才能满足他无休止的欲望和追求,刺激他翻陈出新,继续寻找新的目标。在这样的机制中,诚如梅菲斯特戏谑的结束语所言:
即便他没有把自己交付给魔鬼,
也终将彻底毁灭!(第1856—1867 行)
引发危险的关键其实在开场独白中就已暴露无遗。如果说浮士德此前的学习是为获得真知,工作是为“教人从善如流、皈依正途”(第372—373行),也就是说,其学院生活、学术事业乃至科学实验,还保留了传统意义上对真理的追求、对心灵的教化,那么他一切新的努力和尝试的前提,则是毫无顾忌、毫无操守地背离宗教信条和道德操守,因为:
没有什么顾虑和怀疑让我不安,
也不惧怕地狱和魔鬼——(第368—369 行)
在这个新时代学者豪迈的宣称中,所谓没有什么“顾忌”和“怀疑”让人不安,所谓“不惧怕地狱和魔鬼”,便是表明要为所欲为地去实现个人意志。与此同时,他意识到并且自嘲“一无财产二无金钱”,“没有世间的光鲜和荣耀”,看似程式化的讽刺的戏言,却表明,物质财富、权力地位将成为追求的目标。
依此逻辑,待至《浮士德·下》,时间过渡到19世纪初,此时科学中“物质事实的领域”进一步与“道德和宗教价值的领域”分离,科学离其“心灵习性”和“理智德性”的品质越来越远。在下部中,魔法和炼金术不仅成就了人造的“小人”荷蒙库勒斯,而且成就了“纸币”。魔法和炼金术已逐级冲破科学的一切伦理界限,自行其是,最终成为追逐物质利益、满足权力意志的手段——曾经被神学和形而上学抑制的、作为秘术的“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世界的神秘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