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刘永济屈赋考据的人文性与科学性
陈文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刘永济的屈赋考据,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偏于人文性的阐发,常常并无铁证,如关于屈赋作品的认定和部分字句的改动;第二类则以科学性见长,包括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内容,他的几个主要成果,如《屈赋通笺》各卷的“正字”、“审音”、“通训”各节,以及《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两部专书,集中显示了他在考据和语言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其屈赋研究得到闻一多、游国恩等大家的激赏,主要是在第二个方面。
刘永济 屈赋 考据 人文性 科学性
刘永济所说的“屈赋”,学者们通常称为“楚辞”。从辨体的角度看,屈原所作乃诗人之赋,属于诗的范畴,汉人所作乃辞人之赋,介于诗文之间,两者的文类差异是鲜明的,称之为“楚辞”,有助于显示它与辞人之赋的差异;从溯源的角度看,屈原之作源于六艺之赋,而屈宋之作又为汉赋之祖,所以,称屈原的作品为“屈赋”,也有充足的学理依据。
从事屈赋研究,不能不涉及考据,而考据又是屈赋研究中的困难所在。盖无论是屈原的作品,还是屈原的生平,均疑点甚多,而又难于找到确实的证据。刘永济《研究屈赋之困难及由此而生之疵病》对作品研究和作者研究两重困难有过切实说明:“吾人今日研究屈赋有根本困难二:其一,屈子生于二千二百余年之前,尔时楚国文字尚有与秦文不同者,其作品当由秦汉学人搜集流传,至汉代方写以篆隶,嗣后复由篆隶而行楷而草书,传至赵宋,始有雕本。宋代雕本复经后世翻刻,始有今日通行之本。宋以前写本固不可见(洪兴祖《补注》中间引唐本作某,可见南宋尚有存者),即宋代刻本,亦极难得。在此漫长之时代过程中,其文句之讹夺,音义之变化,篇章之移易,解说之纷歧,殆难指数。即其文中所用鸟兽草木之实,与夫山川县邑之名,亦已几经改更,难于稽考。此关于研究作品之困难也。其次,则楚国史籍,如古所谓楚之《梼杌》者,已无只字留存,所资以考信者,惟《左传》《国语》《国策》下及太史公书数种而已。此数种中,欲求明了楚国之社会经济情况,与其上层建筑之政治文化,亦无充分之资料,尤于屈子生平事迹,记载殊为缺略。即如屈子在政治上之失败,最初由于修宪令,而屈子所修宪令内容,却无一字记载。又如屈子究系先疏绌而后放逐,抑或两度被放?其疏绌与放逐缘于何事?确在何时?其各篇作品究竟成于何年?先后次第如何?今传二十五篇之中,孰为屈作,孰非屈作?凡此种种,皆研究所必须决定者,亦无从确实考证。此又关于研究作者之困难也。”
刘永济的屈赋考据,直面“研究作品”和“研究作者”两重困难,努力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表现了一个杰出学者的风范。所涉内容甚广,凡“屈原的思想行谊、楚国的历史背景、屈赋的成因发展,以及古今各注家的解说是非、古今各传本的文字同异”,均在其关注范围之内。其作者研究,此处不论。就作品研究而言,主体则是下述两个方面:1.现存汉人所谓的屈原作品,哪些真是屈原所作,哪些并非出于屈原之手?2.屈赋文句的审音、训诂和语法研究。前者以人文性见长,后者则以科学性见长。
一、刘永济关于屈原作品的鉴别以人文性见长
刘永济认为,现存汉人所谓的屈原作品,是否应该归在屈原名下,确有重新加以鉴别的必要。理由在于:1.汉人之所以将若干作品归在屈原名下,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作品所传达的理念、感受和情绪,与屈原是一致的;但汉人也可能有误解之处,“盖古人之学,风会不同,未可依据,一也”。2.现存的所谓汉代典籍,许多已非原貌,不一定能作为依据。比如今本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其编辑相传出于刘向之手,有目录所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为证。但王逸《楚辞章句》是否刘向原本,疑点甚多。“此书有一最不可解,启人怀疑者,乃王逸《九思》一篇。据说这篇是进呈御览时后人把他并入十六卷中,标明汉侍中南郡王逸叔师作,也加上注解,成为十七卷。现在要问:这个十七卷是不是即刘向原编?一也。作为十七卷加入王作者为何人?二也。再为《九思》作注者据传是王氏本人,又或以为逸子延寿所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然注中于《逢尤篇》‘思丁文兮圣明哲’句,误以‘当’训‘丁’,不知‘丁’为武丁,与‘文’为文王,皆举二人言也(顾炎武《日知录》亦举此为说)。王氏父子绝不至此,然则究系何人?三也。”“除此之外,洪兴祖《补注》于目录后附一按语曰:‘“按《九章》第四,《九辩》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序之。’洪氏此段既知《释文》(洪氏曾见古本《释文》)篇第为旧本,又说‘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序之’,可知今传王逸本非其旧,一也。后人有改编,二也。”既然如此,重新鉴别哪些作品应该归在屈原名下,哪些作品并非屈原所作,就是必要的了。而鉴别的依据,除了“详究训诂,精核名物”外,知人论世也是一个重要方法,即“由骚辞求索屈子之情思学术,证以楚国之士风,怀襄之时事,旁及后贤疑难诸说”。并据以确定作品的著作权。刘永济的结论是,属于屈原的作品共十篇:《离骚》《九辩》《九歌》《国殇》《天问》《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其他传为屈原的作品并非屈原所作。其结论可能引起的质疑至少有五个方面:1.《九辩》多以为是宋玉的作品,何以定为屈原之作?2.《九章》的后四篇即《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何以被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3.《国殇》何以被排除在《九歌》之外?4.《远游》何以被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5.《招魂》何以被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刘永济确认屈赋篇目,虽也采用了大量传统的考据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铁证不多,往往要依赖“内容和风格”的考察即知人论世的途径来加以说明。清代的姚鼐曾大力推崇“内容和风格”的考察,而对乾嘉考据颇有微词。其《尚书辨伪序》在肯定考证以确凿的证据说话,“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的前提下,更强调风格领悟的魅力,“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钱钟书《管锥编》也曾以“张翼德书法”为例,调侃了所谓“铁证”,而认同“内容和风格”的辨识。风格有时确乎比事实更有力度。从内容与风格的角度来确认作品的归属,并非没有可行之处。但另外一个情形也有必要予以留意:内容和风格的领悟总是与读者的主观体验结合在一起,不同的读者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且同一作者也可能兼长多种风格,而在不同的境遇之下,或志在兼济天下,或向往独善其身,均有其心理的真实性。不同的读者因其知识背景、人生阅历、所处境况的差异,有时不免见其所见,以致各持一端。比如关于《远游》著作权的论证,见仁见智,各种不同的说法即各有其理,或者说,都能自圆其说。
20世纪30年代,刘永济撰《屈赋通笺》,其绪论之三论“屈子学术”,明确将《远游》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他认为:“《远游》一篇,有道家高举之意,不类屈子之言。且全文因袭骚辞文句,至三之一。其为后人所作,殆无可疑。世之读屈赋者,久感其情辞菸邑,喜此篇宏放旷荡,乃曲为之说,而不悟其非,谬矣。虽然,屈子亦自有宏放旷荡,而无方士服气炼形之意。”后来他又写了专题论文《屈子非道家〈远游〉非屈子所作》,系统反驳了王逸、朱熹、王夫之、刘师培、梁启超等人的种种推论,而继续坚持他对屈原学术与人格的基本判断:“虽然,如谓屈子于道家理论懵然无知,则亦不然。此如骚辞设为女媭之责骂,与楚人叙辞相传之《卜居》《渔父》二篇,固皆道家之言也。惟屈子秉性贞刚,其学术思想又受北方儒学之影响,加以救国之情极其热烈,疾恶之心复至深切,与道家轻视现实之旨趣不合。而其时国中上下,则多被道家末流所化,其甚者,遂颓废放浪,苟且偷安,形成听天由命之消极思想,尤为屈子所疾视而思挽救之者。今乃以道家品目屈子,岂不冤哉。况《远游》篇中所具之思想,已非纯粹道家,而与秦汉方士飞升之说相同。”刘永济所理解的屈原,学术正大,品质贞刚,他不能接受任何把屈原庄子化甚至道教化的解读。如果刘永济只是坚持这一学术立场,倒也无须特别加以表彰,其建树在于,他就此做了富于学术魅力的论证。连一向乐于调侃刘永济的苏雪林也说:“陈钟凡怀疑《远游》有许多话与《庄》《列》《淮南》诸书合,乃谓《远游》出于依托。《远游》的道家思想果然浓厚。但陈氏并未举例。陆侃如、游国恩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理由。只有刘永济的《屈赋通笺》,有《屈子学术》一篇,谓屈子学术乃纯粹出于儒家,与道家并无关系。”苏雪林还完整引用了刘永济《笺屈余义》中的《屈子非道家〈远游〉非屈子所作》一篇的主体部分,喝彩道:“这番话说得沉着痛快,掷地有声。”在断言《远游》非屈原作品的学者中,刘永济的论述无疑是最有学术分量的。
刘永济从内容和风格角度将《远游》著作权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其立论虽得到苏雪林等的喝彩,却也不一定能为所有的学者所认可,原因在于,刘永济并无铁证,其论述偏于人文性的阐发。比如,梁宗岱在他写于1934年的《谈诗》一文中,就曾慷慨激昂地断言《远游》为屈原作品:
记得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有人要证明《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其中一个理由便是屈原在其他作品里从没有过游仙底思想;在《离骚》里他虽曾乘云御风,驱龙使凤以上叩天阍,却别有所求,而且立刻便“仆夫悲,余马怀兮”……回到他故乡所在的人世了。
我却以为这正足以证明《远游》是他未投身于汨罗之前所作——说不定是他最后一篇作品。
因为他作《离骚》的时候,不独对人间犹惓怀不置,即用世的热忱亦未消沉,游仙底思想当然不会有的。可是放逐既久,长年飘泊行吟于泽畔及林庙间,不独形容枯槁,面目憔悴,满腔磅礴天地的精诚与热情,也由眷恋而幽忧,由幽忧而疑虑,由疑虑而愤怒,……所谓“肠一日而九回”了。曰《渔父》,曰《卜居》,曰《悲回风》,曰《天问》,曰《招魂》……凡可以自解,自慰,自励,怨天,尤人的,都已倾吐无遗了。这时候的屈原,真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了。“从彭咸之所居”,是他唯一的出路了。
然而这昭如日星的精魂,能够甘心就此沦没吗?像回光返照一般,他重振意志底翅膀,在思想的天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要与日月争光,宇宙终古:这便是《远游》了。
读了梁宗岱的这段文字,一定有不少读者宁可将《远游》放在屈原名下,否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怅惘和失落感;当然也一定仍有部分读者坚持不能将《远游》视为屈原的诗,在他们看来,屈原怎么会有这样浓郁的出世之思?这两种不同的判断,都建立在内容和风格的体验之上,但又都拿不出铁证,作为考据,都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因而也无从说服对方。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两种推论却又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即加深读者对屈原的了解。矛盾的双方其实都在辨析的过程中走近了屈原,读者也在倾听双方的辩论时走近了屈原。所以,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们的结论,但他们所作的内容和风格的探讨,自有其历久弥新的意义。英国哲学史家罗素曾在其《西方哲学史·绪论》中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深入地研究问题而不一定提供确切的知识或教条,这是哲学的特点和价值所在,也是一部分文学研究的特点和价值所在。如果表述得更贴切一些,不妨说,这类文学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哲学研究。在关于屈赋的考据中,这种着眼于“内容与风格”的论证,其实不宜以考据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而应充分关注其人文性,关注其对读者视野的拓展和启迪。这种着眼于“内容与风格”的论证,其实是一种阐释,对它的衡量标准是是否深刻睿智,而不是是否确定无疑。因而,刘永济和梁宗岱虽各持一说,我们却不妨都加喝彩。
《九辩》一篇,自东汉王逸断为宋玉所作,后人多信从不疑。直到明人焦竑,强调《九辩》为屈原所作(《笔乘》卷三),宋玉的著作权开始发生问题。不过,主宋玉说仍占多数。刘永济从辞情与南迁时序两方面进一步肯定了焦竑的观点,将《九辩》的著作权归于屈原名下。他的这一结论曾受到其挚友席鲁思教授的质疑,理由是《九辩》的寒士口吻和“儒酸气”与屈原的贵族身份不合:“篇首‘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不合屈原身份。”“‘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二句,也不合屈子口吻,有点儒酸气。”席鲁思还引了清代陈澧的意见作为参证。现代学者中,和席鲁思见解相近的学者不止一位,比如闻一多,在论及《九辩》时,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作者一作宋玉,一作屈原,如果假定《离骚》的作者是屈原的话,那么《九辩》就绝非屈原的作品。把两篇比较来看,异点多于同点,即使有同点也只是在大时代的线段中的共通点,可是它们在一些小线段中就显出很大的差异。从两篇作品的内容风格来考察,一篇产生在早期,一篇为晚期,因为它们的异点几乎可以抹杀同点。”“《九辩》作者自守的态度很严,这一点《离骚》也是一样的。但屈原的态度是自发的不屈服,而宋玉则是做好思想准备的不屈服态度,故前者是消极的不合作,后者则是积极的不合作;屈原是突见不平愤而怒吼,宋玉则是坚忍接受命运安排,比较心平气和;对于君主,屈原是怒骂,宋玉却是温情;屈原还存在‘王庶几召我’的幻想,宋玉则不免绝望,故所写有点像唐人宫怨诗的情调,为弱者哀鸣的态度。总之,在作品中的火气越来越小,这就是屈原和宋玉的基本不同之点。”苏雪林更直接针对刘永济的观点调侃道:“出人意表者,他竟把千古以来大家认为宋玉作的《九辩》,属之屈原,他当然有他的意见和解说,但理由薄弱,没有采信的价值。”席鲁思、闻一多和苏雪林的解读,想来会有不少读者认同。洪湛侯等从学术史的角度给刘永济的说法以“一家之言”的评断,这是较为中肯的。所谓“一家之言”,是说可自圆其说而不一定能够说服他人。
关于屈原《九章》的“篇目问题”,刘永济认为,《九章》中只有《惜诵》至《怀沙》五篇是屈原的作品,《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四篇,绝非屈原所作,又将《国殇》一篇独立于《九歌》之外,均与一般通行本不同。将《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四篇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其理由有五:一,扬雄未仿。二,刘向《九叹》“犹未殚兮《九章》”,则《九章》并未写毕。三,《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文辞不类,前者颠倒重复,后者用连绵词多至二十五句,有心雕饰,反损自然。四,措辞失当。《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皆用伍子胥事,《惜往日》有“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且有“从子胥而自适”,尤非屈子所忍言。盖伍子胥教吴伐楚,残破郢都,鞭平王之尸,自此以后,吴楚构兵不休,贻害楚国甚大,实为楚之逆臣,屈子绝无以忠许之之理。战国之世,游士盛行,不得志于本国者,每出仕异国,屈子则宁死勿去,其不轻去就,由于忠义之厚,安肯许叛国之人为忠。至于《哀郢》之“伍子逢殃”,刘永济谓此伍子非伍子胥而是其父伍奢。伍奢谏楚平王不应信费无极之谗而疑忌太子建,为平王所杀,谓之为忠,允无愧色。五,《惜往日》有“不毕词以赴渊兮”,《悲回风》有“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既已投渊,何能作赋?语气亦类后人追叙其事,疑为唐勒、景差之徒凭吊屈原之作,一时失名,遂附入屈原赋中。
刘永济的上述结论与论证,苏雪林曾以报一箭之仇的口吻断然予以了否定:“这几条理由没有一项站得住。”并逐条予以反驳。其一,“说扬雄未傍,那是扬雄的自由,并不足以证实那时候没有《九章》。”其二,“刘向未殚,是说屈原‘外彷徨而游览,内恻隐而含哀’,其纡郁难释之忧思,《离骚》不足尽之,《九章》不足殚之,足证《九章》是原来就有的题目。刘向这篇《九叹》,代屈原说话,正是模仿《九章》的。”其三,“作家之撰作篇章,为了环境时代之不同,感触强弱之殊异,决不能篇篇一律。况且什么‘颠倒重复,倔强疏卤’,什么‘平衍寡蕴’,‘少郁变之致’,那也不过是读者的主观,而且这种八股家评文陋习,实不足以挂齿颊。至伍子胥之事,刘说尤为可嗤。子胥于平王有杀父兄之仇,屠戮全家之憾,他的报复,是基于人类天然的情感。他在吴国,固属建国之元勋,亦为谋国之荩臣,属镂之赐,鸱夷之弃,千古同悲。他的人格光明磊落,并无丝毫污点。刘氏以后代兴起的国家观念来批评他,并斥之为‘逆臣’,不知这种国家观念乃是现代西洋产物,中国从前是没有的。(中国人以社稷和王室为国家,真正国家观念则并不明了。)”其四,“谈到‘不毕词以赴渊’,‘重任石之何益’,则屈原采取投渊作为自杀方式,可说经过很长的岁月的酝酿,并非仓卒所决定,所有作品之中,彭咸之名凡八见,所以说:‘何彭咸之造思兮,志耿介而不忘’,《离骚》最后一段乱辞也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难道我们也可说《离骚》乃后人悼屈之词么?”刘、苏两位前辈的论证,涉及诸多层面,而对伍子一典的阐释实为重中之重。刘永济延续了他对屈原的一贯理解:屈原虽没有现代国家观念,但身为楚国贵族,即楚国三大贵族(“楚之三户”)的一族,国的命运与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当然不能容忍伍子胥对楚王的反叛。刘永济对屈原的这种理解,不仅是基于历史的考察,也是基于他个人在抗战期间的心理体验,因而有一种尚友古人的气度和风采,其中包含了几分信仰的意味,而不只是学术的考量。苏雪林以屈原没有现代国家观念加以反驳,自有其学理依据,也许还有可能得到出土文献的支持,但即使如此,刘永济也不会改变他对屈原的理解,而只会适当调整论述的角度。一种人文性的解读,其价值不在结论的确凿不移,而在其阐释确能启发读者。刘永济关于屈原作品的鉴别,当作如是观。
在屈原作品的鉴别之外,刘永济对屈赋传世文本字句的改动,有时也偏于人文性的理解。
屈赋字句的校读是刘永济极为用力之处。刘永济确信:1.今传王逸《章句》非《楚辞》原本;2.古书抄刻,易滋讹误。“既然解决了今传王逸《章句》非原本的问题,(其实即令王本是千真万确的原本,是否即屈原的原稿,尚有问题。)既然知道古书易讹之故,如前辈孙诒让所说,那么校读屈赋必然有当改动的文句。”校改贵有依据,刘永济深明此理,曾将其校改依据分为十一类:依据前人意见而改的;依据相同文句而改的;依王逸《章句》而改的;依据别本异文或引文而改的;将后人因避讳而改的字改复屈赋原文的;将借字改用本字的;根据屈赋用韵规律而改的;因误衍而改的;据形似音近之讹而改的;因字误而改的;从文义看知其讹误而改的。在“依据前人意见而改的”的一类中,“依据戴震的屈赋注而改的文句最多,其次则洪兴祖《考异》及朱熹校本”。从刘永济的校改看,其“校”极为严谨,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符合“校”的原则,即都有切实可靠的依据,并有校记;但刘永济的“改”,却可能引发一部分学者的质疑,盖刘永济所列的十一种改动依据,大都并非铁证,而只是根据某种情理作出的推断。这些情理,虽然刘永济确信不疑,但他人未必赞同。刘永济以个人的推断为据,大面积改动传世文本,所产生的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版本,这并不符合学界对古籍整理的一般期待。针对刘永济的“改”,他的老友席鲁思教授写了专文与他商榷,说他“无事自扰”,“动辄生事”,“窜乱古书”,“自作聪明,乱名改作”,“纷纷徒乱人意”,“好以片面立论,以名乱名”,“名实互贸,寻声逐影,移甲作乙”,“全凭主观,自我作故”,措辞之尖锐激烈,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之外。而刘永济读了,不仅不生气,还就席鲁思的商榷,一一展开分疏。那种雅量,那种气度,真能给人光风霁月之感。这篇商榷之作,就是《屈赋篇章疑信诸问题答席启駉先生》。
二、关于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以科学性见长
与刘永济关于屈赋作品的认定以人文性见长,因而不时招致商榷有别,刘永济在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方面,则以科学性见长,建树甚丰,并得到广泛认可,仅此一项,即足以奠定其屈赋研究的学术地位。例如《离骚》中的“又重之以修能”,《屈赋通笺》卷一曰:又重之以修能 朱熹《楚辞集注》曰:“能一作態,非是。”按作態是。能、態古字通。《怀沙》“非俊疑桀,固庸態也”,王充《论衡·累害篇》引作“庸能”,是其证。
修能 按朱骏声谓能乃態之借字,態之本义,兼姿容才艺言,是也。叔师于此训为“绝远之能”,于《招魂》之“姱容修態”训为“多意善智”,皆从才艺立训,《大招》又有“滂心绰態”,叔师彼注曰:“绰,犹多也。態,姿也。”则用姿容之义。绰態,即修態,足证朱说。蒋骥《楚辞注》以修能为修治之能,戴震亦以洁治训修,皆失之。
“修能”之“能”,经常被读为本字。刘永济则在训诂学、文献学、文化学的基础上,将“能”解读为“态”。“能”仅仅包括了才艺,而“态”不仅包括才艺,还包括姿容、风度。刘永济的解读有理有据,也更能体现屈原风华正茂、顾盼动人的气质。
又如《离骚》中的“薋菉葹以盈室兮”,《屈赋释词》卷中释曰:
《离骚》“薋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诗》曰:‘楚楚者薋’。”洪氏《补注》曰:“今《诗》作茨。”按如王注,则三物连文,于文为冗。《说文》:“薋,草多貌。”其作动词用则为积聚。茨亦积聚也。《广雅·释诂》一“茨,积也”,《释诂》三“茨,聚也”,皆其证。此言积聚菉葹,多至盈室,于词为顺,故知王注蒺藜非也。
《屈赋通笺》卷一亦云:
梁章钜《文选旁证》引姜氏皋曰:“薋,《诗》作茨,《尔雅》亦作茨,蒺藜也。然此茨字疑作众多解说,如茨如梁传:‘茨,积也。’《广雅·释诂》三亦释为聚,是也。聚积菉葹,故下云盈室也。”按《说文》:“薋,草多貌。”段玉裁注曰:“据许君说,谓多积菉葹盈室,薋非草名。”朱骏声曰:“薋,艸多貌,从艸资声,与荠迥别,《骚》注谓借为荠,失之。”三氏皆不从王注,是也。梁氏、段式由多引申为积之说,较以本义说为形状词更为明畅。如王注则累三草而言矣,其误明甚。
刘永济从两个方面有力地论证了“薋”不应如王逸注那样解释为一种植物(蒺藜),一是文意不顺,在一句诗的开头部分连续罗列三种草名,三个名词累积在一起,堆砌拖沓,辞气不顺;二是就训诂而言,无论是按本义解释为形容词(薋,草多貌),还是按引申义解释为动词(薋、茨作动词用则为积聚),都胜于将“薋”解释为名词(一种植物)。这个解释得到学界的广泛采信。
闻一多《楚辞校补·凡例》尝云,他所引用的“古今诸家旧校材料”包括“王逸《章句》引或作本”、“洪兴祖《辑校》所引诸本”、刘师培《楚辞考异》、“许维遹《楚辞考异补》稿本”、刘永济《楚辞通笺》;所“采用古今诸家成说之涉及校正文字者,都二十八家”,包括洪兴祖、朱熹、王夫之、屈复、陈本礼、王念孙、王引之、丁晏、马瑞辰、俞正燮、江有诰、朱骏声、牟廷相、梁章钜、邓廷桢、俞樾、孙诒让、吴汝纶、王闿运、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武延绪、刘盼遂、刘永济、游国恩、陆侃如、郭沫若。从这两份名单,可以见出刘永济屈赋研究的学术地位。而闻一多对楚辞的校补,更多次采用刘永济的成果。如《九歌·河伯》“日将暮兮怅忘归”一句的校补:
刘永济氏疑怅当为憺。案刘说是也。此涉《山鬼》“怨公子兮怅忘归”而误。知之者,王注曰“言己心乐志悦,忽忘还归也”,“心乐志悦”与怅字义不合。(怅当训失志貌,故《山鬼》注曰“故我怅然失志而忘归”。)《东君》“观者憺兮忘归”,注曰“憺然意安而忘归”,《山鬼》“留灵修兮澹忘归”,注曰“心中憺然而忘归”。乐悦与安闲义近。此注以“心乐志悦”释憺,犹彼注以“意安”释憺也。且《东君》曰“心低徊兮顾怀,……观者憺兮忘归”,本篇曰“日将暮兮忘归,惟极浦兮顾(今讹作寤,详下)怀”,两篇皆曰“憺忘归”,又曰“顾怀”,此其词句本多相袭,亦可资互证。又如《九辩》“泬寥兮天高而气清”一句的校补:

这一类具体例证,足以表明闻一多对刘永济屈赋训诂的钦重。
刘永济在审音、训诂基础上对屈赋所作的语法分析,尤多卓见。他在《屈赋释词》中单列“以动词置句首”、“以形容词或副词置句首”等类句式,从语法角度揭示了屈赋的语言特色。其中“以形容词或副词置句首”是屈原作品中使用率极高的一种句式,刘永济一共举了六十二例,如果因为《九辩》的著作权尚难确定而去掉其中的例句,也还有四十三例,仅《离骚》一篇就多达二十二例。兹谨将《离骚》的例句和刘永济的解释引在下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离骚》) 吾纷然既有此内美也。纷然,形容“既有此内美”。“既”,亦副词,形容“有”。
汨予若将不及兮(《离骚》) 予汨然若将不及也。汨然,形容“若将不及”。
忽奔走以先后兮(《离骚》)(予)忽然奔走以先后也。忽然,形容“奔走以先后”。王注“忽”为“急欲”,不如《补注》“疾貌”之训。
忽驰骛以追逐兮(《离骚》)(予)忽然驰骛以追逐也。忽然,形容“驰骛以追逐”。
謇吾法夫前修兮(《离骚》)(吾)謇然法夫前修也。謇然,形容“法夫前修”。
謇朝谇而夕替(《离骚》)(吾)謇然朝谇而夕替也。謇然,形容“朝谇”。
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 予忳然郁邑侘傺也。忳然,形容“郁邑侘傺”。
忽反顾以游目兮(《离骚》)(予)忽然反顾以游目也。忽然,形容“反顾以游目”。
纷独有此姱节(《离骚》,刘永济改为“纷独有此姱饰”)(汝)纷然独有此姱饰也。纷然,形容“独有此姱饰”。“独”,亦副词,形容“有”。
判独离而不服(《离骚》)(汝)判然独离而不服也。判然,形容“独离而不服”。“独”,亦副词,形容“离”。
喟冯心而历兹(《离骚》)(予)喟然冯心而历兹也。喟然,形容“冯心”。
曾歔欷余郁邑兮(《离骚》) 予曾然歔欷郁邑也。曾然,形容“歔欷郁邑”。
耿吾既得此中正(《离骚》) 吾耿然既得此中正也。耿然,形容“既得此中正”。“既”,亦副词,形容“得”。
纷总总其离合兮(《离骚》)(风云)纷然总总其离合也。纷然,形容“总总其离合”。
斑陆离其上下(《离骚》)(风云)斑然陆离其上下也。斑然,形容“陆离其上下”。
忽反顾以流涕兮(《离骚》)(吾)忽然反顾以流涕也。忽然,形容“反顾以流涕”。
溘吾游此春宫兮(《离骚》) 吾溘然游此春宫也。溘然,形容“游此春宫”。
纷总总其离合兮(《离骚》) 纷然总总其离合也。但此以指“宓妃”。
忽纬繣其难迁(《离骚》)(宓妃)忽然纬繣其难迁也。忽然,形容“纬繣其难迁”。
和调度以自娱兮(《离骚》)(予)和然调度以自娱也。和然,形容“调度”。王以“和调”连读,非。
忽吾行此流沙兮(《离骚》) 吾忽然行此流沙也。忽然,形容“行此流沙”。
忽临睨乎旧乡(《离骚》) 忽然临睨乎旧乡也。忽然,形容“临睨乎旧乡”。
由上面的例句来看,将形容词或副词放在句子之首确是屈原作品的一个语法特点。以形容词或副词居首,即以状语居首,这并不符合日常说话以主语居首即以名词或代词居首的习惯,在先秦的子书或史书当中,也很少见到这样的句例,《诗经》虽然是诗,这种句例也不多见。屈赋多用这种句例,乃是为了突出各种状态或情态。比如,“忽奔走以先后兮”,不只是写出了“奔走以先后”的事实,更突出了其“奔走”的迅疾(“忽”),以显示其心情的急切。又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不只是写出了“吾有此内美”的事实,更突出了其“内美”之充实、丰富(“纷”),以显示其高出流俗的品格。屈赋的这种语法特点,后世的赋和律诗也经常采用,就因为可以获得特殊的效果。刘永济对屈赋所作的语法分析,在屈原研究史和语法研究史上都是不同凡响的建树,不仅有助于把握屈原作品和后世诗赋的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段,也有助于阐发春秋战国时代的修辞种类,还有助于拓展现代语言学的视野。
三、结语
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洪湛侯等《楚辞要籍解题》一书。《楚辞要籍解题》“择选历代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楚辞专著共六十二本”“加以评介”,刘永济《屈赋通笺》入选。其评介云:《屈赋通笺》的体例:每篇作题解、正名、审音、通训和评论,先列各家之说,再辨是非,尔后或主某家之说,或申述己见,写出扼要的结论。……论据确凿,自可信从。……
每篇的审音部分,对《楚辞》的读音,凡古代韵书中未曾言及者,皆详明音读,指出韵字所属韵部。若古人已有成说,则辨其得失,所论亦时有可取之处。
《楚辞要籍解题》关于刘永济《屈赋通笺》在学术史上地位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对其屈赋考据的第二个方面的学术史定位,正所谓盖棺定论。
The Humanistic and Scientific Features of Liu Yongji’s Study on Qu Yuan’s Poetry
Chen Wenx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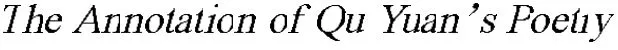
Liu Yongji;Qu Yuan’s Poetry;Textual Criticism;Humanistic Features;Scientific Features
责任编辑:陈水云
陈文新(1957—),湖北公安人,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16FZW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