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纽约市大学白如鹤分校 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美国;2.3.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文学的绝对
〔美〕徐平著 郭蔚臻译 张箭飞审译
(1.纽约市大学白如鹤分校 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美国;2.3.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引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雅典娜神殿断片》及其他著述,本文试图反驳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将“文学的绝对性”等同于“作为绝对性的文学”的断言,进而指出这两位作者不但全然忽视了施莱格尔思想中的矛盾冲突的意义,而且暴露出他们对不矛盾律逻辑的坚守,而这一逻辑正是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特征,也是施莱格尔和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所攻击的对象。
施莱格尔 雅典娜神殿 文学 绝对 浪漫主义 拉库·拉巴尔特 南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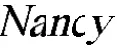
本文的主要目的:质疑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所定义的“文学绝对(the liter aryabsolute)”的概念。通过阅读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我想说明,施莱格尔的写作具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不会允许这种简单鉴别:“文学的绝对性”和“作为绝对性的文学”,这两个术语都统摄在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的“文学的绝对”的名义之下。同时,我也想指出,这种简单鉴别不仅忽视了“张力”在施莱格尔思想中的重要性,而且暴露出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仍然深陷于不矛盾律逻辑(logic of noncontradiction)之中,这正好是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特征,恰恰遭到施莱格尔和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全面挑战。
一
什么是“文学的绝对”呢?正如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在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文学的绝对”指的是“浪漫主义思想不仅关涉文学的绝对性,而且关涉作为绝对性的文学”。换言之,遵循德国浪漫主义传统,这就意味着指浪漫主义思想不仅关涉文学的理念,而且关涉作为理念(dieidee)的文学。对于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来说,“文学的绝对”指的就是文学作为体裁(literature as the genre)这一概念,“一个或许在今天不可定义的概念,但却是浪漫主义者曾经竭力定义的概念。”至于“作为绝对性的文学”,类似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用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的话来说,“(绝对知识)之所以绝对,与其说是因为它是无限的知识,不如说是因为它是在知其所知的同时仍能自知的知识,这种知识因而构成知识的真正的无限性,和其体系。”
显然,根据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的分析,定义文学作为体裁的概念——浪漫派这一尝试其实就是一种确立文学作为绝对知识的意志。换言之,对浪漫派而言,“文学的绝对性”等同于“作为绝对性的文学”,也即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谓之的“文学的绝对”。“文学的绝对性与其说是诗(诗的现代概念是由《雅典娜神殿》断章116所发明的),不如说是诗艺(poiesy),按照词源学说法,而浪漫派总是求助于词源学。所谓诗艺,就是生产。绝对地说,“文学体裁”这一思想所涉及的与其说是文学之物的生产,不如说就是生产。浪漫派诗歌力图深入诗艺的本质,也即,文学之物从自身产生出生产的真相(the literary thing produces the truth of production in itself),接踵而至的就是:诗艺生产以及诗艺自动生产(autopoiesy)的真实——这一点显而易见。如果说,自动生产确实造就了终极实例(ultimate instance)和思辨绝对性(the speculative absolute)的终结——黑格尔很快就要论证:它其实彻底颠覆了浪漫主义,那么,可以说,浪漫主义思想所论及的不仅是文学的绝对性,而且是作为绝对性的文学。(简言之),浪漫主义就是文学的绝对的开端。”
“文学的绝对”之概念,可称作“文学的绝对性”,也即“作为绝对性的文学”,毫无疑问地构成了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整本书的基础。这让他们能够断言:德国唯心主义始终保持着“浪漫主义的哲学视野”;文学的现代概念,从它诞生之时就“受控于”哲学;浪漫主义依旧寄居于“体系——主观(system-subject)”之内;就浪漫派而言,无法生产“绝对的作品”,这种失败意味着“文学绝对的绝对消解”。总之,它允许“文学绝对的某一显著优点”存在,根据这本书的译者所说:
因此,文学绝对的显著优点,其一即为,它提出并执着于文学问题,诸如此类。正如作者的分析所表明,文学,一如人们通常理解,浪漫主义的且现代性的文学概念,文学作为合法化和体制化的学科对象,完全是对某种哲学“危机”的回应。人们接受的文学概念,换言之,也就是假定在诸多方面文学都是异于或者外在于哲学的(因此就可以永远哀叹:文学从外面突侵哲学,或者“理论”侵入文学难题),其实哲学却无时不刻贯穿于其中。当文学做出最全面的真实姿势时,也正是它最大程度依赖哲学之时。
我并非有意低估文学绝对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关乎文学与哲学所有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是近些年来在文学理论领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但是我想要质疑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学绝对”概念的基础。说得更明确一些,对我而言,文学的绝对似乎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为绝对的文学”。然而,在试图定义文学的概念的过程中,浪漫派的确有着将文学绝对化的倾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其说文学自身是绝对的,倒不如说文学是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换言之,将文学绝对化的倾向与文学是一种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在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这里,这种张力关系却因鉴别“文学的绝对”和“文学作为绝对”而消解。这样一来,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不但无法公正地对待浪漫派,而且也不能够欣赏浪漫派的佯谬立场(paradoxical positions)——而后者正是籍此挑战哲学思维的传统方式。
二
这种张力关系在施莱格尔作品中显而易见。
不用说,在施莱格尔作品中,将文学(或艺术,或诗)绝对化的倾向俯拾即是。在他的《断片集》中,他谈论到了“协作诗(sympoetry)”、“先验的诗”,他宣称“诗和哲学应该合二为一”;“哲学所止,诗之所始”;“艺术作品折射宇宙的另一面——unednlicheEinheit”。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他《断片集》第350条中,施莱格尔说道:“无诗歌即无现实。任凭感觉具备,无幻想则无外在世界,同理,即使感觉具备,无心绪则无鬼神世界。谁如果只有感觉力,他看不到人,而仅仅看到人性:只有心绪这根魔杖可召来万物”。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同样在施莱格尔那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感觉,文学并没有如此绝对,而是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一种表现不可表现(the unrepresentable)的间接方式;一种表现思辨概念(speculativeconcepts)无法表现的间接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绝对不是诗,也不是哲学,而是远远超过二者的某物,施莱格尔称作是“神圣(divine)”的东西。在第419条中,施莱格尔说,“神圣,就是源自于爱,升入至纯至臻,高于任何诗歌和哲学。有一种宁静的神圣,没有英雄和艺术家创造所具有那种毁灭性力量(crushing power),只要神圣,就会完善,伟大便是完美。”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施莱格尔,浪漫主义诗歌,一如教养(Buildung)和寓言,是欲成而未成的完美。甚至第116条,即使文学的绝对化达到峰值,我们依然可以读到如下语句:“浪漫诗还在变化中;它永远只在变化,永远不会完结,这正是浪漫诗的真正本质。浪漫诗不会被任何一种理论彻底阐明,只有预言式的批评才敢冒险刻画它的理论。”
显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鉴别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所提出的“文学的绝对”和“作为绝对的文学”,那就是:在施莱格尔那里,施莱格尔没有意识到在文学与绝对的关系层面,文学自有局限,所以试图将文学绝对化,但他意识到文学不过是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如果将他的这个意识纳入考虑,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的鉴别就是不合理的。
从上面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施莱格尔的这种意识非常强烈。在这里,我想补充另一个片段,施莱格尔用一种确凿无疑的语言表述:“诗歌,只是隐含着无限性,并不产生明确的概念,除了直觉之外。它(无限性)是一种无穷无尽的丰富,是理念的混沌——诗歌力求表现这种混沌并将其融合为美好的整体。”
倾向于将文学绝对化与意识到文学是一种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这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张力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张力关系?首先,不能忘记,对施莱格尔来说,文学应该成为自己的理论,同时,它也是文学本身,正如他在断片集第238条中说的那样:“诗应该描写自身,总是同时既是诗又是诗之诗。”因此,如果理论(也就是文学本身)试图定义“文学的绝对”,它是不可能“穷尽(exhaust)”诗的,正如在前面引文中施莱格尔指出的那样,那么,同样的理论怎么可能表现绝对?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文学是自身的理论,那么文学怎么可能表现同样的绝对呢(the same absolute)?看起来,通过将文学绝对化(同时视文学为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施莱格尔事实上已表明表现绝对的完全不可能性。再换个角度来说,通过认定文学是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并揭示文学无法界定自己的理念及自己的绝对,施莱格尔得以削弱表现绝对这一可能性,而绝对是不可能用任何一种概念性语言表达清楚的。
我所指出的是,在施莱格尔作品中存在着清晰可辨的双重姿态。通过将文学绝对化,施莱格尔毫无疑问站到哲学的对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认识文学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将文学与哲学相提并论乃至认为文学应当成为自身的理论,他同样背靠着哲学。换言之,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先是直接地,然后是间接地削弱了思考传统哲学特征的惯常方式(the conventional way of thinking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事实上,张力的两极彼此矛盾,这代表着对具有概念性思考和表现性思考之哲学的双重否定。正如Seyan指出的那样:“在诺瓦利斯和施莱格尔那里,重提表现的难题,既非是想象力的非功利性实践,也非完成哲学未竟事业的雄心勃勃和自我放任的尝试。想象不可想象的意愿标画出的路径将浪漫主义引向新的疆域,在那里,现有知识形式的基础受到激烈的挑战。”
三
在施莱格尔作品中,这种张力绝非偶然出现。恰恰相反,它因“矛盾的理念”显得更加突出,而矛盾恰好是施莱格尔思想的中心。“一切都在自我否定Alles widerspricht sich,”施莱格尔曾说,不仅现实如此,意识亦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施莱格尔反复在强调“两种冲突的力”,“在自我创造(self-creation)和自我解构(self-destruction)中不停地摇摆。”诺瓦利斯断片集《花粉》(Blutenstaub)收录了一则施莱格尔的断片,他说:“一个人如果痴迷于绝对,无法摆脱这种痴迷,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自我冲突,与对立的极端事物并合。冲突注定不可避免,唯一可保持的选择或是假定忍受这种命运,或是承认尚有自由行动的可能而将这种命运变成高贵的必然。”
同样的矛盾概念也解释了为何施莱格尔反复提到了反讽(irony)、机智(wit)、无序(chaos)、反论证(antithesis)。事实上,“断片”这一概念就反映出矛盾概念的特征。
在断片第121条,施莱格尔说:“一个理念也即完善到反讽境界的概念,就是绝对反论证的一个绝对综合(an absolute synthesis of absolute synthesis),是两种冲突思想之间不断自我创造的置换。”在一些断片中,他赋予机智如此特征:“化学的(chemical)”、“断片的天才(fragmentarygenius)”、“受限精神的爆炸(an explosion of confined spirit)”、“联合机智的无序(achaosofcombinativewit)。”在此,机智与理性之间的对比已经很明显了。正如Peter Firchow所说,“机智不是理性:理性是机械性和实验性的;机智一触即发,并且来源于灵感。”
至于断片本身,施莱格尔把它称作“精神的自然形式”,并把它作为传达他的理念的主要载体。在断片集第22条中,他说:
一个构想就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客观的主观萌芽。一个完美构想一定既是完全主观的,同时完全客观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个体。究其起源,它是完完全全是主观和原创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有可能成立;就其特性而言,它又是完完全全客观的、自然的、道德必然的。对可称为未来断片之构思的感觉,与对过去断片的感觉,这两种感觉只在方向上有所区别。前者是渐进的,后者是递减的。本质在于能将客体理想化,同时又能使其现实化:完善客体并部分地在自身里体现出它们。既然那些与理想和现实相合相分的事物就是超验性,或许可以说,对于断片及构思的意识,乃是历史精神的超验性元素。
很清楚,根据施莱格尔所言,断片的特征,恰恰是隐匿在佯谬之中破坏连贯性和哲学的不矛盾逻辑特征。正如Seyan所说,“断片否定了连续表现的哲学(philosophical postulate)并给此种理念基础造成裂痕。这一瓦解姿态恰恰扮演着佯谬的角色,纠缠着哲学不放。”在此,Seyan意指的“佯谬”来自施莱格尔的一篇文章“莱辛文章的结尾”,“就哲学生活的佯谬而言,或许没有什么比那些弯曲的线条更美的象征了。凭借显而易见的连续性和规则性,它们却永远只能表现为片段,因为它们的中心存在于无限。”耐人深思的是,正如Seyan指出的那样,诺瓦利斯同样也谈论到了“弯曲的线条”,并且将它称为“自然对于规则的胜利。”
现在很清楚,矛盾概念在施莱格尔的思想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我想表明的是,施莱格尔思想中显著可见的矛盾概念已经是逻辑不矛盾律(也即传统哲学之特质)的持续颠覆,它的目标,用施莱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对最高知识做无果的追寻”(这个强调是施莱格尔的)。正如Manfred Frank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它是对人性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不连贯性、以及矛盾性的发现。通过这一切它与那乐观的传统之间划上了明确的分界线,不管这传统是敬神的还是形而上学的。”以矛盾概念理解,将文学绝对化的倾向和对文学自身局限的认识,这二者之间的张力看上去像是施莱格尔的游戏策略,从一开始他就以此对抗作为哲学之特征的不矛盾逻辑。换言之,通过在矛盾的两极之间的“摇摆不定”,这种张力才能对其逻辑完全异于矛盾概念的哲学形势我称之为的双重否定(doublenegation)。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的著作,应该注意到的是,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遮蔽张力以便彰显“文学的绝对性”和“作为绝对性的文学”的区别,此举也并非偶然。毕竟,正如他们明确宣称的那样,他们的目的是要“对浪漫主义进行恰如其分的哲学研究”,“以哲学的方法解读这些(浪漫主义)文本”。
如果我的理解无误,这就是他们为何想要区分“文学的绝对性”和“作为绝对性的文学”的原因。因为唯独通过这种区分,他们才得以宣称浪漫主义由哲学所控制,也即浪漫定义文学概念的企图是确立文学作为绝对知识的意志。结果,他们根本不会把存在于浪漫主义之中,特别是施莱格尔之中的张力纳入考虑,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整体上摧毁他们的构想。总之,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的整个构想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无视这种张力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在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的眼中,浪漫主义的特征仅仅是把文学绝对化的倾向,而我则认为,其特征是:认识到文学与其说是绝对的不如说是一种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这个认识却被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看做是:并没有抓住浪漫主义的本质和目的。
显然,在《文学的绝对》一书中,争论沿着这条线索展开,它始于区别“文学的绝对”和“文学作为绝对”,最后以失败于定义浪漫主义的“文学的绝对”而告终。换言之,始于论证浪漫主义和哲学同一性,终于显示浪漫主义乃哲学的失败(former’s philosophical failure)。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其实探讨的是浪漫主义不可能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
浪漫派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甚至对此含混不清,或者把一切夹杂在这个问题之中——浪漫派的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可能性显然说明,它的问题实际上纯粹是言之无物,徒有“浪漫派”或“文学”(还有“诗”、“文学创作”、“艺术”、“宗教”等等)的虚名,只要触及到这种难以划分和难以确定的东西就无限退缩,(几乎)接受所有的名称,却又不能容忍其中的任何一个:那是一种不可命名、没有轮廓、没有形状的东西——说到底,它“什么都不是”。浪漫派(文学)就是没有本质,甚至不存在于其非本质性之中的那种东西。
这种不可能性被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看成是浪漫主义无法避免的失败,但这也可以被看作只是基础的失败——“文学绝对”建立在既是“文学的绝对”又是“作为绝对的文学”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是失败的,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浪漫主义才能成为哲学构想。随之而来的是,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理由宣告“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是空洞的,文学的浪漫主义概念是不明晰、不确定、不可名之物,也即无形、无状、甚至无物。然而,如果我们把施莱格尔作品中存在的鲜明的张力关系纳入考虑范畴的话,我们会说,不明晰与不确定恰好是施莱格尔想要展现出来的文学特质。正是因为表现绝对的不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屡屡尝试去定义文学的时候,必须再三地颠覆之前的定义。“浪漫主义与生俱来的不可能性”,的确如此,但与其说这是浪漫主义的失败,我更愿意说,恰恰相反,这才是浪漫主义的要义所在。
这一理解同样适用于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所指责的浪漫主义夸张和歧义。论及夸张或夸张化,他们说,“这里的夸张,就是,诗的夸张,是从有机隐喻的字面化发展而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既然艺术作品的有机性或者整首诗远远超过(或不止)一个隐喻——诗的夸张化,或诗的消解,是工具的理念或者工具作为一种理念而产生的效应。”至于“歧义”,他们写道:
我们再三重申:断片、宗教、小说、批评都以各自的方式重构文学和文字的体裁:类(Guttung)、物种、特殊性本身的特殊生成,相同成分混合的自主生成。自发生殖(也译作自然发生),即那个时代所谓的偶然发生(generatio aequivoca),它本身具有两种含义,它在任何情况下自我生成。鉴于这个事实,体裁中的每个体裁都以各自的方式同时肯定生殖的歧义,aequivoca的歧义:物种也相当于含糊不清和没有个性的混合。甚至在消解的有机进程中,某种东西始终在抵抗或逃离:比如谢林的消融(Auflosung)中的某种东西始终在抵抗黑格尔的扬弃,施莱格尔小说的某种东西始终在逃离谢林的消融。
在此,这种谴责也是基于对“文学的绝对性”和“作为绝对性的文学”的鉴别之上的。显然,因为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将浪漫主义视为确立文学作为绝对知识的意志,最终他们赋予浪漫主义“夸张”和“歧义”的特征,但却无法定义绝对知识本身。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事先预设了“文学的绝对性”等同于“作为绝对性的文学”,那么浪漫主义当然应该被看作是完全的夸张和歧义。但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在施莱格尔那里,将文学绝对化的倾向已经被对于文学与绝对关系的局限性的认识所倾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把文学夸张化的姿态其实是想要展示表现绝对的不可能性。如果这样理解,所谓的带有“模棱两可的混杂”的“歧义”应该被视为是浪漫主义的一个优点,因为只有哲学产生不矛盾的逻辑以及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所说的“辨识性”。
最后,我想截取《文学的绝对》中的一个片段,它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想要挪用于(appropriate)施莱格尔,反而被施莱格尔所挪用:
可以理解,在这些条件下,文学或诗,“浪漫体裁”其实始终被人当作对文学本身的某种超越来追求,这至少印证了这种东西确实存在。实际上,这无异于指责《谈诗》不能带来他许诺的观念。这样的绝对化或无限化的过程在任何意义上都超过了作为这种完成的一般理论(或哲学)的潜能。这种“自主”运动——自主构造、自主组织、自主分解等等——如果人们能够这样说的话,相对其自身来说永远是无节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如《断片集》第116条指出的那样:“浪漫诗还在变化中;它永远只在变化,永远不会完结,这正是浪漫诗的真正本质。浪漫诗不会被任何一种理论彻底阐明,只有预言式的批评才敢冒险刻画它的理想。”
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从断片集中引用了同样的片段,我认为这是一种标志:施莱格尔清晰地认识到文学在关系到绝对层面上存在局限。但这一片段却被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用来支持他们的论点:文学在与自身的关系上始终是过度的且无法定义自身。然而,即便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论点,依然存在一个有待质疑的问题:他们的论点和引用的片段之间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什么叫做“这个说法,在《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第116条中也提到了”?如果这意味着施莱格尔在这个片段中已经认识到了文学的超越性,那么结论将会是:施莱格尔已经意识到了文学本身不是绝对,而是表现绝对的间接方式。显然,恰恰是因为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不承认这种认识,他们扭曲了这一片段传递的信息,取而代之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组诸如“也(too)”“从某种意义上来说(in a certainsense)”等等来混淆视听。但施莱格尔的信息如此明晰无误以致于他们最后的引用暴露出他们论点的问题所在。
如果浪漫主义真的仅仅是试图建立文学作为绝对知识,真的存在想要将文学绝对化的倾向,那么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所说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一切都是成立的。但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忘了问:为什么我们要将浪漫主义首先看作是一项哲学构想呢?事实上,他们所坚持的假设本身有待于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加以论证。在这个意义上,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在《德意志唯心主义最早的系统纲领》中仅仅指出浪漫主义和哲学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同样的,通过说“施莱格尔兄弟注定去继承家族传统的批评事业;他们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和理论家,而不是诗人”道出施莱格尔兄弟的“家族传统”是毫无意义甚至荒谬的。
这里,关键之处不在于,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是哲学家,所以他们从哲学的立场上来对待这个论题是理所应当的。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哲学立场来反思浪漫主义,他们自己也成为哲学不矛盾逻辑的牺牲品,而浪漫派恰为最先反叛这一逻辑群体之一。结果,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倾向于完全无视浪漫主义中存在的张力,或者被迫将这一张力视为浪漫主义不完全性的标志。哲学从来没学会寄身于张力或矛盾之中,它的任务就是将所有一切转化成一个逻辑的连贯的整体。就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情形而论,他们通过确立“文学的绝对”和“作为绝对的文学”之区别创造一个逻辑的连贯的整体。事实上,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整体是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为浪漫主义创造的一个体系。在这一体系里,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思考,我所说的张力注定会被当做是内在于浪漫主义的难题。很明显,通过区分“文学的绝对”和“作为绝对的文学”,拉库·拉巴尔特和南希不仅遮蔽了张力本身,还从总体上消解了施莱格尔和浪漫主义思考的能动方式。在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真正被哲学所控制的既不是文学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文学的绝对”的作者和《文学的绝对》。
Friedrich Schlegel and“The Literary Absolute”
〔US〕Xu PingTrans.Guo WeizhenProofread.Zhang Jianfei
(1.Dept.of Modern Languages&Comparative Literature Baruch College of CUNY,US;2.3.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Drawing on Friedrich Schlegel’s Athenaeum Fragments and other writing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tradict Lacour-Labarthe and Nancy’s assertion that“the absolute of literature”is tantamount to“literature as the absolute”,and to point out that the authors not only ign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nsion in Schlegel’s thinking,but also betrayed their adherence to the logic of non-contradiction,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tir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nd challenged by none other than Schlegel and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at large.
Schlegel;Athenaeum;Literature;Absolute;Romanticism;Lacour-Labarthe;Nancy
责任编辑:汪树东
徐 平(1957—),纽约市大学白如鹤分校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终身教授。
郭蔚臻(1991—),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张箭飞(1963—),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