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格斯大学,美国 新泽西州;2.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西方哲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红楼梦评论》
〔美〕涂经诒著 邓明静译
(1.罗格斯大学,美国 新泽西州;2.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将西方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拓之作,其巧妙运用了叔本华的艺术理论来研究中国名著《红楼梦》,从深度和广度上论述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美学价值、伦理价值以及悲剧意识。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从生活之本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哲学基础,认为《红楼梦》极度体现了人生的苦痛以及人不断追寻解脱之道,极具厌世解脱之精神,是一部举世瞩目的悲剧,完美展现了叔本华所谓的第三种类型的悲剧,因而被视作为“悲剧中的悲剧”,是“壮美文学”的代表,其美学价值与伦理价值密切相关。写于一百一十多年前的《红楼梦评论》在当时既倡导了一种研究《红楼梦》的新方式,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示范。
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 西方哲学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像很多其他学科分支一样,其发展轨迹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从严复(1854—1921)译介英国哲学开始,各种西方学说流派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听众。因此,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也就非常流行了。
在引进西方学说的众多先驱者中,王国维(1877—1927)或许比其他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贡献更大。他的《红楼梦评论》是学习德国意志哲学的直接成果,巧妙地运用了叔本华的艺术理论来研究中国名著《红楼梦》。它从深度和广度上论述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美学价值、伦理价值以及悲剧意识。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并未将注意力放在现代学者认为值得关注的《红楼梦》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上。因而就连研究《红楼梦》最有名的现代学者吴世昌先生也遗憾地未曾提及王国维这本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吴世昌先生遗漏《红楼梦评论》很可能源于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文本批评而不是小说的文学批评。《红楼梦评论》成于 1904年,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和胡适的文章《红楼梦考证》的发表还早了十多年。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对于小说作者被忽视深表遗憾,他督促自己的学生去研究作者的生平和小说不同版本的成书时间。尽管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胡适的研究可能受到了王国维那本书的启发,不过也没有证据表明相反的情况就是真实的。不同于蔡元培的“猜谜”和胡适的文本探索,《红楼梦评论》代表了一种用哲学思维去研究《红楼梦》。就像王国维在“自序”中提及的那样,他的《红楼梦》解读主要基于叔本华的哲学。
对王国维来说,《红楼梦》不仅提出了叔本华在《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中提及的问题,同时也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王国维首先问道:“生活之本质为何?”追随叔本华的思想,他提出生活的本质无他,只有作为意志行为的欲望而已。人性贪婪,欲望源于得不到满足,而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状态即是苦痛。满足一个欲望,则此欲望才能终止。然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永远多于得到满足的欲望;同时,当一个欲望被满足后,其他的欲望又会随之而起。因此,终极的满足是不可能的。王国维进一步论道,即使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了,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去追求了,那么倦怠的情绪就会随之而来。倦怠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苦痛,因为它使生活变成了负担。因而,人生实如钟摆,来回摇摆于苦痛和倦怠之间。
可以驱散人之苦痛与倦厌者,一般谓之曰“快乐”。但是在追寻快乐的过程中,人除了承受固有的苦痛之外,还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反过来说也是一种苦痛。而且经历过快乐之后,人对苦痛的感觉会变得更加敏感。常见苦痛不屈服于快乐,未见快乐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同时,人类的苦痛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文明的程度愈高,人拥有的欲望愈多,他感觉到的苦痛也就愈强烈。王国维总结道,既然人的欲望不会越出生命本体,那么人生的本质就是苦痛,而欲望、生活和苦痛实际上只是一回事。
在所有的欲望中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欲最为强烈。实际上男女之欲比饮食之欲更为强烈,因为前者在繁殖后代的生理需求的驱使下可以达到生命的永恒延续,而后者仅仅只能满足此生的需求。“因而男女之欲是无尽的、形而上的,而饮食之欲是有限的、形而下的。”进一步来说,既然苦痛的程度与生活欲望的强度成比例,那么男女之欲所致的苦痛显然要远远大于饮食之欲所致的苦痛。寻找引发和治愈男女之欲所致的苦痛显然已经成为人类的当务之急。王国维指出,例如裒伽尔(1747—1794)就曾在他的诗歌中明确了这一问题:
嗟汝哲人,靡所不知,靡所不学,既深且跻。
粲粲生物,罔不匹俦,各啮厥齿,而相厥攸。
匪汝哲人,孰知其故?自何时始,来自何处?
嗟汝哲人,渊渊其知。相彼百昌,奚而熙熙?
愿言哲人,诏余其故。自何时始,来自何处?
如果裒伽尔没有在西方找到问题的答案,那么他应该试试在东方寻找答案。按照王国维的说法,《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苦痛,尤其是男女之欲的苦痛,都仅仅是人自己造成的,因此释放苦痛的关键也就需要人自己去寻找。
在小说的开头有一个关于宝玉来历的神话解释:
却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骼不凡,丰神迥异,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
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
在王国维看来,这一段话体现了生活之欲先于人生而存在,而人生实际上只不过是生活之欲的表现或物化。同时,人之由天真无邪的天堂堕落到充满苦痛的人世,就是其意志自由的罪过所致。对于那块已经获得灵性的顽石来说,这的确是不幸的;无论如何,如果那顽石安于他的命运留在那太虚幻境中,它也许就可以避免经历人间的诸多苦痛。相反,它却尝试通过哀怨和不以为然坚持它到人间的愿望,从而开始了宝玉和其表妹黛玉的悲剧爱情,以及小说中其他的很多故事。
从人世的苦痛中解脱出来的关键必须要被人自己找到,这从叙述宝玉与和尚对话的片段中可以体现出来:
“弟子请问师傅,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
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你那玉是从那里来的?”
宝玉一时对答不来。那和尚笑道:“你的来路还不知,便来问我!”
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
那句“……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的确意味着宝玉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人生是他意志自由的罪过所致。但是当那和尚一问他那玉,他立即意识到他在人世的不幸生活是他自己向往人世之念的后果,且他自己无法拒绝。因此,他想返还那块象征着生活之欲的玉给那僧人,并开始朝着从人生苦痛中解脱出来的路径迈进。
王国维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因为他已经知道生活不能避免苦痛,所能依靠的是解除生活之欲。在完成这一过程的终极阶段,出世者的躯体虽存,但其心已经犹如死灰。另一方面,一个尚未解除自己生活之欲的人反而选择自杀,这并不能被视作获得了解脱,因为他只是不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而追求来生有更好的命运。他对生活的欲望如原来一样保留了下来,且会重现于来生,这样苦海之流将无穷无尽。因此,王国维并不认为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尤三姐之自刎是真正的解脱。她们自杀仅仅是因为不能在此生实现她们的欲望。王国维注意到,“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
尽管自杀在平常看来并不是真正的解脱,但王国维在另一处论道:“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王国维这最后的声明非常有意思,它不仅表明了王国维和叔本华在对待自杀的态度上的差别,而且也为王国维本人的自杀提供了一条线索。像王国维这样极其钦佩叔本华哲学思想的人也会自杀,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另一个谜,要知道在叔本华的哲学中自杀是被谴责的愚蠢行为。一些人甚至因为他声称研究叔本华哲学而嘲笑他言行前后矛盾。但是他与叔本华理论中关于自杀的轻微但非常重要的分歧仍然未被关注。阅读上述引文可知,假如王国维在自杀之前就已经放弃了他的生活欲望,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的自杀在他的哲学中是说得通的。
王国维进一步注意到解脱之道有两种:一是观察他人的苦痛和思考世上的苦痛,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苦痛。然而只有非常之人能通过前一种方式实现解脱;对于常人而言,解脱只能在他自己经历苦痛的过程中去实现,而不是通过认知或者思考他人的苦痛来实现。那些非常之人由于拥有非凡才智,已经洞观了宇宙人生的本质,无需亲身经历苦痛也能知道生活与苦痛不可分割,因而终结其生活的欲望并获得解脱。但常人解脱的过程则是不同的,常人的生活欲望通常会因得不到满足而愈加强烈,又因愈加强烈而愈加得不到满足,重复这种循环则会陷于更大的长久的绝望中,其最终才会领悟到人生的真相而去寻求解脱。通过观他人之苦痛获得解脱可被称为“超自然的也,神秘的也,平和的也”,而通过亲身经历苦痛获得解脱则被称为“人类的也,诗歌的也,壮美的也”。惜春、紫鹃的解脱属于前者,宝玉的解脱属于后者。“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讨论了《红楼梦》的哲学基础之后,王国维继续探讨了它的美学价值。他注意到中国人的精神通常被描述为世俗的和乐观的,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学中很常见。例如,在戏曲和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节,即始于悲伤终于欢乐,始于离别终于团圆,始于困顿终于好运。他宣称:“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但前者(《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因为在厌世和解脱的强调上,《红楼梦》显然与中国人的精神希冀相背离了,“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悲剧理论的影响,在他看来,《红楼梦》是一部举世瞩目的悲剧。在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中,悲剧因其影响力巨大和成就难以企及被视为文学艺术的顶峰。对悲剧而言,巨大的不幸是其唯一必不可少的关键性因素。叔本华基于悲剧呈现的方式将其归为三种类型。其一,悲剧可能会通过极恶之人极其所能地制造不幸而发生。其二,悲剧可能会通过盲目的命运,即际遇和错误而发生。其三,人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导致不幸。普通人物在没有特殊事件或境遇的情况下做平常的事情,也可能因为人际关系明知故犯地致使他人遭受巨大伤害。按照叔本华的观念,第三种类型的悲剧比另外两类悲剧的悲剧感更浓,因为它体现了由普通人的性格和行为而非稀见事件或际遇引发的巨大不幸。因而芸芸众生皆与此密切相关。第三种类型的悲剧也最难被创作出来,因为它必须由最少的起因产生最大的感染力,且其主要应通过人物的立场来实现。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就恰好属于这类悲剧。
我们来看看宝黛爱情的悲惨结局是怎样形成的。宝玉的祖母(贾母)喜爱薛宝钗的温婉而不喜欢黛玉的孤僻,且由于深受命定的“金”(宝钗的象征)“玉”(宝玉的象征)良缘之迷信观念的影响,她认为如果宝玉与宝钗结婚,宝玉的病就会痊癒。宝玉的母亲王夫人与宝钗的母亲是亲姐妹,因此在决定宝玉的婚配对象时,她自然会喜爱宝钗多于黛玉,因为黛玉的母亲只是她的小姑子。宝玉的嫂子王熙凤深受贾母和王夫人的喜爱,她忌惮黛玉的才华,且担心如果黛玉嫁给宝玉,那她在贾府的地位就会被黛玉盖过。因此尽管她看到了宝玉和黛玉之间深深的爱情,但当讨论宝玉和宝钗成婚的提议时,她没有提出异议。同样,作为合理选择成为宝玉第一个妾的袭人,也因黛玉无意中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感到不安,她害怕如果黛玉成了她的上头人,那尤二姐、香菱这样妾的命运会降临到她身上,因而她对宝玉与宝钗成婚的提议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最终,尽管宝玉深爱着黛玉,但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传统道德要求他不能违背祖母和母亲的意愿。结果,“金玉以之合,木(林黛玉的别名)石以之离”。这出悲剧里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卷入其中么?没有。其不幸皆由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和通常之境遇造成。从这个角度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此外,王国维沿袭康德和叔本华提出两大美学品质:优美和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而谓此物曰优美”,且我们拥有的那种心态就是优美。而壮美的美学品质就是从中人们能意识到不利于己的事件和对象,并通常会产生敬畏感。但通过意志的自由超越,人们能够在超然忘我的情境下观照这些事件和对象。事实上,优美和壮美都能让人暂时从生活的欲望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到一种“纯粹之知识”的状态。然而一些与优美和壮美相左的艺术,则不仅不会减少或熄灭人的欲望,反而会加剧人的欲望。对于这类艺术,王国维杜撰了“眩惑”这一术语,并坚持认为色情文学之类的眩惑文学没有任何美学价值。
《红楼梦》当然不是那类眩惑文学,作者在小说开头就申明了这一点:
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欲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红楼梦》无意成为作者明确憎恶的淫秽文学或一个常见情节的爱情故事。那么,《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是什么?既然它是“悲剧中之悲剧”,那么其表现的壮美也就多于优美了。王国维将描述宝玉和黛玉最后一次相见的片段视为“壮美文学”的代表:
[听了傻大姐说宝玉娶宝钗的话,]林黛玉感觉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似的,两只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下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脚下愈加软了。走得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
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又见一个丫头往前头走了,离的远也看不出是那一个来,心中惊疑不定,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
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答道:“我问问宝玉去。”
紫鹃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得搀着她到贾母这边来。黛玉走到贾母门口,心里似觉明晰,回头看见紫鹃搀着自己,便站住了,问道:
“你做什么来的?”
紫鹃陪笑道:“我找了绢子来了。头里见姑娘在桥那边呢,我赶着过去问姑娘,姑娘没理会。”
黛玉笑着说道:“我打量你来瞧宝二爷来了呢,不然怎么往这里走呢?”
紫鹃见她心里迷惑,便知黛玉定是听见那丫头什么话来,惟有点头微笑而已。只是心里怕她见了宝玉,那一个已经是疯疯傻傻,这一个又这样恍恍惚惚,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那时如何是好?心里虽如此想,却也不敢违拗,只得搀她进去。
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却是寂然无声,因贾母在屋里歇中觉,丫头们也有脱滑儿玩去的,也有打盹儿的,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袭人听见帘子响,从屋里出来一看,见是黛玉,便让道:
“姑娘,屋里坐罢。”
黛玉笑着道:“宝二爷在家么?”
袭人不知底里,刚要答言,只见紫鹃在黛玉身后和她努嘴,指着黛玉,又摇摇手儿。袭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语。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座,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袭人看见这番光景,心里大不得主意,只是没法儿。
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
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
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人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袭人见了这样,知道黛玉此时心中迷惑,和宝玉一样,因悄和紫鹃说道:
“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纹妹妹同着你搀回姑娘歇歇去罢。”因回头向秋纹道:“你和紫鹃姐姐送林姑娘去罢,你可别混说话。”
秋纹笑着,也不言语,便来同着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仍旧瞅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
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
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
在这个发展的段落中,悲剧效果通过黛玉和宝玉之间的寥寥数语和对黛玉非凡英勇力量的出色描述强烈地传达出来了。尽管没有哭泣、呜咽和通常的情绪化,黛玉和宝玉的痛苦还是被读者深切体会到了。
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的一致性已经成为西方哲学最喜欢表现的主题之一。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悲剧被看作是一种宣泄,因为其有净化心灵和使人精神崇高的效果。因此,艺术的目的从根本上说也是伦理学上的目的。同样地,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悲剧,尤其是第三种类型的悲剧被视为诗歌艺术的顶点,因为其通常代表了生活可怕的一面,暗示了世界的本质和存在,因而能引导人们去寻求解脱。因此,艺术的终极目标和伦理学上的终极目标合二为一了。循着这一思路,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与其伦理价值有关:
《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可知也。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
如前所述,常人寻求解脱的路径即在生活中经历苦痛。但苦痛本身没有固有的价值,其价值纯粹在于它是人们实现精神解脱的物质媒介。面临极大的苦痛时,人不会为了结束苦痛去自杀或寻求虚幻的感官愉悦来欺骗自己。真正的解脱是禁欲,其次是放弃生的欲望。《红楼梦》的精神显然在于解脱,因此“《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
最后,王国维提出了通过禁欲达到解脱是否足以被视作伦理最高境界的问题。王国维承认,从通常之道德的角度来看,其不是最高境界。例如,宝玉的情况按照世俗传统,他大概会因为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被看作罪人。王国维注意到通常之道德对社会秩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其价值必须被承认。但是,世界和人生的存在,是有一个合理的根据,还是仅仅出于盲目的行动而别无意义?如果世界和人生的存在有一个合理的根据,那么通常之道德应该被视作绝对之道德。但王国维认为,从各方面来看,世界和人生的存在都仅仅是人类远祖所犯偶然性错误的后果。这一观点可从哲学家的暝想、诗人的悲歌和古代诸国的民间故事及神话传说中得到印证。《红楼梦》开头关于宝玉来历的神话故事也能使人想到同样的宗教信条。既然生命的真相是人类远祖犯错的后果,则只要世界上仍然有一个人没有获得解脱,那么祖先的罪过就无法弥补。用通常之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宝玉会因不忠不孝而被谴责;但是从超脱的角度来看,他定会被看作是尝试通过不再从生物学上繁殖新生命来纠正祖先所犯错误的人。他明白祖先的过错,不忍重复这种错误而加重其罪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宝玉定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孝顺。他(宝玉)所说的“一子出家,七祖升天”,意味着他的孝道不同于通常之道德所谓的孝道。
至此,王国维已经成功运用叔本华的哲学来阐释小说《红楼梦》了。然而他天生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运用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他也感知到了其不同。一般而言,过去存在着两种针对叔本华解脱理论的异议。第一,如果像生活一样寻求物化是意志的本质,像叔本华主张的那样,那么说拒绝生活意志似乎就暗示了意志的自相矛盾。第二,如果意志是自在之物,世界形而上的规则和存在是一个整体,那么当其他事物没有同步时,个人通过拒绝生活意志获得解脱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叔本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困难并试图通过求助于神话传说来解决它们,如提倡“前世的经历”和“神的转世”④。王国维并不认为这些宗教神话能解决问题,他提倡世界之解脱必须在逻辑上优先于个人之解脱。因此王国维总结道:“解脱之足以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与否,实存于解脱之可能与否。”
王国维论述的另一点也值得关注。尽管通过禁欲寻求解脱可能不是伦理学上的最高境界,但它至少是一种理想境界。功利主义的伦理理想是寻求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在王国维看来,这种理想被实现的可能性值得怀疑。他强调生活存在两面,即度与量,这两者实际上互为反比例。
当世上有太多的生命时,其度一定会变到最低限度,因为世上的资源和范围有限。终极解决方案要么是限制世上的生命之量,要么是维持生命之最低标准。在这两者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功利主义道德理想和禁欲主义道德理想的不同都似乎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王国维用《红楼梦评论》创造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开拓之作。《红楼梦评论》写在一百一十多年前,当时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仍然是闻所未闻,因而我们不得不佩服王国维吸纳西方观点阐述中国文学作品的非凡能力。王国维的著作可能是现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著作中资历最老的,它倡导了一种研究《红楼梦》的新方式,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示范。
Western Philosoph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ongloumeng PingLun
〔US〕Ching-I TuTrans.Deng Mingjing
(1.Rutgers University,New Jersey,USA;2.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Hubei,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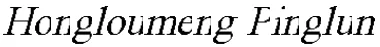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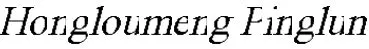
责任编辑:陈水云
涂经诒(1935—),男,湖北黄梅人,美籍华裔汉学家,1966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东亚系,获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罗格斯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系教授,曾任系主任及孔子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论研究。
邓明静(1988—),女,湖北安陆人,湖北大学《当代继续教育》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