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江西南昌330031)《〈尹文子〉序》之写作年代论略
——以公孙龙的学术史资料为观照背景
程水金
(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江西南昌330031)
汉唐以迄明清之际,学者皆以《史记》所载孔门弟子公孙龙与六国辩士公孙龙为一人,从而形成一种谬误的历史话语体系。因此,与辩者公孙龙相关的一切学术史料均与孔门弟子公孙龙发生年代误植。《〈尹文子〉序》称尹文与宋鈃、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正是这一年代误植所衍生的学术话语。而历来辨伪诸公不明是理,既据此年代误植而以《尹文子》为伪书,又以序文自署“仲长氏”为仲长统,进而定序文出于伪托。本文认为,年代误植,其来有自,不足以定《尹文子》为伪书,“仲长氏”亦非仲长统,乃仲长统家族晚辈。其序文写作年代当在魏晋易代之际。今存《尹文子》既非伪书,其序文亦非伪托。
公孙龙 尹文 仲长统 缪熙伯
一、问题缘起
先秦有两个公孙龙,一是孔门弟子公孙龙,字子石;一是六国时辩士公孙龙,字子秉。应该说,这已经是晚近以来学术界的共识,无所疑议。但在汉唐以前甚至直到明清之际,这两个公孙龙,却常常被误认为一人。对于此一问题,现代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曾先后著文六篇,集中讨论公孙龙其人其书之时代及其真伪问题。沈氏认为,中国历史上或曰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有三个不同的“公孙龙”。一是战国初年的孔子弟子公孙龙;二是战国末年的辩者公孙龙;三是晋代人心目中理想的名家或刑名家“公孙龙”。但孔门弟子公孙龙与辩者公孙龙是一直混淆着的,而辩者公孙龙与晋人心目中理想的公孙龙又是纠缠不清的。《汉书·艺文志》所载《公孙龙子》十四篇应是辩者公孙龙的著作,但后来消失了;现在流行的《公孙龙子》六篇则是“晋代人根据一些破烂材料编纂起来的”赝品。虽然我们不能苟同沈氏有关《公孙龙子》其书的最后结论,但其论证过程中提出的某些观念与看法,却颇能证明从汉人司马迁到唐人司马贞与张守节这两位《史记》专门家心目中只有一个公孙龙。
由此而来的连带问题则在于:既然由汉而唐,学人心目中只有一个公孙龙,那么,这个如此老寿的公孙龙也就既是孔门弟子,又是六国时著名辩者,其年辈与资历当然就是稷下学者尹文、宋钘、彭蒙、田骈等人的前辈老师。题名汉末仲长氏所撰的《〈尹文子〉序》,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向度之中形成的。然而,关于仲长氏所撰之《〈尹文子〉序》的真伪问题,却是近代辨伪诸公集矢之地,虽然也有学者以为《序》文非伪,但论证方法却存在较大漏洞,其结论当然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考虑到《〈尹文子〉序》的写作年代以及自唐以来关于公孙龙其人的学术史料背景,则很多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二、《序》文“疑点”之一与钱穆的解决路径检核
今传仲长氏所撰《序》文曰:尹文子者,盖出于周之尹氏,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著书一篇,多所弥纶。庄子曰:不累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于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见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刘向亦以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名家也,近为诬矣。余黄初末始到京师,缪熙伯以此书见示。意其玩之而多脱误。聊试条次,撰定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详也。山阳仲长氏撰。
这篇区区二百来字的短小《序》文,在疑古辨伪的考据家们眼里,不啻千疮百孔,疑误重重。就连《序》文作者没有自报其名,在考据家们有色眼镜的透视之下,竟然也成为造假作伪售欺的明显把柄。既有如此成见在胸,近代辨伪诸公当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条次撰定”的《尹文子》打入伪书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有此学术公案在前,而沈有鼎在讨论汉人心目中只有一个公孙龙的问题时,虽然也注意到这条材料,但却未加任何相关说明,恐怕难以杜绝辨伪诸公悠悠之口而取信于人也。因此,甄别《序》文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不仅是解决这一积年公案的唯一途径,也是讨论引向深入从而推进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否则,犹治丝益棼,徒滋纷乱而已。
首先,《汉书·艺文志》著录《尹文子》一篇,班氏自注:“说齐宣王,先公孙龙。”颜师古注:“刘向云:与宋钘俱游稷下。”《说苑·君道篇》载有尹文与齐宣王问答之事,而《吕氏春秋·正名篇》又载有尹文与齐愍王论士。则尹文的大致年代,当如四库馆臣所言:“殆宣王时稷下旧人,至愍王时犹在欤?”是尹文为齐宣王时稷下先生,而仲长氏之《序》乃与刘向所言以及《汉志》所载皆可相合。
然而,《序》云尹文“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却与《汉志》“先公孙龙”之说直接抵牾。而历来学者亦纷致其疑者,亦并非无的放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辨之曰:“《史记》云公孙龙客于平原君,君相赵惠文王,文王元年,齐宣王殁已四十余岁。则知文非学于龙者也。”而近人钱穆则以为《序》文当有脱漏,原文应是:
尹文子者……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钘、
彭蒙、田骈同学。[先]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钱氏认为:《序》文当本《汉志》“先公孙龙”之意而作,但今传《序》文“乃误脱一先字”。此其一也。其二,所谓“同学”者,“以当时稷下先生皆不治而论议。古者宦学齐称,今稷下之流,皆不仕,乃相谓同学。犹《史记》称‘荀卿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也’。当时稷下先生自避仕宦之名而称学者,后人不深晓,不察同学二字之意,遂妄疑其同学于公孙龙,遂为灭去一先字矣。”
晁氏的质疑,仍然是从年代学的考证入手,姑置无论。而钱氏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改动原文,将“同学于公孙龙”断为两橛,以“同学”二字属前为读,并在“于公孙龙”之前增一“先”字。钱氏之说,虽然甚辩且甚巧慧,但姑不论古人鲜有“先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之类如此冗散复沓的句式,即所谓“相谓同学”以及“同学”二字的这种钱氏用法,遍寻上古载籍,亦绝无证据。
按古人固然“宦学齐称”,且“学”或者亦可称为“宦”,但“宦”与“学”仍然有所不同。《礼记·曲礼上》“宦学事师”,孔颖达《正义》引熊氏(安生)云:“宦,谓学仕宦之事。学,谓习学六艺,此二者俱是事师。”又引服虔云:“宦,学也,是学职事之事为宦也。”是其例也。又,《左传》宣公二年赵盾见灵辄饿,问之,曰:“宦三年矣。”杜注:“宦,学也。”孔颖达疏:“《曲礼》云‘宦学事师’,则二者俱是学也。但宦者,学仕宦;学者,寻经艺;以此为异耳。”杜、孔之说,似乎可以为服、熊二氏之说添一佐证。然清人俞樾却有不同说法。俞氏曰:
古者学而后入官,未闻别有仕宦之学。疏说殊谬,杜训宦为学,亦非。《国语·越语》云:“与范蠡入宦于吴。”注曰:“宦为臣隶也。”灵辄所谓宦者,殆亦为人臣隶,故失所而至穷饿如此。僖十七年《传》曰:“妾为宦女焉。”杜注:“宦,事秦为妾。”此《传》宦字义与彼同。
据俞氏之说,则“宦”即是“宦”,“学”即是“学”,仍然有所区别。齐之稷下先生虽有俸禄但“不治而议论”,未必即如钱氏之说有所谓“自避仕宦之名而称学”。退一步说,即使稷下先生确有“相谓同学”之事,但考诸上古载籍,既无“相谓同宦”之“同宦”之说,更无因为要“避仕宦之名”而有与“同宦”的造词结构相当的“同学”一词,更不会有“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这种形如断尾巴蜻蜓之类的突兀句式。因为古人常有“(与某人)同学于某地某人”,或者径谓“(与某人)同学于某人”之类说法,而绝无“与某人同学”或“于某处同学”这类以介宾结构作状语修饰“同学”之近乎现代汉语的文句。谓予不信,不妨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角度,对“同学”一词的产生时代及其用法略作考察,以明其征。
检“同学”一词,意为同师受业者,大抵产生于西汉后期或者更晚。因为此词于《史记》中尚未出现,而《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乃有用之者,然仅有五例。录之如次:
(1)以令诒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2)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上〉)
(3)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
(4)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敛。(《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传·戴封传〉)
(5)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至权统事,以然为余姚长。(《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由(3)“同学者皆师之”一例可知,所谓“同学”,乃“同学者”一词的省略,因为其他四例之“同学”后,皆可加上代名词“者”字,即其明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学”一词,意即“同一师门受业的人”,其所表达的意义重心在“同”不在“学”,因而可以加上一个“者”字,将“同”字的意义再行补足。既然如此,则其词汇意义及其用法就与“与某人同学”之类句式中“同学”一词的句法功能完全不同。“与某人同学”这类句式中的“同学”,意即“在一起学习”,所表达的意义重心在“学”而不在“同”,因而不能在这类句式的“同学”后面加“者”字而说成“与某人同学者”,相反,倒是可以将“同”字省去,说成“与某人学”。因此,严格说来,这类句式中的“同学”二字,其词汇意义并不稳定,或者说,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词。
不妨稍加检证,假如将钱氏断读的“同学”,当作如同《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那样使用的一个词汇,在“同学”后面缀上一个“者”字,则全句就变成:“尹文子者……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者。”显然不辞之甚!而且同理,古人常用句式“(与某人)同学于某处某人”或“(与某人)同学于某人”,在“同学”之后也不能加“者”字,说成“同学者于某处某人”或“同学者于某人”,因为,如前所述,这类常用句式中的“同学”,所表达的意义重心在“学”而不在“同”,其“同”字可以省略,而“学”字则万不能省。因而此句可说成:“与宋钘、彭蒙、田骈学于公孙龙”,而不能说成:“与宋钘、彭蒙、田骈同于公孙龙”。所以如此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句中的“同学”,不是一个词,即不是现代语言学家所规定的“最小意义单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古汉语中“同学”二字虽然在西汉以前乃至西汉以后,可以连袂出现,但不是语言学家所规定的最小意义单位——词。而作为一个词的“同学”,则是“同学者”的省略,乃产生于西汉末年以后。二者的句法功能完全不同。至于现代汉语中“同学”一词,如:“我与某人同学”或“我与某人是同学”,后面无须带上介宾结构作补语(前一例虽然可以带介宾结构作补语,但是古汉语的遗留,并非纯粹的现代汉语句法),则与西汉以后从“同学者”省略而来的“同学”一词,其词汇意义及其句法功能显然不同。因此,钱氏所谓稷下学者因“避仕宦之名”而“相谓同学”,于古无征,想当然耳。
且也,即使在“同学”一词出现以后,也没有如钱氏所断读的这种如同现代汉语的词汇用法。更何况《三国志》的写作年代与《序》文的写作年代还十分接近,竟然也同样找不到钱氏这种用法的踪迹。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出:钱氏之说,将不是一个词的“同”与“学”读成一个词“同学”,而且钱氏这种读法的“同学”所显示的词汇意义及其语法功能,在与之同时代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是《序》本不误,而钱氏却以今律古,擅改原文,倘若斯文不幸依钱氏之所改而流传下去,则后人必考定《序》文乃使用现代汉语句法与词法,岂非《尹文子》又将成书于中华民国。噫,其可乎?有是哉!
三、《序》文“疑点”之二与辨伪诸公的解决路径检核
除“同学于公孙龙”之外,《序》文作者自称“余黄初末始到京师,缪熙伯以此书见示”,亦是自来疑古辨伪的考据家们作为“误点”而攻之不遗余力的集矢之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李献臣云:‘仲长氏,统也。熙伯,缪袭字也。’《传》称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年,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师’,岂史之误乎?”按李献臣指“仲长氏”为“仲长统”,乃据《后汉书·仲长统》本传而言。《统传》曰:“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故城在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传》既称统之籍贯为“山阳”,又称与东海缪袭为友,则李献臣以《序》文作者乃仲长统,而缪熙伯为缪袭之字,似有其据。且陈寿《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亦皆有明文可稽。陈《志》曰:“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郞。”裴《注》曰:“袭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世。”
稽考范晔《后汉书》有关仲长统的传记资料,其来源当是缪袭所撰《仲长统〈昌言〉表》。《表》文见于裴注《三国志·刘劭传》所引之《文章志》,其友人缪袭亦谓统于“延康元年卒,时年四十余。”唯《统传》“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与《表》文稍不同。考诸史历,汉献帝于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十月即禅位于曹丕,丕即改元黄初,行七年。则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甚至黄初元年,乃同指西历纪元之220年,因而皆可称之为“献帝逊位之岁”。则统卒之年,范《传》不诬。
然则仲长统既于“献帝逊位之岁”已卒,而《序》文所谓“黄初末始到京师”,距统卒之年,至少有六、七年之久,是指仲长统为《序》文作者,则不仅与范氏《后汉书》之〈仲长统传〉相抵牾,且与缪熙伯所撰《〈昌言〉表》文之说亦不合。
《传》与《序》如此相抵,最为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范氏《传》文有误,要么《序》文出自伪托。宋人晁公武即取前法,疑范《传》或误,故曰:“岂史之误乎?”而清人周广业则取后法,指《序》乃伪托,故曰:“恐是《序》出伪托,非史之误。”近人唐钺因周氏之说曰:“撰《序》的人是故作狡狯,影射仲长统。惟未细考仲长氏的年代以至露出破绽。”
如前所述,范《传》的史料来源是传主生前好友缪熙伯的《〈昌言〉表》,我们完全可以怀疑范氏网罗群言或有照顾不周之处,因而有可能将统卒之年弄错;但缪熙伯既为仲长统生前好友,又作《〈昌言〉表》以进呈于朝廷,决不至于竟在亡友物故之年上出现差错。因此,晁公武疑范氏《传》文之误,毫无道理。
既然《传》文决无疑误,那么,“《序》出伪托”之说是否可以成立?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从逻辑上说,两个相对的判断,不可能同真,但可能同假。而所谓“伪托”云者,乃本非其人而假托其人也。也就是说,此《序》文本来出自他人之手,而《序》文却署名于仲长统,此之谓“伪托”也。但《序》文仅署曰“山阳仲长氏撰”,并没有明确宣称自己就是“山阳仲长统”。而指《序》文作之于仲长统者,其人乃《邯郸书目》之作者宋人李献臣。乃宋人李献臣言之而宋人晁公武信之,近代辨伪诸公不之察,又从而狺狺佐讼不已,不知作者与仲长统有何隙何怨,必以如此“狡狯”手段“影射”之而后快?是以《序》为“伪托”者,乃宋人李献臣栽赃于前,而宋人晁公武提讼于后,至近代辨伪诸公,乃煅练罗织以成其狱,且横拉范晔出庭作证而已。
然考之原《序》,作者一则曰:“余黄初末始到京师”;再则曰:“山阳仲长氏撰”。其人非仲长统甚明。而李献臣读书不审,执意嫁名于仲长统,殊不知“始到”云者,首次之谓也,先前从未到过也。而《后汉书·仲长统传》既曰:“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三国志·刘劭传》亦明言:“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郞,早卒。”既然仲长统于汉末已为尚书郞,后又“参丞相曹操军事”,即使没有“早卒”,亦早已到过京师了,何待于“黄初末始到京师”?或者晁公武已经意识到李说有所未安,又自无主见,因而转述李氏之意后,曰:“《传》称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年,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师’”,竟将这极具关键意义的“始”字轻而易举地抹去了,则晁氏实在难脱隐瞒甚且篡改不利证据之干系!更何况“山阳仲长氏”者,乃一地方家族概念,可以“山阳仲长氏”自署者,岂独仲长统一人哉?李献臣《邯郸书目》见《序》有缪袭之字,又有“山阳仲长氏”之自署,便不问青红皂白,楞生生一口咬定仲长统其人而不肯稍纵!此非孟子之所谓“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邪?难道“山阳仲长氏”家族除却仲长统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读书人了么?由此言之,则四库馆臣以多闻阙疑之语气曰:“其山阳仲长氏不知为谁?”其言最为通达,其心亦最为审慎。李献臣“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其立言不谨,贻惑后学千载有余,夫缀学之士,岂能不引以为戒?
四、《序》文写作年代拟测
准上所述,我们认为,《序》文作者应该是山阳仲长统这个家族的某个晚生后辈,因有其家族先贤仲长统与其友人缪熙伯的这层关系,于黄初末年第一次到京师时,便去拜访这位前辈学人缪熙伯。史称缪熙伯“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则黄初末年,仲长氏其人往谒之时,缪熙伯甫进不惑之年,约少仲长统五、六岁,当是此仲长氏之前辈,故《序》文不以“友人缪熙伯”相称。而缪熙伯为鼓励已故友人之后辈子弟读书,便出示所藏之《尹文子》一书让其过录。事后,其人认真研读,依其文意,反复推求,发现其书多所脱误(“意其玩之而多脱误”),于是“聊试条次,撰定为上下篇”,至于书中名理晦奥之言,则“亦未能究其详也”。准此,则作《序》之人既为山阳仲长统家族之晚生后辈,其作《序》之年,又不知当在“黄初末年”得书以后之若干年也,或者已至魏晋易代之后,亦未可知。假定其人黄初末年(226年)已二十岁,至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即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265年),亦仅六十岁。如其人寿至八十或九十,则可能至晋惠帝元康年间尚存。若其书为晚年撰定,则《序》之作年,竟在晋武帝之末年或晋惠帝之初元,亦未始不可能。至于《序》文之所以认为尹文“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此亦秉承汉人自来之说,以辩者公孙龙为孔门弟子耳。而作《序》者不以为意,既不之考亦无须考,徒为因袭时流之见而已,实无足怪者也。
五、本文结论
由于汉人心目中仅有一个孔门弟子公孙龙,提到公孙龙,就立即想到字子石,因而无分乎圣贤弟子与六国辨士。而魏晋之际不仅认为六国时辩者公孙龙仍然是那个字子石的孔门弟子公孙龙,并且还是尹文、彭蒙、田骈诸人的前辈老师,也就是说,这些“不治而议论”、其学虽“本于黄老”而“近”于“刑名家”的稷下先生们,虽其学乃渐行渐远,但其师承渊缘则仍在儒门,而孔门弟子公孙龙就是他们的嫡传先师。这既是魏晋之际的学术史观,也是仲长氏撰《〈尹文子〉序》的时代背景。因此,今传仲长氏所撰《〈尹文〉序》决非伪作,其中所谓“疑误”之点,在有关公孙龙其人的学术史料背景中皆可得到有效说明。而《序》作者仲长氏其人于黄初末年首次谒见缪熙伯,缪熙伯即以《尹文子》一书见示,《序》文作者乃引《庄子》而论其学,又引刘向说以“其学本于黄老”,而己意亦以为尹文之学其“大较”近于“刑名家”,是与后世目录学家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高似孙《子略》乃至《四库全书总目》之论尹文,皆有所不同。而这一点,正是《序》文所透露的学术世运消息之变,足觇魏晋玄理名辨之学方兴之渐。好学深思之士,自是心知其意,岂近代辨伪诸公孔见之所能及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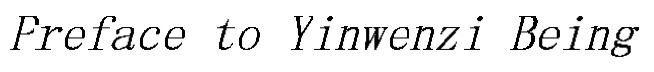
Cheng Shuijin
(Chinese Scholarism Institute,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Jiangxi,China)
Throughoutthe dynasties from Han&Tang to Ming&Qing,mostscholars have mistaken Gongsun Long recorded asthe followerofConfuciusin Shijiasan oratorliving in theWarring States Timehaving the samename.So allthe academic information involvingtheoratorGongsunLonghasbeen confoundedwiththe dataofConfucius fellowliving.So theaccount of Yin Wen learning from Gongsun Long with Yin Wen,Song Xing,Peng Meng Tian Pian in the prologue of YinwenZi is just the wrong academic word derived from this mistake.However,without knowing this causality,past scholars took YinwenZi as a pseudogragh;then considering the signature of prologue’s writterZhongchang Shi(meaning as whose family nameis Zhongchang)asZhongchangTong,they havejudged the writterofprologueistheonewhoforgestheancientpeople.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mistaking of two datas has its own source,which can be deficient to conclude YinwenZi is a pseudogragh,the writterwhose family name is Zhongchang should be the junior ofthis family rather than Zhongchang Tong himself.Thedataofthisprologue beingwritten should bethe changingtimebetween Weiand Jin.Remaining YinwenZiisneither the pseudogragh nor have a forged prologue writter.
Gongsun Long;Yin Wen;Zhongchang Tong;Miu Xibo
责任编辑:陈文新
程水金(1957—),男,湖北新洲人,现为南昌大学国学院院长、赣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