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北京100081)《论语》词语考释五则
——兼论“词的不自由”对字词置换的制约
杨逢彬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北京100081)
“予所否者”的“所”,不等于“若”,仍然是特殊指示代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则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后”不能训“不”。“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应断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而不应断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有教无类”属于当时常见的“有……无……”句式,其中“有”是存在动词。以上几则考释说明,由于词在句中不自由,校改或改读原文的前提,必须是原文“不词”。
所 可 后 惑志 关系
上
予所不者《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后几句《史记·孔子世家》作“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按,春秋及战国早期誓词中多有“所不”,如:
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见《国语·晋语四》,后句作“有如河水”)
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文公十三年)
所不此报,无能涉河!(宣公十三年)
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襄公十九年)
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襄公二十三年)
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襄公二十五年)
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定公六年)
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哀公十一年)
所不掩子之恶,扬子之美者,使其身无终没于越国。(《国语·越语下》)
不用“所不”者较少,如:“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左传》定公三年)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予所否者”即“予所不者”,否、不相通。至于“不”后面的成分,则省略了。孔子的意思大约是,我的话如有不可信的地方,“天厌之!天厌之!”这句的“所”,一般语法书或虚词词典(例如《古代汉语虚词词典》)都从王引之《经传释词》之说,说是表假设的连词,可译为“如果”“假若”。对此,我们不能同意。它仍然是特殊指示代词,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所”相同,表示“……的东西”“……的事情”“……的人”“……的地方”“……的原因”等等。
其理由如下:《经传释词》说“‘所’犹‘若’也”,所举例句有五,其中《诗经·墙有茨》“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左传》宣公十年“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孟子·离娄上》“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等3个例句中的“所”,明显都是代词;训作“若”,一般不为学者采纳,如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孟子译注》等。《古代汉语》注释“所可道也”即为“可说的话啊”,这当然是正确的。“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意为“如有可说的话,说出来也很丑”,“所”指代“话”;而表假设的“如”,是翻译时补出来的。《论语》文风质朴,往往不用假设连词“如”或“若”。例如:“(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排除了以上3个例句,剩下的就是所谓“誓词”了。一个连词,为何仅用于誓词,仅见于春秋和战国早期的几部文献;它从何而来,后来又怎么消失了;在共时语言系统中,它与其他假设连词的关系如何,等等,都说不清楚。但这些,并不是传统训诂所关心的。“所”唯一可解释为假设连词的理由,是它恰恰在假设句中处于假设连词经常所处的位置。故释为假设连词后,句子似乎依然“文从字顺”,而“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恰恰是传统训诂衡量词句解释是否成功的最高标准之一。
如前所述,先秦汉语的假设句,往往不用表假设的连词;而句中用以提顿的“者”,也可视为假设句的标记。如果这种表达方式继续存在下去,“所”有可能重新分析为假设连词;可惜它昙花一现,最终并没有证据表明它已经成为连词。但若将“所”解释为特殊代词,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1.这些誓词中的“所”,后接一谓词性结构,和特殊代词“所”的后接成分十分接近。2.它的引申来源也清楚了。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从‘处所’之义引申之,若‘予所否者’‘所不与舅氏同心者’之类是也。”而特殊代词“所”也正是从“处所”义引申出来的。3.它的去向也很清楚了。随着这种誓词的逐渐消失,存在于这种誓词的特殊代词“所”当然也不见了,但依然存在于其他句式中。《左传》定公三年的“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在成书较晚的《公羊传》定公四年中即为“天下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请为之前列”。4.以之解读这些誓词句,同样文从字顺。如“所不与舅氏同心者”,可译为“如有不和舅舅一条心的地方”“如有不和舅舅一条心的事情”。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杨伯峻先生《译注》说:“这两句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补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后来有些人觉得这种说法不很妥当,于是别生解释,意在为孔子这位‘圣人’回护,虽煞费苦心,反失孔子本意。如刘宝楠《正义》以为‘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字亦指弟子’。不知上章‘兴于诗’三句与此章旨意各别,自古以来亦曾未有以‘民’代‘弟子’者。宦懋庸《论语稽》则云:‘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则原文当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恐怕古人无此语法。”我们以为《译注》所说是正确的。
我们在《论语》《左传》《国语》《孟子》里考察了全部共1683例“可”(《论语》156例、《左传》822例、《国语》447例、《孟子》258例),这4部典籍中罕见主语后直接接一“可”字作谓语者;即便有,如“赵衰曰:‘郄縠可’”(《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也是说“郄縠这人可以(胜任)”,却没有一例主语直接接“可”字可以确定是表示某某同意某某认可的(即“以为可”,实际上是“可”的意动用法)。类似前者的还有一例:“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襄公三年)以上3例郄縠、午、赤都是专有名词。主语直接接“可”的否定形式表示某某不同意,某某不认可,在这4部典籍中并不罕见,如:
子良不可。”(《左传》宣公四年)
公赂之,请缓师,文子不可。(成公八年)
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昭公二十五年)
赵孟不可。(定公十三年)
白公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可。(哀公十六年)
以上5例“不可”都是“不同意”的意思。但主语直接接“可”字表示某某同意某某认可的,却似乎只有《孟子》中一例“百官族人可,谓曰知”。“百官族人可”似乎是“百官族人赞同认可”之意。但从赵岐《注》、朱熹《集注》到焦循《正义》均语焉不详,说不清楚;而且也均未在“可”下读断,而作“百官族人可谓曰知”。朱熹且说“‘可谓曰知’,疑有阙误。”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虽然在“可”下逗开,也只是说“他(指朱熹)也不甚了解,赵岐《注》也没说明白,暂且以我们的意思译出。”综上可见,将“民可”点断,理解为“民以为可”,是不可靠的。
同样,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不行的。《论语》时代语言中固然有“可使”“不可使”,但这“使”是“出使”的意思。《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沈玉成译:“他不配出使反而对使者骄傲,这是国家的蛀虫。”襄公二十六年:“公曰:‘诺。孰可使也?’”沈译:“晋侯说:‘好。谁可以做使者?’”类似的有《国语·晋语二》“知礼可使”,谓公子絷懂得礼数,可以出使也。我们只见到一例例外:“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榖与叶公诸梁,子谷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左传》哀公十七年)但“其可使”谓可使取陈麦,因上“取陈麦”(夺取陈国的麦子)而省,而“民可使,由之”却不具备这一条件。
郭店楚简《尊德义》:“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前两句多断作“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是不对的。除了上述理由外,“而不可使”的“而”字用法也不对,换作“若”“如”方可。断作“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则文从字顺。
与此相反,“民可使由之”的读法,在孔子时代的语言中,却是带有普遍性的。如:“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冶长》),“雍也,可使南面”(《雍也》),“仲由可使从政也与?……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求也可使从政也与”(《雍也》),“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先进》),“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左传》昭公元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告子上》),“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告子下》)。即使将范围缩小到以“民”为主语,我们也可找到诸如“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管子·五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管子·君臣下》)这样的例子。至于下句“不可使知之”,与《左传》庄公十六年“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类似的例子在那一时代的典籍中也并不少见,这里就不多说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王叔岷先生《古籍虚字广义》说:“‘后’犹‘不’也。”并论证之:
“后凋”之义云何?“后”盖与“不”同义,“后凋”犹言“不凋”耳。《庄子·德充符》载鲁哀公传国于哀骀它,哀骀它“闷然而后应,泛若而辞”(今本“若而”二字误倒,奚侗《补注》有说)。《田子方》载文王以臧丈人为太师,臧丈人“昧然而不应,泛然而辞”。两文末二句文义全同。“后应”犹“不应”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荀悦《汉纪》三“不”作“后”,“后”与“不”同义。晋陆机《拟古诗》:“嘉树生朝阳,凝霜封其条。执心守时信,岁寒终不雕。”《弘明集》七释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松柏岁寒之不凋。”刘子《大质篇》;“寒岭之松,处于积冰,终岁而枝叶不凋。”诸言“不凋”,正《论语》“后凋”之义也。
王先生所举第1例,并不足以得出“后”有“不”义的结论。1.且看,《德充符》和《田子方》两事并不相同:“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泛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德充符》)“文王于是焉以为大师,北面而问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应,泛然而辞,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田子方》)《德充符》中哀骀它确实是“应”了,“若辞”(好像要辞)却未辞。《田子方》中臧丈人却未“应”,而且也确实“辞”了。问题是,王先生是从奚侗之说将“泛而若辞”改为“泛若而辞”才得出了结论;而奚侗之说又是不能成立的。奚侗说:
“泛而若辞”,文不成义。当作“泛若而辞”。“泛若”与上“闷然”相对。
按,奚说才是“文不成义”。诚然,“若”可作为助词(有的语法书说是“形容词词缀”)出现在形容词后面,可译为“……的样子”“……地”,这一点和“然”类似;但是,与“然”可组成“形容词+然+而+谓语动词”结构不同,“若”不可出现在类似结构中。因此,我们可以见到诸如“腼然而入面”(《国语·越语下》)“攸然而逝”(《孟子·万章上》)“浡然而生”(《告子上》)“坦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我怫然而怒,……废然而反。”(《庄子·内篇·德充符》)“翛然而往,翛然而来”(《内篇·大宗师》)的许多例子,却未见一例“~若而……”的类似句子。杨树达先生说:“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然古人于此绝不留意,但随本文加以训诂,其于通例相合与否,不之顾也。故往往郢书燕说,违失其真,至可惜也!高邮王氏说经乃始注意即此,往往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故能泰山不移。”(《训诂学小史》,载《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奚侗之说“泛而若辞”,则不审句例之典型,而王叔岷先生从之,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对而言,我们以为陈鼓应先生《庄子今注今译》依武延绪之说将“泛而若辞”改为“泛然而若辞”较为合理一些。陈先生译“泛然而若辞”为“漫漫然而未加推辞”,而译“泛然而辞”为“漫漫然不作答”;两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然则,说“闷然而后应”与“昧然而不应”同义,则顿失犄角。
2.“而后”是一个固定结构,因此“闷然而后应”与“昧然而不应”语法结构并不相同,也即,前者是“闷然而后·应”,而后者是“昧然而·不应”。所以社科院语言所编写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解说“而后”为:“惯用词组,由连词‘而’和时间词‘后’组成。”其功能一为“连接时间上前后相承的两件事情或两种情况,表示后一件事情发生在前者之后。”一为“连接事理上具有条件关系的前后两件事,表示后一件事情的发生或出现是以前者为条件的,即先有前一件事,才能有后一件事。”显然,“闷然而后应”的“后”绝非“不”义。当然,王叔岷先生之举此例,显然只是犯了“前人训诂之学”“不审句例”的通病,是无可厚非的。王先生所举第2例,以荀悦《汉纪》为证,为举证不当。《汉纪》并非改写《史记·项羽本纪》之“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而是改写《汉书·高帝纪下》之“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纪》卷三改之为:“楚地悉平,独鲁后降。”这种改写当时很常见。《史记》之改写《尚书》《左传》《国语》,《汉书》之改写《史记》,都是如此。改写和被改写的文字,并不是每个字词都一一对应的。如果“独鲁后降”的“后”有“不”义,依王先生的逻辑,那么“独鲁后降”的“降”也有“下”义了。而且,杨树达先生说:“早些年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对于《汉书》,曾下过一点工夫,知道荀悦《汉纪》与《汉书》文字不同的地方,一定是《汉书》对,《汉纪》不对。后来偶读顾亭林先生的《日知录》,先生说了一句话,恰恰是这个意思。我当时一面感到前人读书的精细,一面自己也增加了一点校勘上的自信。因为我有过这样的实践,所以我现在可以大胆地说:荀悦这个人虽然是一个汉朝人,但是他对于《汉书》文字的了解力,实在是低能到万分。不过他虽然低能,胆子却又极大。他对于《汉书》的文句有不了解的处所,便毫不客气地大改特改起来,往往因此弄得牛头不对马嘴,将班固原文的意思丧失得干干净净。”按,顾炎武语见《日知录》卷二十六,原文为:“荀悦《汉纪》改纪、表、志、传为编年,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惟一二条可采者。”所以,王先生所举第2例,更不足为据。至于其余几例晋以后的诗文,说服力就更弱了。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前句或作“乱石崩云”,后句或作“惊涛裂岸”“惊涛扑岸”,难道能因此说“穿”有“崩”义,“拍”既有“裂”义,又有“扑”义吗?异文和互文一样,都不是语言内部的证据,只能作为旁证,不能作为主证,更不能作为唯一证据。而王先生往往以异文作为唯一证据。最后几例晋以后的诗文甚至连异文都算不上,就更缺乏说服力了。而且,一个词有本义和直接引申义、间接引申义,在词义的引申链条中井然有序;一个字也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要说某字有某义必须说出其来龙去脉。因为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试问“后”的“不”义是引申义还是假借义?是如何引申或假借的?这些都无法说清。可知这是一个伪命题。
本文下一部分指出,原文若经共时语言的全面考察而文从字顺,由于词在句中的不自由,词语置换(包括将某字读若某字)受到极大限制,其概率因而极低。此点必须注意。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宪问》:“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从“夫子”到“市朝”的断句有歧异。何晏《集解》在“固有惑志”后出注,曰:“孔曰:‘季孙信谗,恚子路。’”可见《集解》是在“固有惑志”后断句。而朱熹《四书集注》在“肆诸市朝”后才出注,并言“夫子,指季孙,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后人依据“其有疑于寮之言”,则多将“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一气读下。当今较好且较有影响的注本中,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潘重规《论语今注》、李泽厚《论语今读》等都将“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连读。杨伯峻先生译为:“他老人家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另外,分析《论语》句法的名著《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也是此十字连读。在“固有惑志”后断句的只有孙钦善《论语本解》和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断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我们赞成断开之说,理由如下:
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引子服景伯的话为“夫子固有惑志,缭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不但在“固有惑志”后点断,而且可以明显看出,“缭也”正是“于公伯寮”的改写。以下几点是语言内部的证据,更具说服力。
2.“有志”“有……志”的结构,一般其后都不接“于”字介宾结构。一般来说,动词谓语后接“于”字介宾结构在《论语》时代是很常见的。如:“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句为“逞寡君之志”,不带“于”字介宾结构;后句为“逞志于君”,带有“于”字介宾结构。又如:“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而杀之。”(《左传》成公十六年)“尔死,我必得志。”(哀公十一年)前一例接“于”字介宾结构而后一例无之。我们统计,《左传》中“得志”共计出现25次,其中12次后接“于”字介宾结构;5次后接“焉”字,如“苟得志焉,无恤其他”,而“焉”是“于之”的合音;只有8次后面无“于”字介宾结构。但是,“有……志”“有志”后接“于”字介宾结构却极为罕见。我们在《左传》《国语》《孟子》中共找到25例含有“有……志”“有志”的句子,其中只有《国语·吴语》的1例后接“于”字介宾结构:“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另有一例后接“焉”字:“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左传》成公十五年)其余23例都不接“于”字介宾结构,也不接“焉”字。如:
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左传》桓公十一年)
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僖公二十三年)
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宣公十七年)
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襄公九年)
诸侯有异志矣!(襄公十六年)
崔子将有大志。(襄公二十五年)
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襄公三十一年)
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定公四年)
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孟子·公孙丑下》)
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同上)
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万章下》《尽心下》)
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国语·周语中》)
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二年)
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昭公二十六年)另有两例“无……志”的例子,也不接“于”字介宾结构:“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左传》襄公三年)“子家弗听,亦无悛志。”(襄公二十八年)综上,应以在“夫子固有惑志”后点断为宜。
3.根据上引各例句归纳,“志”的意义为“想法”。“惑志”即“迷乱的想法”“胡涂的想法”。有的古汉语词典“志”有“志向”义而无“想法”义,恐怕不妥。其实,“想法”是涵盖“志向”的。用“义素分析法”分析可知,志向=[想法]+[大的]+[坚定],即“大的、坚定的想法”。上引各例中,“大志”可以解释为“大的志向”,但“贰志、归志、异志、他志、死志、去志”等词组中的“志”很难理解为“志向”,而理解为“想法”,则滞碍顿消。以上各词组分别为“另外的想法”“回家的想法”“不同的想法”“其他的想法”“必死的想法”“离开的想法”。即使“大志”理解为“大的想法”,也差不离。王力先生等所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志”的第一个义项为“心意”,得之。
4.“诸”为“之于”二字的合音字,而代词“之”一般不指代谓语后的“于”字介宾结构的宾语。代词“之”指代前面出现过的成分时,一般指代主语、谓语动词的宾语,或整个句子所指的事物;我们未见“之”指代介词的宾语,至少在《论语》一书出现的几百例代词“之”中,未见此种用法。一般认为,介宾结构的宾语在句中不是表述的重点,不是强调的对象。这与我们未见“之”指代介词宾语,应该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如果读为“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之于)市朝”,“之”指代的又是“公伯寮”而非“夫子”,那就正好是指代介词宾语了。这与我们的考察是不相符的。正因为后句的“之”一般不指代处于非强调对象位置上的介词宾语,所以,从语感上看,“之”更像指代“夫子”,但子服景伯显然不会将“夫子”“肆诸市朝”。而将“于公伯寮”断开,则完全不同了。何乐士先生在《左传虚词研究》一书中得出结论,“于”字结构前置,“大都出现在表示强调的句子中”。如:“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于文,皿虫为蛊。”(昭公元年)“许于郑,仇敌也。”(昭公十八年)“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哀公十三年)正由于“表示强调”,所以“于”字结构可以单独为一句。“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正是这样的句子。正因为此,太史公才能将它改写为“缭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5.如果读为“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从语法结构和词义上分析,也得不出“他老人家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的意思。如果要得出这个意思,介词“于”在此句只能用以引进施事者,同时它也是被动句的标志。但是,一方面,介词“于”表被动一般都紧接动词,“于”和谓语动词之间没有宾语。我们常见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之类“于”字紧接谓语动词的句子,罕见“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之类句子;另一方面,若要引进施事者,充当谓语者必须是与主语、宾语可以建立广义施受关系的行为动词、关系动词、状态动词,“有”却是存在动词。张猛在《左传谓语动词研究》中说:“行为动词……通常主语是施事,宾语是受事。……表示动作的施事的成分如果要出现在行为动词的后面,必须通过介词‘于(于)’引进。……关系动词在语义功能和结构形式上都与行为动词相似。”而“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的“有”是存在动词。在存在动词作谓语的句子中,表示拥有者或存在者的成分通常处于主语的位置上,表示所拥有者或供其存在者的成分通常处于宾语或补语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存在动词与主语宾语之间并非广义的施受关系,自然也就不可能通过介词“于”引进施事成分于动词之后。我们通过对《左传》中1206个存在动词“有”的全面考察,情形也确实如此。至此,可以明确地说,“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决不能译为“他老人家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
6.有鉴于此,“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的“于”诚如许世瑛在《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中所分析的,只能“相当于白话的‘对于’”。于是,“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他老人家固然对于公伯寮有胡涂想法,但我的力量还能把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后句的“他”,如前文所说,在语感上,无论原文或译文,都是“夫子”而非“公伯寮”。但显然,子服景伯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要想表达“夫子固然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或类似意思,一般会写成“夫子固惑于公伯寮”,如:
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国语·晋语一》)
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管子·君臣上》)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荀子·正名》)
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其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吕氏春秋·慎行论》)
因为“惑”属于状态动词,自然可以通过介词“于”引进施事。以上6点,足够证明在“固有惑志”后点断是正确的;“于公伯寮”则单独为一小句。

有教无类
《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何晏《集解》引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见教,即被教。马说意为所有人都被教育,不分种类。赵纪彬《论语新探》中有《“有教无类”解》一文,影响很大。赵文说:
自东汉至今,解者有马融、程颐、朱熹、王船山、冯登府、刘宝楠、刘恭冕、章太炎、梁启超和今人冯友兰先生等十二人。就中除王船山而外,均以此章为孔丘自述教育宗旨,义即不分尊卑贵贱,不问出身,超阶级地教育一切人。今按:此种训解,纯系望文生义,揆之《论语》全书,毫无根据。
又说:
总而言之,《论语》‘有教无类’的‘教’字,乃是奴隶主贵族对于所域之民施行的教化,发布的教令,以及军事技能的强制性教练。但是,不论政治经济上的教化、教令,或军事战阵上的技能教练,全为上施下效的强制性措施,目的在于将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精神绳索强加于民,迫之必从,而与在‘人’的内部进行‘诲知’的教育,有严格的阶级界限,不容混同。
赵氏还认为,“无类”不是不分“种类”,而是不分“族类”。
“教”“诲”二词究有何不同,《王力古汉语字典》说:“两个词都有‘教导’义,但有细微差别。‘教’带强制性,‘诲’重在启发、诱导。”我们以为这一解说是比较正确的。教,教育,教导,传授。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作名词或动词,在词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赵氏“教”“诲”两词的例证,局限于《论语》一书;而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具有强制性的,用于人类交际的符号系统。也即,使用者必须遵循当时当地时空中的所有使用该语言的人的使用习惯。这就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当时当地其他记录同一语言的典籍来认知该语言。具体到“教”“诲”两词,可以通过《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来考察其词义。通过这一考察可知,它们绝非如赵氏所云“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如,“教”的宾语经常是国君、贵族。例如: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称“郑伯”,讥失教也。(《左传》隐公元年失教,谓失教于共叔段)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隐公三年)
见大子,大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闵公二年教之,谓教导太子)
晋侯使郄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僖公十五年之,指郄乞)
(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僖公二十三年子,指狐毛、狐偃,跟随重耳逃亡的贵族)
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襄公三年)
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国语·周语上》)
子教寡人和诸戎、狄而正诸华,于今八年。(《晋语七》)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梁惠王上》)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同上)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
教人以善谓之忠。(同上)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离娄上》)相较于“教”,“诲”的书证较少,但其宾语也有为“民”或指代“民”的: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故诲之以忠。(《左传》昭公六年)
是故圣王……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墨子·辞过》)
正因为“教”“诲”词义相近,当时就常结合成一个同义词组:
文公问于胥臣曰:“吾欲使阳处父傅讙也而教诲之,其能善之乎?”(《国语·晋语四》)
若是,则文王非专教诲之力也。(同上)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墨子·明鬼下》)
古之圣王……发宪布令以教诲。(《非命中》)
综上,当时语言中的“教”“诲”二词是没有什么“严格的阶级界限”的。
为了证明“有教无类”“乃是奴隶主贵族对于所域之民施行的教化,发布的教令,以及军事技能的强制性教练”,作者强为之说曰,“有”通“域”。实际上,“有……无……”是《论语》时代的语言中的常见句式,我们至今常说的“有备无患”即属这一句式。其中的“有”当然是“有无”的“有”。例如:
凡天灾,有币无牲。(《左传》庄公二十五年沈玉成《左传译文》译为:“祭祀时只能用玉帛而不用牺牲”)
必报德,有死无二。(僖公十五年沈译:“有必死之志而无二心”)

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襄公三年,又见《国语·晋语七》沈译:“在军队里做事宁死不犯军纪叫做‘敬’”)
《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襄公十一年沈译:“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
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襄公二十四年沈译:“有基础才不至于毁坏”)
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襄公二十六年沈译:“有礼仪就没有败坏”)
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哀公三年沈译:“有不卖力气的,就按规定处罚,不加赦免”)
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罢(疲)。(《国语·周语中》)
必事秦,有死无他。(《晋语三》)“有教无类”属于这一句式,其中的“有”当然是有无的“有”,是存在动词。当然,它绝不通“域”。
因此,“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便是“有教无类”,即不分类别,人人我都教育。
本文下一部分对这一则考释有所总结,可结合着看。
下
引子:关于唯一性和排他性读者不难看出,以上五则考释除第一则外,都是在原有诸家的考释中证明孰正孰误,而未独出机杼,发为新解。有专家审阅我的书稿后得出结论说,该稿的缺陷是创新性严重不足,因为该稿主要证明以往诸家之说孰正孰误,而少否定各家而独辟蹊径,提出新解者。对此,我不能认同。考释以往众说纷纭未臻一是的疑难词句,第一个步骤是考察以往诸家之说中,哪家之说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也即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如果某家之说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也就意味着其他各家之说不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同时也就意味着再做任何独出机杼的新解,必定归于失败。这是因为正确结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固然,歧义词组和歧义句是存在的,例如“咬死了猎人的狗”和“我在屋顶上看见了他”,一为歧义词组,一为歧义句。但歧义词组和歧义句占词组总量和句子总量的比例极低,且大多数歧义词组和歧义句在具体语境中都可化解,如“我在屋顶上看见了他”之前或有“我站在窗前”或之后有“于是我叫他赶快下来”,都不致造成是说话人站在屋顶上的歧解。因此,实际语境中几乎所有的句子都是非此即彼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原则即基于此点。
除非以往诸家之说都不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即在当时语言中扞格不通,这时才有独出机杼发为新解的必要。但这新解必须是在全面掌握语料的基础上得出,而且放到特定上下文中必须文从字顺。从我们的实践看,以往诸家之说都不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这种情形是有的,但并不多见。所以我们独辟蹊径的新解,所占比重在全稿中所占比例也就不高。
但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有一个前提,即考察以往诸家之说中,哪家之说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也即哪家之说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进而确定其他诸家之说的非正确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王力先生说:“假定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我们试把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可能这十种意见都是新颖可喜的,但是不可能全是正确的。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但是也可能十种解释全是错误的,因为都是先假设了一种新颖可喜的解释,然后再乞灵于‘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那末,这些假设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王力先生指出的“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许多学者依然认为解读某一词句十人十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此种背景下,谁的说法最好,就如王力先生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所指出的,端赖“新颖可喜”。而“新颖可喜”的最重要指标便是能否“截断众流,独出机杼”。一部解读古书疑难词句的书中,却没有多少“截断众流,独出机杼”之说,当然便是“严重缺乏创新”了。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讲求可验证可重复的,也即用某种科学方法研究某一问题,多人分头研究,最终殊途同归。这点我们在《〈论语新注新译〉导言》已有所阐述,此处不赘。具体到考释先秦古籍疑难词句,如何做到殊途同归呢?笔者初步结论可粗略总结为“一堵一疏”。
堵:校改或改读原文的前提,必须是原文“不词”
我们在《〈论语新注新译〉导言》中指出了一种解读古书的常见的错误做法。第一步,常常是指出现在通行的理解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例如孔子)的一贯思想,等等,因此这句话必须重新解读。第二步,或者是改变句读从而改变句子结构;或者是说对某词某字应重新理解——通常是找出该词该字的某个很偏的意义放入该句子;如果实在找不到该字作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或是通过故训、因声求义等办法,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除改变句读,其余的我们姑且统称之为“字词置换”。然后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学者们往往注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迭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
为什么说这种做法错误呢?因为它是从语言系统外部去求证的。我们在《导言》中曾经指出,语言是一个系统,而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的证据,其可采信度相差极大,绝对不能等量齐观。那篇文章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此不赘。
我们是由孔子的语言得知他的大体思想的。然后,再由他的思想去反推他的语言,以达到细化或具体化他的思想的目的,这本身就是循环论证。此点我们也不想多着笔墨。我们要说的是,某一传统的解读如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似乎不相符,引起怀疑是可以的,但怀疑本身并没有成为证据。好比由某人的几次偷盗行为确定该人是小偷。该地还有几次偷盗没有破案,我们可不可以怀疑就是这个小偷施行的呢?当然可以怀疑。但怀疑本身不能成为证据,还得在偷盗行为本身上找证据。与此类似,要证明古词句的确切含义等语言问题,还得在语言本身即语言内部找证据。因为,词语是表达概念的符号,它并不与思想直接挂钩。因而从思想、情理等等“不合”引起的怀疑或推测,顶多只能成为一项假设。那么,这种假设有多大可能确实是真的呢?这就要从词的不自由说起。
陆俭明说:“现代汉语中动词作句子的谓语并不自由,要受到很大限制。有相当一部分动词(约占50%)根本就不能单独作句子的谓语。……另有约50%的动词,如‘喝、去、知道、抽、说’等,虽然可以单独作句子的谓语,但也要受到语义上的限制。只有在表示意愿、对比或祈使的句子中,这些动词才能单独作句子的谓语。”郭锐说:“语法位置对进入的词语有选择限制。”正如德·索绪尔所指出的,在语言系统中每个要素的位置主要是由它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决定的。其实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也无论是动词还是其他词类,由于上下文各语法成分的限制,进入某一语法位置都是不自由的。拿动词来说,每一动词都有自己的论元结构,即每一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各不相同。我们假设某一句子中主、宾语已经确定,那么,可以填进谓语位置的动词就只有若干个,而绝不是所有动词。所谓词的不自由即指此。词在组合中不自由,指特定句子限定了其中某一语法位置上只能出现一组词而非某一词性或某几种词性的所有的词(因为同一语法位置可以出现不同词性的词)。词在聚合中不自由,指这一组词是有选择性的而非任意的。
姑以上文第二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来作为例证,“由”所出现的语法位置上,可以出现若干词。如果我们将“由”“知”互换位置,作“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大约这样的句子出现在《论语》成书的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由”的位置上可以随意替换任何动词。
“截断众流,独出机杼”的创新者所用的方法往往是替换句中某一个词(或换字以换词,或不换字而将原字读若另一字,或不换字而将原字理解为另一词)。假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出现于《论语》成书年代的语言中,是文从字顺的,句中的“由”却并非原住民,原住民另有其人,例如是“抽”“迪”(二字皆以“由”为偏旁)或“遊”(与“由”古音相同)中的一个;由于词的不自由,从上述几个字中的某一个讹误成“由”而这两句依然文从字顺,其概率微乎其微(即,可以在“由”的语法位置上出现的词,与上列几个字重叠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后者的标准是形近或音近,与前者候选标准不同)。相反,概率极大的是,1.如果“由”本误字,或误读(即“由”字不误,但应读作某字),那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传统的理解)不能文从字顺,而应为所谓“不词”;2.如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文从字顺,则主张改“由”为某字或读“由”为某字者不能文从字顺,而应为所谓“不词”。由此可知,a.如果古书中某句话文从字顺,则不应怀疑有误。b.怀疑有误而改之,基本上不会正确。c.校改或改读原文的前提,必须是原文“不词”。
如果古书中某句话文从字顺,而认为这句话中本有误字,或这句话中某字应读为另一字,这样的概率可说是微乎其微(因为某语法位置上的候选词有限,原为某字,恰恰错成候选词的某字,这样的概率很低)。即使微乎其微,我们且放大其概率,假设这依然是可能的,那下一步便是填进去某字,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应该填进某字而不是其他字呢(1.填进此字虽经“考证”,但从语言系统外考证,等于没考证;用故训、声训、形训等等说两字相通,也仅仅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也等于没考证。2.某语法位置上的候选字不止一个)?这又是一个低概率。而且,认为某字有误,便只能从与某字形近或音近的字中去选择,但形近或音近的也只有若干个字,这若干字与误字所在语法位置上的候选字重叠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又是一个低概率。几个低概率相乘,其可能性几乎为零是不言而喻的。如认定“民可使由之”的“由”有误,而填进去“遊”字,作“民可使遊之”;但“遊”有绝大可能性不是“由”所出现的语法位置上的候选字。所以,在原文文从字顺的情况之下,仅仅根据情理、思想等语言外因素就认定(而非仅仅怀疑)原文有误,而用其他字、词置换,是十分危险的。
有人可能说,我改为“民可使遊之”不也文从字顺吗?且慢,我们这里所谓“文从字顺”不是光凭感觉的。《诗经·终风》“终风且暴”的“终风”之释为“西风”“终日风”感觉上似乎也文从字顺,但经高邮王氏一考察,就掉了底子。我们所说的“文从字顺”,指的就是要像高邮王氏之考察《终风篇》那样,也进行一番共时语言的全面考察而得出的结论。这正是下文要说的,此处不赘。有人可能会说,高邮王氏岂是你能够学到的?我们说,高邮王氏之释“终风且暴”那样精湛绝伦的妙技,古人很难学到。因为,他不如王氏那样博闻强识,他不如王氏那样藏书丰富。但到了E时代,只要你在这个知识爆炸却举世嚣嚣,“众皆竞进以贪婪”的时代坐得下冷板凳,这一目的是有望达到的。
同样,改变句读从而改变句子结构“制造”的句子,也不能凭感觉以为“文从字顺”,同样必须对它进行一番共时语言的全面考察。事实上,如同上一部分第二则所证明的,这种人造的句子在当时往往是扞格难通的。所以,上述“校改或改读原文的前提,必须是原文‘不词’”,对于“改变句读从而改变句子结构”之例,同样管用。
但如果原句经过共时语言的全面考察而不能文从字顺,当我们认识了“词在句中不自由”之后,反而能推论出正确的考据其实是很可靠的。所谓“正确的考据”有一前提,即经过共时语言的全面考察是文从字顺的。在此前提之下,为什么很可靠?第一,某一语法位置上所出现的字词有误,而这一语法位置上的候选字其实有限,而非以前认为的数不胜数,这就大大缩小了范围。第二,某字词有误,而误字一般只能从形近或音近的若干个字中间去寻找,这也大大缩小了范围。第三,候选字采用的是语法标准,形近或音近的字是采用其他标准,这就好比平面上两条不平行的线必然相交,它们相交的那个点上出现的那个字词,就是原句讹误之前的那个字词。我们以王念孙的考据名篇为例:
《(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释文》:“佳,善也。”河上云:“饰也。”念孙案,“善”“饰”二训皆于义未安。……今按“佳”当训“隹”,字之误也。隹,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维”)。唯兵为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上言“夫唯”,下言“故”,文义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争,故无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皆其证也。古钟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
首先,“佳兵”不词。周秦文献中,“兵”从不受“佳”这类词修饰。而“佳”也只出现在“佳丽”“佳人”这些词组中。这就符合“原句不能文从字顺”这一条件。而“夫□……故……”的□这一语法位置上可以出现的字词可谓是极少的,而且必须首先从与“佳”形近或音近的字中间寻找,结果“隹”是唯一的候选者。将它置换“佳”字,也文从字顺。
可见,原句是否文从字顺,是进行字词置换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原句文从字顺,进行字词置换绝难成功;原句不能文从字顺,进行字词置换则有可能成功。但要做到后者,绝非易事。
下文将要提到的王氏对“终风且暴”的“终”的精湛考释,也是字词置换。与上引将“佳”置换成“隹”这种文字的置换不同,《终风篇》的置换只是词的置换(例如将“终日”换成“既”),而未置换字形。对于换词不换字这一类型,原句文从字顺,进行词的置换更不可能成功;原句不能文从字顺,进行词的置换成功几率则更高,且进行置换相对较为容易(因为就在该字形的词和义位中找寻原词或原义位)。限于篇幅,稍暇笔者将将此论文下一部分在进行升级扩容后对此展开深入论述。
其中,发现原句不文从字顺,相对较易;找到原词尤其是原字从而成功实现置换,尤为大难。王念孙的伟大,于此可见。必须老实承认,我的新著《论语新注新译》的160余例考证中,没有成功换字的考证。同时必须指出,各学术期刊、论文集中我所见到的字的(而非词的)置换论文,也没有一篇能望王氏的项背。
由上文又可见,以上各步骤,都是在语言系统内部来求得解决的,而与情理、思想等无涉。原句文从字顺,仅仅根据思想、情理的可疑便进行字词置换,根据以上论证,可说是此路不通。
疏:通过考察各要素的关系确定词义
我们在《〈论语新注新译〉导言》中说:“王氏父子固然十分注意采纳故训(古代注家如何说,《说文》如何说,等等),采纳因声求义的办法(例如释《老子》“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的“施”为“迤”,意为“邪”),以及采纳辨析字形,特别是通过出土文献辨析字形(如释《左传》隐公六年“从自及也”之“从”为“徒”;又如上引释《老子》“夫佳兵者”,为“夫唯兵者”,说“隹,古‘唯’字也……古钟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的办法。但是,综观王氏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干名篇,其中起关键作用而不可或缺的是,征引大量的书证,特别是与被证词句同一结构同一句式的书证。其原理,无非是通过综合归纳抽绎这些书证,考察疑难词句所出现的上下文条件。”我们也照此办理。为什么非得如此?因为,诸如故训、因声求义、辨析字形等等,都只是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古代注家往往也是言人人殊的,当此之际,我们何所从乎?但既然在语言系统中每个要素的位置主要是由它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我们便可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考察弄清楚该位置上是A要素还是B要素、C要素。因为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一旦梳理清楚这种关系,该要素的意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这样做,较之义训、声训和形训的使用更为有效,而得以成为高邮王氏的不二法门。当然,王氏是将它与义训、声训和形训配合使用而相得益彰的,但两者的轻重和所起的作用显然有别:前者是自足的,而后者是非自足的。
以《论语·学而》“贤贤易色”为例。当时“易”两个意义,一为“交换”,一为“轻视”。如为前者,“贤贤易色”的意思就是孔安国所说的“以好色之心好贤”;如为后者,它的意思便是“重贤轻色”。我们可将“易”的两个意义视为A要素和B要素。通过对共时语言的全面考察,我们注意到A要素出现的位置大多为“以……A……”的句式,如《左传》僖公三十年的“以乱易整,不武”,又如《孟子·梁惠王上》及《滕文公上》的“以羊易之”“以小易大”“以粟易之”。但偶尔也会是“A之以……”或“与……A……”,如“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孟子·梁惠王上》)“逢丑父与公易位”(《左传》成公二年)。即,A要素须与介宾结构共现。
而B要素,则直接带宾语:“虢必亡矣。……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左传》僖公二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襄公四年)“己丑,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易秦故也。”(襄公十一年)“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襄公十三年)“且夫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国语·晋语七》)
可见,“贤贤易色”句式正同“贵货易土”,为两个谓宾结构组成的联合结构。
说得更具体一点,1.特定的上下文锁定了多义词诸多义位的一个。2.既然每个句子中的词都受其他词的限定,通过对处于组合和聚合矩阵中的特定词的考察(例如对“终”在“终风且暴”“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中的考察),就有可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被考察词在句中的意义。我们将其总结为“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如以上书证归纳出“终~且~”这一格式,“终”在这一格式中的意义也得以凸显。
又如,赵纪彬《论语新探》说“有教无类”的“有”通“域”。我们在本文第五则考释中通过对共时语言中“有币无牲”“有死无二”“有备无患”“有基无坏”“有礼无败”“有常刑无赦”“有优无匮”“有逸无罢”等共时书证的汇集,归纳出“有……无……”的格式。“有教无类”属于这一格式,其中的“有”是存在动词,当然不会通“域”。
“贤贤易色”的考察,也是通过书证的汇集与格式的归纳,从而弄清楚在“贤贤易色”这一组合中“易”的确切含义的。
本文的其他四则词句考释,也是这样做的。
高邮王氏父子的代表作也都是这么做的(详见《〈论语新注新译〉导言》)。
这样做,是符合“语言学主要是研究语言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
一旦这样做了,由于某一共时语言中被考察要素与周边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只要具备一定语言学素养且能读懂古书的人去加以考察,其结果往往殊途同归(详见《〈论语新注新译〉导言》)。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翻阅一下“截断众流独出机杼”的研究,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研究一般不会通过书证去归纳格式,从而弄清楚处于某一格式中的词的确切含义。它们往往将怀疑或假设当作证据本身,然后通过只具有可能性而缺乏必然性的故训、因声求义、辨析字形等,尽量往他们预设的方向靠拢。一旦靠拢,这一考据便大功告成;于是便宣称只有这样,才是“正解”,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云云。用这种“方法”对同一词语加以考察得出的“成果”,往往会多种多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知道,合于词句原义的结论只有一种,而错误的结论则可能无穷多。按考察疑难词句上下文条件即考察与其他要素关系的办法,十个人得出结论往往殊途同归,这与“合于词句原义的结论只有一种”相吻合;沿着思想、情理推导语言的法子去做,得出的结论往往言人人殊,这与“错误的结论无穷多”相吻合,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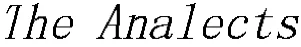
Yang Fengbin
(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cademy,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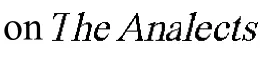
Suo;Ke;Hou;Huo Zhi;Guan Xi
责任编辑:卢烈红
杨逢彬(1956—),男,湖南长沙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史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考释先秦汉语疑难词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