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论唐宋诗歌对偶之新变
罗积勇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相对于魏晋六朝,唐宋诗歌对偶发生的变化主要在于:借对的出现,假平行对和流水对的自觉经营与普遍使用。催生变化的原因是相对固定的对偶形式与不断变化的表现内容间的矛盾。由唐到宋其间对偶也发生了变化:第一,突破了天然成对的局限,取得了以对偶的语言形式表现任何事物的经验,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数字对上。第二,宋人力避唐诗对偶之滑熟,而在声律、句法和意象选取方面作了种种新的尝试,为后人留下了经验与教训。
对偶方式 语言形式 声律 意象 变化
“唐宋对偶之变”有两重意思:一是相对于魏晋六朝,唐宋时发生的变化;二是指从唐代到宋代,其间对偶辞格在运用上的变化。
唐代是一个在文学方面登上新高峰的时代。在诗歌方面,近体诗平仄、粘对和押韵的规范已经初步形成。此时唐人一方面欲变革六朝形式至上、以辞害意的流弊;另一方面,他们又酷爱诗文的对偶形式。于是,唐人致力在形式维护与内容准确表达之间寻求平衡,深入挖掘汉语语言文字的潜力,创造了既表面照顾工对、又不影响内容表达的借对形式。唐人还创造性地运用假平行对、流水对和数字对。宋人在对偶运用的许多方面均承唐而发扬光大,但同时他们也力避唐诗对偶之滑熟,而在声律、句法和意象选取方面作了一改唐法的种种尝试。其目标是达致“瘦硬”之美,但他们的尝试有成功之处,也有不成功之处,为后人留下了经验与教训。
一、为了达到对偶的工整效果而又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唐人尤喜用借对
自南北朝后期以来,文人们就特别注重对偶的工整,这在当时一些著名作家如庾信、何逊、阴铿等人的诗中表现尤为突出。自唐以来就更强调工对,从《文镜秘府论》所录之唐人诗话中不难看出唐人对工对的偏好。但与此同时,当时的诗文评论者也在强调辞不害意,强调诗要有气势,有气韵。事实上这二者是有冲突的。让我们看看唐代诗人是怎么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他们主要是在科举考试时严守声律、对偶之苛刻规则,在平时创作中,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另一方面,在矛盾出现时,他们创造了既不影响意思表达又在表面上可以“合式”的办法,如“借对”、拗救等。这样,在唐代,关于对偶的两种对立的主张,在诗人的实际创作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为了达到工对效果而又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唐人尤喜用借对。借对,是一种变通理解的工对,即如按作者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来理解,其对偶并非工对,但如对某些影响对偶工整的字词按同音联想或多义联想来理解,则便符合工对要求。借对分借义与借音两类。

所谓借义,是发生在多义字词本身,当说写者所用该多义字词的某个义项与另一句中相对应的字词并不能构成严整的对偶,而该多义字词的另一个义项,却能与之构成严整的对偶时,说写者便藉此诱导读者,让读者想起这另一个义项,以其意义来满足工对的要求。如杜甫《曲江》诗曰:“酒债寻常处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按诗意,“寻常”是平常的意思,此义与对句的“七十”对不上,但“寻常”又是长度单位,古八尺为寻,二寻为常,这个义项是数词,与“七十”正好相对。古尺比现在短,平伸一手约当“寻”,平伸双臂约当“常”,故“寻常”可引申出平常义。因此,在对句“七十”的诱导下,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寻常(平常)”的另一个数字义。
唐代诗人所借之“义”有时是固有义项,有时则是修辞临时义。据笔者分析,其借义之途有三:
第一,借用多义词的固有义项。前举杜甫诗“寻常”一词即是如此。
第二,借“简称”的字面义。温庭筠《山中与诸道友夜坐闻边防不宁因示同志》:“龙砂铁马犯烟尘,迹近群鸥意倍亲。风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戊己:汉代有戊己校尉,此为其简称词。庚申:道教认为人身之内有三尸虫,每遇庚申日,乘人之寐,向上帝诉人之过。所以道家于此日,辄不寐以守之。“戊己校尉”与“庚申日”二义本不对偶,但是其简称“戊己”与“庚申”均为干支,可借字面形成工对。
唐代科举考生所作试律诗中此类借对颇多,如顾封人《月中桂树》:“能齐大椿长,不与小山同。”大椿:《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后以大椿喻指长生。小山:《楚辞》淮南小山《招隐士》有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巃嵸兮石嵯峨。”此句言月中桂树与淮南小山所咏桂树不同。此处“小山”本指“小山辞赋中所说桂树”,但又借“小山”字面义以与“大椿”相对。此亦与简称有关。
又如薛存诚《御制段太尉碑》:“雅词黄绢并,渥泽紫泥分”。上句中的“黄绢”,字面上虽与“紫泥”构成对偶,但实际上,“黄绢”是“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缩略语,这八个字是“绝妙好辞”的隐语,原是蔡邕用来称赞东汉曹娥碑文的话(详见《世说新语·捷悟》)。
类似的例子还有张叔良《长至日上公献寿》:“九重初启钥,三事尽称觞”。这里的“三事”是“三事大夫”的缩略语,即指三公,此特指上公。它在语里上与“九重”并不对偶,但作者借字面义与之对。
第三,借复音词中的“字”的其他义项。复音词词义与词中“字义”(语素义)的不尽一致,这一点也可帮助构成借义对,如王良士《南至日隔霜仗望含元殿炉香》:“节当南至日,星是北辰天”。“南至”:指冬至。因为冬至时太阳最偏南,故又称南至。在这一词中,语素“南”加语素“至”的意义并不完全与“南至”的词义吻合,与“北辰”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故“南至”与“北辰”在语义上并不对偶,但在字面上却对偶。

借音对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对子中某一单音词在意义上并不符合工对要求,但与这个词同音而未出现在该句中的另一单音词的意义却符合此处的工对要求,于是作者有意诱导读者想起这个词,以成全工对。如“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柏”与“百”同音,而“百”与“九”构成工对。
文中用到的这个单音词与作者诱导读者想起的同音词二者在意义上一般没有关系,如刘长卿《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的颈联:“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其中的“沧”与“苍”同音,借“苍”与“白”对,但“苍”之义与“沧州”无关。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本用之字词与借来构成对偶的字词有时也会有些关系,如唐代司空图《杂题九首》其八:“舴艋猨偷上,蜻蜓燕竞飞。”“舴艋”就是指像“蚱蜢”一样的小舟。最初,人们把像蚱蜢一样的小舟叫作蚱蜢,用的是“像什么就叫什么”的命名方法,为了区别,后来造出“舴艋”,这样就成了两个词,构成一对同源同音词(现代汉语中“舴”与“蚱”读音已有区别)。
就体裁而言,近体诗中律诗和排律的首联和尾联并不要求对仗,其他部分则要对仗。如此说来,人们因为追求对仗工整而生发的借对,主要出现在律诗和排律的中间部分,而不大可能出现在首联和尾联。出现在律诗中部的,如白居易《西湖留别》颔联:“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皇”借同音词“黄”与出句中的“翠”相对。“五马”运用了双关手法,指刺史官职。出现在排律中部的,如唐代张乔《试月中桂》:“与月转洪蒙,扶疏万古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每以圆时足,还随缺处空。影高群木外,香满一轮中。未种丹霄日,应虚玉兔宫。何当因羽化,细得问玄功。”其中第二联“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中的“下”借“夏”与“秋”相对。
二、为了达到既能自由达意,又能保持句子基本对称的目的,充分运用了宽对、假平行对的对偶方式
魏晋六朝特别是齐梁以后过份追求对偶的形式方面,有时导致辞不达意和以辞害意的后果,这一点在初唐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感。但是,作为律诗,对偶是不可或缺的项目,从唐代开始,诗人便努力在其中寻找折中的方式。他们发现了宽对和假平行对是较好的折中方式,于是便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更加普遍地运用这些在汉魏六朝就已存在的对偶形式。唐宋宽对的运用形式较之前一历史时期更丰富,限于篇幅,此不细叙。
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五律、七律诗中,宽对常与工对配合而用,宽对与工对的搭配成为唐宋诗歌中的自觉追求。如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诗中颔联工对,颈联宽对。宋代如欧阳修《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啼燕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此诗颔联工对,颈联则为宽对。又如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此诗则颔联宽对,颈联则为工对。实际上,这种有宽有严的搭配蕴含着唐宋人的一种美学追求。
对偶从宽,还可以是句法结构从宽。因为古人对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对应的字要在词性上对品,即要求“字对”。而在字字基本对品的情况下,结构可以不论。北京大学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将这种结构从宽的对偶叫做“假平行对”。
应该说,有意构造假平行对,是从唐代开始的,到宋代则大为盛行。
比如名词对名词符合对偶法则,但对出来的句子,在语法结构上并不一定相同,因为名词在句中可以作主语、宾语和状语等不同成分。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出句中“人世”作状语,对句“山形”则是主语。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颈联:“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坏壁”是状语。
再有一种假平行对是单句、复句相对。如李白《谒老君庙》:“流沙丹灶灭,关路紫烟长。”出句是因果复句,对句则是单句。宋末元初诗人郑思肖《二砺》其一之颈联:“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啮空林。”出句是复句,意思是“(我)秋送新鸿而哀破国”,这是连贯复句,并且其中“秋送新鸿”是动宾结构。而对句则是单句,并且其中与“秋送新鸿”构成字字对偶的“昼行饥虎”是偏正结构。
据笔者研究,假平行对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只存在于个别作家中的特例,事实上,它在试律诗中通行,唐代试律诗中的例子非常多,仅搜《文苑英华》卷180、卷181,就有:
刘公兴《望凌烟阁》(卷180):“丹楹崇壮丽,素壁绘勋贤。”第一句,名词“丹楹”是主语,第二句名词“素壁”则是状语。陶拱《秋日悬清光》(卷181):“烟霞轮乍透,葵藿影初生”。第一句是说:在烟霞之中,一轮太阳时隐时现。“烟霞”作状语。
在试律诗中通行,就证明已被社会普遍认可。唐宋人喜欢这类对偶甚至还与他们的审美趣味有关。假平行对中的结构不对称,唐宋人也能感觉得到,有时甚至是诗人有意调整词序、句法而导致的,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事实上,恰恰因为同时感觉到了这种语里的不对称和语表的对称,才使人觉得有趣,使人产生一种灵动和错综之美感。
三、为了使叙事、说理流畅,避免魏晋以来对偶的呆滞,此期广泛运用了流水对的对偶方式
提到对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出句与对句各说一事,两者平列对举而不分先后或不强调时间先后的那一种,即学界通常所说的“平行对”。但是,与平行对相对的还有一种“流水对”。流水对就是指出句与对句语意连贯、上下因依并且不能颠倒的对偶句。这种流水对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唐以前也一直在使用,其形式也一直有所发展,但是在诗歌中有意锻造并大量使用流水对,是从唐代开始的。从初唐到盛唐,以诗叙事的手法渐趋成熟,杜甫更是常常用律诗甚至排律来叙事,在其对偶联中,便出现大量的、形式多样的流水对。所以说,流水对类型的完备也是在唐代基本实现的。宋人不但叙事,而且更喜欢说理,于是宋诗说理的时候也用流水对,其他赋、论、四六等文体中说理自然也多用流水对,结果将流水对推广到了各种文体。关于流水对的类型,罗积勇、张鹏飞《流水对类型新论》一文论之甚详,该文将流水对为分五个大类,各辖若干小类。即:一分为二型,过程连贯型,因果连贯型,词语粘合型,问答型。这五类流水对在唐代均出现了,宋代续有发展。下面各举其例。
一分为二型,如李商隐《别薛岩宾》:“还将两袖泪,同向一窗灯。”
过程连贯型,如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宋代陆游《游山西村》颔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其《临安春雨初霁》颔联:“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均是。
因果连贯型,如唐代罗邺《鸳鸯》:“一种鸟怜名字好,尽缘人恨别离来。”二句构成因果关系。又如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句构成假设条件关系。再如张众甫《送李观之宣州谒袁中丞赋得三州渡》:“古渡大江滨,西南距要津。自当舟楫路,应济往来人。”划线部分两句间是一种推断关系,也属于广义因果。
词语粘合型,是指以出、对句体现转折、让步和递进关系的对偶类型,这三类关系一般需要关联词才能明确,如唐·令狐楚《相和歌辞·从军行五首》其四:“纵有还家梦,犹闻出塞声。”去掉关联词,让步关系就不能显现。宋人诗中更喜用,如杨亿《泪》颔联:“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表达递进关系。又如陈师道《春怀示邻里》颔联:“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著尘沙。”表达的是转折关系。
问答型流水对,如孟浩然《流别王维》:“当道谁相假?知音世所称。”又如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这是流水对兼宽对。问答型流水对,在杜甫那里运用到极致,最富表现力,如《秦州见敕目》:“旧好何由展?新诗更忆听。”《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之三:“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此型流水对,宋诗人也用,如黄庭坚《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出句是反问句,等于是已作了回答:世上有千里马。对句延伸开去:既有千里马,为何未有人提起?因为世间缺少伯乐。不难看出,这种延伸作答是学的杜甫。
四、利用数字对追求强烈对比效果,以及造出一些并非自然成对的对偶以求新奇之趣
数字对可运用于列举、夸张和对比,这三类用法在魏晋六朝时其实都已出现,不过,在那时这些用法的实用功能色彩强,而美学色彩不够,比如那时用以体现对比功能的数字对,不仅在形式上构成对比,而且在内容上也构成对比、对立。到唐代,对比可以仅仅是语词形式上的,而出、对句表示的内容有时并不对立,如唐代王湾《次北固山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两”与“一”各表多、少,在语表上构成多与一的对比,但“两岸”与“一帆”从意思上看并不对立。在唐诗中,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梁鍠《闻百舌鸟》:“敛形藏一叶,分响出千花。”濮阳瓘《出笼鹘》:“一点青霄里,千声碧落中。”宋代也有同类例子,如黄庭坚《登快阁》:“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这种现象体现了程千帆先生所说的唐诗“一”与“多”两个相对的美学范畴。当然这里所说“一”是指极少,故凡是极少、极多相对的,如杜牧《池州春送前进士》:“楚岸千万里,燕鸿三两行。”卢纶《题天华观》:“朱字灵书千万轴,苍髯道士两三人。”均可归入此类。内容并不对立,却可以用对立性的语言形式来表达,魏晋六朝文人在试验“反对”时最先明白这一点。而在数字对中运用这种手法,是从唐代才全面展开的,如李白《江夏别宋之弟》:“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陈去疾《骐骥长鸣》:“迹类三年鸟,心驰五达庄。”三年鸟,出《史记·楚世家》:“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宋人沿用这种手法,如黄庭坚《寄黄几复》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营构这类数字对时,更加注重一个“趣”字,如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颈联:“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又如陆游《自嘲》颔联:“骑驴两脚欲到地,爱酒一樽常在旁。”这类数字对的语表对立而语里并不对立,本身即构成反差,就有趣,而苏轼、陆游选来对应的两事物又往往是出人意外的,如“两脚”与“一樽”,一俗一雅,反差很大。而骑驴两脚之所以快接触到地面,是因为驴太瘦太矮。这些都是产生谐趣的根由。
两事物本身并不成对,但在用以表达它们的诗句中却显现为对偶,这往往需要对所欲表达的事物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巧妙的提取。范成大《初归石湖》颔联:“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远看行于稻田的人,只能看到他的半个身子,这是观察所得的。如果不观察、无体验,则面对“人一个、鹭一只”这种场景,便难以构造数字对了。当然观察过后,要将其转化为数字或别的类别的字,以构筑人为的词句对偶。这种功夫唐代诗人特别是著名诗人是具备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强调自然成对,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但实际上,诗赋文章主要要表达和体现的是作者所欲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并不能提供天然的成对成双的事象,所以,诗文对偶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天然成对。从杜甫开始,到中唐,到两宋,文人诗赋文章中人工撮合的对偶渐占主导,一般是经过观察、思考,提炼表现对象中可能配对的元素,通过语言的巧妙组织,来得出新人耳目的对偶句,从而使对偶辞格的表现能力、适应范围大大提高,至此对偶就不仅仅是装饰性的了。
五、从中唐到宋,部分诗人为力避滑熟,在声律、句法和审美境界上做了些一反传统的创新尝试
一般认为,到沈佺期、宋之问,五言近体的格律已经定型,随后七言近体的格律也被确定。近体诗的格律是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摸索而形成的,一句之内平仄交替,出、对句间相应位置平仄对立,邻联之间相粘,等等。五、七言律诗的颔联和颈联是两个相粘的对子,排律除首尾句外,其他部分亦须对仗,这样的诗联除了具有对偶的对称美之外,还有声律的均衡美,念起来十分谐和、流畅。中唐以前,唐代诗人大多谨守格律,故其诗联之声律给人的感觉便具有很高的可预期性,即人们常说的滑熟之感。为了对冲这种滑熟之感,诗人们开始在诗歌句法上追求骨力,开始广泛使用一些仅见于诗句中的特殊句式。如杜甫《晚出左掖》:“楼雪融城湿,宫云去殿低。”出句中的“融城湿”实际上要理解为“融城,城湿”,“城”既是前面动词的宾语,又是后面谓语形容词“湿”的主语,这便是特殊兼语式。宋诗中亦有其例,如欧阳修《戏答元珍》颔联:“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两句的语义结构为:残雪压枝,枝犹有桔;冻雷惊笋,笋欲抽芽。除此之外,还在语序方面做文章,如杜甫《陪郑广丈游河将军山林》十首其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这里突破了一般的文法,是按照诗人的实际经验组合、连缀而成的。诗句很好地传达出了诗人的实际经验:先看到垂着的绿色物体和绽放的红色花朵,然后才判断两者分别为“笋”和“梅”。杜甫这一类的诗句还不少,如“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紫收岷岭芋,白种陆池莲”,均是将颜色词提到了句首,产生了“前景化”的效果。又如王维《严少尹与诸公见过》:“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第一句本当言“三径松菊荒”,现调整为“松菊荒于三径”,又省略“于”字,使其结构看起来跟对句“图书共五车”相同,其实不同。这种语序的不同寻常的安排确实能打破预期,产生悬念。在唐代,这种特殊语序句子的出现往往与适应押韵、平仄或对仗的需要有关。
到宋代,由力避“滑熟”进一步上升到追求“瘦硬”之美的高度,因此句法的锤炼、语序的调整更加受到重视,很多的时候并非出于被动适应格律的需要。据宋代陈善《扪虱新话》卷八记载:“王荆公尝读杜荀鹤《雪》诗云:‘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惟闻拆竹声’改云:宜作‘禽飞影’、‘竹拆声’。又王仲至《试馆职》诗云:‘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指尘埃看画墙。’公为改云‘奏赋罢长杨’,云:‘如此语健。’”所谓“语健”就是有骨力,具“瘦硬”之美。
为避“滑熟”,唐代杜甫已开始尝试“折句对”。所谓折句对,是指用不合诗歌音读节奏的散文句来构造诗歌中的对子(下文举例以“/”表示一个节奏单位)。如杜甫《赠别郑炼赴襄阳》:“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中晚唐诗人更热衷于此,如贾岛《赠胡禅归》:“井/凿山含月,风/吹磬出林。”杜荀鹤《戏赠渔家》:“养/一箔蚕/供钓线,种/千茎竹/作渔竿。”据我们查考,作品中偶用此类句法的唐代诗人有:储光羲、李颀、杜甫、韩翃、僧护国、李益、韩愈、白居易、李绅、贾岛、张祜、李商隐、于武陵、杜荀鹤、贯休。
宋诗话及笔记把“折句”作为诗中对偶运用的手法加以提倡。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八“鲁直诗体”条:“今谓此体鲁直剏见,仆谓不然。唐诗此体甚多。……读之似觉龃龉,其实协律。”应该说,所谓折句“其实协律”的说法是武断的。王楙之所以要如此说,还是为了追求“瘦硬”之美。不过,这种滥用折句的做法后来并未成为主流,最多只是在律诗中偶用一联,以调和工与宽,显得不滑熟。
用拗格来中和声律之滑熟的努力,起始于杜甫,中晚唐渐多,而登峰造极则是在宋代。唐人平仄合律的诗歌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预期,使他们产生快感,但也易因重复单调而使人生倦。于是有些宋代诗人便通过下拗字,用险韵,打破读者的心理预期,试图以拗折生涩的声韵来体现奇峭劲健的风格。所谓拗律,就是解构正常的声律规则,这种拗律虽起于杜甫,但当时并未引起唐人的重视,到宋诗人黄庭坚等人的手里才得到充分重视与运用。黄庭坚在《题意可诗后》中说:“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宁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庾信之时,诗之格律尚在形成过程中,诗人尽可以试验,而黄之时已存在唐代以来的成熟定型之格律,包括正格和变格,所谓变格就是“拗救”,即如有某处违正格,当平而仄或当仄而平,则必须在本句或对句的相应位置补一平声字或补一仄声字,以达到均衡。但在黄庭坚等诗人的笔下,却可“拗而不救”,如其《题落星寺四首》其三:“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第一句第六字当平而仄;第三句第五字当平而仄,三仄尾;第四句本应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格式,但第四、五、六字完全不合格律,即使将五、六字平仄理解为有意互换,未完全破坏均衡原则,仍有第四字破坏平仄交替的基本原则;第五句失粘,且三仄尾;第六句三平调,犯唐人之大忌。或许黄庭坚是想用三平调对应上句之三仄调;第七句第六字当平而仄。如此密集地破坏规则,确实能打破读者的心理预期,但是否非如此表达不可,如此表达了是否便有了瘦硬之美,恐怕也是见仁见智。
宋代诗人为了力避滑熟,还尝试将一些非典型的、怪异的甚至不雅的意象用到诗中,以期打破读者耳熟能详的唐诗的优美、优雅意境。苏轼《次韵沈长官三首》其三:“造物知吾久念归,似怜衰病不相违。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称鼓帆为“帆初饱”,称涨水为“水渐肥”,一饱一肥,全用俗人粗语,这一方面是苏轼对自己当时境遇的自我解嘲。同时,试对比唐诗“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等诗句,不难发现鼓帆、涨潮本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且常常表现为优美意境,苏轼用俗语来写它,颇有解构的味道。梅尧臣《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这首诗的颈联中的“霜落熊升树”是一种不常见的景象,唐诗中很难见到。黄庭坚学苏轼“以俗为雅”,走得更远,其《戏呈孔毅父》“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以古人戏谑语入诗。他在比喻、象征时,也有意选一些不优美的“瘦硬”物象,如《弈棋二首呈任渐》其二:“偶无公事客休时,席上谈兵校两棋。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其实,改变唐人的套路并不难,但要像苏轼那样透过这种改变来显现言外之意,已是比较难,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苏轼那样的境遇和体验,而要透过这种改变以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则是最难的。我个人认为,一些宋代诗人透过这种改变找到了一种“趣”,可算是比较成功的,如前举陆游诗:“骑驴两脚欲到地,爱酒一樽常在旁。”又如杨万里《霰》:“雪花遣霰作前锋,势破张皇欲暗空。筛瓦巧寻疏处漏,跳阶误到暖边融。”
当然,也有不少宋代诗人仍在学唐,致力寻找和表现优美意境。有时,走同一条路,宋人并非一定不如唐人,如王禹偁《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颔联的意境,平心而论,比唐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The Study ofChanges in Poetic Antithesis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Luo Jiy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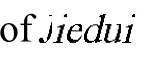
Antithesis’s Pattern;Language Form;Rules of Tone;Sentence Pattern;Change
责任编辑:卢烈红
罗积勇(1961—),男,湖南衡南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汉语词汇、修辞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辞格审美史”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BYY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