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从乡村到荒野:华兹华斯与梭罗“自然”之比较
张箭飞 杨丽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诚如“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精魂所系的“自然”亦是一个概念深水区。在“自然崇拜”这把大伞之下,聚拢着血统不一、面孔各异、气质悬殊的浪漫主义者,而甄别他们的差异(从政治理念到风格特征到历史影响等)一直是浪漫主义学的传统任务。本文聚焦两位最具代表性作家华兹华斯和梭罗,细察浪漫主义的“自然崇拜”核心概念如何本土化(localization)和个性化。地貌方面,华兹华斯多描写耕地、果园、牧场、茅舍、绿篱等乡村风景(rural landscape),而梭罗着力于原始森林、无人海湾、草原大漠等荒野风景(wilderness);时间方面,华兹华斯常常使用农时、乡村节庆来标记自己对于自然变化的感受,而梭罗则根据气候与天气来记录和沉思自己的生活;人物方面,华兹华斯精于刻画村民、猎人、收割者、采集者、乞丐等乡村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而梭罗刻意远离城镇生活和文明世界,引飞禽走兽昆虫花朵为自己的同类。二者之间的差异亦具体而微地反映了英国浪漫主义与美国超验主义的差异。
人文地理 自然 乡村 荒野 四季 居民 本地性
诚如“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精魂所系的“自然”亦是一个概念深水区。在“自然崇拜”这把大伞之下,聚拢着血统不一、面孔各异、气质悬殊的浪漫主义者,而甄别他们的差异(从政治理念到风格特征到历史影响等)一直是浪漫主义学的传统任务。前赴后继的学者或思想家,从勃兰兑斯(1842—1927)到A.O.洛夫乔伊(1873—1962)到以赛亚·伯林(1909—1997)等均有相当精彩的描述或界定努力。随着人文地理学家和环境史学家的加入,一度无所不包、歧义丛生且极易滑动的“自然”渐渐锚定在“有机世界”、“户外景色”、“尚未被人类活动所改变的环境”、“生态系统”等意义范畴,进而被段义孚(Yifu Tuan 1930—)视为“乡村(countryside)”和“荒野(wilderness)”的同义词,“美景(scenery)”与“风景(landscape)”的近义词,而风景又被其后的W.J.T米切尔(1942—)界定为可与“空间(space)”“地方(place)”乃至“权力(power)”等值切换的概念。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开始“人文地理学”转向,大兴各种跨界研究,段义孚和米切尔堪称这一潮流的重要推手。因此,最近三十年的文学研究多与风景学和生态批评交互联动——后两个学科与人文地理学交叠内缠,共用很多理论话语,互补大量批评案例。沿此路径推进的学者,不断发现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书写(writings of nature)”所蕴藏的人文地理(cultural landscape)资源。因此,描述和解释诸如地貌、动植物、气候、民居、人口、人种、生活方式等这些原本属于人文地理学领域的中心任务已然成为一些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目标,不少浪漫派作家重被定位成植物学家(如卢梭)、地质学家(如歌德)、香料达人(如济慈)、园艺学家(如华兹华斯)、观鸟人(如梭罗)等等——相类的探索不仅提亮了原处于弱光区的浪漫主义之“物理性”、“气候性”、“区域性”、“时差性”等,亦使文学想象与人文地理/现实的仿写互塑关系跃然自显。

一、风景类型:乡村与荒野
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之强力一翼,“湖畔派”实指一群曾在英国湖区定居或暂住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包括三大中坚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以及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柯勒律治长子哈特利(Hartley)、兰姆、德·昆西等数十人。这群湖畔住客,仅有华兹华斯兄妹是真正“当地人(native)”,长居并终老故乡格拉斯米尔村。华兹华斯一生完全浸入湖区环境,最具影响力的诗歌因湖烟水光而起,为山色岚气而作,推动了英国公众审美趣味之巨变,提升了湖区在全欧的美誉度,同时,亦使整个湖区成为“华兹华斯郡”,乃至公众认可的“浪漫主义文学圣地”。
就风景偏好判断,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灵魂人物,华兹华斯与其他浪漫派甚至湖畔同道旨趣大异:拜伦迷恋东方仙境,雪莱神往冰峰绝境,柯勒律治则沉醉于中古幻境,后三人的“自然”基本位于想象空间,超拔脱尘,令人神往却难亲临,而华兹华斯的湖区则是一个美丽而不遥远的地方,居于粗陋城市和乌托邦之间,引人一游为快。这也是为什么华兹华斯诗歌会被称作韵体导游手册,与其畅销的散文作品《湖区指南》(1810)一起,建构了一个长盛不衰的旅游胜地。在这个意义上,华兹华斯更多地遥承了欧洲文学的牧歌传统,与维吉尔(公元前70—19)、贺拉斯(公元前65—8)、蒲伯(1688—1744)共享一个理念:在乡村,人们可以摆脱城市的邪恶和痛苦,“靠着大自然的恩赐自给自足”——对于这一理念,梭罗将在《瓦尔登湖》里给予修正或颠覆。
作为英德浪漫主义的旁支晚辈,美国超验主义继续光大华兹华斯等人的自然之爱,但他们所爱的自然具有全新的地貌特征,在刷新既存的本土“荒野书写”传统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独立,此后真正意义的“美国文学”出现在欧洲读者视野,并一直保持“自然写作”或“生态文学”这一文类的优势。
美国一度存在于北美荒原之中,它的文学,在还未蜕去“英国殖民地文学”胎记之前,就以观察和记录新大陆自然景象之特长激发了旧世界的地理想象。早期作家,如约翰·史密斯(1580—1657)等“展示人们有关新大陆和自然的种种影像:纯洁的处女地,富饶的伊甸园,恐怖的丛林,咆哮的荒野。”“处女地”、“伊甸园”、“荒野”等字眼表明北美大陆是森林密布、野兽/野人出没的原始蛮荒之地(wilderness),而在欧洲传统概念里,也即基督教概念里,荒野等同凄凉之地,受诅咒之地(cursed ground),未被耕种,常有恶魔出没,引诱人类堕落。正是因为这种道德/宗教定性,欧洲人长期对荒原避之不及,直到18世纪末期,经由拜伦等人大力颂扬,荒野逆袭成功,几乎与“崇高”同义,赢得艺术家和读者的敬畏之情。但“荒野”要真正升值到与“上帝”共用圣坛的高度,则要等到美国梭罗、缪尔诸人自然散文和荒野游记深入人心。
虽然备受华兹华斯诗歌影响,但梭罗的风景偏好另取一极。如果说,在前者诗歌里,作为城市对立面的乡村象征着宁静与道德,那么,在后者的散文游记里,乡村则沦为荒野的对立面。比照华兹华斯格拉斯米尔村,波士顿远郊小镇康科德依然保留着新大陆处女地余韵,湖泊、林地、田野、荒野交错交织出如画甚至崇高的风景。许多居民就是种地为生的自耕农和伐木工人(也许有人兼营一些贸易),但在梭罗的眼里,小镇却代表着“平庸的日常”和日常的枷锁:“我在康科德许多地区,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从事着成千种的惊人劳役。……他们的不幸是,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他们不如诞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来给他们喂奶,他们倒能够看清楚了,自己是在何等的环境辛勤劳动。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

人们常对梭罗瓦尔登湖畔两年野营生活心神往之,但他本人感到康科德环境还不够野性,便到缅因、科德角、加拿大等更远离人类文明的地方旅行。在缅因森林漫步时,梭罗感叹道:“在从山上往下走的这段旅程中,我充分体验到了大自然的原始,以及它未被驯服也不可驯服的本质——当然,其他人可能会用不同的词语来形成这种体验。”
华兹华斯也喜欢与妹妹一起户外徒步,却没野外独居的经历。受限于整个湖区地理现实和他个人的美学旨趣,他的自然鲜能获得“未被驯服也不可驯服的本质”。在《露丝》一诗里,他凭借想象虚构了一位来自美国佐治亚的青年,这位“荒野里的黑豹”所描述的北美荒野看起来更像舞台布景:“他谈到没树的青青草原,/谈到许多湖泊宽阔无边,/一簇簇的仙岛奇境/星罗棋布地点缀在湖面……”显然,真正的荒野超越了华兹华斯的经验范围,却在梭罗的体认领域。
二、四季: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
昼夜交替、四季更迭使自然呈现不同样貌,人对自然的感知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获得不同的视觉印象和心理感受。一般而言,人们对事物、事情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但并非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时间”。人类最初形成的时间概念是自然时间,即以存在于自然界中客观存在体的往复运动或变化的一个循环作为量度单位,如年、月、日、季节等,并逐渐发展出区域性“社会时间”,如一个村庄的教堂钟声和宗教节日。从华兹华斯和梭罗的四季书写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时间体系。既与他们环境密切相关,更是反映了对于自然变化的不同感知。再以华兹华斯《诗行:记重游怀河沿岸之行》为例。此诗记叙诗人兄妹在夏季(1798年7月)重游怀河。诗人从“喧闹的城市”重返“树影婆娑的怀河”,急切地要投身于大自然中获取滋养。但诗人所突出的时间不是夏季或七月,而是“挂果”的农时:“茅舍村落,青青果园。/这季节,果树正在挂果。”写于同年10月《采硬果》,被铭记为“永难消亡的美好日子”并没具体日期,他所描述的“感官盛宴”是与“秋收”景象联系在一起的:“…………可那些榛树,/高而直,悬着簇簇诱人的果子;/没人见过的景色!我站了一会,/急促呼吸着,只觉得心在膨胀,/……“季节(season)”一词,源自拉丁语,意味“播种”,标明了季节的“农业”特点。按照西塞罗观点,四季堪称第二自然(secondnature),但本质上仍属于服务或参照农业生产的社会时间。华兹华斯深谙维吉尔以来的牧歌,虽然没像梭罗那样真正躬耕畎亩,但久居乡间,对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奏非常敏感。
除了农时,华兹华斯还常常使用乡村社会的各种节庆来标记自己对于自然变化的感受,如《颂诗:忆幼年而悟不朽》,此诗意在表达他的一个要旨:儿童比成人更亲近自然,所以更具神性。诗人回顾幼年(其实也就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我的愁思不再把这季节辜负;/我听见回声在山间来去奔突,/……整个儿世界都欢乐;/陆地和海洋/沉浸于一片喜洋洋;/怀着五月之心一颗,/每头牲畜都像在过节日……/千百个山谷的八方四面,/儿童到处在把那新鲜的花朵采摘……”诗歌锁定在“五朔节(May Day)”鲜花绽放的春景和村民欢庆场面,象征人类童年阶段,“天堂展开在我们身旁!”,最重要的是,浪漫主义“回到自然”与“回到童年”扣合,以此,华兹华斯将通常空间化的“自然”时间化为“童年”。
比较之下,梭罗基本采用自然时间——长到春夏秋冬,短至一天之中的日升月落风起闪电来划分他的生活阶段甚至性质。他逃离小镇,亦避开它的时间方式:农时、钟表、教堂钟声和火车汽笛。他虽然为生计考虑,垦种了一块豆田,却不按照农夫邻居的教导,错过正常的播种施肥时间。梭罗写道:“我的一天并不是一个个星期中的一天,它没有用任何异教的神祇来命名,也没有被切碎为小时的细末子,也没有因滴答的钟声而不安。”因此,他也不按照小镇的“社会时间”作息。当然,他观察到火车时间对于本地生活的影响:“一个管理严密的机构调整了整个国家的时间”,“农夫们可以根据火车汽笛来校正钟表”,“我有一些邻居,我本来会斩金截铁地说他们不会乘这么快的交通工具到波士顿去的,现在只要钟声一响,他们就已经在月台上了。”他犀利地讽刺本已被奴役在土地上的乡村居民又被火车拖进更大的时间牢笼:城市——在那里,人们早九晚五,按时工作和礼拜。
梭罗日记一般按照四季编排,如《瓦尔登湖》。1846年夏季,他遁入湖畔,开始记录隐居生活,经过七次修订,最终两年生活呈现为一个季节性循环:夏—秋—冬—春。此外,梭罗1837到1861年期间林间田野散步的观察日记,在他死后由一位朋友以“春、夏、秋、冬”为题出版了4卷。题目也常以季节命名,如《季节》、《秋天的日落》、《冬天的禽兽》、《冬天的湖》、《春天》。
在瓦尔登,梭罗看、嗅、听、尝、触四季轮回,潜心观察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河流湖泊四季、三旬、一日、早、中、晚的变化。例如,在“湖”这一章,他细致地记录湖水颜色与时间气候之间的波动关系:“在天气好的夏季里,从稍远的地方望去,它呈现了蔚蓝颜色。特别是在水波荡漾的时候,但从很远的地方望去,却是一片深蓝。在风暴的天气下,有时它呈现出深石板色。……我看到当白雪覆盖这一片风景时,水和冰几乎都是草绿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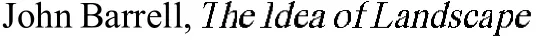

三、居民:高贵的野蛮人与自由的动物
按照段义孚等人的观点,风景或环境乃是文化的建构,呈现出人(类)地关系的种种形态,即是荒无人烟的沙漠、荒原、雨林、甚至天空,亦能显示、映现、投射出人的活动、欲望、想象以及社会关系。因此,“地理学将其学科身份界定在人类文化和自然环境之交互作用的独特关注中”;因此,风景/环境中的人(figures in landscape)一直是风景学和生态批评的传统关注,直到近10年,协同人类建构了文化的自然的非人类行为者(doers),如动物,进入多方学科的研究领域。在此语境下审视华兹华斯的乡村人物和梭罗的荒野动物,亦能窥见二者的差异。
华兹华斯写得最多的人物是村民、村童、游民、疯子等,其共同特点是:生活在乡村,已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带着乡野和山林的气息”,无忧生死,天真纯朴,信赖大自然,靠“天宠(naturalgrace)”吃饭,如“我们共七个”中的小女孩、“坎伯兰的老乞丐”、“山林闺女露丝”等。这类人物也即浪漫派垂青的“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滥觞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曾引起伏尔泰的严厉批评:“他指称卢梭想要我们像动物‘四脚爬地’,行为学习野蛮人,因为他认为野蛮人是完美无缺的。这样的解释尽管可信但不确切,高尚的野蛮人和回归自然的套语即由此而来。”大异于拜伦、柯勒律治诸人的人物猎奇,华兹华斯则从日常生活萃取“诗意”,将乡村居民,特别是边缘人物崇高化为更简单更健康的“乡下人”,与北美印第安人、大洋孤岛土著、中世纪黑森林武士等“野蛮人”等量高贵。
在《迈克尔》一诗中,诗人动情地描述老牧羊人和大自然浑然一体:“不论刮的是什么风,狂风唱的是/什么调,他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往往,当别人谁也不曾留神,/他却听到了南风在音乐吹奏,/仿佛远处高山上传来的风笛。……谁要是猜想,这里的青山、翠谷、/溪流、岩石,都与牧羊人的心境/漠不相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原野,他常在这里畅快地呼吸;/这山岭,他曾多少次健步攀登;/这些熟悉的老地方,把多少往事(他的辛劳与艰险,本领与胆量,/欢乐和忧愁)铭刻在他的心底。”这种境界即生态批评激赏和鼓励的“人地和谐”关系。
比较之下,梭罗笔下鲜见“迈克尔”、“西蒙·李”、“露西·格雷”等华兹华斯式乡村人物,倒是通过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他把自己塑造成了美国读者心目中的“高贵隐士”,或“荒野潘神”:“我从不觉得寂寞,也一点不受寂寞之感的压迫,只有一次,在我进入森林数星期后,我怀疑了一个小时,不知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是否应当有些近邻,独处似乎不很愉快。……当这些思想占据我的时候,温和的雨丝飘洒下来,我突然感觉到能跟大自然做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就在这滴答滴答的雨声中,我屋子周围的每一个声音和景象都有这无穷尽无边际的友爱,一下子这个支持我的气氛把我想象中的有邻居方便一点的思潮压下去了,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在想到过邻居这回事。”当然,他的“自给自足的原始主义”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此类质疑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一个讨论高潮。论者认为巴尔赞持论公正:“他的身边还是带着文明的产物:衣服、钉子、种子和木材,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不过,当人们在阅读他对自己隐居生活的叙述,分享他的巨大的幸福的时候,是不注意这些矛盾之处的”。
实际上,梭罗不时提到自己的荒野访客和同道,如那个加拿大伐木工,一如华兹华斯的老牧羊人纯朴和睿智:“他认为荷马是一个大作家,虽然他写的是什么,他并不知道。再要找一个比他更单纯更自然的人恐怕不容易了。罪恶与疾病,使这个世界忧郁阴暗,在他却几乎不存在似的”。
但更多时候,他与动物旼旼穆穆,引鸟兽为灵魂伴侣,正所谓“久为野客寻幽惯、山鸟山花吾友于”。在“禽兽为邻”一章中,他一一记录下与他共处一个生态系统的各种动物:狐狸、浣熊、鹧鸪、猫头鹰、潜水鸟、梭鱼等,就连一般人厌恶的老鼠,他也观察和比较它的习性:“还在我造房子那时,就有一只这种老鼠在我的屋子下面做窝了,而在我还没有铺好楼板,刨花也没有扫出去之前,每到午饭时分,他就到我的脚边来吃面包屑了……我们很快就亲热起来了……”。字里行间流露出人鼠之间的信任、亲密和互娱,令人想到蒙田关于猫的妙比,真难分清:是梭罗在玩老鼠呢还是老鼠在玩梭罗。更重要的是,他的观察不时跳脱以前博物学家的“俯瞰低等生物”视角。例如,在多次仰角、全程“跟拍”了一场红黑蚂蚁大战之后,他由衷感概:“我自己也相当激动,好像它们是人一样。你越研究,越觉得它们和人类并没有不同”。
梭罗讽刺康科德居民沦为土地、金钱和火车时刻表的奴隶,他对人类邻居避而远之。但,一写到动物,梭罗就不吝赞美:“在森林之中,有多少动物是自由而奔放地,并且是秘密地生活着的,它们在乡镇的周遭觅食,只有猎者才猜得到它们在那儿”。其实,他对荒野动物的定位亦可视为是对自己的描述。一如水獭,他也藏身密林,过着“何等僻隐的生活”,但某一次却被猎人一般的税务官抓住。
综上所述,可见华兹华斯与梭罗的一个重要区别:华兹华斯有很强的社群(community)意识,精于描绘乡村群像;梭罗自认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本能地排斥社群主义和文明世界。基于这样的态度,他更留意动物的生存方式,而不是他的同类。因此,根据华兹华斯诗歌,我们可能复述/补充巨变时代的英国湖区,它的人口构成、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等,而梭罗动植物书写则在20世纪中期兴起的文化导向的动物地理学(zoogeography)占有重要一席,激发后继者与他互文思考诸如“动物空间(animalspace)”、“野兽地方(beastlyplace)”等要题,进而重新思考动物如何为特定区域(如英国湖区、瓦尔登湖)和景观留下印记。
四、一个“自然”,多种表述
“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语境下的“自然”一直是西方观念史/文学史学界各种看法的交锋之地。伯林曾说:“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由此推及“自然”,自然同样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伯林语),尽管持论严谨的韦勒克也曾试图锚定至少是“欧洲浪漫主义的统一性”。上述讨论显然无法支持一种普遍的“自然崇拜”或“自然主义”,反而显示:一如专有名词浪漫主义(Romanticism)已经分化细化为小写的复数浪漫主义(romanticisms),“自然”,这个曾像“上帝”一样需要大写的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内包多重含义、歧义的复数名词。而华兹华斯和梭罗,各以自己的自然书写,印证了当代人文地理学家的一个构想:在不同空间规定之下(如英格兰、新英格兰)辨析诸如“自然”、“乡村”、“荒野”这类概念(concepts)的本地性、个人化以及演变路径。Countryside VS Wilderness: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dsworth’s and Thoreau’s Writings of Nature
Zhang JianfeiYang L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Justlike“romanticism”,“nature”which anchorsRomanticismhasremained open to heating arguments.Asa conceptualumbrella,“nature”usedto shelterromanticsofdifferentdegrees,kindsand schools,therefore,todiscriminate various romanticism or romantics or romantic writings of nature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Romanticism Studi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focus on Wordsworth and Thoreau,the two most canonical romantics’writings of nature,in order to observe how“Returnto Nature”,the romantic fundamentalnotion,is localized and personalized.In terms of landform,Wordsworth usually describes rural landscape,such as cultivated lands,orchards,cottages and hedges,while Thoreau focuses on wilderness,such asprimitive forests,unpeopled bays,prairie and deserts.In term of time,Wordsworth always uses farming seasons and rural festivals to mark his feelings for nature's change,while Thoreau records and contemplates his life according to climate and weather.In term of character,Wordsworth is famous for depicting the daily lif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rural characters,such as villagers,hunters,reapers,gatherers and beggars,while Thoreau is deliberately away from the urban l ife and civilized world,and treats animals as his own kind.The contrasts between them specifically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Romanticism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Cultural Landscape;Nature;Countryside;Wilderness;Seasons;Residents;Locality
责任编辑:涂险峰
张箭飞(1963—),女,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风景。杨丽(1980—),女,武汉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生,主要研究自然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