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关键词”的提法,来自苏珊·海沃德的《电影研究关键词》。这本书里有句话影响了我:“关键”的意义大于普通元素,也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没有必要的热情,就别妄想大家有所触动。这里说的“大家”,指的不仅是影迷群体。现在的观众早不满足像以前那样看个热闹了,了解电影不再是电影人的专利—反而是很多电影人声称自己不看电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写这些关键词时,就是想站在一个现代影迷的立场,把潜在的观众(读者)当作“影迷”相待。因为,即使在电影业的低迷时期,某些艺术性、低成本电影仍然存在,且偶创奇迹。这一事实说明,真正的影迷没有消失,而是融入了同质化的观众之中。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说:“今天的电影不知道暗指,也不理解幻觉:它在一个超技术、超效率、超视觉的水平上把一切连接起来。没有空白,没有间断,没有省略,没有沉默,如同电视一样,随着自身图像特性的消失,电影被日益同化。”(《艺术的共谋》,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套用波德里亚的口吻,把这句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当电影本身可以反映的特别的幻觉,在社会上、在各种媒介中随处可见时,作为独特艺术的电影就归零了。
不管是哪种观众,在经历这一切之后,基本都有了一个共同认识,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电影的确应当发生变化。现在的电影不同于早期的娱乐化,已经涵盖了审美、个性、价值观等生活里常见的元素。假若,你问一个陌生人对一部电影的看法,或问他喜欢什么电影,大致就能判断出对方的品位和性格。事实上,电影的确成了一种寻找同类的标识。“怀着一种过度的好感来看西部片、恐怖片、喜剧片,看待这些惊人的冒险,充满了奔涌诗意奢华的画面,瞬间闪现而且几乎无法解释的美。简言之,电影不仅仅是一门艺术,电影是关于电影的神话。”据一篇文章所示,法国小说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1982)曾这样评价过和自己同处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新浪潮“手册派”电影人。佩雷克除了写奇怪小说,也制作电影,如一九七四年那部《沉睡的人》,那时新浪潮已经过去了。就当佩雷克的确有过这个说法吧。这也是我此刻的做法,作为一个现代影迷,我加入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就是希望让大家都能感到一种期待,或者说“过度的好感”。只有这样,才能客观看待新浪潮时期的“电影神话”。
关键词:电影之子
第一个关键词“电影之子”,要从电影这种城市文化说起。对于从小成长在乡村的我来说,“电影”近似于虚无的美妙向往,往往说起外面缤纷的世界时,才会用到“跟电影里演的似的”这种话。没想到,乡村凋敝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还没反应过来,电影就闯入了我们这辈人的生活。一点不夸张,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完全没有电影。露天放的、电视上演的那些片子都没留下什么印象,正经进电影院看第一部电影,已经是九十年代,是我在县城上小学的时候。
那是一部香港片—《新少林五祖》,说的是洪熙官为了保护一张藏宝图浪迹江湖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同龄人的记忆里,这样的故事很多。我印象深刻是因为,电影里飞檐走壁、武功高强、保护儿子的父亲形象,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父亲,虽然他只是一个吊儿郎当的电工。
回忆电影比回忆别的什么,容易动情。大家可能早就接受了电影—作为我们生活的某种见证。因此,我很喜欢安托万·德巴克那本《迷影》的最后一章“塞尔日·达内:电影之子”。
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1944-1992)这人一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对电影的爱特别真挚。德巴克在书中说,“达内向来都是借由评论电影的方式在谈他所身处的世界”。如果只是谈论电影,总有一天会谈完,生活永远继续着。后来读到他谈父亲在自己小时候失踪,“不仅从未见过他,也无缘与之重逢”,这句话一下击中了我。父亲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地“失踪”了—我肯定见过他,只是那时没有记忆。虽然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关于电影的经历,因为父亲的闪现,我似乎能理解达内自称“电影之子”的那份心情。
 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1944-1992)
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1944-1992)一九七三年,达内当上了《电影手册》的主编,可是这位历史上最年轻的主编却说,自己“在《电影手册》的时期,是《电影手册》历史上最失败的时期”。那个时期,除了新浪潮电影大将、杂志核心作者特吕弗与戈达尔决裂,把杂志拖得疲惫不堪之外,也到了一个为电影寻找新定位的时间节点。本来,友谊是私事,但放在“新浪潮”这个话题下,挚友分道扬镳,的确有预言性。就是说,他们背后那个时代文化,从热火朝天的现实,过渡到了“过去的幻象”。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的《电影手册》上,法国学者让-路易·科莫利(Jean-Louis Comolli)写过一篇《关于新观众的笔记》,指出了新观众(新观察者)的困惑—
新的电影—即使仍旧得依附黑暗的放映厅而存在,却想超越其限制—亟欲成为外面世界的延伸,并对其作进行评论:在此情况下新观察者于是迷失了方向。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一方面仍受制于电影院的部署,遂会因为那些能够符合他的期望值的满足感而迷醉在电影中,但另一方面,电影又导致他时刻得处在跟自己、跟他人交战的状态中,他不停地被世界的影响所左右:这种让意识一直维持清醒的状态,跟放映厅所促成的认同效果两两相悖,彼此抵触。
这不就是当下观众和真正影评人看法相差巨大的原因吗?电影需要营造幻觉—过去的观影感觉在这时起作用,而现代的观众在面对电影时越来越冷静,执着于旁观,而不是沉浸。可实际上,人很难真正理解一个事物。我不觉得自己从小到大看懂过任何一部电影,就連导演本人,也未必能通过电影准确地表达了自己想说的。这里面有各种问题,自身才能,政策影响, 等等。
其实,人们看电影,都是在确认自己对生活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就是看懂了电影;感觉不对,可以说电影不好。
一九五六年,特吕弗写了一篇关于奥逊·威尔斯电影《阿卡丁先生》的文章,他早料到观众对“懂与不懂”电影的反应:
毫无疑问,人们会觉得这电影看不懂,但同时也肯定会看得很兴奋、刺激、充实……因为其中充满了我们最想从任何一部电影中找到的东西—抒情和创意。
抒情和创意,这都是对“感受”的更新,可以肯定一点,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中,所谓“好和不好”也是一样—大家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就没改变过吗?不仅当下的事物在发展变化,人看待过去事物的观点也在变。人的善良,人的情感,人的梦想,等等,这些才是艺术中稍微稳定,并且具体一点的东西。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布勒东说过:“电影这个手段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能将爱的力量给具体化。”除了具体在情绪上,还具体到片中人物的言行上—我们天然地觉得法国年轻人生来浪漫、开放。其实,在新浪潮早期的历史上,他们也有看到好莱坞电影里的亲吻镜头而惊呼的时刻……我在《迷影》里看到这一段描写时很惊喜,因为自己当年看法国电影时,就经常有类似反应。
也许,人对生活的感觉,总是迟钝的(艺术往往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电影变了,一部分变得越来越深奥,一部分变得越来越肤浅。
我们可以对照电影频道的老片重播和院线上的老片重映。看看是不是这样?
塞尔日·达内“电影之子”的说法换种表达,就是“看电影长大的一代”。这是和我完全不一样的一代。我成长在一个电视普及、电影衰落的年代。“首先,它失去了记录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能力;其次,它在视觉文化的场域中越来越被边缘化了—电视和广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走了电影的半壁江山,不是吗?”(《迷影》)当然,不能说全是坏处,电视的兴起也促动了短片的发展;而在新浪潮时期,电视台因为需要内容填充,收购了很多年轻人拍的短片……这还不是我想说的。
我想说的是,任何情感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包括年轻人(或者资本)对电影的高度热情和无奈观望。
 电影《阿卡丁先生》海报,1955 年
电影《阿卡丁先生》海报,1955 年培养起一代迷影人的法国电影新浪潮,为什么值得怀念?二战后的法国,由于大量好莱坞电影在本土倾销,银幕上电影里的世界,和法国年轻人的生活出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年轻人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无视。在一个谁能把身边的生活拍进电影,谁就能走上了时代前沿的时刻,新浪潮电影人用反对好莱坞电影,以及法国模仿好莱坞拍摄的电影的方式开始了反抗。他们写评论、拍电影,很快赢得了社会上年轻观众的喜爱,从此电影也慢慢地成为一种值得被讨论、被尊重、被赋予更多意义的现代文化之一,这就是理由。
关键词:电影院
二○二二年六月,美国电影导演伍迪·艾伦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拍电影的兴奋消失了很多,这与现今电影的媒介改变有关,“现在我拍电影、上映新片,感受不到跟以前一样的快乐。得知五百个人一起看我的电影,感觉曾经很不错,现在我不晓得我对拍电影是什么感觉……”在这里,伍迪·艾伦用的词意是“cinema”,而不是“film”或“movie”。之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批评“漫威电影不是电影”的新闻吵得很热闹,可能就是我们这边的媒体搞错了这几个词的不同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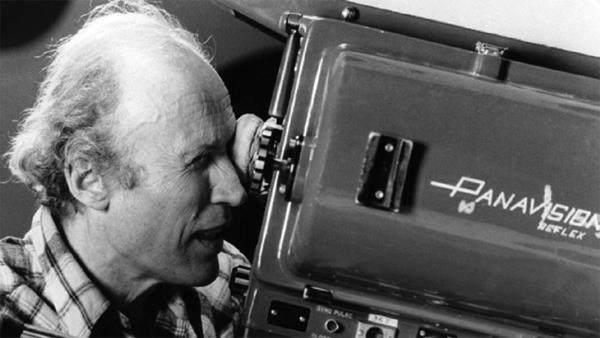 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1920-2010)
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1920-2010)就这个问题,一个爱电影的海外朋友告訴我:“cinema”是指,导演在其中有系统、严谨、统一的视听语言技巧和个人风格的电影。按这个意思说,漫威电影的确不算“电影”,同时我也终于理解为什么,在法国新浪潮电影人那里,经常听到“cinéma”,并且从语气中可以嗅到一丝骄傲。
其实,早期知识分子是看不上电影的。“在有声电影发明前,全世界不少人—尤其是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对电影不屑一顾,在他们眼中,电影只是一种节日集会上供大众消遣的游艺节目,或是一种不入流的艺术。”特吕弗明显话里有话。
应该说,至今法国人那种对电影的骄傲之心,很大可能就是从“新浪潮”所带来的改变开始的—至少,新浪潮电影人让电影和文学一样,得到正视。聪明的新浪潮电影人,深知电影作为新艺术,太年轻、不持重,必须和文学挂钩。一九八二年四月,特吕弗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的电影《枪击钢琴师》《祖与占》完全是由那些令自己欣喜若狂的小说激发的灵感—注意!这时特吕弗已经不强调“生活”和“真实”了。或者在真实生活中,就有不少法国年轻人,除了进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在读小说,这都有可能。不得不说,特吕弗一直在利用“媒体”深化“第一人称”电影,也就是“作者论”与文学的渊源。特吕弗原话是,自己导演一部片子时的雄心就是,“要使它和长篇小说一样”。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特吕弗也好,夏布洛尔也好,都是法国电影界的巴尔扎克、司汤达或普鲁斯特。”(米歇尔·塞尔索《埃里克·侯麦》,李声凤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在《埃里克·侯麦》这本书的前言里,作者写道:“电影,是放映的场所,也是自我认同的场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也是穷人休闲的长沙发,但同时也是神话的创造者,它与历史、道德、观念之间所维系的并不是一种简单而单一的关系。”关于电影的几个方面都说到了:放映、自我认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底层人的娱乐、一种未来强大的文化。
这个排序是有意味的,场地是基础。据《欧洲时报周刊》一篇关于巴黎电影院的报道可知,一八九五年卢米埃兄弟放映了影片《工厂大门》之后,电影院在巴黎就出现了,并且发展快速。电影与视听研究所(l'IRCAV)所长罗朗·克雷东说:“在法国,特别是在巴黎,人们可以看到最多的不同电影。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这儿形成了一个永不衰竭的电影之爱。人们会注意到,法国人钟爱自己的文化特殊性,各种媒体时刻不忘谈论电影,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 (伊婵《巴黎的电影院》)
这几乎像一个由来已久的记忆。法国影评人路易·斯科雷吉回忆起“Cinema时代”:“六十年代早期,有数十个观众曾用狂热且盲目的方式,在践行着自己对电影所怀抱的满腔热情。”(《迷影》)这种热情,既表现在影迷去巴黎的各个电影俱乐部看电影,还表现在他们走进放映厅时,都“习惯往前靠”,这样可以离电影人物更近一点。这正是“新浪潮”崛起时。
新浪潮电影时期,很多和创作者差不多年纪的年轻观众走进电影院,为自己熟悉的生活欢乐和悲伤过。
到我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县城里的影厅,大约容纳百来人。当那个时候的我,随着门前的人流一起,通过一个厚厚的遮光门帘,走进偌大的放映厅,在七弯八拐的狭窄过道边,找到自己的位置,坐在紫红色天鹅绒座椅上,扭头看去时,周围全是年轻人。
这是我少有的机会,和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做同一件事。等灯光暗下来,安静随之降临,没有人再说话,银幕两侧各有一个安全门的灯亮着……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在我的回忆中很恍惚。说实话,我几乎不记得自己当年看过的具体的电影了,但在电影院灯光暗下来前那种被人群包围的感觉,却为我带来了持久的有些激动的回味—看电影就是建立在感受上的,很多时候没必要评价电影好坏。
如今,“cinema”传统成了过去式。新一代电影人和过去的电影人工作一样艰辛,却再也得不到那种直接的、单纯的反馈了。这种失落的情绪,可以说,遍布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在电影行业。
我现在写的,也是一种关于看电影的感受。这种感受在我小学毕业,在小城闲逛,路过电影院时爆发过一次。我发现,那时的电影院已经出租场地,办起了江南丝绸展销会,门外堆着好几排当初我坐过的绒面椅子。我背着书包,站在那里,看了半天进进出出的人。
再后来,电影似乎就完全离开了我的生活。二○○三年前后,我离开学校,电影院好像就是我在社会上游荡时悄悄活过来的。标志是身边终于有年轻人会聊最近看了什么片子。我挺惊讶,因为自己很久没有看电影了。后来我为了和他们有共同话题,也去看了几场电影。据后来的资料说,电影院随着新兴的房地产行业再次兴起。不过,在我们小县城,为数不多的楼房也没见增多。之后有段时间,电影似乎又没声音了。而我忙于在广告公司打工,整天跑各个公共场所推销电梯广告—可是我一次也没去过电影院。
电影再次成为话题,电影院再次人满为患,是在二○一六这一年国产电影《美人鱼》上映时。那是我进电影院次数最多的一年。再次走进电影院看大银幕,我已经清楚知道一个影迷的快乐了,比如像《迷影》这本书里写的那样,影迷如何选座位—“当我们跟银幕近乎零距离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了我们一直试图进入的光影流转中。我们让自己淹没其中,因为我们想忘了那确实存在的景框,我们想要‘看而不见……然而,假如说当真存在一股想让自我尽可能地消融在剧本当中的盲目愿望……”
过去的观众—我指新浪潮以前,“没有哪一个知名的知识分子会上电影院,更遑论在看完电影后去谈论它们。然而,巴赞却像是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般在谈论电影”(达德利·安德鲁《巴赞传》,张田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那时看电影。是一种“堕落”的表现,拍电影更不是一个好职业,所以导演侯麦根本不想家里人知道自己做导演。一直到他成名后,家里人才知道他除了当老师还拍电影。
新浪潮时期的电影俱乐部,相当于小型“电影院”。电影俱乐部的风靡,也代表电影在年轻人心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当这些来自巴黎拉丁区一个个电影俱乐部的年轻人,开始为一部电影争执不下,为一个导演发起论战,为一个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被开除而走上街头游行,引起“五月风暴”……还能说什么呢?
到了我这一代,情况有变。表面上看似是个电影受人追捧、票房不断翻番的年代。我就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年代,看电影和电影院的关系改变了吗?
大家可以在电影院这个空间里放松下来,我们可以共同感受投射,共同和电影的来处(也就是身后某处)站在一边,而电视的构造原理,造成它始终在我们对面。还有就是,电影不可停止,更像生活一旦开始,必须撑到结局,谁手上也没有遥控器。
前几年,我走进大型商场看电影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电影院都建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是个独立的建筑。而商场里都有美食街,美食街尽头是电影院,有时还同时有几家不同名称的电影院。这个年代,电影院里聚集的不仅是影迷,更多的是一些逛商场逛累了的“观众”—这些人不在乎电影演什么,只在乎和朋友歇歇脚,或者多待一会儿,尤其是那些甜蜜的恋人们。当然,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电影处境,无可厚非的现代生活。
一些问题是科技进步解决不了的,赛日尔·达内说:“电影的奇观体验既是百分之百个人的,却又得在一个挨着彼此—有时是恋人之间—的团体中才算成立。”有点像京剧的没落,实际上就是一种戏迷生活方式(盖碗茶一喝,戏楼里一坐,戏折一哼)的消失。
法国哲學家萨特小时候就经常和母亲去电影院看电影,他有文化的外祖父对此很不理解。老一辈文化人都喜欢去按三教九流把座位分开(“等级分明”)的剧院。萨特在《文字生涯》里热情洋溢地回忆了关于电影院的这段往事:“观众混杂在一起,好像不是为了娱乐欢庆而是发生了一场灾难才聚集在一起的。在电影院里的礼节被取消了,这反倒显露出人们之间真正的关系,及依附关系。”(沈志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萨特看到的这一点,对于后来的“新浪潮”也非常有前瞻意义,新浪潮拍了半天,拍的不就是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
特吕弗有句话是:“我们既在体验电影,也在借助这种体验来生活。”它解释了我为什么偶尔从街边走过,就想起记忆中晾在电影院外面被晒破了的座椅,因为那是一段生活的印记啊。
新浪潮导演侯麦在一九七一年接受《视与听》杂志采访时,记者问起电视兴起对电影的影响,他说:“你坐在电视屏幕前,却没有沉浸其中。但在影院里,观众则会连绵不绝地浸没在银幕里。”是啊,电影最重要的沉浸感,有一部分就来自电影院。所以,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后来关于电影院的忧虑来自更多方面(也有电影自身的问题)时,记者在电影《春天的故事》(1990)上映时问他对此怎么看,侯麦说自己没有什么“影院崇拜”,电影在影院,或在家看区别不是很大,尤其对于“未来的人”而言。
现在因为疫情影响,影院关门不少,比观影场地(建筑物)消失令人伤感的是,它在人们的生活里,似乎越来越可有可无。而我们如今就是侯麦口中的“未来的人”,是只能每天靠刷手机获得安全感的人。害怕沉浸,多余享受沉浸,最后在另一种幻觉中迷失。
关键词:迷影
法国人为虔诚的现代影迷创造了这个词“迷影”,中国影迷将这个词说成是一种电影时代的精神遗产。其实,“cinephilia”的希腊字根,原意指对电影的爱,就是说,关键在于爱,这种人类本能。
当然,“迷影”能称其为一种文化的前提是,大家达成了一种共识:最好的电影时代过去了,“迷影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什么是最好的,还要另行讨论。总之,这个看上去有些距离的词,是一个讨论过去式的、略带悲情怀旧色彩的文化术语。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不是说,电影文化也是这样呢?
法国导演阿贝尔·纲斯有过感慨:“再看以前拍摄的影片真让人感到悲哀。从物质上来说,它们都没有用了,差不多什么也没留下……”这是物质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有胶片保存问题,战争、自然条件等,让很多电影提前消失了。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其他文化群体好像都不如“迷影”群体中的怀念者的比例大,或者是我个人视野的局限?在《迷影》这本书最后的段落,作者安托万·德巴克也写到这种心态:“但凡触及这种方式的迷恋,往往都会染上一层怀旧或是忧郁的色彩,亦即一种与‘电影之死紧密纠结在一起的弦外之音。”他把那些人称为“迷影忧郁症”,说他们对电影执迷,“总会以各自的世界观去把客观的世界给取代掉”。在影评人塞尔日·达内看来,“这种相对健康的疾病的症状之一,是该世界早已成了另一个世界”。
“迷影文化”和“电影文化”不一样。电影是一个现代科技下的“工具”,是影迷与过去(记忆)交流的媒介。迷影文化,可以说是对这个过程的一种带着爱的描述。当我把“迷影”作为一个主题写下来,带有遗憾地强调时,就已经承认了一个问题,比如好奇我在说什么的人会问,电影院不是每天都要上映电影吗?你们失落什么?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不存在了?
之前,我提出“电影漫游症”的说法,是建立在作为一个现代影迷快乐的基础上的。经典电影已经组成的那个世界足以满足我个人。谈到什么不存在了,我似乎有点惭愧。要回答眼下这个问题,应该从我们网上买票,按时去电影院,就可以看电影的生活方式开始。谈电影非常容易,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高見,可以写成评论。但作为一个大众话题,电影人人有份。我曾遇见一个人,对方只关心娱乐八卦,知道所有新人明星,一开始我不知道和他谈什么,后来他说,某某虽然有很多粉丝,但还没到火候演电影。原来在他心中,电影还是比明星有价值的。这倒让我吃了一惊。
大家都看到了一种事实:电影不只是电影本身那么简单,二十世纪以来,电影达到了超越文学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一种强势的大众文化。
我们身边的人不是经常为好电影越来越少愤恨吗?这种心情,也是针对各自心中的好电影来说的。一旦电影上升为“精神”,就意味着只有少数影迷拥有这种不灭的、对电影的热爱,所以才会有伤感。
对电影的这种情绪由来已久,新浪潮代表人物特吕弗在《眼之愉悦》后记里写道—
在《领圣体者》的结尾,我们看到一位神甫几乎失去了信仰,他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主持弥撒。电影就在那一刻定格,神甫依然在念着弥撒经,我用另一种方式解读这一幕,我对自己说:“是的,伯格曼想要告诉我们,全世界的观众都在疏远电影,但他依然觉得应该继续拍电影,就算我们产生怀疑,就算电影院里空无一人。”(王竹雅译,凤凰出版社2010年)
伯格曼的这部《领圣体者》就是我们说的《冬日之光》(1963)。当我坐下来,想看这部电影时,可能是因为没有在宗教氛围里生活过,感受十分不好。
从这生发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看电影比其他事更需要一个集体氛围,无论是观看,还是谈论。投射现象是电影独有的,“电视不是一种投射,而是一种拒绝”(戈达尔语)。我同意戈达尔这句话。虽然,你可能觉得戈达尔是在维护自己的电影事业,但我觉得,电影和生活的关系就是投射。“……摄影机必须面对光线,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的状态一样。我们首先接收光线,而后才把光线投射出去。”(《戈达尔对话加文·史密斯》,《电影评论》1996年3月、4月)
在家用投影机普及前,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那个年代不流行谈文学。很多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和他们某段感情必然有关,我经常听到人们说起当时发生了什么,看了什么电影。这时候,我就在一旁,静静地,回忆起自己对那部电影的感受。后来,我看电影《苦妓回忆录》时注意到一句话,“生活是可悲的,如果我们没有依靠幻想而活的话”。可能我就想表达这个意思。这部根据马尔克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对我个人来说,最动人的是直面未来的生命力。电影结尾,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喊出“我为爱情而疯狂”时,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真诚,我们反而会认真想象他下一句将喊出什么。“从今天起整个世界似乎很美好了!”他喊。
 电影《冬日之光》海报,1963 年
电影《冬日之光》海报,1963 年很多人谈起过自己为什么喜欢电影。我就觉得,人可能有一个情结,喜欢明知遥远,却犹如眼前一般真切的事物—既不意味着发生,也不意味着不会发生。可能我小时候生活在县城里,但我却可以通过电影,“看”到了墨西哥人、法国人、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如何过节、如何交朋友的……这种“眼之愉悦”是电影带来的。
在家用投影机普及后,情况依然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