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莉·鲁尼(Sally Rooney)
萨莉·鲁尼(Sally Rooney)在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都柏林文学地图》中,有这样一句极尽褒扬却也恰如其分的评述:“都柏林创造着英语世界文学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事实也确是如此,当我们谈及爱尔兰和都柏林文学时,谈论的往往是奥斯卡·王尔德、威廉·巴特勒·叶芝、詹姆斯·乔伊斯、约翰·班维尔、克莱尔·吉根这些誉满全球、堪称明灯的文学大师。至于近年来被文学界盛赞为“千禧年一代首位伟大小说家”的萨莉·鲁尼(Sally Rooney),虽然她绝大部分人生经历都在爱尔兰,但任何试图从爱尔兰文学传统或是爱尔兰前辈先贤的创作脉络中,找寻鲁尼继承和转化痕迹的举动,或许都只能是无功而返。
倘若非要刨根究底,所谓的线索可能也只有寥寥几条。比如,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不仅是鲁尼和塞缪尔·贝克特、威廉·特雷弗等前辈大师共同的母校,同时也是鲁尼小说《正常人》中男女主人公康奈尔和玛丽安相约求学的地方,而在乔伊斯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两个浪子》《死者》(均收录于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三一学院”也曾作为地标频繁出现。又比如,在鲁尼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费利克斯演唱的爱尔兰民谣《奥赫里姆的少女》,在《死者》中也被达西先生演唱,正如达西先生的歌声成为葛莉塔意识觉醒的关键驱动一样,《奥赫里姆的少女》也唤起了主人公艾丽丝深藏心底久未爆发的强烈感动。
一
作家塑造虚构人物,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两者之间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同构或是投射的关系—虚构人物身上无可避免都会有一些作者的影子、沾染上作者的气味—虽然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主人公艾丽丝在给朋友艾琳的信中已经写道:把作家和作品联系起来“没有为公众带来一点好处,还使得文学话语完全围绕‘作者这一角色展开,他的生活和个性的诸多不堪细节势必被人毫无缘由地翻检审视”。但事实上,鲁尼借助艾丽丝之口陈述自我的文学观点,就已经套牢了“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况且在小说“致谢”部分,当提及书中艾琳的某段思考时,鲁尼也称“如有谬误,责任都在艾琳和我”—这也恰恰说明了虚构的“艾琳”和作为写作者的“鲁尼”本身就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是无法完全撇清关系或割裂独存的。
在鲁尼先前的两部小说《聊天记录》《正常人》,以及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我们都能窥探出明显的“鲁尼基因”。这些基因的组成,既表现在外在的标识或身份,也体现在内在的思想和情绪上。比如,虽然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鲁尼破天荒地塑造了费利克斯这个流水线上的“蓝领”,但除此之外,“文学青年”的身份几乎归属于鲁尼笔下的每一个小说主角:《聊天记录》里的弗朗西丝是个年轻诗人、博比热衷于唱诗表演,《正常人》里的玛丽安是“小说迷”、康奈尔是文学专业学生,《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的艾丽丝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艾琳则是位文学杂志编辑。这些被牢牢限定在文学领域的人物形象,无论如何都很难回避鲁尼的人生履历和社交圈子。又比如,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鲁尼还借助小说人物之间大量的对话和通信,陈述了对于政治、历史、文明、宗教、爱情、消费以及当下疫情的思考,这些又何尝不是代表着鲁尼自己的社会关切?况且她也曾在采访中说过:“小说的事件可能是假的,但所有情感经历都是真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作家本人一样,鲁尼小说中的人物也始终处在动态成长的过程之中。在鲁尼二十六岁发表的处女作《聊天记录》中,主人公弗朗西丝和博比还都是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而在之后的成名作《正常人》里,小说男女主人公虽然结识于高三,但时间的轴线已经拉长到了大学四年;至于这本出版于鲁尼三十岁时的《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则跨过了大学阶段,把更多的叙事定格在了已经步入社会的主人公们身上。在《聊天记录》和《正常人》里,鲁尼让主人公们的阅历和思想都迟于自己几年,并用回溯过往的视角审视他们失控的生活、认知的蝶变;而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除了二十九岁的艾丽丝、艾琳、费利克斯之外,鲁尼还一反常态地塑造了三十四岁的西蒙—这个比自己略微年长、和自己拥有相同政治信仰的男主角,故事里西蒙所表现出来的游离、焦虑和沮丧,似乎也暗藏着作为写作者的鲁尼对于未来生活的另外一重洞察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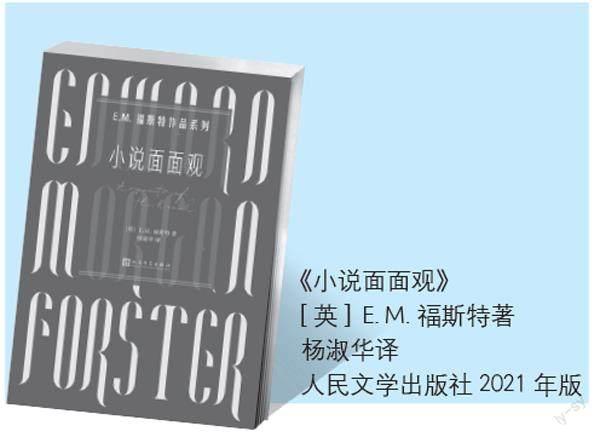
英国作家E. 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写道:“小说的基础是事实加X或减X,这个未知数就是小说家本人的性格。”鲁尼的小说虽然绝大多数都着墨于年轻人的爱情,但之所以从未被归类在“青春伤痛文学”的狭隘范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鲁尼宽阔深邃的视野。她对社会多元人群倾注了强烈的关注,这种关注也正是鲁尼最为难能可贵的“X”。从《正常人》里的玛丽安,到《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艾丽丝,鲁尼多次把目光投射到了精神病患者身上,如同凝视着真实生活中的朋友一般,鲁尼凝视着她们的孤独、厌世和无奈,给予发自心底的悲悯和共情。而在《聊天记录》和《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鲁尼还多次写到性少数群体,他们和正常人一样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既没有遭遇外界任何的异样眼光,也从不对自身情况讳莫如深;鲁尼时常展现出对“与性和解”的期待,在她看来,对性的认识应该回归简单和平常,任何过于深入和琐碎繁冗的思考,都只会让人生的困惑越来越多,疲惫的生活更加疲惫。
二
文学界对于鲁尼的评价向来有些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鲁尼的小说“从头到尾都精彩绝伦”“令人手不释卷”,况且年纪轻轻的鲁尼,其作品早已入围过布克奖,还一举囊括了英国国家图书奖、英国女性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而反对者则牢牢咬住鲁尼的“自我重复”不放,认为她总是保守地延续着固定的主题,书写着近乎雷同的人物形象。且不论托马斯·哈代一辈子都在谈论离奇荒诞的人生宿命,索尔·贝娄绕来绕去都在书写知识分子形象,单是当我们环视鲁尼的小说序列时,就足以惊艳于她在小說结构上的不断探索和极具美学意义的反复重构。可以说,从《聊天记录》到《正常人》,再到《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每一个鲁尼都是新的。
和绝大多数作家的处女作一样,鲁尼的《聊天记录》也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但第一人称的直抒胸臆并没有成为鲁尼自我禁锢的“温室”,在接下来的《正常人》中她就开始尝试隔章切换视角,双主线的叙述模式犹如考究对称的巴黎古典主义建筑,和谐而工整。而在最新出版的《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鲁尼虽未在结构上“大动干戈”地另起炉灶,但也展现出既擅长“大手术”,又做得了“微整形”的叙事布局能力。不同于上部小说里类似于平行符号的绝对双主线,鲁尼让故事结构如同甲骨文里的“大”字一样,从“双线并联”到“单线串联”再回归“双线并联”,并且依旧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对称。艾丽丝和艾琳两个原本并行不悖的叙述对象,在小说行进到四分之三时因为相约度假而碰到一起,戏剧冲突曾一度剑拔弩张,但随后又在理解中复归于平静;随着度假结束,合而为一的叙述线再次分开,而此时曾经夹杂些许颓丧和戾气的两人,都已迎来久违的阳光心态。
虽然很难从爱尔兰的文学传统中找到鲁尼继承“衣钵”的蛛丝马迹,但这并不等于说鲁尼的创作就是无源之水。作家科林·巴雷特就认为鲁尼的小说很好地承接了美国作家B.E.埃利斯“早期的那种紧凑、从容到酷的文风”,而作家安妮·恩赖特也评价《正常人》等作品是“十九世纪小说里的那种引擎”,至于鲁尼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滥觞于英国的书信体小说以及《帕梅拉》《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代表作品。虽然《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主要叙事视角还是第三人称,但鲁尼在小说中每逢双数章节都会插入一封艾丽丝和艾琳之间的往来信件,这些以“我”之口娓娓道来的书信,调和了小说单一的叙述模式,拓展了相对狭窄的叙事视角,让作品兼具了第一人称的共鸣感和代入感,也同时拥有了第三人称的客观性和全知性。英国书信体小说从十八世纪后期走向没落,随即被亨利·菲尔丁所创的第三人称小说取代,鲁尼自觉扛起了英语文学文体探索的责任,让书信体和第三人称这两种曾经存在取代关系的文体,在特殊的共存交融中焕发出了新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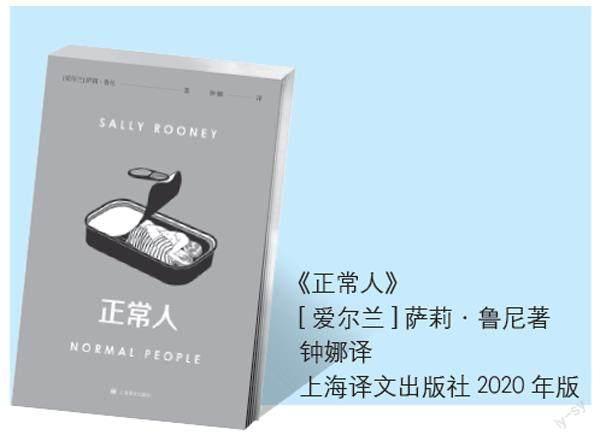
英国文学向来有关注政治历史的传统,以伊恩·麦克尤恩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为例,《教训》(2022)以编年史形式讲述二战后遗症,《蟑螂》(2019)用卡夫卡笔法写英国“脱欧”困境,《我这样的机器》(2019)以复活图灵为线索讲述人工智能对历史的创造。不同于麦克尤恩们将政治历史背景杂糅于故事叙述的“毛细血管”之中,鲁尼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对政治历史的思考几乎被限定在了艾丽丝和艾琳的书信往来之中;在和朋友聚会时,费利克斯甚至提醒艾琳,“不要一进去就开始聊国际政治什么的,人家会把你当怪胎的”,“艾琳说她本来也不懂什么国际政治”。一边是在通信中刨根究底地探讨那些事关人类社会发展最深层次的问题,一边又是过着最日常寡淡的生活,精神的撕裂难免把主人公们推向焦灼煎熬的深渊,现实的不如意在如此对比反差中显得更加真切。
三
相比《正常人》《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等小说所构建的绝对平衡工整的结构框架,鲁尼笔下的人物设置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非对等的情境关系。“非对等”势必带来话语的失衡、交流的障碍、相处的困境。鲁尼所要展现的正是“千禧一代”年轻人在出身、收入、形象、地位等诸多客观因素的侵扰之下,始终挥之不去的脆弱乏力和焦虑失态。
早在《聊天记录》中,鲁尼就通过弗朗西丝和博比这对情侣、梅丽莎和尼克这对明星夫妻以及弗朗西丝和尼克的出轨恋情,展现了三段感情在非对等关系下的种种难堪。前者是性格上的差异,弗朗西丝乖巧礼貌,博比粗鲁任性,两种人设简直天差地别;中者是角色上的倒置,妻子梅丽莎绝对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丈夫尼克不过是个依附妻子的“花瓶”,这一家可谓是“女才男貌”;后者是财富上的悬殊,弗朗西丝的原生家庭寒酸窘迫,维系大学生活都堪称艰难,而尼克的日子则过得声色犬马、衣食无忧。即便《聊天记录》还只是鲁尼个人风格探索时期的处女作,但鲁尼小说创作的切口已经就此打开,即建构多对亲密关系,并解剖这些亲密关系内部的种种非对等性,或是借此扶持新的亲密关系、制造新的裂痕,或是让原本的亲密关系发酵变味,在其内部滋生一重又一重的新烦恼和新矛盾。
不仅是涉身其中的虚构形象,就连旁观故事发展的读者,都无法不因鲁尼笔下复杂难堪的人物关系而心生疲惫。不过,鲁尼所要做的,似乎就是为了呈现人生疲惫的穿透性和不可变更性—无论是试图做出改变还是努力保持不变,心力交瘁的状态都将一如既往、难以扭转,只不过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正常人》里的男女主人公的关系,相比弗朗西丝和博比则要稳定,鲁尼精妙地营造了多轮反转,让世俗青睐的天平忽左忽右。在小镇里如鱼得水的校园宠儿康奈尔,上了大学却陡然变得忧伤起来;在家乡零余孤僻的玛丽安,来到首都求学后则摇身一变成了社交名媛,两人处境彻底颠倒。鲁尼借此讨论了一个她在《聊天记录》和《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都反复谈及的问题,那就是身份地位、家庭環境这些与生俱来的因素,在非对等关系中起到的主导作用。可以说,即便康奈尔和玛丽安最初看上去“男强女弱”,但两人原生家庭的财富地位差异,特别是双方父母存在的劳务雇佣关系,早已决定了玛丽安在种种方面都凌驾于康奈尔之上;直到玛丽安的畸形家庭暴露在康奈尔面前,康奈尔挥拳砸向家暴玛丽安的哥哥时,两者的非对等关系才因各有劣势而被放缓。小说结尾处,玛丽安向赴美求学的康奈尔的一句表白“你去吧,我会一直在这儿”,看似温情而动人,事实上又何尝不是男女主人公各自无奈妥协的权衡折中。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是鲁尼三部长篇中恋爱关系建构最为稳固的,可以说,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虽时有波澜,但几乎都没什么动摇破灭的危机。然而即便如此,鲁尼对身份、家庭差异下非对等关系的阐释却没有半点削弱。在艾丽丝和费利克斯之间,鲁尼的落笔依旧还是金钱和精神:一方面,艾丽丝的作家“光环”和颇丰收入,让身为体力劳动者的费利克斯时常处于自尊心受压制的状态,费利克斯的调适方式是转嫁压力,先是以“施虐者”的形象抢占话语高峰,他会嘲讽性格孤僻的艾丽丝“你似乎也没什么朋友”,也会摇身一变成为“卫道者”,诘问艾琳或西蒙“你怎么从来不来看她”,看似充满关心,实则却是带着攻击性质的先发制人;另一方面,费利克斯始终因自己微薄的收入而感到自卑,他一边艳羡着艾丽丝的富有,一边嘲笑着收入还不及自己的艾琳,自以为这样就能获得虚无的平衡。
至于《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的另一对情侣艾琳和西蒙,他们都成长在非正常的家庭。鲁尼将艾琳塑造成了前两部小说里“弗朗西丝+玛丽安”的翻版,和弗朗西丝有个情绪失控的父亲、玛丽安有个家暴她的哥哥一样,艾琳也有一个“算不上恶毒,就是很疯狂”的姐姐,以及对这一切都不闻不问的妈妈。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童年决定论”所阐释的,原生家庭的暴戾和缺爱,无疑造成了成年艾琳在感情中的过分依赖,好比玛丽安一度心甘情愿地对杰米表明“我喜欢男人伤害我”,对康奈尔提出的“不要跟学校的人讲(恋爱)这件事”的要求也毫无抵触一样,艾琳也一门心思地满足于与西蒙相处中的种种被动,她有时称呼西蒙为“爸爸”,也表明自己“很享受听你(西蒙)指挥”,同样,她对西蒙和别人约会、不公开她的女朋友身份也安之若素,她既害怕失去西蒙对自己从小到大的庇护,又享受着被支配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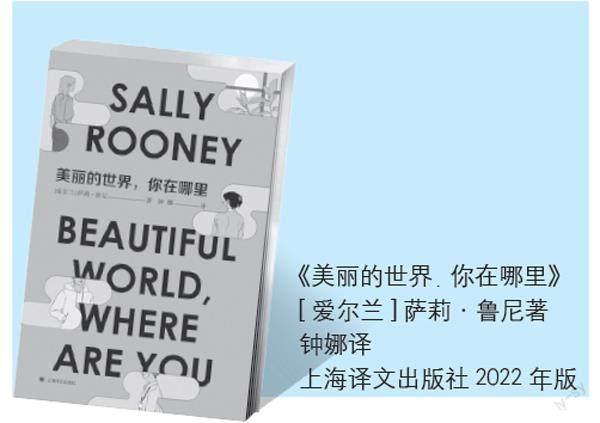
不过,正如将最新长篇命名为“美丽的世界”一样,鲁尼从来都不是一个丧失希望、沉沦颓丧的写作者,她崇尚美国作家乔治·艾略特“女性自我唤醒”的观点。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结尾,鲁尼交代了艾丽丝的自我提醒,“费利克斯还活着,你(艾琳)还活着,西蒙还活着,于是我就感到无比幸运,幸运得让我害怕”;也交代了艾琳人生新的变化,“我怀孕了……他(西蒙)听后哭了,说他很高兴”,“他再次提议我们可以考虑结婚”。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莱昂纳德·科恩那句尽人皆知的歌词:“万物皆有缝隙,那才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