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对古罗马文学家和语法学家奥卢斯·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125-180)的生平知之甚少,他可能出生于罗马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并在那里长大、接受成人礼,随后在雅典受教育,再返回罗马从事司法工作,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民事裁判员。他广泛阅读希腊文、拉丁文著作。厚达二十卷的札记类著作《阿提卡之夜》是其唯一传世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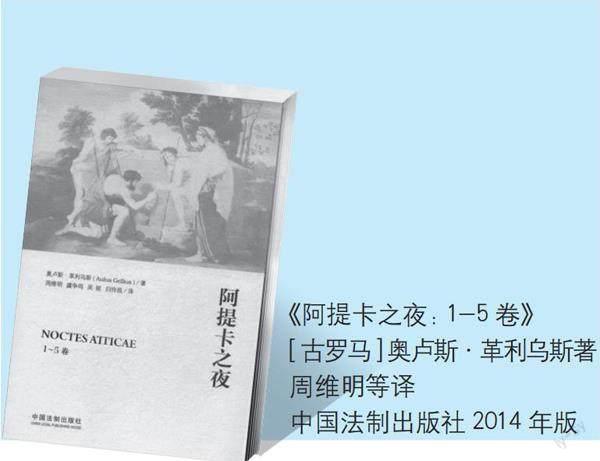
阿提卡是古希腊中东部地区,主要城市包括了雅典。据作者自述,阿提卡冬夜漫长,十分难熬,他就抄书自遣。札记内容则是哲学、历史、文学、美学、法学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三教九流、风土人情、文化娱乐、吃穿住行无所不涉;散文杂记、传说典故应有尽有,真可谓地地道道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百科全书。
后人各取所需,常有所获。举一个例子,《阿提卡之夜》是转述《十二表法》条文的二十一部古书之一。顾名思义,《十二表法》就是刻在十二块板子(表)上的法律,李维说板子是铜的,故而这部法律又被称为《十二铜表法》(后来有人考证,认为板的材质其实是象牙)。《十二表法》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它是平民和贵族反复斗争的结果,在公元前四四九年完成;公元前三九○年,高卢人入侵罗马,该法典被占领军焚毁,既未保留残片,也无抄本传世。现在所知的文本,是后世学者从各种文献中收集、整理而成的。(《十二铜表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
法学家正是根据革利乌斯的《阿提卡之夜》相关记载,还原了《十二表法》第四表第四条“婴儿自夫死后十个月内出生的,推定为夫的子女”,以及第六表第四条“不愿意确定(事实上已长期和她同居的)丈夫对自己支配权的妇女,每年应离开自己的家三夜,因而中断占有(她)的一年时效”,这是古罗马一项颇为古怪的规定,换句话说就是,妻子一年之内如果有三个晚上不与丈夫同居,她的财产即归她自己所有。
革利乌斯所参阅的古典书籍,现在大部分已经遗失。这有点像给《三国志》写注的裴松之,裴松之写注时参考的书,现在也基本失传了。西哲有云“书自有其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有些书留下了,而更多的书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
二
传世的《阿提卡之夜》在西方文学史与古希腊罗马历史也占有重要位置,是西方古典学绕不开的书目。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引用过该书内容。爱读札记的钱锺书也钟爱此书,学者张治梳理过,《管锥篇》引《阿提卡之夜》七处,有四处见于《容安馆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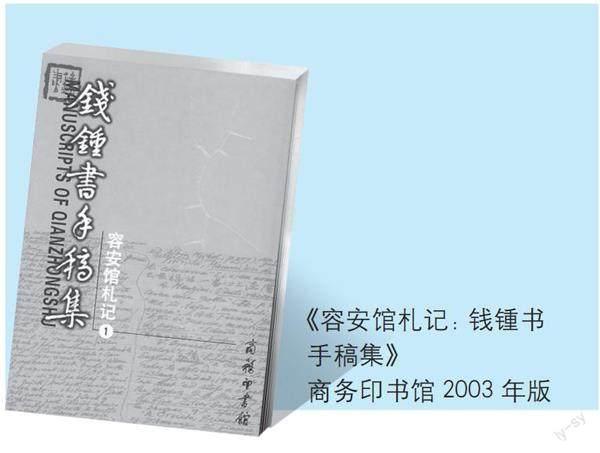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八十一则评价:《阿提卡之夜》“即《日知录》、《蛾术编》之体,序中所举诸书,皆吾国札记劄记之类”。这只是钱锺书对中西札记内容庞杂、体例相似的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札记,虽然体例相似,贯穿其中的精神却截然不同。中国古人的札记,如顾炎武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读书札记《日知录》,内容汪洋,他的门人潘耒将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一语中的,是“通儒”拯救“世道人心”之作。《日知录》第一卷谈《易》,在儒生看来,《易》正是经天纬地之法,而在这张无时无刻不悬置眼前的大网笼罩之下,天地之间的“怪力乱神”都可以简单、万能地解释为“气运之疵,亦是法纪废弛所致”。“格物”格得太“道貌岸然”了,不好玩。相对的,就缺少“天真的好奇”。王鸣盛的《蛾术编》,同样如此。
《阿提卡之夜》里的抄书,显得更为轻松。比如第一卷第一章,就抄写了普鲁塔克讲述的毕德哥拉斯所使用的测量尚在人世时的赫拉克勒斯身高的方法。也更具理性精神。革利乌斯详细地记录了古罗马的各种占卜术,如看动物的内脏分布,看飞鸟的痕迹,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严重怀疑”,他明说自己不相信占星术,并摆出几处逻辑严密的反驳。论科学精神,对星座越来越痴迷的现代人,可能远远不如两千年前的古人。
革利乌斯也会记下一些“怪力乱神”的材料,比如“学问精深的哲学家塞奥弗拉斯特说,在帕弗拉戈尼亚所有的山鹑都有两颗心,而泰奥彭波斯说在比萨尔提亚兔子有两个肝”。看架势,如果条件允许,他会去现场查验甚至解剖一番,就像因维苏威火山喷发,吸入含硫气体而中毒死亡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普林尼一样,身上有着浓浓的“天真的好奇”。维苏威火山大爆发时,普林尼前往灾区,目的是为了救援灾民,同时也认为这是研究火山爆发千载难逢的机会,最后死得其所。
三
由于该书卷帙浩繁,牵涉的知识面极广,再加上是使用了较为晦涩难懂的白银时期的拉丁文(革利乌斯在引用古希腊文献时,则直接用古希腊文,古羅马智识阶层,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很正常的事),给中译者设置了不小的障碍,这也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中文全译本面市(钱锺书读的是洛布版英译本)。
约在十年前,我年长的朋友虞争鸣先生和他的小组,开始着手翻译拉丁文原著《阿提卡之夜》,并参考了英、法诸多译本,最后拿出了行文雅驯、注释详细的中文全译本,完成了这项颇为浩大的工程。中国法制出版社最终花八年时间(2014-2021),分四册发行(每册五卷)。真可谓功德无量。
读完二十卷《阿提卡之夜》,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革利乌斯在他厚厚的札记中,竟然无一个字提及当时贤明的皇帝马可·奥勒留(121-180)。
革利乌斯和马可·奥勒留年龄相仿,后者是当世明君,还是虔诚的斯多葛派信徒。革利乌斯对当时各种哲学流派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札记中也记录了不少斯多葛派的话语,按理,他不该漏掉马可·奥勒留。更重要的一点是,革利乌斯和马可·奥勒留的交际圈有重叠:有一位共同的老师马尔库斯·弗兰托(Marcus Fronto,100-166)。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革利乌斯和马可·奥勒留见过面的文献证据,但是,从常理推断,我们不可否认两人见过面的极大可能性。
身为“帝师”,弗兰托是极为荣耀的,这可以从两人的通信中感受出来(弗兰托和马可·奥勒留曾密集通信,也有数量可观的书信内容留存于世)。在无数个举火宴席畅谈的夜晚,弗兰托理所当然会向自己的学生革利乌斯谈起另一个著名的学生,当世明君马可·奥勒留。而革利乌斯却在厚厚的札记当中无一字提及马可·奥勒留,这更有可能是有意避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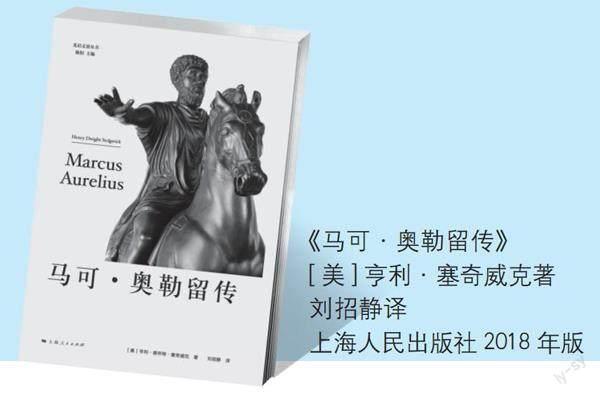
四
革利乌斯的“有意避开”,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在革利乌斯生活的年代,学者们享受到了最好的博雅教育,熟悉人们在哲学、修辞、历史、文学等方面展开的“最杰出的思考和写作”,然而他们自己却缺少创作力,原创文学陷入中衰。“这是一个批评、归类、分析和比较时代。”(亨利·德怀特·塞奇威克《马可·奥勒留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他们对前代作者产生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对罗马早期作者的热情再度复苏。公元二世纪,古罗马弥漫着复古之风,西塞罗和加图是弗兰托、革利乌斯这些学者们的偶像。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在革利乌斯看来,西塞罗所处的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星空璀璨,而他要做的,只是拼凑西塞罗留下的黄金碎片了。
这种社会风气,也决定了革利乌斯的写作方向。革利乌斯在书中抄录的大多数文献材料都是历史文献,虽然他也记录了和同时代文人的多次会饮,但是讨论的都是对文学、哲学、修辞学问题的解读。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他信手建立的“文学宝库”,是供孩子们“消遣之用”,也是供自己“回忆之用”。复古主义,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革利乌斯在书中基本上不涉及当代事件,也不涉及罗马社会中很多尖锐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当时已经成为社会议题的基督徒问题),也很少表露自己的政治偏好和倾向。除了是“复古主义”的抄书信条使然之外,也不排除他特意与政治力量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在革利乌斯的记忆之中,流放哲人也是常有的事。革利乌斯另一位重要的老师法沃里努斯(Favorinus,81-150),是当世杰出的演说家、哲学家(偏重怀疑论),曾深受明君哈德良(76-138)的宠幸,可是在一三○年前后失宠,后被流放。
《阿提卡之夜》第四卷第一章,记录了一大群来自三教九流的人,聚集在帕拉丁宫的前厅等待着向皇帝致意时,法沃里努斯对某位自吹自擂的语法学家的嘲讽。在整章嘲讽的文字过后,革利乌斯却不提最后皇帝到底有没有出来接见。这位皇帝,即安东尼乌斯·皮乌斯(Antoninus Pius,86-161)。相比学识上的兴趣,革利乌斯对政治似乎比较冷淡。

五
另外,我们读历史很容易会犯“后见之明”的毛病,总是不自觉地站在全知的角度解读历史人物,总觉得在相同时期的那些伟大心灵,都是相互认识,相互辉映的。以马可·奥勒留为例,我们对他的好感,最主要是因为那本他于鞍马劳顿之中留下的传世之作《沉思录》,哲人王朴素而真诚的内心独白,读来让人感动。但是,当时的人,如革利乌斯自然不会有这样的观感。
马可·奥勒留的这本《沉思录》,是一本写给自己的修行手册。他在世时,没有想过出版(当时的出版是手抄)。后来稿本可能是被他的女婿或好友收藏起来,历史上可考的最先述及此书的记录,见于三五○年一位哲学家的讲演录,此后五百多年,此书默默无闻,直到公元九百年左右,人们又知道此书尚在人间(《沉思录》梁实秋译序,作家出版社2017年)。也就是说,《沉思录》被人广泛阅读,是很后来的事。
当时的革利乌斯根本不知道马可·奥勒留写下了《沉思录》,他不可能“后见之明”地看到《沉思录》在后来的时间长河之中如此的畅销,如此的重要。在革利乌斯来看,马可·奥勒留充其量只是一位对斯多葛感兴趣的明君。对“复古主义者”的革利乌斯来说,他不会太在意同龄人马可·奥勒留。对过去的美好想象、对同时代的忽视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去问每一个时代的作家,他的偶像是谁?给出的答案大多是古人。
斯多葛派,由塞浦路斯岛人芝诺(Zeno)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在雅典创立,之后的代表人物是塞内卡(Seneca)、爱比克泰德(Epictetus),马可·奥勒留是斯多葛派最后也是最完美的代表。斯多葛主义为什么会在马可·奥勒留身处的年代走向衰弱?英国历史学家莱基认为,是罗马社会的日趋腐败与堕落使斯多葛主义—斯多葛主义要求相当大的自控能力—对许多罗马人失去了吸引力。
在马可·奥勒留之后,斯多葛流派走向衰落,其余晖以火花的形式偶尔地閃现在后来者的笔端,比如笛卡儿在《关于方法的演讲》中显露出他对斯多葛主义的学识,我们也能在叔本华的著作中读出斯多葛主义对他的影响。然而,仅此而已。
由于所站的坐标点不同,不同的人回望历史,在头脑中形成的历史图像是不同的。在革利乌斯看来,斯多葛主义,已经彻彻底底走向衰弱。他是自然而然地“屏蔽”了马可·奥勒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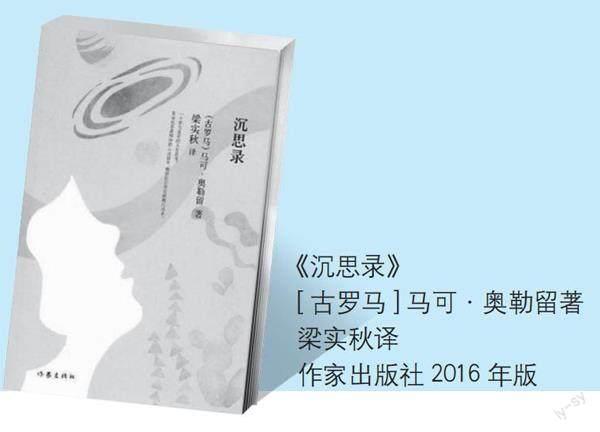
六
弗兰托、马可·奥勒留、革利乌斯三个人的交际,存在先后顺序,有点类似纸牌游戏中的“接龙”。
至少在一三九年,弗兰托就已经是马可·奥勒留的修辞学老师,两人的通信大致覆盖了一三九年到一四三年这个时间段,这正好是马可·奥勒留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根据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的自述,从弗兰托身上,他“注意到一个暴君所具有的猜忌、狡诈与虚伪,并且一般讲来,我们所谓的贵族阶级都缺乏慈爱的天性”。
大约在一四六年至一四七年之间,马可·奥勒留放弃了修辞学,最后转向了斯多葛主义。按照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的自述:“由于拉斯蒂克斯,我才注意到我的品格有改进与锻炼的必要……不要写空疏的文字,不要作老生常谈……要避免修辞、诗歌与绮丽的文辞。”(《沉思录》梁实秋译,作家出版社2017年)可怜的弗兰托为此感到气馁,却也无能为力。(亨利·德怀特·塞奇威克《马可·奥勒留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正如《马可·奥勒留传》作者所说,由于受到外部敌情和内部衰颓的双重威胁,身为帝国继承人的马可·奥勒留要在空余时间里花费大量的心思去处理繁重的帝国事务。艺术和智识消遣,无法满足马可·奥勒留的内心,他要过的是“严肃生活”。(同上)
一六一年,马可·奥勒留和弗兰托“似乎又重归于好”,“彼此都回到了那个老话题—修辞学”。身为斯多葛信徒,马可·奥勒留睡得很少,弗兰托在一六一年写给马可·奥勒留的一封书信中乞求,“要注意区分白天黑夜,要有充足的睡眠”。(同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修辞学家弗兰托对斯多葛主义的委婉批评。
 《阿提卡之夜》,1666年版插图
《阿提卡之夜》,1666年版插图革利乌斯与弗兰托的相识,要迟于马可·奥勒留。据《阿提卡之夜》记载,有一天哲学家法沃里努斯要去看望患足疾的前执政官弗兰托,邀革利乌斯同去。这是革利乌斯和弗兰托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到了弗兰托家中一看,许多学问渊博的人在座,正在进行一场有关颜色及其名称的讨论。这正是修辞学的范围。两人就顺势加入了讨论。
一四三年,马可·奥勒留任弗兰托为执政官,任期短暂,只有两个月,“这很可能是皇帝对弗兰托为马可的家庭教师的一种奖赏”(同上)。而法沃里努斯卒于一五○年,也就是说,革利乌斯和弗兰托的第一次见面在一四三年至一五○年之间,也正是马可·奥勒留放弃修辞学,让弗兰托即可怜又气馁的时光。在革利乌斯面前,他对马可·奥勒留具体會是怎样的评价,不得而知。也许有些许牢骚吧,也许这种情绪也影响了革利乌斯对马可·奥勒留的观感。
七
我们说过,革利乌斯可能出生于罗马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他在乡下应该有舒适的别墅,过着体面的智识的生活,享受与朋友夜宴、畅谈的时光。这也与马可·奥勒留“苦修者”的气质格格不入。
革利乌斯在《阿提卡之夜》中多处提到斯多葛主义,总体的态度是,嘲讽了社会上夸夸其谈的斯多葛派信徒,而对斯多葛主义历史上的真正先哲如芝诺等人持有尊敬之情,从中也可以看出革利乌斯个性保守与崇古。在革利乌斯看来,他身处的年代很难找到真正的让人敬佩的斯多葛信徒,至少不包括马可·奥勒留。
《阿提卡之夜》第十九卷第一章是一篇很有趣味的长文章(《阿提卡之夜》中的札记,短的很短,而篇幅较长的,往往都很有趣)。抄录如下:
我们乘船从卡西奥帕(Cassiopa)渡过狂暴、宽阔而波涛汹涌的爱奥尼亚海到布伦迪西乌姆(Brundisium)去。第一天的那个夜晚,几乎整夜都刮着猛烈的侧风,将海水灌满了船……
同一艘船上,有一个有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在雅典时,我便知道此人名望颇高,并且对自己年轻的学生管束甚严。在如此危急时刻,在这天与海的喧嚣中,我向他望过去,想知道他的心境是怎样的,他是否无所畏惧、镇定自若。而后我看到这人非常恐惧,面色惨白,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痛哭流涕,也没有发出任何这类声音,但是他的脸色和慌乱的表情与他人相差无几。
而当天空开始晴朗,海面回归平静,危难之火熄灭后,一个来自亚细亚的富有希腊人朝着这个斯多葛哲学家走来,在我看来,此人衣着考究,带着很多行李和随从,其自身的体态和气质无不散发出奢华的气息。这人以一种近乎揶揄的口吻问道:“啊,哲学家,当我们处于险境时,你害怕得面色惨白,而我则无所畏惧,面不改色,这意味着什么?”
革利乌斯真是沉着、可爱,在如此危险时刻,还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所谓的斯多葛哲学家,看能否遵守自己的信条。我甚至怀疑,文中那位来自亚细亚的富有的、衣着考究,带着很多行李和随从的希腊人,就是他本人。
根据斯多葛的信条,天灾人祸之类,不受我们控制的,就无须担忧,而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完全能够控制的事情上,那就是保持内心的平静。
斯多葛派哲学家“略为迟疑”,作了大段大段的回答。革利乌斯还算满意,就把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大段大段论述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当革利乌斯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或质问着)经历过风暴的斯多葛哲学家,不知他会不会想起那位同门师兄—弃修辞学而投奔斯多葛主义的皇帝马可·奥勒留?革利乌斯的嘴角会不会有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