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古代历史著作提到某些名称(有些是专有名词),不只是命名,言语配置往往承载额外的负荷。词与义,舛互移位亦常见,语义关系的罅隙中闪露难以确认的叙述迷径,或仅仅成为某种符号性修辞。暧昧之处直如文字涂鸦,不期然代入晦涩的隐喻和暗示。
风雨怅然,只为古人犯难。读书也是折磨,无聊中又捡拾风化剥蚀的文本碎片,按覆若干词语之生成与扩衍,乃以慰留逃逸的记忆。当然,若干疑问依然未解,抑或无解。
外? 戚
所谓“外戚”,是指帝王的外姓亲属。《词源》释义:“帝王的母族、妻族。”这个定义涵盖后妃本人及其家族,此条举例便是《史记》之《外戚世家》。太史公笔下的“外戚”是以后妃为主名,又间或述及其家人行状,故司马贞《索隐》谓:“纪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后妃捎带后族,原是拢到一起来说。
太史公所记外戚,乃汉初至武帝时诸帝后妃(有谓“秦以前尚略矣”)。如,高祖吕后、戚夫人、薄姬,文帝窦后、王美人,景帝薄后、栗姬、王夫人,及武帝陈后、卫后、王夫人、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钩弋夫人等,凡十余者,传述各自身世及宠幸之事。但吕后地位特殊,《史记》另有《吕太后本纪》,主要写高祖崩后其临朝称制,及诸吕作乱,终为周勃一班老臣所夷灭。《外戚世家》兼及外家事况,但诸吕只简略带过。文帝窦后昆弟前后故事記载稍详,如窦长君、少君如何被上手段监控,以防“效吕氏大事也”。
《汉书》无“世家”一体,胪述高祖至平帝后妃作《外戚传》,列于《西域传》之后。这显然是另册处置。汉代外戚干政是大问题,班固对汉家宫闱亦颇鄙夷,其传末曰:“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城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乌嘑!”《汉书·外戚传》所记后庭人物,高祖至武帝一朝与《史记·外戚世家》相重,二者对读,记事详略互见。
值得注意的是,于《外戚传》之外,《汉书》又单置《元后传》,讲述元帝皇后王政君故事。传主只元后一人,篇幅竟抵《外戚传》三分之一。此女之所以大书特书,亦是因为身份特殊,她是王莽之姑,对王莽篡汉柄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莽新朝只十几年,而这王政君却是汉兴以来临朝最久的宫闱政治家,有谓“历汉四世(按,即元、成、哀、平四帝)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按,新都,指王莽称制后,改国号“新”,以洛阳为新室东都)。
《史》《汉》之后,史家不以“外戚”概称后庭,“后妃”之目大抵始于陈寿《三国志》,抑或司马彪《续汉书》。彪书早佚,清人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从《御览》中辑出司马彪所记后妃二十九人,想必专立名目。司马彪与陈寿是同时代人,其书与《三国志》孰先孰后不好说。陈氏奉曹魏为正统,《魏志》置《后妃传》,蜀吴二志各置《二主妃子传》《妃嫔传》,但各志均无《外戚传》,盖因魏蜀吴三方实无外戚秉政。《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九月,诏曰:“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有鉴于两汉外戚擅权,曹丕于开国之初作此规训,以免后患。三少主时期,郭太后(明帝郭皇后)每以诏令预事,看似已不再遵守成命,如《后妃传》谓:“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但这不能说是后族乱政,司马氏父子诛曹爽搞废立诸事,实是假太后之名,拿她背锅而已。郭氏父兄尽皆封侯不假,可域中已是司马氏天下,没有外戚恣横的空间。

蜀吴闺庭不成典规,但外戚未起风浪。东吴孙权临终前,皇后潘氏欲效仿吕后专制故事。可孙权尚未咽气,她就被缢杀。《吴志·妃嫔传》说是宫人所为,注《通鉴》的胡三省认为是“吴史缘饰,后人遂因而书之云尔”。历史不乏阴谋或阴谋论。
陈寿之后,范晔撰《后汉书》亦不以“外戚”作后宫叙事,单列《皇后纪》(含妃嫔),将后妃提升至帝纪规格,如太史公《吕太后本纪》。东汉太后临朝几成常态,权位庶乎诸帝。东汉外家权势熏灼,范书却无“外戚”之目,乃将邓训、邓骘、窦宪、窦武、何进那些后妃家人分置列传。从辑佚的《续汉书》残篇来看,司马彪已有成例。之前《汉书》将后妃作“外戚”,而霍光、卫青、霍去病等外家人物亦各自立传,
由内及外,及至内外剥离,词义变化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刀光剑影。后世撰史,将“后妃”与“外戚”分别设传,大抵始于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其后唐人撰《晋书》,亦照此办理。之后,史家所称“外戚”,仅指后妃娘家人,不包括她们自身。
校? 事
三国官制有“校事”一职,用以伺察臣民言行,具体说就是侦察、检举、处置言论不当和心怀不轨的官员和士民。曹氏魏国初建即设校事官,曹丕称帝后权任更重。东吴亦有这类职事,谓之“典校”。以后延至两晋,又称“校郎”。《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七月“门下校郎刘祥入言事”,胡三省注:“自曹操、孙权置校事,司察群臣,谓之校郎,后遂因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曰:“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关于校事、典校,《三国志》记述散见于魏吴二志,即魏之高柔、常林、徐邈、程晓传,吴之顾雍、步骘、朱据、潘濬、陆凯、是仪、诸葛恪诸传(包括裴注所引诸书)。如,《魏志·高柔传》谓:
[高柔]迁为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高]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赵]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赵]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
这里说到的校事卢洪、赵达二人可谓恶名昭著。曹操赋予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的权力,以致大小官员无不畏惧。鱼豢《魏略》记录当时曹营流传的一句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太平御览》卷二百四一引)这是人人自危的局面。高柔为官一向“明于法理”,认为赵达等人“以憎爱擅作威福”,严重破坏官场职司,向曹操进言当废止校事之设。老曹明知他们是坏人,却想着坏人有坏人的用处,整人的事情贤人君子做不来,只能任用赵达这些恶棍。这是他用人驭众的机窍。不过,将之比作叔孙通以群盗壮士助刘邦争天下,实是不伦不类。
赵达作恶太多,最后还是被曹操处理了。但曹丕上位后不改章程,任用刘慈、刘肇等为校事。《高柔传》:“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高]柔皆请惩虚实……”又,《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一例,叙文帝时校事刘肇在成皋县敲诈勒索,与县令衙吏发生械斗。直至明帝、齐王芳时,这班人依然猖獗,高柔、何曾等大臣曾一再奏劾。嘉平中,黄门侍郎程晓(曹操谋臣程昱的孙子)上书痛陈其害,才罢去校事官。
东吴自孙权设置典校,起初有吕壹、钱钦数辈,亦是操纵权柄,擅作威福。如,《吴志·步骘传》谓传主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擿抉细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又,《朱据传》曰:“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朝中将相几乎都被监视告密,有人竟因不断告密而获几种罪名。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等都曾被监视,甚至丞相顾雍因告密竟被拘禁。典校如此猖獗,太子孙登屡次进谏请罢校典,但孙权一直不听,诸大臣没人再敢说话。后来大臣李衡在孙权召见时,口陈吕壹多条奸罪,长达数千言,致使孙权面有愧色。之后,孙权终于狠下心,诛杀吕壹,以平群臣之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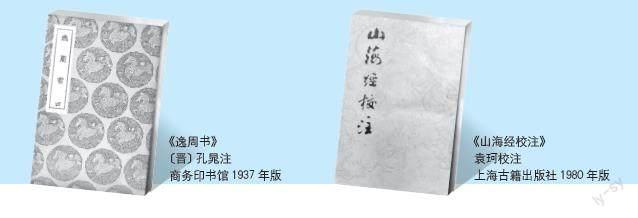
孙权死后,其少子孙亮继位时才十岁。大将军诸葛恪辅政,为笼络朝政,废除典事。但及至吴末帝孙皓即位,不但恢复典校,后又听张俶建言,加设称为“弹曲”的纠察官。《吴志·孙皓传》天纪元年(277)裴注引《江表传》曰:“[张]俶表立弹曲二十人,专纠司不法。于是爱恶相攻,互相谤告……”张俶其人靠告讦上位,做了主持弹劾官员的司直中郎将,很快又身败名裂。如谓:“[张]俶奢淫无厌,取小妻(按,指妾)三十余人,擅杀无辜,众奸并发,父子俱见车裂。”谮白别人竟并不掩饰自己胡作非为,实滥权导致变态。
魏之校事,似乎不属正式职官序列,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将之列为魏相府散属。据《御览》引《魏略》,校事后改为抚军都尉,比二千石,第四品。此说不见于《魏志》纪传。吴之典校,属中书省,本是校核官府文书的职事,案牍中爬梳剔抉,扯出无中生有的故事。
开? 府
曹魏建国后,有一种作为官员加衔的赐命,就是“开府”,官称“开府仪同三司”。开府,字面意思是开建府署,辟置掾属。两汉制度唯三公开府,三公即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东汉皆去“大”字,大司马改太尉),亦称“三司”。但汉末战乱改变了固有体制。献帝初平三年(192),李傕、郭汜、樊稠攻陷长安,共秉朝政,各以将军名号开府,时谓“与三公合为六府”(《后汉书·董卓传》)。或为将军开府之先例。
其实,曹魏享有“开府”或“仪同三司”的官员并不多,拢共算来只是以下数例:魏景初三年(239),黄权(蜀汉降将)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正始元年(240),刘放以中书监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孙资以中书令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正始二年,王凌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嘉平二年(250),郭淮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甘露二年(257),孙壹(东吴降将)拜车骑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其中“开府”连带“仪同三司”者,仅孙壹一人。
这里有一个疑问:“开府”之号,是否等同“仪同三司”,二者是否同位语关系?或“仪同三司”是否作为“开府仪同三司”之缩略写法?
“仪同三司”始于东汉殇帝时,《后汉书·邓骘传》谓:“延平元年(106),拜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又谓:“[仪同三司]始自[邓]骘也。”车骑将军秩二品,位于三公之下,称“仪同三司”,即品秩及相关待遇援引三公仪制,自是赐位特进。但《邓骘传》未有“开府”之名,许多学者以为“开府仪同三司”起于蜀降将黄权。其实《黄权传》亦未见“开府”名号。至于“仪同三司”是否作为“开府仪同三司”之省略用法,清代学者于此颇有争议,但看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魏方镇年表》,明显是用“仪同三司”表示“开府”之义。
卢弼《集解》于《蜀志·黄权传》“权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句下注释援引诸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开府”可追溯到东汉明帝时,东平王刘苍以骠骑将军辅政,班固作《奏记》表賀,有“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宜及府开,以慰远方”数语(《后汉书·班固传》),即证为后汉开府之始。明帝是东汉第二个皇帝,照这样说,刘苍开府比邓骘还早半个世纪。
查《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开府”与“开府仪同三司”分作两个词条,因为撰写者不是同一人,行文有差异。一谓:“凡开府,地位即与三公相当,品秩、俸赐亦与三公相同。”一谓:“仪同三司,谓开府之仪制援引三公成例。”看上去是一个意思,也没说区别是什么,不明白为何要设置两个词条。
赤? 壁
赤壁所在,古来聚讼纷纭,主要轇轕于蒲圻、嘉鱼二说。二十世纪末,蒲圻被命名为赤壁市,似乎了结一桩公案。当然,另有黄州一说,过去颇有影响,主要缘于苏轼赤壁二赋。从蒲圻到苏轼谪居的黄州是好长一段江流,赤壁寻址千里邈邈,讨论者多不介意是在南岸还是北岸(江左还是江右)。其实,南北也是问题所在。
按蒲圻、嘉鱼诸说,赤壁在长江南岸。《水经注·江水三》谓:“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江流自西而东,其“右迳赤壁山北”,表明其地在南岸。《水经注》所记之处在蒲圻下游,大致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第27页,三国吴荆州)标示“赤壁”的地方(但第六册第28页,北宋荆湖北路,又在蒲圻近旁注记“赤壁山”,大概是出于保留历史争议的考虑),这是学者将赤壁定于南岸的主要依据。
记述赤壁之战的《三国志》对这个地名未作说明,亦未给出具体方位。关于战事本身,陈寿记述过于简率,而裴松之注主要引述《山阳公载记》《江表传》,虽有所增补,并未能让人窥识整个战局。读者对赤壁之战的认识,更多得之于小说《三国演义》。史书缺省处,小说家有酣畅淋漓的发挥。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借东风,火烧赤壁,华容道关羽释曹……这一步步推演,除去火烧一节皆为小说家结撰。
陈寿撰史多为曹公讳,老曹失利之事不多说。《魏志·武帝纪》仅寥寥二句:“[曹]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另如,《蜀志·先主传》先是提到孙权派周瑜程普率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然后亦三两句交代过去:“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而《诸葛亮传》对于战事本身仅“曹公败于赤壁”一语带过。

《吴志》各传叙述稍详。《吴主传》谓:“[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但从这段文字看,此役规模并不很大。其余如程普、黄盖、韩当、周泰、甘宁、凌统诸传,只表各自参战有功,未作具体陈述。《吴主传》说曹操撤退时烧了剩下的船只,而《先主传》则谓刘备一方“焚其舟船”,明显不对茬。《吴志》诸传唯独《周瑜传》对战局有细节描述,其谓黄盖用诈降之术发起火攻,略似小说家笔墨:
……[孙]权遂遣[周]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虽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威,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据此推断,曹军船舰曾渡江抵南岸作战,“遇于赤壁”或即此义,按此其地在南岸。然而,“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接下去的战事应发生在江北。黄盖放船延烧曹军及岸上营寨,战火即起于贴近江北的水面上。再看,先头“遇于赤壁”一句,乃提挈语,指周瑜、程普与刘备“并力逆曹公”的决胜之局。参互《先主传》“与吴军水陆并进”云云,可知当东吴水师在江北登陆之际,刘备所部即自陆上出击。
刘备的部队就在夏口。据《先主传》《诸葛亮传》:当阳之战后,刘备南撤,集合刘琦部属万余人俱到夏口,而并未渡江至南岸集结。夏口是汉水入江处,位于长江北岸,在《三国演义》中这地方称“三江口”,即所谓“三江水战,赤壁鏖兵”之处。陈寿书写“遇于赤壁”或“战于赤壁”,未予具体定位,而小说虽将战事置于江北一线,却亦闪烁其词,实未展示“赤壁”之场景。“赤壁”所在,终究是一种符号性存在。
孔? 雀
孔雀产于岭南及域外温热地带,古人视为稀罕之物。《汉书·南粤传》记载,汉文帝派陆贾去安抚粤王赵佗,粤王以藩臣贡献诸般珍物,其中有“孔雀二双”。又,《西域传》谓罽宾国出产孔雀(作“孔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则谓滇国“多出鹦鹉、孔雀”。
秦汉以前鲜有提及孔雀。《诗经》中出现的鸟类多达二三十种,如:雎鸠、鸠(鸲鹆,即八哥)、鸤鸠(布谷鸟)、鹑(鹌鹑)、鹊、鹤、黄鸟(黄雀)、鸮/鸱鸮(猫头鷹)、燕子、鸨/雁/鸿雁、鹳、鸿(鸿鹄、黄鹄)、雉/翚、鵻(鸽)、鸳鸯、鹈/鹈鹕、凫鹥(野鸭、鸥鸟)、乌鸦、脊令(鹡鸰)、桑扈(斑鸽)、鷻(雕)、鸢(鹰)、鷮(长尾雉)、仓庚(黄莺)、鵙(伯劳)、鹭、桃虫(鹪鹩)……当然还有传说中的凤皇(凤凰),但就是没有孔雀。《诗经》的风雅颂都产生于北方,那时北人没见过孔雀,而再往南去的荆楚之地亦未有此物,故屈原未将孔雀引入诗中。但《九歌·少司命》有“孔盖兮翠旌”之句,注者多将“孔盖”释为孔雀翎毛制作的车盖,未知确否。
汉语文献最早提到孔雀大概是《山海经》和《逸周书》,如《海内经》有谓“孔鸟”者,郭璞注曰“孔雀也”;《逸周书·王会解》亦云:“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但《山海经》《逸周书》都经汉人羼补(尤其《海内经》明显是后来增入),不好说是否两汉时期之见闻增广。唐段公路《北户录》“孔雀媒”条称:“《周书》曰:成王时方人献孔鸟……”这里说的《周书》就是《逸周书》,《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未见“方人献孔鸟”之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曰:“火离为孔雀。”而同书卷九十引是书曰:“火离为鸾。”这么说孔雀也就是鸾。古人所说的鸾鸟是一种虚拟的珍禽,即凤凰、玄鸟一类神鸟,可见汉代对于孔雀的认识仍羼入想象的成分。不过,那时已知孔雀产自南方。如,《盐铁论·崇礼》讨论如何接待蛮夷来朝,大夫说要以“列羽旄,陈戎马”的场面以示威武,贤良则谓“羽旄”那类装饰蛮子不稀罕—“南越以孔雀珥门户”。
以孔雀(孔鸟)入诗赋,大抵亦汉代诗人所为。枚乘《七发》,吴客向太子描述登景夷台所见景物,即有“孔鸟”等飞禽。刘向《九叹·远游》亦见“孔鸟飞而送迎兮”之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则有“鹓鶵孔鸾”之名,按张揖训释,“孔鸾”即孔雀与鸾鸟。这是混合虚构与非虚构的混沌叙事。诗人想象楚地已有孔雀,上林苑之无限空间何其不有。
汉末乐府古辞《孔雀东南飞》(《玉台新咏》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开篇以孔雀为起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诗序介绍,此诗是写“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的婚姻悲剧。这里有个问题,汉末建安时庐江是“郡”而不是“府”,其地在今安徽西部(三国魏吴双方在江北江南各设庐江郡)。作为行政区划的“府”,是唐以后才有的设置,可以肯定此序必是后人窜补。
《辞海》条目说,孔雀在我国仅见于云南西部和南部。這是一种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留鸟,其自然分布未见于长江流域。诗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俨然作为迁徙性的候鸟来描述,况且自西北往东南方向飞行,亦不合其习性。当然,史书多有西域献孔雀的记载,一不留神从西北飞来亦未可知。当然,贤哲说读诗不能抬杠,这里用作起兴或毋庸细究,但不妨作想,此句抑或另有来源。
鹈? 鹕
古代史官记述自然界反常现象,称之祥瑞或灾异,以为王朝兴衰、人事休咎之征验。正史中这类记事通常分别载入天文、五行、符瑞诸志,但《三国志》未列志篇,祥异现象主要记录于帝王纪传。譬如,魏文帝曹丕登基前,各地相续出现黄龙、白雉、凤凰、麒麟等物,这些祯祥似乎预示着天命神明之应。但什么是祥瑞,什么是灾异,有时候官方的解释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譬如,诸臣亟劝曹丕代汉践祚之际,太史丞许芝普大喜奔来报告—蝗虫来了,这下可好了!灾异如何成了祥瑞?因为蝗虫亦被视为受命之符,古人以为此物乃“阳气所生”,介虫之孽就被解读为鼎革易祚的消息。
曹丕做了皇帝的第四年,亦即黄初四年(223),又出现了一个奇异景象,《魏志·文帝纪》谓:“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灵芝池方于上年建成,有说在洛阳,有说在邺都(《历代宅京记》持前说),这不去管它,反正是宫苑之景。鹈鹕,又名塘鹅,是一种大型水禽,喙下带有可伸缩的喉囊,样子蛮可爱。成群鹈鹕聚集皇家园林,难道不是好事?可曹丕就觉得是不祥之兆。其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这里所说的“曹诗”,指《国风·曹风》的《候人》一诗。其中“维鹈在梁,不濡其羽”一句,以鹈鹕翅膀不沾水喻悖逆之象。如毛传云:“鹈,洿泽鸟也;梁,水中之梁(按,梁,鱼梁,捕鱼筑的水坝)。鹈在梁,可谓不濡其翼乎?”郑笺云:“鹈在梁,当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曹丕逼献帝禅位而登基,其合法性打了折扣,这是他心头的一个梗。“维鹈在梁”或是上天借鹈鹕发出警示,亟须检讨“远君子而近小人”的问题。他心知肚明,当初劝进的那帮小人马屁拍得太过分,现在要找“俊德茂才、独行君子”做门面。当然是史家在给他找平衡。
鹈鹕之事亦见《魏志·王朗传》,是谓:“黄初中,鹈鹕集灵芝池,诏公卿举独行君子,[王]朗荐光禄大夫杨彪……”御座自省,引发求贤与举荐的君臣互动,王朗要让位杨彪,华歆要让位管宁,忙着向文帝表忠心。《宋书·五行志三》记曰:“于是杨彪、管宁之徒,咸见荐举。此谓睹妖知惧者也。”杨、管二人有古君子之誉,一向与曹魏政权不能啮合,文帝欲拜太尉,皆不受。
鬼? 目
东吴末帝孙皓迷信巫觋占验,《吴志·三嗣主传》记述其在位时不断有祥瑞现世,甚至闻说某处野菜疯长也被视为吉兆。如,天纪三年(279)八月记事:
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分。又有荬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草,荬菜作平虑草,遂以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
东观(中书省机构,藏文书经籍,掌修国史)官员们根据图例判识,鬼目和荬菜皆“瑞草”,因之黄、吴两人都被召进宫里做了郎官。(以汉制论,“银印青绶”属高阶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其实,这里所说的两种野菜并非罕物。后者又称苦荬菜、苦苣菜、败酱草,是南北常见的菊科野生植物。但前者称之鬼目者,大概就是古人所谓“苻”之一物,《尔雅·释草》曰:“苻,鬼目。”郭璞注:“茎似葛,叶圆而毛,子如珰也,赤色丛生。”今之《辞源》释义:“鬼目,草名。即白英。俗称白草子,蔓生。叶似王瓜(按,即土瓜),有茸毛;子赤,圆如龙葵。入药。”这跟《尔雅》的解释对得上,这鬼目菜是一种茄科野生植物,亦南北皆有,只是长得如此高大,世所罕见。

《齐民要术》卷十有“鬼目”一条,说的应是另一物。贾思勰引郭义恭《广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饮酒。”又引《南方草物状》曰:“鬼目,树大者如李,小者如鸭子(按,鸭子应是鸭卵,此句疑前后倒错)。二月花色,仍连著实,七八月熟,其色黄,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武平、兴古、九真有之也。”其所引《南方草物状》好像不是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今本《草木状》未见此条。又引裴渊《广州记》曰:“鬼目益知,直尔不可噉,可为浆也。”接着就提到《吴志》记载孙皓时黄耇家那株长达丈余的鬼目菜。然后再引顾微《广州记》曰:“鬼目,树似棠梨,叶如楮,皮白,树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齐民要术》此卷记述种种稀见草木(所谓“非中国物者”,即非中原之物),皆引晋人著作,抄撮他书,存其名目而已。
贾氏这里介绍的“鬼目”,应是一种乔木状果树。此条中间插入《吴志》所言黄耇家巨型鬼目,分明胡乱羼入,是将木本和草本鬼目混为一谈—鬼目菜既“长丈余”,便误以为是某种树木。其实,从这夸张笔墨中不难领会撰史者讽喻之义。黄耇家鬼目菜长成“祥瑞”的第二年,东吴就亡了。
按《本草纲目》记载,“鬼目有草木三种”。李时珍是将木本鬼目称作“麂目”(见卷三十一果部),另有白英和羊蹄草两种为“草鬼目”(见卷十八草部)。
所谓“木鬼目”,不知究竟为何物,如今不见说起。《齐民要术》引《南方草物状》举其产地,均为南方温热地方。交趾、武平、九真三郡,两晋时属交州(三郡均在今越南中部),兴古郡在宁州南部(今云南省砚山、文山一带),可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第四册,两晋时期)。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