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虫之声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这样的未见与既见,在《诗经》中反复出现,可以视为中国抒情诗的一个基本主题,甚至,如《召南·草虫》这首诗的第一章,就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小雅·出车》里。然而,如诗人学者杨牧(王靖献)在他那本《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中所指出的,对于歌谣传统中基于主题而形成的套语,前代学者往往忽略其中旨在唤起的某种形式感和音乐效果,习惯于将之凿实为历史记述,遂生出种种曲解和附会。
诗,首先是一种歌,它音乐性的一面要求诗人能够像作曲家一样,去吸纳过往种种已有的现成的曲调,加以组合和变化,从而利用寥寥几个字的声音组合就唤起某种共有的情感记忆;而它诗性的一面,却同时也在呼唤某种崭新的虚构,或者说创造。作为诗的这两个方面,都在拒绝一种简单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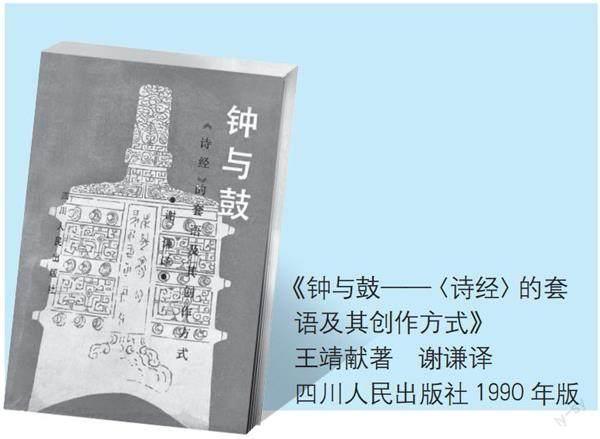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这首诗开始于一种微弱的声音。喓喓,拟声词。草虫,现在一般认为就是蝈蝈,但从诗人的角度,也可以就是一种泛指,因为只是听到草中的虫声罢了,并没有亲见。趯趯,跳跃的样子。阜螽,即蚱蜢。能聽到虫声,往往是在寂静的深夜,诗人被虫声惊醒,起身四顾,又看到跳跃的蚱蜢。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仿佛就是《草虫》前两句的扩展版。在自然的声响和场景背后,有一个倾听和观察的人存在,而他为何能够听见和看见这一切微细之物呢,如果不是因为孤寂和无从诉说的心事。
过去经学家多纠缠于草虫和阜螽的生物学特质及其隐喻,但又没有太多科学依据,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先设定结论之后的倒推式臆测,比如将草虫比作君子,阜螽比作女性,凡此种种,未免有“死在句下”之嫌,因此后来姚际恒《诗经通论》就曾很严厉地批评过郑玄和欧阳修,“郑氏曰,‘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邪辞也。欧阳氏本之,又谓‘喻非所合而合。前辈说诗至此,真堪一唾”。
诗人之所以提到草虫和阜螽,虽可能源于生活实录,但落实到纸面上,令诗人更为惊异的,或许是在“虫”“螽”和“忡”之间的声音关联,以及心灵所感知到的内在声音和悸动与外部宇宙之间若有若无的应和。随后的“未见君子”,正是从这所听所见和所思中忽然兴起的。当代民谣歌手陈粒有一首《奇妙能力歌》,开头的几句歌词,“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这里面独属于诗人的思维跳跃,很可以作为“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的现代版注解。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在《小雅·出车》中,这两句被简化为一句“既见君子”,而“既见君子”作为一个句式在《诗经》中也的确更为通行,曾出现在九首诗歌中,共计二十余次,相比而言,反倒是“亦既见止,亦既觏止”这样看似冗长的表述,是《草虫》所独有的,或许,也可以视为这首诗的核心。
《草虫》的主旨,历代聚讼纷纭,择其要者,有两种主流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首讲述新婚的诗,“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是未嫁时的紧张慌乱,随后的“既见”“既觏”,是成婚的程序,“我心则降”“我心则悦”“我心则夷”,则是表达婚后的喜悦之情。但南宋崔述的反对意见很有力,他引用《豳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和《邶风·泉水》“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论证当时女子出嫁时唯有悲伤才是最庄重和习以为常的礼节,若直接表达嫁人后的喜悦,有违《诗经》时代的人伦常理。另一种意见以朱熹为代表,认为这是一首妻子思念丈夫的诗,“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朱熹的意见在宋以后影响很大,当代学者也多采用之。但崔述对此却仍有所保留,“但玩其词意,未见其当为大夫之妻,亦未见其必谓妻之思夫也。小雅与诸国风称见君子者多矣,皆不训为思其夫,何独《汝坟》《草虫》在二南中即为思夫诗乎。既不可知其人,无宁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诗人本意也”(《读风偶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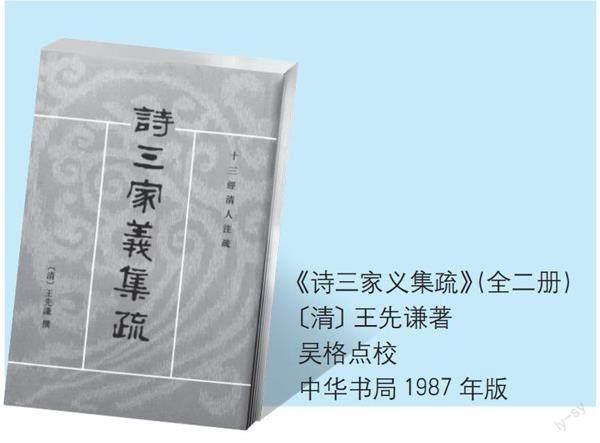
历代对于《诗经》的解释,多专心于实词,如“亦既见止,亦既觏止”这两句中的“见”与“觏”,就是被反复推敲的公案。觏的本义为遇见,但似乎与“见”的意思有点重复,所以自从郑玄引用《易经》“男女觏精,万物化生”之后,“觏”就常被解释为“媾”的通假字,意指婚媾或交媾。然后,若从婚媾之说,就要面对崔述的反驳;若从交媾之说,未免过于猥亵,前人也多有驳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觏”应该通“遘”,依据也是“遇见”和“见”重复,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就认为,“上言‘见,下不当复言‘遇见,鲁诗作‘遘义长”。
至于崔述同时质疑的两种主流解释—新婚说和思夫说—它们之间还有一个最为本质的分歧,就是这个令诗人忧心忡忡的未见之君子,到底是从未见过,还是很久未见。新婚说自然认定从未见过,从未见到既见(初见),从既见(初见)到既觏(无论这个“觏”字被解释成哪种意思),这个句法上的递进关系和周代婚礼程序的实际递进是一致的,非常自然,这也是古老的新婚说一直没有被废弃的重要原因。而以朱熹为代表的持思夫说的学者,要面对两个解释上的困难。首先,因为这位妇人想要见到的并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熟悉的丈夫,那么,“既见”和“既觏”自然就有重复之嫌,为了解释这种重复,“觏”字就只好仍被或显或隐地暗示为夫妻同房,如竹添光鸿《毛诗会笺》:“见与觏自分深浅。见,犹见其面而已;觏,遇也,合也,因与君子相偶而言之。一意翻作两意,由浅而深,风诗往往如此。”其次,既然是思念之作,那么“既见”和“既觏”又从何而来?通行解释是,诗句中的“既见”和“既觏”只是一种虚拟之辞,一种幻想中的自我宽慰,比如程俊英《诗经注析》更是举李商隐《夜雨寄北》为证,认为“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虚实对比的修辞手法,正是受到《草虫》的影响。
我们再次面对在读解《诗经》时经常会遭遇到的一对矛盾,即汉学的以经解诗和宋学的以今解诗,这两种解释路径既彼此攻击和消解,又相互补充与激发,最终,用始终残留的困惑和疑点,为我们打开属于诗的幽暗道路,等待一代代的读者重新有所发现。
《说文·见部》:“觏,遇见也。从见,冓声。”觏是一个典型的形声字,它的意符自然是“见”,而它的声符“冓”其实也在为“见”作限定,意谓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见”。《说文·冓部》:“冓,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凡冓之属皆从冓。”冓是一个象形字,如木头的交叉堆积,它和“见”组合起来用以形容一种特殊的见,我觉得就类似后世所说的“执手相看”。若将觏简单地通假为“媾”或“遘”,就都忽略了这个字最本质的意思是“见”。而从有距离的单向度的“见”到身体彼此感知的“执手相看”,本是一个大的飞跃,没有理由认为是一种重复。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有句云,“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在见(观)与觏之间明显的分别,早被诗人所领悟。
倘若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探讨,就必须去留心“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中的虚词。
“亦”这个字,前人要么就不解释,要么就认为是一个无意义的发声语助词,也偶尔有训为“若”的,但实在是缺乏训诂学证据,更多是一种揣摩文意后的倒推。但“亦”原本實在是一个有意义的字,它是上古汉语并列复句中较为常见的关联标记,语义上表示类同,语法上具有关联功能,类似于后世的“且”“又”“也”。毛郑不解释,是因为从新婚说的角度“亦”的本义非常顺畅,不需要解释;后世很多学者视之为无意义语助词,则因为从思夫说虚拟相见的角度,没法用“亦”的本义来解释。在古典解经系统里,发声语助词的说法实在是一个大箩筐,任何讲不清楚的虚词都可以往里面扔。

“亦既”连用的语证,《诗经》里似乎仅见于《草虫》,此外可见于《尚书·梓材》:“亦既用明德”。但《卫风·氓》有“亦已焉哉”的句子,“已”和“既”义通,可以互参,“亦已”的用法似乎在先秦更常见,比如《离骚》的“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综合这几处的文意,“亦既”和“亦已”都显然是在表示一种完成时态,并且这种完成显然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而不是将要完成的虚设,它们的意思,如果用现代汉语表达,大概会类似于“也就这样”。
再来看“止”字。旧解再次视之为无意义语助词。而在甲骨文和金文里,“止”是一个象形字,象征足趾之趾。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论证《诗经》中一部分用于句末的“止”字当释为“之”,因为“之”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的写法,是在“止”字下面加上一横,象征足趾在地上行动,本义近似于“往”。这两个字因为非常相像,后来文献传抄时渐渐就被混用。所以后来陈世骧《中国诗字原始观念试论》在讨论“诗”字古文写法的字根时,径直就把古文里的“止”和“之”当成一个字,只是兼有相反两义,即停止和去往,并以此作为基础论据,来展开他对中国诗的发挥,“足之动又停,停又动,正是原始构成节奏之最自然的行为”。我们现在虽然能确认“之”和“止”在古文里也是两个字,但如果说“之”字中隐含一个“止”的字根,大抵还是不错的。
但于省吾论证完《草虫》中的“止”即“之”字,继而又断定这个“之”字是一个指示代词,代指所见君子,这倒未必可从,因为即便是“之”字,在古文中作为语气助词的例证其实也比比皆是,不一定就非要作为代词。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的两个“止”字,即便最初就是“之”字,也依旧是语气助词,只不过,它是一个饱含深意的语气助词,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寻找相应的表达,我觉得有点接近于“就好了”,既表示满足,又似乎有点意犹未尽。同时,“止”字恰与君子的“子”协韵,是一种复杂的情感震荡着具体的人身。
我听到草虫的鸣叫,我看到蚱蜢的跳跃,但我没见到你,忧愁的心波动不息。也就这样见到就好了,也就这样执手相看就好了,我的心也放了下来。《草虫》的第一章,就此大抵可做如上的直译。这是一个人在见到另一个人之后的剖白,也是唯有在一段感情真正发生之后才能够体验到的心路历程。台湾的李辰冬也认为这首诗是见面后所写,他将这段译成:“当草虫嘤嘤在叫,阜虫趋趋在跳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您,心里一阵子一阵子地忧愁,现在既然见到了,也遇到了,我的心就放下了。”就诗意而言,也颇有感染力。但他依据这一章和《小雅·出车》字句的相仿,非要将《草虫》凿实为尹吉甫见到南仲之后所写,却大可不必。而此外的解法,如三家诗所谓“好善之作”,方玉润所谓“托男女情以写君臣念”,其实也都是这首抒情诗可以激发出来的引申义罢了。正如崔述所言,“既不可知其人,无宁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诗人本意也”。一首抒情诗,最重要的不是诗的本事,而是诗试图抵达和唤起之物,是其中可以克服时间超越历史的、更为普遍和恒久的情感。
这两个相见的人,可以是异性,也可以是同性;可以是之前从未见过,却也可以是已见过很多次。对于一段深刻的感情,这两种情况可以说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既可以是倾盖如故,初见即如旧相识;亦可以是万物皆相见,日月长新花长生。“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也就这样见到就好了,也就这样执手相看就好了。正是在那些被作为无意义语助轻易搁置的虚词中,藏有多少无从示人的波峭,每一步都是庆幸和满足,每一步又都通向未知的探索。在中国的抒情诗中,男女,君臣,美善,政治生活与儿女私情,往往就是这样混融在一起,从而令人世变得整全。
《草虫》的第二、第三章,可以视为这种感情剖白的复沓,但在诗意的发展上,或有几点还可以略述。虫鸣螽跃,属夏秋夜深之时,常在家屋周围;采薇采蕨,为春夏白昼之事,需赴野外高山。借此微细之昆虫和野菜,诗人贯穿了日夜和四季,也将视野从一隅之地拉升至群山之上。而从“则降”到“则说”“则夷”,可以视为一个遵从爱的秩序的人渐渐能够抵达的安宁。
廖平有言,“《诗》之未见、既见,即《易》之未济、既济”;又言,“《诗》本灵魂之学,人由性情以进修,则卷之在身心,放之弥天地”。正是灵魂的漫游让人忘记时间,所谓“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而读《诗》亦如读《易》,我们在其中找寻和企图安放的是自己不断变化着的身心,而非凝固的历史或僵硬的情感。
厌浥行露
《诗经》中多男女相悦相思之辞,即便是出于弃妇弃夫之口,也每每是一派中正平和之音,怨而不怒,恨而有情。唯有一首《行露》,是彻底决绝的拒斥与愤怒。
历代都同意这是一首有关婚姻诉讼的诗,但诉讼双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诉讼的前因后果,进而落实到具体词句的解释上,却众说纷淆,也没有可靠文献予以定论,是《诗经》中尤为难解的篇章之一。这种诗歌措辞上的纠缠晦暗,和诗人在情绪处理上的斩截干脆,形成非常鲜明的反差。
而这种晦暗的源头,是两个隐喻,即行露之喻和雀角鼠牙之喻。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首章只有三句,且意思有不连贯的地方,同时在句法和语气上似乎和后两章又有点脱裂,甚至冲突,所以过去一直有人怀疑此处存在错简遗漏。然而,面对古典文本的疑难费解处,如果没有足够过硬的实证材料予以支持,动辄用阙文或通假的方式予以疏通调和,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思路,因为这些疑难处或许恰恰也是一个契机,迫使我们放弃已有成见,去体会千载之上的某种新鲜与陌生。如果说“作家就是那种写作困难的人”(托马斯·曼语),那么,古典的解释者,也至少应该是那种乐意被困难推动前行的人。
就这《行露》首章而言,第一个困难可能在于句读。旧时常见的句读是三句连读的,即在“厌浥行露”之后用的是逗号。厌浥,是双声联绵词,即幽暗潮湿;行露,道上的露水;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幽暗潮湿的、道路上的露水”。这突兀而来又戛然而止的第一句,和第二、第三句之间显然是有些跳跃的,这也是有人认为此处有阙文的一个原因。但古典文献原本没有现代这些复杂表义的标点,句读只起到一个停顿断句的作用,如果在这里使用一个后加的逗号会出现问题,那应该质疑的是逗号而不是原文本。因此,后来有些学者如吴闿生、闻一多、俞平伯、陈子展、袁行霈等,在“厌浥行露”之后就纷纷选择使用句号。一旦如此,我们会立刻感受到一种简劲之气扑面而来,犹如遭遇小林一茶俳句的开头“露水的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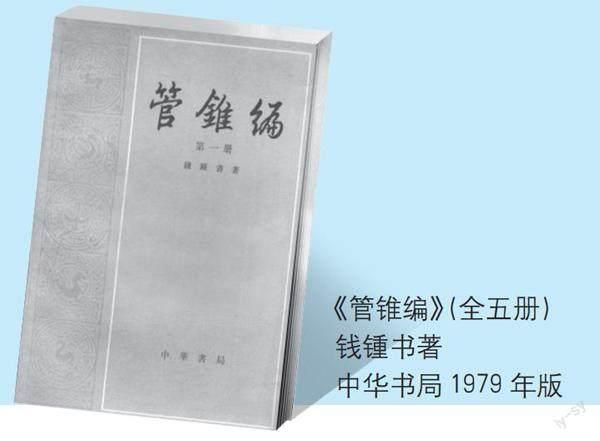
“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这是周作人所译的小林一茶有名的俳句,其首句的断言和后面的转折构成一种委曲缠绕的关系,虽然有无尽的意思欲说未说,但总体的基调,是认识世界黯淡真相之后努力振拔向上的姿态。而《行露》的首章,其实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才好。
“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这一句有两种相反的解释,一种大致可以译为“难道不摸黑起早赶路吗?说是(惧怕)路上露水太多”,这是将路上有露作为理由来放弃早行,“以行人之惧露,喻贞女之畏礼”(孔颖达),比喻女子以男方礼数不到为由婉拒男子;另一种是“难道不摸黑起早赶路吗,说什么路上露水太多?”这是认为路上有露这个理由不足以让人放弃早行,比喻女子对打官司这件事的毫不畏惧。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拈出“比喻之两柄”,“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词之学,亟宜拈示。斯多葛派哲人尝曰:‘万物各有二柄,人手当择所执”。同样,一句话因其语气轻重缓急,时常亦有“两柄”。细细体会这两种解释,前一种消极委婉,后一种积极刚烈。自郑玄以来,历代学者从教化守礼的角度,多取第一种解释,尤其到了朱熹,以“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尔”来解释“谓行多露”,清代马瑞辰又引诗经“岂不”句式的通例(如“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岂不怀归,畏此谴怒”等),怀疑此处的“谓”为“畏”的假借,更是几成定论。但这种消极委婉显然和末章结尾“虽速我讼,亦不女从”的严词峻斥在气息上有所不合,以至于接下来无论是用何种赋比兴来予以附会,都很难解释晓畅,这可能是首章被怀疑有阙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假如我们放弃固有的在解释传统中形成的所谓定论,回到文本本身,就会发现,若取第二种解释,首章和二三章之间的文气就完全贯通了。因此,这一句是王夫之和林义光解释得好:
女子之讼狱,贞者之所忌也。忌讼狱之伤贞也,而侘傺烦冤以惮于屈,无已而死之,死抑不得所谓,则弗获已而从之……明王兴,方伯之教行,淫乱之俗革,且弗能保物之不犯,况丁乱世,履危机,而遇凶人之健讼者乎?必无讼,而后以全其贞,是必天之无露,而后可无濡也。(王夫之《诗广传·论行露》)
夙夜,谓于未旦之时出行也。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言岂能以道上多露遂不早行乎?盖以早行不能避露,喻将慎重择匹,不能畏强暴之侵迫。人之早行,未有因多露而辍者,且察后章之意,行露之女乃不畏强暴,非避强暴也。旧解以畏多露而不敢早行,失之。(林义光《诗经通解》)
露水會弄湿身体,如同打官司这个事情会玷污名声,尤其是玷污一个女子的名声。但一个人倘若真的有要事在身,会因为害怕露水就放弃早起赶路吗?倘若一个女子真有绝大的冤屈,会因为害怕玷污名声就甘受侮辱与损害吗?王夫之就此区分小贞与大贞,“大贞者,保己而不保物者也”,名声乃身外之物,真正的坚贞是去很好地守护住真实的自己,而不仅仅是守护名声。人在世间行走,难免会遭遇各种闲言碎语,以及诬蔑中伤,正如路上早起的行人难免会遭遇露水侵蚀。旧时礼教杀人,很多时候利用的就是人对名声损毁的惧怕,汉代经学解诗亦多从礼制教化出发,但诗三百本是礼教尚未成形之际的产物,其中自有一种无畏的朝气。“必无讼,而后以全其贞,是必天之无露,而后可无濡也。”露水是天意,讼事是人情,既然无可逃避,不如就在露水中赶路,在讼事中抗争。

由此,“厌浥行露”,是对天意、人情乃至命运的认识与慨叹,但同一个认识和慨叹可以通向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本是认清命运真相之后的向上一跃。
行露之喻外,还有雀角鼠牙之喻。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如何理解雀角鼠牙之喻,前提在于判定雀到底有没有角,鼠究竟有没有牙。宋代以后不少学者将“角”与鸟喙联系在一起,近世闻一多《诗经新义》和于省吾《诗经新证》又从音韵训诂角度,训“角”为“噣”,以证鸟喙之说。于是,雀实有角,鼠实有牙,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推演“谁谓女无家”的意思,即“女(汝)实有家”,如陈子展就此认为这首诗为一个女子拒绝一个有家室的已婚男子强迫与之重婚而作。但这种解释,与情理和诗经惯用句法都不吻合。钱锺书《管锥编》对此辨之甚详:
盖明知事之不然,而反词质诘,以证共然,此正诗人妙用。夸饰以不可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谁谓雀无角?”“谁谓鼠无牙?”正如《谷风》之“谁谓荼苦”,《河广》之“谁谓河广”,孟郊《送别崔纯亮》之“谁谓天地宽”。使雀噣本锐,鼠齿诚壮,荼实荠甘,河可苇渡,高天大地真跼蹐偪仄,则问既无谓,答亦多事,充乎其量,只是辟谣、解惑,无关比兴。
钱锺书据段玉裁的说法,认为“鼠无牙”是说鼠没有强壮的大齿,是属于实情,后来刘毓庆进一步考证,认为这里的“牙”是指类似虎狼野猪之类在门齿两侧的犬齿,而老鼠是只有门齿臼齿而无犬齿的。因此,雀实无角,鼠实无牙,这才是我们思考这个隐喻的前提。
进而,雀无角鼠无牙虽是人人应当知道的真相,但大众判断一件事往往只依据表象,如见雀鸟穿进屋中就以为其有角,如见老鼠穿破墙壁就以为其有牙,这种想当然的判断若不加深究,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而谣言、毁谤的传播逻辑正与之相通,譬如见到一个女子身陷婚姻诉讼,就先断定这个女子不够清白。“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这里的“女”和末句“亦不女从”的“女”一样,都通“汝”;“家”,应当解释为室家之约,即婚约。谁说你和我没有婚约呢,如果没有婚约怎么会将我囚禁呢?这是对于围观看客心理的犀利嘲讽。雀鼠穿破我屋墙,是事实,但并不能就此推导出雀定有角鼠定有牙;同理,如雀鼠一般的你侵犯我囚禁我也是事实,但从这个事实并不能推导出我们就有婚约。雀本无角,鼠本无牙,你我本没有婚约,这些才是无论怎么穿墙破屋都不可改变的真相。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这两句是女子为此桩官司的定性和申辩。大意是说,你虽然能把我囚禁起来,我们之间依旧是没有婚约,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这两句是女子最后主观的表态:你虽然企图通过诬告我的方式将我们之间的关系合法化,我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顺从你的。
一名女性,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侮辱与损害,很多时候是潜在的和隐性的,如雀鼠之穿墙破屋,并不是正大光明以角以牙之名,然而一旦得逞,似乎又会一而再再而三,并且利用女性对于名声的担忧,将这种霸占合法化。很多落后国家至今仍有所谓的“强奸婚姻法”,即强奸事件的加害者只要与受害者结婚,即可免于刑罚,同时受害者也得以保全名誉,一张结婚证就可以将无数罪恶合法化。这首诗要描述的,大致也是类似的状况,即一个强暴之男在侵凌女子之后,企图以既成事实来要挟她结婚,然而女子誓死不从。
牛运震《诗志》论《行露》:
章首似截去一句,别格冷韵。得力在叠两“行露”字,婉绝峭绝。隐语拗调,三句中多少曲折。陡接“谁谓”,咄咄逼人。雀说有角,奇!末二句说得豪门富户,真不值一盼矣。足令狂子败兴。雀鼠,骂得痛快风流;“室家不足”,说得冰冷;“亦不女从”,拒得激烈。
总结一下,这首诗的晦暗不明在于两个隐喻。首章“行露”三句,有两种相反解释,又疑阙文,但如与小林一茶的俳句“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如此”相参照,便豁然开朗。小林以露水之脆弱比喻人世之脆弱,《行露》作者则以露水之潮湿比喻人生道路上遭遇之烦扰。在此相似的悲剧性体验和悲观认知之后,两位诗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向上一转,虽然人世脆弱如朝露,人却依旧在这世上怀抱种种热望;虽然人生难免遭遇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扰如露水侵身,人却就是要携带着这些困扰继续前行。这寥寥数句中,有人世间恒久的柔弱与刚强。
行露之喻,描述的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感受,以及在这种感受之后的决断。而雀角鼠牙,其微妙疑难之处在于它既是喻,也是隐。闻一多《说鱼》:“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事物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事物说得不明白。”女子遭受男子侵犯,這是很难直接讲出来的身体上的伤害,需要含蓄;而随后又被男子强说成夫妻关系,则是子虚乌有的毁谤,是精神上的二度伤害,必须要澄清。诗人以雀鼠喻强暴之男,以雀鼠穿屋破墙隐不正当的侵犯,又以雀角鼠牙反讽该男子试图将这种非法侵犯合法化的荒谬无稽,可以说是“一喻多边”,层层递进,虚实相映,将种种要澄清之冤屈要隐藏之伤害,一一讲述,这是诗的能力。
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于此处体贴甚微:
“谁谓”四句,连类精切,情词恳至,覆盆之冤了然可见。……总是实无,而迹则似有,负屈难明,莫见昭雪者也。
“谁谓”二句本是两层,语意甚急,反复申咏之,得其解。凡说诗到难通处,要把旧时讲解尽数撤去,只将本文吟咏玩索,翻覆百遍,其义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