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备受瞩目的人物。这位文坛秀士“身兼数职”,一生创作颇丰。小说、随笔、诗歌、评论,甚至芭蕾舞剧,均有涉猎。同时代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雨果和波德莱尔都对他推崇备至。一八三五年,长篇书信体小说《莫班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及其长篇序文的出版将戈蒂埃推至风口浪尖,惊世骇俗的艺术主张和离经叛道的故事情节使得作品的评价两极分化。雨果认为这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作品,报刊界则痛斥它是“不堪入目的垃圾”。首先激起惊涛骇浪的是如同抗议书般的序文。作者在长达三万多字的序言中凝练出“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主张,反对文学艺术有任何“实用”的目的,提倡赋予美和艺术自由、突破现实社会的束缚,这一主张的提出标志着法国唯美主义思潮的诞生(廖星桥《唯美主义的代表作〈莫班小姐〉》,《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第15页)。小说塑造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莫班小姐,她不愿做深闺淑女,一生被社会规则的枷锁束缚。为了弄清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她女扮男装成骑士泰奥道尔(Théodore)。在与年轻寡妇萝赛特(Rosette)和诗人德·阿尔贝(D?Albert)的交往中,她不断调整生活方式,试图冲破封建的牢笼,逐渐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探索出一种独属于她的生活方式。从裙装到骑装再到戏装,服装作为社会的反映和内心的表达,见证了莫班小姐对自我身份的质疑、纠结与和解,伴随着她对自由的懵懂认知、极力渴望与坚定追求。
小说由作者的客观叙述,德·阿尔贝和莫班小姐分别写给密友的书信交替而成。男女主人公的书信更像是长篇私人日记,记录着对自我经历的思考。莫班小姐的服装变化是叙述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首先,人物塑造离不开服装的衬托,服装是性别特征的外化:“裙装”的华丽繁复凸显了莫班小姐深闺淑女的身份,“骑装”的干练潇洒帮助她伪装成男性,而“戏装”的长裙和配饰又将其短暂地变回女性。其次,服装变化推动情节发展:从“裙装”到“骑装”,莫班小姐经历了女扮男装的冒险;从“骑装”到“戏装”,她被识破真身,与两位情人共度良宵后再度踏上旅程。最后,服装是社会和内心世界的反映:“人类身体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着装的身体,服饰是社会塑造与个体表达的媒介,服装是心灵按照社会与时代的品位赋予身体的形式。”(宋炀《软蜡上的封印—近世纪西方女性服饰与身体关系的言说》,《艺术设计研究》2016年第3期)对莫班小姐来说,“裙装”是社会规则和家庭环境强加给她的,“骑装”是情势所迫的个人选择,最后穿上“戏装”与两位情人共度良宵则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度探索。莫班小姐不同时期的服饰变更反映了她在不同阶段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作家戈蒂埃通过书写莫班小姐对自我的探索和对自由的追求,阐释了自己对艺术和美的独特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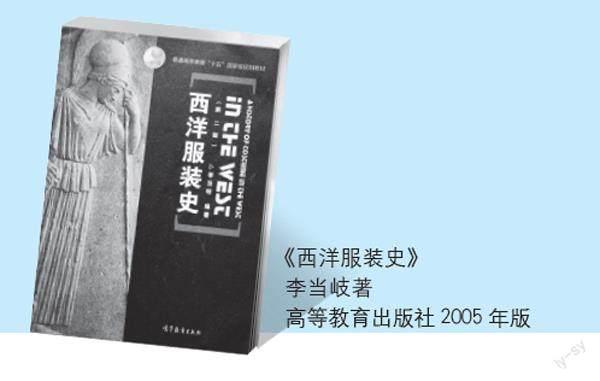
裙装:童贞纯洁,礼教束缚
现代社会的服饰趋向多元化,女性服装不再局限于裙装。然而在历史上,相比于十八世纪末就开始脱离古典样式的男装,女装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开始摆脱传统样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真正实现现代化。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女装一直围绕着紧身胸衣、裙撑和袖型大做文章(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尽管作者并未在书中明确点出莫班小姐生活的年代,但结合其原型—路易十四时代的同名女歌唱家,和书中男女服装的式样,可以大致推断出故事中的莫班小姐也生活在十七世纪。尽管十七世纪的欧洲局势动荡不安,王公贵族们仍在追求奢靡和时髦,服装呈现装饰过剩、奇装异束的特点,这个阶段被称作服装史上的巴洛克时期(同上)。
尽管作品中很少出现对莫班小姐身着裙装的直接描写,我们仍可以通过德·阿尔贝对情人的想象推测出传统女装的华丽和繁复。在诗人的幻想中,他的梦中情人应该“身着猩红色或黑色丝绒长袍,配有白缎子或银色平纹布袖衩,上身一件短开衫,梅迪契式的大皱领,一顶像爱莲娜·西斯特曼戴的那种任意型毡帽,饰有长而卷曲的白色羽毛,一串金项链或钻石项链,许多各色珐琅镶嵌的粗大指环,戴满了所有的手指”(《莫班小姐》,艾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以下仅标页码)。
作者花较多笔墨直接描写的传统女性装扮则是莫班小姐女扮男装离家时被丢弃的“白色长袍裙子”。“路边一丛犬蔷薇里,我瞧见有个白色的东西在抖动,一个银铃般清脆柔和的声音闯入我的耳朵:‘我是您的童贞,我亲爱的孩子;我身穿白袍,戴一顶白色花冠,全身是白……”(第142页)前文德·阿尔贝也提到“所谓单纯,就是身穿白袍,头发不带鬈”(第8页)。白色作为单纯的象征,强调了莫班小姐过去童贞纯洁的传统女性身份。藏有她白色长袍的抽屉则是“白色幻梦的棺柩”,此后她认为自己“已成为一个男人,或者至少表面上是男人”(第142页)。对莫班小姐来说,曾经身穿白色长袍的纯真淑女生活不过是虚幻的梦境,如今大梦初醒,脱下它意味着与过去懵懂的生活告别。

除了象征纯洁,“白色长袍裙子”还折射出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她们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精神自由。在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活动空间受限,时间受到严苛的安排:“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我们被妥善地系在母亲的裙子上,九点钟,最多十点钟,就躺进洁白的小床,在我们干净整洁且隐蔽的小房间里,被贞洁地禁闭和反锁到第二天清晨”(第141页);在思想交流上,女性参与度有限,没有发言权:“我们主要的事情,是笔直地坐着,穿好紧身褡,装好裙衬,眼睛得体地低垂,呆板僵硬赛过人体模型和上发条的玩偶。人们不许我们发表意见,不许我们参与谈话,只许在有人向我们提问时回答是或不是。”(第141页)十七世纪后半叶,紧身胸衣的胸腰部位嵌入许多鲸须,将女性上身塑造得更为纤细瘦长。裙子至少要两条叠穿,裙拖最长可达十米(《西洋服装史》)。紧身胸衣挤压女性身体,夸张的裙子限制她们的行動,将她们禁锢在家中,那些所谓的“美”的标准都是对女性身体的否定和基于男性视角的重塑。然而对于莫班小姐来说,她“喜欢马、剑术以及所有激烈的体育运动……讨厌双脚并拢、两肘贴身地端坐……不喜欢服从社会上的起码习俗”(第199页),但由于裙装的束缚,她只能远离这些爱好。换言之,传统女装并不是莫班小姐自由选择的,而是时代、社会和家庭强加给她的。她不愿意做单纯呆板的提线木偶,排斥社会和家庭强加给女性的种种规则,这也是她选择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她与传统女性裙装的告别可以视作与传统意义上纯洁、顺从的女性身份决裂的开端。
 《莫班小姐》1897 年版插图
《莫班小姐》1897 年版插图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决裂是不完全的,莫班小姐对自我的探索也才刚刚开始。首先,莫班小姐女扮男装主要是为了通过和男性的直接交往“观察和深入地研究他们”(第137页),这样才能将真心完整地交付给对方。在莫班小姐写给友人的信中,她非常爱用“了解”“学习”“知晓”等动词及其衍生词汇,反映了她对两性关系相关知识的好奇和渴望。换言之,尽管此时的莫班小姐萌生了一定的自主意识,但仍然受制于传统的婚恋观,女扮男装不过是测试配偶的手段。其次,穿上骑装是莫班小姐万般无奈下的尝试。她希望挣脱女性身份带来的枷锁,即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选择。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想要以女性的身份达成此目标是不可能的,所以莫班小姐才会转而求助于相对不受束缚的男性装扮。最后,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穆里尔·达尔蒙(Muriel Darmon)在《社会化》(La Socialisation)一书中提到的,社会化在婴儿未出生前就开始了,受家庭、学校和媒体等多因素影响,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诚然,服装可以被看作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延,但要想进一步看清自己的内心,绝不是脱下女装、换上骑装那么简单。一开始,莫班小姐自己也表示:“男裤穿在我身上,并没进入我的灵魂。”(第144页)受制于传统女性世界的内心与男性世界的外表之间不断的冲突,正是在尝试的过程中,莫班小姐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
骑装:闯荡历险,身份诘问
无论这一步多么微小艰难,脱下传统裙装、换上男性骑装这一行为就代表着莫班小姐迈出了自我探索的第一步。从与传统女性身份的不完全决裂逐渐过渡到自我意识的完全觉醒,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作者并未特意刻画莫班小姐的骑士装扮,而是寥寥几笔点明了几个要素:“穿着靴子和男式短裤,还有一顶插着羽毛的大帽子……佩戴着这把长剑”(第143页),“紧身上衣上多开三四个扣眼,用结实的皮带绳仔细系牢”(第234页)。莫班小姐的好骑术和好剑术也帮助她迅速与男性打成一片。正是在与男性群体的相处中,她对自我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内心深处对这种自由生活的渴望被激发了出来。
刚出走时,她认为骑装只是一张与人交往的方便名片,并不意味着与灵魂的契合。然而在与男性伙伴们日益频繁的交往中,她发现:“由于听所有的人都称我先生,见我真被当作男士对待,我也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我的乔装仿佛是我的本色,我简直记不起曾经穿过别样的服装。”(第199页)莫班小姐对内心世界的明晰是由外而内、靠服装具象化的,身体逐渐适应骑装,骑装也开始契合她的灵魂。“开始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说:‘我累了,穿着这身衣服,好些事情真别扭。现在这种情况不再有了。”(第246页)由于始终身着男性服装且生活在男性圈子里,莫班小姐身上残留的传统女性特征逐渐淡化,开始习惯用男性的方式生活。她不用再忍受夸张的裙撑,也不用再遵守死板的上床时间,而是可以骑马恣意闯荡,尽情享受自由的乐趣。
尽管表面上莫班小姐已经告别了传统女性的身份,但与萝赛特和德·阿尔贝的相处和交往又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和纠结。在与二人的交往中,莫班小姐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一方面,男性的精神世界对她缺乏吸引力,她在精神上与女性更契合。在和男性群体的交往过程中,她洞悉了他们人前殷勤、背后下流的虚伪面孔,厌恶这种巨大的反差。另一方面,莫班小姐始终希望能够破解两性结合的快乐的奥秘。因此,肉体上无法克制的欲望让莫班小姐饱受困扰:骑士服帮助她轻松地融入男性群体,但也在她和其他男性之间竖起了屏障,导致她陷入“肉欲的煎熬与折磨”(第256页)。她被精神和肉体上的矛盾紧紧拉扯,在以骑士泰奥道尔的身份与萝赛特交往时,她遗憾自己不是男性,无法与她结合。“如果我是个青年男子,我会多么爱萝赛特!会怎样地仰慕她!我们的心灵确实契合无间……遗憾的是我们的爱注定只能是柏拉图式的。”(第240页)
 《莫班小姐》1924 年版插图
《莫班小姐》1924 年版插图和二人的交往让莫班小姐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她认为自己“永远不能完整地爱一个人……身上总有些没有得到满足的东西在嗥叫……不知道该在哪儿驻足,只好永远摇摆在二者之间”(第247页)。正是在这种摇摆的痛苦中,莫班小姐更加接近自己的内心世界,意识到自己是具有“女人的灵魂和肉体,男人的气质和力量”的独特个体,既不是被裙装束缚的传统女性,也不是骑士装束包装出来的男性。作者借德·阿尔贝之口解释道,莫班小姐拥有的两性美与希腊神话中雌雄同体的赫耳玛佛罗狄忒(Hermaphrodite)如出一辙。在奥维德(Ovide)创作的《变形记》(Métamorphoses)中,赫耳玛佛罗狄忒在水面注视自己的倒影时,水仙女萨耳玛西斯(Salmacis)疯狂地爱上了他。他们双双跳入水中,男身和女身合而为一。此后,赫耳玛佛罗狄忒便以带有男性生殖器的少女形象出现。德·阿尔贝感叹道:“两个都很完美的身体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两种如此不相上下而又如此迥然不同的美,结合成一个高于二者的美。”(第133页)
戏装:雌雄难辨,虚实并存
“女人的灵魂和肉体,男人的氣质和力量”,这是莫班小姐在第一种服饰变更中探索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然而精神和肉体的需求、男性和女性身份不断交替地占领上风,导致莫班小姐始终无法获得归属感。在感情上,莫班小姐认为“雌雄同体”的自己无法完整地爱上别人。面对萝赛特的多次示爱,莫班小姐始终无法正面回应,最后只能落荒而逃;面对德·阿尔贝的欣赏和追求,她自白“确实对他有兴趣有好感”,但也不认为这种感情是爱。此时,莫班小姐对自我的质疑渐渐褪去,但内心仍在纠结,而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注定不能持久。
小说的高潮是莫班小姐被德·阿尔贝识破真身,分别与两位情人共度良宵后再次离去。而正是在三人共同出演莎翁的戏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时,德·阿尔贝逐渐参透了莫班小姐真身的秘密,并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告白。莫班小姐则借出演同样女扮男装的角色罗瑟琳(Rosaline),迎来了与自身存在方式的和解的契机,作者戈蒂埃也借此揭示了一位女性在封建年代独特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方式。
戏中的罗瑟琳是一位公主,服装非常华丽:“连衫长裙用一种闪色衣料缝制,在亮处呈天蓝色,在暗处呈金黄色;紧而窄的半筒靴……猩红色的丝袜……裸露到肘部的胳膊,从一簇圆形花边中伸出……戴着戒指和指环,缓缓摇动一柄色彩斑斓好似微型彩虹般的羽扇。”(第177页)但罗瑟琳公主为了逃亡不得不乔装成男子,她的“装束极其风流倜傥,剪裁得高雅别致,装饰着金银刺绣和系带,近乎路易十三宫廷的精雅情趣;一顶尖尖的毡帽,插着一根蜷曲的长羽毛,覆盖着他美丽的发卷,一柄金银丝嵌花的佩剑在旅行披风下隆起”(第179页)。刺绣、缎带、花边、饰纽等多种装饰无一不彰显出十七世纪服饰的华贵和夸张。通过对服装的直接描写,将莫班小姐优雅淑女的女性气质和英俊绅士的男性气质分别展现在读者面前。戏中男女装交替,隐喻莫班小姐内心世界的摇摆,剧终罗瑟琳重新换上裙装这一情节也暗示着戏外故事的走向。
戏剧落幕后,莫班小姐重新穿上戏中罗瑟琳的裙装。“头发束着珍珠饰带,身着棱形长裙,宽宽的花边襟饰,红后跟的皮鞋,还有美丽的孔雀毛羽扇”(第253页),华丽繁复的装扮刚好呼应了开头德·阿尔贝对情人的想象。而当莫班小姐脱去层层衣裙,“只穿一件料子透明的普通衬衣,像一个白色的幽灵”(第257页),又可以使读者联想到她离家闯荡时换下的“白色长袍裙子”,象征着她童贞纯洁的传统女性身份。在与德·阿尔贝探索两性关系的快乐时,莫班小姐似乎又回归了传统女性的身份。然而这种回归是表面的、暂时的。一方面,莫班小姐选择穿着戏服而非传统裙装面对德·阿尔贝,就意味着她并不想重拾深闺小姐的身份。可以说,这场欢爱是演出的延伸,既是对德·阿尔贝识破她真身的奖励,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两性关系的好奇。如今,在精神和肉体上充分自由、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莫班小姐已经不是那个曾经被裙装束缚在闺阁的少女了。另一方面,莫班小姐的传统女性身份只停留了一晚,她在欢爱过程中向德·阿尔贝吐露了心声:“今晚我为您脱去男人的服装,明天清晨我还会为所有的人重新穿上它。想好了,我只在晚上是罗瑟琳,整个白天我都是,也只能是泰奥道尔·德·塞拉讷……”(第255页)莫班小姐没有被再次穿上的裙装束缚,也不再质疑纠结,而是选择将男性与女性的力量相结合,继续踏上旅程。至此,以怎样的服装示人对她来说已经不再重要,莫班小姐的内心告诉她,要一直在路上、始终享受自由。
 电影《莫班小姐》海报,1967
电影《莫班小姐》海报,1967与德·阿尔贝共度春宵后,莫班小姐穿着同一件戏服拜访了萝赛特,并向她亮出了真实身份。小说中假意略去莫班小姐与萝赛特的独处细节,通过杂乱的床铺和仆人的话语暗示读者两人发生的关系。一夜过去,莫班小姐已经不见踪影。她脱去戏装,再次换上骑装,开启新的旅途。此时身着骑装的她已不同于往日,因为在切身体会了和不同性别的两人的亲密关系后,她迎来了对两性的新认知。通过和德·阿尔贝的欢爱,她已经解开了异性恋结合的快乐奥秘,肉体不再因无法满足而躁动;也因为和萝赛特度过的一夜,莫班小姐终于可以回应女性细腻的爱,不再为两人之间柏拉图式的爱感到遗憾。在灵与肉同时得到满足后,莫班小姐与自己和解了。她选择摒弃两性冲突,化为两性共存,用自己“女人的灵魂和肉体,男人的气质和力量”面对生活,用自由开放的态度创造接下来的人生。
 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
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莫班小姐是一位“叛逆”的女性。她不认可时代和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选择用女扮男装的方式弄清闺阁之外的生活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名淑女,她拥有超乎常人的决心、毅力和勇气,与当时环境教导女性应该拥有的柔弱气质毫不相符。她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对自我意识的关注以及对自由的坚定向往都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从裙装到骑装,她选择用行动挣脱社会的枷锁,用实践探索内心真正的渴求。然而,与两位情人的交往让她对自己产生了质疑。对灵与肉冲突的纠结导致她无法从精神和肉体的二元世界中解脱,从而短暂地迷失了探索的方向。幸運的是,从骑装到戏装,莫班小姐抛下生活中示人的男性装扮,尝试在雌雄难辨、虚实并存的演出过程中审视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和解,最终超越了性别身份的限制,明白了生而为人的意义—自由。她也用行动实践了这一理想,即继续出发、不断开拓。
作为唯美主义先驱,戈蒂埃在序文中凝练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又在莫班小姐的故事中反复论证。小说的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与序言中的思想主张密切相关。作者在序言中大力抨击的伪善者,可以在小说中外表光鲜、内心龌龊的骑士身上找到对应。同样,德·阿尔贝可以被看作戈蒂埃的代言人,小说中诗人对完美情人的向往隐喻作者对美的追求。作者借德·阿尔贝之口表明,莫班小姐雌雄同体的状态所呈现的美是高于男女二者本身的,只有男女结合才能尽善尽“美”,因为它们在融合过程中达到更高的境界。然而,故事以莫班小姐的再次出走为结局,是否意味着作者也认为“绝对的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作者希望借此启示,“美”是无止境的,需要人类的不断探索和追求。
尽管小说大篇幅地描写了德·阿尔贝的内心世界,但落脚点仍是书名中的莫班小姐。她身上的一切都与她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这似乎也象征着作者注定不被当时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美学观点。闺阁中的条条框框和束缚女性身体的传统裙装就像社会现实为戈蒂埃套上的枷锁,而莫班小姐打破规则、大胆出走的行为正是戈蒂埃对同时代作家只求功利的辛辣讽刺和自己跳出局限的决心。莫班小姐认清自我后对自由的坚定追求又体现了作者反对文学受现实生活限制、坚持艺术至上、美学自由的执着。在不断变更服饰、不懈探索自我、坚定追求自由的莫班小姐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位倔强艺术家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