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这些陪媪或女傅常是些严苛古板、易发怒的动物,比继母还更让人畏惧。
——《滑稽小说》第一卷第二十二回
《滑稽小说》是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保罗·斯卡龙(1610-1660)唯一的小说作品,与索雷尔的《费朗西荣的滑稽故事》、菲勒蒂埃的《市民小说》及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一起被法国学界誉为“十七世纪四大小说”,描述了一个剧团在勒芒巡演时遇到的一连串滑稽事儿,并插入了数个改编自西班牙作家的情爱故事。身兼诗人与戏剧家身份的斯卡龙,极尽戏仿与嘲讽之能事,以勒芒这座外省小城为舞台,贬低高贵思想与伟大精神,讥讽古代英雄人物,挖苦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嘲弄身边人物及其所处社会环境,这其中被嘲讽得最彻底的、最荒唐可笑的,则是作者自己。
斯卡龙出生于法国的长袍贵族之家,父亲是旧制度下巴黎高等法院的推事(议会议员),母亲是布列塔尼议会议员之女。二人婚后产下八子,斯卡龙是其中第七个,而这八子之中,只有三个存活下来。继姐弟陆续夭折后,年仅三岁的斯卡龙丧母,其父独自抚养孩子数年,后逐渐感到厌倦,不堪忍受鳏夫生活的他,遂于一六一七年与弗朗索瓦兹·德·普莱再婚,与之生下四个孩子,有三个活了下来。
普莱虽出身外省的贵族之家,却嗜赌成性,频繁出入赌场,随着她所输钱财越来越多,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人也越来越吝啬。像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里的主子们一样吝啬,她甚至将糖罐口改得越来越小。之后,她又多次向债务人放高利贷,并因此获罪。为了将家产尽数留给自己的孩子,普莱想方设法地谋夺家产,还动不动便责罚原配所生的孩子。年幼的斯卡龙遭了鞭打却不肯屈服,反而对继母加以讥讽,甚至还顶撞他的父亲。被激怒的父亲,决定遂其继母的心愿,将他“流放”到外省亲戚家中。一别数年,斯卡龙再次回到家中时,变得更具反抗意识了。而这次,父亲和继母为了摆脱他,将他送去了寄宿学校。不服从管教的斯卡龙,一面嘲弄教授拉丁语的夫子们的迂腐与笨拙,一面与同学们一起偷看情色小说,对卖弄学问充满了厌恶(埃米尔·马涅《斯卡龙和他的圈子》)。
斯卡龙对人世的嘲讽态度,自他幼年时期便这样形成了。十九岁时,斯卡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便被送去教会,穿上教袍。怎么都不像个教士的他,丝毫不愿践行严苛的教义与戒律,后来他还在《滑稽小说》第一卷第一回里言道,球场女主人的慷慨,是因“她对戏剧的热爱远胜于对教堂的讲道与晚课”;在第二卷第二回中,斯卡龙将蹩脚剧本与教士布道相提并论,农民见到拉戈旦“如痴如癫地夸张朗诵,以为他在宣讲神谕”。面对父亲的冷淡与继母的责骂,斯卡龙总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甚至还在继母去世后,为她写了篇《因便秘去世的太太的墓志铭》来嘲讽她的吝啬:
长眠于此之人,那么好索取
那么会索取
寧可去死,也不愿交还
她吞下的泻药
 保罗·斯卡龙(1610-1660)
保罗·斯卡龙(1610-1660)二
这些短故事,比那些充斥着过分谦逊守礼的君子、多多少少有些不合时宜的想象中的古代英雄人物事迹,更贴近我们的习俗,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滑稽小说》第一卷第二十一回
小说这一体裁之所以能够在法国文坛长期占据首要地位,不仅是因其自由性、多元性、创新性,更在于它的容纳、求异、反抗,甚至是反英雄、反传统、反小说的。《滑稽小说》便是这样一部拒绝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试图将现实生活搬进虚构故事,并力求贴近读者与现实的戏剧式小说。
在斯卡龙的时代,写作并不是崇高而又宏伟的志向,在贵族式的或宫廷式的奢华迷幻里,鲜有人会说:“我要成为作家。”熟稔西班牙语的他,阅读了大量西班牙小说、故事、诗文,尤其是塞万提斯、克维多、玛利亚·德·萨亚丝、卡斯蒂略·索洛萨诺、马特奥·阿莱曼等人的作品,然后将之化为己有,汲取、翻译、改编、创作,一点点地拾掇起来,精雕细琢,形成自己的滑稽讽刺之国,供人在茶余饭后闲话。据魁北克大学苏菲·皮隆教授考证,《滑稽小说》还受到了十六世纪西班牙作家维兰德兰多的《有趣的旅行》的影响。对斯卡龙而言,西班牙讽刺小说中的反讽,是他反抗同时期以玛德琳·德·斯居德里的长篇累牍高达二百一十万字的《阿勒塔梅讷或伟大的西吕斯》及贡贝维尔的过分夸张的《博莱克桑德》为代表的英雄小说的一种手段。
因文中大量的对现实人物、地点、事件的改写,斯卡龙的这本《滑稽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影射小说的影子。这种将身边人物搬进作品里充当角色的做法,颇受读者偏爱,不少同时期作家都曾采用过。针对读者的种种猜测,历史学家亨利·查登(1834-1906)详细考察了《滑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之间的关联,并出版了《无名的斯卡龙及〈滑稽小说〉中的人物类型》一书。
自一六五一年第一卷《滑稽小说》首次印刷(第二卷于1657年出版)至今,已有数十个版本的《滑稽小说》陆续出版,其中不乏部分改编、续写本。一七三七年由意大利演员们在巴黎勃艮第府剧团上演此剧,一七七五年起,《滑稽小说》被爱尔兰诗人兼作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翻译成英文,后又被陆续翻译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一九九三年,日本翻译家渡边明正将其翻译成日语—《滑稽旅役者物语》。二十世纪,包括加尼耶经典文丛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含七星文库版)、弗拉马利翁出版社、法国美文出版社等在内的多家著名出版社纷纷推出不同版本的《滑稽小说》。此外,历代法国文人学者对其反复分析、研究、评注,评论性专著达数百本,被法国文学界誉为必读古典作品之一。目前国内尚无《滑稽小说》的中译本,更无对这种写作风格的系统研究。
三
拉戈旦夹紧双腿,马尥起蹶子,拉戈旦沿着因重力自然形成的斜坡下滑,坐到了马脖子上……不幸的人被马鞍前桥夹住了腚。
——《滑稽小说》第一卷第十九回
滑稽讽刺并不单是戏仿。让·勒克莱在他的《改编成滑稽体的古代文化及法国滑稽讽刺浪潮(1643-1661)》一书中指出:“在文学批评领域,它首先被视作一种文体,更广泛来说,是一种审美,其特点是活泼且不受拘束,采用了类似闹剧、不协调等特征的滑稽手法,并汲取了十六世纪意大利滑稽诗作的经验,发展至今,滑稽讽刺这个字眼,已具有了跨历史的特征,包含了所有具有夸张、怪诞等滑稽特征的艺术形式,这类滑稽,有时甚至有些粗俗的,涵盖了自拉伯雷的文学作品至二十世纪初的默声电影作品。”滑稽讽刺风格于十七世纪初在法国兴起,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其写作方式与投石党之乱紧密相连。在当时,“几乎整个民族都以最滑稽可笑的笑话、最怪诞不经的想法和表达作为自己的乐趣”(保罗·莫利洛语),从萨拉赞、圣阿茫到斯卡龙,滑稽讽刺写作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样式。一六三○年至一六五○年前后,为滑稽讽刺写作的蓬勃发展阶段。这种滑稽讽刺风格与滑稽写作十分相近,两者都转向非英雄式的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主人公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小贵族阶级或没落的绅士们。这两种体裁,都是对传统英雄传奇作品的反抗,拒绝如骑士文学那般的理想主义。然而,严格意义上的法国滑稽讽刺文学,却随着斯卡龙的去世,路易十四中央集权的加剧,逐渐走向没落。

滑稽讽刺风格,既是对英雄体裁的改写,也是十七世纪关于崇古与崇今的争论,即“古今之争”的体现。如何写小说?哪些材料值得推崇,哪些内容又不值得一提?《滑稽小说》是斯卡龙的一次大胆尝试,与同时期的大部分作品相比,算是个“异类”,是对正统与经典的篡改。热拉尔·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二度文学》中指出,滑稽讽刺的篡改是通过搬移诗句、将风格通俗化、添加夸大的描写、添入过时旧物、对主题进行滑稽模仿等实现的。滑稽讽刺反對古典主义将古风、古式当成范本的做法,遂在其作品中对其加以嘲讽。作为滑稽讽刺风格的领军人物,保罗·斯卡龙在惹人发笑的同时,嘲讽人间百态、讥笑世间万物,包括作者自己。斯卡龙的《滑稽小说》是搞笑的、讽刺的,代表着一种融合了喜剧、怪诞、浪漫与现实等不同风格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形式可追溯至讲述处于社会底层的下等流浪汉们的冒险故事的西班牙流浪汉文学(如《托美斯河上的小癞子:他的身世和遭遇》《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生平》《混蛋传》[又译《骗子外传》]等),从功能上来说,两者存在着共同之处:一方面都是为了引人发笑或娱乐大众,另一方面,则是归纳启迪或批评警醒。我们须辨析“滑稽讽刺”是如何成为滑稽写作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斯卡龙又怎样从全新的角度赋予戏剧主题以中心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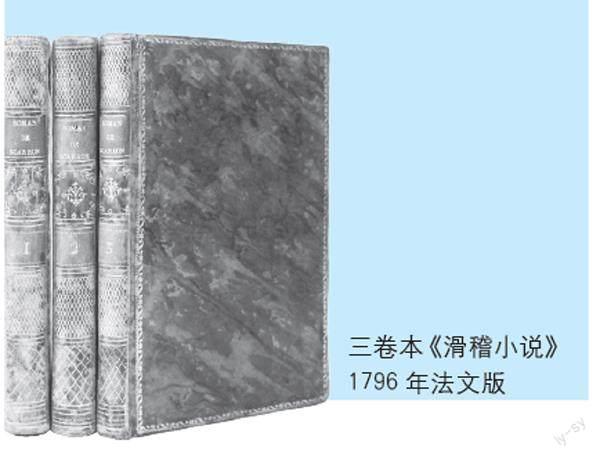
与几乎全无高雅可言的流浪汉文学不同的是,滑稽讽刺风格的主人公多是失去社会地位或被降低等级的人物,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意味着来自社会下层、底层,人物的出身也并不是最低贱的,甚至有可能是高贵的,且小说人物还承载着社会道德层面的意义。滑稽讽刺体裁的小说是活泼的,也是混乱不堪、错综复杂的,充满了笑料与荒谬怪诞。滑稽讽刺小说的作者常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情节、玩笑,或粗俗的表达来引读者发笑。此外还借助戏剧元素以便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故而,“滑稽讽刺比滑稽更为‘大胆,因为滑稽只笑那些令人觉得好笑的,而滑稽讽刺则决心嘲笑一切,尤其是那些严肃之事”(保罗·莫利洛语)。
四
拉戈旦被蜜蜂蛰得,从头到脚都肿胀起来。就他眼下这副模样,一个新出生的、尚未接受母亲舔舐的小熊崽的熊样也比他此刻的人样更有样。
——《滑稽小说》第二卷第十六回
让·塞鲁瓦在其编撰的《滑稽小说》序言中指出,“斯卡龙的人生像一部小说,而他的小说又像极了他的一生”。十七世纪的文学传统便是将故事虚构视作“一层以事实为材料编织的或薄或厚的纱,所有怀揣好奇心的读者都可以轻轻掀起其一角”。《滑稽小说》讲述的是普通人的平凡故事,却又是怪诞不经的荒诞故事。因过于离奇,我们怀疑它的真实性,又因过于真实,我们怀疑它便是作者本身所经历的实事。
《滑稽小说》常借助讽刺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第一卷第四回中,像上流社会女子一样热衷于设宴款客的拉皮尼尔勒太太,又瘦又干巴,虽不算丑,可是她“干巴得太狠了,每次剪烛花的时候,她那枯瘦的手指,能让火给点着了”。同一回中,写拉皮尼尔勒的疑心病,半夜醒来见屋里没人,他发怒、愤怒而起,错将母山羊当成他老婆并以为自己捉到了红杏出墙的妻子。这是有别于闹剧的滑稽,也是小说的第一个小高潮。《滑稽小说》还常通过设置悬念、营造反差(包括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滑稽突梯”,钱锺书语)、机械性反复、“掉书袋”、“用典”、反讽、暗示、隐喻等手段来“引人发笑”,用“不合规矩的”语言,讲述或真实或虚构的不合常理之事。
《滑稽小说》的写作形式甚至受到了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关注,在整部作品中,作者与读者之间始终保有一种密切联系,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种趣味性契约。文中多层次的叙述和陈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强烈的互文性,使得文本像一张稠密的织物,这也导致虽然小说主题是大众的,其读者却更可能是一些知识阶层,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阅读量。《滑稽小说》也会被当成“反小说”,一本嘲笑、讽刺小说的小说。另外,叙述者对文本的干预、僭越、对故事情节及风格的评论,俯拾皆是。这种叙述本是为了体现故事的真实性,却给人造成一种刻意、人为的感觉,也就形成了某种悖论。论及其新颖之处,还不能不谈及它的叙事结构、叙事形式。《滑稽小说》中纵横交错、首尾相连的叙事结构,多层立体的叙事视野,不断变化的叙述者,被拉伸、延长的叙事时间,不断被打乱的叙事线,让整个叙事在不同的时空里自由穿梭,可谓是一种新的滑稽叙事,比之前许多滑稽故事更为复杂多样。其整个构造十分复杂,表面看上去虽杂乱无章,却是在无序中建立秩序,在小说中谈论对小说的反思。叙事者并不总是处于全知全能的视角,除了第三人称叙述外,不同人物角色以第一人称进行的回顾性叙述,且贯穿全文的叙述者不时地会用第一人称直接与读者讨论,主叙事与回顾性叙事反复交叉、叙事主体不断变化,使得故事套故事,回忆连回忆,让人不禁怀疑小说的结构是无止境的,照着此法,怕是可以永远循环地写下去。
《滑稽小说》构思巧妙,循环嵌套,叙事中夹着叙事,过去中连着过去,时间仿佛是可以无限拉伸的。这种对叙事时间的探索,就像毕飞宇在《推拿》里刻画的那个九岁盲童小马发现时间的真相的过程。历经四年煎熬,他终于在十三岁的时候,认识到时间既不是圆形,也不是三角形,更不是封闭的。时间拥有无限的可能,有形而又无形,甚至是无我、无时间本身。我们的小说叙事呢?何尝不是存在着无限可能呢。然而,梳理《滑稽小说》中的层层人物关系时,会让人觉得叙事线条不够清晰,故事结构又错综复杂,这种繁杂,与巴洛克风格的繁复,不无关联。冗长的句式,大部分章节几乎都没有分段,人物对话没有标点,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全要靠读者自行辨认,有的章节甚至连句号都没有几个,或新颖或古风的诙谐词句,大段大段似是无关的插入故事,多处早早就埋下的伏笔后来却没有明确交代,不断被打断的叙事线,不停变化的叙事者—“我”(不由得让人想起北岛的《波动》),中断的故事很久之后才又重新“拼接”上,“无序的结构”像生活本身那样“杂乱无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绝对主角或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主人公,有些人物的出现、出身,似乎并没有详细的交代,有的甚至是来无影去无踪一样,无从谈起,无从知晓,仿佛只为了做这戏剧舞台的一角装饰;有的人物,虽是倾注了不少笔墨,甚至可以说是小说的主人公(如“天命”和“拉戈旦”),却也像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写到的长妈妈一样,终是“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
以上种种,无一不在考验着当代读者的耐心。这种复杂性与非连贯性,很难让读者能够像读一般的通俗读物那样“顺畅”或“赏心悦目”地完成阅读过程。虽然《滑稽小说》中有很多笑话,可其中的笑话与“包袱”,都是作者的“别有用心”,若非对当时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及作者的生活交际圈子有一定的了解,很难能够察觉出作者的意图及其暗含的种种影射。故而,这并非一本易读的作品,可能会让许多读者对之望而却步。它要求读者真正地进入到作品中去,甚至是参与到其中,与之对话、辩论。这些特征,赋予了本书现代性意识,无论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得之,对这些问题产生好奇心,对作品的发生过程存有疑惑,对其结构与特点的探究,乃至想为这本未完成之作,续个结局,做个交代,正是它得以成为“经典”的原因。
 《滑稽小說》插图
《滑稽小說》插图五
众所周知,我已放弃上流社会的万般虚妄很久了。
——《滑稽小说》第一卷第二回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小说里的“我”,一直是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自一九七七年法国作家兼评论家朱利安·塞尔日·杜布罗维斯基以“自我虚构”来定义他的小说《儿子》以来,叙事学中对“我”的研究层出不穷。而《滑稽小说》里不断变化的“我”,不仅仅是作者、叙述者、主人公三重身份,还是不断变化的小说人物,他赋予了那些并非英雄主角的小人物叙述的权利,让他们来讲述自己的过去、遭遇。层层嵌套的叙事,就像他坐在这些人物的中央,聆听他人的同时,又向他人分享自己的人生。这种叙事,十分具有现场感、戏剧感。其中穿插的各种口语化的表述,让读者仿佛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穿越回十七世纪,像个隐形人一样,观察一幅幅友人间的对话场景,似若置身于薄伽丘的《十日谈》之中。
斯卡龙写作《滑稽小说》的时候,正值不惑之年。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也许还只是年富力强的壮年,本应是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人生景象,可对于这个小个子男人来说,他已经患病太久,卧榻近十年了,能不能活到五十岁,都还是个未知数。从一六三八年的那次风湿病开始,他就卧床不起,后来虽有过好转,一六四一年却又再次恶化,之后一日不如一日。下半身逐渐瘫痪的他,在一六四八年的一封《致读者书》中写道:“我的身材矮小,身子瘦骨嶙峋的。发量不少,用不着戴假发,只是生了许多白发。我的视力还好,但头总耷拉着,使得这一侧的眼睛凹陷得厉害。我以前的牙齿很齐整,跟珍珠似的,如今却都成了黄色,以后怕会是深灰色。眼下,左边的牙掉了一个半,右边的掉了两个半,还有两颗被蛀蚀了。我的小腿和大腿之间,起先是个钝角,后来变成了直角,最后成了锐角,我的大腿和我的上半身之间也有这样一个角,让我整个人看上去颇似Z字形。我的手臂和腿都萎缩了,手指也是。”
斯卡龙的这幅自画像,写成于《滑稽小说》出版之前。评论家让·塞鲁瓦在他的《小说与现实:17世纪的滑稽故事》中提到,卧病在床的斯卡龙,回首往事时才发觉,一六三三年至一六四○年间在外省小城勒芒度过的八年时光,许是他这一生最快乐的。是以,他在《滑稽小说》里描绘的外省景象,虽是滑稽可笑,却也活泼喜人。而他生命最后的时间里,随着病情加重,他的痛苦、身体的疼痛、生活的窘迫,也都更多地流露在他的诗作里。他的一生虽不至贫困潦倒,却时时拮据,乃至在他死后,他的遗孀还埋怨他欠下了许多债务。
他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娶了一位聪明伶俐、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这个女孩是亨利四世之友、巴洛克诗人兼作家阿格里帕·德·奥比涅的孙女,自小在美洲长大。在修道院与半身残疾的斯卡龙之间,女孩选择了后者。婚后的生活,虽满足了她举办沙龙、结交名流的欲望,但要日日面对这样一个被人嘲笑说施见面礼时都要借助滑轮来拉动帽子的斯卡龙,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是悲是喜,通过她在斯卡龙死后,决定烧了这位滑稽作家的遗稿之举来看,读者是能大致品出个中滋味的。斯卡龙去世若干年后,拉封丹将《滑稽小说》改编为剧本,十九世纪作家卡蒂勒·孟戴斯以斯卡龙为原型,创作了悲喜剧《斯卡龙》。他的遗孀,斯卡龙太太,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小姐,嫁给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后被封为曼特农夫人。剧作家拉辛,因在法王面前谈及斯卡龙而遭到放逐,终身不再得召见。自此,在王宫里,滑稽讽刺作家斯卡龙似是成了个禁忌,整个十七世纪下半叶,几乎都没人再提起他的作品,这种现象持续至路易十四去世,十八世纪来临,才得以终结。
斯卡龙在临终前作了不少与相对活泼的《滑稽小说》的风格甚是迥异的抒情诗,其中差异最为显著的,则要数他的墓志铭。该文情真意切,一曲凄凉,令人扼腕,堪称绝笔之作。
而今长眠于此之人
让人生怜却非艳羡
遭尽万般死亡苦痛
生命才算最终逝去
路人,切莫弄出声响
留心别把他吵醒了
这是可怜的斯卡龙
初次得以入眠之夜
——斯卡龙先生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