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蕾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1907-1964) 的《寂静的春天》,在世界生态文学史上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蕾切尔·卡森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乡村小镇,在母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就对自然有着热爱。一九五一年出版《我们身边的海》,介绍了从海洋的起源到它的形态,从海洋中的生命到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一九六二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在这本书中,她以非虚构的形式,叙述了人类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和环境污染,各种野生动物、植物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严重破坏生态平衡,最终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生存危机。该书出版后,引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不幸的是,卡森因病于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去世。从一九七九年起,国内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介绍《寂静的春天》,并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部作品在自然万物的相互联系中,表现出鲜明的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它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环保运动,而且为人类认识自身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一直是相互纠缠作用于人类的,人类对每一种关系的理解导致的观念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人类整体的发展。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于人类的历史变化进程中的。在远古时期,人们都相信“万物是有灵的”,人与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因此,他们与自然和睦相处并且崇拜自然,原始人类对自然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浪漫主义的作家。郭沫若在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与歌德思想共鸣的其中两点就是对原始生活的敬仰和对自然的赞美,认为:“他肯定自然,他以自然为慈母,以自然为友朋,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傅。”“他亲爱自然,崇拜自然,自然与之以无穷的爱抚,无穷的慰安,无穷的启迪,无穷的滋养,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阶级制度,反抗既成宗教。”(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对于西方浪漫主义者而言,普遍地具有皈依自然、亲近自然,反抗工业文明、社会现实的倾向,自然是他们生命情感或者灵魂的归宿,由于他们生命、情感的存在,“自然”才有了意义。换句话说,人在自然中仍然是“中心”,正如爱默生所说“世界就是这样相对于人的灵魂而存在,为的是满足人对美的爱好”(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到了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则不再从“人类中心”的立场来理解和认识自然,而是以生态主义整体价值观来认识和理解世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一种理解世界方式的转变,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无限度利用带来的生态危机导致的结果,这部作品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也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密切相关。究其本质而言,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是人类为了生存世界的永续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
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谓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就是把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众生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来看待,人只是这个系统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征服或主宰自然万物的一种力量,自然界的每一个物种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其存在意义是相同的,其价值是以生态整体平衡为依托而显现的。这种价值观不同于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它强调万物众生之间的联系,人不是万物的“核心”,而是生态链中的一环,相互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彼此共生共存。生态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遭遇破坏,都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最终对人类造成伤害。这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理解有不同的内涵及深刻的差异,但由于“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联系,人们在思考这种关系时都会注意到两者的内在关联。十九世纪的爱默生对美国文化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自然观的整体倾向虽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但也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他认为:“自然对人的助益不仅在于它的原料,而且在于它的过程和结果。自然的所有部分持续不断地相互合作,为人带来福利。风播撒着种子,太阳蒸发着海水,风又把蒸发的水汽吹向田野;在地球的另一边,冰又把这水汽凝集成雨;雨水滋养着植物,植物供养着动物;如此形成了自然以神圣的施舍养育人的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梭罗则在《瓦尔登湖》中诗意地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寂静的春天》同样描述了万物共生共荣、彼邻和谐相处的景象:“美国中部曾有一座小镇,一眼望去,镇上所有生命都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生。小镇周围是一大片繁茂的农场,阡陌分明,宛若棋盘,田地里庄稼茂盛,山坡上果木成林。每到春季,怒放的白色花朵覆盖着青翠的原野,如流云一般摇曳生姿;秋日里,橡树、枫树和桦树的斑斓亮色透出茂密的松林,如火光一样灿烂。那时常有狐狸在山间嗥叫,野鹿半隐在秋季的晨雾中,静悄悄地穿过田野。”这种万物共生共荣的思想观念,使他们对破坏生态平衡的各种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追求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自然生命的价值。卡森在与爱默生、梭罗等人的联系中确立的这种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是《寂静的春天》富有震撼力的思想。用理论的语言表述,就是现代生态哲学在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联系与思考中,逐渐建构起“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主义价值观,确立了“普遍共生”的原则。《寂静的春天》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认为:“控制自然是一句极端自大的宣言,它源于远古时代原始的生物学和哲学观念,当时的人类認为大自然本来就应该为自己服务。”(《寂静的春天》,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实在是人类自身的不幸,由此,《寂静的春天》对人类控制自然、破坏生态整体联系的种种行为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描述,其包含的批判性和深刻反思精神引发了人类对“生态危机”的高度重视。

《寂静的春天》中写到的那个诗意盎然的小镇,后来有一种令万物凋萎的疫病突然而来,改变了一切,整个小镇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陷入一片怪异的死寂。这是美国无数小镇中的一个,是什么扼杀了美国无数小镇的春日之声?卡森这撕心裂肺的呐喊指向了人类对自然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失衡和生态危机。在卡森看来,地球的生命史就是一部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动植物的形态与习性,而从地球漫长的岁月来看,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微不足道。只有在人类出现之后,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才终于有一个物种掌握了改变自然的伟力。掌握了改造自然力量的现代人,轻率而鲁莽地打乱了自然演变的节奏。大量实验室合成化学物品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消灭了被现代人称为“害虫”的生物,另一方面这些化学物品乃至有毒物质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污染、生物组织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和致命后果,这些化学物品不仅污染了土地、伤害到土壤中的生物,而且污染了水资源、造成人类饮用水的危机和各种与水有关的生物的灭亡。除草剂的滥用和土地的污染又祸及地球的绿色植被,大量依赖植被生存的动物消失不见,鸟鸣听不到了,天空降下了死亡之雨,这个世界蒙受污染的渠道多种多样,不折不扣是一个“毒物时代”。人类原想把“自然”改造得称心如意,却事与愿违,不仅自身殃及其中,出现了一些恶性疾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遭到了自然的报复,许多昆虫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产生了抗药性。因此,卡森说:“以杀虫剂等化学武器防控昆虫的行为恰恰说明我们对自然缺乏了解,引导自然进程的能力尚有不足,只能无谓地诉诸蛮力。人类应当常怀谦卑之心,面对大自然,技术至上的狂妄心态没有丝毫容身之地。”(《寂静的春天》)原本是正向循环的自然生态系统,由于人类野蛮加入的改造力量,带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反向循环,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事实证明,人类面对大自然常怀谦卑之心,尊重大自然的生态发展规律才是人间正道。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提出:“为了实现与其他生物的和谐共处,人類想出了无数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新方法,它们的背后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我们必须时刻铭记自己正在与鲜活的生命打交道—它们有一定的种群数量,在压力和反作用力的作用下会出现兴衰消长的变化。只有充分认识到生命本身的力量,并小心地将其引导到对人类有利的方向,我们才能实现昆虫与人类的和解与共处。”(《寂静的春天》)在这里,蕾切尔·卡森意识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人类面对自然生态系统不应狂妄自大,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建构一种新的生命伦理。正如施韦泽在《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所认为的那样,只涉及人的伦理是不完整的,要对人及所有生物的生命都给予关爱、同情和帮助,这才是敬畏生命、对所有生命行善的“尊重生命的伦理”。这种扩展人的道德边界,跨越种群的界限,把万物生命看作是自己同类的新的生命伦理,也是《寂静的春天》在反思人类粗暴干预自然的过程中所思考的问题,因此,卡森赞同昆虫学家乌里耶特的话—“我们有必要调整自己的哲学观念,摒弃身为人类的优越感。”(《寂静的春天》)
与这种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和新的生命伦理相对应的是《寂静的春天》在整体中重视万物之间的关联性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首先,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自然万物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因此,《寂静的春天》在叙述结构上也是一个整体的“关系网”,部分与部分之间都是在现实因果关系的逻辑中展开。人类为了控制自然,滥用化学物品、杀虫剂、除草剂等去消灭害虫,化学物品污染了水源,水里的生物死亡;污染了土壤和绿色植被,土地上的动物也难逃厄运。土地上的水蒸发形成有毒的雨水落到地面,又造成对生态整体系统的破坏。这种整体的关联性结构说明了对于大自然中任何物种的伤害都会影响到生态整体的平衡,所以,《寂静的春天》关心着每一种生物的命运,严厉质问:“是谁做出了决定,让这些毒物链开始启动,让死亡的波浪层层延展开来,就像鹅卵石在澄净的湖面上激起了一圈圈涟漪?……而对这千百万民众而言,生物各从其类的天然世界仍然有着深邃而不可或缺的意义。”在整体中关注事物的关联性意义,就是要求在生态系统中认识每一种物种的价值,重视生态系统中万物众生的自然性价值,这也是生态文学应有的审美性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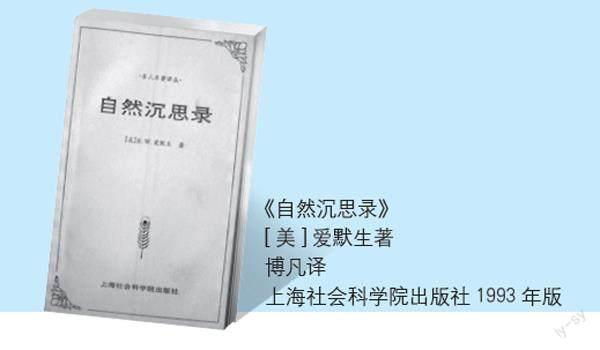
其次,与这种叙述结构的整体性和关注事物的关联性相关,《寂静的春天》作为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作品有所区别,它不再以“人”为中心展开叙述,而是表现自然世界万物众生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两者的区别,王诺在比较爱默生和梭罗时说得特别清楚,同样是关照自然:“爱默生说:‘从那些宁静的景色当中,特别是在眺望遥远的地平线时,人可以看到与他自己的本性同样美丽的东西。梭罗却说:‘在这裸露和被雨水冲刷得褪了色的大地上,我认识了我的朋友和‘我们伟大的祖母。他要观察和认识的就是这伟大祖母本身以及她所有的子孙—所有动植物兄弟姐妹。显然,梭罗强调的是整个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孩子,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平等的兄弟关系。”(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爱默生在自然中看到的仍然是“人”,梭罗看到的是与人相关、但却是独立于人之外的那个“存在”。《寂静的春天》所叙述的就是那个万物众生的“存在”,她在生态的意义上关心着鸟、鱼、兔子、浣熊、负鼠、蚯蚓、昆虫以及草、树、花等各种生物的命运,她也关心人,但“人”不是叙述的中心,人与虫鸟草木的叙述意义是同等的。在这里她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自然界的神奇与美丽,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人利用技术控制自然带来的生态危机以及对于人自身的伤害。异域的经验也在昭示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要重蹈覆辙,尊重生态规律,维护“生命共同体”中生命彼此交融的正向发展是人类理应承担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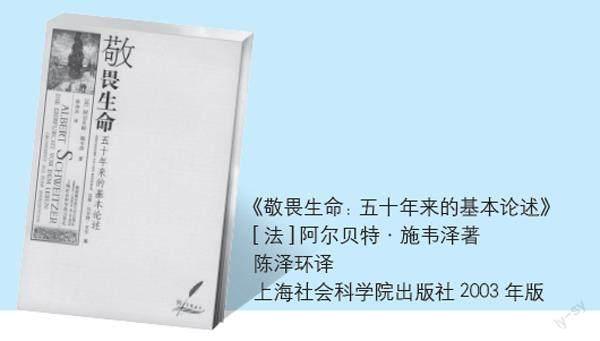

《寂静的春天》在第一章“明日寓言”中写到了那个美国小镇陷入了一片怪异的死寂。“鸟儿怎么都不来了?人们谈起这件事都觉得困惑不安。后院给鸟儿喂食的地方冷冷清清,就算零星看到几只小鸟,也都奄奄一息,浑身痉挛,再也无法飞翔。这是一个静默无声的春天。从前那些日子,小镇的黎明回荡着知更鸟、猫鹊、鸽子、松鸦、鹪鹩的大合唱和其他鸟儿的和声,可如今再也没有鸣禽百啭,山野林泽间只余一片寂静。”为什么会这样?请读一下《寂静的春天》,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愿人类不再有“寂静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