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大家的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可谓是得享高龄。但回顾他的生命史,却不由震撼于他的知识与思想创造成就,不仅是那些标志性的文学批评名著,就像这部《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Un long Samedi: George Steiner avec Laure Adler)虽貌似一部小书,但也让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大学者的风骨和风范,实在是当得“大家小书”之誉。即便是在谈话之中,一代大家是可以有着怎样的“举重若轻”的潇洒姿态,真有些“谈笑间,知海学山了然胸中”。斯坦纳身份颇为特殊,虽然生于巴黎,但籍贯却是维也纳,而族裔则是犹太人,日后求学牛津、哈佛,如此德、法、英语皆擅长,更是难得的贯通型学人。虽然他更多以文学批评家、翻译理论家之类而名世,但其卓识通达,可谓一代大学者。读他的作品,时时仿佛有灵光迸现,能受到思想的刺激,这种阅读感受并不多见。他的作品中既有深度的个案研究如《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丁·海德格尔》等,也有宏观性的如《悲剧之死》《何谓比较文学》等,可谓是“入得深海”“进得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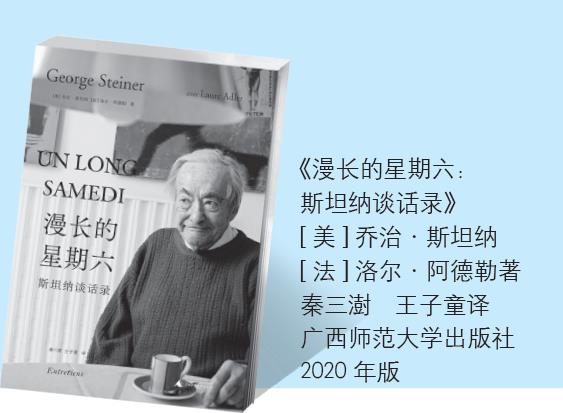
斯坦纳会非常坦率地说:“我完全缺乏伟大创造者的天真与愚蠢。”在他看来:“伟大创造者那纯真的神秘是非常深奥的,作为局外人我们并不能理解。”(《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秦三澍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这里非常有趣的是,他实际上概括了“伟大创造者”的三个特征,即天真、愚蠢、神秘;同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局外人”与“创造者”。即“伟大创造者”有其自身独特的创造语境和境界,这是不身在其中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所谓“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如此坦陈自身个性缺失的态度(无论其是否有自谦成分),充分表明了一个大学者的可贵,即谦逊之美德。真正的学者,即便不是费希特所高标的“人类的教养员”,能够“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甚至高端目标当为“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商務印书馆1994年),但也至少应当是知学知耻、守义不辱,能够在知海无涯中感到自己的渺小,而不断地省思、不懈地求知、不屈地循道,在推进学术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境界、人品与格局。
斯坦纳当然也意识到时代退步的大浪,他说:“在我们的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冗词中找到借口。”(《逃离言词》,1961)显然,他对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和政治语境的孽根性是有深刻认知的,所以他会求助于艺术和知识的审美之维,在他眼里:“阿波罗的竖琴是理性和谐的乐器……是彻底人性化的、受神启的乐器。”(《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这里,通过神授的乐器将艺术、理性、和谐恰到好处地调节于一处,很有妙手天成的那种水到渠成感。
 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
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斯坦纳给自己的定位当然还是一个学者、批评家,但他的判断却是:“创作者和评论者(或者解读者)之间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算的。”(《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如此自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正是一种“知学”与“知辱”的表现,也体现出一个求知者和寻道者的阔大胸怀。实际上也未必就完全是如此,创作者中也有境界较低的,阐释者中也有伟大人物,彼此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真正高明的阐释者也可能成为创造者。但恰是这种胸襟和气魄,使得他见地不凡、格局自高,所以他才能认识到:“没人能拿走我们牢记于心的东西。它和你在一起,它生长,它变化。你自高中时代背诵的伟大文本与你一道改变,随着你的年龄、所处的环境而改变,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同上)这个关于“伟大文本”的论述是饶有意味的,因为它是作为创造性阐释者的学人斯坦纳的亲历体会之言,是具有自立底色意义的“定海神针”之语,颇有“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气象和气魄在,所以他会这样说:“伟大的文本可以等待几个世纪。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在那篇出色的文章中说的:‘不必心急,一首伟大的诗可以忍耐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书籍终究会到来,处于危险中的不是书,而是读者。伟大的文学文本包含着再生的可能、不断追问的可能,但它并不会在那儿静静等着成为大学研讨会的材料,或一份被解构的文件。那是本末倒置。”(同上)这里进一步给“伟大文本”赋值,让其具备永生常存的意义。这也是他作为伟大阐释者的价值所在,他告诉后来人一种获致精神不朽的捷径所在,即自铸伟作、留待青史。所谓“后世相逢或有知”,正是对于那些精神史伟大人物和作品的最佳酬报,不是那种汲汲于现世的功利奖赏,更不是被劣质化的帽子头衔。真正的智者从来不会忧虑自己的俗世价值,伟大的文本同样不会畏惧失传,因为“伟大自然会有人懂”,只不过不必期之于朝市之间,正所谓“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

更为撼人心魄的,是斯坦纳的这个判断,他说:“真理不一定在欧洲。它会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这个判断极有意味,无论是“真理”还是“道”或“梵”,那种至高无上的体现宇宙根本规律的东西是存在的,但一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群人甚至某个地域文化体所独控的。斯坦纳非常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尤其超越了黑格尔那种“天降大任于我族”的片面的执念与狂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不仅超越自身,也真心地钦佩异族文化的伟大:“我相信印度的奇迹,因为印度具有梦幻般的创造敏感度,有着发明的力量和极致的原创性。”(同上)欧洲的贤哲们不乏对东方,尤其是亚洲的推崇,印度更是他们的精神圣地,康德、赫尔德、歌德、席勒无不对印度饶有兴趣,奥·施莱格尔更是成为德国首位梵文教授,叔本华则借助印度思想成就了自身的哲学体系。比较一下前贤,这种知识与精神追求的承继性和差异性都会有所呈现。但以斯坦纳专业学者的批评家身份,对印度思想原创性的如此描述,确实还是让人印象极为深刻!我看重的,其实更是这种出自其思想家直观的判断,或者说“直感”是绝非不重要的,因为当他在漫谈对话中不经意地脱口而出时,这种观点其实正是他长期沉思之后的精华积淀。
我不能说这部《斯坦纳谈话录》就能媲美《歌德谈话录》,但至少法国媒体人阿德勒(Laure Adler)的工作,是非常有潜力和可能性的。那些零星出版的当代思想界的谈话录,具有“激活思想的马刺”的功用,不能不为之击节,《伯林谈话录》《赛义德谈话录》等都是,但若论及其短小精悍和妙语迭呈,仍以是书后来居上。这种由某个作者专门进行的谈话,是需要精心准备和匠心营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特别表彰阿德勒的工作,没有他的努力,我们很难收获这样一部如此精致而高品位的“准经典式的”作品。当然精彩的短篇访谈也是有价值的,不过需要不断打磨,譬如“当代思想家访谈录”丛书也不错,收录了四位法国人福柯、布迪厄、德里达、利奥塔和一位德国人哈贝马斯的访谈,也可作为一种参考。但总体来说,我还是更欣赏这种有备而来、悉心规划,同时又顺其自然、行云流水的访谈方式,虽然最后的文字薄如蝉翼,可思想的力量却无比厚重有力,此书当可为一范式。但也有未被翻译過来的,譬如斯洛特戴克的谈话录(Peter Sloterdijk: Ausgew?hlte ?bertreibungen Gespr?che und Interviews, 1993-2012),也同样富有思想开掘的潜力。
借用斯坦纳的一声叹息:“安静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昂贵、最奢侈的东西。”(《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所以,伟大的智者多半会选择归隐的方式,他们在喧嚣浮躁功利的滚滚红尘中隐身而去,希望在“东篱”“南山”之间寻到思想者的位置。其实只有在繁华历尽、沧桑阅毕之后,才会意识到“寂寞”(Einsamkeit)是一种多么重要的品质和原则,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构建者们是要如何的“理智”与“智慧”,才会将这一貌似古怪的概念列为基本原则?在我看来,这就应是学者共和世界的“元规则”。而斯坦纳,无疑是真的能体会这一可贵原则并身体力行的智者之一!
英国作家拜厄特(Antonia Susan Byatt)认为斯氏乃“一位来得太晚的文艺复兴巨人……一位欧洲玄学家,却有着了解我们时代主流思想的直觉”(转引自彭桂芝、何世杰编著《中外翻译史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这真是非常高的评价。不仅如此,关键是她捕捉到了斯坦纳的“直觉”意义,即在很多时候,我以为不仅是诗人、艺术家,甚至是批评家、学者、科学家,都需要灵感的,用德国人的概念就是“Daemon”,正是凭借这种“精灵瞬间”的过程,我们可以成为时代精神与时代潮流的“捕风者”。
何其幸又何其不幸,这位欧洲玄学家在新冠之年(2020)辞世而去,这也确实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通过这部小册子,斯坦纳给世人展现出的不仅有对话的智慧,更有学人之美德,这是一种既有洞察世事的明慧,也有谦逊居卑的自觉,非大智者不能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斯坦纳虽为文人,但可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