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让人们看世界的脚步放缓甚至停滞下来。得益于完善的防疫措施和严格的管理政策,澳门较早实现了本地病例清零的状态。二○二○年九月起,凭借有效期内的核酸检测报告,来去澳门都不用隔离。澳门的电视媒体甚至骄傲地打出了这样的口号—“世界这么大,你只能去澳门”。上一次对澳门的印象定格在二○一八年,恰巧遭遇了寒流。时隔三年,澳门有了不少变化。氹仔的轻轨开通了,除了“威尼斯人”之外,还有命名为“巴黎人”和“伦敦人”的酒店开门迎客。在朋友的安排下入住澳门大学校区内的酒店。澳门大学在二○一五年整体搬迁到了横琴岛,其在氹仔的原校区则分别由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旅游学院进驻。横琴校区像是一个硕大的生态花园,湖泊和湿地贯穿其间。住宿地聚贤楼位于行政楼旁,下方是一个中式园林长廊,被红色的鸡蛋花和竹林包围着。园艺工人每天定时来园内打理盆景。清晨我打开阳台门透气,鸟儿会飞进来打招呼。聚贤楼内有两家餐饮,一家主营顺德菜,也提供港式点心;另一家据说是开了没多久的法式餐厅,有早中晚各式套餐。餐厅同时售卖自制的面包和蛋糕,他们家的牛角包香气四溢,每次出门都忍不住带上两个,定价为七澳门元一只,约合人民币五块多。一中一西的两家餐厅,味道正宗,也代表着澳门的一种融合度。
美食之外,这次澳门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和图书馆相会。澳门大学校园由何镜堂院士进行整体设计,图书馆被放置在中心轴上,左手边是大学展示馆,一楼陈列了国家领导人赠送的礼物、校区的整体模型;大型电子展板实时呈现学校的各项科研数据。二楼则承担了艺术展览的功能。二○一五年刚建成时曾访问过图书馆,这次在吴建中馆长的详细介绍下,对于外部中式、内部西班牙风格的设计理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图书馆的顶楼望下去,可以看到一块被阳光照耀着的平台,木质藤椅上学生们用放松的状态遨游书海,成为这一空间内的“动”“静”交汇之处。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澳门大学盆景园
澳门大学盆景园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是我一直想去,却屡次错过的地方。出发前的一个月,就和趙冼尘馆长在邮件中沟通了访问的主题、敲定了去访的时间。有点兴奋的我们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二十分钟。踏入图书馆所在的大楼,大厅里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立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名为“古地图中的大湾区”(展览时间2021年3月29日至4月16日)。
一
展览的开卷语提示说:“大湾区城市群是人类在经济、文化等活动日益频繁和高度融合后,在合适的交通条件、宜居宜人的地理环境下,受惠于各种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等人类文化高度发展而形成的新型生活场所。” 展览以“大湾区”为关键词,展示了目前世界上知名的三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古地图。展览中呈现的二十多幅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古地图分别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亨廷顿图书馆、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在我国各个朝代绘制的官方版本中,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条件极为优越,自唐宋以来便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明清以降,澳门及香港更先后成为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港口城市。此外,展览中的大部分地图是由西方航海家和传教士绘制的,由于个人收藏或宗教的原因,流转或聚集到了上述图书馆。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到访的那天恰是展览闭展前一天。可能是我们看得太过认真,也可能是我们随身的复旦标示袋暴露了身份,一位年轻儒雅的男士上前询问我们是否就是来访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他便是澳科大图书馆的助理馆长杨迅凌先生。杨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主攻图书馆专业,进入澳科大后,被丰富的地图资源吸引,又学习起了古地图的相关知识,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杨先生同时承担着图书馆技术服务方面的业务,真是一个繁忙的多面手。大湾区的古地图展主要就是在他的策划下完成的。展览作为澳科大二十一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准备时间只用了两周。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高质量的展览,则源于平时的积累。这样的积累一方面要归功于学者对材料的熟悉度,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澳科大本身在古地图收集方面的突出性。
在杨迅凌先生的专业讲解下,我们获取了地图之外的诸多信息。古地图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帮助我在后来的参观和座谈中,更好地理解了澳科大图书馆的藏书理念。古地图的收集和购买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有时候也讲求机缘巧合等因素。因此,澳科大的重点不是追求原版地图,而是去复制珍藏在世界各地的古地图。
地图有实用的功能,也反映着人们的世界观。大湾区的古地图向我们打开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认识中国的变化进程。观展时最引起我关注的是这些地图的收藏地点,其背后一定有着历史的脉络或有趣的故事。展览中一幅描绘一九二二年大湾区以及港九铁路建设的地图,标示的收藏地点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地图的下方用铅笔字清晰标记着“J. M. Braga collection”。“Braga”这个姓氏,看似熟悉又陌生,鼎鼎有名的香港九龙何文田加多利山布力架街(Braga Circuit)便是以这一姓氏命名的。这个葡萄牙家族的几代人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J. M. Braga的全名为何塞·马里亚·布力架(Jose Maria Braga),也被称为杰克(Jack),学界习惯译作“白乐嘉”。他后来将自己的收藏捐赠给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我们所看到的这幅地图来源于他的特藏。周振鹤先生曾在考据澳门地名由来谜团的文章中提到白乐嘉和他的特藏。
 展览“古地图中的大湾区”
展览“古地图中的大湾区”根据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s://www.nla.gov.au)的记录,白乐嘉特藏(J. M. Braga collection)的时间范围是一八六二年至二○○○年,内容包括日记、书信、图书、手稿、传记,个人档案(个人证照、财务和法律文件)、笔记、新闻报纸、照片、缩微胶卷、徽章、明信片等。其中的大部分材料记录了他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六年在澳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在香港的生活。作为一个兴趣广泛的收集者,白乐嘉的收藏主题涉及历史(尤其是葡萄牙在东亚的殖民、二战期间港澳的资料)、宗教、医药、文学、工程学、经济、地理和语言相关。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将他的身份定义为历史学家、记者和作家。
白乐嘉于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于香港,父亲何塞·伯多禄(Jose Pedro Braga,1871-1944;香港习惯译作“布力架”)是葡萄牙人,母亲奥利弗·宝琳(Olive Pauline)是澳大利亚人。一九二四年,白乐嘉来到澳门,在圣若瑟神学院教授英语,并与奥古斯塔·伊莎贝尔·达卢兹(Augusta Isabel da Luz,1898-1991)结婚,两人育有七子。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六年间,他担任了澳门水务公司的总经理。在这段时光里,藏书和历史研究是他赋予最大热情的事。白乐嘉从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抵达澳门的时间节点开始记录和收集澳门的历史。除了图书、地图、报纸和手稿外,他还创建了一系列档案和时间清单。他用英语和葡萄牙语为当地的报纸撰写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香港,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进出口业务公司。看似主业从商,却延续着写作和研究的兴趣。他尽可能地收集战时澳门的印刷品、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其中就包括《澳门印刷的开始》(1963年在里斯本出版)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一九五二年,他访问了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并接触到了《耶稣会在亚洲》(Jesuítas na ?sia)。这套共计六十亿卷的手抄本是对一五四九年沙勿略到达日本后西方传教士在远东传教活动的原始记录。白乐嘉把这些手稿看作是他收藏的最重要的部分。今日的学者公认,该手稿是研究中国明清天主教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清代社会史的重要的一手文献,大到发生在康熙年间被称作“礼仪之争”的伦理学和神学争论;小到航行于澳门和日本之间的黑船所载运的货物表。很多是在当今可见中文文献中没有记录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在一九五二年,白乐嘉的三个儿子赴悉尼学习,他本人也计划在安顿好各项事宜后移居澳大利亚。一九六六年,白乐嘉将自己的收藏卖给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随后两年中,他的资料分几次运送到了那里。不过,这两年里他一直住在纽约,继续追求商业利益,直到一九六八年才与家人汇合。
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七二年二月,白乐嘉作为顾问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工作,这一经历帮助他完成了其特藏的基本清单。其间,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一项重要任务—将《耶稣会在亚洲》的手稿翻译成英语,希望能为出版做准备,可惜只完成了很小的一部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白乐嘉在旧金山逝世。二○○六年是白樂嘉特藏来到澳大利亚的四十周年,他的侄子斯图亚特(Stuart Braga)获得了准许来重新整理白乐嘉特藏,并更新相关材料的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白乐嘉的家族长年扎根澳门及香港两地。他的父亲布力架一八七一年出生于香港,一九○二年至一九一○年间担任香港电报局经理。一九○六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他一直都是路透(Reuter)通讯社的香港经纪人。布力架是香港立法会的第一位葡萄牙籍成员,一九三五年被任命为大英帝国的官员。前文提到的位于香港九龙的布力架街就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三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布力架幼年在外祖父罗郎也(Delfino Noronha,1824-1900)的家中长大。罗郎也是香港早期的印刷商,曾在澳门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College)学习排版印刷技术。这所由耶稣会传教士建立的教育机构,在当时培养了一批熟练掌握新式排版印刷技术的实用人才。受外祖父的影响,布力架从一九一○年起开始经营自己的印刷业务。他的材料(Braga Papers)目前也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二
在古地图展中,有一张杨迅凌先生特别重点讲解的地图—由荷兰制图师芬彭士(Joan Vingbons)所绘《从广州到北京内河航线图》(Caerte de river, van Canton, 1668)。明清时期,西方人被禁止从海路直接进入北京,欧洲来访使团和入华传教士大都只能选择从澳门和广州出发,沿北江通过水路前往北京。在这幅地图上,以广州(Canton)为内陆的起点,经过三水(Samsoù)沿北江一路而上到达南雄(Namhùm),在那里翻越唯一一段约七十华里的大庾岭山路后进入江西赣江,沿赣江顺流而下经鄱阳湖入长江,经江南(今安徽、江苏两省)、从扬州转入京杭大运河北上直抵北京。地图上所呈现的连通着广州和京城的河流实际上是由多段江水及运河连接而成的。
我也和杨先生讨论,为何此图被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收藏,当时只是讲到和哈布斯堡王朝与神圣罗马帝国有关。回来后,我继续向他请教,杨先生向我详细梳理了该地图的来龙去脉,我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完善了对这一知识点的认识。原来芬彭士这张图收录在《布劳-范德海姆地图集》(Atlas Blaeu-Van der Hem)中。布劳家族是在荷兰黄金时代帮助定义了制图的家族。十六世纪初,该家族制作了一些欧洲最知名的地图、地球仪及地图集。威廉·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1571-1638)于一五九六年成立了布劳印刷公司。一六三三年,他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使得布劳家族有权使用公司海员提供的最新信息,并获得所有现存图版与海图的所有权。这个职位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约翰·布劳(Joan Blaeu,1596-1673)。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二年间,约翰·布劳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著名的《大地图集》(Great Atlas),地图集以拉丁语、法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编辑,根据版本的不同,装订成九至十二卷。它是十七世纪出版的规模最大、价格最昂贵的书籍,六百幅地图描绘了整个已知的世界。一百多年来,布劳的大地图一直是世界地图册的标准,也只有富有的收藏者才有机会入手这样一套世界地图。野心勃勃的收藏家、阿姆斯特丹律师劳伦斯·范德海姆(Laurens van der Hem,1621-1678)早在一六四五年就开始收集地图和地形图。一六六二年,当《大地图集》的拉丁文版出版时,他收藏了一套,并根据自己的想法整理了地图册中的航海图,用一千八百多张地图、图表、城市景观、建筑版画、肖像等放大了各卷的内容。所有的图纸都根据地图册的大小进行了调整。如果它们太宽,就折叠起来;如果它们太小,就放大;如果原始纸张太高,则会缩小其格式,或将其切成小块,然后分别粘贴在空白页上。范德海姆的这套地图在套色方面生动地体现了十七世纪尼德兰的色彩审美等细节。他本人撰写有一篇关于“装饰艺术”(Verlichterie-kunde)的文章,记录了套色师们的工作方法。范德海姆找人精绘重制的这套地图便称作《布劳-范德海姆地图集》,其中就包含了芬彭士的这张图。范德海姆去世多年以后,他的后人于一七三○年将他收藏的地图卖给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或译作尤金亲王),后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陆军元帅。欧根家族又把这些地图卖给了维也纳的皇家图书馆,也就是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二○○六年一月按照原样重制以八卷本形式出版。
在与杨先生一来一往的学术交流中,不断感受到探求新知的乐趣。根据他提示的线索,我继续兴致盎然地摸索一番,不仅发现地图与二○一九年夏天阿姆斯特丹之旅之间的神奇互动,也注意到荷兰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与地图之间的奇妙缘分。在阿姆斯特丹新市政厅内的市民大厅看到过地面上镶嵌着的大理石地图—三个扁平半球地图,分别是地球的西半球、天球的北半球、地球的北半球。位于水坝广场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历时七年建造完成,于一六五五年正式开放,它是十七世纪荷兰共和国最大的建筑工程。地面所绘的这三个半球便是复制于约翰·布劳的一六四八年地图。根据地图专家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所著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八章的记载,这幅地图是献给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外交谈判中的西班牙首席代表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及西班牙和后来组成联省共和国的行省之间历时更长的“八十年战争”(也被称为“荷兰独立战争”)。在深入了解布劳家族的过程中,我又发现艺术史领域对维米尔与布劳家族的地图的研究。维米尔十分热衷在自己的作品中绘制地图,他绘制的地图,不仅是为了装饰画面,其精准也不亚于制图者。法国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勒·托雷-比尔热 (Théophile Thoré-Bürger)就曾指出维米尔“对地图的狂热”。中国美术学院欧阳琼在其毕业论文《维米尔的地图—对十七世纪荷兰地图出版商布劳家族的研究》中指出,在维米尔为数不多被公认的三十多幅作品中,出现地图、地球仪、天体仪的多达十幅,其中有七幅绘有挂墙地图,而其中的五幅便是出自布劳家族。如维米尔早期创作的《军人与微笑的女郎》(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1658),醒目位置的挂图是荷兰和西弗里斯兰地图。这张地图是由威廉·布劳在一六二一年出版印刷的,后来还出现在维米尔的《读信的蓝衣女子》(Woman in Blue Reading a Letter,1663)一画中。维米尔的童年是在地图业无比盛行的时代背景中度过的,布劳家族在地图的套色和装饰方面与维米尔油画中地图的视觉呈现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
澳科大图书馆重点收藏了数量不少的广州古地图。十六至十九世纪,广州与澳门两个城市在西方地图上常常同时出现,两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商品交易和文化的碰撞都在这里发生。图书馆收藏的广州古地图按内容主题可以划分为表现不同时期广州城区历史变迁的“广州城图”;以从珠江洋面眺望广州城的景观为绘画视角的“广州城地志画”;另一类“广州府地图”的区域大致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
数量丰富的古地图以及这种随时能够办展的能力一定是有坚实的支撑基础的。在与图书馆同仁的座谈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全球地图中的澳门”这个已经开展了近八年的项目。项目以全球史观为视角,以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为线索,收集整理散落在全球各地的相关古地图,并进行数字化和出版。二○一三年九月至今,项目已搜集了超过七千张与澳门研究相关的中外文古地图。除了举办多次国际研讨会和展览外,项目同名资料库(Global Map of Macau,http://gmom.must.edu.mo)已经上线。澳科大图书馆还出版了《驶向东方》《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等会议论文集和地图集。杨迅凌先生看到我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特地送了一本大开面的《明珠星气 白玉月光》画册给我。画册完整地记录了作为项目成果之一的“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地图文献珍藏展”。
“全球地图中的澳门”项目有一个关键人物,戴龙基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馆长,二○○九年十月受聘为澳科大图书馆馆长。根据《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中所载《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地图项目大事记》,我们大致可以管窥整个项目是如何被推动和发展的。细细读来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项目的起源是澳科大的教员在观看了澳门博物馆举办的《海国天涯:罗明坚与来华耶稣会》展览(2012年11月29日至2013年3月3日)后,电邮戴馆长和杨迅凌,提到这些是澳门研究的珍贵资料。戴馆长便与澳科大社会与文化研究所负责人讨论了以地图收集为主线开辟专题收藏。根据早年在北大工作时所做的调查,马上联系了自己在图书馆界的馆长朋友。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郑炯文、马小鹤等给予热烈回应,愿意接受澳科大前往调研、搜索和复制哈佛馆藏的相关古地图。同时,戴馆长还将视线放到了欧洲。通过北大图书馆的学术网络,他联系上了意大利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东亚馆藏负责人余东女士,那里收藏有一些很重要的中国制明末清初地图、传教士的地理著作和欧洲制的古世界地图和航海图。在澳门基金会的资助下,项目成型。二○一五年初,戴馆长和杨迅凌以及专家组的成员们访问了罗马,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沟通了复制地图和办展等各项事宜。
二○一五年七月,澳门科技大学成功举办了“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地图文献珍藏展”。展品的创作年代从十二世纪至十九世纪,著名的葡萄牙制图师里贝罗(Diego Ribero)一五二九年创作的世界地图(Carta Universal en que Se contiene todo lo que del mundo se ha descubierto fasta agora hizola)就在其中。里贝罗是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效力的葡萄牙人,他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最著名的制图家。麦哲伦携带他所绘制的地图进行了那场著名的穿越太平洋的航行。皇家贸易部的两名主要官员—首席宇宙学者(cosmographer)和首席航海家具有保留官方地图的权利。里贝罗与所有探险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是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的好友。他们两人一个是宇宙学者,一个是领航员。在那个时代,宇宙学者会参与修改样板图表,给领航员上课、考试,检查图表和仪器。首席航海家的任务是培训船长,开发导航设备,最重要的是把航海家们带回来的新信息记录在“国王样式”(Padrón Real)世界航海图中。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的父亲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是英国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代表人物,布里斯托设立有约翰的纪念碑,位于可以鸟瞰整座城市的山坡上。约翰·卡伯特是西北航道(自大西洋通过加拿大北极岛至太平洋的航路)著名的探险家,塞巴斯蒂安跟随他的父亲参加了一四九七年从布里斯托爾出发到纽芬兰的航海活动。一五一八年,塞巴斯蒂安被任命为西班牙贸易部的主领航员。一五四四年,他根据自己获得的当时有关西班牙皇室在世界各地统治地区的最佳信息制作了第一幅新大陆地图,在安特卫普印刷。在这幅里贝罗的地图上,注记有“China”(中国)、“Cantam”(广州)、“Mare Sinarum”(中国海)等,这是第一次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标注“广州”。特别是地图中珠江口内侧,广州右下方一个标示为“Matan”的地名值得注意。在澳科大图书馆的二楼,也陈列着该世界地图的放大复制版。杨迅凌先生特意将“Matan”所在的位置指给我看。学者们倾向于认为,“Matan”很有可能指代的就是澳门。里贝罗的世界地图,除了展现精确的地理信息之外,还可以看到各种动物的标示散落其间,尤其是在印度和非洲的区域,有很多大象的图标,这些信息都在引导着人们更深入探究。动物的图标不一定描绘真实的知识,有时是作为装饰性元素存在的。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研究海洋史、澳门史的普塔克教授(Roderich Ptak)曾对地图里记载的异国动物进行了研究(《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收录于《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他提到了不同版本的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中所展示的动物,并比较了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里的动物信息,特别是有关虚构的动物—西方的“独角兽”的描述让人兴趣盎然,也让我重拾起童年时代爱看的《蓝精灵》中的相关情节,独角兽的兽角具有净化水源的功能。在《全球中的澳门》(第二卷)中,也收录了邹振环先生讨论地图与动物之关系的文章《〈坤舆全图〉与大航海时代西方动物知识的输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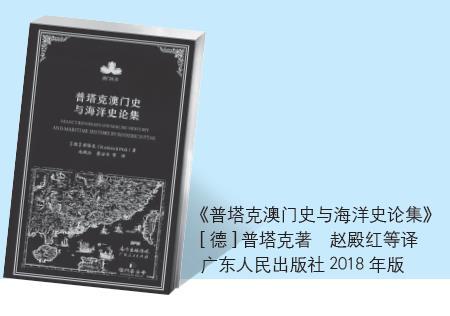
除了里贝罗的世界地图,二○一五年的展览还展出了其他重量级的古地图,比如一六○二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坤舆万国全图》原刻本(存世只有6件,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所藏是保存状况最好的一件)。一五八四年至一六○三年,利玛窦在中国编绘了多幅不同的世界地图。为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世界地理观。不过,为了适应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利玛窦将中国绘制在了地图的中央。其他展品还有一六三四年汤若望《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目前所见传世最早的包括南极区在内的大型中文全天星图)、一六六七年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中东至中国和北亚路线图》(Tabula Geodoborica Itinerum a varijs in Cataium susceptorum rationem exhibens)绘制了历史上的“一带一路”,图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澳门。
根据戴馆长的自述,项目的根本目标是“支持澳门研究”,基本责任是“将收集到的资料最大限度地转变为学者、研究人员所需的数据”。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项目收集的古地图已经成为研究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乃至早期全球化的重要资料。从这些古地图里我们看到,澳门是十六世纪全球化进程启动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视窗和贸易枢纽。在项目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中,除了强调澳门在“西学中传、东学西渐”中的角色,也促进了以历史文本解说的范式来研究地图的转向。长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透明范式”(Transparent paradigm)将地图作为建构知识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认为地图是单一透明的。这就使得地图被推定成是准确而可靠的历史依据,并要求学者和制图专家去不断讨论地图的精确性。这一范式将地图作为一个中立的、纯粹的信息来源。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地图也有着“隐藏的信息”。历史范式(Historical paradigm)视地图为历史文件,每一幅地图都表达一个观点,包含多层次的意义。比如在这次展览中看到的一些地图,更像是风景画,制图师在记载水文地理情况的时候,的确会掺入想象。而有的时候,地图更是一种权力,既传达知识,也含蓄地强化社会的和政治的秩序。
 狩野内膳绘《南蛮屏风》(16至17世纪)
狩野内膳绘《南蛮屏风》(16至17世纪)在古地图展中,还有日本浮世绘版的东京湾地图。杨迅凌先生告诉我,澳门的许多书籍是在日本出版的,他们尚未和日本取得太多联系。我告诉他,在位于长崎的文化博物馆,有一个“长崎与中国”的展厅,里面展出了部分他们会想要收集的版画(地图)。此外,二○一九年底我在神户市立博物馆看到了很多古地图。博物馆以“南蛮艺术”(日本沿用中国“北狄南蛮”的说法,“蛮”一词在《日本书纪》时代指朝鲜半岛南部未开化之地、萨摩之西的五色岛、萨摩七岛和琉球。十六世纪起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南亚地区殖民,并将贸易的范围扩大到了日本。因此将通过印度的果阿、中国的澳门等这些路径中转来到日本的欧洲人称为“南蛮”)为馆藏的核心,所收藏的狩野内膳的《南蛮屏风》生动地描绘了十六七世纪日本与西班牙、葡萄牙间传教与贸易的情景。神户市立博物馆的古地图收藏主要来自三个人物(南波松太郎、秋冈武次郎、池长孟)的捐赠,共计有八千多件。除了硕大的屏风地图外,有一个伊万里烧瓷器的日本地图让我印象很深。因此我也建议澳科大日后可以前往这些地方继续扩大收集。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澳门本地葡人融入当地生活的程度也很高。这次朋友安排我们到位于路环黑沙滩的法兰度餐厅用餐。来澳门这么多次,其实还是第一次去由澳门葡人经营的葡国菜餐厅。车子一路开进路环区域,就看到很多葡人在跑步健身。朋友提前向我们说明这家开设于一九八六年的饭店有一大特色,从开店以来就不装空调,一直使用吊扇。虽然夏日的黑沙滩很炎热,喜欢美食的客人还是会上这里来。红色的方格桌布,敞开式的窗户外是热带岛屿植物。头顶的吊扇慢悠悠地按它的节奏转动着,毕竟四月中还不算闷热,傍晚的微风特别惬意。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们点了马介休(腌制过的鳕鱼)、澳门炒饭和烤乳猪,道道都超过我曾经的体验。离开的时候,我们被满墙的各国货币所吸引,于是折返店内,找到老板询问其中原委。他用英语告诉我们,原先是顾客的自发行为,觉得好吃便贴一张本国的货币在墙上,以表明有这个地方的人來过了,是一种推荐和留念的意思。后来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老板索性就定制了玻璃柜,把它们装裱起来。我们还发现,可能是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已经有了,最近流行的是把自己的名片裱在上面,看来真的是实名诚意推荐了。聊得开心,忘了时间,我们出门时已经是店内最后一批客人了。几位本地葡人也结束了工作,他们提着包袋,骑着自行车,哼着歌曲,欢快地消失在夜幕里。
这次在澳门认识了几个新朋友,澳门古籍修复协会和圣若瑟大学(前身为圣若瑟书院)图书馆的同仁们。因为疫情,图书馆定制的材料无法从欧洲准时运来,书院的修复工作被搁置了。他们都很年轻,侃侃而谈中透露出的是对专业的坚定和热情,让人动容。在澳门,也会了旧友。我有一位“吃货”朋友,澳门好吃的地方,她如数家珍。还有一位长辈兼老友,她本人的很多经历也代表了澳门人与澳大人的真实想法。她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看着横琴校区是怎样一层层盖起来的。她培养出来的年轻同事曾在二○一三年来到复旦做交流生,从澳大毕业之后进入对外交流的领域工作,这次我们的访问就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结束澳门访问的当日,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我发了一条短信向他道谢,感叹今日澳门在电子支付和交通移动方面的便利,他回信说,“澳门正在努力跟随祖国的步伐发展,下次来一定会更加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