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文学的道理讲得比文学更形象更鲜活,很喜欢王安忆这样的文字。这本《小说六讲》篇幅不大,不知不觉就看完了。这是作者二○一五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期间的演讲集,初版时名为《小说与我》(2017),纯然出于自己的经验与体验,整本书娓娓道来,像是与朋友叙旧话家常,有时也不去顾及小说学叙事学那些学理性的东西。前面两章有些自传的意思,写自己早年读书与人生遭际,掺和进去的情感分寸拿捏得特别好,增之一分或矫情,减之一分则枯燥。又叙说自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经历,尤其是因聂华苓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在美国结识陈映真给她带来的“启蒙”。第三章谈类型小说,以及类型和非类型小说的分际,她举述具体文本,让你自己去寻绎定义。第四章她谈自己的“小说观”,由一堆暧昧的文字筑成一种可信的存在,内中带有从感官王国走向思想王国的逻辑。综合起来看,前面几章也是一种独特的年代阅读史。第五章是记述她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课工作坊如何与学生互动,如何训练他们做田野调查,构建故事的能力。最后一章谈张爱玲和《红楼梦》,特别难又特别大的题目,在她手里举重若轻,妙语频出,冷处偏佳。读完全书,忍不住想对她说,别写小说了,写评论吧!
讲故事的人来讲道理,道理还在故事中,讲得引人入胜,这是最好的小说学。
好故事 = 好道理
书中有一章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怎样才称得上一本好小说?”这题目展开去论证怕是几个博士论文都装不下,但王安忆就用几百字把它说清楚了,最后总结道:“当一部小说好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就很难把它分类了,也就是说超出分类了。至于好小说的标准,很难说它有什么,只能说它没有什么。它肯定是不无聊,它也不低级,它还不乏味。”多么简单明了,但你须自己去体会,比如什么叫作“没有什么”,什么是“无聊”和“低级”,是“高级”的低配版还是不入流?她不用高深概念,不让读者心里发怵,但这种大白话叙述交给你的,既是实,也是虚。像是国画里那种留白的“虚”,亦如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字字写实,而词语背后的意思须你自己领悟。她所有的道理都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讲。

一位读遍当代名家的文艺男对王安忆有这样的评价,说她在文学上很有“野心”,她想表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大上海”,类似狄更斯笔下的“大伦敦”,或巴尔扎克笔下的“大巴黎”。当然,她自己从来未曾如此表白过,这是她的聪明之处。她想要说的,一切都在故事与人物中,自己去看吧。读她的评论著作,亦可作如是理解。
王安忆的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有些人物出现在虚构的小说中,有的也出现在纪实的散文随笔中,让人不辨真假,在我记忆中都成老熟人了。她写那些被岁月摧残仍保持优雅自尊的女性,有的连名字都未曾给她们取一个,因为她赞赏的是那一类人独有的群体气质:从社会上层一个跟头栽落下来—被抄家,钱弄光,全家只剩那双未曾劳作过的纤手去挣一口吃饭活命钱,可是她们却还能保持姿态不难看。比如住在她家弄堂底的儿科医生一家。先说之前他家生活的与众不同:长年用两个保姆,一个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资金紧缩离开他家去隔壁家帮佣。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饮食要比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一人坐在厨房里“慢慢享用”。“慢慢享用”这个词语她在几部作品几个人物上都用过,即使是一杯清豆浆,一碗薄粥,一小碟酱瓜,女主人坐下来独自一人“慢慢享用”,便已内蕴丰富意境全出。运动来时,这些女人才真正显示出人的教养是怎么回事。王安忆在好几个作品中都细细描绘过这幅场景:有一日,作者走过后弄,看到那家进驻了抄家监督者的女主人就在那些人的眼皮子底下就着水龙头淘米起炊,一边还安详地回答着监督者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而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變。再说回儿科医生家那位美艳耀眼的大儿媳,运动来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担起了全家涉外方面的全部事务,比如每当召集有问题人家里弄开会,她便提个小板凳走到那个狭小漏风油毛毡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这也是王安忆常用的短语),领受照章宣读或即兴发挥的训斥。她两手放在膝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外,并不胆怯接受人们好奇的注视。每逢周四里弄大扫除,她穿上高筒套鞋,提着铅桶,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头上扎一块羊毛方布围在颏下像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她提水桶很稳当,扫地也很干净。再然后,她隔三岔五去里弄居委会领活计,编织小孩风雪帽或连衣裤,但她的美丽并不受损,依然引人注目,气质摄人。“这一家都具有这种气质,这气质会叫人着恼”,其实这户人家没什么大事,却惹来抄家批斗大祸,恐怕就缘出于此。王安忆曾说起,她母亲茹志鹃先生对这户人家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们有气节!”

专业评论家或认为这样的评论与表述“不够高级”。就好像一直有评论家认为勃朗特与奥斯丁的小说立意不高。是的,直到今天,再把《简·爱》《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从头至尾翻一遍,你也依然找不出她们有何“高级立意”。你只是赞赏书中那些美好的场景,机智的对话,英格兰乡村的美丽—从根上分杈的树丛点缀绿野间,喝水的马,散步的女人,橄榄球场的孩子……伊丽莎白步行三英里去尼日斐花园看生病的姐姐,到人家门口时两脚和裙边全沾满了泥,但她的脸庞却因为长途步行而格外红润鲜艳,引起了达西先生的注意。是的,这并不高深,但就像《红楼梦》中宝黛顶头初见吃一大惊:“这个人好生面熟!”《安娜·卡列尼娜》中渥伦斯基猛抬头撞见正步下火车的安娜—所有的雾气都散去后,那一瞬定格成经典,却说不出为什么。
你喜欢简·爱也不是为了她被罗列出来的种种优点,你为她感到欣喜,不是因为她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但是要让读者以近乎信仰般的态度来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像凝视珍物那样去抚摸其中细节,那些擅用故事讲解人生的,能在我们心头萦绕再三:也许那就是好故事的道理?
好道理 = 好直覺
小说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玩法),却很少像王安忆这样关注创作理论。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就出版了探讨小说叙事的《故事和讲故事》一书,她与张新颖教授的《谈话录》更是显示她对理论的执着。但她身在院校,却不像学院派那样固守学科和书本上的概念,她的理论往往带有“直觉”的敏锐。所以,她说着说着又会转为故事。比如文学的“类型化”,也就是简约化公式化。许多人举金庸武侠小说为例。就武侠而言金庸是一代大师毋庸争辩,但“成人童话”一说总归无法摆脱“类型”的框架。
作家在大学开设文学创作课,纳博科夫可算是王安忆的前辈。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康奈尔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其后以这些讲稿为基础整理编辑成《文学讲稿》(以及《俄罗斯文学讲稿》)出版。《文学讲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较多地引用和分析作品原文。王安忆佩服这位前辈,并非因为《文学讲稿》,而是他的小说。她拿纳博科夫的作品为例来讲解“非类型小说”的颠覆性特点,不是以《洛丽塔》为例,因为这书名人名,都已成为专有名词了,因而也极易被模仿被套路。她剖析的是《防守》,那部小说好像不太有名,却是很难被模仿。纳博科夫写一个天才棋手,一个怪咖,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爱,总之是没有人间欲望。这样一个人,等于活在抽象的世界中,活在某种概念中,在小说中如何化为具象的表现是一个问题。小说很难从专业角度去表现棋艺,技术性太强的叙述自然枯燥,但如果抛开弈棋的思路又怎能表现那种超越俗世的逻辑?这是对小说家极具挑战性的地方。王安忆认为纳博科夫完成得很好,天才怪人的世界是由几何线条构成的,他着迷于那些分割均匀的平面格子,那些格子在他眼中是有生命力的,下棋就是启动其中的有效活力,他的征服欲由此产生而后膨胀。等到怪人棋逢对手败下阵来时,他觉得其中的逻辑似乎与外面的具象世界有所连接,但他总是找不到这连接的入口,他被困死在抽象世界中,又隐约感觉外面有个真实世界,他难辨真假,最后只能纵身一跃结束所有的挣扎。王安忆对此构想表示激赏,给予高分评价。她的直觉评论非常棒,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看过的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基本的思维框架与《防守》略同,最后的结局却还不及纳博科夫写的有意思。
要说文学所能提供的种种幸福感,最高级的自然是创新。由于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种幸福感,许多人只能满足于模仿。世界越来越复杂,文学的想象力却越来越类型化单薄化。

但王安忆并不看轻有套路模式可依的“类型小说”,因为它受众广大,契合大部分人的思维路径。这是可以习而得之的叙事模板,她的写作课是要训练学生熟悉那些套路,进而从基础的“类型”转向独具创意“非类型”。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他把作品中那些原来并未显示出深长意味和特殊价值的文字,如珍珠出蚌般地展示给读者。他问他的学生:“爱玛读过什么书?最少举出四部作品及其作者。”王安忆在课堂上则是让学生们想象,若是鲁迅携许广平探望母亲,那位不受待见的朱安夫人会不会露面?或是露面会不会坐在一起吃饭?坐在一起吃饭会不会聊上几句?聊几句的话会说些什么?王安忆告诉学生,你们也可以说这是些“八卦”,但八卦进入了文学便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张爱玲将自己的散文集起名《流言》,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文字因而有了自在的生命,它能够让虚拟变为现实,当然,这现实不是那现实,它在另一个世界,那一个‘信的世界。”
好故事 = 好哲学
王安忆讲故事和讲道理,都充满世俗的哲学思维。那种非专业的哲学,也就是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抉择思路。比如,要不要请假去超市抢购大减价的商品,怎样在两个各有优缺点的求婚者中选择终身伴侣,如何看待过日子的“体面”,是否要去谋求一份高薪却无法顾家的职位……我发现这正是她的目标—既非完全脱离具象又不陷入虚无当中。她思忖物质与精神的舛迕,用故事来讲哲学,以哲学漫步寻求文学终极指向。
她讲述托尔斯泰,用自己的哲学心灵去捕获另一种哲学精神。《复活》的旧贵族聂赫留道夫走在西伯利亚流放者队伍里,《战争与和平》的皮埃尔(同样是贵族)则走在拿破仑军队押解的俘虏队伍里。托尔斯泰总让他高贵的主人公以自愿方式进入最底层,经受炼狱之火,就像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复活。最打动人心的是,事情是如何走到这个地步?托尔斯泰从来不回避交代经过,如何会由常态走进非常态,这正是文学可以施展身手的地方。但王安忆并不满足于膜拜偶像的非凡创作能力,而是从中看到常人不能窥见之处。谁都知道托翁对作品主人公寄予最终救赎的希望,但王安忆偏偏指出:“托尔斯泰每每走到人物的终局时候都流露出无能为力。”尽力洗去自己罪孽后行走在西伯利亚荒袤大地的聂赫留道夫,结果是在“西伯利亚要塞司令温馨的家庭里看到一种不受苦又可以不犯罪的生活”。安德烈公爵濒死时,所有的恩怨情仇全融为一体……可是,这难道就是终点吗?似乎也不是。文字能够抵达的目标已经完成。看托尔斯泰的传记,他晚年沉迷于音乐,王安忆的猜测是他对世界的看法已经突破形象,进入到形而上的层面,需要更有力量的符号才能描绘他那个宏观性的存在。音乐的抽象性暗示了这种可能,但是完全脱离具象又容易陷入虚无。
她的写作与个人经验密不可分,她的哲学也贯穿于一路的写作表达中。曾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陈映真对她有“启蒙”之功,这对于几乎被贴上张爱玲传人的她来说真是有点讽刺意味。张爱玲从不隐晦自己爱物质爱钞票,并把这生活哲学坚守到底。王安忆写小说和随笔,也多少带着欣赏的意态描绘老上海那种人家,一种富裕颐养的气质和教养。大约是一九七二年光景,她们有一伙人长时间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到上海,活动着想要投考地方或是部队文工团。要点不在考不考得上,而是她去拜访投师的那户人家(我似乎在王安忆好几处作品中见到过对这户人家的描述)。那是插队江西的一名女生的家,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的长相略微粗拙,穿着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家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幢公寓里。在那个年代竟有这样的人家:“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家的母亲。灯光从后面照着她,有一股慵懒闲适的气氛,这样疾风暴雨的年代,它甚至还散发着一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穿越了时代的关隘。”

許多人都注意到,当人们将王安忆与“小资教母”张爱玲扯到一起时,她总是脸露不悦,有时急急分辩几句,有时懒得多说。但她有过一篇长文认真声称,陈映真才是她的“精神偶像”,只是自己终究让他失望而已。那篇长文自始至终让人看到的是数年来双方交流的不畅、无奈,有时几乎鸡同鸭讲,偶尔的心意相通也是因为一者丧母,一者失父发生在差不多时间。所以,王安忆说这是她的一厢情愿。是她的梦想。一九八三年她和母亲茹志鹃一起去美国爱荷华参加聂华苓夫妇主办的“国际写作计划”,其间她见识了不同国籍的作家,还有许多当时在国人眼里视为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和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她学习享受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她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最初在翻译小说里被译成“意大利脆饼”)。她说:“我在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淇淋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十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她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她看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括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她坚决认为:假如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她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人就是陈映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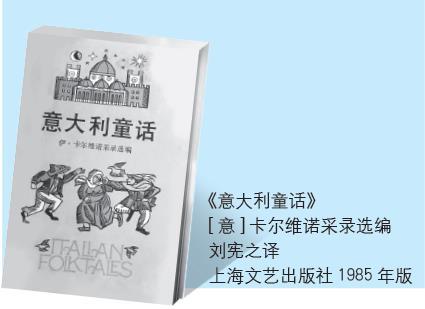
也许是陈映真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让她在一堆琐碎的物质海洋中看到一股清流。但王安忆也说过,陈映真面对人们向他诉说具体生活遭际不怎么在心,“你说你们过得苦,人在哪个地方不苦?这种有什么可多说的?”如同西方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的认知那样:为了宏大目标,踩碎路上的小花小草算得了什么。但是给饥渴者吃喝,给赤身者披衣,给异乡人关爱,即便是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岂不也是做在世界。
后来,我们关注她的作品时,她早已偏离自己的舒适区,向着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进发,有时却又返回那些多年老粉们期待的描写场域,让出版社和评论家们或诧异或兴奋乱作一团。她自己懒得去作解释。
温柔不是不讲实话,而是怎么讲实话,以及在非冷酷不可的实话之外多点什么—譬如,海明威小说,一旦失去了大时代光环的加持,其局限和缺点很容易被看穿,尤其是他始终停留于三十岁之前的心智程度,以及因此无可避免的虚假狂暴和感伤,更难以糊弄有年岁有生命阅历的成熟眼睛,所以人一到某个年纪和心智程度就只能告别它。然而,正如西哲所云:“你若不回转小孩的样式,就断不得进入天国。”那些温柔地谈论海明威小说的好心人,在冷酷的实话之外,便是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的笔墨带回自己成长时期的天真。
《小说六讲》有一篇讲到“童话与悖论”,介绍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收集编撰的《意大利童话》,王安忆完整地转述了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野兔和狐狸。有一天,狐狸在树林里看见兔子快乐地跳来跳去。狐狸问兔子为什么那么高兴,兔子回说它娶了个老婆。狐狸恭喜兔子,兔子说不要恭喜它,因为它老婆很凶悍。狐狸说那你真可怜。兔子说不,也不要同情它,因为老婆很有钱,带给它一栋很大的房子。狐狸再道喜,兔子又说不要恭喜它,因为房子已经一把火烧掉了。狐狸说可惜可惜,兔子说也别觉得可惜,因为它那凶巴巴的老婆也一起烧掉了。
很哲学吧,很符合王安忆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