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身体的中介而传到自我的“作用”,我们把这些作用叫作感觉。
—马赫《感觉的分析》
“您上周每天平均屏幕使用时间为×小时××分钟”,手机定期会弹出这样一个信息窗口,告知用户过去一周里屏幕使用的时间。如果打开手机的“设置”,你就可以看到更为详细的数据,例如与上周使用时间的比较、屏幕总使用时间以及各个软件的使用时长……事实上如今我们已经很少直接观看世界,而是仅仅观看视场中的一块区域—那几英寸大小的屏幕,正可谓“一屏障目”。视觉虽然一直都是各种感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但它仍然尝试“篡权”,阻碍甚至阻塞了其他的感官通路。
然而不禁想问的是,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进行的观看,究竟看到了什么?这大概是很多人根本不会提出的问题。看,就是看啊!屏幕虽然是固定的有限平面,但是已经(过度)满足了所有人“左顾右盼”以及“东张西望”的愿望。这几年流行起来的短视频类软件更加造成了一种上下滑动的观看习惯。如果一个短视频无法在几秒钟里抓住你,你就会迅速划掉它,转向下一个短视频。即便眼睛停留在一个物体表面,思绪却在不停地游移,乃至不自主地分神,期盼离开。我们每天观看的时间很长,收到的信息量也很大,但是其实看到的内容很少。视觉虽然依旧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感官,但是却面临不断“贬值”的危机。

丹尼尔·贝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曾经断言:“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这里的景象在原文是“sight”,具有視场、视域的含义。他进而宣布,群众娱乐(马戏、奇观、戏剧等)一直是视觉的。
《道德经》(第十四章)有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按照老子的这个说法,我们现代人时常都处在“恍惚”状态。
每一次观看漫威或者DC电影,尤其是在3D影院中,观众都不得不在昏暗的背景中费力找到“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找到一个眼睛的关注点。或者说,观众需要在几十分之一秒内认识到那不是焦点,导演并不想让你仔细看到这里。也许因为经费不足或者赶工,这一块的CG渲染被偷工减料了;然后,在下一个几十分之一秒内,你要努力地跟上对象迅速的移动,例如,奇异博士发出的“拉格加多尔之环”从银幕一侧飞行到另一侧……观影之后,观众再一次欢呼好人战胜了坏人,拯救了世界。在后怕之余,影片再次印证了大众的心理预期—这个世界还是有救的。主角和英雄们发出的招数似乎继续在观众头脑中穿梭、飞舞;回家后,观众极有可能依然会感到头昏脑涨,眼球肌因过度使用而疲劳酸痛。这种电影好像用银幕上的画片,直接牵扯着观众的眼球。那无非是更为复杂的逗猫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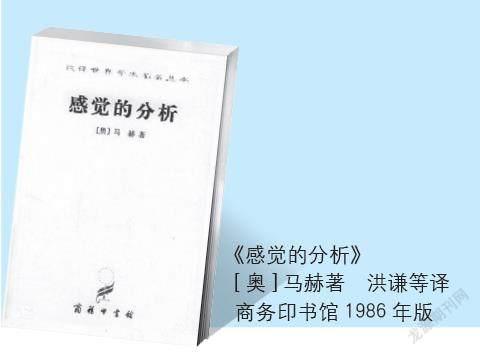
在这样一个视觉泛滥而又贬值的氛围中,《天地玄黄》(Baraka,1992)简直就是一个异类。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部“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影片。它的导演罗恩·弗里克(Ron Fricke)并非高产的商业片导演,而更像一个隐者—他每隔很长一段时间,会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大众的视野。在此之前他还拍摄过一部类似的电影《时空》(Chronos,1985,片长42分钟)。在这部电影中,弗里克似乎已经找到自己特有的电影语言和拍摄手法。《时空》不是一部实验性的作品,可以视为《天地玄黄》的先导。在二○一一年,他又推出了《轮回》(Samsara)。
《天地玄黄》全片没有情节,也没有旁白,原片中也没有字幕—某些视频网站后来加上了片中场景信息和背景介绍,可谓画蛇添足。看完之后,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或者说,它提供了一种极度纯粹的观看体验,不可名状。本文就尝试将这种不可名状言说出来。
观看《天地玄黄》的最佳方式自然不是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而是应当这样做:虽然不必沐浴更衣,斋戒焚香,但可以将自己的手机关机,插入到家中的米缸里,再把米缸放到厨房里看不见的角落,以免时不时想要摸手机。你应当独处一室,周围没有第二个生灵。观影时最好窗外狂风暴雨或者大雪纷飞,关掉所有的灯,陷入自己的沙发里,半仰望地看着投影出来的影片或者大屏幕,让自己被画面“包裹”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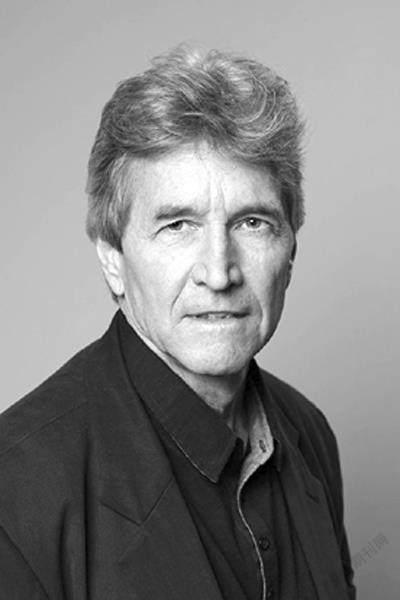 罗恩·弗里克(Ron Fricke)
罗恩·弗里克(Ron Fricke)《天地玄黄》全片似乎是一系列空镜头的串联。它什么都没有说,但似乎又表达了很多。在欲言又止之间,是恰到好处的留白。在观影过程中,你甚至会出现情绪的剧烈波动,看完后意犹未尽,若有所思。《天地玄黄》可以提供这个时代最为匮乏的感受—沉浸体验。我们越来越缺乏一种凝神聚气的观看、注视、定睛的能力。
如果翻阅各类电影网站,你会发现《天地玄黄》毫无例外地被归入“纪录片”(documentary)的类别。然而笔者认为,《天地玄黄》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别(genre),因为还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标签,索性暂时不去命名它。罗恩·弗里克花费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来准备和拍摄这部影片。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影体验,但是每个人看到的内容可能截然不同,甚至一个人每次看同一部电影的体验也会差异甚大。《天地玄黄》似乎是一部“未成品”。它每一个镜头很少超过十秒钟,但是在一个小时三十多分钟的时间线上,导演创造出了一种连续性和整体感,观看者都能体会到,这与连续看一个半小时的短视频是不同的。《天地玄黄》看似是“拼贴”(bricolage)作品,但它丝毫没有琐碎、断裂的感觉,反而营造出了一种宏大的史诗感—虽然它既没有历史,也不是诗歌。有评论认为它属于“诗性纪录片”,其实也有些词不达意,姑且算是尝试去标记那种不可名状的观影体验。
然而问题是,《天地玄黄》是一部纪录片吗?纪录片的直接使命是要去“记录”(document),而记录的对象则必定是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特定事件,事件中必然包含着人、物或者其他存在者。通常一部纪录片总是关于特定对象(集合)或主题的纪录片,例如动物、环境、风光、历史、人文等,不一而足。因此,纪录片通常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它记录的对象一般不是随机分布在时间线上的散点事件,而是能够构成一定逻辑顺序或者主题(内在)关系的系列。《天地玄黄》不是这种狭义上的纪录片。它包含了上述所有的元素,但又不仅仅止于单一的主题。
 《天地玄黄》剧照
《天地玄黄》剧照喜欢看纪录片的观众,在观看《天地玄黄》时,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错愕感—如果它是在记录的话,似乎违反了纪录片的基本原则,即被记录对象的地理位置是相对可定位的,但其时间却是模糊的、不详的。很多事件可以发生在某时某刻,也可以发生在彼时彼刻,换言之它们缺乏明晰的时效性。当然有人可能提出一到两个反例:科威特燃烧的油井和科威特—伊拉克边境上的80号公路—伊拉克军队撤退时被多国部队大量击毁击伤,因而又被称为“死亡公路”。这两个镜头是《天地玄黄》拍摄时间的偶然—恰好在一九九二年海湾战争之后。然而,作为观众同样可以对这两个镜头做出“非/去时效性”的观看—燃烧的油井,沙漠中遮云蔽日的浓烟,各种装甲车、卡车烧焦的残骸,制造出了和平年代的“末世感”,甚至让人想起《神曲》中炼狱的入口。在一个看似时效性的场景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对永恒性的追求。在《天地玄黄》中,观众是否知晓导演拍摄的场景指向何物或者何事,其实并不会影响其观影体验。甚至影片中的一些场景,你今天去看和一百年之后去看,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变化微乎其微的自然对象,例如大峡谷中的拱石,抑或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莫多龙;一些人文景观也是如此,例如也门的驴车、印度加尔各答街头乞讨的儿童和在巴西圣保罗街头露宿的流浪汉……反之,在拍攝完成之后一些貌似“永恒之物”的突然消逝,也会给人带来恍若隔世的感觉—纽约世贸中心北塔旋转门,里面的人流穿梭如瀑。不禁令人感叹,逝者如斯夫。
笔者认为,在《天地玄黄》中大致可以看到三个不同层面的内容:一、景点和景观;二、历史和文化;三、观想本身。当然这三个层面可能是交织存在于每一帧画面里的。
 《天地玄黄》剧照
《天地玄黄》剧照如果你带着观看一般纪录片的视角去观看《天地玄黄》,大概首先看到是一系列的景观。“景观”(spectacle)是一种特定人群的消费对象。全球化时代的景观提供给一个国家中间阶层的,大致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为那些无法抵达现场的人,提供一种审美慰藉;其二,是为那些可能抵达现场的人,提供一种审美准备或者说预演。第一个人群有可能转化为第二个人群,这是全球大规模旅行创造出来的可能性。但是在图像时代,这也衍生出一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在抵达现场之前,已经先行看到了作为景观的图像—以往要么是以风光图片、明信片、海报的形式,后来则变成《孤独星球》那样的旅行指南、手册……纪录片自然也是其中的一种。所有这些图像在人们头脑中制造出来的景观,一方面可能制造了某种在场的“虚假意识”,另一方面却激发了真实的欲望—很多人要以此来“按图索骥”。即便原片中并没有提供类似观影指南般的拍摄信息,如今观众仍然可以使用网络的反向搜索功能,找到那个景观的所指。
初代的全球旅行者,和古代的朝圣者不同的是,在他抵达现场的那一个瞬间,首先是将自己头脑中的景观和他正在看到的实景进行比对。这种对比是为了找到那个完美的“打卡点”,按照景观的构图方式拍下一张标准的“打卡照”;再加上美颜和滤镜之后发送到朋友圈,然后等待亲友们的点赞。这样才算是“功德圆满”,赚回了团费和机票。这就是桑塔格所谓的“停下来,拍张照,然后继续走”。因此,“摄影既是一种确证经历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否定经历的方式”(《论摄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景观的标准回报,就是那一声“哇哦”—矫揉造作的惊讶,严丝合缝的惊喜。这似乎成了全球旅行者的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审美中的反向实证主义,即用实景来证实景观,甚至用实景预定情绪。对一些人而言,旅行的目的只不过是去“复刻”一个标准的镜头。这是一种审美的腐败。时下流行的vlog,更尝试是将“我”放置到景观中去,营造一种陌生人的断断续续的凝视感。
 《天地玄黄》剧照
《天地玄黄》剧照按照这种方式,在观看《天地玄黄》时,少部分观众可能无不自豪地说,这个地方我去过;而另一些观众则可能心中发愿说,我要去那个地方,看那样东西。看到景点和景观本无可厚非。
导演弗里克尝试在文化多样性上水平地展开,同时在历史的纵深和绵延上垂直地延伸。因而,我们会在《天地玄黄》中看到第二个层级—即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影片中的很多场景无疑会给人带来强烈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例如印度加尔各答垃圾场里翻垃圾的人。观众立刻会将自己“代入”这样异样场景中—他们为什么要在如此肮脏的垃圾堆里翻垃圾?我会在什么情况下,做出同样的举动?一个印度老妪在恒河浑浊的水中清洗自己的假牙后,将之塞入嘴中。任何文化冲击都会产生一种“反弹”—观看者会不自觉将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的进行比较,并进而反思自己当下生活的合理性。
任何以视觉为主要载体的活动都带有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色彩。眼睛总是在寻找陌生之物,或者说,拍摄行为本身就预设了某种“异域感”。然而,弗里克却是反对东方主义的。如果数一下片中涉及的地点和场景,不免会感到惊讶,他的拍摄点绝大多数在亚非拉,而真正属于“西方”的场景比例很低。甚至你会感觉弗里克在刻意地回避“西方”—真正属于欧洲的镜头屈指可数,例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法国兰斯大教堂。假设有个当代中国的纪录片导演要来拍摄一部类似的影片,他会选取哪些地点和场景呢?可能被拍摄的场景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要看没有被拍摄的场景。
在《时空》中弗里克主要使用的是电子音乐,辅以西洋的管风琴来表现宏大。但是《天地玄黄》的“曲风”为之一变,他使用了大量的东方的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例如尺八、鼓、拉美排箫、佛铃和喇叭等。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影片的配乐迈克尔·斯特恩斯(Michael Stearns),在此不再赘述。
《天地玄黄》提供了审视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视角。当一车间的女工,在印尼爪哇盐仓集团烟草工厂的车间里,用非常简陋的工具手工制造卷烟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当东京地铁车站里的人如潮水般“流出”地铁车厢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而当一群黄色的小鸡在传送带上纷纷掉落,然后被分拣、烫喙、标记上色……你是否感觉到,自身命运和这些小鸡是何其相似。人作为一个有机体被镶嵌到机械的流水线上,成了一个可被替代的“部件”。
 《天地玄黄》剧照
《天地玄黄》剧照弗里克使得观众产生了一种“对熟稔的疏离”。例如,他从摩天大楼的视角俯瞰拍摄纽约派克大街—两侧的大楼仿佛是摩崖石壁,笔直的大街上行驶着的车辆如蝼蚁爬行。这原本是任何一个都市人所熟悉的街道场景,这样一拍却显得异样陌生。人本是街上的一员,抽离出来看,一切皆是如此茫然。将熟悉的对象和场景变得陌生,本身就有一种反省甚至惊醒的意味。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在哪里?芸芸众生是自主地在行走,还是被看不见的手牵动而奔命?
《天地玄黄》还尝试了一种“反叙事”或者叫“非叙事”的手法。在一般的影片,导演总是要通过镜头语言来向观众“講故事”—爱情、战争、科幻、警匪等。故事的核心就是一套叙事。叙事总有内在的逻辑和发展动力。例如,在警匪片中警察找到乃至缉捕真凶就是一个预设的目的。然而,弗里克的纪录片中丝毫找不到任何故事。在《天地玄黄》中,当你观看每一帧画面,都无法预测下一帧画面。因为它没有打算来讲故事。在观看几分钟之后,你就会乖乖地缴械投降,放弃一切预期,因为你已然明白这里没有情节。你要么立马走人,要么耐着性子继续。换言之,在几分钟的观影中,导演就“驯服”了观众,更确切地说,是说服了观众放下了自己头脑中的观影套路。“无意义”的拼贴如同一个镜面,照出了观看者自己的心境。你自己不得不成为意义的创造者。英语中“幻想”(fantasy)的希腊语词根“phantasia”,就来源于“光”(phaos)—看并非一个单纯的被动过程,想与看本是一体同源。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使用视觉,但很少有人想过视觉为何起源。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视觉的高度文明呢?
视觉原本是一项生存手段。我们可能都知道,像青蛙这样的动物对静止对象可能视而不见,而对移动对象(例如一条毛毛虫或者振翅的飞蛾)却有极为敏锐的捕获力。生理学告诉我们,视网膜本身要求有视野的变化才能正常活动。如果你的眼睛持续盯着一个不动的东西(例如墙上的一个斑点)—视网膜接收到一个不变的刺激图形。大约在五分钟之后,这个图像就会忽隐忽现。因为视网膜适应了那些刺激,就停止做出反应了。(卡洛琳·M·布鲁墨《视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人类视觉的这种特性大概也是来源于进化远祖的捕食—狩猎能力。
有一种理论认为,生物体中的视觉基因“PAX-6”起源于植物—一种叫作涡鞭毛藻浮游植物最早进化出来的视紫蛋白(rhodopsin)。植物内部的这种蛋白可以帮助它找到光源进行光合作用。而PAX-6几乎决定了此后地球上每一种视觉动物的视觉能力,或者说有了它,生物才有了感光器官。可以想象的是,有视觉的生物—无论多么初级—要比没有视觉的生物,在生存方面强大很多。
对动物而言,视觉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与想象有关的一种能力,它主要来源于捕食。试想一个远古生物A,它要捕猎一个会移动的对象B。在第一个瞬间T1,A看到了B。然后B按照一定的轨迹逃遁,A的视觉场捕捉到了B的运动轨迹。假设在下一瞬间T2,B恰好进入了A的视觉盲区,例如躲到了一块石头后面。那么一个成功的捕猎者就会假设B会出现在运动轨迹(或者其延长线)上,于是就可以在下一个瞬间T3,尝试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进行搜索,直到再度发现B(瞬间T4)。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捕猎的成功概率。换言之,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捕猎过程中,只有在T1和T4,狩猎者A是真正“看见”了对象B,而在T2和T3,都需要用自己的“想象”(一种大致的预计)来填补视觉的“空白”,例如躲在石头后面的B(也可能不在那里)。这意味着,可能从一开始,视觉和大脑的想象力,即猜测、预计某种并非由感官直接把握的对象,就必须是共生并行的,两者缺一不可。或者说,对于狩猎者A而言,它必须预设在T1看见的对象与T2看见的对象是同一个B,而不是C—也就带有了最为质朴的“同一性”观念。而且即便B短暂地离开了它的视域,例如在石头后面,它并没有消失—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假设,即连续性。反过来,B如果要逃避A的捕食,是否具有视觉能力,也是意味着生死的差别。两者都是大脑的重要功能,也是生物演化的里程碑。
视觉在这种意义上,有别于其他几种感觉(味、嗅、触、听),它所感知的对象可以是“无远弗届”的,甚至是“不在场”的。而由于其他感知能力的物理特性,则要求对象“在场”或至少“在附近”。也可以说,视觉对瞬间变化的捕捉能力是最强的。如果用工程语言来说,视觉的感知刷新率是最高的—捕猎往往就发生在剎那间。上述的这种虚构能力极可能构成了生物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飞跃,蕴含了一种朴素的因果观念,也为人类的其他能力—例如言语和语言—做好了准备,从而打开了通向更为复杂的文化系统(仪式、宗教、哲学、伦理)的大门。
从边沁到福柯,从桑塔格再到布列森,“凝视”(gaze)几乎已经成了从摄影到电影领域中的“老生常谈”。而厄里(John Urry)提出的“观光客的凝视”,其实意味着一种模仿,即效仿狩猎行为,这种凝视和猎人一样是在收集猎物。然而,观光客的凝视其实并非真正的凝视,其目光其实很难在一个对象或场景上长久停留。它包含了一种浅尝辄止的轻浮。这种短暂或者说不愿意停留的目光本身,分分秒秒会背叛“凝视”这个语词本该带有的意涵。
《天地玄黄》尝试恢复本真意义上的凝视,它的很多镜头给出了一种废墟感,而非美感,一种苍凉。很多人在文明的遗址中看到了自己的有限和渺小—拉美西斯神庙中的雕塑依然带有某种神秘的光泽,但是它离开我们已经三千多年了。有些镜头则是极度具有冲击性—印度恒河沿岸的火葬,逝者的头骨在柴堆中逐渐碳化。它表现的并非日常生活,而是一些人生中逃不开却一直在回避的话题,例如生死。
某些镜头又会给人不明觉厉的感受,例如巴厘岛上卡维山圣泉寺的凯卡克舞。原片中没有任何介绍和解释,这个时候观看者只能去“克服”那种视觉冲击,而无从回答心中的疑问—这是什么?或者他们在做什么?无论是好奇还是惊诧,都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加以处理和消化。而当镜头配上了字幕—“卡维山圣泉寺的凯卡克舞”,姑且不论此时语言的逻辑压制了视觉,观影者很容易就被这样一行字打消了自己内心的情绪和体验。文字在这里好像给出了一个回答,其实空洞无物—它提供了一个清单,又是一种不求甚解,回避内心的逃遁之法,它也会阻塞一种本真的可能性。所以我赞同导演的做法,没有字幕,没有旁白。而当画面出现了一行文字之后,人的心绪就被“诱拐”了,不再能够看到舞者面部紧绷的肌肉,以及精细的微表情。弗里克的做法因此是非常违反商业逻辑的,不给出出处和来源,不告知地点和时间,也就是不想成为按图索骥中的那张图。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