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祸乱不断,黄巾造反,十常侍作乱,董卓擅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盖因汉室衰落,诸镇和士族豪强趁势崛起,各以武力争天下。经过二十多年兼并战争,形成魏、蜀、吴三国鼎峙局面。然而,三国的存在只是一个短促的历史过程,前后不过几十年。魏、蜀、吴三国建政与消亡时间分别如下:
曹魏,220年至265年,凡四十六年。
蜀汉,221年至263年,凡四十三年。
东吴,222年至280年,凡五十九年。(按:孙权迟于229年称帝)
据此,三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其时间跨度可以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魏黄初元年,220)献帝禅位、魏文帝曹丕登基算起,迨至东吴天纪四年(晋太康元年,280)末帝孙皓降晋为止。之前蜀汉已亡于曹魏,旋而司马炎以晋代魏,曹魏亦亡。所谓三国,亦即自魏、蜀、吴相续建国到三国归晋这一段,前后六十一年,一个甲子的轮回。这是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给出的定义,今之《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卷)亦持此说。
不过,除去以上六十一年之说,三国的时间界定尚有另外两种方式。
一者是下沿止于晋。根据帝王纪年定义,三国应该从魏文帝曹丕登基算起,至陈留王曹奂咸熙二年禅位、晋武帝司马炎践祚为止,也就是魏黄初元年至晋泰始元年(220-265)这一段。按朝代轮替,汉晋之间这四十六年是三国时期,其下限无须延至东吴灭亡。司马炎以晋代魏后,东吴国祚尚延续十几年,但因地缘格局变化,实际上它只是作为地方割据政权而存在。所以,史家多以魏晋为统绪,这也是《资治通鉴》编年纪事循从的体例。
一者是上沿向前推至汉末黄巾起事。说来有趣,这是小说《三国演义》的叙述时间,即以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为起点,下沿至司马炎灭吴(280),也就是晋太康元年一统中国,前后九十七年。小说家这个叙述时间,实际上是参照《三国志》的历史叙事来确定的。谢钟英《三国大事表》大体亦是这个时间段,只是谢表将起点上推至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并不妥切(前十二年只录入孙坚破妖贼一事)。以纪传体书写的《三国志》虽无明确时间起点,但陈寿显然是在讨伐黄巾这个节点上将汉末诸镇引入叙述,因而后世的史学家们对三国历史亦通常作宽度观察。以中平元年为起点,是以大事件为标识,如曹操、刘备、孙坚、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陶谦、公孙瓒诸纪传,无不追溯到灵帝或十常侍时期的活动。因而,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国,自是包括从征讨黄巾开始的历史过程,迨至魏、蜀、吴建国之前这个时间段,皆在其中。
曹丕受禅登基乃魏国建国之日,但陈寿是以曹操受封魏公作为魏国之初建。《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213)五月丙申,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诏曰:“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同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这里提到所置尚书等职都是魏國之官。如《魏志·钟繇传》“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华歆传》“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王朗传》“魏国初建,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也是指他们在曹操时期的魏国所任之职。曹操作为汉相,实际上抛开了许都的汉廷班列(那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在邺城的魏国署置成了权力中枢。
土地人口(郡县)是立国之本,有了社稷宗庙和官府署置,曹魏俨然已成一国。这时候的魏国,名义上相当于汉初异姓王之封国。刘备作为汉中王时期的蜀汉,孙权受封吴王时期的吴国,亦为诸侯之国,各自政权来源于此,故而史家皆称之“初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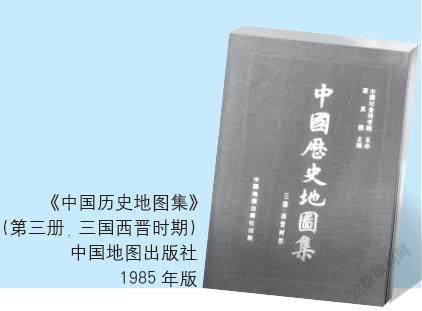
刘备入蜀五年后,于建安二十四年平定汉中,即自封汉中王。《蜀志·先主传》所载蜀汉群臣上表献帝的文告中写道:“臣等辄依旧典,封[刘]备汉中王……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在汉帝被曹魏挟持的特殊情况下,这种臣僚立君的王权授予并非不具合法性。刘备上表说明,这只是国难之际“依假权宜”的办法。他以宗室身份立诸侯国,自然是伸张“祚于汉家”的资格与权利。当年,灭秦后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地就在汉中、巴、蜀诸郡,这是高祖重返关中的龙兴之地,刘备何尝不想复制从汉中出秦川的霸业之途。二十五年,曹丕以魏代汉,取缔了大汉国号。刘备一看母体不存,第二年便赶紧称帝,乃将自家的诸侯国升级为帝国,其年号“章武”。
同样,东吴初建亦在孙权称帝之前。《吴志·吴主传》曰:“自魏文帝践祚,[孙]权使命称藩……”东吴因擒杀关羽怕刘备报复,投靠曹魏自是权宜之计。于是,曹丕策命孙权为吴王。跟曹操、刘备一样,孙权也是以藩王立国。但是曹魏的绥靖之策并未笼络住东吴,孙权作为魏国之藩国,却不用曹魏纪年,一开始它就有自已的年号,曰“黄武”。东吴占据荆、扬二州之大部,以及整个交州,本来就有自己的地盘和署置,国家实体已在,所以吴国的历史就从黄武元年(222)算起。这一年是魏黄初三年,蜀章武二年。但孙权七年之后才做皇帝,改用“黄龙”年号。
陈寿撰《三国志》,面对三国鼎峙的格局,分别作《魏书》《蜀书》《吴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初版)书前“出版说明”介绍说,这三部分在宋以前曾是独立流传,南宋以后的刻本才合为一史。其根据是《旧唐书·经籍志》将《魏书》归入正史类,而《蜀书》《吴书》则另入编年类,可见是三书而非一种。不过,仅据唐志很难说之前魏、蜀、吴一直是“各自为书”,更早的《隋书·经籍志》正史类所著录“《三国志》六十五卷”,显然是三书合为一体的本子(卷帙跟今之传本相同)。但不管《三国志》原是一史还是三书,它所叙述的魏、蜀、吴三国,是在共时态架构内不相统摄的三个主体。
陈寿做《三国志》,着眼于兴替轨迹,其叙史意态和手法表现出左右兼顾的暧昧特点。就是一方面承认分裂时期的政体国体,各述其事,不作简单的正邪之辨;另一方面并不掩饰其倾向性,乃将曹魏奉为正统,试图体现历史演化的某种目的性。可谓“笔则笔,削则削”,自有其春秋笔法。不过,在陈寿之前,做曹魏历史的有王沈《魏书》、鱼豢《魏略》数种,东吴则有韦曜《吴书》,唯独蜀汉无史。陈寿撰史自然是利用了魏国、吴国那些史乘的基本材料,只有蜀汉史料是他自己采集。有一点不能不说到,史料亦是语料,利用人家的文本或素材,亦难免带有那些史官各自表述的意况。
陈寿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魏书》内容最多,是因为魏国幅员辽阔,人事广众;尤其陈氏以曹魏为正统,叙事愈求详尽,客观上可取用的材料亦多。除此,《魏书》还给一些既非魏国官员亦非曹营人物设传,如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臧洪、陶谦、公孙瓒之类。作为汉末诸镇,他们或曾与曹操处于敌对状态。将这类人物置于其中,体例上相当不谐。故刘知幾讥曰:“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史通·断限》)陈寿这样处理,无非是因为曹魏建国乃所谓“以魏代汉”,法理上继承了前朝的一切,所以只能将那些汉末方镇归置于魏。
当然,刘备亦以宗室血脉主张承祧汉室的权利,只是历史未予蜀汉这份资格。蜀汉的正式国号就是“汉”(承绪两汉之“汉”),陈寿以“蜀”名之,就是褫夺其继承权。其实,《蜀书》亦收入若干汉末人物,譬如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入蜀前他们父子先后为州牧,虽说与刘备同属汉宗室,但二人与蜀地之“汉”并无半点关系,刘备取益州乃鸠占鹊巢,最终靠武力打进来,将刘二牧塞到这儿大概算是“属地管辖”。
至于《吴书》,开卷《孙破虏讨逆传》也是两位汉末人物,乃孙权父兄孙坚和孙策,是他们父子奠立了东吴基业,置于卷首自是顺理成章。但《吴书》亦有乱开户头的问题,孙权和三位嗣主传以下便是刘繇本传,这有点类似《蜀书》按地域归置的做法。献帝兴平中,刘繇为扬州牧,与袁术、孙策争夺地盘,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后来成为东吴疆域的那些地方。这样一个本非孙氏集团人物,按说亦应于《魏书》设传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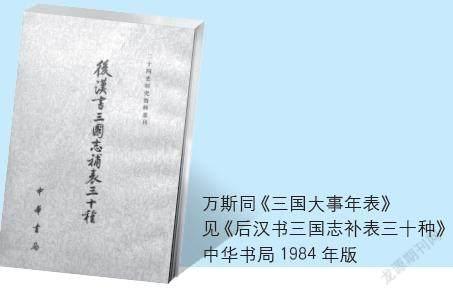
《三国志》体例不是必须讨论的大问题,三国史叙事框架很难找到一种合理体式,陈寿的处置实是勉为其难。清人牛运震批评陈寿多有吹毛求疵之语,其谓“卓、表、二袁等皆属汉季群雄,应入后汉,不得属之三国”(《读史纠谬》卷四),他只考虑体例整饬,实是割裂了叙史脉络。三国的历史首先是三国之前那些人物所创造,若是撇开那些汉末人物,说不清三分天下的局面是怎么来的。从黄巾作乱到三国归晋,是一个持续兼并和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就三国史而言,被转述的历史存在乃史家眼里的王道之轨,而非一个王朝的故事。
所以,三国的人与事,实际上涉及三朝。其上端包含了东汉灵帝以来的主要史实,而献帝在位的三十三年尽在其中;下端则兼容晋朝开国之初的十六年,其间活跃着一大堆由魏入晋的人物,如羊祜、杜预、卫瓘、贾充、王濬、阮籍、嵇康,等等。当然,还有晋武帝司马炎,还有司马炎追谥的宣(懿)、景(师)、文(昭)三帝,亦在故事之中。
不到百年的三国,实是折叠了汉末与晋初,两头跨界正好占了一半。
三国之学形成于清代。学者著文引用《三国志》魏、蜀、吴三书,渐而形成一种规矩,不作“魏书”“蜀书”“吴书”,概称“魏志”“蜀志”“吴志”。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劄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提到三书就各称某志。周一清《三国志补注》卷一至卷五标目犹作“魏书”,卷六以下改称“魏志”“蜀志”“吴志”。潘眉《三国志考证》目录列魏蜀吴三书,行文皆称“志”。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则是“魏书”“魏志”混着用。至于近世以来,皆称各“志”,而不以“书”名。
清人周中孚对此颇为不解,乃谓:“三国志,大名也;魏书、蜀书、吴书,小名也。《蜀书·杨戏传》云:‘戏以延熙四年著《季汉辅臣赞》,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又,《董允传》注,论陈氏立《夏侯玄传》,亦曰‘《魏书》总名此卷云《诸夏侯曹传》’。此其证也。但自来引者,俱曰魏志、蜀志、吴志,岂因大名而改称欤?”(《郑堂札记》卷五)(按:其谓“《董允传》注”,实为该传所附《陈袛传》裴松之注。)文中所举二例,用以证明陈寿原著和裴注引其书名是“书”而不是“志”。作为目录学家,周氏亦竟疑惑,以为“小名”跟从“大名”而改。
其实,晋宋之时已有改称某“书”为某“志”之例。如《武帝纪》建安十三年,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云云。又如《先主传》“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语下有裴松之案:“《魏书》(按,指王沈《魏书》)载刘备与孙权语,与《蜀志》述诸葛亮与权语正同……”但事实上,裴松之注释中“书”和“志”两种写法都有。其曰“书”者,尚不止周中孚所举二例,如《吴志·鲁肃传》裴注辨刘备、孙权连横之计所出,亦有“《蜀书》亮傳云……”之语。
学人文章里改“书”为“志”,大抵有一个好处,可以避免《三国志》之《魏书》《吴书》与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相重名而造成混淆(当然,还有二十四史中关于北魏的《魏书》)。但是避免了与他书相混,却将目录学家搞糊涂了,以为是行内切口。

不妨指出,《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国志》,分作三书,书名各是《魏国志》《蜀国志》《吴国志》。这是其“各自为书”时期的书名,而“魏志”“蜀志”“吴志”或是其简称,倒未必是“小名”跟从“大名”而改。
书名歧出的源头或来自书坊,旧时《三国志》某些版本亦作“魏志”“蜀志”“吴志”之目,如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即是。但因金陵书局同治覆刻本(简称“局本”)改作“魏书”“蜀书”“吴书”,又延至中华书局标点本。
陈寿撰《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虽说不尽合理,体例上亦显得别扭,却代表了某种构想性的叙事意图,就是企图寻找一种统辖性的历史存在。三国故事前有曹丕以魏代汉,后有司马氏以晋代魏,在他眼里,汉—魏—晋,连成一条线,就是一个实体。
秦汉时期形成的大一统局面是可以产生多种解释的历史记忆,从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帝国的专制已是无远弗届。但另一方面,用钱穆的话来说,那正是“国家民族之抟成”(《国史大纲》第三编第七章)。这种“抟成”,核心是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框架,将春秋战国以来裂土分封的贵族专制改造为具有行政意义的郡县制度,这样政治上似乎就顺理成章地纳入儒家先贤设计的礼治之道。可是东汉末年的乱局打破了这种大一统,士族豪强以武力纷争,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战国以前的局面。顾炎武称战国时期“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时期亦是如此。不必说反复无常的吕布,就连刘备也是今儿挂靠曹操,明儿投奔袁绍,跟吕布好过又闹掰。战事纷纭之际,亦是政治伦理混乱时期。陈寿以曹魏为正统,显然是基于以魏替汉这样一个事实,自然将王朝兴替作为合法性的历史演化轨迹,成王败寇即是政治正确的伦理逻辑。所以,他极赞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魏志·武帝纪》评曰)。
在陈寿眼里,重要的是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没有具体的“国家”观念。或者说,他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宗庙社稷之类。譬如,他一再记述曹魏诸帝庙祭之事,而蜀汉、东吴这方面的缺失无疑道出草创之国的寒怆与简陋。
《魏志》有一个重要缺省,就是少了司马懿、师、昭、炎祖孙四人的列传。陈寿不予司马氏祖孙设传,乃是避讳之故。因司马炎受禅做了皇帝,尊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其父司马昭为“文皇帝”,一家子都搞成皇帝麻烦就大了。虽说宣、景、文皆虚号,亦奉祀于宗庙。陈寿以晋臣身份撰史不能无视那些牌位—若置于列传,无法避其名讳,干脆作缺省。以后唐人撰《晋书》,在武帝司马炎之前,专列宣、景、文三帝纪,都是正经按皇帝规格来供奉。
不做司马氏祖孙四人列传,给读者造成极大不便,要了解他们的事略,只能到《三国志》相关纪传中去搜寻。因为避讳,其中自然不是直书其名,如司马懿尊称“司马宣王”或“宣王”,凡提到他的地方都这样变通处理,这是提前给人加封。大概陈寿自己也觉着这么称呼未免别扭,所以《武帝纪》是从头到尾不提司马懿。司马懿是曹操早年亲自收罗的人才,曹为丞相后他就是掾属(见《晋书·宣帝纪》),若先以“宣王”名之,实在不成体统。《魏志》最早提到司马懿是在《文帝纪》末尾,也就是曹丕临死前,诏命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等人共辅嗣主。在曹魏政权中,之前不曾露面的“司马宣王”,一出场就进入了权力核心,成了顾命大臣,给人感觉十分唐突。

当然,这事情不能全怪陈寿。史家对本朝皇帝的避讳,自《史记》《汉书》已成定例,如太史公作《孝武本纪》,称汉武帝为“今上”或“上”,亦或“今天子”。说来史汉二书有其幸运之处,就是没碰上司马懿祖孙这类前朝为臣本朝为帝的主儿,毋须多重避讳,从而避免了此等缺漏。当然,那是因为司马迁、班固未曾身历二朝。
但不管怎么说,陈寿不设司马氏诸传,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其后范晔撰《后汉书》就不列曹操传。曹操亦虚名皇帝,被他做了皇帝的儿子曹丕尊为“武皇帝”。范晔是南朝宋人,跟曹魏还隔着两晋,其实犯不着这么小心从事。不过,《后汉书》董卓、袁绍、刘表诸传中倒是直书曹操名字,这是仿照太史公作《秦始皇本纪》的做法。因为是前朝,太史公直截道出始皇帝名为政,二世名胡亥。但范晔只会照搬成例,至于如何处理后来被追封为帝王的人物,《史记》没有现成样板,他便照着陈寿避讳司马諸帝的做法,干脆绕开曹操。
之后,这种避讳自是成了史官家法。唐人令狐德棻撰《周书》,魏征撰《隋书》,都未给李渊立传。宋代薛居正、欧阳询做新旧《五代史》,亦不做赵匡胤传。所谓断代史,就这样隐去若干重要的当事人和许多历史细节。避席畏闻文字狱,史家岂敢不玩历史虚无主义。
《三国志》无志表,有关三国地理情形,可资参考的文献首先是《续汉书·郡国志》和《宋书·州郡志》,其次是郦道元《水经注》,以及《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几部著名地志记述州郡沿革的内容。
司马彪《续汉书》纪传已佚(今存清人汪文台辑本),今存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等八志,保存于范晔《后汉书》。范书本无志,南朝梁人刘昭注书时用《续汉书》八志补入,宋代以后这八志就与《后汉书》合刊为一书,得以流传至今。其《郡国志》,仿照《汉书·地理志》体例,“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尤其录入东汉以来之郡县分合变异,比较接近三国时期实际情况。司马彪是西晋史家(晋宗室,司马懿侄孙),他记述汉末诸镇事况的《九州春秋》(亦佚)多为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因其生活年代距离汉末三国不远,《郡国志》对于三国政区地理自是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而且,刘昭的注释补充了原文未详之处,故此志常为学者考证援用。但后世著述者引书亦常有舛误,如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引用此志每每误作“《后汉书·郡国志》”。
《郡国志》说的是三国之前,而《州郡志》所载则是三国以后。沈约撰《宋书》是在南朝齐梁之间,与三国隔了晋宋两代,加之南北朝分治,政区变化很大。不过,《宋书》各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尽可能将每一种典章制度追溯到两汉之前,而《州郡志》对三国时期郡县政区沿革皆有载录,这一点对读史者特别有用。譬如,扬州吴郡诸县,三国吴多有更名或析置,此志说明甚详:
嘉兴令,此地本名长水,秦改曰由拳。吴孙权黄龙四年,由拳县生嘉禾,改曰禾兴。孙皓父名和,又改名曰嘉兴。
富阳令,汉旧县。本曰富春。孙权黄武四年,以为东安郡。七年,省(按,即撤消)。晋简文郑太后讳“春”,孝武改曰富阳。
桐庐令,吴分富春立。
新城令,浙江西南名為桐溪,吴立为新城县,后并桐庐。
……
三国魏蜀吴三方都曾于荆州建制,以致郡县改易频数。如宜都之立,《州郡志》参互晋宋地理文献,梳理如下:
宜都太守,《太康地志》(按:即《晋太康三年地记》)、王隐《地道》(按:指王隐所撰《晋书地道记》)、何志(按:并指何承天、徐爰所撰《宋史·州郡志》)并云吴分南郡立,张勃《吴录》云刘备立。按《吴志》,吕蒙平南郡,据江陵,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县。初,[孙]权与刘备分荆州,而南郡属备,则是备分南郡立宜都,非吴立也。习凿齿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刘备改为宜都。
曹操析南郡置临江郡,刘备改临江为宜都,《武帝纪》《先主传》均不载,《州郡志》综核诸家之说以补史阙。
魏蜀吴三国号称三足鼎立,其实土地人口相差很大。曹魏幅员辽阔,长江以北,辽东至西域,皆是其国土;据有司、幽、冀、青、徐、兖、豫、并、雍、凉十个州,以及荆、扬二州之北部,还有西域长史府所辖地域。蜀汉仅得益州,包括今之云南、贵州和四川大部,甘肃、陕西一部分,以及缅甸北部地区,但以一州而论,其面积甚广。东吴占有荆、扬二州大部,以及整个交州;长江以南中东部地区尽在其版图中,包括今之两湖、江浙至闽粤,并延及越南中部。三国疆域具体划界,可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时期)。总之,以国土和人口寡众比较,魏国体量最巨,吴次之,蜀最小。不过,如果不计入魏之西域长史府,仅以州郡论其面积,三者相差不算太悬殊,只是人口呈梯度差距(三国人口问题颇为复杂,古今学者都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然而,三国鼎峙局面终究维持了四十余年,地理和地缘因素不可忽视。

魏蜀两国以秦岭为屏障,尽管诸葛亮、姜维不断越境北伐,终是寸土未得,而直到邓艾、钟会入蜀之前,两国边境没有明显变化。魏吴之间有长江天堑阻隔,但东吴地盘不尽于长江以南,它在荆、扬二州江北占有数郡,构成西南—东北走向的狭长缓冲区。这片江北(西)领土倒是曹操拱手相让,《吴主传》谓:赤壁之战后,“曹公恐江滨郡县为(孙)权所略,征令内迁。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按:指建业以西至皖口一段)遂虚”。又,《宋书·州郡志》亦谓:“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东吴以江北(西)为营,屡出濡须口向巢湖、合肥方向进攻,但终而未能蚕食魏国地盘。三国之中,曹魏实力虽强,自建国以后,却较少主动出击蜀汉和东吴,这也是三国边境大致不变的原因之一。
疆界变化最大之处在于蜀吴边境,具体说就是荆州。赤壁之战后,刘备掌握大半个荆州,后来因东吴讨要,让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建安二十四年(219)秋,蜀汉初建,其时尚据有洞庭及湘水以西部分。是年冬,东吴擒杀关羽,蜀汉所占荆州土地尽皆丧失。
魏晋南北朝文献中多有“州家”(州牧或刺史)“台家”(指尚书台,犹言政府)“军家”之称,与署置、职事相连缀的“家”字,表示与前词关联之主人。按这般组词,“国家”一词无疑指国君。周一良《三国志札记》有“家”之一条,曰:“古代言国家者,国指诸侯,家指大夫。东汉称天子曰国家……皇帝之称为国家,家字与台家、军家之家用法相同。”又曰:“魏晋沿袭后汉旧习,亦称皇帝为国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周先生举述《三国志》及裴注引文所用“国家”数例,并为说明:

《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国家指汉皇帝,非谓中国。
又,《庞德传》,“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王凌传》注引《魏略》,“太傅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国家皆指魏帝。
《吴志·鲁肃传》,“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此自国家事。”国家皆指吴主。
其实,《三国志》使用“国家”一词不太多。这里尚可补充几例—
《魏志·刘表传》,刘表死后,傅巽劝说刘琮归顺曹操,有谓:“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此处国家所指比较暧昧,字面上意思是汉帝(事在建安十三年,其时曹操尚未封魏公、魏王),但献帝既为曹操所挟持,自然实指曹操。
又,《崔琰传》裴注引《续汉书》,曹操欲诛太尉杨彪,孔融去说情,曹操推说是“国家之意也”,这当然也是曹操的旨意,但字面上国家仍指献帝。
再有《蜀志·马超传》,杨阜对曹操说,倘若放过马超,“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这是建安十六年,曹操尚为丞相,国家亦当指天子。
不过,亦有例外。《武帝纪》建安十八年,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诏书大赞其功德,有“俾我国家,拯于危坠”之语。国家一词,这里不是献帝自谓,应作社稷、宗庙之义。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