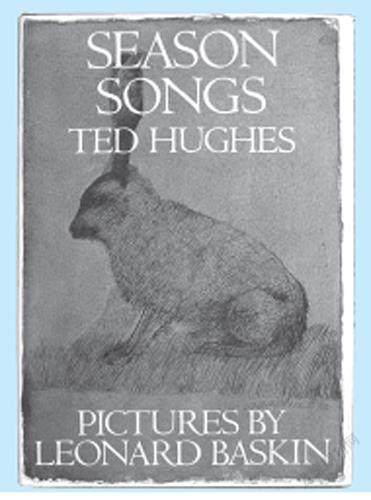
轻轻一声轰响,它们将你卷入
其精神失常,汇聚起一个逃出生天的摩天轮
噩梦—尼亚加拉瀑布
扇动着上举的轰鸣双翼—复归坍塌
地球上的多数宜居环境中,都有鲜明的四季轮转。古人观星,发现北斗七星斗柄指向依时有别,遂将四季更替称为斗转星移;现代人认定,地球绕日公转致太阳在南北回归线间的往返移动形成春夏秋冬。全球随季节流转的物候、气候变化规律,乃是地球生灵所能感受到的最直接、最根本、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动植物、鸟类、昆虫、水文、气象在气候的种种条件变化中,度过自己的四季,有生之欢欣,成长之苦恼,变形之令人惊异,死亡之无从规避。
在特德·休斯(Ted Hughes)的《季节之歌》(Season Songs)中,首先来到世间的是三月里降生的小牛犊,一个光闪闪的造物,可人得就像电影里的小爵爷方特洛伊,他从一开始就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他的黑块块,他的白片片”,“在他短小利落的形象中闪闪发亮”。然而,生之美好、成长之茁壮、竞争性的顽强生命意志,无时无刻不随身携带着生物自身的死亡趋向;最可悲的是其社会性,养牛的产业,“他的整个种系”,都是“被缚牢”在产奶场和屠宰场的大机器上的。
悲剧性的归宿既已锁定,该如何度过步入屠宰场之前的有生之涯?被屠宰的牲畜,是《季节之歌》中不时出现的主题之一,也是人类役使自然的象征。在当代生活中,没有了古人为平衡捕猎、食用动物而进行的献祭程序,缺少了这精神性关联,食用菜畜变得天经地义。这使得人作为地球主宰者存在的同时,也切断了自己从自然生物界而来的血脉根源,是人类精神性本体种种“断根而亡”的表现之一。
休斯总是在诗歌中反复强调当代人类处境的这一悲剧性,在儿童诗中他也从不回避它的残酷。因为对他来说,儿童并不缺乏理解力。他对待儿童的态度,是既不屈尊俯就,设定他们只能领会明亮、美丽、幼稚、小清新;也不把他们当作微缩小大人,他们是“儿童是成人之父”意义上的儿童,对所有来到自己面前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儿童的感受力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大人学习。他们看事物往往会像剥去皇帝的新装那样毫不留情,成人则因经验所致的心理防御系统而失去了这种直接性。
《季节之歌》也常常不被当作儿童诗看待,原因之一在于休斯使用的是儿童和成人(体内的那个儿童)可以共享的通用语言—在爱的直接交流中呈现的“意象和感知觉的某些波长”。这一波长区域的捕获是休斯儿童诗歌大获成功,被儿童、成人广泛接受的基础。
三月在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一条三月里的河,此时正是她走过枯冬的寒碜破败,生机乍现的时候。从形销骨立的贫瘠中走出的丰肥河流溢出“一窖藏不住的鳞茎毛茛”,像一头纯银的母猪般的鲑鱼……其新生的蓬勃势能仿佛是微服巡游的“大海之大能陛下”。冬春之对立、死生之冰炭,自然法则以一条河流的嬗替戏剧年年巡演。
既是因季节之冬,更是因人类的无情滥用而致“病弱已久”的地球,在三月的手术过后,在阳光的灌注滋养中,让人宽慰“她不会死了”(《三月的清早与众不同》)。休斯在看似绝望的事物中找到他的关注主题,在死生交替的双声部韵律中定下春之基调。这一基调也是休斯四季之声的基调,是他所有自然诗歌、动物诗歌的基调:自然,是永恒的生与死的角力场;生之欣悦、死之悲悯的张力阈是心灵剧场里恒常不灭的纯诗。
四月的第一天,看上去和冬天里一样光秃的橡树,突然间就彻底不同了。全部的春之生命活力已在枝丫间呼之欲出,整个橡树,带着在休斯灵魂中的凯尔特古老神圣性,成为他眼中蕴蓄着“无形强光”的一枚“隐形的太阳”。如果说不是人人都能感觉到这些内在于橡树的强大生命光芒的触碰,那么当春天的特快列车呼啸而过,少女怀春般为他守候着的橡树满树叶片的“脸红和骚动”,则是当事人、过来人都能会心一笑的妙喻。(《骗局》)
四月是世界的生日,大自然赐予礼物的季节,万物在此时更生,连民族自豪感此时都参与到新生之春的合奏中,日后的“英国桂冠诗人”休斯始终以儿童“诗教”为己任,在不落痕迹中让它随春风化育:
……一阵风潮、骚动
腾卷南方
那光亮如银的
紫罗兰丝绸—那是自英格兰
所有文雅哺育的
郡中世家提升起的
一派温柔。
然而更重要的诗性化育,无疑是对儿童想象力的培养,使他们学会保持创造力的流动与鲜活。紧随上节之后的春天,便是喧闹孩子撒欢般脱了缰的春天:
当燕子剪断约束住世界的弦索
斑尾林鸽拍打翅膀几乎翻着跟头飞行
你只是无法点数紧随其后混乱中的万物
像整个马戏团随着铁环满地翻滚
这股生气进入到了夏天,就难免更冲动、奔放、热烈、丰饶。有“以数以百万计的他之赠礼”“令富饶的夏季大海/再富裕一百萬倍”的鲭鱼,有在爱欲驱动下如被魔力附身的神庙舞者一般的鸽子,有像只燕子一样轻盈、到处翻飞、工作了整整一夏天的夏之本身,有收获时节向地球航来的火红满月“获月”令虔诚的人们去榆树和橡树林中跪伏夜祷……夏之生气,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休斯当作夏之精灵来描写的雨燕身上:
掠过院中的石头,它们迸发出
弹片四射的恐怖。咧着青蛙般大嘴,
戴着高速路护目镜,国际盗匪们—
在三四股铁丝般尖叫拧成的套牛绳上
相互交错争先
在它们死亡的飞车道上180°打轮急转。
它们猛击飞过,箭羽刚硬,
在凛冽空气中顺风转向,在房顶上空上下翻飞。
然后再次消失。它们冲飞的劳作余天空一点黑痣,
它们极端的、轻捷急停的疯狂
还有它们旋转的刀片翼翅
迸射进碧空,星点闪耀—
不再是我们的了。
被这般描写的雨燕在一个没有雨燕知识的人看来,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心里还免不了嘀咕,一只鸟儿,至于这么彪悍吗!不幸的是,作为译者和笔者的我,就正是缺乏这一知识的未曾见过雨燕的一代城市居民,所以这一段的翻译对我而言,是整书中最难处理的几处之一,因为知识储备不够。休斯熟悉的雨燕、鲭鱼、三文鱼、椋鸟等的禀赋习性,以及他亲历农场生活对马牛羊等的亲近了解,都不在我的知识系统之内,这使得常常是理解的困难超过了语言表面的困难,语言从来传达不了你不能真正理解的事物。
于是我暂停翻译,先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搜读、观看各种关于雨燕的知识、视频。这才惊异地发现,这种叫声尖锐刺耳、翅膀如同镰刀的鸟类是地球上的鸟族飞行冠军之一。它之所以俗名“swift”(疾速的),正是因为它的特性:不停息地在空中快速盘旋、飞翔,几乎从不落到地面或植被上,有许多雨燕甚至在空中过夜,这也是为什么在《捕猎夏天》中,诗人写它“边睡边飞”。雨燕属的学名,来自希腊语的“Apus”,意义亦是“没有脚的鸟”。古人命名事物多是仓颉造字式的“观鸟迹虫文”而后落于心理感受。雨燕属中的褐雨燕飞行时速最高可达352.5公里/小时,相当于一架低速飞行的飞机。知此再看休斯诗歌,将可以和飞机比比速度的鸟类比作垂直线上的疯狂飙车族,只能说一点也不过分—F1赛车在人造地面上也只能突破400公里/小时。如果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理解,译到该诗最后,恐怕也联想不到,诗人将那只未能起飞便坠毁了的新生雨燕比作“我的小小阿波罗”。这个貌似漫漶的比喻,其实非常切情切景,诗人用作暗喻的是在测试时于地面上发生事故炸毁的“阿波罗1号”飞船,故而此处当译作“我的小小阿波罗号”。
休斯果真是一位悉心感悟自然生物的诗歌导师,一位巫灵式的长于接通生物内在生命力量的诗人。翻译《季节之歌》,于我而言,也是一趟跟随休斯学习自然生灵的诗性之旅,补上在童年时代缺少的一课。
在《季节之歌》中,于春天,休斯处理的是重生及其艰难性的主题;夏天,是实现春之丰饶、收获和达至其最大值的主题;秋天,是自然的衰败和腐化;冬天,面对的是自然的沉寂和存在物的消亡。
休斯季节诗的写作开始于一九六八年,最初是为白金汉郡奇尔特恩区小米森登村(Little Missenden)有古老传统的秋收丰年祭(Harvest Festival)活动而写的五首秋季歌,五首诗集结发表时都以第一行诗代题目,分别是后来的《树叶》《七愁》《保卫者》《某天来临》《雄鹿》。
这里再就版本问题交代几句。在英国,《季节之歌》由费伯出版社先后出过三版:一九七六、一九八五、二○一九年版。本中文版的翻译是依照费伯社二○一九年版加上此前出现在《春夏秋冬》和第一版中的《捕猎夏天》《保卫者》《雄鹿》《两匹马:1-5》四首诗,因而本中文版收诗三十七首。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新年始于秋季,一日始于黄昏,休斯的季节歌写作实际上也是始于秋季,始于《树叶》一诗。这首诗可以说是整本诗集的由来。最初写出来为孩子们在节庆活动中演唱的《树叶》一诗改编自儿歌《谁杀了公鸡罗宾?》(Who Killed Cock Robin?)。这首英国儿歌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最初收录于一七四四年出版的《大拇指汤米好听歌曲集》(Tommy Thumb’s Pretty Song Book),一本大小适合于儿童手握的漂亮小书。
公鸡罗宾是谁(一说是知更鸟),原型儿歌的意义是什么,已然失落于历史的烟尘,被笼罩在了神秘当中。但是“谁杀死了树叶?/我,苹果说,我把它们全杀了”。这样的来回往复、一问一答的结构,显然是完全保留了原型诗的结构要素,“谁杀了公鸡罗宾?/我,麻雀说,/用我的弓和箭,我杀死了公鸡罗宾”。《树叶》也保留了原型诗中大多数的提问,或只稍作改动,“谁来接住它们的血?”“谁来织它们的裹尸布?”“谁来给它们挖坟墓?”“谁来给它们当牧师?”“谁来做主祭?”“谁来抬棺?”“谁来唱赞美诗?”“谁来敲响丧钟?”并且为提示新作所受到的原作影响,最后由知更鸟(罗宾)来敲响丧钟。
除了《树叶》一诗有显而易见的儿歌来源,《金色男孩》有约翰·巴利科恩(John Barleycorn)的神话来源,《秋日自然笔记·3》中核桃追求成长为另一棵树的过程采用了童话形式,《季节之歌》里的多数诗歌,并没有体现休斯惯于使用神话、创造神话的诗歌雄心。这个阶段的儿童诗写作,对休斯来说,是在完成对抗上帝的《乌鸦》(凭此休斯成了一位大诗人)之后一个精神状态相对放松的时期。如他在《树叶》中所暗示:“谁来给它们当牧师?/我,乌鸦说,因为众所周知/我研究《圣经》彻底之至。”休斯徜徉在田野、农场、院落、房舍周围,将自己沉浸于更新自然感受、重获养分之中,同时也更新着自己的诗歌语言。所以,尽管这本诗集属于儿童诗范畴,语言难度却明显高于《乌鸦》,隐晦的修辞和巧妙的措辞每每令译者绞尽脑汁,以期获得在汉语中可以被当作诗来接受的传达。当然整本诗集在节奏、用韵等很多听觉设计上,休斯追求的效果是“在儿童的听觉范围之内”,很多歌谣模式和韵脚鲜明的诗在召唤英语读者将其大声朗读出来。比如《某天来临》的重复诗节和复沓用韵。这方面诗歌要素的传递,恰是翻译之天然所短,翻译永远只能是照顾“意义”在先,声音考虑在后,声音要素只能依从译入语的条件而定。凑韵译出的诗作几乎无一不是失败之作。
因为文化的异质性,中国读者可能对约翰·巴利科恩未必了解,这里也略作一介绍。这个人名是“约翰+大麦粒”的意思,约翰是英语中拟人化时的通用名字,就像德国人的汉斯;长期以来,大麦粒都是麦芽酒的关键成分,可以说,没有大麦粒就没有低度啤酒和苏格兰威士忌,所以,巴利科恩可以是酒精的委婉语。苏格兰大诗人罗伯特·彭斯于一七八二年写有《约翰·巴利科恩:一首谣曲》,通篇把大麦的生长全程作了擬人化的描写,生之维艰和人对之的杀戮尽用充满了斗争的残酷性。彭斯的创作对巴利科恩形象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采用的故事是本来就有的民间传说,早于他创作一百五十年前,这个名字就已经进入英语方言为人所知。后来,在杰克·伦敦的小说、史蒂芬·温伍德的歌词,以及休斯的《金色男孩》等不断出现的文学再创作中,共同的主人公约翰·巴利科恩,都隐喻、强化着大麦种植、生长、收获和酒精蒸馏的循环及其性质中所具有的愤慨、痛苦、死亡和重生主题。可以说,历经磨难而顽强不息的约翰·巴利科恩形象是一万两千年人类的大麦种植历程在英语文化中结出的一颗文学象征宝石。
休斯在秋季诗篇的最后《大麦》一诗中,再写大麦,将其作了女性王国的比拟,咏赞了这些“受雇于大地,受雇于天空,/受雇于大麦,成其为大麦”的女王们是如何度过严冬、劬劳生长、威武成熟传承下整个大麦王国的。丰收、胜利的图景,是天地间的一场浩大舞蹈:
她们就这样赢得了她们的王国。
然后她们穿戴金甲,准备加冕。
每一位都带刺、披羽,如一支柔美的武器,
戴上她之王国的王冠。
然后全部女王们的遍布田地
回旋在一场舞蹈中
和她们看不见的舞伴,风
天地间一个独舞者。
大麦就是这样传承下了大麦王国。
作为休斯复杂性程度最高的儿童诗,《季节之歌》的意象系统、音步韵脚韵律体系都相对更追求精准,具有脚踩大地、扎根于地球特性和人类生活的特点;不像他其他的儿童诗集,有的更追求文字游戏的快乐狂欢,有的着力于创造更为异想天开的出奇意象。因而这本诗集中的很多动植物形象、季候特征、人的行动场景都具有精神延展性,深入开掘了场景可能的和内在的精神本质。
如他的《秋日自然笔记·5》,诗中场景无非是诗人在苹果树下烧一本快照相册。在这一场对某个不再有价值的东西施行的简单火葬中,诗人执一根树枝,面对过火的相簿册页,“灼照的眩晕中,我劝诱它顽固的羽毛”。在他身后的深秋果园,大自然的背景里“所有能够逃离的事物,现在安静地迁徙”。当诗人看着燃烧的相册“焦黑皱缩/成灰白的飘落。簇聚之物的核心过火硬化”,很自然地便生发出哲思“万物//都需经此。每一粒子/及其闪现。万物必定离去”。在照相镜头般扫过火中的自然场景后,最后的特写是“一只惊慌的乌鸫,精瘦、警觉,数落/到处缓慢的曝光起底—逃离,归来”。人及其行动完全地融合在以相机镜头效果记录、感知、衍伸、开拓出的季节肃杀收尾戏剧中,一首以火葬为象征形式的关于消逝的哀歌。
《秋季自然笔记·4》是我作为诗人最佩服的休斯季节诗章之一。作为一个诗人,意味着首先你的感知觉系统是与众不同的,凭此你加速造化、放缓神明、变形万物、创造出另一个世界。当这个新世界与原生世界的千丝万缕关联能被人一眼看出,你会成为一个可以深入人心的艺术家,如果不容易看出,你的传播会受到局限。休斯这首诗的前三节堪称是艺术家感受力工作的杰作,很少有人能感知到一棵在风中起伏的繁茂榆树“周身的饱满绷紧嗡嗡如鸣”,更少人能感受到此时的榆树“如一艘风帆悉张的航船”;而当这个诗人的沉重感受进入物我合一、大海地球合一的恍惚幻境:
因为大海是一艘航船的根
因此地球也是我的根。
当树身的膨隆(海浪的翻涌)从榆树顶托起乌鸦
树干和桅杆都是我的家,它们摇晃我,它们提供我给养。
你知道他有幸遇到了神来之笔,这是真正的来自无意识能量的灵感在工作,因而诗句会有一定的不确解处,这属于真正的诗之神秘。作为诗人,你也会知道,你有幸获得这种诗的时刻,太少太少。括号中的增译是为了体现休斯一语写双意的能力,不增此,你在漢语里不会感受到他感受到了什么。诗歌翻译,首先在于深入透辟的“理解”,包括理解诗人心灵的创作机制和创作过程。这一理解,高于理解字面语言本身。
休斯的诗歌通常让人感觉到它们被一种不停息的、急迫的能量所驱策,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诗人对“想象”运作的倚重,这是他衡量人是否具有积极的内在生命的一个标杆。诗人常常予以谴责的是科学“准确记录事实”的做派已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技术化时代人类的心灵充满了内在的怠惰和对世界的疏离。人作为生物性的精神存在,必须以其内在活跃性去实现与世界的创造性相遇,否则便是错过今生。这种“想象”运作结出的硕果有时是极度震撼的,如在描绘以铺天盖地的群飞为特色的椋鸟中(《椋鸟驾到》):
现在是群情沸腾跳蚤的特写。
现在是一阵寂静—
末日恐慌的这群谛听了一瞬。
然后,轻轻一声轰响,它们将你卷入
其精神失常,汇聚起一个逃出生天的摩天轮
噩梦—尼亚加拉瀑布
扇动着上举的轰鸣双翼—复归坍塌
于神经质的原子们
无法操控的重量。
只有大力神般的诗人,才能以其想象之力举起神经质的群飞椋鸟创造的摩天轮噩梦—在双翼上举的同时又坍塌下落的一匹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不是椋鸟的奥秘,而是心灵遇合椋鸟才能在创造中实现的奥秘,属神的作为。休斯靠着这样的诗性作为,启迪着儿童的灵魂、开发拓展着他们的想象空间,期许“每一个新的儿童都是自然纠改文化错误的机会”。
《季节之歌》结束于《温暖与寒冷》一诗。前三节每一诗节的开头四行通过冰冻和与钢铁有关的意象描绘了冬天的冰冷苦难。然后是以“然而”开头的两节四行诗:“然而鲤鱼在它的水深处/像行星行于天宇。”借此展示自然世界的另一面向,动物们做好了对冬之寒冷的应对准备,尽管有的带着苍茫无助“野兔沿公路走失/像根扎向更深处”。在诗的结尾、同时也是整本诗集的结尾,休斯以其典型的黑色幽默风格扩展出人的意象,“流着汗的农夫们/在梦中翻身/像公牛在烤钎上”。一方面睡梦中的温暖农夫形象给予读者以安慰,同时诗人又似笑非笑地提醒读者人类也是动物。
时间与季节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无处不在的力量,时间不会放过任何事物,但时间的活力是如此迷人,正是它,是休斯季节诗的魅力之源。冬天过后便是春天,当你读到最后又可以回到诗集最初,重读新生命的降生,或者带着你已被更新了的感知觉系统开始写一首自己的新生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