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零后”上海作家沈大成是近年文坛的一颗新星,她擅于书写超现实故事,她的短篇小说构思奇崛,集超现实和后现代风格于一体。基于对当代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批判,作者创作了一系列新奇的景观空间,故其小说可称作“造景小说”。“造景”即在写作中制造一片新现实区域,这里有着与日常现实不甚相同的规则、特征和条件,显得离奇荒诞,但仍是现实主义小说,因其叙事和写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关注的对象和议题也与当下现实密切相关。沈大成的小说关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小人物,用变形的造景方式,描绘当代个体和集体的心灵状态与生存体验,以漫画式幽默、中立而富有治愈感的笔调,为小说铺上一层科幻感和未来色彩。
一
沈大成所建造的情景空间主要有四个类型。第一类是平行空间。这类故事通常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微型国度或异常空间中,平行空间有自身的特殊规则,同时又与“常规”的现实空间相分离,并构成对话关系。例如在空间极度紧张的“折叠国”中,一切事物都被尽可能地压缩折叠,它象征着异样的、怪诞的生活可能,并与“我”常驻的空间形成互不侵犯但互相凝视的对话;再如聚居着胖人的“圆都”,则是一个膨胀型的空间,其居民从普通的现实城市中出逃,来到了一个专为胖人定制的城市,圆都空间同样平行于常规的社会空间,它的乌托邦色彩也来自与不完美现实生活的对照关系。这类故事处于现实空间与平行异态空间的对话中,沈大成尽可能地维持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而不让故事承担起明显的批判色彩,保持自身的神秘和开放性。
第二类是打开暗道空间。这类小说没有另外开辟新的空间,而是制造了一部分有特异功能的个人或小团体,他们的私人生活甚至身体内部就隐藏着另一种存在状态、另一重生活空间,这些秘密空间并不挤占原有的日常生活,只在孤独时展开,一旦到了白昼之下,世界的褶皱就再度弥合,沈大成笔下的特异功能者,多是为了回避或暂时脱离都市日常法则。例如《配音演员》中,给一部经典动画片中“狗”角色配音的男演员,自愿变成了他所配音的狗,并以狗的身份在给“羊”配音的女同事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回归了正常生活,二人再次成为同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狗”的演员短暂获得了逃离常规秩序的特殊能力;类似地,《义耳》中不喜欢聆听都市纷繁复杂声音的人,装上了义耳,于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寂静,只有必须沟通时才有声音,这种幻想显然对话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喧闹;另一种生来特异的人种“口袋人”则是其身体内部就蕴藏了多重空间,他们像袋鼠一样,皮肤下面的口袋是可以打开的,但这异常的身体空间让他们常遭受怀疑和排斥。特异的秘密空间,与主流的社会秩序间构成了一丝冲突,但并不剧烈,他们都能找到在两种空间之间平衡的方式,在寻常空间中过着双重生活。
第三类是日常空间的畸变。这类小说将社会中已有的场所作为故事展开的基础性空间,将其变形。沈大成选取的场所本身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多为密闭性的、人流量较小的空间,或本身具有隐喻特质,例如象征衰老和死亡的养老院(《黑鸟》)、出版社最高处幽闭的阁楼(《阁楼小说家》),或是密密匝匝都市楼群中无人知晓的神秘空房间。在小说《空房间》中,“我”对门的空房间自主生产出了猫咪、小学生和大量的女性内衣,小说将空间本身的生产性从人类活动中直接抽离,转而诉说空间自身的欲望及其自我满足的机制,由此,空房间是都市迷宫中潜藏着的神秘能量原点。火车车厢也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空间,如同社会学抽样,将不同阶层、年龄段、职业和性别的人拦截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它在轨道上有序地驶向同一个目的地,在抵达终点之前这个空间必须保持平衡。在小说《待避》中,作为杀人犯的“我”最终被抛出火车,流放到野外,沈大成用箱型火车、线性轨道和无边荒野的三种拓扑学组合空间,重述了一个关于谋杀和审判的寻常故事。空间畸变类造景,是在现实和奇幻之间的穿梭,它通常扭曲了现实空间的一部分,但偏离得并不多,其内在逻辑仍然是现实主义的。

沈大成的第四类造景则是建造崭新的空间,这类小说直接构想了全新的科幻基础。虽然沈大成表示,自己的小说并不是科幻类,但像《在世界末日兜风》和《星际迷航中的小事》《星际迷航中的另一件小事》等都借鉴了科幻题材常用的背景设定,诸如小行星撞击地球、地球居民乘坐宇宙飞船向太空移民等,都设置了未来的空间基调。《次级人》《分裂前》等小说,是对当下非常明显的现实问题和景象进行了再创造,重新构筑了现实基础,比如无法结婚、无法体验家庭生活的人,会被政府以次级人的身份,分配到某个志愿者家庭中,做沉浸式体验;《分裂前》故事中的人类都是可以自体分裂的,他们自行选择死亡时间,在死亡的同時分裂为新的人,这种想象摧毁了常规的家庭秩序,使人们彻底成为国家的财产。第四类造景模式与前三类不同,它不依赖于一个不断与之对话的“现实空间”,相反,这类故事自给自足地完善了情节发生的逻辑,当中没有明显的“特殊空间”与“寻常空间”的冲撞或争辩。
二
沈大成的造景活动首先是基于现实基础建立,随后对裂变出的其他微小空间进行变形或扩大化处理,但这些造景空间存在的基础都较为薄弱,作者显然也无意让其生长为对抗性的秩序。于是,沈大成的造景空间的力量、强度较低,作者擅于提出和描述问题,但进而又将其悬置,不批判也不解决。
空间不仅承载着人类活动和社会行为,也投射和生产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精神状况。沈大成的“造景”空间,通过一系列变形手法,将空间与权力,以及后现代社会多方面的关系编织在了小说文本当中,表现后现代人类在都市空间中的生存状态。沈大成尽管拓展了许多空间,构想了若干乌托邦或异托邦式的场景,但她对空间权力的重新设置和讨论都颇为有限。沈大成所制造的异度空间的确存在着正常与异常、主流与边缘、显现与隐蔽的对立性结构,但这些空间由于大多是隐藏于人们身体或心灵的内部,或是只被小范围人群知悉及接纳,因此这些空间十分脆弱,甚至可以随时被隐藏、被折叠,并向宏大秩序做出让步,因此是脆弱的空间。
例如在胖人天国“圆都”中,沈大成对于这片乌托邦的兴建和衰败都是一笔带过。圆都作为梦想之地,短暂地存在旋即消逝,“像烤棉花糖时离火焰太近,美丽的糖块被烧焦了”。最终圆都的居民们不得不继续踏上放逐和追寻的旅途。显然,圆都只是徒具乌托邦的外形而已,它内在的力量是薄弱的,作者仅仅想象了一种美好的瞬间,接着让它自然消失。作者的目标并不是对现实进行尖刻讽刺,尽管圆都的出现是因为胖人在常规的国度并不快乐,但圆都的灭失却仿佛只是无端的遗憾。
关于星际迷航的两则故事中亦是如此。这两篇小说的背景都是运载飞船装满了地球居民,飞往太空新的宜居星球。就是在这艘挪亚方舟式的飞船中,发生了指挥官和平民之间的小型冲突。一位女士因违反规定,超额携带了大量行李而遭到处罚,她表示抵抗,奋力为自己争取从轻处罚,但最终竟被永久性地流放到了太空,成为宇宙浪人。沈大成对于这次冲突结局的处理,同样是非典型的:“随即,像一条大鱼往海洋中娩出一颗鱼卵,大犯罪家的个人舱从移民飞船上弹射了出去。蛋舱洁白的外壳上亮着灯,它优美地一边自转,一边扑进黑暗世界。”这种冷漠的中性化处理方式,增加了小说的荒诞幽默氛围,但也骤然弱化了冲突中的非正义和根本矛盾。沈大成让“船”的特殊空间专属于她的风格,而不是进入一种普遍的可预见的文学传统中。
沈大成造景空间是脆弱的,因为她专注于小人物、小事件的书写,想象了平凡生活中一些隐藏着特异功能的人群,他们的确能够形成一定的破坏性或对抗性势力:吃头发的理发师,不被日复一日的工作吞并,相反从工作中满足自己的特殊诉求;捕杀特殊动物的赏金猎人,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依旧从事着内心的坚守;夹克男在冷漠的中年知识分子圈中,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使他悲哀而固执地试图重返青春和温情的岁月……但所有秘密的生命力都十分薄弱,因此只能隐而不宣。怪人们的秘密只是一小片令人遗憾的自留地。沈大成笔下所延展出来的造景空间,畸变、平行或隐藏的空间,都像是美丽的肥皂泡,它们或破碎,或与现实达成和解,因而也就总是带着一丝遗憾。这一特征在《屡次想起的人》这部小说集中更为明显,沈大成所构建的现实之外的天地,并不摧毁理性的语法秩序,也不提供安慰。
三
沈大成的造景空间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她通过书写个体空间的非理性状态,反映集体空间的非理性特征,进而呈现荒诞的、密不透风的当代都市生活面目。当荒诞常态化,成为社会的普遍项时,不合理的事物便为自身谋求到了合理叙事,但集体荒诞一旦分散到每个微观个体身上,便又显现出其荒诞的一面。沈大成正是将镜头聚焦到小人物的私人生活中,书写私人生活如何被集体性的荒诞和焦虑吞并,这是一种卡夫卡式的思路。
但沈大成并不精确设定故事发生的时空,因此我们既能从中找到当下生活的映射,也可以接收到一种潜藏的未来指向。一般来说,文学中的地理景观应当与作者自身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相一致(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但沈大成笔下的地理景观并不是中国化的,也不具备某个特定的文化特征,而是一些中性的、想象的国度,换句话说,沈大成更关注的方面在于更具普遍性的现代都市空间,而非本土空间。沈大成在上海长大、生活,但广义大都市生活体验比上海本土风物更明显地影响了沈大成的小说写作。
沈大成的小说尽管经历了多种奇异的变形,但她最为统一的关切是后现代都市空间对人的异化。马克思曾定义“异化”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关于现代社会和工作对人的异化,沈大成本人也深有体会。在后现代社会,“异化”中压制性的关系,更突出地体现为一种强大的裹挟着万物的“流”,对人的个性、每个人存在的多样形态展开的变异,如今几乎每个人的生存信仰、评价体系、存在状态,都被迫地一致起来。小说《工作狂》里的“我”本来有自己的一套上班摸鱼哲学,但后来还是没有抵抗得住“红舞鞋”式公司的可怕氛围。在这样一个公司里,每个员工都像童话故事里脱不掉红舞鞋的女孩一样,都被一种现代魔力驱使着为老板不停地旋转。大型的后现代之“流”吞并了小人物的私人时空。

沈大成看到并成功表现了都市这一建立在秩序、规则之上的生存空间,这种空间迫使人袭用某种现成的生活模式,并为之同化的现象,但是在体会到了异化所带来的孤独、颓废之后,只有少数人会与之抗争,即便行动也往往以失败告终。《实习生》的第一句话便是:“实习生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认为后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超空间”,这种新的空间范式与我们现有的感知系统还无法相匹配,因此当主体置身于这种“超空间”中时,并不能通过感官和认知功能的协调加工来整合杂多信息,从而也就难以辨别自己在纷繁复杂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實习生》中的公司几乎是一片无效的空间,每个人都浑浑噩噩却忙碌地在其间浪费生命。三名实习生花了几周时间也弄不清各间房的职能区别,公司的各个大大小小的空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未知数,黑暗的走廊,等待着宣判的楼上会议室,三位同学寻求庇护的楼下仓库,全都是笼统的、无法定位的、令人迷失的空间,在这里大家连自身的主体性也迷失了,一位姓方的男同学始终被喊作“小刘”,直到他最后接受了。大家都“被凝缩、抽象、简化成了一个通用型符号”。
另一方面,沈大成的都市生存焦虑是夸张的、超前的,富于预言色彩的,尽管她很少真正去设定故事背景的具体时间。小说对应的都市空间并不是上海,也不是当下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城市,但作者却从当代时空中抽象出了城市普遍的荒诞性,因此她笔下的城市具有了一些未来感、电子感。例如《逃脱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现实空间,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通过调整自己脑后的旋钮来保持精神状态稳定,情感和理性的比重都是可以按照一种科学精确的方式来调试,这种构想重述了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而后者通常更多地出现在科幻作品中—我们已经在《黑客帝国》中看到过这种后脑旋钮的设计。个性的灭失,私人时空的湮没,个体被巨大的后工业怪兽之口吞噬,这既是当代生活的现实,也携带了对未来技术社会的忧惧。
书写当下,既是追溯性的也是前瞻性的工程。沈大成赋予许多小说人物以特异功能,似乎是给出了一种解决之道,一种逃离庸常生活的渴望,但结局又多是屈服和遗憾,从而再次强化了后现代都市生活无法摆脱的强大的网状结构。正是小说中潜藏的未来指涉,增强了关于生存的绝望和虚无的体验。未来就包含在当下时间、历史时间的夹层里,当下已经在孕育未来,所以她即便是写今天或过去,读者也能接收到一种遥远的焦虑。
四
沈大成的小说有种逃离现实的隐含期待,但仍与现实保持着乖巧的遵从关系,由此呈现出的节奏是幽默、可爱而舒缓的。小说所涉及的主题本身都颇为严肃,但她对这些题材的处理手法却别具一格,她以温和而轻快的笔触讲述这一切,使得故事引人发笑,但又透着强烈的孤独感。
沈大成的幽默来自一种动漫镜头式的写作。动漫本身就源于对生活的夸张变形,即用一些非常规的、扭曲变形的方式讲故事,在写作中打破一点逻辑常识,以更新对现实的感受力。沈大成熟练地使用了动漫镜头式的变形手法,在一些本来应该聚集着张力的情境中,她却使用夸张、充满视觉感的慢镜头消解掉了紧张情绪,从而使小说顿然变得幽默可爱。例如在《待避》中,“我”明明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在即将遭到列车员逮捕时,本应是一个焦虑、惊慌的情景,但“我”眼前出现的景象却是这样的:
我首先看到一团挪动的灰尘,之中有一截跳舞的蓝裤子,视线往上移一点,它穿在帮我补票的列车员的身上……列车员迈开疯魔的步伐,一晃三摇,身体一次次来回撞击两边座位,靠那股反作用力获得前进的动力,每撞一下他的头还是往相反方向弹跳,脸上凝固着木偶式的呆笑。他不时碰到旅客伸出座椅的手脚和头颅,把他们撞得飞起再跌落……
动漫感镜头的特写消解掉了冲突,呈现出新奇可爱的怪诞感。“我”似乎又溜到了常规的心理逻辑之外,作为火车车厢中竭力隐藏自身的失范者,“我”本应是被动、悲惨地接受即将到来的审判和流放,但“我”却如此平静,反而是逮捕“我”的列车员疯魔又呆滞,惹人发笑;车上的乘客本应以恐慌的凝视加剧这场审判的严肃性,然而他们却都在安睡,仿佛这是一场发生在“我”梦境之中的秘密审判。这种颠倒了常规逻辑且夸张的镜头特写,制造了黑色幽默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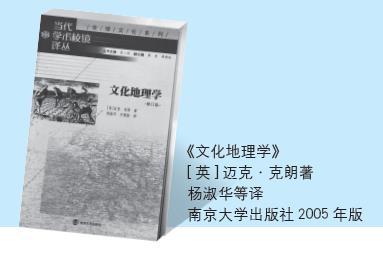
后现代小说书写都市生活体验,常用的断裂、失焦、破碎感,在沈大成这里并不明显,相反她书写后现代体验的笔触是实心的、确定性的,尽管怪异,但看起来天真且诚恳,甚至带有一丝“治愈”风格。“治愈系”一词来自日本,是当代日本文化中备受推崇的生存观。现代日本在经历了国家创伤、复苏及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再到泡沫破碎和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漫長的历史进程后,治愈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日本的历史及现实做出的回应:它接受了现实的不确定性,放弃了目的论式的宏大阐释,只求心灵上短暂的舒缓和慰藉。
同样,沈大成也通过构想一些温和、幽默又怪异的景物空间,带来舒缓、治愈的阅读体验。沈大成细心地搭建着她的景物空间,她有种特殊的耐心,来使这些明显是虚构的装置看起来逼真。她在虚构的现实中展开了丰富的细节陈设—虚构食物、影视剧、综艺节目、童话故事等,这些细节并不一定有效服务于故事情节,但却使得故事饱满丰厚、“假得真实”,富有温馨感。另一方面,沈大成也放弃了去追问、解释和解决的思路,仿佛是要描绘并接纳一切孤独和遗憾。她的故事通常都是以忧愁又淡漠的方式结束。在胖人乌托邦圆都陨落的最后,她只是轻轻写道:“我们在别的地方再相见吧,记住我的奶油馅面包,记住我的巧克力布丁!祝你幸福,祝你幸福!”

小说《在世界末日兜风》聚焦在小行星撞击地球、地球毁灭前的最后一个下午,作者重新讲述了人类家园从建立到逐渐废弃的漫长过程,最终,世界在三个陌生人的废墟兜风中结束了。作者称:“在世界末日的下午兜着风、吃着零食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态度。”沈大成自称为“小职员型作家”,她接纳了日复一日的繁忙工作,感受着都市空间的挤压,也接收到了现代生活的废墟感,因此她的小说,是在其实际生活的内部徐徐展开,通过想象力实现变形和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