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德者》是纪德发表于一九○二年的作品,纪德本人将《背德者》的文体定义为“叙述”(récit),认为“叙述”不同于“小说”(roman),但出于中文习惯,在本文中依然笼统地称其为“小说”。此书初版仅刊行三百册,问世后在法国文坛立即遭遇了一场惨败,甚至几乎成为一出“丑闻”,纪德的不少亲密好友由于这部小说的出版与他发生尖锐的争执。在一九○二年一月八日的日记中,纪德语带自嘲地写道:“为什么我要把《背德者》印三百册呢?为了稍微掩饰一下我的亏本销售。如果印一千两百册,那就是四倍亏损,我就要四倍心痛了。”对于书中主人公米歇尔的言行思想,尤其是他反宗教、反传统、反常规的道德倾向,法国评论界当时多有责难,甚至频繁转向对纪德的人身攻击,逼得纪德不得不在当年十一月《背德者》加印时增补了一篇《前言》,强调自己“并不愿意将这本书打造成一份控诉书或辩护词,同时我亦避免做出判决……总之,我并不试图证明任何东西,只求把我的画作绘制清楚,阐述明白”。
所幸,时过境迁,随着纪德的思维方式与写作手法逐渐得到接受和理解,《背德者》的地位水涨船高,其文学与思想价值也越发凸显。纪德在《前言》中写过:“一部作品真正的好处,与读者一时之间对它产生的兴趣,是两件大相径庭之事。宁可冒着第一时间无人问津的风险去言之有物,也不要迎合一群沉迷废话的公众而失掉未来,我认为,这么想绝对算不上自命不凡。”《背德者》赢得了未来,甚至被后代学者认为开“存在主义文学”之先河,视其为现代小说的典范。

在中文世界中,相比《窄门》《田园交响曲》等在民国时代便得到译介的篇目,《背德者》的汉译历史要短得多,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现了第一个完整译本。关于这部作品的意涵,学界也众说纷纭。客观而言,作为一本具有强烈思想性的作品,《背德者》的文意确实略显晦澀,尤其是纪德在《前言》中明确强调:“无论米歇尔凯旋或是屈服,‘问题’依然存在,作者亦无意对胜利或失败盖棺定论。” 纪德作为小说的创作者,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旁观立场,不对米歇尔的行为与思想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单纯地加以记录和表现,进而把下结论的权利交给读者。虽然熟悉纪德生平经历的读者都能看到,米歇尔与纪德本人的人生轨迹存在诸多重合之处,比如纪德在文学自传《如果种子不死》中,就书写过他在北非、瑞士、意大利的旅行见闻以及与阿拉伯儿童的交往片段,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背德者》中,纪德只是把自己的部分经历借给了米歇尔,继而让他以一个独立的虚构人物身份在小说的布景中自由行动。从《前言》中也可以看出,纪德极力反对把米歇尔与自己“混为一谈”,更不愿承担米歇尔引发的“义愤”。当然,纪德作为创作者,彻底的“无我”状态显然难以做到,我们始终可以认为他在写作《背德者》的过程中带入了一些自我剖析的成分,甚至在梳理纪德精神演变的过程中也可以引入小说中的某些思想作为参考。这与上文提到的内容并不矛盾,只是某种旁证,绝非直接把纪德与米歇尔画等号。
一九四九年,纪德在与让·阿莫鲁什的一次访谈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人的目标是上帝还是人的目标是人呢?
—我相信委实正是这个问题,而我相信这个问题的转移指出了我在写作生涯初期,当我写《背德者》时,我的思想所经历的演变。我过去觉得人的目标可能是上帝,而渐渐的,我终于把问题完全转移了,并且得到这个有点过于自信的结论:不,人的目标是人,并且用人的问题代替了上帝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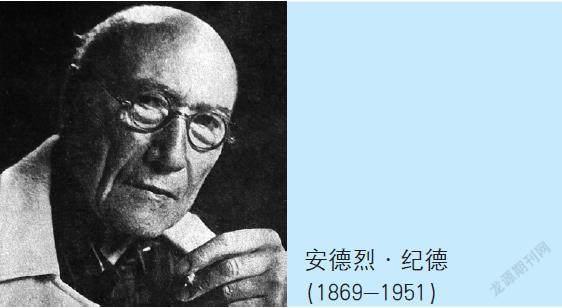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纪德在创作《背德者》时,正在思考人的目标究竟是人还是上帝,而《背德者》的成书,无疑可以视为对这个问题的一次回答,并由此延伸出新的问题:如果人的目标是人,会导致哪些后果?这些问题当然与纪德本人息息相关,构成了其思想脉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不过,如果将其仅仅局限于纪德个人,那么必然是一种简化,因为纪德思考的这个问题,已足够被称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具备着更宽广的普遍性。所以,相比小说情节与纪德生平经历之间的关系,《背德者》中包含的整体思想理念,才是读者需要优先厘清的内容。而关于这一点,就要从小说的标题谈起。
尽管《背德者》被完整翻译成中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早在民国时代这部作品便已经在学界有所提及。不过,关于这部小说标题的译法,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定论。在一九四二年完成的《〈新的食粮〉译者序》中,卞之琳将其译作“不道德人”。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长文《试论纪德》中,盛澄华则使用了“背德者”这个译法(日后李玉民的译本以“背德者”为题,多半来自于此)。第一位旅法女博士、三十年代以纪德作为博士研究对象的学者张若名,在一九四六年发表的文章《纪德的介绍》中使用过“叛道者”的译名。直至当代,查阅这部小说的多种汉译以及相关学术论文,还可以发现“蔑视道德的人”“藐视道德的人”“违背道德的人”“非道德者”“非道德的人”等多种译法。这些译名的具体意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背德”“叛道”强调的是对现有道德秩序的反叛背离;“蔑视道德”“藐视道德”强调的是轻视不屑的态度;“非道德”强调的是出离于现有的道德体系之外;“不道德”则是在现行道德体系内做出的否定性判断。各种译法虽然有所关联,但在意义上都各有偏重,对于如何理解米歇尔这个人物也会带来极大的差异。在所有这些译名中,“背德者”当然名声最大、流传最广,也称得上最为精炼,但并未彻底得到公认。存在如此多译名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证明标题涵义的模糊性,亟待进行梳理和辨析。
小说的法语标题,是“l’immoraliste”。在法语字典中,这个词汇的意思通常有两条:第一,“提出一些与现有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不同或相反的生存准则的人”;第二,“试图对现有道德提出质疑、加以轻视或拒绝予以重要性的人”。单纯从字典中给出的解释来看,除了卞之琳的“不道德人”,其他各种译法都可以从中找到依据。(考虑到卞之琳接触、了解纪德的作品是通过英译本而非法语版,这部小说的英译标题是“The Immoralist”,而英语中“immoralist”一词的意思恰恰是“不道德的人”,所以卞之琳的译法在英文词典中同样有其依据。)换句话说,字典中的解释并不足以成为译名的有效支撑,对于纪德笔下的“l’immoraliste”这个词,还需要从思想史中找出来龙去脉。
在法国最具学术权威性的“七星文库”版《纪德作品集》中,学者皮埃尔·马松在附录里对这部小说进行过一次综述。他在其中写道:
纪德极有可能从尼采那里借来了这部叙述的标题,在尼采笔下,这个术语反复出现—“我们这些immoralistes”;“immoraliste发声”;“我是第一个immoraliste”。
“七星文库”版的注解虽然简略,却为我们指明了“immoraliste”一词的思想史渊源:纪德在创作过程中,与尼采的思想产生过强烈的应和。纪德一方面精通德语,可以自主阅读尼采的德语著作,另一方面,他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出版的尼采法译本也颇为熟悉。纪德与尼采存在思想关联,小说中米歇尔与梅纳尔克的诸多言论中闪现着尼采的身影,这一点在欧美学界已有定论。更重要的是,“immoraliste”这个词,在德语中同样存在,而且恰恰被尼采本人使用过,例如马松提到的“我是第一个immoraliste”,尼采的原文便是“ich bin der erste Immoralist”。相比于纪德的“immoraliste”在法语翻译界众说纷纭的景象,德语译者对尼采的“Immoralist”的处理办法却出奇地一致,以上文马松引用过的三句话为例:
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善恶的彼岸》,魏育青、黄一蕾、姚軼励译)
非道德主义者的话。(《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
我是第一个非道德论者。(《瞧,这个人》,孙周兴译)
尼采的德语译者不约而同地将“Immoralist”译为“非道德”,说明对于该术语的涵义,中文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尼采本人对他的“Immoralist”一词也进行过解释。他曾这样写道:“从根本上讲,我的‘非道德论者’一词包含着两重否定。一方面,我否定一个类型的人,它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最高的类型,即善人、好心人、慈善者;另一方面,我否定一种道德,它作为自在的道德而发挥作用并起着支配作用—那就是颓废之道德,说得更明确些,就是基督教道德……我还在另一种意义上选择非道德论者这个词语,用作对于我自己的标志和奖章;我以拥有这个词语而自豪,它使我出类拔萃,高蹈于整个人类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尼采的“非道德”虽然包含着两重否定,否定却并非其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通过否定“克服”旧道德,抵达新道德。

尼采对于现有的道德体系,无疑保持着一种背弃、轻蔑的态度,但他的终极目的,是另辟蹊径,从人类的生命意志出发重建道德的根基,这才是真正的重心所在,也只有这一点才能成为他的“标志和奖章”。因此德语译者将其译作“非道德”是十分妥帖的做法。我曾与复旦大学德语系的李双志老师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尼采的非道德,是反对基督教道德,“他要推翻基督教对善恶的整个定义,也就是重估一切价值,所以否定的是何以为善,而不是简单地走到善的对立面去。他要建立超人道德。当时有很多人误解他,以为尼采是给犯罪者辩护,其实不是”。
现在,让我们从尼采回到纪德,回到他的这部小说。纵观主人公米歇尔的前后经历及其思想转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严重的病痛中康复之后,身体与精神都发生了颠覆性的重大变革,对于现存的道德体系,他当然是背弃的、轻蔑的,但之所以背弃和轻蔑,是因为他发现了新的价值,并理所当然地将其置于旧价值之上。所以,违背道德、蔑视道德,其实只是他在新建道德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并非他的目标与重心。在这方面,除了米歇尔在“道德”方面的演化,小说还从多方面进行了影射。例如,在小说中,纪德为米歇尔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身份:一个年少成名的渊博学者,精通多种语言,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如数家珍。但是,在精研学术的过程中,他沉浸于历史,日常的真实生命却陷入了停滞,遭受了忽略。当他的身体逐渐康复之际,他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渊博学识与人生严重脱节:“我终于对当初曾令自己引以为豪的学识产生了蔑视。这些研究,最开始曾是我全部的生命,如今在我看来,仅仅只和自己存在某种完全偶然的、约定俗成的关联。我发现自己不同以往,而我依然存在,哦!多么快活!与这些研究无关。作为专家,我感觉自己颇为愚笨。作为人,我是否认识自己?我几乎才刚刚诞生,尚且无法知道自己生下来到底是谁。这就是必须学习的内容。”
米歇尔经历了一次新生,他开始重新学习如何认识自己、成为自己,并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了深度结合(他的做法与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的看法不谋而合)。“我再也不是过去自己严厉且极具约束性的道德所适应的那个孱弱而勤勉之人了。这不只是单纯的康复,还有一种生命力的重新迸发与增长,涌动着更充沛、更热烈的血液,它必将逐一触动我的思想,浸透一切,激发并渲染我体内最遥远、最精微、最隐秘的神经。”在这一刻,米歇尔的学术与人生完成了统一。于是,他的研究兴趣从纯知识性的语文学研究,转向了文献中隐匿的那些充满激情的野蛮人物,并在这一过程中回应着他自己的生命力度,甚至“对于某种更加野性未驯的境界产生了一种悲剧性的冲动”。
米歇尔在职业方面的研究,以及后文中他在法兰西公学院开设的课程,标志着一种全新价值观的形成。“谈到盛极而衰的拉丁文明时,我描绘了它那充满艺术性的文化从平民大众中兴起,以一种分泌物的方式,最初显得血气过多、精力过剩,接着很快就凝固了、硬化了,反对精神与自然之间任何真正的接触,在生命力持久的表象下掩盖了生命力的萎缩,形成束缚,精神被拘于其中,萎靡不振,很快衰弱枯萎,然后死去。”米歇尔的这一学术观点,对应着他的个人经历,他也体会过这种“萎靡不振”的阶段。而当他在意大利拉韦洛的山崖上脱下外衣,在阳光下暴晒,“把全身都献给太阳的光焰”,让身体与自然真正开始接触之时,他重新活了过来,生命力再次勃发。在小说中米歇尔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倒是多少愿意见见我的同行,那些考古学家和语文学家,不过,和他们谈话,并不比翻阅一本优秀的历史辞典更有乐趣和激情。最开始我还会期待在几位小说家和诗人身上发现他们对于生活更直接的理解,然而即便他们拥有这种理解,也必须承认,他们几乎从不表露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让我感觉根本没有活着,只满足于表现出自己活着,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把生活视为令人恼火的写作障碍。而我也不能对此责备他们,因为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我自己犯了错……另外,我所谓的“活着”到底是指什么呢?—这恰恰是我希望别人能告诉我的。这些人一个个头头是道地谈论着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却绝口不提激发这些事件的动机。
米歇尔口中的这些同行,其实就是曾经的自己。对他们的批评便相当于自我批评。通过这一批评,米歇尔指出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生活是虚假的、造作的、浮于表面的。米歇尔想知道的,恰恰是“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生活的本意与真谛,这才是他心心念念要去追求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自己曾经的学术立场产生了背离与轻视,但最根本的内核,不是否定而是肯定,是建设,是彻底的价值重估。

正是由于这一点,米歇尔与梅纳尔克的对话在整部小说中显得异常重要。梅纳尔克,这个仿佛从《人间食粮》中走出的人物(《人间食粮》中也有一位“梅纳尔克”),直白地道出了真相:“您知道是什么把如今的诗歌尤其是哲学弄得死气沉沉吗?是因为它们脱离了生活。希腊人曾经直截了当地把生活理想化,于是艺术家的生活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成果。哲学家的生活,则是对其哲学思想的身体力行。同样的结果还有,诗歌、哲学都与生活相结合,哲学滋养了诗歌,诗歌表现了哲学,而非相互无视,这便产生了一种令人赞叹的说服力。今天美不再起什么作用,行动也不再关心自身有何美感,而智慧则在一边自行其是。”梅纳尔克的这段话,其实就是米歇尔“重生”后长期实践的行事准则—“身体力行”,“与生活结合”。在梅纳尔克的言论中,王尔德活在当下的享乐主义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生命意志交替闪现,但梅纳尔克与米歇尔的关系,就犹如王尔德、尼采与纪德的关系一样,并非导师面对学生,而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默契。
如果把米歇尔学术眼光的改变视作其道德立场演化的一种隐喻,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米歇尔的“immoraliste”,并非刻意在个体伦理诉求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构建一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而是把现有的道德体系从根基上加以抹除,以此建立一种全新的个人化道德。他为了实现自身的一切可能性(他将这种生命意志视为道德的最高准则),最大限度地对自我的内在需要予以满足,由此演化出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并由此造成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与马赛琳的悲剧结局。但就米歇尔的个人立场而言,他的目的是实践全新的道德主张,违背、蔑视现有的道德体系,只是实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把“immoraliste”理解成尼采式的“非道德者”,似乎更贴近于纪德的用意。
当然,在这部小说的所有译名中,“背德者”是流传最广、最为人熟知的一个,因此我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沿用了这个译名,就像普鲁斯特的巨著如果按照法语原文直译,应该是“寻找逝去的时光”,但因为约定俗成的缘故,“追忆似水年华”早已成为通行的译法。通过这篇文章,我希望读者能够对纪德笔下“immoraliste”的思想史内涵有所了解,至于米歇尔的行为思想究竟如何定性、如何判断,从作品的前半段看,米歇尔从病危走向康复,纪德对他的价值观似乎颇为欣赏,而从马赛琳的逝世这个最终结局看,纪德又似乎对米歇尔的唯我心态暗含某种批评,至少是心存警惕的。不过,情节如何设置未必可以作为作者态度的根本依据,纪德对米歇尔的态度,实在是颇为含混。
纪德更像是给米歇尔提供了一些情境,然后观察他究竟能走到哪一步,包含着哪些正与反的可能性。对此,纪德早已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当然,我并非试图断言,保持中立(我几乎想说:模糊性)是一位大师的确切标志。但是我相信,许多大师十分反感于……下结论—准确地提出一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已经预先得到解决。”既然保持模糊性是纪德的用意所在,而且他如此“反感于下结论”,若是在这里越俎代庖帮他给出结论,显然与他的意图相悖,对于小说刻意的含混也是一种破坏。甚至应该这么说,小说立意的这种模糊,恰恰是它的现代性所在。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萨特《恶心》中的洛根丁,他们的精神处境也都充满着迥异的解读空间。因此,我选择追随纪德,把判斷的权利交给读者,在审判米歇尔时反思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