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北京,清帝逊位,民国肇造。大清门早已易名中华门,紫禁城里六岁的宣统依然称孤道寡……异代鼎革之际,纷纭而陆离,诗集《碑》(Stèles)就在这异质斑驳的时空里悄然付梓,寥寥八十一本,见证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由“中华帝国到自我帝国的转移”(谢阁兰《致孟瑟龙书》,1911年9月23日)。
在他一生不辍的随想《异域情调论》里,谢阁兰将自己归为“天生的异乡人”。于他而言,漂泊不是命运的诅咒而是新生的祝福:借此,他摆脱了母亲的桎梏,逃离令人厌倦的“教会的长女”法兰西;像他钦仰的兰波一样,从布列塔尼从米什莱笔下那最凶险的海岸起航,听凭海风燃入肺叶,任由最遥远的气候黝黑皮肤(兰波《地狱一季·坏种》)。
而在走向远方走向自我深处的旅程中,最早引他感悟异域之美的是高更。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五岁的医学博士谢阁兰刚刚成为法国海军军医。说来也巧,他当时任职的多浪号海轮正好负责将三个月前在希瓦瓦岛上辞世的画家高更的遗物运返欧洲。在临行拍卖会上,作为这位绝代避世的画家最初的知音之一,谢阁兰买下了高更的几幅畫,和其寓所“快乐之屋”大门四周的浮雕匾额。浮雕上的两处铭文“盈满神秘”“饱含爱意,就会幸福”成了谢阁兰塔西提岛时代的座右铭,在他以当地土著文化为素材的第一部小说《亘古斯民》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在接触高更的素描并且生活于其中之前,我简直不曾真正睁眼看过斯土斯民。”日后谢阁兰曾对高更一生的挚友蒙弗利德这样慨叹。从此,异域与生命之美构筑起谢阁兰的文本世界。
六年后,一九○九年,即光绪、慈禧相继离世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两年,谢阁兰作为法国海军见习译员,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颇为诡谲的时刻,踏上这片他梦牵魂绕的大地。如果说塔希提之于谢阁兰是不期然的偶遇,那么,中国则是他着意的追寻。在谢阁兰看来,这个遥远的国度对于欧洲意味着三重的异域:东西对峙,各在天一方,让它成为空间的异域;悠久的历史,使之成为时间的异域;而执着此世、不以天国为念的文化传统则令其成为文明的异域。
 《碑》(Stèles),1912年初版本
《碑》(Stèles),1912年初版本那么,面对这完全的他者,自己又当何为?描摹风情,醉心猎奇?当然不!他绝不愿做一个“平庸的旅人或观光客”,津津于棕榈骆驼、民族衣裳,他孜孜以求的是相左大于相和的异己感,是“相契”唤醒的“相异”,是“有关”隐寓的“有别”。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亘古斯民》中,谢阁兰曾为毛利人的文化失忆扼腕,但到了中国,他领略了世间最坚韧的文化记忆。路畔、寺内、坟前,那一方方默立的碑碣,将生与死、今与昔,逝与驻、完整与缺失铭于一处,让他在这行将倾圮的帝国里不无吊诡地体认恒久。
而从“化为与石之肌理相契的石之思”的碑文上,谢阁兰为自己的诗思找到了理想的表现形式:每首诗所在的矩形空间宛若一方碑;静立于右上角的几个汉字,是诗的题辞,它们多取自中国古籍,偶尔也出诸诗人的匠心,与下面的法文诗遥相呼应,读者若识得中文自可沿流讨源辨出典故与名句,而若不谙汉字也无妨,就像远天的星辰,纵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一样照亮我们的眼眸;法文诗则有若碑铭,通常分为两部分,主体敷陈“中华帝国”,结尾则转向“自我帝国”,有若碑末的铭辞。
诗集《碑》中,谢阁兰依照方位将诗分为六辑:南、北、东、西、“路畔”、中。序言里,谢阁兰写道:
面南之碑,载述王命,及君王对贤哲的礼敬;铭刻对义理的颂美,对圣朝的讴歌,皇帝颁与臣民的罪己诏,南面而坐的天子颁订的一切。
出于谦敬,友谊之碑将面向正北、面向玄德之极而立。爱情之碑将面向东方,以便晨曦为它们的容颜更添温柔,淡却恶相。面向血染的西方、面向猩红的殿宇而立的,是战争与英雄之碑。别的,路畔之碑,将依随道途漫不经心的姿态……
 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
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有些碑,不向南也不向北,不向东也不向西,亦不朝向任何不定之点,而是指向那方向里的方向,中。
显然,不同方位的碑寓意亦自不同:南为君;北为友;东为恋;西为力;“路畔”为行旅,为世界;而中,则为“自我”。六个方位,六十四首诗,集合起来,勾勒出生一副命的面相,绘就一个自我的帝国:个体生命是它的纪年,心灵是它的疆域,自我是它的君王。
整部诗集中,“中央之碑”的声音最为深邃、最为幽约:那里是“中央之中”,在那里,“我”,这“自我帝国”的君王,竟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个不认识的自己:“我看见:—我看见一个惊慌失措的人,一个貌似我却又逃离我的人”(《记珠》);那隐藏于自我深处的“神魔”令我愕然无措:“该以怎样的典仪礼敬那栖息我身、萦绕我洞穿我的神魔?该待之以怎样的善举抑或恶行?/我当抖动衣袖以示尊敬还是燃点恶臭之物将其驱逐?”(《致隐秘的神魔》)
“中央之碑”歌咏欲望,欢欣与苦楚交织的吁求中盈满尼采的气息。“释放我身内一切美丽的囚徒吧—那些陷于专横牢笼里的欲望,并,作为恩泽与酬报,/让那惬意的豪雨洒下我的帝国”(《释放》)。虽为石,却澎湃着爱与生命,谢阁兰指端的“碑”,有时,宁愿死去,也要让生命与爱重新奔流:“这诗,这赠礼,这渴念—/将一起从你的死去的石间剥离出自己,哦!不定,不住—任自己恣肆于她的生命,/去和她一起生活。”(《不住之碑》)
“中央之碑”中,井的意象仿若无解的方程:“我将敞开门,她将走进,我所等待的人儿,至为强大却无丝毫不逊的人儿,/统御、嬉笑、歌唱,在殿宇、芙蓉、死水、阉寺与花瓶间,/直至她所了悟的那个深宵,被轻轻推入井中。”(《紫禁城》)井是通途,是囚笼?如爱?如死?经过异国诗心的淘漉,光绪与珍妃的传奇升华为爱的寓言。
《碑》是时间之诗,楮页间写满诗人的永恒之思。雕梁画栋,飞檐斗拱,那一木一瓦看似不如西方建筑中的大理石、花岗岩坚固,但“长久并不存于坚固。不变亦不栖于墙垣,而是寓于你们自身—悠悠的人,绵绵的人”。材质再坚固也难逃岁月的侵蚀;而人生代代无穷已,真正的长久在于世代相继,在于文明绵亘。《卜陵诏》中,那位中国君王,在为自己择选身后的安息之所,面对生命的流逝,他从容旷达,悠悠言道:“死宜于居住”。而结尾处那句“我将谛听人语”,满蕴生之眷恋—不无对基督教彼岸向往的揶揄:纵然生命离去,“我”仍愿留在人间,留在大地,而不愿去天上,“一边在蓝色中打转一边唱圣歌”(《漫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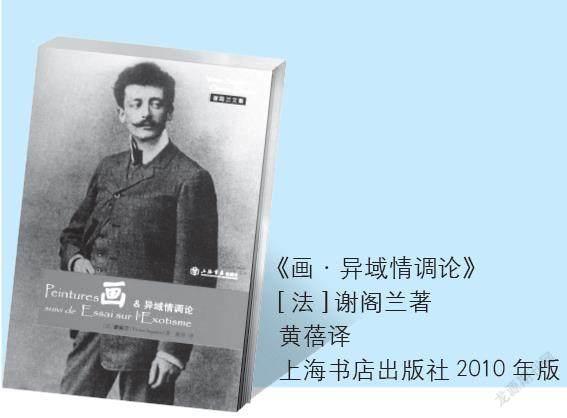
手稿中,謝阁兰曾一度将《碑》命名为“中国时刻”。而那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不是南方的口岸,不是口吐白沫的长江甚或白河,不是所有自海而至的人的中国。而是中国的边陲与内陆。在给友人皮埃尔·于杜尔彼德的信中,谢阁兰说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是四川的中国;还有另一个行省,那通往突厥斯坦的走廊;还有一个,在西藏的边缘;还有一个,在黄土地里刻成的:最不可思议的,最荡人心魄的,最尘土飞扬的,最古老的—渭水之滨的泥土的、黄色的中国。在那里,黄色的人有了皮肤的颜色与文字的形状”,在那里,“别的山撕裂天空,高高擎起山尖的痛苦,任凭山谷深深沉陷”。而在他异域之眼的眺视中,“那里”倏然间变成“这里”—“这里,翻转的大地将裂隙藏入腹中,抚平崎岖,掩抑峰岭……”(《黄土地》)最中国的山川瞬时化作异国诗人的灵魂风景。
至于“时刻”,谢阁兰几乎不曾属意过中国的当下,他究心的始终是“史书中还没有人碰过的十万个皇家题材;是城邑迁变、生灵涂炭;是朝代更迭与惨烈的灭亡,是外来信仰发散出牵缠混杂的新理念,即:摩尼教与景教,以及夹在外交使团中的异族公主。”易言之,他要谛听的是典籍的长廊间中国缥缈的跫音。而无论那细微的脚步来自《诗经》《礼记》,还是《论语》《左传》,谢阁兰都一一谱成自我的心曲。放言“日亡吾乃亡耳”的夏桀,一变而为以欢乐统治自我、以欢乐征服世界的心灵帝王(《恣乐的君王》);“西征于青鸟之所憩”、与西王母相期瑶池的周穆王,则仿若从现实驰向想象的诗人(《出发》);《逸驾》一诗,以《诗经·鲁颂》中的“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起兴,继而转为对思想之马的咏叹:“我被我的思绪驱策,不受羁鞚的牝马啊—或骑、或骈、或驷,曳着我无尽的车辇”;最后,马儿消失了,唯有麒麟载着“我”徐行于诗与梦的家园。《庸匠》一诗,乍看似乎是《诗经·小雅·大东》的简单迻译:“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但结尾两句,却新义陡现:“世间庸匠指摘天上同业诈伪与无用。/诗人说:它们发光。”—在庸常的世界里一无所用,却将这世界的庸常照亮,星如此,美与诗如此,诗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写给友人孟瑟龙的那封信中,谢阁兰深情地忆起塔希提,在那片热带岛屿上,他的生命第一次绽放,他写道:“波利尼西亚群岛生活的两年,我快乐得睡不好觉。有时清晨醒来,泪水会在阳光初升的醉意中落下。唯有快乐之神才知道这苏醒是怎样地宣告白昼的来临,又怎样地昭示那连白昼也无法度量的不停歇的幸福。”
而在中国,他迎来了生命的另一个黎明,那是自我生命时刻与“中国时刻”—其实,从传统中国的角度看,谢阁兰的“中国时刻”更像是一个由边裔、中外交通铸就的“夷狄时刻—共同孕育的时刻;在中国,他树起一方方文字的丰碑,刻下自己诗性的觉醒”。他的诗既不是用“法语来讲中国话,也不是用汉语讲中国话”,而是像《碑》的第一首诗《无名号》所言:它所要写的是“那没被言说的”“那不曾颁布的”;它并不铭刻任何一个中国朝代:
而是铭刻这独一无二的时代,没有日期没有终点,且以无法诵读的文字命名,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创立并致敬,
在那个晨曦,他成为贤哲与心之御座的摄政王。
本文所引诗歌,均为作者翻译
李? 爽 主编? 《书城》杂志出品? 文汇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快乐与至乐》收录钱旭红、何怀宏、葛兆光、张汝伦、陈嘉映、张信刚、晏可佳、钟扬、冯平、江晓原、孙周兴、胡翌霖、孙向晨十三位著名学者的十六篇文章,话题涉及哲学、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兼具广泛性和深刻性。本书以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为入口,在东西方文化视野的对照下,用哲学的眼光,把一些深奥的前沿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高新技术课题或交叉学科的课题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同时,本书反思和观照的是当今人类以及未来人类的生活,不止是知识的碰撞,更是思想和思维方法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