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1932-1982)
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1932-1982)一
乐迷都知道巴赫专家、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1932-1982),但他后来跨界搞的纪录片大多无关音乐,所以粉丝如我也并不关心,即便知道古尔德自己很看重。自从读了帕西克的《多相大脑:脑半球的音乐》(Polyphonic Minds: Music of the Hemispheres),才想起來这一块。我在加拿大居住久了,越发理解古尔德和加拿大的联系,也读了一些加拿大北方的书。缘分所至,我开始了解古尔德录制的广播剧《孤独三部曲》。令人吃惊的是,古尔德据传不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按说对他人的反应毫不关心,可是他对人的故事怎么这么感兴趣?而且是那种细腻深挚的关心和细品。这是一部跟音乐无关的“作曲”。第一部《北方的概念》中,唯一的音乐是西贝柳斯的第五交响曲,作为巴洛克音乐中常见的通奏低音来用。第二、第三部索性更极端,人物介绍和叙事都没有,只有众多声音进进出出地倾诉。古尔德绝非随机选取这些声音,而是相当刻意,从第一部开始,他跟录音师常常工作到凌晨,细修每个字甚至每个音节,连火车声都用来形成结构。三部曲的形成历经十年,每部都是在几百小时录音的材料基础上编辑出来的,完全是古尔德式高度控制的产物。在这一点上,更大胆的约翰·凯奇的《收音机音乐》就不同,毫无排布,任由人声随机发生。
加拿大的北方,一般特指几个原住民区:育空、西北和一九九九年才成立的努纳武特。这些地区寒冷广袤,人口极少。它们本身因为承载殖民历史,有说不完的故事。当年的殖民者,虽然跟当地的原住民没有美利坚土地上那么暴力的冲突,但矛盾和破碎的历史叙事无处不在,至今也并没简化多少,更没有一个能讲清楚的未来,本身就是让叙述者对付不了的“对位”。古尔德在多伦多长大,原本跟稀薄的北方相去甚远,这些地方他为了录音才去的。不过他有北方情结、孤独情结,也有多声部情结,跑去录制纽芬兰岛、因纽特人、温尼佩格等省的门诺会,把录音做成多声音进行的广播节目。他的视角当然是白人的视角,即便对北方原住民所遭受的忽视愤愤不平,也并没有为之直接呼吁。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北方生活简单地浪漫化,这些真实的人物揭示了北方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在其中冥想,挣扎着令自身获得安宁;有人意识到孤立环境中人与人的互助何等重要,但躲不开的流言也让人窒息发疯;有人在单调的生活中焦虑,唯愿某个周末能逃离一下,然而这完全是奢望;有人则痛恨外人对爱斯基摩和冰屋的符号化,倾诉北方的丑陋:肮脏、没有卫生条件、生活贫乏,只能酗酒或者反社会,常感空虚无傍,渴望逃离,人命在贫乏的生活中终于夭折。对于《北方的概念》,古尔德也说,表面是讲加拿大的北方,“其实事关人类灵魂的暗夜。它是一篇倾诉人类孤独境地的散文”。第二部《晚来者》和第三部《大地的安静》中,录音伴随着海浪声、铁轨声,背景声甚至时时淹没人声。更多的时候,完全不同的意见同时出现,男声女声,彼此淹没。这些人各自吐槽,但声调柔和有控制,措辞有分寸,到底是好脾气的加拿大人,甚至让我感觉是古尔德本人的一种投影。
话说,我喜欢的加拿大小说家赫依(Elizabeth Hay)写过一本以北方极地黄刀镇(Yellowknife)为背景的小说《空中的夜晚》(Late Nights on Air),就有这种苦寒里的顺应,以及完全在收音机声音中建立的故事与政治,女人爱上男人,因为他的声音。作者好几部作品的故事背景中都有古尔德的巴赫。“他的巴赫稀疏、抽象但神秘。它从来都不美丽,当然更不滥情。这是个北方人的巴赫,像冷天一样刺穿听者。”这是钢琴家都巴尔的话。文学评论家斯坦纳说古尔德的巴赫“闪光,尖锐,干燥,奇怪地让人陶醉,好比加拿大冬天的清晨”。冰冷和干燥,不好说是巴赫的必然或者固有,或许这一切都偏巧发生。加拿大作为一个偏远的国家,居然把巴赫深深吸纳到文化中。
技术狂、录音狂古尔德,到底也是复调狂。在这些纪录片中,他精心设计了声音和故事的进进出出和同时进行,比如常常有一个主要声音先出来,如同音乐中的赋格主题,最后抵达巴赫音乐中常见的四声部,并且往往有一个声音占主导,确保人能听清。这是他的“复调广播”,也可能是他的一种自传。比如第三部的重点稍稍偏离北方,聚焦在门诺会成员,背景是教堂礼拜的声音。门诺会成员不看电影电视,没有通常的娱乐,就在这自我设限的生活中平静度日。可以想象,其会员总会有一部分逐渐远离,有一部分始终坚守。这种冲突也是古尔德的对位日常。
不少人会问古尔德不专心多录或者多写音乐,浪费时间在“广播剧”上干什么?但古尔德认为这就是一种创造,跟写作音乐一样。此时的古尔德,告别舞台已经三年,潜心在录音室里生活,作曲的尝试并未成功,不过他有了那句著名的“子宫一样宁静的录音室”之说。录音室是家园,更是“多声部”的最终实验室。
二
帕西克此书,从多声部音乐讲到大脑的多任务本质。从欧洲多声部音乐的源头讲起,颇为烦琐。顺便说一下,帕西克本人在美国著名文理学院圣约翰大学教书,既研究科学史又开钢琴独奏会,大约对古典学也有几分修为,所以不管讲什么,动辄考据古希腊起源。
多声部的教堂音乐,有史记载大约是九世纪开始的—世人往往夸大欧洲复调音乐之早,其实古希腊并无多声部音乐传世,格利高里圣咏更是单声部的。据帕西克说,多声的概念始于对教义的紧张辩论。十四世纪,马肖(Guillaume de Machaut,1300-1377) 的弥撒是现存最早的多声部弥撒,如今看来它已经复杂而精致。之后的佛罗伦萨,有过回归古希腊单声部音乐和各种悲剧的复古倾向。比如物理学家伽利略的父亲文森佐(Vincenzo Galilei,1520-1591)和同道形成的小圈子“Florentine Camerata”,因为要回归戏剧,总要讲故事,结果在宣叙调音乐中不小心挖出了歌剧这个大坑。音乐的复杂、多向和多重才能容下音乐家无尽的梦想。
多声部音乐大师远远不止巴赫和他的同时代人。二十世纪,勋伯格、韦伯恩、里盖蒂、艾夫斯等,赋格作品数不胜数,当然不再那么格式化。里盖蒂有一部半恶搞的《为一百个节拍器而作的交响诗》,一百只节拍器渐渐同时作响,不过这已经不是巴赫复调那种人脑自以为能够处理的情形。从一个“声部”开始逐渐增加,大脑终于吃不消并且放弃了,然后改变了应对方式,一百个“声部”退为无声部,好比花布上的小点点。
有趣的是,帕西克举出作曲家韦伯恩的著作《通向新音乐之路》(The Path To The New Music),其中以多声部的欧洲音乐为例,外加物理学家亥姆霍兹对声学的研究,证明西方复调的独特,尤其是钢琴和管风琴音乐,帮助人类抵达人声所不能及之处。韦伯恩也提到巴赫高度成熟的复调艺术和欧洲人格外推崇的秩序。不过,人类也好,所谓西方人也好,真的进化成干干净净的理性了?非也。同时代人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写的是心理的分裂、多变、不可测与不和谐。在普鲁斯特这里,语言虽然强大,但还远远不够,音乐、气味还要一起闪闪发光才能传达那些大大小小的自我。关于人心的欲说还休、举棋不定,这种文学作品多如牛毛。用帕西克的话来说,自十八世纪始,欧洲文学中以多重自我、分裂人格为素材的作品越来越多,它已经成了文学中一个活跃的永恒题材。人脑的奇诡,任何一种文化中的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观察到,所谓文学即是人学(岂止文学,政治、经济、商业、文化甚至科技,处处是人的空间),人脑的不确定性给了创造和想象空间,也提供了少数人操纵多数人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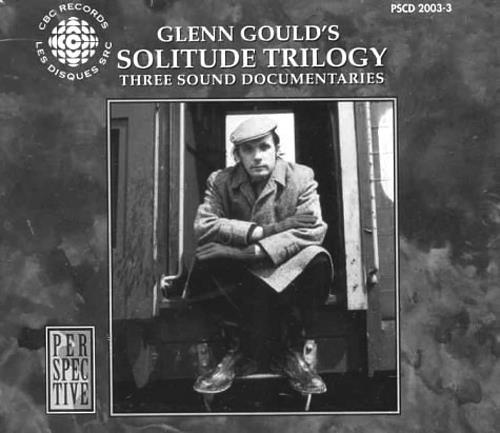 古尔德《孤独三部曲》(1992)
古尔德《孤独三部曲》(1992)然而韦伯恩对多声部音乐有这样振聋发聩的概括:“好几个声部同时发声,结果是增加了‘深度这个维度……乐思在空间中发散,而不只是一种声音。”这句话击中了我,勾起了我对语言、音乐的种种想象,甚至让我联想到星空的图景,那种稀疏星球点缀于太空的动感……星垂平野阔,这已经是射向四方的发散之意了。古尔德的粉丝,都会提到他指下巴赫的多维,以及空旷感和空间感。深度、空间感,本不能听出来,不过我们的经验还是聚焦出这样的语词。
帕西克的重点是西方音乐中的多声部,也指出多声部普遍存在于世界音乐中,只是西方音乐留下了比较明晰的记谱。但人脑并没有照着乐谱演奏,这么说来那些未留乐谱的“即兴多声部”文化,也许更接近大脑的样子?我想的是,音乐天然就包含意识的多头并进,比如无论东西方,歌词、舞蹈陪伴音乐都极为常见,如果说声音并无语言上的意义,那么声音與语言或者形象的“正交”,加以反复互相包裹,会产生什么?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所以不妨这样问:任何一个物体的颜色、声响、气味、名称都会同时涌入大脑,大脑日日面对如此紧张的多任务处理,怎么做到从容不迫?当然这是神经科学中的“大坑”,慎入。单是两眼怎么合作出一个影像,就足够科学家写出不少论文。
一八六三年,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论音调的感觉》(Sensations of Tone)揭示声音的物理规律以及人耳/人脑处理声音的机制,并且指出任何声音都包含无限泛音,所以任何单一乐器上的声音也是“多声部”。巧合或水到渠成,若干年后,勋伯格的一组五首管弦乐小品中出现了,其中的第三首“色彩”(Farben)中,和声运动降到简单级别,几乎完全以色彩变化来叙事。我初听昏昏欲睡,因为色块变化的脉络毕竟松软难握,直到看了人家的分析图才有点恍然,这一定不是勋伯格期待的反应。而韦伯恩曾经把巴赫《音乐的奉献》中的六声部赋格改编成管弦乐版本,那种复调支撑下的澄澈对我则是很好的启蒙—这个改编版的重点也在于用音色来叙事—长号负责主题,圆号、小号、竖琴等各执所本。也就是说,多声部不仅可以是多声线,还可以是音色的分叉。韦伯恩的多维空间说,也可以引申到多头并进的语言、颜色以及节奏。有趣的是,韦伯恩把勋伯格的管弦乐小品改成了双钢琴,并且很成功。它们本来出自音色的生长、膨胀,却又在颜色的减缩中获得另类生命。
三
也许,多任务的状态,是生命的自主,也是环境的激励。
我自己是非常讨厌一心多用,有时一边忍不住看书的时候穿插看手机,一边痛恨自己。我知道不专注是最能毁人的习惯。不过,韦伯恩关于多维度和深度之说,令人琢磨。我猜,最毁人的是不断切换任务(context switch),而未必是平行的多任务,毕竟后者是人类面对的现实,也是大部分动物面对的现实。从基本的日常活动,比如行走,到后天掌握的奇奇怪怪技能(体育、音乐等),技能从初学时的虚弱、失控到缓缓吸收为自我的一部分,一直都在注意力分散(因为要协调多头操作)和挣扎着记忆的过程中,体验分裂和整合。
我在管风琴上练习之前,常常会在钢琴上练习比较复杂的双手部分,之后再和脚合到一起。但好像,双手在钢琴上形成的肌肉记忆,并不能完全移植到管风琴上,哪怕只用到一个键盘。这指的还不是觉得键盘视觉上的别扭,而是钢琴上手能自动找到的位置,换到管风琴上不一定了,因为没记住。原来人在管风琴和钢琴上的坐姿、重心、身体和手的角度都不同,而这也是肌肉记忆的一部分,虽然意识并不知晓。弹琴是个整体运动,其中有些参数改变之后,整体都会变形。当然,不仅是音乐,但凡涉及身体的重复和反射的活动,身体也参不破自己的奥秘。没有身体(包括手指)的带动,音乐家只靠大脑学不会多声部演奏—身体虽然不够聪明并且能力有限,但它拥有自己的“底层CPU”,坚定地执行指令,执拗起来意识都劝不动。我在这里所说的“身体”,是指肌肉、脊髓与大脑皮层神经元的协同运动。音乐老师往往鼓励慢练或者变节奏练,有时是为了打破肌肉记忆,让意识与无意识互相拷问—两者同样构成多相,且能互相转化。
总之,人脑是个大怪物,复杂到难以捕捉规律,但陪伴了人类百万年,有一定的可控性。记得一位脑科学家说过,对于大脑,普通人可能对其复杂性估计不足,但也会以人脑之桀骜为借口,不愿行自控之事。而对付人脑,让自己听自己的话,总像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拔那么难。人心难测,因为单向的用力总会撞到天花板,话语往一个方向堆积到一定程度,一定开始分散,一定有阻力产生,对立面会慢慢涌现,没有哪个方向会无限顺风顺水。
就拿古尔德来说,当年对他刻板化的种种传说,如何退隐、如何特立独行流通若干年之后,终于有人跳出来说“都是装的”。人不会只有一个维度,真相也不会那么极端,虽然思维和语言往往始于极端。古尔德自己就呈现出立体的多声部:他有些自闭,留下许多不能跟人共情的轶事和笑话—可是他居然喜欢偷听陌生卡车司机休息时的谈话,说明他对他人生活不失兴趣;他喜欢孤立和安静(当然同时又抱怨太孤独,渴望伴侣),但也并不远离现实。他是个骨子里的加拿大人,主持过加拿大电视和广播节目,对社会、经济、道德诸事都十分关心。现代乐迷只知道他的巴赫,而他也曾经是那一代加拿大人引以为豪的思想者。二○一七年,《北方的概念》制作五十年之际,加拿大CBC电台索性做了个新节目《重访北方》,找来一些古尔德当年的熟人,采用古尔德式的多(人)声进行,但不回避音乐,大大方方把古尔德演奏的巴赫插入到谈话中。北方如旧,普通人对北方的怨念、对极光的恐惧也如旧,然而五十年间,轮回并不存在。世间已无古尔德。
四
“凡事皆有定期,天下万物皆有定时。”这在农业社会里十分可信,而工业社会更多的是人造的、更精细的周期和计时。对音乐家来说,周期和节奏“具体而微”,任何多声部音乐都离不开总体的协调和对准。
书名所谓“脑半球的音乐”,不仅是指多声部音乐在脑中的处理,更是指作为“音乐”本身的人脑。为此帕西克引用了脑神经科学家布扎基的著作《大脑的节奏》(Rhythms of the Brain)。此人看上去确实是个有趣的脑科学家,喜欢把音乐和大脑的波形类比,所以跟帕西克很合拍。布扎基在书中说,“一个神经元简直能跟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媲美,不仅能响应某些频率,自身还能产生频率丰富的回响”,“神经元还能动态调整响应的频率,就好比音乐家在不同音符之间换了乐器一样”。
曾经,研究者认为大脑皮层的各个“模块”要连接起来才能工作,必须有个“中枢”指挥它们;并且,神经网络是由一些天然被动的组件构成的,除非必要,它们就一直懒洋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认为大脑并不那么被动,更非像齿轮零件式的机械相加。虽然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远未确定,但也有些认知获得了广泛承认,比如大脑并没有一个管理中心,? ? ? 而是一系列神经回路(neural circuit)互相作用的结果,它們能渐渐自我调整到一个协作的状态。协同工作的时候,它们甚至呈现出惊人的简单。
对大脑的运动形态,帕西克有个说法,“波粒二相”,虽然这在科学上还远未确认。在电磁波之中,粒子本身也是波,主流神经科学研究认为神经元(也就是神经细胞)在成簇、成组的形态下才能体现振荡。布扎基则认为,各个神经元本身就是振荡器(但其振荡方式却又不可能是经典的钟摆式),当两个频率相同的“振荡器”相遇的时候,就跟光波一样可以互相抵消或者放大,这也是帕西克所谓神经元“二相”之本。人大约有八百六十亿个神经元,小到半厘米,长到一米多,每个神经元就是大脑中和声的一个声部。他说神经元一起工作,犹如交响乐队,外界的刺激犹如指挥,但乐队也可以丢开指挥自己演奏,大脑也可以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运行,并在恰当的时间形成所需的方向。
研究者们目前同意,大脑有分布性,但也并非诸多微大脑各自为政。每种神经活动,往往至少涉及几十个模块。而大脑活动的一部分重要特质,也就是分组的神经元的活动,就如波浪一般。不太精确,但能清晰地展示大脑皮层活动波形周期的办法,就是脑电图(EEG)。就拿听觉系统(包括耳部、神经通路和大脑的听觉中枢)来说,它能把连续的自然声音分块并且解析,这就是理解语言的基础。人说话的节奏,就以大脑皮层内神经元波动的节奏为本,此外听觉神经细胞的节奏也跟听觉神经中枢神经细胞匹配。所以,大脑的处理节奏,跟说话的节奏、耳朵解析的节奏是相配的,这可以算布扎基离经叛道的说法,几乎是脑洞大开了。
大家公认,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振荡一旦出了问题,比如过度划一,并且不断加强,就是癫痫病。任何能规划节奏的神经元,抑制能力都是节奏的基础。这种节奏,居然还是可以遗传的。一般人脑电图频率可以从小于1赫兹直到大于35赫兹,就好像心跳、步行有自己的节奏,越紧张兴奋越高频。神经元活动形成的脑电波,在任何时刻都是多个波形的叠加,就好比声波,任何一个音都是无数波形的叠加一样,即便动物在睡眠状态,不同阶段也会呈现不同的波形。
帕西克说,布扎基的实验表明,老鼠大脑的海马区中的振荡器频率有个宽广的范围(0.02到600赫兹,不连续、阶梯式),各波段之间的频率比是接近2.17的无理数e, 也就是不存在整数的分母分子,也就注定脑电图是不可重复的,取决于它们当下的互动—也正像乐队成员一样,可以即时协调节奏。帕西克说,当年开普勒发现星球的轨道比例也是无理数,也不能重复。这当然没错,不过帕西克可能忽略了一点:开普勒的发现并非巧合或者唯一,大脑波段的频率比例更不是偶然,因为世间几乎“所有”数字都是无理数,从星球的距离、质量到声波、电波,真正的有理数只存在于想象或者圆整之中—哪根木头恰有1.1米长,哪辆车的速度能在任何确知的瞬间抵达正好80公里/小时?但凡你我能名状的数字,几乎只存在于抽象之中,无论是音乐中左右手的1∶2比例,每分钟80拍,还是房间中的“3个人”—后者中的人数确实十分严谨,但若无对“人”的抽象分类化、集合化在先,又何来计数呢?各种想象、人造之物,往往都指向一些“确定”和“名状”。人拥有大脑,但永远无法重现一个瞬间;数学让人追寻名字,但数字其实都逃逸了天罗地网。
而人又是一定要将无理数变为有理数的,这倒不是帕西克的观点,而是我在普通生活中的经历。就拿我略熟悉的音乐演奏来说,乐器上强调慢练,让身体和大脑从容同步吸收多任务,就是个神奇的隐喻:大脑中复杂的波形并不能重复,但人还是自动找到一个大约的“公倍数”,让它成为一个可重现的过程,这就是所谓学习吧。跟这种愿望相反的是,美国先锋作曲家南卡罗(Conlon Nancarrow,1912-1997)那些用自动钢琴演奏的练习曲(比如33号),声部间的节奏比也是无理数(/2),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公倍数能让它们再相遇,两手同时出发之后,再也不会对齐,音乐响起,有始无终。所以,万物或有定时否?细看之,周期都是自欺欺人,退后百步看,却又是避无可避。
布扎基的许多观点也许还没有获得普遍认可,不过在我看来极有诗意—一向被认为无规则运动的大脑神经元,居然暗含一些内在节奏,并在悄悄“指挥乐队”,虽然谁也看不准它的节拍。神经科学界对大脑活动节奏的研究似乎还比较少,大多都集中在睡眠周期、癫痫病或帕金森病等课题,布扎基的观点还没获得足够的实验佐证,但让帕西克,也让我惊喜不已。大脑乃世上玄妙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敢猜测着去认知它。
多相平行,意识和身體合成了人。这是帕西克书末的话。我深有所感的是这个寓言:多相、无理数比例,都指向生命的“不可能”,它终将粉碎,终将离散。万物之周期和不成周期之间永存张力;人类用自己不能重复瞬间的大脑去丈量同样不能重复的世界,却又顽强地追逐周期感、时间感,并以此求索模式,圆整乾坤。我们居然多多少少做到了这一点,在一个不能名状的世界中不倦地开口,叫出了万物。在那些呼喊不出的时刻,人又会制造新话语去类比和“备份”那些不能言说的。从另一个方向看,大脑多相,故言说所不能至之处,世界多歧。
参考书目:
1.Polyphonic Minds: Music of the Hemispheres, by Peter Pesic, MIT Press, 2017;
2.Rhythms of the Brain. by Gy?rgy Buzsák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The Brain from Inside Out, by Gy?rgy Buzsák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4.A Day in the Life of the Brain, by Susan Greenfield, Penguin, 2016;
5.Wondrous Strange: The Life and Art of Glenn Gould, by Kevin Bazza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Solitude Trilogy: The Idea of North (1967); The Latecomers (1969); The Quiet in the Land (1977), produced by Glenn Gould;
7.Late Nights on Air, by Elizabeth Hay, McClelland & Stewart, 2007;
8.The Path To The New Music, by Anton Webern, Edited by Willi Reich, Universal Edition, 1963;
9.Return to North: The Soundscapes of Glenn Gould, https://www.cbc.ca/radio/ideas/revisiting-glenn-gould-s-revolutionary-radio-documentary-the-idea-of-north-1.4460709CBC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