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瓦斯科维什是波兰靠近捷克的一处小山村,山谷里只有这一处聚落,在这里手机经常收到捷克的信号。书里介绍,“在地图上只能看到一条路和几栋小房子,没有任何的文字标注”。确切说,一共是七栋房子。杜舍依科女士、大脚和鬼怪,三位独居者是村里常住居民,其他几栋木屋是城里人夏季休闲度假的别墅。冬季来临,城里人离去,杜舍依科女士替他们照料房屋。这地方人烟稀少,四周是麋鹿、野猪和狐狸出没的山野,不免孤独与荒凉。
托卡尔丘克小说《糜骨之壤》将故事设置在这样一个地方,是用悲伤的语调定义眼前的世界。所谓人与大自然的话题,也是人与人的故事。
地图上那条路,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连接着数公里外的柏油马路,通往别的村子和乡镇,通往有商店、诊所、消防站和教堂的地方。镇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警察局。杜舍依科女士经常开车穿过山隘去镇上,有时也四处转悠。在这个故事里,许多场景推至村子以外,情节勾连着森林与乡镇,不多的几处空间构成某种互动关系。
这儿冬天很冷,“不向冬天低头”的女主人公和两位男士,习惯于人世的冷漠,他们都是独往独来的孤僻老人。三人中间只有大脚是这儿的原住民。
故事一开始,大脚就死了。杜舍依科和鬼怪给他料理后事,他们给尸体穿衣服时,发现一根动物骨头卡在他喉咙里。在大脚的房间里,他们发现砍下的鹿头和鹿角,他是在食用鹿肉时被骨刺卡住噎死的。一个生物吞食了另一个生物,然后刽子手就这样遭到了惩罚—杜舍依科这样想着,想到这人一贯偷猎和盗伐木材的非法行径,他早就应该遭受天罚。
然后,奇怪的命案接踵而至。乡镇警察局长莫名其妙地死在井里。森林里发现福南特沙克的尸体,他经营的养殖场里的白狐都跑了出去。采蘑菇爱好者那场舞会后,活跃于政商两界的董事长也死在林子里。最后,沙沙神父家中着火,神父被烧死。这是本书的几个核心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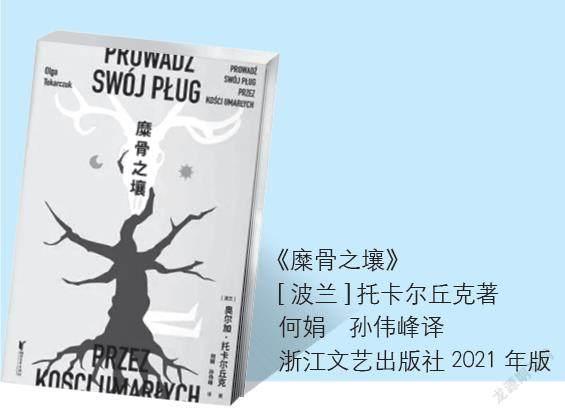 bFi79wfIIxnxZCAKETs1H4yU47sJgLOmoyT8wo3YtE4=
bFi79wfIIxnxZCAKETs1H4yU47sJgLOmoyT8wo3YtE4=虽说疑案迭现,警方却总是草率地走个过场。托卡尔丘克并不着眼于侦探过程,显然她不想写成一部犯罪小说。自大脚和警察局长身亡后,主人公杜舍依科女士几次敦促警方查明案情。不过,她认为几桩命案都是动物的报复。死者尽管身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偷猎者或狩猎者(在她看来二者没有区别)。女主人公的言行给小说赋予浓厚的环保主义色彩,她对狩猎、伐木、采石这些人类干扰大自然的活动都深恶痛绝。
因为一同处理大脚的后事,女主人公和鬼怪开始有了交往。“鬼怪”是她给人家取的绰号,这人身材纤细瘦骨嶙峋,活脱是素描草草勾勒的人形。他原先在马戏团工作,不知是会计还是杂技演员。大概由于原生家庭的某些问题,或是杜舍依科所谓男性随着年龄增长患上的“睾丸素自闭症”,鬼怪是那种很难与人交往的性格。这人精细,好像有洁癖,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小说对鬼怪自己的核心家庭没有交代,但他结过婚,有一个在本地做警察的儿子—书里出现过几次,杜舍依科称之为“黑大衣”。不过,在这个故事里,他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很容易混入所谓“沉默的大多数”。
奇怪的是,书中竟没有提及女主人公自己是否有过婚姻和家庭,也没说起她是否有子女。只是在梦中出现过她的母亲和外婆。她为什么要搬到边远的普瓦斯科维什居住,也不见说起。
托卡尔丘克笔下,这种缺省处理或是作为性格塑造的一种手法。
夏天到来时,一位名叫波罗斯的昆虫学家进入森林。他在调查红翅扁甲虫的栖息地,欧盟对于腐生甲虫有一整套详尽的保护意见,波兰林业部门对此显然未予重视,专家很气愤。杜舍依科听他讲述虫卵和幼虫如何在树木上孵化和生存,得知木材一旦被送往锯木厂,甲虫就“毫无痕迹”地死去。在她看来,这种无人知晓的死亡便是莫大的“丑闻”。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糜骨之壤》海报,2017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糜骨之壤》海报,2017她想知道哪些虫子是有用的,这个问题差点惹恼了昆虫学家。波罗斯告诉她,在大自然领域,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说。他说的很专业,物种分类有其科学的客观依据,不能凭着对人类是否有用来定夺。颠覆人类中心主义是环保人士的重要理论,多元主义示意将人本主义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整个生物界,这关涉若干基本伦理问题。
喜欢思考的杜舍依科女士绕着屋子转圈,一遍遍地思忖生命的价值含义—
是谁把世界划分为有用和无用,又有什么依据?难道蜚蠊就没有活着的权利?在仓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呢?还有黄蜂、雄蜂、野草和玫瑰,它们都没有权利活着吗?谁有这样的智慧去评判孰优孰劣?
她跟昆虫学家相当投契,只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他对那个叫国家林业局的机构抱有情绪化的态度。鬼怪见她屋里来了陌生男人,感觉有些怪怪的。他们喝了酒之后,波罗斯装着弹吉他的样子唱歌,唱大门乐队的摇滚歌曲,循环往复地唱道:“一个孤独的演员,风暴中驰骋的骑士,从我们的诞生之地出发……”她让波罗斯在自己家中留宿。普瓦斯科维什的雷鸣之夜。她掀开被子,让他睡过来。上了年纪的人,已经没有年轻人的激情和缱绻之意,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同志。
杜舍依科是知识女性,早先是桥梁工程师,后来做過教师。这时她已退休,不过还在附近乡镇学校兼课教英语,课时不多,一周只去一次。现在她的活动范围不出乡镇小社会,但是她操心着人与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关系,在她眼里,万事万物皆有联系。
小说是第一人称叙事(这一点很重要),一切都从她的视角写出,自然伴有大量内心活动。比如,她热衷星象学,遇事都要研究星盘运势,书里经常是大段大段的基于星历计算的推理,包括那些类似中国人对于生辰八字的说法。这让人觉得她有些神神叨叨。她试图说服迪迦,星象星变是人事休咎的重要征验,从希特勒遇刺到斯大林去世,再到瓦文萨崛起,都能从星盘变化找到依据。迪迦是与她合作翻译布莱克诗歌的一位年轻人,在镇上的警局做文员。迪迦问她代表警察的是什么行星,她说是冥王星,不过它还代表情报部门和黑手党。
 电影《糜骨之壤》剧照
电影《糜骨之壤》剧照作为叙事人,杜舍依科的言述颇有幽默感,语调平和却很随性,能感觉到她很自负,带有某种强迫症,有些中国人说的一根筋的特点。当然,她也不失女性的温婉和敏感,以及岁月积累的历练和成熟。总之,这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性格。她觉得波罗斯过于情绪化,其实她自己内心充满愤怒,她早已向警方举报大脚的偷猎行为。但警察认为,她干扰合法的狩猎活动是一种过激行为,她纠正说,不是过激,是愤怒。
在镇上庆祝圣休伯特节的活动现场,沙沙神父滔滔不绝地为狩猎布道,那些言辞当场激怒了我们的女主人公。她挺身而出,大声抗议。她知道,神父也是那伙狩猎队中的一员。
警方曾怀疑杜舍依科涉嫌董事长命案,因为听说舞会后董事长是搭乘她的车离开的,她被带到警局问话。她说她当时在外面抽烟,舞会结束时就没见他人影,她里里外外都找过。警察没有确切证据,因为没有人看见董事长上了她的车。警方询问时还提到警察局长和福南特沙克的命案,她尽量详细陈述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说着说着忍不住搬出那套占星术理论给警察上课。她被拘留四十八小时,然后被开释。
其实,董事长死后,迪迦和鬼怪就对她产生了怀疑。他俩是最接近她的人,注意到她一些异常行为。这时传来神父家中遭遇火灾的消息,一切都跟狩猎活动联系到一起了,很容易联系到她的一贯立场,她对动物的关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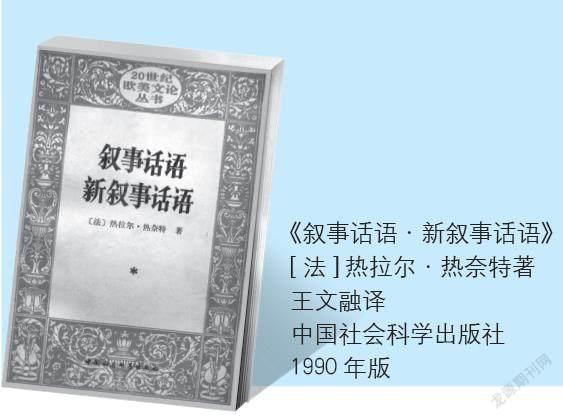
在临近结尾的倒数第二章,杜舍依科向他们坦白了自己作案的过程。原来那几桩命案都是她一人所为,是她在替动物们报复人类。大脚的屋里留下一张集体狩猎照片,她据此按图索骥地寻找目标—警察局长、福南特沙克、董事长和沙沙神父,都是那张照片上的人物。前面三人都是被某种“表面光滑、坚硬的大型工具”击中脑部,警察一直想不出那凶器是什么物件。谁知她是将冰块装在塑料袋里作为重击的武器,拎起塑料袋提攀,像掷链球那样甩到人家脑袋上(这老太年轻时拿过链球全国亚军)。干掉福南特沙克时,她在林子里设置了捕猎陷阱,先是套住他的腿脚,然后挥动塑料袋里那个“冰冷的拳头”。她还偷了波罗斯用来引诱昆虫的信息素,击倒董事长后将那东西洒在他身上,制造了昆虫爬满尸体的现场。她用大脚留下的鹿蹄在雪地里弄出动物袭击警察局长的假象,让毙命者头部留下动物血迹,似乎是动物充当了连环杀手的角色。
在犯罪小说里,这都是不错的桥段,但从她嘴里这样和盘托出,只是最后的释疑。如果编织在探案推理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迷雾重重的悬疑效果。当然,托卡尔丘克不是作侦探小说,叙事重点不是谋杀过程,是谋杀的行为动机。
小说理论家讲到第一人称叙事,主要讨论人称与叙述层、视角局限,或是如何突破那种局限的巧妙僭述,等等。其实,它有一个不常被人提起的特点,就是让读者产生面聆坦言的近距离感觉,使叙述更显得真实可信。面对第一人称的讲述,读者通常是毫无选择地相信叙事人所说的一切,同时其性格和喜好亦往往在言语中纤毫毕现。这跟生活中的情形不太一样。平时听到一个陌生人在说什么事情,你未必毫无保留地相信人家所说的。故事内的“我”就不一样,这陌生人总是成了信得过的人,这是叙事文本颇为神奇的地方。
譬如,就像现在面聆杜舍依科女士的言诉,因为她是作为叙事人的主人公,你就没有把她当作陌生人。她用她第一人称的可信性维持着一种“不可靠的叙事”,把你骗到最后。
也许不应该用“骗”这个说法,这样说不太恰当,她所说的一切无非是选择性陈述,或者只是向警方隐瞒了某些事况。正如热奈特所提示的,不能将故事内的受述者与读者相混淆(《叙事话语》第五章),她那些误导性陈述都是说给警察听的,而非针对读者。如果你不想找事儿,或许你在警察面前也会这么说。
最重要的是,她用自己那些言述,包括那种执着而无助的形象,关于星座的迷思,以及种种天真纯朴的感受,在读者意识中建立起叙事的正义性。
迪迦和鬼怪没有向警方告发,他们对她的动物保护主义的环保理念显然有相当程度的认同。迪迦在布莱克的书里给她留下暗示,警方已将她锁定为目标。书上迪迦用铅笔画了线的一段话里,有这样几句:“能够解读星象的人,常受星象影响之苦……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的主体,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罪犯呢?”
一向颟顸的警方终于开始行动了。当警车驶入村里,她躲进锅炉间和车库之间的小暗室,小心躲过了搜捕。警察收队的时候,她在暗处听见鬼怪对他那个做警察的儿子大声嚷嚷,“等她出狱,我就跟她结婚!”
当然,她并未经受牢狱之灾。趁着夜幕,她翻山越岭逃到捷克境内。处女座在捷克的天空亮了起来,她在这边的納霍德市的书店里找到自己的朋友。过了几天,波罗斯开车来了,为她举办了一个假葬礼,杜舍依科女士从此人间蒸发。看到这里,或许会有读者想起小说开卷第一章的题记,是引用威廉·布莱克的诗句:
某次,一个温顺、正直的人
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
从此便向着死亡之谷走去。
有一点很明确,杜舍依科女士跟她谋杀对象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不能说完全没有,只是他们中间有人杀了她的狗),亦非出于利益之争,而是某种信念支撑着她,使之一再挥起那个“冰冷的拳头”。
杀死动物的狩猎者都是罪犯,于是她杀死那些罪犯,将自己变成了罪犯。这是小说的基本敘事逻辑。以动物们的名义问罪复仇,将正义诉求变成了擅用私刑的一桩桩血案。读者不难从法律角度认定其行为正当与否,但是其中涉及的伦理困境未免让人晕眩。环保主义的高尚动机,为何衍生出反社会的极端行为?可是,波罗斯、迪迦、鬼怪,还有镇上的牙医,以及那个被杜舍依科称为“好消息”的服装店售货员,这些人都成了她的同情者甚至是她的同道(甚至来村里度假的女作家还认为她是这里“唯一的好人”),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都是让人掩卷深思的问题。
细思极恐,且令人匪夷所思。极端环保主义者所怀有的悲剧式的献身精神,以煽情与感伤气质掩饰着思想的荒诞,让理想与情操将人们推向迷惘之地。
地理上的普瓦斯科维什是一个边缘性隐喻,杜舍依科女士游走在社会和法律的边缘,她自己说过,已经没有哪个地方能让自己产生归属感。她不屑于与世人同流合污,对于普世价值自然心怀抵触,她默默地想着:“我为什么要屈服于它们,按照它们的要求思考呢?”
故事最后,她隐居在捷克某处原始森林边上的昆虫观测站,那无疑是波罗斯的领地。已经成为“死人”的她,现在自然无事可做,每天绕着自己的房子转圈,一次朝这个方向踩出一条小路,一次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她常常认不出自己在雪地里留下的脚印。

托卡尔丘克这部小说,看上去丝毫不涉及政治问题,只是杜舍依科依稀流露对之前那个逝去的时代的怀念,当然怀旧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作为叙事话题的环境和生态意识形态,实际上正是后现代政治议题的转换。这是后冷战时期的政治正确。知识界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权运动,动物保护主义与种族问题、嬉皮士运动、女权与性别认同,等等,都是从那个时代兴起的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当阶级斗争派生的诸多意识形态问题开始淡化,许多前卫人士纷纷从传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某种非物质主义价值观。像杜舍依科就是这类人物中的“这一个”。
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如今已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说到底,杜舍依科女士那种极端思想也是基于这种普世的价值理念。但是,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人们更进一步,她亟望修改法律,给予动物与人类相等的地位和权利。那次,她在市政部门控诉捕猎野猪的那些人,面对表情麻木的办事员和一只贵宾犬,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她大声疾呼—
事实上,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在生存和适应环境方面提供帮助,给予它们对等的关怀和爱护,因为在这方面它们给予我们的要比自己得到的多得多。要保证它们能够有尊严地活着,给它们埋单,使它们能在每学期的营养成绩册上拿到学分。我也曾是动物,也生存过,吃过……
她是把野生动物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这有错吗?当然她不会不知道,在她伸张动物权利的同时,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有无数的人们尚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可是现实的苦难并不影响她拯救动物的激情。
人们在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就像杜舍依科女士强调蟑螂和老鼠都有生存的权利,实际上更多转向了动物中心主义,或是另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二○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