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在哈佛作家工作室任教,要求在座的每个学生现场背诵一首诗。有位学生選择了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代表作《爱丽尔》—“一嘴黑甜的血,阴影,及其他”(Ariel, by Sylvia Plath,自译),“请不要选这首,我已经厌倦西尔维娅·普拉斯了。”格丽克评论道。
那一年,露易丝·格丽克尚未加冕诺贝尔文学奖。那位读诗的学生,莱斯莉·贾米森,还没有写出让她一举成名的非虚构文集《十一种心碎》(The Empathy Exams)。
众所周知,普拉斯的批评者们认为她囿于几近偏执的个体伤痛。后来,格丽克的诺奖授奖词是“让个体性的生存具有普遍意义”。一位深谙个人痛苦之深邃的伟大女诗人,否定了另一位化痛苦为绝唱的女诗人。这令年轻的贾米森备感失望。
我是人:但凡人性,皆非陌生。
—泰伦提乌斯
一九八五年,西尔维娅·普拉斯自杀二十二年后,莱斯莉·贾米森出生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往前倒推三年,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改变了美国诗歌创作方向”而成为第一位死后被追授普利策诗歌奖的美国女作家。在她去世前三周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的开篇,普拉斯写到间谍卢森堡夫妇被送上电椅的那个夏天,“我老是禁不住去琢磨,电流沿着人的一根根神经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生生烧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而这道电流烧过普拉斯的神经,以某种神秘的导体,流经贾米森的脊椎。
在这部小说里,普拉斯抛出的问题是:一个八岁写诗、十八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十五年功课全优,赢得全世界最大的女子学院全额奖学金的女孩,为什么突然睡不着、读不进也写不了任何东西,被关进疯人院,被囚禁、被电击。在外界看来,普拉斯有着太多“个体问题”(作为二战后的德国后裔,极尽自卑;九岁时父亲去世;丈夫出轨),这部小说是“彻底的忘恩负义”。她的诗歌局限于私人情感的表达,爱情的幻灭、精神分裂的迷狂,包含着令人战栗的黑暗和力量。人们诟病她的自怜,言语间的暴露癖,意志的缺失乃至正能量的匮乏。
“西尔维娅和我一样,我们都为那伤口的浓稠而沉醉—为它战栗,然后深感羞耻。”在《关于女性痛苦的大一统理论》一文中,贾米森共享了这种“痛苦的囤积”。如果将普拉斯的问题换算成贾米森的,那么,或许可以局部地表述为:一个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哈佛、耶鲁毕业的知识女性,为什么对自身的存在充满耻感,为什么急于渴望男性的关注,饮食失调、严重酗酒,自损于支离破碎的恋情。看上去,这也是个人的:她的家族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过至少一次离异史;在童年,家中的男性总是缺席的,备受仰慕的父亲、经济学家迪安·贾米森永远在前往全世界各个国家工作的路上,而且经常出轨。在某种程度上,普拉斯和贾米森的自白可以进一步推演为女性共享的主题:不满足的、被抑制的自我,对男性的崇拜与反抗,背负自怜自艾、多愁善感的罪名,声张痛苦的权利被取消……经过时间的验证,这些个人情绪的演绎越来越散发出普适化的光泽,痛苦作为一种复杂而不可或缺的权利,指向了全人类的范畴:精神痛苦(一只歪曲视像的钟形罩子)及其慰藉—对同理心的呼唤。

同理心是贾米森写作的基点,是让她蜚声文坛的非虚构处女作《十一种心碎》的主题,也是她的自白式写作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底层假设—一种超越唯我论的可能性,它承认了个体没有死板的边界,是有孔隙、可互渗的,人与人之间有着万有引力般的法则。她在《在威士忌和墨水的洋流》(The Recovering: Intoxication and Its Aftermath)中对此有明确的阐释,这一顿悟是通过贾米森本人以酗酒者的身份参加匿名戒酒互助会的经历发生的,她在酒鬼们千篇一律、不约而同的自述、共鸣和混响里发现了“陈词滥调”的价值,它意味着我们并不像自己所认为、所宣扬的那么独一无二。人类灵魂有着近似的肌理,汇聚成教堂地下室里的一曲和声,上升为一种至高的存在,一个更大的梦。这让她敢于以自白的方式创造性地将非虚构新闻调查糅合于对自我的活体解剖,不讨喜地“将内心最难以启齿的那一面启齿诉说”—对男性目光的贪婪渴求,病态的自我放纵,情感关系中的自私和背德—行文往复不断地回到“我、我、我……”寄望于这个“我”经由一条原初的、隐秘的地下河流,终将通往其他的“我”。百分百的同理心是可能的吗?贾米森本人也未能如此断言。但毫不意外,对贾米森“自我中心”的接受度是评论界与大众对贾米森观感的分歧所在,前者不吝溢美之词:“不断解构和突破着自己对于痛苦的认知,将自己关于医学和心理学的个人经历投入思考,将这一切变成对于自己的一场考验。”(《纽约客》)后者指认她借同理心的光环自我陶醉。
需要指出的是,自白者从不是灵魂的牧羊人,完美无缺的同义词是虚伪。他是与所有人同行的迷途羔羊,命运推动他往前踏出一步,在自白中超越自白,缝合创伤,洗净血骨。如果足够幸运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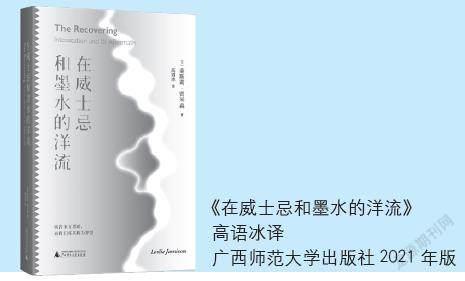
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痛苦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对她自己的屠杀,莱斯莉·贾米森的痛苦经由书写衍生为一场敞开的对话,收到了无数读者的回响,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是为了活下去。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琼·狄迪恩的《白色相簿》以这个著名的句子开头。在莱斯莉·贾米森的第三本非虚构集《52蓝》(Make It Scream, Make It Burn)中,它的一个变体“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是为了再活一遍”成了其中一个故事的标题。当《大西洋周刊》说“这个时年三十岁的女孩是琼·狄迪恩和苏珊·桑塔格的孙辈,近半个世纪以前……《向伯利恒跋涉》与《反对阐释》为文学自省的强度与思考的激烈程度立下了令人生畏的标准,《十一种心碎》是这些前辈的后继者,但另一方面,贾米森的文字中那混合着哲思与机智的特有温度已经为这种写作方式开拓了另一种全新的方向”时,将贾米森视作狄迪恩的后继者并非停留在纸面上。
大学毕业启程前往拉丁美洲之际,贾米森的脑海里毫无疑问飘浮着狄迪恩的影子。作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潮流中升起的文化偶像,狄迪恩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写作范式:沉浸式的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真实”(truth)取代了“事实”(facts),文学技巧压倒了客观记录,提醒着写作者的在场和人性感知世界的方式。
一九八二年,琼·狄迪恩和丈夫前往内战中的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进行了一场为期两周的旅行,写下《萨尔瓦多》(Salvatore),对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质疑。三十年后,贾米森前往玻利维亚的波西托,降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银矿,在矿井深处直面底层工人代代相传的死亡。
狄迪恩正面记录了自己听见恐惧的齿轮转动,自己的内心被击溃、被羞辱的时刻:清晨在著名景点也是抛尸悬崖,似乎正在上驾驶课的一男一女;路中央的尸体赤身裸体,在这个国家把衣服留在死人身上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情;圣萨尔瓦多的超市里充斥着法国鹅肝酱和印着曼哈顿地图的海滩大毛巾……在玻利维亚的超市里,贾米森着迷于拿着本子做笔记,记录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新鲜沙拉和荷兰罐装奶粉上面色红润的姑娘。抓住贾米森的恰是狄迪恩所表达的溃败和力不从心:“我忠实地将它记录—一种我知道如何去演绎的‘色彩’,一种归纳性的讽刺,一个足以给整个故事画龙点睛的细节。在我将它记录下来之时,我意识到我不再对这种讽刺感兴趣,这个故事也不会被这样的细节点亮,这也许将是一个没有任何精巧谋篇布局的故事,甚至,比起故事,也许这更是一个真实的暗夜。”(Salvatore, by Joan Didion, 自译)
狄迪恩在场,狄迪恩讲述。贾米森在场,贾米森成为坐标中心,她像一个旋涡把世界吸入自己的世界,包括她当时正在阅读的狄迪恩。“我常常感到自己就是被狄迪恩摒弃的那种角色,迷失在超市的过道里,不断寻找各种细节,我是来找净水药片的,却在离开时买了一本带着价签、写满了国家苦难的简读本。”(《十一种心碎》)这是异国他乡的社会观察,更是贾米森自己内疚自省的“生活研究”。
“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是为了活下去。”狄迪恩的论断中所揭示的叙述与存在的关系,可以视作贯穿《52蓝》全书乃至贾米森整个写作史的线索。在贾米森的故事里,人被自己的生活所震慑,作为一种防御,他们吐出话语虚空而坚实的丝,编织出自欺的茧将自己包裹、保护,免于坠入崩溃、绝望的空洞:一个重病的纽约单身女人自称与世隔绝,却声称和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产生了精神共鸣;一个照顾着一对自闭症双胞胎的母亲已经足够筋疲力尽,却在每天早上五点半起身,只为步入虚拟游戏蓝绿色大理石泳池边永远不需要起身的生活;一位摄影师用二十五年、两万三千张照片执着于帮助和记录一个墨西哥家庭,事实上他们对她的意义要比她对他们更多……人讲故事的本能是不可遏制的,它定义了我们。这种“叙述”不仅仅局限于个体谵妄,也膨胀成为集体梦想,它在贾米森笔下延伸到战争摄影师的镜头语言,乃至饱受内心煎熬的作家詹姆斯·安格在写下他的纪实名作《现在,让我们赞美伟大的人》时字里行间尖叫的愧疚感。

最终,贾米森开始对狄迪恩的怀疑产生了怀疑:“狄迪恩重申了她对于所有这些‘故事’及其虛假的连贯性的怀疑……她如何在一个充满自欺的世界里,将自己说成看破一切的怀疑论者。”(《52蓝》,高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贾米森的态度经过同理心的软化,包含了更多对人类的温柔和宽宥,“或许我太害怕了,对于人们为了继续活下去而跟自己讲的故事,没有办法予以拒绝”(同上),也因为她就曾是一个只有依靠不断对自己编故事才活下来的人。在书中,贾米森袒露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拉斯维加斯恋情,他具象化为一盏牛仔形象的霓虹灯,他唇间的烟头飘出的是真实的烟雾。这场异地恋是刚刚经历分手、急于用一段新的关系胡乱修补破碎心灵的贾米森和对方精心维护的一个白日梦—午夜赌场里的鲨鱼缸、摩天大楼顶层的套房—像一颗人造莱茵石,有且只有迷人的一面,和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一样,炫耀着真诚的虚假和美丽,不可能实现的愿景,也最终要在日光之下原形毕露。
叙述的背后,原动力是比海更深的渴望,因渴望而泛滥,而上瘾,而迷失,而复原。“生活的定义之一或许就是故事线永远都在改写。我们把为自己写好的剧本交出来,换得的是我们的真实人生。”这是人生的惊奇给予贾米森的答案。
评论家迈克尔·罗宾斯评价露易丝·格丽克:“每一首诗都包含着露易丝·格丽克的激情,隐含着露易丝·格丽克的哀伤和痛苦,但是,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和写出这样的诗歌。”
在这个“但是”里,贾米森敏感地嗅到了异样的气味:一个诗人,只有用智识和技巧跨越自己的痛苦才能成为“重要的”诗人。
我们总是追求极尽宏大,掘进于时代、国家、民族、种族、阶层的地层。
个人的宇宙是渺小的吗?是的,同时也无限广阔。
正如贾米森文在手臂上、提醒自己的这句箴言:“我是人:但凡人性,皆非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