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下二册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算是了却他藏在心中十年的一桩宿愿。一九四二年,他被关押在日军监狱时,曾许愿“再做一种关于杜诗的著作”,到此终于得偿。此书出版十年后,他专门撰写了一篇《我怎样写杜甫》,在《南洋商报》一九六二年元旦特刊上刊发。在这篇文章中,他纵谈家事、国事、天下事,详细陈述了自己撰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堪称作者的夫子自道。香港《人生》杂志、台北《中华杂志》等报刊先后予以转载。一九六八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还出版了陈湘广(Charles K. H. Chen)的笺注本《我怎样写杜甫》,可见此文在当时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一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曾祥波中译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在书后附录此文。显然,此文对于理解洪业其人及其杜诗学是十分重要的。
《我怎样写杜甫》应该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娓娓道来,流畅生动,特别好读,虽然时过境迁,仍然有一种如临讲演现场的氛围。《洪业传》作者陈毓贤对洪业的讲演水平赞不绝口,对我这样无缘一见洪业、更没有荣幸领略其讲课或讲演风采的晚辈来说,读过此文,好比旁听了洪业的一场讲座,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在这场讲演中,洪业对《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有这样言简意赅的描述:“上册是本文,下册是子注。在上册里,我选译杜诗三百七十四首来描写杜甫的生平,说明其时代之背景与史实的意义。在下册里,我注明各诗文的出处,中外人士的翻译,历代注家的讨论,时常也插入我的驳辩。再概话来说:上册说杜甫是这样的;下册说杜甫不是那样。上册迎神,下册打鬼。”这是对此书内容与主旨最简洁生动,也最提纲挈领的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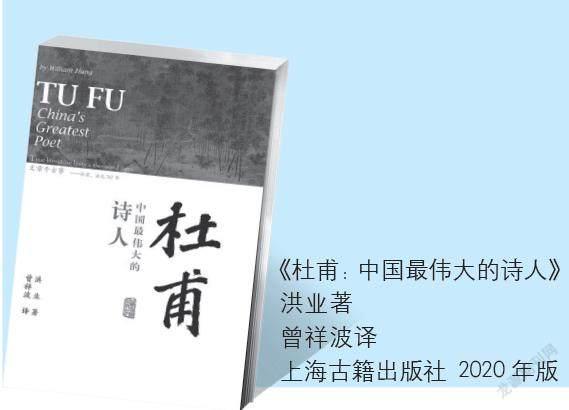
在这里,我要特别揭出“迎神”与“打鬼”这两个词,它们不仅突出地呈现了洪业的语言表达风格,而且体现了洪氏杜诗学的特点。所谓“迎神”,是正面塑造杜甫的形象,确立杜甫的历史地位。这一方面,历来治杜诗学者用力良多,成就显著,无论是历史上的“诗史”之称,还是洪业在本书标题上所标举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称号,皆是迎神功绩的表现。所谓“打鬼”,是对历来加于杜甫、杜诗或杜集身上的谣言、误说、讹传,以及各种不实之词进行考辨、订正、洗汰,力图肃清其影响。这一方面,历来学者也煞费苦心,成绩虽然不少,问题依然尚多。最值得重视的是,在杜诗流传过程中,有些旧“鬼”尚未驱走,仍在以讹传讹,而新“鬼”又从而滋生。
洪業在《我怎样写杜甫》中说:“鬼有中外大小之分别,打有轻重疾徐之别。”只要是“鬼”,不分中外古今,他一概都打,视其危害性之大小,打法有轻重疾徐之别。我对洪业打外国“鬼”特别感兴趣。毕竟其他杜诗学者罕有这一方面的条件,更少有这一方面的业绩。这是洪业杜诗学的重要业绩之一。在《我怎样写杜甫》中,他举了几个离奇有趣的例子,其中一个是:“乾隆年间,在北京,有一位饱学多才、著作等身的西洋传教士,汉名为钱德明,字若瑟。他老先生有一篇用法文写的《杜甫传》,可算是最早介绍杜甫的专文。他写到离开史实愈远愈妙。”譬如他写到安禄山的队伍在道上捉住了杜甫,几个军官报告给目不识丁的安禄山,问他要不要将诗人带来供他消遣云云,真是不知有何根据。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总之,“钱德明把杜甫写成一个很有趣而甚无用,忠君爱国而遁世逃名的诗人,写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这当然与真实的杜甫有很大的距离。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是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后深受乾隆皇帝信任,在北京生活了四十二年,在十八世纪来华传教士中算是汉学水平很高的,当代学者或称其为“十八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龙云《钱德明: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但是,他文章中对于杜甫的诸多异想天开的描写,亟应予以澄清。
洪业在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在杜甫身后一千多年,居然出来一个外国女诗人,冒充杜甫写作。这些诗见于一本用法文翻译的中国诗选,书名汉译过来叫作《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亦称《玉书》。“这是法国一位有名的青年女诗人在她二十三岁的时候,用假名发表的。书中选有杜诗十四首,二首是别人翻译真杜诗,而此女为改头换面,遂与原译不同。十二首全由这位女郎为杜甫捉刀:无论题目、字句、意义、神态,全与杜诗无涉。此书于一八六七年出版,流行甚广。”《白玉诗书》问世以来,已经重版了四次,后来又出了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丹麦语等多种语言版本,抄袭仿作也不少。这些“洋装的假杜甫,登台表演”,误导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让洪业慨叹不已。
 洪业
洪业这两段故事可以说是杜甫接受史和杜诗传播史上的“今古奇观”,但是,洪业叙述时的语气,仍是一如既往的温柔敦厚。《白玉诗书》作者是朱迪特(Judith Gautier),一开始化名为“Judith Walter”。洪业在文中有意不提这个作者(译者)的名字,是有意替她藏拙。这种嫁名中国最伟大诗人的诗歌创作,作为文化挪用或者文学误读来看,也许是不无趣味的个案,但是,从杜诗传播接受史来看,在喜欢把考据当作侦探办案的洪业眼里,朱迪特小姐就不免被看成一个嫌疑犯了。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实际上就是一部《杜甫传》。在我看来,洪业以英文撰著此书,主要面向国外读者,其目的在于把杜甫这个中国的“诗神”迎到英语世界去,当然不能不在书名中标举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历史地位。现在译回汉语,为了忠实于原文,尊重洪业书名原意,直译其名,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灵活一点,更多地尊重中国著述命名的传统习惯,完全可以译为《杜甫传》,或者《杜甫评传》《杜甫诗传》,至少更简洁一些。当然,书名可以中式,亦可以西式,这是见仁见智的事。

二十世纪以来,致力于杜甫研究或者杜集整理笺注的学者可谓多矣,举其名家,则有闻一多、刘文典、岑仲勉、郭沫若、程千帆、叶嘉莹、谢思炜等先生;为杜甫作传者也不乏耆宿名家,比如冯至有《杜甫传》,朱东润有《杜甫叙论》,陈贻焮和莫砺锋皆著有《杜甫评传》。与上述诸多名家相比,洪业的杜诗学有什么特点呢?
洪业的杜诗学,可以远溯至他的少年时代。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开始圈读清人杨伦的《杜诗镜铨》,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对杜甫和杜诗的理解。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目睹卢沟桥事变和华北沦亡的时势和国势,他对杜甫和杜诗的理解也逐步深入。他越来越深刻地理解父亲当年说的话,杜诗是学诗的典范,杜甫则是做人的典范。他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书中最后一段话是:
他(杜甫)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长,是忠诚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职的官员,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入的研习,得以理解人类本性的力量和脆弱,领会政治的正大光明与肮脏龌龊。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国度。
最后这句话曲终奏雅,画龙点睛,指出了杜甫的当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当代性和世界性,我以为,正是洪业杜诗学最为着力之点,也是其显著特色之所在。

一九四○年,《杜诗引得》出版。这是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编纂的第一部诗集引得。洪业撰写了长达六万多字的长篇序言,文中说:
昔在宋时,已有麻沙传孙觌《杜诗押韵》,元时有曾巽申《韵编杜诗》十卷,皆学者寻检《杜诗》之工具也。其书皆早佚,不可知其详。清康熙时练江汪文柏编《杜韩集韵》二卷,仅可检知《杜诗》曾否押此韵,是否有此句耳,不能得其题,不能知其在集中之卷第也。朝鲜摛文院编有《杜律分韵》五卷,仅录律诗,以韵编次,非可以检《杜集》某本中之某诗者也。近日本饭岛忠夫、福田福一郎合编《杜诗索引》,先以仇氏《详注》目录逐题编号,然后以杜句之末字,按五十音顺编入《索引》,下注见某卷第几题,凡知《杜诗》全句者,用之甚便。唯学者之于《杜诗》,有仅知句中二三字而欲检其全诗者矣,有欲知其诗中之习用字眼所曾道之名物者矣,此《索引》不足以应用也。按西人于其重要之诗人,辄为编一字不漏之“堪靠灯”(concordance),极检寻应用之便,今编《杜诗引得》,盖师此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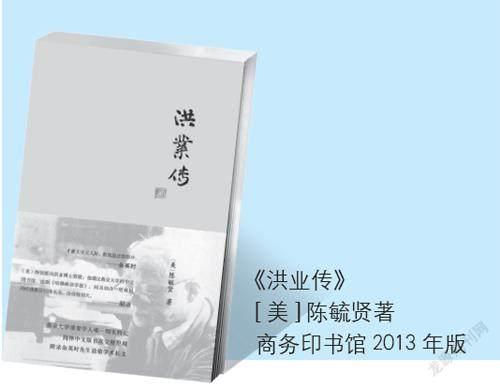
这篇序文是迄止一九四○年关于杜集编纂流传史的最新、最全面的成果,上面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一篇简短的杜诗索引编制史。作者的目光,不仅上溯宋代,而且及于朝鲜、日本等东亚汉文化圈,更遠至于西洋。在洪业眼中,《杜诗引得》的编撰,不仅要超越古人,更要超越外国人,使此书一出,便能在世界汉学史上成为最为实用、最为方便的检寻工具和学术参考。从这篇序言中可以看出,洪业致力于杜诗学研究,一开始就是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自觉。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洪业写信给他多年的师友、哈佛燕京学社托管委员的埃里克·诺斯,表示希望到美国讲学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与外界隔离了四年,对这四年学术界有什么进展都不知道。很急于知悉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和自由中国的汉学活动。”(陈毓贤《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3年)实事求是地说,这四年(1941-1945)美国汉学界虽然有些新的进展,但并没有出现与杜甫研究直接相关的重要成果。但是,在哈佛大学讲学,显然方便利用哈佛大学的藏书,也方便请教相关的文献专家,这是一九四○年至一九五二年间的燕京大学所无法比拟的。不妨将《杜诗引得》与《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作一比较。《杜诗引得序》除了评述日本学者近编《杜诗索引》之外,只引用并评述了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的英译杜诗以及德国学者萨克(Erwin von Zach)的杜诗德译本。英译本和德译本皆出版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离序文撰写之时很近。在撰写《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时候,洪业利用西方汉学文献的条件今非昔比。他在书的《引论》中说:“撰有中国典籍译本书目的玛莎·戴维森(Martha Davidson)女史,惠我以大量杜诗译本书目。”戴维森编撰有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是名副其实的书目专家,洪业在她帮助下获得各种杜诗译本,并对钱德明、朱迪特(Judith Gautier)、安德伍德(Edna Worthley Underwood)和朱其璜(Chi-Hwang Chu)、艾思柯、洛威尔(Amy Lowell)、萨克、魏理(Arthur Waley)等人的杜诗译本一一检视。一九七一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戴维斯(Davis)以英文出版其新著《杜甫》,洪业除次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书评外,又于一九七四年在《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上发表《再说杜甫》一文,那一年他已经八十一岁,尽管垂垂老矣,但他一直在关注世界汉学界有关杜甫研究的最新成果。
洪业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最为自矜的一个发现是,杜甫并没有像传统杜诗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爱长子,而偏爱次子。“为何这件事对洪业来说感情负荷那么重?”陈毓贤在《洪业传》用心理学分析的眼光,作了如下推测:“莫非他潜意识里把杜甫当作(他的父亲)洪曦,把杜甫长子当作自己,而把杜甫次子当为(他的弟弟)洪端?”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无论如何,这里面体现了洪业对于杜甫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是他的“迎神”工作的一部分。在他崇拜的神面前,他是谦卑的。
陈毓贤的推测中含有一种比拟,将洪业比作杜甫之长子,这与另外一种比拟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哈佛、耶鲁等地讲授杜诗,以及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出版,为洪业进一步奠定了杜甫研究权威的地位。不仅如此,很多与晚年洪业有往来的友生也以杜甫来比喻他。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杨联陞《呈洪先生》七律一首。从诗中“朗咏新句追秋兴,细写长编注史通”两句可以看出,洪业《剑桥岁暮八首》此时已经写成,同时,洪业也已经着手注释《史通》的工程(《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一九五六年圣诞节,洪业在家里招待周策纵等友生,周策纵有诗致谢,其中也写道:“乱离老杜情何限,书卷飘零又岁寒。”(《圣诞日洪煨莲先生招宴有作》,载《周策纵旧诗存》)一九六三年,洪业寿登七十,程曦作《寿洪煨莲教授七十》表示祝贺。其中有“杜陵漂泊诗犹在,庾信栖迟赋可成”两句。洪业为被日军逮捕入狱的六位燕大同仁作《六君子歌》,诗体模拟的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其晚年诗作精华《剑桥岁暮八首》更是拟学《秋兴八首》。杜甫的声音与身影,时刻盘旋在他的生命中。总之,杜甫是洪业的神,给四十岁以后的洪业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洪业是一个诗人,自幼接受庭训,为其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之诚在《送洪煨莲赴美讲学序》中,肯定洪业“于学无所不窥,尤专精于史,著书满家,他若《左氏传》《史通》《杜诗》,皆有撰造。最为人称道者,成群书引得逾数十种,又思创为《目录学大辞典》,谓之工具书,所以省翻检之劳也。”又评论洪业之为学,“有西人之密,兼乾嘉诸儒之矜慎,实事求是,取材博,断案谨,无穿凿附会之弊,扬己抑人之习”。(《邓之诚文史札记》)洪业治杜诗,既“迎神”,又“打鬼”,其视野与手法正是兼融中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