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与语言一样,都是一种建构权力关系的媒介。观看先于语言,能够直接诉诸人的感性,并在无形中限制语言与行为的立场與内容,人无须通过言语就能在意识中形成主体建构。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多重视线交织而成的权力网络之中,通过视线来确定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确立自己的位置,并直接对人的思想与行为构成影响。
影像是视线的产物,是对视线的抽象与隐喻,并成为视线的承载物。我们在观看影像的过程中,都必须将它所蕴含的信息还原为视线,才能够感受、理解并想象其中的含义。这个过程也是权力关系的传播与建构的过程。影像所承载的知识与信仰往往会在观看者解读或欣赏影像的同时植入到他们的意识之中,在他们的思想感觉中繁殖、复制,形成新的传播与建构,逐渐让人异化为权力关系的工具。因此,自摄影术发明之后,照片的可复制性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相结合,迅速成为大众传媒的宠儿。从最初的画报杂志到后来进入每一个家庭的电视乃至现在将整个世界紧紧联系起来、人人都无法摆脱的互联网,影像都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元素之一。所有经由大众媒体及宣传渠道传播出来的影像信息,都是被扭曲、被改造过了的,被运用在了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在思想建构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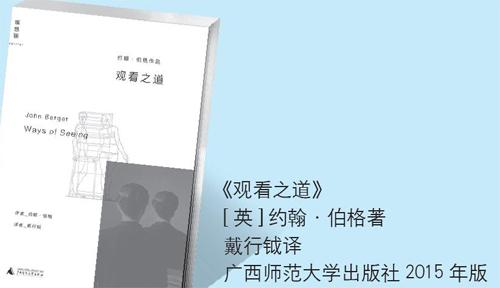
这一点在社会性别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长期形成的父权社会早就已经利用影像、语言等媒介在人们的意识中塑造出僵化的、易于控制的性别形象。一方面使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另一方面给男性贴上赚钱养家、勇敢强硬、风流倜傥等男性气质的标签,男性就必须是詹姆斯·邦德式的形象,给女性贴上柔弱、依附、顺从、乖巧、美丽、贤惠等女性气质的标签,于是玛丽莲·梦露塑造的“金发美人”形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好莱坞女神,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衍生出各种大同小异的形象,在世界各地横行。充斥于街头各类户外广告以及时尚杂志彩页中的性别形象,基本上也都是这些类型的翻版,每发行一次,这类僵化的性别意识就加固了一层。人们模仿这些虚假空洞的人物形象去改造自己,让自己成为影像所夹带的那些与性别相关的知识与观念的寄主。
 “无题电影剧照”系列之一
“无题电影剧照”系列之一在《观看之道》一书中,约翰·伯格指出:“生而为女性,命中注定在分配给她的有限空间内,身不由己地领受男性的照料。女性以其机敏灵巧,生活在这样有限的空间之中和监护底下,结果培养了她们的社会气质。女性将自己一分为二,作为换取这份气质的代价。女人必须不断地注视自己,几乎无时不与自己的个人形象连在一起。”内在于女性身上的 “观察者”(surveyor)与“被观察者”(surveyed)这两种既联系又完全不同的因素便不断地塑造女性身份。“结果,女性在男性面前的形象,决定了她所受的待遇。为了多少控制这一过程, 女性必须生来具有这种控制能力, 并使它深入内心。女性本身‘观察者的部分对待‘被观察者的部分,以向旁人表明,别人可以如何对待她。这一典型的自我对待,构成了她的风度。”这样的性别观念作为某种视线被移植到影像上之后,男性作为观察者、审视者、评判者的视线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导,而女性则往往变成了“物品或抽象概念的活动对象”。
一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有一些女性摄影家开始着手创作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以往刻板的女性形象的自拍像,运用反讽、挑衅、对峙等创作姿态,对男性主导的影像话语权发起挑战,她们拒绝以惯常的男性审视的视线来塑造自己,而是力求创造自己的影像语言,打破男性视线中早已坚如磐石的女性形象,让人们看到作为真实的人的女性形象,而非理所当然取悦男性的物化了的女性。
这批女性摄影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辛迪·雪曼(Cindy Sherman)。从一九七五年开始,辛迪·雪曼就开始有意识地拍摄一些自拍作品,她把自己化装成各种不同的角色。一九七七年大学毕业之后,她开始创作著名的“无题电影剧照”(Untitled Film Stills)系列。这个系列一共有七十多幅作品,她根据出版物上的一些老电影剧照,将自己装扮成剧照中的人物造型,凭借她一人之力,用影像构建出一系列看似脆弱可怜、茫然若失且总在期待中的女性群像。尽管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创作这些作品,“用那种形象是为了表达我对性的暧昧态度,和这类女性形象一起长大,而且电影里也总展示这些东西,我喜欢这些形象,然而你却应该做一名好女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对当时既有的那种性别观念的质疑与反思,多多少少都体现了女性主义意识在她身上的觉醒。
在“无题电影剧照”系列中,她把自己打扮成昔日明星、家庭主妇、街头流莺、深闺怨妇、官邸女佣、职业女性、搭便车女郎、图书馆员等形象进行自拍。原本在电影中被具体叙事语境塑造成男性欲望的客体,经由辛迪·雪曼的镜头突然从束缚人物角色的语境中挣脱出来,以控制男性眼光的主体形象主动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样的反转让这些人物形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将观众的视线重新抛回观众自身,从而阻断了观众按照自身习惯认知来消费这些人物的欲望,通过对这些令男性神往的女性形象的集合,来揭示泛滥成灾的大众传媒烙刻在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庸俗品位与认知,也使人联想到传媒所遮蔽的那个复杂的现代社会。可以说,这些作品在现实层面上也为人们瓦解既有的那种刻板性别观念提供了一个入口,激发了人们的性别意识,让人探讨并反思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
 《女人及其他视觉》中的摄影作品
《女人及其他视觉》中的摄影作品另一位摄影家朱迪·戴特(Judy Dater),与她的丈夫杰克·维尔伯特(Jack Welpott)合作,系統地拍摄了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形象,并于一九七五年出版了摄影集《女人及其他视觉》(Women and other Visions)。她将拍摄对象放置在日常生活的私密环境中进行拍摄。其中家具、墙纸、绘画挂件、装饰品、床单和衣服等材料全都是由拍摄对象自己进行选择、布置、摆设和装点的。朱迪·戴特用大画幅相机将这个场景里的细节全都事无巨细地拍摄下来,拍摄对象往往处于画面正中央,她们或身着便服,或一丝不挂地展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凝眸直视着照相机,而她们的视线也直接穿透相机投注在观看照片的每一个人身上。
在当时那个时代,摄影对于人体的表现总是遵循着某种既定的、强加于个体身上的某种性别气质,如男性人体就必须是强悍健壮的、符合男性气概的形象,而女性人体则理应是某种理想美的体现,必须是丰满柔润、曲线完美的理想化的、抽象化的女性形象。然而朱迪·戴特却丝毫不顾这些既定的气质,而是将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普通的状态纳入镜头之中。在她的作品中,那些女性或欢乐或悲伤,或彷徨不安或气定神闲,她们的皮肤曲线也都不加以修饰,保持着该有的皱纹与松弛。朱迪·戴特的自拍像更是对那种典型的、社会期待的女性形象的嘲讽与奚落。这些作品非常直观地表现了人内心的孤独与忧郁,以及人的身体在时间摧残下所留下的痕迹。这些以严厉的视线审视人的自然状态的作品,展现在世人面前,无疑就是一道刺眼的、撕破人的幻想与谎言的亮光,让人们不得不揭开蒙蔽在自己意识之中的虚伪的性别气质,对社会上宣传、塑造的那种性别形象与性别观念提出质疑。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西方摄影界出现了大量关注讨论性别及社会性别问题的摄影家,如朱迪思·戈登、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卡塔琳娜·西维尔丁、苏珊·希拉、霍·斯彭斯、南·戈尔丁等。他们或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形象去挑战人们心目中“理应如此”的刻板印象,或直面身体的不完美、生命的脆弱,或挑战歧视性视线,展示各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处境,让人们摆脱既定的性别认知局限,并且通过他们自身的人生和语言,来实践、修正这个世界对于“标准”“价值”“人”的定义。
二
亚洲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以摄影的方式对“女性性”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摄影家,如日本的石内都、韩国的朴英淑等。
 长岛有里枝
长岛有里枝一九九一年,在策展人笠原美智子的策划下,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举办了日本第一个探讨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问题的摄影展“女性的自拍照”。该展览不仅在日本摄影界也在日本社会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该展览以及笠原美智子后续在社会性别问题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日本女性以摄影的方式进行性别问题的探索。
一九九三年,年仅十九岁的长岛有里枝凭借拍摄家庭所有成员裸照的《家庭肖像》一举登上摄影舞台,在美术公募展“Tokyo Urbanart#2”上获得PARCO大奖。当时,评委之一的荒木经惟对她获奖的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与她同时期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还有HIROMIX(利川裕美)与蜷川实花等人。她们也都发表过自己的裸体自拍作品。在她们的影响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摄影家创作出绚丽多彩且挑战人们既有观念的摄影作品。
一九九五年,从武藏野美术大学毕业的长岛有里枝连续出版发行了两本摄影集YURIE NAGASHIMA(风雅书房,1995)与empty white room(Little More,1995);同年夏天,又与美国摄影家凯瑟琳·奥比(Catherine Opie)一起举办了双人展“家族 共同体”。在长岛有里枝的这些作品中,家庭中的成员是平等地赤裸相对的,而她的自拍照则表现完全悖于人们既定印象中的那种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以挑衅、邪恶、戏谑、叛逆的各种坏女孩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她的作品经由当时日本大众媒体的转化,被歪曲为女孩子秘而不宣的私密生活照,遭到严重的消费,但这样的作品依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冲击,激发了大量女性以摄影的方式进行创作,为日本摄影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在这之后,摄影学校里女生数量急剧上升,甚至超过了男生数量。一些杂志媒体也紧跟其后,纷纷出版发行面向女性的摄影类杂志。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的女性摄影家数量大增,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成为日本摄影的重要力量。
在这些先行者的带动下,日本摄影家也越来越关注社会性别问题。二○○○年之后,日本摄影中与社会性别相关的摄影作品逐渐呈多元化现象。摄影家们深入探讨因性别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泽田知子将自己打扮成各种不同性格、不同职业的人物形象,利用自动证件照拍摄机等摄影手段,以自身为客体,从不同角度解构当代社会中人们在性别、职业、身份等方面的固定思维,探索人的内在与外在之间的距离与联系。斋部香从二○○○年开始便通过网络征集女性模特,进行深度采访,探寻拍摄对象最真实的一面,并与模特一起以表演的方式展示她们内心想要表现的真实状态,最终以照片的方式呈现。她希望用这样的创作打破社会强加在个体身上的各种框架与标准。在《充气娃娃会梦见胎儿吗?》中,菅实花将充气娃娃做成孕妇的样子进行拍摄,并以真人大小的尺寸加以展示,激发人们对女性所具有的“母亲”这种身份以及“生育”功能的各种想象与思考,并在某种未来语境中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世界的影响。
三
在中国,摄影领域中与社会性别相关主题的作品则是在晚近这十余年里才出现的。尤其是二○一二年左右开始,许多年轻的女性摄影家开始通过自身的人生和语言来进行社会实践,利用摄影创作,积极探讨社会性别,思考性别平等,反抗性骚扰与性暴力等社会问题。她们大胆地用影像来刻画并表现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例外状态,并勇敢地促使人们就性别问题以及由性别观念导致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
 郭盈光《顺从的幸福》摄影作品之一
郭盈光《顺从的幸福》摄影作品之一女孩们美好易损的青春期、每个女孩身上的独特性以及女性身上的某种共通理念是罗洋十余年来不变的拍摄主题。从二○○七年开始她捕捉拍摄自己身边的朋友、陌生人,用她敏锐的感性去发现每个人身上与众不同的特性。这些女孩在她的镜头下完全放下了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精神负担,显露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她们直视着镜头外的观众,或心思忧郁,或无所畏惧,当这些照片被罗列在一起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共性便脱颖而出,那是一种女性特有的独立精神。在这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场面里,这些女孩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维度,倘若我们抱持着以往习得的那些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那么我们在这些女孩肖像中可能会遭遇难以想象的挑衅,倘若我们仍然隔着影像顽固地与她们对峙,那么我们的心灵可能会不断地受到冲击。而且,这些女孩的肖像一旦被注入意识之中,我们就很难将其忘却,她们将会在之后的日子里不断地从记忆中跳出来,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女性的强大。这些作品也与罗洋自己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她自己的话说:“摄影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任何的生活体验、感受,我都会通过影像表达出来,并通过拍摄,更了解人、了解生活、了解世界。”换言之,这些影像同样也是投向她自己内心世界的真挚视线,在揭露和确认自己的同时,也促使欣赏者不得不反省自己和社会。
 廖逸君《实验性关系》摄影作品之一
廖逸君《实验性关系》摄影作品之一郭盈光在三十岁那一年辞去摄影记者的工作去伦敦艺术学院学习,也是因为这样一个转变,让她深切体会到年龄对女性的“重要性”,也让她因此感到焦虑。她主动地将自己推到了新旧婚姻观冲突的最前线,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相亲公园—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举着一份自己写的相亲广告在那里站了很多天,以这种“给自己征婚”的行为艺术来了解中国式安排婚姻的脆弱与无奈,并希望通过作品引发人们对于女性价值认知的思考,鼓励人们用勇气和行动去主动争取一种“不顺从的幸福”。在这个作品中,郭盈光用照片事无巨细地还原出那个“婚姻人才市场”的现场状况,并以第一人称视角拍摄下人们对她的评价与讨论,以视频的方式展示,当每个观众经由照片进入到这个“市场”内部,暴露在她曾经遭遇过的那些视线、言语和动作下的时候,估计都不得不被这种婚姻观念的荒诞性震撼。作品中那井然有序的相亲现场以及那些振振有词、明目张胆的歧视,如实地诉说着传统婚姻观念对人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禁锢与压抑。因此观看者只要把她建构的那个残酷场面同现实稍微加以比照,便不難对自己置身于同一时代的压力与扭曲产生对抗的欲望。
我们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往往也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尤其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温情脉脉、情投意合、貌似平等的表象之下,往往隐藏着秘而不宣、不为人知的权力失衡。廖逸君的作品《实验性关系》探讨的就是这种与每个人贴合得最紧密的权力关系。她说:“作为女性,我曾经以为我只能爱上一个比我更年长和更成熟的人、一个保护者、一个良师益友,直到我遇见了我现在的男友莫若。因为他比我小五岁,我理所当然的情侣关系彻底颠倒了。我变成了那个有更多权威和影响力的人。我的一位男性友人问我怎么可以用和他选女友一样的标准来挑选男友,我想:‘啊!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呢?!”于是,在这个作品中,廖逸君的男友仿佛处于权力关系中的绝对弱势,被她任意摆弄,时而被包裹成一颗寿司,时而被挂在晾衣竿上晾晒。她常常把自己刻画成一个主导的角色,而她的男友处于服从的地位。而摄影在这个关系中,仿佛就是权力的象征,为她留下了掌握权力的证据。不过,她绝非要鼓吹用一种女性的权力去颠覆、取代男性的权力,而是要通过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的方式为观众提供一个理解权力关系失衡的可怖状态,让人们明白不论是哪一方占有强势权力,权力关系的失衡都是对人性的伤害。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不再强迫自己扮演男性视角中的那个楚楚可人的女性角色,在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很多女性已能够有效地实施独立自主的权利。她们必须独立面对自己的欲望,掌握自己的生活,解决自己内外交杂的矛盾与困惑。在钱儒雅的《食肉植物》系列中,男性的裸体承担了多重象征的功能,既象征了一种基于欲望的性吸引,也象征了人潜意识中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他者,甚至也象征着双重性别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将个人的性别意识引到了一个令人迷恋的更为复杂的境地。在《我们》这个系列中,她以自拍的方式努力把握潜伏在自己身上的两股截然矛盾的力量,“自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伙伴……我经常和自己争吵,有时候她很害羞安静,但是另一个暴躁易怒,有的敏感神经质,有的麻木而冷血,有一个是胆小没用的,还有一个胆大但是不计后果……自我肖像总是一个复杂的命题,该揭露多少呢,一张影像的真实程度又有多少?你戴了什么样的面具?”这样的疑问,她也借由自己的身体表演与影像抛投给了观众,当这个问题与她自己的自然性别相重合的时候,则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我们对女性的想象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我们对自己的想象又有多少真实性?
在作品《向着身体的解放》中,甘莹莹将自己的身体与行为抽象化地进行表现,展示出两种不同的女性力量,一种是对抗的、碰撞的、迸发式的力量,一种则是柔和的、暧昧的、抒情式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某种性政治上的平衡感,抽象化的影像让她的身体与行为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任何人都能代入其中去思考性政治上的正义。她表示:“对我来说,从根本上打破这种被统治的、被束缚的、被剥夺的地位,只有解放了身体和这些加诸灵魂上的束缚,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
在这些女性摄影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形式截然不同、内容异常丰富的创作实践。在她们的创作实践中,摄影不再是单纯的记录,也是一种瓦解各种意义的手段,是批评与重审社会价值标准的渠道,是重建与表现个体认知与观念的媒介。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体验以及源自各种信息的间接经验都构成了她们创作的基础。她们从个体的记忆经验出发进行自己的社会化尝试,再将这一过程重新转换成视觉、文化以及社会上可以共情共鸣的媒介物。
 甘莹莹《向着身体的解放》摄影作品之一
甘莹莹《向着身体的解放》摄影作品之一本文无意于讲述与社会性别相关的摄影史,只是希望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一些摄影家们的创作来理解人们如何运用摄影的媒介来探索与性别相关的问题。
摄影与语言文字不同,无法直接、精确地描述人的思想观念,但却能够通过影像建构具体的情境,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陌生化,从而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感官上,激发人们运用自己的经验与思想对全新的感官进行分析思考,最终形成新的认识。因此,这些摄影家在探讨性别问题的时候,往往需要将创作直接作用在自己的身上,她们不逃避社会中相关的现实问题,深刻地挖掘自身的经验与感性,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对自我及个体身份形成有效的超越,最终将她们的经验、感受及思想真诚地表现出来。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用作品述说着被我们选择性忽视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些问题,诱发人们对习以为常的性别观念与认知进行批判与反思。我们也必须以诚恳的心态去倾听、理解她们的述说,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