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金山钱氏对江南文化做了两项特殊贡献,值得今人铭记。第一项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冬天,钱熙祚(1801-1844)出资,率领弟弟熙泰、同邑顾观光、南汇张文虎、平湖钱熙咸、嘉兴李长龄及海宁李善兰,“寓西湖,就文渊阁校书”(白蕉《〈钱鲈香先生笔记〉序》,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他们三度去杭州四库全书文澜阁,抄书四百三十二卷,校书八十多种。回到金山后,顾观光、张文虎等人把录得的钦本与江南藏家诸本详细校勘,定为善本。第二项是在道光十七年(1837)的春天,朝廷强令开采位于金山县的秦望山、查山,石块用于修筑海塘。金山,县以山名,却本来少山。两座不足十丈之高的山丘位于钱氏阡陌之中,一旦开采,百姓坟茔毁去不说,十里山水颓然,一方文脉残断,局势万分危殆。当此之时,富户钱熙祚挺身而出,义捐运费,说动了官府改在吴兴县的大山里采石,保住了这两座孤山,令金山地区至今仍然有山,事迹遂传诵为“钱氏守山”,为乡人所撰的《张堰镇志》记载。

道光二十四年(1844),钱熙祚资助的这一丛书雕版刻成,開门刷印,求购者中有远自朝鲜赶来的。为此,钱氏专门建造了一座四层楼的藏书阁,储版藏书。书楼和丛书均以“守山”之训作命名,这就是清末读书人都很熟悉的金山“守山阁”和《守山阁丛书》。《守山阁丛书》当时就很成功,书楼和丛书命名得更是不同凡响。“守山”,人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家国天下情怀涵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也隐然其中。然而,还是有一些钱氏命名“守山”时不知道的重大意义,越到后来越显现出来,今人也就看得更加清楚。
首先,《守山阁丛书》的刻成,标志着清代中叶以后松江府及上海地区作为藏书、刻书中心的地位的上升。江南是传统的刻书、藏书中心,有钱就刻书,诗书以传家是古训,书界有“苏本”“浙本”“建本”之誉。从狭义的江南来说,苏、松、常、杭、嘉、湖,尤以苏州府的藏书家最为著名。明代万历年间,常熟毛晋的“汲古阁”驰名江南;清代顺治年间,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异军突起;乾隆年间,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建造完成;到嘉庆年间,吴县黄丕烈的“士礼居”蔚为大观。然而,文运流转,时至道光年间,经过又一次的财富积累,地处海辄的松江府文风强势崛起,出现了一批大藏书家、藏书楼。嘉道之际著名文人龚自珍(1792-1841)因父亲担任苏松太道道台,青年时期在上海住了十二年,两个儿子还都入籍上海。以龚自珍读书、交游之广博,他在内阁、翰林院都不曾寓目的版本,回上海时却在李筠嘉(1766-1828)的“慈云楼”“古香阁”里觅到了,因而对本地的藏书风气刮目相看。“大江以南,士大夫风气渊雅……上海李氏乃藏书至四千七百种,论议胪注至三十九万言。承平之风烈,与鄞范氏、歙汪氏、杭州吴氏、鲍氏,相辉映于八九十年之间。”(龚自珍《〈上海李氏藏书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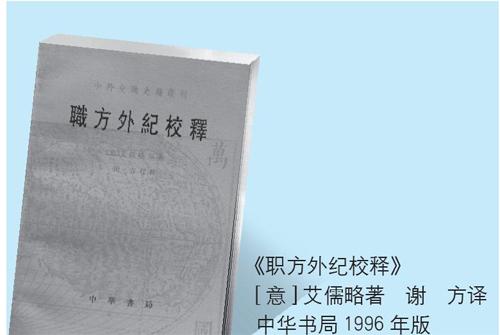
继万历年间因棉布生产的经济繁荣之后,康熙年间开埠,雍正年间苏松太道移治,沿海地区的南北货贸易令上海地区又一次财富集聚。富而好礼,读书、藏书、刻书的风气渐渐兴盛,已有领先江南的势头。龚自珍说上海李氏的“慈云楼”可以与宁波范氏“天一阁”相称,并非虚语。金山钱氏“守山阁”之外,上海十六铺大沙船商人郁松年荟集的“宜稼堂”五十万卷藏书更是惊人,晚清时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丰顺丁日昌的“持静斋”,甚至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无不取自“宜稼堂”。时至晚清,上海地区的图书收藏、刊刻、印刷、发行,古今并行,中外杂糅,福州路的图书事业已然引领了江南和全国。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选一个事件来象征“上海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心地位的开端,鸦片战争前就从事校勘,战争甫结束刊刻、发行的《守山阁丛书》庶几可以应之。《守山阁丛书》之外,金山钱氏还编辑了《艺海珠尘》《小万卷楼丛书》和《指海》。这一系列丛书的刻成,标志着上海地区的刻书、藏书事业的强势崛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鸦片战争之前金山及松江府各处藏书家的崛起,为清末上海地区新式图书事业的繁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他们正好居于上海图书事业从江南边缘到近代中心的中间时期,具有新旧时代过渡的蕴意。
其次,《守山阁丛书》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套延续“江南文化”学术传统的著作,其蕴含就体现在书目中。我们知道,钱熙祚编辑《守山阁丛书》的动因是他购得了常熟刻书家张海鹏(1755-1816)“传望楼”的《墨海金壶》。该书楼在嘉庆年间过火之后,难以为继,残版散出,被金山钱氏收购。为了补齐和校勘这些残版,钱熙祚起意去杭州西湖边的文澜阁抄书。按张之洞、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提示,一九二一年上海博古斋影印《墨海金壶》一百一十五种(原为117种),大部分是翻刻宋、元版本的经史注疏。在江南考据学风气中,该丛书采入了几种“乾嘉之学”的经史考证作品,如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古韵标准》。眼光独到的是,《墨海金壶》收录了西洋教师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作品《职方外纪》。收入这一本西学作品,异乎寻常!表明江南的一般读书人确实是见识宏阔,并不拒斥泰西学说!现在看起来,《守山阁丛书》中的经史考证、诸子异说的版本之优良都是其次的,西学才是它的价值核心。当时“海内好学之士皆欲得其书,朝鲜使人至以重价来购”(张文虎《〈守山阁剩稿〉序》,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原因在此。阮元(1764-1849)是嘉道年间的江南学术领袖,曾在他主编的《畴人传》中收录了牛顿(奈端)传,推崇西方自然科学。他在《守山阁丛书》序中表扬说:“其书采择校雠之精,迥出诸丛书之上。”阮元亦应该是特别赏识了这一点,才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

钱熙祚和他邀请的这一批编书、校书、刻书的学问人,眼光独到,匠心独运,收录了许多难度极高的西学著作。在十七世纪初的明末就进入江南的西学,被称为“利徐之学”,即由利玛窦、徐光启等中西人物合作奠定,主要是指其中的欧洲天文、历算、数学、医学、哲学等自然学说。我们知道,《职方外纪》是杭州李之藻编辑《天学初函》中的一种。正是沿着《墨海金壶》的线索,《守山阁丛书》从“四库全书”的《天学初函》中又抄出了《简平仪说》(熊三拔、徐光启)、《浑盖通宪图说》(李之藻)、《圜容较义》(利玛窦、李之藻)三种。其他西学著作,如《晓庵新法》(王锡阐)、《五星行度解》(王锡阐)、《数学》(江永)、《推步法解》(江永)、《天步真原》(穆尼阁、薛凤祚)、《远西奇器图说录最》(邓玉函、王徵)、《新制诸器图说》(王徵)等七种,加上《职方外纪》,本丛书一共收录了西学著作十一种。又据《书目答问补正》提示,一八八九年上海鸿文书局、一九二一年上海博古斋影印《守山阁丛书》一百一十种,西学占了十分之一。继徐光启万历年间引进之后,西学的种子又一次在上海地区复苏,再度与传统的儒家经学角力。
我们注意到,《守山阁丛书》的刊刻始于一八三五年,那時候还没有鸦片战争,金山学者已经在复兴西学。一般学者都喜欢说鸦片战争以后,清代士人才开始“睁眼看世界”。也有说因为粤籍或在粤学者更加关注“夷情”,所以在西学研读和传播上得风气之先。然而,我们看到金山的这个知识群体,他们并不是受了坚船利炮的刺激才研读西学的,而是在此之前就一直自习天文、历算、测量、力学。确实,广东人对鸦片战争反应强烈,粤商潘仕诚刻《海山仙馆丛书》收录了《几何原本》(利玛窦、徐光启)、《测量法义》(利玛窦、徐光启)、《测量异同》(徐光启)、《勾股义》(徐光启)、《圜容较义》(李之藻)、《同文算指》(李之藻)、《火攻挈要》(汤若望)、《全体新论》(合信)、《翼梅》(江永)。但是,《海山仙馆丛书》中收录的西学著作,刊刻时间晚至一八四九年(咸丰己酉);《守山阁丛书》则是筚路蓝缕,从一八三五年(道光乙未)就开始了。研究中国的学者有说“冲击-反应论”,强调鸦片战争的震慑作用;另有主张中国内部的思想文化变化,称为“内在理路”。如果说《海山仙馆丛书》的解释模式适用于“冲击-反应论”的话,那我们理解《守山阁丛书》则可以顺着江南文化已有的进步线索,按照思想上的“内在理路”,看他们如何遵循着一种学问自觉,走上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
《守山阁丛书》刻成的第三项意义还在于,它为咸同之际开始的“洋务”和“变法”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西学人才。在“守山阁”校书、刻书的人物中,钱熙祚积劳成疾,过早去世。丛书刻成之日,他在北京等候政府表彰,猝然去世。钱熙祚去世后,他的哥哥熙辅,弟弟熙泰,堂弟熙经,儿子培让、培杰,还有姻亲韩应陛,继续出资出力,聘请更多学者加入选书、校书、刻书。这一系列丛书的刊刻,令金山知识群体人物走出江南,享誉全国。精通数学、天文、地理和医学的学问大家,金山钱圩人顾观光(1799-1862)是刻书的实际主持人。钱熙祚去世之后,他继续守山阁图书事业。海宁秀才,继承“乾嘉之学”数学成就的李善兰(1811-1882),被邀请了一起校读数学书。顾观光为他的《四元解》(1846)作序,帮他刻印《麟德历解》(1848)。这些数学、天文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直接传承的是清代“乾嘉之学”;再追溯的话,他继承的就是明末的“利徐之学”。一八五二年,李善兰被邀请到上海英租界墨海书馆,和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1856),那就和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直接贯通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和后九卷的翻译,都和上海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可贵的延续性案例并非偶然。从明末徐光启,到清末李善兰,在众多的传承人中间,有王锡阐、梅文鼎、江永、钱大昕、李锐等人,也有“守山阁”学者这一群体。这一学者群体,都是过去所谓的“吴派”“皖派”,以及他们的余脉。百多年中,“利徐之学”“乾嘉之学”一直在江南徘徊,却都离上海不远。顾观光、李善兰,是清末最早精通西学的江南学者,他们的活动地就在上海。值得再一次强调的是,他们的老师并不是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而是万历年间已经到达江南的耶稣会士。
校书、刻书、读书,沉潜往复,守先待后,最后才是自己立说著书,这是古人研究学问的最佳方法。因为《守山阁丛书》的刊刻,聚集起来的专业学者不止一个人,而是一整个群体。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们是江南和全国最早,也是唯一精通近代数学、历算、天文、地理的人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特殊的知识群体:全国士子都还在皓首穷经,苦读“文科”(四书五经)的时候,江南学子已经另辟蹊径,迎难而上,研习起“理科”(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即清末所谓“格致之学”)。继上海徐光启、仁和李之藻之后,江南学者在清代道咸之际再一次对西学孜孜以求,研读、翻译和著述“利徐之学”。我们至今还是不太明白,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等学问换不来秀才、举人、进士功名的科举时代,是什么样的力量激发了金山和江南士人的学术热情,去学习“格致之学”?大家知道,“格致之学”(自然科学)能够拿出来到社会上去“经世致用”,那是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推动的洋务运动以后了。在西学筚路蓝缕、困顿寒酸的嘉道年间,他们自带盘缠,自备枣梨,耗尽家产,并没有实用目的,为的只是守住前人的学问,刻下能被后代认可的“不刊之说”。在没有找到更加确切的解释之前,我们只能说这些不带有功利目的的奉献行为,是来自一种“纯学术”的冲动,是受到了自然之理的感召。
“同光中兴”中的洋务运动,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一度向西学开放。伦敦会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以及地方官办的苏州书局、杭州书局、金陵书局刊刻了不少“天文、历算、推步、测量”和“声、光、化、电、重学”著作。这些活动中隐隐约约地都有《守山阁丛书》知识群体的身影。上海地区的学者又一次得风气之先,因而在近代科学、文化、出版和教育事业中有大的施展和发挥。顾观光在一八六二年去世,这一年十月,清朝在北京开设了“京师同文馆”(外语学院)。一八六六年,同文馆增设“算学馆”(数学系)。如果顾观光还在世的话,同文馆总教习(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1827-1916)或许就会选这位精通算学、几何、天文、历算和重学的金山学者来担任教习。李善兰赶上了时代,经曾国藩幕府推荐,丁韪良聘请他担任算学馆教习(系主任),是同文馆里唯一的华人教习。
另一位有幸进入清朝“同光中兴”事业的学者,是南汇县周浦人张文虎(1808-1885)。张文虎也是被曾国藩罗致到幕府的,作为著名幕僚,受到洋务大员的推荐而显露头角。清末政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真正有能力的干才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尤其在直隸,在两江。张文虎、李善兰这一群专业人士都有实际才干,都不是一般用来装点门面的摇头晃脑儒生。曾国藩、李鸿章把他们招至幕中,继续校书、刻书、教书,主持学术和学校,对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起了重要作用。清朝同光之际开始的“变法”,既不是民间的诉求,也不是中央的号召,而是出于“中兴”大员在内忧外患逼迫之下的不得已、不自觉的地方治理行为。因此,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才是“变法”的中枢,而支撑幕府的人才,则是像张文虎、李善兰等来自基层的地方学者。按张文虎《舒艺室诗存》中记录的情况看,他在同治二年(1863)就已经进入曾国藩在安庆的幕府,并且在文官中扮演士林领袖的角色。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文人们以苏东坡生日为名在周缦云家里雅集,张文虎为主盟,出席者有海宁李善兰、瑞安孙衣言、阳湖方元徵、归安杨见山,以及王孝凤、叶云岩、陈小舫、刘开生、李小石等(参见《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8页)。张文虎凭着过硬的考据和广博的见识,一八八二年被江苏学政黄体芳(1832-1899)聘请为江阴南菁书院首任山长。南菁书院取朱熹“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之意,是清末“变法”以后第一座开设数学、天文、历算课程的地方书院。张文虎和李善兰,一南一北,掌握了地方和中央新派学问的枢纽,可见《守山阁丛书》知识群体的领袖作用。
当代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大多是通过张文虎、李善兰的治学事迹,或者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才依稀知道一些《守山阁丛书》以及金山钱氏的事迹。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门比较粗疏的学问,不需要查证很多,就可以下很重大的结论。比如我们尽可以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不顾徐光启在此前的两百多年已经翻译了《几何原本》;我们也常常说近代数学只是从京师同文馆算学馆开始的,而不顾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的数学学问其实从“利徐之学”“乾嘉之学”而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评论说《几何原本》和“乾嘉之学”中的数学知识非常有限,不成体系,落后于时代。但是当了解了《守山阁丛书》以及这个知识群体的事迹,我们至少会同情地理解这批知识人的“守山”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地方上的知识人士是如何用搜书、校书、刻书的方式,传承着一种殊关重要的学问,守先待后,发扬光大,确实是一种了不起的科学精神。
二○一九年,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有一个关于江南文化在县、镇、乡级地方转型的研究计划。为了搞清楚《守山阁丛书》的刊刻情况,我和中心特约研究员项宇博士、马相伯研究会会长马天若于二月十一日一起访问了金山区张堰镇。接待我们的是老朋友,原金山区教育局局长、上海顾野王文化研究院院长蒋志明先生。作为数学教授,蒋院长非常崇敬徐光启,曾在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专程邀请我到金山,向师生们介绍明末的数学翻译成就。作为金山亭林镇人,蒋院长对《守山阁丛书》中的人物、环境和刊刻有直达基层的了解,远超我们从书本上得来的印象。经他热情接待,我们踏勘了秦山,面对这座颓然的孤山,我们对金山人的“守山”精神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冠病毒疫情稍缓,我和项宇博士又一次驱车前往张堰镇,这一次同行的是金山钱氏后人钱基敏女士,她多年来奔波于上海市区和金山及江、浙各地,孜孜不倦地编写金山钱氏家族史。地方人士对本土文化的坚守精神,远超我们的想象,让我们感受到这才是一种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这一次陪同钱女士的访问,金山区文旅局陆佰君副局长正式接待我们。陆副局长除了支持和鼓励钱基敏女士的家族史研究之外,还郑重提出要与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等机构合作,做好“守山阁文化”的发掘、研究和推广工作,令大家都很兴奋。我们都说“守山阁”这个名字起得好,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要加以介绍和推广。蒋志明院长的概括更加好,他说金山人的“守山精神”,就是要守住三座大山。一守秦山,那是自然之山,鱼米之乡的环境不能毁去;二守书山,那是文化之山,藏书读书,刻苦求实的风气不能中断;三守人山,那是人才之山,金山人在“吴根越角”地带创建出来的繁盛文脉要一代代地传承下去。金山人的“守山精神”,何尝不是江南文化的精神,上海文化的精神?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每思及此,看到这一群群、一代代地方人士的坚守,觉得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还有希望。以此小文,代为钱基敏女士《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书序,并对金山人的“守山精神”再一次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