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九盈先生,是入学后第一个学期教我们古代汉语的老师。那还是一九七八年春夏的事。由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为汉语、文学与文献三大块,我学的是文学,而何老师是汉语教研室的,所以自从上完这门课,就再也没有与何老师有过任何的交集。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读到一篇有关何老师在澳门某大学讲学的报道,报上还刊登了他的一帧照片。那时我还有剪报的习惯,特别是刚到北美,消息闭塞,也没有互联网、微信这样便利的通信工具,在报纸上看到来自母校的消息,又是教过自己的老师,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于是就把这篇报道剪了下来,收在自己的剪报资料箱里。后来搬过很多次家,再后来互联网普及了,报纸很少有人看了,现在人人都用微信,我这半箱子的剪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丢在了哪里。说这些,只是想说我与何老师的交往真的十分有限,但当年何老师的敬业,他对教学的一丝不苟、对学生的热情帮助,至今难忘。
一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系里给我们安排了三门专业课:中国古代文学史、语法修辞和古代汉语。这三门课的分量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就看怎么学。我是从偏远的西北地区考入北大的。坦诚地说,与从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特别是与老三届同学相比,我的底子薄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上大学前,我不但读过的书少,就连见过的书、听说过的书也少。为了尽快适应大学生活,那几年我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昼夜不停地转,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除了专业课指定的书目外,我还给自己增加了许多额外的学习任务。像《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庄子》《史记》,都是在第一学期内读完的。当时,系里把古代汉语课安排在第一学期,不但所学内容与另一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先秦两汉部分相辅相成,而且在教学侧重点与分析作品的角度上又互为补充,让我获益尤多,在我看来,那实在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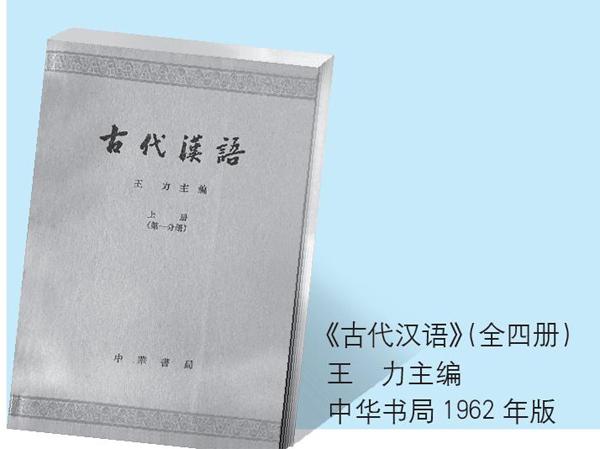
相比漢语专业大师级的前辈学者如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老先生,教我们古代汉语的何九盈老师跟后来教我们“说文解字”的曹先擢老师,都是汉语专业中的小字辈。何老师一九五六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一九六一年毕业留校任教。给我们上课那会儿,也就四十多岁,相当年轻。课上课下精力充沛,连走起路来都透着一股精神劲儿。
古代汉语课开在一个大阶梯教室,几个班合在一起上,人很多。每次上课,何老师都准备得特别充分。哪些语法现象、词语用法、字义词性需要板书,那些例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哪几个汉字,哪些内容需要重点讲解,他都掌握得恰到好处。相对于文学,语言要枯燥得多,古代汉语就更是如此。要想教得叫座,老师就得花更多的功夫。何九盈老师全是凭着自己扎实的功底,一肚子的学问,把那些“之乎者也矣焉哉”之类的东西讲得魅力无穷、趣味盎然,他的课颇受同学们的欢迎。
在学这门课之前,我很少琢磨虚词的作用与意义,只要不妨碍对古文本意的理解,对虚词,我的态度基本是忽略不计。但经过何老师的分析讲解,我才发现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虚词在不同语境下,通过不同的用法,同样起着不同的表意、表情作用。相对于数不胜数的实词,虚词的数量极为有限,可就是这么有限的虚词,却能真正传达出古文的神韵意趣来。难怪有人说古代汉语中的实词如同是骨骼血肉,虚词却是神情声气。例如人人都熟悉的那段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而”“之”“亦”“乎”“自”等虚词用了十几个,差不多是总字数的一半,但如果没有这些虚词的连接,这几句话简直就无法读下去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虚词的重要。后来,我写《庄子散文的语言艺术》一文时,曾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详细阐释《庄子》一书中虚词的用法。这个想法,就是萌生于何九盈老师的古代汉语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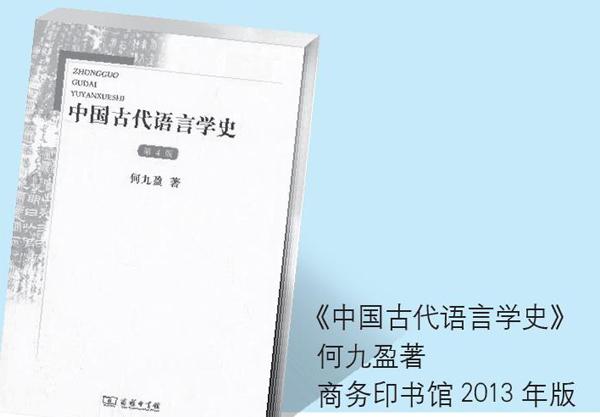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老师讲课,都很重视“史”。每个文学现象、每位重要作家的师承关系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来龙去脉都梳理得清晰明了。何老师讲授古代汉语也深谙此道。当然,何老师讲的不是古代汉语史,此处所说的“史”指的是古代汉语词语的演变、发展史。例如,一个词最早出现在哪个时代的哪篇文章或诗歌中,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这个词的词义、词性发生了哪些变化,随着语言的发展又有了哪些新的含义,等等。我记得讲“之”字的时候,何老师引出了古籍中许多“之”字的例子,条分缕析,从“之”字的出现,它的本义“之,出也。象艸过屮,枝茎益大有所之”(《说文》),到“之”字作为动词“自伯之东”(《诗·卫风·伯兮》)、代词“宣王说之”(《韩非子·内储说上》)、助词“口之于味,有同耆也”(《孟子》)等各种不同的用法,光是一个“之”字就讲了差不多整整一节课。听课的时候,很佩服何老师年纪不大,学问却蛮深。
由于我高度近视,不管什么课,总是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前排。这样,不但老师的板书可以看得更清楚,听起课来也更专注,少受外界的干扰。尽管我一向坐在前边,可我并不擅长交际,很少走到讲台前跟老师交流。大约是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下课我正准备收拾书包离开,何老师突然走到我面前,问过我的姓名、班级之后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课堂笔记吗?我很疑惑地把自己的笔记本递了过去。何老师翻开看了几页后又问,我可不可以借你的笔记看一下,下次上课的时候再还给你?我当然点头同意了。在我的一生中,任课老师要求看学生的课堂笔记,并且还要带回家看,这是头一遭,也是唯一的一次。我虽然答应了,也把笔记本交给了老师,心里却又困惑又好奇,不明白何老师究竟要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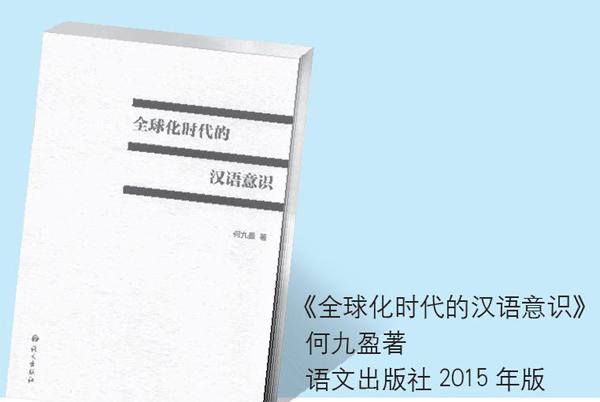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又到了上古代汉语课的时间。我急匆匆走进教室,还未落座,便看见我的课堂笔记本已经端端正正地放在了讲台上。再一抬头,何老师正招手示意我过去。何老师一边递给我笔记本,一边对我说,你的课堂笔记,记得很详细,也很认真。古代汉语跟其他课程相比,比较难,可是有意思,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领域。如果你对古代汉语有兴趣,想进一步钻研的话,我可以推荐几本书给你。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你的笔记本里有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最后,何老师还特意拍拍我的肩膀说,谢谢你这么认真地听课。
谢谢我认真听课?老师感谢学生?我太吃惊了!我印象中,当时中国人并没有常常说“谢谢”的习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还得以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宣传“五讲四美”,提倡大家使用“请”“谢谢”“不客气”之类的文明礼貌用语。然而,何老师居然谢谢我认真听讲,闹得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一向都应该是学生感谢老师的,哪儿听说过老师谢谢学生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拿了笔记本回到自己座位上的。不过,何老师的这一句“谢谢”,却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拿回笔记本,大致翻了几页,没发现什么,就写上了当天的日期,并在当天笔记之前标注“何九盈老师看过此前的笔记”,就照常上课了。当晚回到宿舍,就着宿舍昏黄的灯光,我更仔细地一页页翻看我的本子,发现在一些空白处留下了何老师工整的笔迹,有的是批注,有的是补缺,有的是纠谬。好像是“扁鹊过齐,齐桓公客之”那句,我把一個“客”字的使动用法记错了,何老师不但改正了我的误记,还补充了另外两个例句加以说明,并标明出处。此外,何老师还改了我笔记中的很多笔误、记错的例句,补上了一些由于当场来不及记而留出的空白或者需要核对查找的字。这可是将近一个学期记下的厚厚一本课堂笔记。上课时,因为我不想落下讲课内容,字写得很快,字迹也很潦草,有时还用自创的缩写符号,还有的字甚至后来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了,没想到何老师竟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地帮我全部改正并补上。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一位对学生这么认真精心的老师,肯花这么多时间校正一个普通学生的课堂笔记,更何况我与何老师并无任何其他私人交情。当时与我床连床、面对面的同屋苏牧兄听我一个劲地感叹,了解到其中原委之后,也禁不住连声赞叹何老师真是位少见的好老师。
二
除了古代汉语课,我们班同学与何老师另外一次交集是在系里一些老师主动为我们七七级学生开设的“小灶”课上。那也是我们入学后不久的事。

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几乎个个都是经历过一番过五关、斩六将的磨难才考到北大来的,因此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七七级(还有七八级)学生的强烈求知欲以及刻苦学习的精神,恐怕在中国高校史上也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我们的老师也刚刚蛰伏了十来年,好不容易才从干校、牛棚,或其他不相干的行业回到三尺讲台上,终于可以专心做学问、搞教学,迫不及待地要在学术、教学领域大显身手。总之,对学术、学问的共同渴望让师生两代人就这么碰撞在了一起。据我所知,当时的中文系,无论是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的老一辈名家学者,还是年富力强、独当一面的中年教师,都对七七级厚爱有加。就在我们刚刚入住三十二楼,还没搞清楚北大校园究竟有多大、文学专业骨干教师都姓甚名谁,甚至连班里同学都还没认全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张剑福老师就已经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跟同学们商讨需要组织些什么样的学术活动,安排哪些讲座,大家有什么希望要求之类的事了。此外,还有很多老师自发地到宿舍来看望大家,介绍文学专业各教研室的基本情况、各位老师的研究课题与学术专长,了解大家的学习兴趣、研究方向,等等。也有的同学为了与老师取得进一步的交流,索性直接上门。几乎所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造访都来者不拒。北大中文系师生间的这种互动互访,我不清楚是老北大一直就有的传统,还是新北大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师生关系。
刚入校时,中文系办公室不在五院,就在我们宿舍楼三十二楼的二层。系办公室旁有一间很大的房间,用作会议室。系里常常利用这个房间为新生举办各种活动。当时,校园内的学术气氛很浓,学生的思想也很活跃。几乎每星期,甚至每天,都有校系各级学生会、各个社团举办的各种名家讲座、座谈会、专题讨论会。这类消息一般都是通过“三角地”的布告栏传播的,那里各种颜色的海报每天都在不断地更新。系里也常常为我们开办各种各样的专题讲座。这些课程表之外的讲座,被大家戏称为是开“小灶”。我记得第一位请来给我们举办讲座的是吴组缃先生,最后一位便是何九盈老师了。
何九盈老师给我们开的是系列讲座“古代官制的演变”。中国古代官制与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皇权统治的超稳定性,有着直接的联系,是理解中国社会形态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课题。何老师先从秦始皇建立起的以皇帝为中心的三公九卿制讲起,引述了大量文献说明秦代官制的结构,并以翔实的考证说明每一官职的职权范围;然后介绍汉代官制的变化,特别是汉武帝如何进一步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起中朝制等。何老师的讲座涉及不少考证和资料的引用,从中可以看出他学识很渊博,思维缜密,推论也很严谨。通过这几次讲座,让同学们不但对秦汉两代的官制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开始对做学问有了更具体、更感性的认识。至少我自己就有一种被何老师引入学问之门的感觉。
何老师的课本来是一个系列,他计划从秦代一直讲下去。可是这门“小灶”课只上了两三次就突然被系里叫停了,之后也没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后来有小道消息说,其他年级的学生发现老师给七七级开“小灶”,很不满意,遂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说老师偏爱七七级,“偷偷开小灶”,并认为这样做对其他年级的同学很不公平。其实,何九盈老师的课并非秘密,老师也并不领取额外的讲课费,纯属自愿。而且三十二楼住着几百名学生,有东语系、西语系的,也有中文系各个专业、各个年级的,男生女生都有。很多课大家都一起上。办讲座的事也是公开的。听讲座的同学并不仅仅限于七七级。我就亲眼见过一些不是我们班、我们年级的同学也在听课。至少有一次坐我旁边的同学就是七六级汉语专业的。可能是因为以前没有老师给其他年级同学额外开课的先例,于是就被认为是偏爱七七级了。
由于有人提意见,何老师的课只讲到汉代就不得不中断。此后,系里再也没有组织过这种开“小灶”式的课了。对学生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好在后来老师与学生越来越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老师来学生宿舍与大家聊天,当然聊得最多的仍然是学问。
三
在大学期间,与何老师的交往很是有限。出国以后,干起了教中文的行当,才发现何老师教的古代汉语倒成了我在工作中直接获益最多的学问之一。
我在海外教中文,绝大多数学生的母语是英语或者法语。对于只需要用二十六个字母就可以完美地表达自己的人来说,汉语的方块字简直是天书,一个个汉字都像是由莫名其妙毫无规律可言的笔画组成的一串串密码。学汉字之难“难于上青天”,还真一点儿都不夸张。西方语言学家,把英语之外的所有语言按照母语是英语者的学习难易程度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与英语相近,比较容易学的,如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第二类与英语稍微远了些,相对难学一点儿,如德语、印尼语、马来语等。第三类则是与英语相距更远,自然也更难学的语言,如俄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越南语、希伯来语等。而汉语与韩语、日语还有阿拉伯语这四种语言被归入了最难学的语言类,也就是第四类。而且即便同属第四类,由于韩语与阿拉伯语属于表音文字—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发音规律,看到文字就可以读出来—相对容易学一些;属于表意文字的汉语,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实实在在是最难学的语言。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以英语或者法语为母语的。怎么教?我是学中文出身的。在背景五花八门的海外中文教师队伍中,我算是最科班出身的了,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自然被同事们当作了教汉语的“权威”。于是,当年读研究生时跟曹先擢老师学的“说文解字”,还有跟何九盈老师学的古代汉语就都派上了用场。凡是跟我学过中文的学生,汉字阅读能力都明显强过其他中文學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从曹老师、何老师那里学来了给学生分析每一个汉字的由来的本事,能讲出汉字中的故事,让学生理解每一个方块字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学出兴趣,自然也就没有了畏难情绪。
很可惜何老师只教了我们一门古代汉语课,外加两三次中国古代官制的讲座。此后,我再无缘向何老师请教了。直到最近才发现,何老师的研究范围涉及很多我现在非常感兴趣的领域,例如他的《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一书研究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历史、普通话的历史、汉语如何走向世界等;他的论文《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概括了“二十世纪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两大公案;还有他与人合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自著的《汉字文化学》,着重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这些都与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是很有用的参考书。我很希望有一天,还能再次见到何老师,再次面对面地向他请教。
时光流逝似水。从何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我也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迈入了花甲之年。何老师为我改正补白课堂笔记的事,或许他早已忘记,于我却是历久弥新。二○○八年,我在《一份抹不去的记忆》一文中记述过此事(收入《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年),只是不知何老师是否见过这篇文章。





